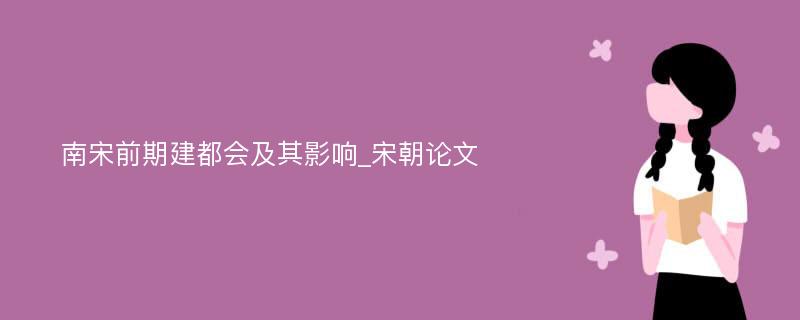
南宋初年的建都之議及其影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年论文,南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定都臨安,歷代史家評論對此基本持否定態度,但幾乎都未曾探究建都的具體經過。現代史學界對此問題的研究以陳樂素《南宋定都臨安的原因》一文爲代表。①此後,林正秋《南宋定都臨安原因初探》②、《杭州興起與南宋定都》③兩文注意到定都臨安的經濟因素,從“太湖流域的經濟關係”與“當日杭州在經濟上的地位”兩個方面說明了選擇臨安定都在經濟上的合理性。申小紅《試論南宋定都臨安》還試圖就宋人的審美情趣說明其文化合理性。④諸文對定都過程的考察不够全面,往往止于引述,甚少討論具體争論的背景及其用意,對建都之議的影響更未涉及。這都給本文留下了大量的討論空間。
建都之議是靖康淪喪後至南渡初期朝野間最重要的國是之争,反映出朝野間對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等時局大勢的看法,其過程的曲折反復,體現了主戰、主和各種政治勢力的此消彼長,主戰派的某些主張,激進冒險,高調而未必切于實際;主和派的某些建議,確實出于具體情况考慮,不可一概斥之爲畏縮退讓。簡言之,可分爲三個階段:(一)堅守中原時期。争論集中在返都汴京,或是駐蹕應天、長安、鄧(州)襄(陽)?(二)顧望中原時期。争論集中在駐蹕揚州,還是建都襄(陽)荆(州)、建康還是武昌?(三)走向偏安時期。江南局面初成,争論集中在建都建康,盡可能保有恢復中原的希望,或駐蹕臨安,就此宣告退守江南一隅?
一、堅守中原之不可能
建炎元年三月,在汴京淪喪後不久,知淮寧府、宋宗室趙子崧就向流亡的趙構康王元帥府建言:“若有獻議擁兵南渡者,似未可聽。大王麾下皆西北人,孰肯渡江?渡江之後,中原豈可復收?”⑤此說首倡南、北之議,代表了當時朝野間堅守中原、伺機恢復的輿論。具體落實到建都問題上,鑒于張邦昌僭位汴京,首先被考慮到的是南京應天府。建炎元年四月,元帥府副元帥宗澤首倡“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于是趙構“决意趨應天”。⑥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在汴京開封東南約一百二十五公里處,兩地同處平原,無地險阻絶。⑦選擇此處駐扎,顯示出與敵對峙的抗戰决心。同月,金兵進犯應天府,嘉州防禦使韓世忠引所部擊破之,民心稍安。⑧五月,監察御史張所按視陵寢還,鑒于形勢的變化,指出應當還蹕汴京。⑨就地理位置而言,應天與開封相去不遠,並無根本不同,從張所奏疏的還蹕“五利”來看,回蹕開封主要還是出于政治意義上的考慮。這一時期,主張還都汴京最力的是宗澤,至建炎二年春正月,宗澤共上疏十二封,反對留滯應天與南渡建康,而要求還都汴京。⑩宗澤的理由也出于政治考慮,諸多奏疏可一言以蔽之,“我京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11)實事求是地說,宗澤奏疏中並無太多可供實際操作的建都考慮,故而“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黄潜善、汪伯彥皆笑以爲狂”。(12)儘管後人對此有不同意見。(13)但必須看到,汴京此後仍陷入敵手,紹興二年四月劉豫僞齊建都于此,其地成爲“西南去宣司三千余里,東南去行在四千餘里,外無應援,內乏糧儲,勢力孤絶望”之地。(14)這說明當時南宋政府尚無捍衛應天、汴京這類平原地區城市的力量(此後駐蹕之地揚州的陷落,也再次說明了這一點)。尋繹宗澤的建都之議,不難發現其中並未提出可以付諸實際操作的措施,更多强調的是汴京的政治意義。後世贊同宗澤意見者多以“河北義旅數十萬”爲最重要的依賴條件。王夫之《宋論》對“義軍”問題的分析要冷静得多:
所謂豪杰義社者,固無能爲也……義軍之興也,痛故國之淪亡,悲衣冠之滅裂,念生民之塗炭,惻怛發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腦者,數人而已……其名曰萬,而實不得半也。即其實有萬,而可戰者,不得千也。可戰者千,而能不大勝則前、小挫則卻者,不得百也……義社恃大軍以成,故鵬舉一班師,而數十萬人不知何往。大軍恃義社以進止,則義社一敗釁,而大軍不足以孤存。兩相恃則兩相失,女直以專一之兵,直前而無待,左披右靡,又惡足以當之?(15)
岳飛北伐時期,南宋軍事局面比起宗澤守汴時大有改善,義軍之不可依恃仍然如此。更何况靖康剛剛淪喪之後的較短時期,在宋金正規軍力量懸殊、義軍不遑組織訓練的情况下,實際上不存在戰略上對等攻防的條件。汴京作爲無險可守的北方平原地區城市,僅僅以“河北義軍”爲依憑,是遠遠不够的。南宋初年,宋軍只有通過地形上的優勢(水域或山地),才可能對金人騎兵進行有效的防守,如建炎三年韓世忠水師的黄天蕩大捷;以及紹興元年陝西吳玠依靠和尚原山谷地形,以床子弩等遠距離殺傷武器防守獲勝,都說明了這一點。直到岳家軍騎兵部隊及其相應的“野戰”之法的創建(16),以及劉錡在順昌大捷中創造的步兵標槍、長斧、拒馬木協同戰術的興起,南宋軍隊才在平原地區與金人的作戰中取得了一定的優勢。
相比宗澤而言,李綱的建都之議考慮比較全面。建炎元年六月,李綱上《十議》,其二《議巡行》專論建都問題,他的意見是:“天下形勢,關中爲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爲西都,襄陽爲南都,建康爲東都。”(17)就在同一個月,京兆府路經略使唐重“率長安父老子弟請上駐蹕漢中,治兵關中”,提舉陝西常平公事鄭驤則上疏稱“長安四塞天府之國,項羽弃之高祖,李密弃之太宗,成敗灼然,願早爲駐蹕之計”。(18)以關中爲天下形勢之上的論調,興于秦漢,極于隋唐,其時關中沃野千里,經濟發達,地勢下瞰中原,易守難攻,所謂“陝西山川四塞,形勝甲于天下,爲自古建都重地。雄長于茲者,誠足以奄有中原矣”。(19)但自隋唐以降,關中的經濟已經由灌耕、漕運並重變爲主要依靠漕運,自給自足變爲依靠外界補給,難以在經濟上立足爲都城。宋代開國之初,曾經有遷都之議,最終仍居留開封,就是出于漕運經濟的考慮。(20)靖康難後,中原兩淮地區淪爲戰場,百業荒廢,江南一地成爲主要的補給基地,時人所謂“取財于東南,募兵于西北”(21),如果要從千里之外的江南,經過盜匪橫行、僞政權把持、金人覬覦的中原兩淮區域,將大批糧食通過漕運進入關中,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高宗與臣下討論駐蹕關中問題時就指出:“倚雍之强、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止可備萬人糧,恐太少。兩浙若委付得人,錢帛猶可溯流而西。至于糧斛,豈可漕運?”(22)直至理宗端平元年,朝廷議復三京,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喬行簡上疏反對,一條重要理由就是:“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絶。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鐘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23)無食即無兵,南渡之初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部隊頻頻請食,朝廷財政極其窘迫。(24)而爲了更加便利的應付軍隊的補給問題,高宗朝廷一方面鼓勵軍隊屯田(25),另一方面不得不以非常規的方式直接將各地轉運使甚至戶部官員直接委派爲軍隊的供應官以備急需。(26)張浚以“據形勝以固根本”的理念經營半壁關中(27),無法倚仗江南漕運,不得不徵用蜀中的糧食與民力,蜀地爲之凋敝,這在張浚被罷免之後成爲其屢遭詬病的一大罪狀。可見建都關中只是一種追憶歷史的幻想,並不切合當下實際(事實上,建炎二年一月,羅梭攻陷長安,請上駐蹕的京兆府路經略使唐重本人亦死難(28),駐蹕已不可能)。對此問題,當時已經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建炎三年六月,中書舍人季陵就指出:“國家之根本在東南,東南之根本在建康。雄山爲城,長江爲池,舟車漕運數路輻湊,正今日之關中河內也。”(29)除了地理形勢之外,漕運經濟成爲衡量建都之地的最重要因素,這正是建康爲“今日之關中”的理由。
在這一形勢下,執政黄潜善、汪伯彥主張巡行東南、駐蹕建康,而李綱本人也在建炎元年七月提出了折衷方案,“夫襄、鄧之地,西鄰川、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達江、淮,可以運榖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願爲今冬駐蹕之計”。(30)即駐蹕鄧州、襄陽之間,居中策應,西接關中(長安),東連江南(建康)。應該說,從兼顧全域(尤其是經濟地理層面)考慮,鄧州、襄陽具有相當的優越性。但從當時流亡南宋政權的力量來看,尚不足以在平原開闊地區與金人抗衡,這與難以駐蹕應天、汴京出于同樣原因。因此,高宗雖然暫時采納李綱的建議,但朝臣多以爲不可,其中衛尉少卿衛膚敏和中書舍人劉玨的意見具有代表性,前者以爲:“睢陽駐蹕,鹹以爲宜。但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不足以容千乘萬騎。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况我斥堠不明,烽燧不謹,萬一奄至,將如之何?”(31)後者指出:“南陽城惡,亦不可恃。”(32)事態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預見的正確,建炎二年春正月,金人焚鄧州,而截留于此地的四川輕齎綱以及存聚的芻粟糧草等爲駐蹕準備的經濟物資,悉數爲金人所有。(33)駐蹕鄧襄之間,實際已不可能矣。
既然駐蹕汴京、應天、長安便及鄧(州)襄(陽)都缺乏實際操作的可能性,建炎元年冬十月丁巳朔,高宗登便舟前往淮甸,準備南渡。沿運河路綫,先後次泗州、楚州。癸未,至揚州。(34)由此至建炎三年二月,一直駐蹕于揚州。這就進入了建都之議的“顧望中原”階段。
二、顧望中原時期
“顧望中原”時期又可分爲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駐蹕長江北岸的揚州時期;第二階段是渡江後對建康、武昌與荆襄三個建都地點的争論。
儘管此前朝中早有駐蹕建康、依托長江天險的主張,但流亡政權在將近一年半的時間內駐守長江北岸的揚州,表明了相當强烈的顧望中原的戰略姿態。吏部尚書呂頤浩建議以揚州爲基地,“陰爲過江之備,而大爲拒敵之資……以俟夾淮一戰,此不易之策”。(35)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揚州的地理位置相當重要,所謂“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36)也因爲如此,揚州作爲南方政權在長江以北的最後一個重要駐守城市,向來都是北方入侵者席捲之勢達到頂點時的一個“祭旗式”的犧牲品。試想,北方軍隊從黄淮平原一鼓作氣南下,眼看就要直抵長江,在北岸稍作休整,即可渡江一統南方,而揚州橫亘眼前,成爲北方軍隊休整之前需要最後攻克的據點。北人亟需喘息,南人背水一戰,就此鑄成了歷來揚州戰况之慘烈,以及由此帶來的對揚州的報復性屠城的頻繁發生。南宋初的揚州焚城(37)、明末清初的“揚州十日”正是此類例子。由此可見,雖然揚州地處運河系統的樞紐位置,漕運便利,可以滿足建都的經濟要求,但就軍事地理的意義而言則總是處于背水而戰的絶境,不適合建都的防禦要求。早在建炎二年,尚書吏部侍郎魏憲就指出:“維揚南枕大江,自古未有背天險而爲都者。”(38)建炎三年,起居郎兼權直學士院張守也有類似建議。(39)事實上,建炎三年二月壬子,金人進犯,高宗立即放弃揚州,馳往長江南岸的鎮江。(40)此後,終高宗一朝乃至整個南宋時期,朝廷駐蹕之地再也没有越過長江一綫。
第二階段,建都之議中的地點集中于長江下游的建康、中游的武昌,以及上游的襄(陽)荆(州),三者連接,正好建構起一條襟帶長江的防綫。紹興三年,呂祉有一番頗得高宗贊許的議論:“今屯兵淮甸表裏雖一,而上下不接,如人之身四體不備……自四川而下,有襄陽、荆南、武昌、九江、池陽、太平、建康、鎮江,皆沿江也……當命將分兵戍守,使相維持。自遠近視之,皆隱然如敵國焉,則共奠王室,有磐石之固矣。”(41)從呂祉的議論可以看出,這時的局面已經由淮甸南北的縱向進取之勢,改爲沿江東西的橫向防禦之勢,重心由中原變爲江南。還有一點需要特別指出,堅守中原時期“駐蹕鄧(州)襄(陽)”的觀點與顧望中原時期“駐蹕襄(陽)荆(州)”觀點實有區別。以武當山脉下的襄陽爲中心,往北,鄧州、南陽座落于伏牛山脉下,兩山之間,向西是前往漢中的谷地通路,向北則直趨中原;往南沿漢水方向,則指向長江上游重鎮荆州。由這樣的地形可見,“鄧襄”並舉,是北進的路向,“襄荆”合稱,是南退的路向。兩者看似都以襄陽爲主,實則體現出了直接在中原作戰與據守長江以顧望中原的不同意圖。(42)
客觀地講,儘管高宗在建炎三年二月爲了逃避金人進犯,倉皇退至杭州,但在這一時期他並未將杭州作爲駐蹕的長久之地。建炎三年三月一日,形勢稍緩,高宗就發布詔書稱:“昨金人逼近,倉促南渡,暫至錢塘,勢非得已……錢塘非久留之地,便當稍進,務要駐江寧,經理中原。”(43)並召見此前力主不宜駐蹕揚州的衛膚敏,詢問建都事宜,衛膚敏認爲:“爲今之計,莫若暫圖少安于錢塘,徐詣建康。然長江數千里皆當守備,如陸口直濡須,夏口直赤壁,姑孰對曆陽,牛渚對橫江,以至西陵、柴桑、石頭、北固,皆三國南朝以來戰争之地。至于上流壽陽、武昌、九江、合肥諸郡,自吳而後必遣信臣提重兵以守之,而江陵、襄陽尤爲要害,此尤不可不扼險以爲屯戍也。”(44)同一時期,迪功郎張邵(45)、殿中侍御史王廷秀(46)、將領岳飛(47)都有類似建議。可見,建構長江防綫成爲這一時期朝野間的共識。不同聲音主要集中在駐蹕于長江防綫的上游、中游還是下游。同年三月,和州防禦使馬擴上書建言三策,上策退居巴蜀,中策定都武昌,下策駐蹕金陵。(48)駐蹕巴蜀,再由關中進取中原,實無操作之可能,此點前文已經加以分析。御史中丞張守的反對意見就指出這一點:“擴乃西人,知關陝殘破,不可以遽往,欲先幸蜀,以便私耳。(49)馬擴三策的新意是提出了駐蹕武昌的可能性。這一可能性因張浚的再次提出而進入朝廷的正式議事日程,張浚建議:“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而別委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令呂頤浩扈駕來武昌,張俊、劉光世從行,庶與秦川首尾相應。”(50)基本意圖也是由武昌而及巴蜀,再由關中進取。此議最初獲得高宗認同,遂于五月任張浚爲宣撫處置使,統領川陝、京西、湖南北路,進行前期準備。隨後在建炎三年五月,高宗進駐建康。(51)八月,再議駐蹕武昌事宜,而此時主要以江浙士大夫爲代表的反對聲音出現了,認爲“鄂岳道遠,饋餉難繼,又慮上駕一動,則江北群盜乘虛過江,東南非我有矣”,時相呂頤浩成爲反對意見的代表。其實,駐蹕武昌還是建康,其意義在于伺機退守巴蜀或湖湘,還是力保江淮東南之地?這一區別在將領們的意見分歧中表現得很明顯,張俊、辛企宗支持駐蹕武昌,因爲一旦有變,可以自岳鄂幸長沙;韓世忠堅决主張留駐建康,他認爲一旦前往武昌,則等于放弃江淮,東南之地不保。(52)最終高宗的考慮則是武昌其地四通八達,“敵之可來者五六”,難以防衛,最後决意“定居建康,不復移蹕”(53),進而由此布置了防江措施。(54)張浚等人駐蹕武昌的建議隨之落空。
高宗最終放弃駐蹕武昌計畫,可能出于兩個原因。首先還是漕運問題。我們雖然找不到此年的具體數字,但直到宋金和議達成之後的第三年(紹興十三年),倉部員外郎王循友還指出:“國家平昔漕發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余萬,和糴之數又在其外。而近歲上供之數才二百八十余萬,除淮南、湖北凋殘最甚、蠲放之外,兩浙號爲膏腴沃衍,粒米充羨,初無不耕之土,而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55)既然淮南、湖北凋殘最甚,則難以支撑駐蹕武昌的物資消耗是可想而知的;而兩浙膏腴沃衍,稻米充羨,便于就養,選擇其地是可以理解的。其次,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則因爲武昌不利于逃避金人入侵後的追擊。在此前(建炎三年二月)的逃難中,高宗得以迅速撤離至杭州,乃是依賴運河水運的便利;江南水道縱橫,金人騎兵難以迅速展開追擊,所謂“錢塘有重江之阻”(56),而且,江南入海便利,可由海道迅速前往福建、廣東。如果駐蹕武昌,一旦遇襲,有三條退路,一條由長江逃避,由于路綫太長,而且直面江北,會遭到沿途襲擊,最終再經建康還得通向江南;一條由西南方向向湖南退避;一條由東南方向經九江向江西退避。湖南、江西都是多山地區,大規模遷徙行動難以展開,經濟也不如江南發達,退避至此,也難以長期駐蹕。如果再由其地退避前往福建、廣東,其間間隔羅霄山脉、武夷山脉,行進艱難,遠不如海道便利。張俊、辛企宗等將領爲了逃避金人主力在江淮東南一綫的進攻,試圖改由岳鄂退守長沙,這種打算只能奏一時之效,一旦金人改變進攻方向,將主力調往武昌,守軍很難退卻。一言以蔽之,駐蹕武昌,只宜進攻,不宜退守。六個月前剛經歷了倉皇逃難的高宗已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進取中原的信心(57),而此時金人正由中原伺機再進,夏天甫過,南宋朝廷的最大時務就是防秋,既然以防禦爲主,自然不會選擇駐蹕武昌這一方案了。
三、建康與臨安之争
建都之議中顧望中原的長江三策,荆襄、武昌都不適合,剩下的選擇只有建康。然而建炎三年八月,金人再次入侵。十一月,建康陷落。流亡朝廷由建康經鎮江、平江、杭州、越州逃至明州,又航海至舟山群島(58),再航海至臺州、温州,最後回到越州(改紹興府)。(59)在流亡期間,建都之議仍不絶于耳,要求返還建康者有汪藻(60)、廖剛(61),呂頤浩提出移蹕武昌(62),高宗最終于紹興二年正月移蹕臨安。(63)此次在争議聲中有意識地選擇臨安爲駐蹕之地,與建炎三年二月逃亡中初駐杭州的臨時性行爲不同,實際上拉開了“建都之議”第三階段的大幕,即建都建康與駐蹕臨安之争。
建康與臨安作爲建都之選,其優劣極爲分明。二者的區別,在戰略上體現爲“防淮”與“防江”的不同姿態。建都建康,指揮中樞緊靠長江,則淮甸成爲第一道防綫;建都後方臨安,則淮甸雖有若無,長江成爲第一防綫。就積極的方面說,防淮則尚存中原半壁,防江則只留存江南一隅。就消極方面說,“守江必守淮”是南方防禦北方的基本常識,守淮意味著開闊的警備緩衝地带和充分的防禦準備時間,所謂“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潜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从而防哉?”(64)换言之,無淮則長江天險爲敵我所共有(此點甚至在20世紀的“淮海戰役”中也是國、共交戰雙方的共識)。正因爲如此,加上建炎三年的逃難糾正了朝野間對敵我形勢强弱的模糊判斷,駐蹕武昌及荆襄的聲音基本上泯滅無聞了。如紹興五年三月李綱之議(65),紹興九年五月左迪功郎張行成《芻蕘書》二十篇中的《議都三篇》。(66)提及武昌、荆襄,一般都只是强調其地爲屏衛江南的長江防綫鏈條上的重鎮,須駐扎大部隊,委以重臣,以配合拱衛建康的都城地位。這一時期,駐蹕建康的提議幾乎成爲唯一的主流聲音。(67)從漕運的動向可以看出,紹興二年五月起,南宋政權開始在建康屯積糧草(68),修築宮室。(69)同時期,臨安的特大火災也許減小了建都其地的可能性。(70)但是,鑒于此前逃亡的經驗,紹興三年九月,高宗布置防務,將禁衛親兵部隊安排在沿海港口地段,作海上逃避的準備。(71)幸而一秋無事。紹興四年,知建康府呂祉等人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反復陳說:“欲守東南,則淮甸荆州皆不可失……今駐蹕臨安,僻在海隅,諸將重兵皆屯江左,相去遠矣。以臣觀之,必于沿江一帶措置,而移蹕向前。”(72)因此,紹興四年十月,高宗再次下令移蹕建康。(73)但又首鼠兩端,逡巡不定,一直停留于平江(今蘇州)觀望。至次年二月,以“建康營葺未就緒,而平江素無官府”的荒唐理由,回蹕臨安。(74)三月,移浙西安撫司于臨安府,增臨安地望之重(75),透露出長期留居此地的意圖。正是針對這一傾向,朝臣士大夫紛紛力倡建都建康之議。先後有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綯(76)、張浚(77)、監察御史劉長源(78)上疏,眉州布衣師維藩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79)時逢諜報劉豫有南侵之意,張浚再次“力陳建康之行爲不可緩”。(80)應該說,南宋朝廷對于劉豫僞政權並不畏懼,因此,八月甲辰,高宗詔諭將士親征。九月,發臨安,次平江。在平江居停期間,又經趙鼎提議,有回蹕臨安之意,直至紹興七年正月,因淮西等地連連告捷,形勢大好,經張浚力争,才動身移蹕建康,于三月辛未抵達。(81)三月辛巳,命百司漸赴行在,“所謂(臨安)留守司,名存而已”。(82)四月癸巳,建太廟于建康,以臨安府太廟爲本府聖祖殿。(83)五月,直龍圖閣、知建康府張澄言臨安、建康均爲駐蹕之地,而財賦所入多寡殊絶。詔與權免分撥二年。(84)七月乙酉,詔即建康權正社稷之位。(85)由這些迹象可以看出,這次駐蹕建康,是意圖最爲明確、儀式最爲正式的一次籌備建都之舉。如果不出意外,朝野間輿論普遍要求的“定都建康”似乎將成定局。
不幸的是,八月戊戍,發生了“淮西兵變”事件。中侍大夫、武泰軍承宣使、行營左護軍副都統制酈瓊叛。(86)淮西兵變的直接起因是張浚罷免劉光世軍職,劉光世所部酈瓊不自安,遂叛投劉豫。高宗駐蹕建康,原本是因爲淮西大捷,有了拱衛建康的江淮屏障;現在淮西兵變,門戶大開,建康處在敵方直接威脅之下;另外,罷免劉光世的倡議者張浚因兵變去位,建都建康也就失去了最大倡議者。所以,剛剛進入軌道的建都之舉面臨著突然中止的危機。九月,御史中丞周秘言宰相張浚失謀誤國,稱“建康兵火之後,全乏第舍,而浚建議移蹕,謀不素定,使倉卒遷徙之家暴露失所,罪十五也”。(87)已經將建都建康之議列爲張浚的罪狀之一。高宗在談論回蹕問題時更是說:“張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國用,何嘗得尺寸之地,而壞事多矣。此等議論(“恐回蹕之後,中外謂朝廷無意恢復”)不足恤也。”(88)張浚本人在去位之後最爲擔心的也是建都建康之議遭到廢弃,史稱“自趙鼎召歸,浚每以回鑾爲念。洎罷政登舟,諸人往餞,猶以此言之”。(89)儘管有陳功輔、張守等朝臣仍持此議不變(90),但高宗回蹕臨安之意已决。紹興七年十月,又將臨安聖祖殿改回爲太廟。(91)十一月,奉九廟神主還浙西。(92)同時,大興工程,全面整治臨安水道。(93)紹興八年二月,離開建康。(94)至此,建都建康已經無望,駐蹕臨安成爲定局。《宋史·高宗本紀》稱:“是歲,始定都于杭。”(95)紹興九年,當金人歸還河南地界後,高宗甚至告諭輔臣:“河南新復境土,所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96)其治國之重心,已經完全立足于東南了。所以,胡寅在這一年就指出,“始十餘年間,凡有詔令,必以恢復中原爲言,所以系百姓心也。今乃于臨安增修母后淵聖宮殿,是不爲北遷之計也。然則居杭者乃實情,而恢復者乃空言耳”。(97)到紹興十一年,宋金和議成。紹興十四年,高宗言:“朕于《晋書》取《王羲之傳》,凡誦五十餘過。其《與殷浩書》及《會稽王箋》所謂‘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巳’。其論用兵誠有理也。”(98)這段話最爲明確不過地表明,在高宗的頭腦中,偏安東南即爲國是,恢復中原已不在議事日程中矣。
建都臨安之緣由,除了林正秋先生指出的經濟因素之外,就其選擇的毫無徵兆的突然性而言,本文以爲更重要的因素恐怕只在于其地便于出海逃避。關于臨安的地理位置,淳熙十五年陳亮上書有過如下總結:“吳會者……其地南有浙江,西有崇山峻嶺,東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舟楫者之所畏,敵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99)一語道破。建炎四年十一月,秦檜就提出要在入海口岸做好以海道逃遁的準備(100),其後果然奏效。這很可能是秦檜力主和議之前得到寵信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不要忘記,史載秦檜本人由金逃歸就是經由海上路綫,可見他對此道的選擇頗有些心得)。終高宗朝,這都是一條常備的避難快捷方式。如紹興三年九月,高宗布置防務,即將禁衛親兵部隊安排在沿海港口地段,作海上逃避的準備:“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陰軍沿海地分。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爲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101)以至爲民間傳爲笑柄:“和州布衣何宋英上書:‘今國勢危于累卵,而方且費國用造御舟,乃于海岸欲爲避寇之計。天下聞之,舉皆失笑……與其坐困一隅,不若進幸建康,以壯國勢。’”(102)
自建炎元年首倡建都之議,至紹興十一年和議既成、駐蹕臨安終成定局,十五年間争論不休的國是“建都之議”,由堅守中原不得,一變爲顧望中原,再變爲偏安江南。在定都建康幾乎成爲事實的時候,因淮西兵變而望風潰退,遂成建都臨安之定局。所以,呂中《大事記》極爲憤概地質問:“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黄爲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黄爲之乎?自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檜爲之也。六年,浚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爲之乎?”(103)以定都臨安爲標誌,高宗一朝就此恢復無望。高宗之後,南宋諸帝再有北圖之舉,也是積重難返,事倍而功半了。
四、建都之議的影響
南宋初年的建都之議對南宋一代的影響極爲深廣。政治上,建都之議既定,南宋立國方針以守勢爲出發點,失去了恢復中原舊河山的先機,國運日蹙之態勢已成。經濟上,全力經營南方,則在客觀上促進了江南及閩廣之地的發展。北宋以江西之地人才輩出,南渡之後則以閩地人才大盛,學風漸次南移,與經濟重心南移不無關係。
建都之議的最終結果還造成了某些區域重要性的突然加强,從而促進這些區域在各方面的迅速發展。以在宋代突然崛起的重要城市瀘州爲例。瀘州爲成都與重慶之間的樞紐,所謂“自州而東,江水兼衆水之流,浩瀚洋溢,吳楚百石大舟可方行而至。自州以西,水陸兼濟,不十日可抵成都,瀘州驚則兩川盡城守矣”。(104)問題在于,瀘州的這一地理位置優勢自古已然,爲何在宋代突然彰顯,從而導致其地的政治地位提升及城市規模擴大呢?這與建都之議造成的南北局勢有密切關係。以成都爲中心的川北平原(成都府路)是蜀中的政治經濟中心區域,在北宋時期可以北上通過利州路的川陝通道連接中原,也可南下經梓州路(瀘州)、夔州路(重慶)通過長江一綫連接荆楚。建都之議既定,陝西大部已不復爲南宋所有,利州路已不可通往關中,所以蜀中與臨安行在的通路只剩下唯一的南下路綫,這是從未出現過的新情况。因此,瀘州遂成爲川峽四路中內可溝通成都府路(成都)、夔州府路(重慶),外可連接蜀中與江南的綫路樞紐,其政治地位立刻變得重要,而城市規模也因之而擴大了(即以現狀而言,重慶直轄之後,瀘州即以“四川唯一的出海口”作爲宣傳其地緣經濟重要性的口號,兩者頗有相通之處)。一部《宋史》四百六十九卷,結末述及邊面蠻夷,獨以瀘州一地作結,可見其地望之重。
文化上,建都之議成爲南宋文人縈繞于心而揮之不去的話題。以類書之編纂爲例,類書作爲應用性工具,最能見出一時代文化的普遍需求與關注重點。寧宗、理宗時期的章如愚所編《山堂群書考索》是南宋類書中品質較高的一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不但淹通掌故,亦頗以經世爲心。在講學之家,尚有實際。”(105)其書最爲特別的一點就是專門設立了與建都之議密切相關的諸多門類,如前集卷五十八“地理門·江左經略中原”;“地理門·荆襄形勢”;“地理門·江淮形勢”;“地理門·江淮襄陽巴蜀”。(106)又,別集卷二十三“邊防門·江”、“邊防門·淮”、卷二十四“邊防門·海”、“邊防門·襄”、卷二十五“邊防門·蜀”。(107)不難看出,其列舉諸話題及其地理位置皆是建都之議中的重要之點。
北宋皇帝喜言陳法,其風波及文人,此點已有研究者指出。(108)而南宋文人喜言軍事地理,似未見論者提及,此點正由南渡以降建都之議使然。如遺民詩人鄭思肖《即事八首》其四:“徉狂全性命,守死混樵漁。道否懷才老,心高涉世疏。掌中籌地理,燈下論兵書。愧我非諸葛,何人顧草廬。”(109)“籌地理”與“論兵書”並舉,正表明其念念不忘亡國肇禍之始乃在于建都之議未得其適。以陸游爲例,宋史卷三百九十五本傳載其上二府書稱:“江左自吳以來,未有舍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于權宜,形勢不固,饋餉不便,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憂。”又載:“游爲炎陳進取之策,以爲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讀放翁詩“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固然知兩地出于詩人親身游歷,然瓜州渡之涉建康,大散關之涉長安,則放翁心目中自有一種建都之議的個人意見。又如王阮,《宋史》本傳載其于孝宗初年對策言:“臨安蟠幽宅阻,面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于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于進取……今東南王氣,鐘在建業,長江千里,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110)本傳又載:“知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杰也。’”范成大曾以使北議國書禮震驚金廷,獲譽一時,其出使途中飽覽中原山川,熟知地貌,一一見于《攬轡録》。他讚賞王阮的議論,實際上也表明了自己以建康爲基地、顧望中原的立場,范成大的北行絶句名篇《州橋》:“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泪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如結合石湖對建都之議的態度,更覺議論深切。再如辛弃疾,其《美芹十論》第四篇“自治”云:“顧今有大者二……一曰:絶歲幣,二曰都金陵……錢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勢相去亦無幾矣,豈以爲是數百里之遠而遽有强弱之辨哉!臣不爲數百里計也。”稼軒之論,可參見《宋史》卷四百三十四《葉適傳》載:“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111)葉適又于江北招攬兩淮流民,建構堡塢,“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112)這正是建都之議第二階段所謂“防江”、“防淮”之辯。辛弃疾自北來南,正是當時所謂的流民、歸正人,並因此頗受南宋小朝廷的猜忌。以稼軒《美芹十論》合葉適之建議與行動參互觀之,可知稼軒詞“生子當如孫仲謀”之句,實乃“防江必先防淮”的建都之議的文學表述;進而言之,防淮之舉措,必當以建康爲基地,以兩淮流民(“歸正人”)爲主力,此乃稼軒胸懷大志,自薦于南宋小朝廷而不獲大用,感慨身世,發爲浩嘆之辭也!
南宋文人詩賦歌咏,無不時時處處見出建都之議的影響痕迹,其例極夥,聊舉一二。如曾極作《金陵百咏》,其中《鐘山番人窟》:“千群鐵騎遠來侵,鑿穴鐘山用意深。天塹連空遮不斷,烟塵直到海中心。”(113)隱斥駐蹕臨安、以便避海之無用。又如劉過《襄陽歌》:“十年著脚走四方,胡不歸來兮襄陽。襄陽真是用武國,上下吳蜀天中央。銅鞮坊裏弓作市,八邑田熟麥當糧。一條路入秦隴去,落日仿佛見太行。土風沉渾士奇杰,嗚嗚酒後歌聲發。歌曰人定兮勝天,半壁久無胡日月。”(114)極言襄陽連接吳蜀、溝通秦隴之地利。劉過又有《望幸金陵》:“建業水大勝,武昌魚有味……泰華不易得,天下關中爲本根。懷哉金陵古帝藩,千船泊兮萬馬屯。西湖真水真山好,吾君亦豈忘中原。”(115)武昌、金陵、關中以及上詩所舉襄陽都是建都之議中以收復中原爲目的的駐蹕之地,末句“西湖真水真山好,吾君亦豈忘中原”,其諷刺定都臨安之意盡在不言中。又如陳文蔚《石潭道中追賦大江》:“……恃此一葦航,焉能恨南極。雲屯十萬衆,守衛以人力。撫御有良將,成城衆心得。江淮唇齒勢,如家護墻壁。守淮即守江,淮民須愛惜。我朝聖澤深,不在險在德。”(116)劉宰《寄呈王浩翁府判》:“只今淮上未安集,二虜南望猶睢盱。要知兩淮須保障,保障一撤長江孤。邊臣之慮不及此,但知椎剥供苞苴……”(117)兩詩所持皆是“防江必防淮”的建都之議。直到南宋覆滅,遺民詩中仍有建都之議的迴響,又如孫嵩《明妃引》:“禍起當年婁敬謬,後人獨恨毛延壽。”(118)《明妃曲》是王安石以來兩宋文人常在詩歌中吟咏的老調,但孫嵩這裏彈奏出了新聲,“婁敬謬”除了指西漢婁敬所獻和親之策外,還隱以婁敬的建都關中之議影射南宋的建都臨安之議,斥其爲誤國之舉。再如宋無作《武穆墳》說:“若論將軍勇,神京反掌圖。中原數千里,可惜葬西湖。”(119)亦是抱憾于建都杭州的失誤。
如果說,就時情全面考慮,堅守中原稍覺力孱,建都汴京、應天、長安、鄧(州)襄(陽)、揚州的確不切實際;那麽顧望中原時期,不采納建都荆(州)襄(陽)、武昌的建議,而是建都建康,應該是緩急可濟、左右逢源的上上之策;只可惜在建都建康就要成爲事實的前夜,在高宗患得患失、驟興驟亡的逃跑心態及其舉措之下,最終卻選擇了最少出現在朝野士大夫建議中的下下之策杭州作爲駐蹕之地。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下,窮斯爛矣。建都之議延續至紹興十一年宋金和議確定,以駐蹕臨安告終,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預示了南宋朝廷偏安一隅、不思進取並最終覆滅的結局。南渡初的建都之議及其最終結果,廣泛而深遠地影響了南宋一百五十餘年政治、經濟、文化諸多領域,這一話題是言之不盡的。
①原載《思想與時代月刊》1947年7月第四十七期,收入包偉民選編:《浙江大學中國古代史論文集·史學文存·1936-20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②《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82年第1期。
③《杭州研究》2008年2期。
④《船山學刊》2011年2期。
⑤《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建炎元年三月丙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册,第68頁。
⑥《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建炎元年夏四月戊辰”,第1册,第88頁。
⑦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册《宋·遼·金時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年,第12~13頁。
⑧《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建炎元年夏四月戊寅”,第1册,第93頁。
⑨同上,卷五“建炎元年五月丙辰”,第1册,第113頁。
⑩同上,卷十二“建炎二年春正月丁未”,第1册,第216頁。
(11)同上,卷九“建炎元年九月乙巳”,第1册,第172頁。
(12)同上。
(13)如呂中《大事記》(《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建炎元年秋七月癸醜”附録引,第1册,第152頁)就說:“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南。三者不同,言京城之策爲上。況宗澤數月間城築已增固,樓櫓巳修飾,壟濠巳開浚,寨柵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失此一機,中原絶望矣。”
(14)《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五“紹興三年五月已未”,第1册,第845頁。
(15)《宋論》卷十《高宗·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193~194頁。
(16)此點參見曾瑞龍《經略幽燕:宋遼戰爭軍事災難的戰略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中的相關論述。
(17)《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建炎元年六月庚申”,第1册,第117頁。
(18)同上,卷六“建炎元年六月辛未”,第1册,第130頁。
(19)《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二“陝西一”,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2500頁。
(20)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7頁。
(21)《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建炎元年六月丙戍”,第1册,第136頁。又,卷八十九“紹興五年五月辛巳”(第2册,第258頁):“給事中廖剛言:‘臣嘗謂國不可一日無兵,而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被于江淮不知幾萬數,初無儲蓄之備,日待哺于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不勝其困矣。’”
(22)《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二“建炎四年三月乙丑”,第1册,第480頁。
(23)《宋史》卷四百一十七《喬行簡傳》,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9792~9793頁。
(24)《建炎以來系年要録》中此類記載甚夥,如第1册,第511、509、514、517、518頁。
(25)同上,卷四十“建炎四年十有二月”,第1册,第575頁。
(26)同上,中此類記載甚夥,如《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九十六“紹興五年十有二月丙午”,第344頁。茲不贅舉。
(27)同上,卷二十四“建炎三年六月庚申”,第1册,第383頁。
(28)同上,卷十二“建炎二年春正月戊戌”,第1册,第211頁。
(29)同上,卷二十四“建炎三年六月癸酉”,第1册,第386頁。
(30)同上,卷七“建炎元年秋七月已巳”,第1册,第149頁。
(31)《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七“建炎元年秋七月癸醜”,第1册,第152頁。
(32)同上。
(33)同上,卷十二“建炎二年春正月壬子”,第1册,第218頁。
(34)《宋史》卷二十四《高宗本紀一》,第300頁。又,關于高宗南下的運河路綫,可參見《中國歷史地圖集》第六册《宋·遼·金時期》,第22~23頁。此圖爲政和元年區劃,較之同書第62頁“嘉定元年區劃圖”更接近建炎元年的原貌。
(35)《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十九“建炎三年春正月戊戌”,第1册,第296頁。
(36)《宋史》卷四百一十七《趙範傳》,第9802頁。
(37)《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建炎三年二月戊辰”,第1册,第311頁。
(38)同上,卷十七“建炎二年八月戊午”,第1册,第269頁。
(39)同上,卷十九“建炎三年春正月戊戌”,第1册,第296頁。
(40)《宋史》卷二十五《高宗本紀二》,第307~308頁。
(41)《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六十八“紹興三年九月壬戍”,第1册,第880頁。
(42)如《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二“建炎四年三月甲戌”(第1册,第483頁):“禦史中丞趙鼎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荊襄左顧川陝,右視湖湘,而下瞰京洛,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爲行闕,而屯重兵於襄陽以爲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願詔張浚未可長驅深入,姑令五路各守其地,犄角相援可也。’”趙鼎的用詞就是“荊襄”,建議的駐蹕之地是長江南岸的公安。
(43)《建炎淮揚遺録》,《全宋筆記》4編8册,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84~85頁。
(44)《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建炎三年二月丁巳”,第1册,第305頁。
(45)同上,卷二十一“建炎三年三月”,第1册,第356頁。
(46)同上,卷二十二“建炎三年夏四月癸醜”,第1册,第364頁。
(47)《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國朝建炎以來年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8)《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四“建炎三年六月巳酉”(第1册,第319頁):“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委健吏以撫淮甸,破敵人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爲上策。都守武昌,襟帶荊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爲屏翰,是爲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制戰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徙,是爲下策。”
(49)《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四“建炎三年六月巳酉”,第1册,第379頁。
(50)同上,卷二十三“建炎三年五月戊寅”,第1册,第371頁。
(51)同上,卷二十三“建炎三年五月乙酉”,第1册,第373頁。
(52)《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七“建炎三年閏八月丁亥”,第1册,第407頁。
(53)同上,卷二十七“建炎三年閏八月丁醜”,第1册,第405頁。
(54)同上,卷二十七“建炎三年閏八月辛卯”,第1册,第422頁。
(55)同上,卷一百四十九“紹興十有三年六月戊子”,第3册,第80頁。
(56)同上,卷二十“建炎三年二月癸醜”引王淵語,第1册,第302頁。
(57)參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二十六“建炎三年八月丁卯”(第1册,第402頁)引《國史拾遺》載高宗《與元帥(宗維)書》。
(58)《宋史》卷二十五《高宗本紀二》,第313~315頁。
(59)同上,卷二十六《高宗本紀三》,第317~318頁。
(60)《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四十“建炎四年十有二月”,第1册,第575頁。
(61)同上,卷四十八“紹興元年冬十月甲戍”,第1册,第658頁。
(62)同上,卷四十九“紹興元年十有一月戊戌”,第1册,第667頁。
(63)《宋史》卷二十七《高宗本紀四》,第331頁。
(64)《宋史》卷四百一十七《趙範傳》載“趙范上史彌遠書”,第9801頁。
(65)《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十七“紹興五年三月癸卯”,第2册,第233頁。按,此段文字自“且于建康駐蹕”至“然後建康可都”,《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康表十·國朝建炎以來爲年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於“紹興五年”下引作趙鼎語,然文稱“詔前宰執條上攻守策”,趙鼎時爲宰輔,應以李綱爲正,故不取。
(66)《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八“紹興九年五月癸卯”,第2册,第739頁。
(67)只有極個別的例外,如《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一“紹興六年五月癸酉”載知鄂州荊湖北路安撫使王庶語,第2册,第396頁。
(68)《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五十四“紹興二年五月辛酉”,第1册,第727頁。
(69)同上,卷五十四“紹興二年五月庚午”,第1册,第730頁。
(70)同上,卷五十四“紹興二年五月庚辰”,第1册,第732頁。但需注意這只是很次要的因素,因爲臨安在南宋初年火災不斷(參見陳國燦《南宋城鎮史》第八章《城鎮管理和社會保障》表8-1《南宋時期部份城鎮重大火災情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0~332頁),但這並未影響到高宗駐蹕於此。
(71)《建炎以來系年要録》卷六十八“紹興三年九月乙亥”(第1册,頁889):“仍命世忠措置所部沿江至平江府江陰軍沿海地分。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郭仲荀爲檢校少保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提舉宿衛親兵楊沂中兼權殿前司公事。”
(72)同上,卷七十七“紹興四年六月”,第2册,第86頁。
(73)《宋史》卷二十七《高宗本紀四》,第342頁。
(74)《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八十五“紹興五年二月丁亥”,第2册,第189頁。
(75)同上,卷八十七“紹興五年三月丁酉”,第2册,第229頁。
(76)同上,卷八十七“紹興五年三月癸醜”,第2册,第237頁。
(77)同上,卷一百二“紹興六年六月已酉”,第2册,第410頁。
(78)同上,卷一百三“紹興六年秋七月”,第2册,第424頁。
(79)《咸淳臨安志》卷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0)《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四“紹興六年八月甲辰”,第2册,第430頁。
(81)《宋史》卷二十八《高宗本紀五》,第353~356頁。
(82)《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九“紹興七年三月辛巳”,第2册,第497頁。
(83)同上,卷一百十“紹興七年夏四月癸巳”,第2册,第500頁。
(84)同上,卷一百十一“紹興七年五月甲子”,第2册,第507頁。
(85)同上,卷一百十二“紹興七年七月乙酉”,第2册,第531頁。
(86)同上,卷一百十三“紹興七年八月戊戍”,第2册,第535頁。
(87)同上,卷一百十四“紹興七年九月乙丑”,第2册,第545頁。
(88)同上,卷一百十六“紹興七年閏十月戊子”,第2册,第575頁。
(89)同上,卷一百十四“紹興七年九月丙子”,第2册,第553頁。
(90)同上,卷一百十四“紹興七年九月辛巳”,第2册,第556頁。又,卷一百十八“紹興八年春正月戊戌”,第2册,第593頁。
(91)同上,卷一百十六“紹興七年閏十月壬午”,第2册,第573頁。
(92)同上,卷一百十七“紹興七年十有一月癸未”,第2册,第589頁。
(93)同上,卷一百二十三“紹興八年十有一月癸巳”,第2册,第664頁。
(94)同上,卷一百十八“紹興八年二月癸亥”,第2册,第599頁。
(95)《宋史》卷二十九《高宗本紀六》,第361頁。
(96)《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百二十五“紹興九年春正月己亥”,第2册,第711頁。
(97)同上,卷一百二十五“紹興九年春正月己亥”,第2册,第710頁。
(98)同上,卷一百五十二“紹興十有四年八月庚子”,第3册,第120頁。
(99)《陳亮集(增訂本)》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6頁。
(100)《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三十九“建炎四年十有一月癸亥”,第1册,第567頁。
(101)同上,卷六十八“紹興三年九月乙亥”,第1册,第889頁。
(102)同上,卷一百九十“紹興三十有一年六月”,第3册,第720頁。
(103)同上,卷一百六“紹興六年冬十月癸亥”引用,第2册,第456頁。
(104)《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二《四川七·瀘州》,第3376頁。
(105)《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五,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150頁。
(106)《山堂群書考索》,揚州:廣陵書局影印明正德年間建陽劉洪慎獨齋本,2008年,第374~376頁。
(107)《山堂群書考索》,第1366~1379頁。
(108)陳峰、王路平:《北宋禦制陣法、陣圖與消極國防戰略的影響》,《文史哲》2006年6期。
(109)《全宋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1998年,69册,第43416頁。
(110)《宋史》卷395《王阮傳》,第9490~9491頁。
(111)《宋史》,第10061頁。
(112)《宋史》,第10062頁。
(113)《全宋詩》,50册,第31513頁。
(114)《全宋詩》,51册,第31807頁。
(115)同上,第31810頁。
(116)同上,第31933頁。
(117)同上,53册,第33408頁。
(118)同上,68册,第43156頁。
(119)同上,71册,第4475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