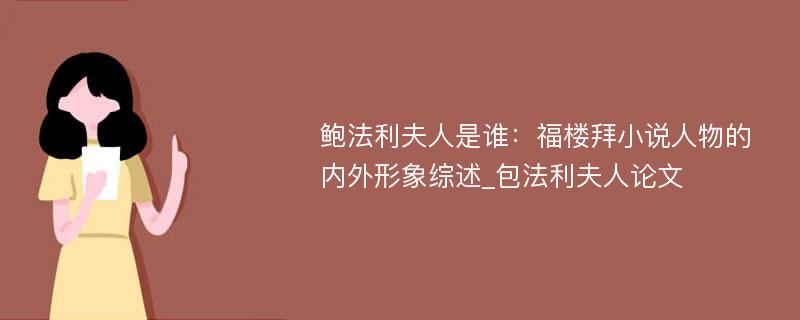
谁是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小说人物文本内外形象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楼拜论文,谁是论文,夫人论文,文本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自诞生起一直吸引着学者、文人及普通大众的阅读兴趣。如果说一百五十年前的那场诉讼①刺激了随后小说的发行,一百五十年之后,单凭小说中几段女主人公的风流韵事已无法保证小说的可读性。然而,无论是作品文字本身,还是小说塑造的种种人物,都在二十世纪读者的阅读中展现了更多层次的魅力。主人公爱玛·包法利已成为世界文学史上鲜明又神秘的女性形象之一。谁是真正的包法利夫人?她是否就是作者本人?福楼拜给了她怎样的文本形象?广大读者又如何认同或批评这位诺曼底少妇?本文试图围绕这一系列拷问,探讨福楼拜在该人物创作上的艺术手法以及人物在文本内外形象的不定性,并由此更好地理解福楼拜的创作原则。
一、包法利夫人探源
诸多学者和读者认为,小说取材于福楼拜父亲的学生德拉玛尔和他第二任妻子德尔菲娜的故事,几乎是真实的写照②。该判断主要源自福氏好友杜刚(Maxime Du camp)在作者逝世后不久出版的《文学回忆录》。然而,通过对福楼拜书信和手稿的仔细研究、对已有重要批评文献的参考总结,克罗蒂娜·戈多-麦其(Claudine Gotho-Mersch)女士在其博士论文《〈包法利夫人〉的诞生》③中指出,德拉玛尔家的故事并不是小说创作的源泉,它更不是把小说标榜为“现实主义”典范的有力凭证。杜刚的回忆录中充斥着大量的杜撰成分,有很多细节都难以考证,可以说是根据小说文本想象德拉玛尔一家的故事。而1890年(福氏逝世十年后),记者乔治·杜波斯科(Georges Dubosc)赴鲁昂附近里镇(Ry)的调查更错误地拉近了杜刚讲述的逸闻与真实事件间的距离。杜波斯科认为里镇就是小说永维镇(Yonville)的原型,该镇的风貌和人物都与小说中描绘的相匹配。遗憾的是这位记者并没有带着批判的眼光进行探访,而是轻信了当地居民自豪且夸张的“讲述”。福楼拜在后世的声名更让“包法利夫人”成为里镇人民的“文化遗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里镇当地文学社和商会的资助下,德尔菲娜女士拥有了新的墓碑,上面除了真实姓名之外还赫然写着“包法利夫人”;小镇还借该联系发展了其他旅游景点,如爱玛的花园,爱玛的婚礼等④,义无反顾地加固了文本人物与逸闻之间的联系。然而,福楼拜从德拉玛尔的故事中提取出来的可能只是男女主人公的出身和社会身份——丈夫是乡村医生,妻子出身农家。当作家已经在草稿上设计了夏尔·包法利的死亡时,德拉玛尔先生尚在人间,而其夫人也没有被证实是服毒自尽。
事实上,福楼拜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已拥有更多其他原材料。虽然《包法利夫人》是福楼拜个人风格的革新篇,但在创作内容上,它与福楼拜早期的个人写作经验难有着必然的联系。早在青年时期,福楼拜就写过小说《激情与美德》(Passion et Vertu),故事中的主人公如爱玛一样对爱情有着很多幻想,为了摆脱家庭去美洲和情人相聚,毒死丈夫和孩子,不料收到情人的决裂信,后服毒自尽。小说取材于1837年10月5日鲁昂日报上的一则小故事。可见,福氏早已对相同题材进行过文本练兵。另外,福楼拜是个搜集材料、分析材料的高手。《罗多维卡回忆录》(1es Mémoires de Mme Ludovica)是其案头的重要材料。该回忆录用第三人称讲述了雕塑家布拉迪耶(James Pradier)之妻路易斯(Louise)的风流韵事,以及她最后债务累累破产的细节。《包法利夫人》中大量有关爱玛金钱困扰的写作主要参考了这部匿名回忆录。在爱玛性情勾勒方面,福氏早期的《情感与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可谓是《包法利夫人》的试笔,故事中两位男主人公的心理描写有很多与爱玛类似的地方,他们都是受浪漫主义文学深刻影响的青年。
福楼拜在书信中揭示过《包法利夫人》的创作动机,他最初希望描写“一个在外省乡间生活的处女,在痛苦中老去,最后进入一种神秘主义和幻想出来的激情的状态”⑤(Flaubert,326)。为了让故事更便于理解,更有生气,贴近生活,他保留了故事的背景,特别是“色调”,选择了一个更人性、更真实的主人公。从这点上看,作者写作重点并不是刻画一个鲜明的文学形象,他更关心人物所处的环境,让人物在环境中诞生,被环境所控制。“包法利夫人”是外省风俗的产物。德拉玛尔一家的故事可能给福楼拜提供了创作小说的框架,而这次福楼拜所要努力的,是创作出一种与年轻时代作品不一样的风格。如果说布耶和杜刚的点拨⑥是福楼拜艺术转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包法利夫人》的成功却不能单单归结为这两位朋友提供的趣闻。所有的作家都从身边的故事中吸取创作的素材,而福楼拜所做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书记员”,他更是“创造者”,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二、“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虽然福楼拜在书信中强调“《包法利夫人》没有任何真实性。这是一个完全捏造的故事。我既没有加入任何个人情感,也没有加入任何个人经历。”⑦(Flaubert,324)不少评论家和读者还是习惯将作者个人生活和小说人物故事联系起来,寻找作者在作品中的投影。福楼拜逝世后,“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句福楼拜的“告白”被一再引用,以期证实作品中的个人色彩。然而,很少有人去考证这句话的真实性,以至于它也成了福楼拜最痛恨的“成见”⑧之一。法国学者德·彼亚兹(Pierre-Marc de Biasi)追根溯源,指出福楼拜从来没有在其书信或手稿中写过此话,它的诞生仅源于道听途说:早期著名福楼拜学者热内·德尚玛(René Descharmes)在他的评论作品中揭示,福楼拜的通信人阿梅利·波斯凯(Amélie Bosquet)的一位知己曾提及,当波斯凯小姐问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创作来源时,福楼拜一再强调“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根据我而出。” ⑨这个发现被福楼拜研究者们陆续间接引用,出现在众多著名评传中,直至最后成了似乎不可辩驳的事实。然而,当事人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一插曲,从而使这一判断来源的真实性无从考证。“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只能勉强成为评论家对该作品传记式点评的论据。
诚然,如果真要追溯包法利夫人和福楼拜之间的个人渊源,福氏年轻时期的作品可能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思路。作家和爱玛一样,年轻时深受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创作中也不乏夸张且煽情的段落,第一部《情感与教育》便是其传记式的自我描写。1859年11月在写给波斯凯的信中,福氏坦言道:“年轻时代我疯狂地爱过,一往无前地、深刻地、默默地爱过。夜晚仰头望月,计划带她私奔、带她去意大利旅行,为她怀抱崇高的梦想,经受身体和精神上双重折磨,闻到她臂膀的芳香时就痉挛,在她的目光下脸色骤然苍白,这一切我都经历过,非常深刻地经历过。我们每个人都在心中有一间皇室闺房。我只是将它用高墙围砌起来了,而它并没有被摧毁。”⑩(Flaubert,384)然而,福楼拜很快醒悟到,这种浪漫主义的腐蚀只会把人物推向无穷尽的幻想之国,他批评青年时代的自己,更鄙视爱玛这个人物:“这是个有点反常的人物,一位被虚伪的诗歌虚伪的情感笼罩的人物”(Flaubert,326)。他从自己的经历中跳了出来,努力将自我从作品中消除,或者说对曾经的自我进行解剖,满足于展示。作家在创作时,靠近每一个人物,成为他们。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福楼拜是他笔下的任何人物。
三、文本中的包法利夫人
不管怎样,包法利夫人首先诞生于福楼拜的文本。《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部人物传记,更不是包法利夫人一生的素描。从人物履历叙述的完整性上看,小说勾勒的主要是夏尔·包法利的一生,以其入学开篇,以其死亡终结。“包法利夫人”直接指向女主人公的社会身份:包法利先生的夫人。福楼拜并不希望读者轻易地将其替换为《爱玛》或《爱玛·包法利》。文本中冠于此头衔“Madame Bovary”(包法利夫人)的人物并非一直等同于女主人公爱玛(11)。第一个出场的是夏尔的母亲,任劳任怨循规蹈矩的传统女性。后又指代夏尔的第一任妻子:干瘪丑陋的迪比克夫人。而爱玛只有等到去沃比萨尔参加舞会的时候(第一部第七章!)才第一次冠上了这个头衔,而且一出现就和她丈夫绑定在一起:“星期三下午三点,包法利夫妇登上那辆敞篷轻便马车……”(12)。(福楼拜,31)而这三个女人之间一直处于交织、争夺的矛盾状态。自从爱玛从其他两位女性那儿继承了这个称呼后,便跳不出该“牢笼”。小说结尾,爱玛服毒自尽,夏尔的母亲希望重新修复和儿子的感情,取代包法利夫人的位置,而一向柔弱的夏尔却“拒绝了她……母子关系无可挽回地决裂了。”(福楼拜,242)
如果说夏尔的母亲恪尽职守,做好称职的“包法利”夫人,那么爱玛对于这个称呼,有的仅是抗拒和厌烦,然而“外省风俗”——福楼拜在完稿后发表前给作品添加了这一副标题——最后还是把她钳制在她的社会身份上。正如爱玛的第二任情人罗多尔夫说的:“包法利夫人!……哎!所有的人都这么称呼您!……可这并不是您的名字;这是另外一个人的!”(福楼拜,106)爱玛自己也曾经“巴不得包法利这名头——如今也是她的姓——能响当当的,书店的封皮上见得到,报纸杂志三天两头提起,全国上下没人不知道。”(福楼拜,41)然而这个名字不能带给她幸福,它定义了爱玛的社会处境,而她为逃脱这个名字所指向的平庸现实所做的一次次努力最终必然化为虚妄。她扮演的始终是原来的自己,她的思想一直停留在修道院中的爱幻想且多情的“爱玛·鲁奥小姐”那个阶段,对自己未来身份的设想从来没有变化过。心理姓名与社会姓名的落差造成了她必然的悲剧结局。
福楼拜并没有在文本中一蹴而就,直接全面描写包法利夫人——爱玛——的形象,他选择通过其他人物的视角来认识这个人物,通过大量的心理描写来架构人物的精神面貌,因此读者看到的是丰富且多变的女性形象。比如爱玛的外在美是透过一双双周围人物眼睛的观察来展现的;夏尔眼中的爱玛“多么美”;在书记员莱昂眼里,她是一位夫人,在永镇鹤立鸡群;而在第二任情夫罗多尔夫眼中的她更具肉感。在文本中,包法利夫人不是唯一的、肖像式的人物,福楼拜只是罗列了她给人的不同印象,而这些印象又处在变化中:罗多尔夫最后厌倦了她,莱昂惊讶于她对自己的控制,夏尔对她的爱慕经历了真相带来的震撼。而包法利夫人自己也永远无法认清自己,她希望成为别人,在别人的生活中设想自己。这个“别人”可以是浪漫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可以是舞会上的伯爵太太们;可以是和罗多尔夫私奔后的幸福爱人,也可以是拉加尔迪的情人。正如阿兰·彼西纳(Alain Buisine)指出的“爱玛的心理易受他人影响且被动,她从来不是真正的自己:她臣服于所有异己性幻想。”(Buisine 47)一向强调写作“精确性”的福楼拜在小说中并没有刻画一个精确清晰的女性,反而塑造了一个神秘且多变的形象。而该形象在读者的阅读中更加幻化得多姿多彩。
四、读者眼中的包法利夫人
福楼拜曾自信地认为包法利夫人是个典型:“相信吧,所有我们虚构的都是真实的……此时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国二十个村落里痛苦、哭泣。(13)”(福楼拜,245)而读者通过阅读,把小说发现的“隐藏的东西”反照回自身,产生共鸣。福楼拜本人就在小说发表后收到一封来自读者的信件,勒鲁瓦·德·尚特彼小姐(Mlle Leroyer De Chantepie)感叹到“从一开始我就认出她,喜欢她,如一位早已相识的朋友。我将我自己和她的经历等同起来,以至于觉得这是她,也是我。(14)”虽然福氏本人反对这种爱玛式的小说阅读方法,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部作品的伟大魅力之一来自于包法利夫人的世界性。每个人或多或少地在其身上认出了自己,可怜同情或批评警醒。而不同读者的阅读由于受到其自身期待视野以及阅读背景的影响,会塑造不同的“包法利夫人”。
小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它并没有成为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外国作品“复译”高潮的来临,小说在几年间出现了二十多个译本,其中不少著名翻译家为塑造包法利夫人的中文形象而废寝忘食。这些不同的译本,让包法利夫人在中国的形象更加多元。
“包法利夫人”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从福楼拜的文本中走出来,带着变幻着的并不清晰的形象,在文学、戏剧、影视领域继续进行形象再造。法国罗杰·达科斯塔(Roger Dacosta)出版社就曾收录了多篇“包法利夫人”的文本再造:《包法利夫人的化身》(15)。陈亚亚将她的大学生活片段集锦为《复旦的包法利夫人》,香港著名戏剧导演林奕华把台湾的名媛们搬上舞台,港台京三地阐释《包法利夫人们》的美丽与哀愁……这些包法利夫人们都和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保持着割舍不断的联系,她们都是包法利夫人的“另一个”。而正如彼西纳说的“爱玛,就是他人”(16)。她永远无法找到最恰当的化身。福楼拜创作的不是一个诺曼底小城市的可怜少妇,而是一群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缩影。正如李健吾先生所说:“有多少怨女从挨骂认出自己!……他的作品却怎么钻进泥的灵魂!”(17)
包法利夫人,她正如小说开篇夏尔的帽子,神秘却真实。小说的社会原型已不重要,究竟谁画出来的更加准确也没有多大争论的意义。她的力量就在于,她在福楼拜笔下真实地存在着,在读者的阅读中真实地存在着,不管带着怎样的妆容。
福楼拜曾说过:“人像食品……我呢?我像一块软而发粘的、臭烘烘的通心面奶酪,你得吃上多少次才能培养这种爱好。最后你终于喜欢上它了,可那只能是你经过数不清有多少次它把你胃搅得想呕吐以后。”(18)小说刚诞生的时候带着官司的味道,包法利夫人也像臭烘烘的奶酪一样,而一百五十年之间对它的品尝却让我们越来越迷上这位神秘的夫人。在学者、评论家以及普通读者的阅读中,包法利夫人的形象无论是否更加清晰,都离不开对福楼拜文本的细读。谁是包法利夫人?永远有无数的答案自圆其说而又无法排除其他的可能性。福楼拜曾这样点评他所欣赏的作家:“没有一个伟大的天才曾总结过,没有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曾总结过,因为人类本身一直处于运动中,不做总结……生命是个永恒的问题,历史也是,一切都是”。(19)(Flaubert,336-337)这位克鲁瓦塞(20)的隐士,凭借着包法利夫人不定却又真实的形象,也在文学史上跻身于“伟大的天才”之间。
注释:
①小说于1856年10月1日起在《巴黎杂志》上分六期连载,发表时虽然已有多处删节,但当时帝国检察署还是对福楼拜和杂志提起诉讼,指控《包法利夫人》“败坏公德,亵渎宗教”。
②诸多中译本的译序中介绍了该创作来源,如许渊冲在其译本序中告诉读者“《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取自现实”,并粗略地介绍了德拉玛一家的故事,包法利夫人即德拉玛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德尔芬,参见福楼拜著,许渊冲译:《包法利夫人》,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健吾译本的序言中,艾珉也提到“他接受路易·布耶的建议,决定以德拉马尔的故事为素材,创作一部刻画当代外省生活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参见福楼拜著,李健吾译:《包法利夫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郑克鲁在漓江出版社译本的译序中也提到该轶闻:“德拉马尔·赫阿丽丝-德尔菲娜的故事构成了《包法利夫人》的蓝本”。参见福楼拜著,宋维洲译:《包法利夫人》,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年。已故福楼拜研究著名学者李健吾先生也在《福楼拜评传》中点出该故事:“见于当时鲁昂报纸”。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桂林:广西师范出版社,2007:43。
③Gothot-Mersch Claudine,La genèse de Madame Bovary,Paris,Librairie José Corti,1966.作者后成为法国七星诗社文库福楼拜全集的主编之一。
④Geoffrey Wall,"Who was the real Madame Bovary?" Introduction of Penguin Classics' edition of Madame Bovary,2002,tanslated by Geoffrey Wall.
⑤文中福楼拜书信引用,均出自法国伽俐玛出版社1998年版福楼拜《书信集》,由笔者自译。斜体字参照原版标出。1857年3月30日致勒鲁瓦·德·尚特彼小姐。
⑥杜刚在回忆录中强调,采用德拉玛一家故事做蓝本是福氏另一好友布耶的建议,然而福楼拜和布耶两人都没有亲自证实过这一说法。
⑦1857年3月30日致勒鲁瓦·德·尚特彼小姐。
很多读者习惯把福楼拜和女主人公爱玛联系起来,作品问世后不久波德莱尔的评论中就指出爱玛的“男性特征”;也有学者参考福楼拜和柯莱女士的恋爱经历,认为他是文中的罗道尔夫;也有读者则从税务员比内身上看到了福楼拜暗藏的身份。
⑧福楼拜憎恶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曾编过一本《成见辞典》(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cues)。
⑨转引自Pierre-Marc de Biasi,“Madame Bovary,c'est qui?” Dans le magazine littéraire,novembre 2006,p.53。
⑩1859年11月致阿梅利·波斯凯。
(11)参见法文版本,因为大部分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在文字上做了阐释,进行添加,使“包法利夫人”只指代爱玛本人。
(12)文中涉及中文译名和文本引用,均出自周克希译本,福楼拜著,周克希译:《包法利夫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13)1853年8月14日致路易斯·柯莱。
(14)转引自Jacques Neefs,《Une revolution dans les lettres 》,dans le magazine littéraire,novembre 2006.pp.30-31.
(15)Voir les incarnations de Madame Bovary,Paris:Ed.Roger Dacosta,1933.
(16)Voir Alain Buisine,《Emma,c'est l'autre 》,dans Emma Bovary,Paris:Ed.Autrement,1997,pp.26-51.
(17)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桂林:广西师范出版社,2007:6。
(18)转引自:朱利安·巴恩斯著,汤永宽译:《福楼拜的鹦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2。
(19)1857年5月18日致勒鲁瓦·德·尚特彼小姐。
(20)Croisset,福楼拜的家乡,福楼拜在那里度过了一生大部分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