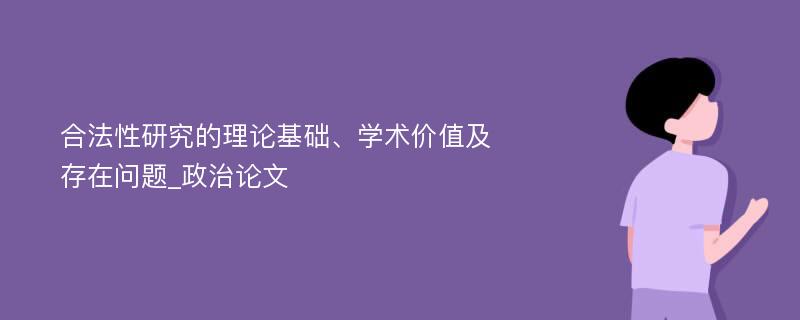
论合法性研究的依据、学术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法性论文,学术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关合法性的研究虽在本世纪就由西方学术界提出,但在中国大陆学者中引起关注的时间并不很长,因此对于这一研究所涉及到的一些前提性的问题还来不及加以审视与批评。比如,合法性研究的提出有无客观上的依据,其学术价值何在?它会不会是一个“假问题”?尤其面对着学术研究本土化的趋势,像合法性这样一个似乎是“西方话语”中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的语境中有无研究必要和可能?西方合法性研究究竟提供了哪些可资借鉴的成就、存在着哪些不足?如果没有对这类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就很难确立合法性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避免盲目性。职此之故,本文尝试着提出这些回答加以讨论,以就教于方家。
一、合法性研究的提出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黄宗羲曾在《明夷待访录》中指出:三代以后特别是秦汉以后的帝制时代虽然形式上有法(制度、法律),实则是“无法”,是“非法之法”。为什么还会有“非法之法”?他的理由是,这些制度、法律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利欲之私”,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显然,黄宗羲在这里提出了含义不同的两种“法”:一种是现存的法律、制度,另一种是合乎黄宗羲“天下为公”标准、即合乎道义准则之“法”。如果不符合人们的道义标准,一种法律制度尽管被制定出来、在形式上是存在的,但实质上却是“非法”的。法国当代著名法学家雅克·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也曾指出:“不正义的法律不是法律”,与黄宗羲此说可谓不谋而合。这样,黄宗羲实际上就触及到了当代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合法性问题。
所谓“合法性”概念是对英文“Legitimacy”一词的意译,也有的学者将其译为“正当性”或“正统性”。这一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研究领域是由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本世纪初最先提出的,尽管人们对这一观念所作的具体定义不尽相同,但对其基本含义还是存在着约定成俗的一致认识。从直观的语义上说,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注:参见(美)杰克·普拉诺等著:《政治学分析词典》“合法性”条,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也就是说,对于合法性的含义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从政治统治的主体一方说,合法性意味着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必须具有的属性和功能,即必须有能力使被统治者认为这种统治是“应当服从”的,从而获得被统治者哪怕是最低限度的认可或自愿服从;从统治客体的角度看,合法性意味着被统治者基于某种价值、信念而认可、支持某种政治统治,将其视为“正当”或“应当”的。可见,合法性概念最核心的含义是指人们内心所认为的“合道义性”、“正当性”或“适当性”,从而所谓“合法的统治”、“合法的权力”也是指人们内心“认可”的统治与权力,因而它和人们通常理解的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是不同的。正象黄宗羲的上述观点所显示的那样,统治者根据自己制定的法律进行统治,这在形式上固然于法有据(合法),但如果人们在内心里根本就不认可这些法律制度,觉得它们本身就是“不公正”或“不适当”的,则从某种价值观念或道义原则来说,这种统治在人们心目中就可能是“不合法”、即缺乏合法性的。所以,在英语的语境当中,人们用Legality表示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而用Legitimacy表示由认可或自愿服从而产生的统治合法性。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学术界对于Legitimacy一词尚无公认的理想译法,“合法性”译法也许只是一种差强人意的选择。除使用较多的“合法性”一词之外,海外华人学者也有采用“正当性”译法的。(注:参见彭怀恩:《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台湾风云论坛出版社1992年版,第85—88页;陈璋津译、G ·泰尔朋著:《政权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政权》,台湾远流出版社1990年版,第五章第二节。)在日本的学术界,则是使用“正当性”或“正统性”这类日文汉字来翻译Legitimacy,有的则是同时使用“正当性”和“正统性”的译法。(注:参见(日)加藤新平:《近代国家论》第一部《权力·国家权力的正统性》,弘文堂1961年版,第34页。)从字面意义上看,“合法性”确实容易和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合法”相混淆。本文采用这种译法,主要是这一用法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已经比较普遍,合法性一词已经有了约定成俗的、相对固定的含义。遍检我国80年代中期大量译介的西方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术名著,大都使用了“合法性”这一译法,因而具有学术对话上的方便。另就语义而言,“合法性”意义上的“法”在汉语语境中原本就有“标准”、“规范”乃至“正义”、“公道”等含义。如《慎子·威德》篇说,“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管子·任法》篇也说,“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另外《词海》(1989年版)关于“法”的解释除有“法律”、“标准和规范”之外,并指出“法在世界各国语源上都兼有公平、正直、正义等含义”。从这一意义上说,使用“合法性”一词以表明Legitimacy所含“合乎某种正当标准”之义,应是比较妥贴的。
正如一位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自从韦伯以来,合法性这一概念日益为学术界广泛接受,“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一个关键术语”。(注:王列:《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职能》,载《文史哲》1994年第6期。)如韦伯以后的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希尔斯、 埃森斯塔得,政治学家李普塞特、伊斯顿、达尔、阿尔蒙德、亨廷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哈贝马斯、葛兰西、卢卡奇、阿尔都塞、波朗查斯等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时和兴:《关系、限度、制度: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与社会》第六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俞吾金:《意识形态论》第八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胡伟:《合法性问题研究:政治学研究的新视角》,载《政治学研究》1996年第1期。)受到这一学术潮流的影响, 近年来这一问题也日益受到我国研究者的注意。在涉及到政治权力和政治统治问题,以及国家理论问题时,人们使用合法性概念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在历史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这一考察角度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尽管人们在合法性的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但是从韦伯关于合法性概念的理论元点出发,至少对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任何政治统治要想得以维持,不仅需要通过暴力恐怖所带来的强制性服从,还需要社会成员起码限度的自愿服从,即:起码得有足够数量的人在心里觉得这种统治是“适当的”、“正当的”从而是“应该服从的”,政治统治才能维持下去。简言之,政治统治实际上是暴力和同意的统一体。
二、合法性研究的现实依据与学术渊源
理论说到底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合法性问题之所以会引起学者们如此浓厚的兴趣,从根本上说,就是由于这一分析视角能够与人们对现实的政治经验相吻合,能够让人们注意到政治统治中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即:政治统治中客观存在着的非强制性因素,或者说一定限度的自愿服从(同意)问题,因而它的提出是有其现实的客观依据的。因为,人类政治活动的经验和当代政治学研究的结果都已经反复表明,政治统治固然不能离开暴力或物质的强制力,但是纯粹的暴力强制只能带来短暂的军事性的“征服”,而不可能实施有效的统治。单纯的暴力强制首先需要持续地投入大量的镇压力量,即古人所谓“以威力起者,始终尚乎威力”,(注: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4《孝武帝》。)动用大量的资源,以惩治公开的反对者和威慑、监视其他社会成员。但任何社会具体承担统治或管理职能的人都是少数,处于被统治或被管理地位的人总是占多数,即使在最号称“警察国家”的地方也不可能每人身边站一个警察。所以,这种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最终会由于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为继。其次,统治者的身份及其所颁布的法律政策如果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在社会成员中缺乏罗素所说的起码的“情感度”,(注:(英)罗素:《权力论》,靳建国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或者说外在的法律规范不能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道德信念,不能由“他律”内化为“自律”,就会在实际生活中发生对法律、政策的“集体规避”的问题,使之形同虚设,统治也难以收到实效。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一些煊赫一时的军事征服性帝国之所以在历史的舞台上来去匆匆,倏忽兴灭,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未能获得起码的合法性,未能实现由“征服”向“统治”的转变。用当代学者殷海光的话说,没有合法性的赤裸裸的权力的确是非常“容易伤风的”。因此,人们对于一定政治统治的起码认可或自愿服从,即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治体系得以稳定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基础与前提。或者说,合法性是任何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的必然要求。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历史上的统治者们尽管不大可能有兴趣从事合法性的理论研究,但是直觉和政治经验却会使他们一般都懂得怎样争取人心,提高统治的合法性,节约政治成本。朱熹曾批评说,即使汉高祖、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也只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其实,这种“假仁借义”正透露了君主们谋求统治合法性的事实!由此而言,合法性实际上是政治统治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之一,是与政治统治的存在相始终的。尽管在不同类型的政治统治中,合法性容或有程度上的不同,但只要存在着政治统治,就会存在相应的合法性问题。
既然自有政治统治以来,合法性问题就是一直存在的,它就势必会在人们的观念中、在以往人们的政治思维中有所反映。尽管过去人们没有使用今天“合法性”或“Legitimacy的说法,但与之含义相接近的提法其实早就存在。如亚里士多德就根据是否“旨在照顾全邦的共同利益”的标准,把政体区别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3页。 )他所谓的“正宗政体”,就是根据一定的正当、正义标准(是否顾及共同利益)所作的价值判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具有合法性的政体。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语境中,也有所谓“正闰”或“正统”说,即把合乎某种标准的王朝称为“正统”王朝,否则即为“闰”,亦即非正统王朝。尽管历代判断是否合乎正统的具体标准有所不同,但是根据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的研究结论,在“正统”一词中,“正之为义尤重于统”,即“正统”首先是指“正”,即合乎正义,其次才是指某个王朝具有一脉相承的统绪,因而它主要体现的是一种道德评判(Moral Jugment )。(注: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79—80页。)饶先生此论也颇合“正”字的原始意义:汉许慎《说文解字》即训“正”为“是也”。而《词源》“正统”条的解释则是,“旧称一系相承、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为正统,反之则为僭窃、偏安。”似未能全面、准确揭示“正统”含义。可见,“正统”一词就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王朝合法性。与这种“正统”说相对应,人们对于合乎某种“正统”、“正义”标准的君主则称为“正位”、“真主”、“真命天子”、“得天理之正”等等,实际上就涉及到君权合法性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现象是,自古及今,人们在探究历史上一些王朝兴衰、统治良恶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从“人心向背”方面找原因。这就是在从合法性角度考察政治统治基础问题,说明人们早已意识到了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尽管没有使用合法性这一提法,但也注意到政治统治中的非强制因素。从他们关于国家的社会职能问题论以及关于意识形态的作用的论述中,就不难看到这一点。如马克思就曾指出,和专制国家一样,资本主义国家“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性质所产生的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432页。 )恩格斯则说,“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只有政治统治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才能持续下去。不管在印度和波斯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而英国人则由于在印度忽略了经营灌溉这类“社会职能”,使得他们的统治不能和前人“一样具有某种合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522—523页。 )为什么阶级的政治统治必须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前提,为什么只有在执行了社会职能时它才能维持?这固然是因为,国家只有履行了社会职能才能控制公共资源,进而达到对全社会的控制,最终实现统治阶级的利益。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政治统治“并不因此就成为国家的全部内容”,国家的社会职能并未失去独立的价值。(注:参见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虽然国家的社会职能首先是服从政治统治需要的,但是国家通过社会职能所提供的却是公共服务,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所提到的“经济职能”和“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762—763页。)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结论看, 这种公共职能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其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一般不具有使用上的排他性。即:由于国家在形式上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力量”,它通过公共职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如安全、秩序、以及水利交通事业等在客观上是可以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个人消费或享受这些产品不会有损于其他人的消费,因而不能也无须由统治阶级所独占。这样从效果上看,国家社会职能的实现就有可能在客观上反映被统治阶级的某些愿望和要求,从而使被统治阶级在一定限度内将国家的政治统治默认为是具有“合理性的”而加以接受,并将一定的统治者视为其利益的代表。也只有当国家执行了其社会职能、获得被统治阶级一定认可之后,政治统治才能“持续下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术语说,国家执行其社会职能,客观上反映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也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关于法国农民政治态度的著名分析也有助于对上述思想的理解。他指出,由于农民的生产方式使之互相隔绝、分散,不能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677—678页。)可见, 正是由于作为主宰者实即统治者的专制政府有可能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履行社会公共职能,客观上有可能成为农民利益的保护者,所以能够被农民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表,受到农民的支持。换句话说,这也就意味着专制政府在农民那里具有一定的统治合法性。
马克思在谈及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时指出,“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个人”,往往把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抬出来作为生活原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和意识,一则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492页。)而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100页。)沿着这一思路,恩格斯把国家视作“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卷,第253页。)列宁更加明确地指出,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都需要两种职能,即暴力职能和牧师的职能。牧师的职能就是“安慰被压迫者,”使之“忍受这种统治”;或者一方面采用暴力的方法,一方面采用“欺骗”、“自由主义”的或“让步”的方法。(注:参见《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478页;第3卷,第43页;第2卷,第276—277页。)显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单纯的暴力职能并不能建立一个阶级的有效统治,还必须借助于意识形态的“教化”、“粉饰”或“欺骗”功能,使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人们的观念中“普遍化”、“合理化”和“道德化”,在被统治阶级中获得起码的自愿服从,才能达到这一目标。从合法性的研究角度来看,这也就是取得统治合法性的过程。这样,经典作家们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合法性研究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意识形态在统治合法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问题。正是在马克思上述思想的启示下,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如卢卡奇、葛兰西等人才在研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时,合乎逻辑地把视线延伸到统治合法性问题。
概言之,合法性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语言认识与研究合法性问题,在中外思想史上可谓渊源有自,因而也是当代政治学、法理学与社会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合法性研究的学术价值
既然合法性问题是政治统治中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则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无疑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那么对于政治学来说,合法性研究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究竟有哪些方面的学术价值?由于目前国内政治学论著对于合法性问题大都处于输入和借用西方学者成果阶段,从而对于这些前提性的问题缺乏必要的反思与审视,这里也不得不略加辨析。
首先,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必然推动对意识形态与政治统治相互关系问题的深入研究,深化人们对国家职能内涵的认识。谈到意识形态,以往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多少会产生误解,似乎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用以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批判时的一个术语。而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却让人看到意识形态问题在政治分析中的意义。我们知道,合法性这样一种政治现象是和社会成员的合法性观念直接相联系的,或者说,合法性首先是人们头脑中合法性观念的直接产物。而合法性观念亦即人们关于何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是“应当的”、“值得服从的”一类认识,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的标准或规范又直接来自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借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泰尔朋(G.Therborn)的话说,正是通过意识形态对政治主体的“建构机制”,社会成员才得以形成这些关于合法性的价值规范。也正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一定时期的统治阶级和国家政权总是千方百计地宣传和灌输对其有利的意识形态,把操纵意识形态作为统治合法化的主要手段。这样,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必然引导人们追寻意识形态问题,谈到合法性问题也必然要涉及到意识形态在政治统治过程中的地位和功能问题。反过来说,通过对意识形态在统治合法化过程中的研究,也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和清楚地把握和描述政治统治过程。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当中,与合法性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如卢卡奇就曾在《合法性和非法性》一文中这样写道:“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说,合法性和非法性概念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向组织起来的权力这个一般性的问题上,并且最终引向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上。”(注:(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王伟光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从而, 伴随着合法性概念日益成为现代政治分析中的一个“关键术语”,意识形态研究也逐渐成为现代政治分析中的重要一环,这无疑会拓宽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丰富政治理论的内涵。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意识形态研究复兴”迹象,在某种意义上就说明了这一点。(注:参见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八章“西方意识形态研究的复兴”。)另外,以往国内学术界一般把国家职能分为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或公共职能),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涵盖了文化意识形态职能,但是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提出来。合法性研究则使人更加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在政治统治过程中(亦即合法化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利用文化意识形态谋求统治合法性是国家统治活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而意识形态职能、或者说合法化职能其实是国家职能中的重要方面。这样,合法性研究的提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国家意识形态职能的重视,必然会促有关国家职能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国家职能理论的进一步丰富。(注:参见王列:《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职能》,载《文史哲》1994年第6期。)
其次,合法性研究命题的提出,也会加深人们对政治权力具体运作情况的认识,丰富对政治统治内涵的理解。合法性研究使人们进一步看到,政治权力的运行固然离不开暴力强制,但又不仅仅是一个暴力强制过程,它同时还是一定国家政权谋求统治合法性过程;政治统治是以一定阶级的经济统治地位为基础的,但政治统治也不仅仅是经济力量的统治,它还必然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霸权(hegemony),即经济统治最终只有通过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宰制”才能实现。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立场上看,透过对合法性问题的研究,人们就可以更清晰、更深入具体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借助经济上的优势,以国家机器强制力为后盾,利用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功能造成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的从属—驯服心理,最终实现统治的全过程的。正如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波朗查斯所指出的,“用政治机构和机构的合法性,我们可以表明它们对于一种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关系。合法性里面特别是包括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特有的政治影响。”(注:(希腊)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2页。)事实上,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正是沿着马克思当年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思想,又借助合法性问题的分析角度,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统治关系的。
合法性问题的提出,对于推动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问题的研究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一研究的实质性结论在于,任何一种政治统治要想维持其稳定性,必须以起码程度的“人心归向”、即必须以获得起码程度的合法性为前提。这样,合法性问题,实质上也就是人心归向问题、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统治权的认同问题就成了考察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问题的重要因素。沿着这样的思路,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思索合法性危机(合法性的丧失)与政治危机、政治不稳定以及政治变革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统治者如何采取合法化措施以巩固统治等一系列问题。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合法性”也就成了当代政治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此外,合法性研究的提出,也会促使人们用一种更为复杂、全面的眼光看待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克服那种机械简单、如影随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思维模式,充分认识一个民族的政治、法律文化、心理习惯、价值规范系统等方面的相对独立性与重要作用。
总之,合法性研究确实拓宽了政治学的研究领域,启发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纵深思考。
四、问题与不足:对现有合法性研究的检讨
见于学术界对韦伯这位合法性研究开创人物的普遍“敬畏”心理,一位西方学者曾在他的书中自我告戒,“不让自己对韦伯成就的敬畏蜕化为崇拜。”(注:见(英)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中的《作者序言》,刘东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让我们也以同样的态度,从马克斯·韦伯开始,简要回顾一下几位有代表性的西方学者的合法性研究。
我们知道,韦伯是在研究政治统治过程中人的“服从”行为时,提出合法性问题的。在他看来,人们服从某种政治统治的动机可能是多方面的,如可能出自习俗、畏惧惩罚的情绪、物质利害关系的考虑等,“除了这些因素之外,一般还要加上一个因素:对合法性的信仰。”不过韦伯强调,没有这种基于合法性信仰的服从、单凭其他动机“不可能构成一个统治的可靠的基础”,“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信仰。”(注:(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上卷第238—239、240页。 )这就是说:第一,基于合法性信念的服从动机是和其他动机(利益、习俗等)并列的一种单独的变项,是和利益考虑无关的,如同一位韦伯研究者所说,这种服从“是出于自发,而不是出于谋划”,是一种乐于给予的服从”;(注:前引《马克斯·韦伯》第107、110页。韦伯也这样解释他所谓的服从:“服从者的行为基本上是这样的进行的,即仿佛为了执行命令,把命令的内容变为他的举止的准则”。见《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40页。)第二, 这种基于合法性信念的自愿服从是“构成一个统治的可靠的基础”,因而在各种服从动机中是更加重要、具有最终保障作用的方面。(注:参见(美)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张华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第87页注25。)这一点也是和他的统治定义相吻合的。从狭义的理解和界定出发,韦伯把统治解释为“建立在一种被要求的、不管一切动机和利益的、无条件顺从的义务之上”、“依仗权威(命令的权力和服从的义务)的统治”。(注:《经济与社会》下卷,第265页,另外参见269页。)就是说,基于合法性信念的统治和出于自愿的服从,实际上是政治统治的本质内涵与特征。
这种关于现实统治是“合法”的观念又是从何而来?依照韦伯的观点,由于合法性是实现统治的最重要条件,任何统治都会试图“唤起并维持”人们对它的合法性信念,其途径是根据统治的三个方面基础或“内在的正当理由”,即基于传统的神圣性、基于统治者个人超凡魅力、基于法理(依照某种公认的原则和法定程序)的依据,使被统治者要么因为对传统权威的崇拜,要么因为对统治者个人超凡魅力的崇拜,或者因为对合理的法律制度的信任与义务感,产生“应该服从”的合法性信念。于是在这三种合法性信念的基础上,政治统治获得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即传统型、超凡魅力型和法理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种相应的政治统治类型。(注:参见《经济与社会》上卷,第241—270页,下卷第277—278页;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6页。另外参考帕金对韦伯合法性理论的阐释,见《马克斯·韦伯),第112页。)
可见,统治的主要根据在于被统治者的合法性信念,这种信念与利益、经济因素无关。(注:从整个思想体系上看,虽然韦伯有时候也承认经济因素在政治统治中的重要性,但韦伯研究者们一般认为他还是更加重视精神观念方面。)这种仅从观念层面解释合法性根源的思考方法,实际上包含着这样一种循环论证:由于被统治者认为统治是合法的,所以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既然统治者能够继续统治,所以统治是合法的。(注:参见前引奥罗姆:《政治社会学》,第80页。)显然,从这种方法并不能说明合法性信念及合法性产生的真正原因。另一个与此相联系的问题是,韦伯把自愿服从作为政治统治的重要方面,似乎只要统治者“试图唤起”或“要求”合法性信念,被统治者就乐于响应,就会产生合法性信念,就使统治者当然地获得合法性。这显然是有意无意地淡化和掩盖政治统治中必然存在的暴力强制、阶级压迫、利益摩擦和价值观念冲突的事实,从而很难从常识和情理上令人信服地解决这样的困惑:为什么被统治者一定会心甘情愿地服从?难怪弗兰克·帕金不无讥讽地说:“韦伯最清楚不过地知道,政治制度史根本不是由奴才对其主子表示爱情的编年史”,却偏偏又把对统治的服从解释为“被压迫者们心甘情愿鞠躬唯谨地去协同行动”!(注:前引《马克斯·韦伯》, 第108页。)最后,基于明显的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相对主义色彩,韦伯主张各个民族在历史和文化方面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否定人类共有的价值观念和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规律。这使他“原则上反对任何在社会历史中寻求普遍法则的观念,甚至对普遍观念本身的价值也素有怀疑”,而主张祛除价值判断,反对归纳和演绎的方法,采用描述的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立场。(注:特纳:《探讨马克斯·韦伯》,收入前引韦伯《学术与政治》附录五,第187页; 另外参见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95页。)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在合法性分析中忽视甚至拒绝把握问题的确定、本质的联系,而停留于现象的描述和列举,造成许多理论上的矛盾和混乱。
继韦伯之后,西方许多有代表性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如人们熟知的李普塞、帕森斯、伊斯顿、阿尔蒙德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发展了合法性研究,使得这一研究更加丰富精致,对政治问题更有解释力,但他们和韦伯的基本立场和思维模式仍是相同的。如李普塞一方面注意到,某些情况下统治的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认为有效性“主要是指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长期持续的有效性,也可以给予一个政治系统以合法性”,似乎看到经济因素、国家满足社会成员需求的能力与合法性之间的相关性;一方面却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具体说明有效性究竟如何导致合法性。(注:参见(美)李普塞:《政治人》,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60页。)帕森斯认为合法性来自社会的价值规范系统,即社会的“制度模式根据社会系统价值基础被合法化”。(注:(美)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梁向阳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另外参见第144页。)他对合法性的概念界定以及对合法化过程的分析要比据称是“含混不清、不着边际”的韦伯明确、清晰,但同样也将价值规范视为产生服从动机的独立因素,而且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注:参见前引奥罗姆《政治社会学》第121、111—112页。 )伊斯顿从区分不同类型的支持着手分析了合法性问题。他认为,系统成员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可区分为特定支持和散布性支持,前者是因某种特定诱因,如利益和需求的满足而带来的支持,后者是一种与特定政策输出、成员的利益和需求无关的支持。散布性支持主要来自成员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信仰,即相信政治系统当局、政治系统的典则是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道义原则和是非感”的,因而觉得服从当局、尊奉典则的要求“是正确的和适当的”。正是这种基于道义和是非原则、而与特定利益需求无关的散布性支持,使政治系统产生了合法性。可见,他也是从合法性观念出发,去分析“散布性支持”、“无条件依附”和统治合法性的起源。(注:参见(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22、329、335页。)阿尔蒙德把合法性问题与政治文化、 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结合起来,对于合法性的研究贡献颇丰,但他关于合法性基础的看法也是直接来自韦伯,(注:(美)G·阿尔蒙德和G·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霈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6—38页。)从而,他对作为韦伯合法性理论前提的合法性观念起源问题也是不加质疑的。
总之,这种合法性理论只是将被统治者对于一种政治秩序是否赞同、认可作为合法性的标准,“而缺乏对大众的赞同、认可的依据的说明”;(注:陈炳辉:《试析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2期。)它封闭于政治统治与精神、 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方面,把合法性观念、信仰视为与利益、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无关的孤立因素,而没有把视线进一步延伸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更深层次。这样,问题似乎就应该停留在信念的层面止步不前,合法性观念成了一个无须追问的、既定的支点和前提,成了无源之水。这实际上还是马克思所批评的“观念统治着世界”的主张,并未说明合法性的实质、根源何在。
另外,西主马克思主义学者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合法性问题。如葛兰西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是通过暴力强制职能和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教育职能的有机结合实现其统治的,即资产阶级以暴力强制为后盾,确立其在文化、道德、知识方面的统治权,同时又借助这种文化统治权为其暴力强制提供合法性,使之成为被“积极同意的权力”。因此在发达国家中,夺取国家政权只是摧毁了统治阶级的外围堑壕,无产阶级革命的更主要目标是通过长久的“阵地战”,取得对于市民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以获得最终胜利。(注:参见邹永贤、俞可平等著:《现代西方国家学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六章第一节。)阿尔图塞则通过“再生产”概念说明,一个社会为了维持其存在必须再生产出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意味着劳动技能再生产,也意味着劳动者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顺从态度”即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后一种再生产是通过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等一系列“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实现的。从而意识形态是无法选择的、被强加于人的东西,人在不可避免地成为“意识形态动物”的同时,也就丧失了真正的主体地位。(注:参见前引王列:《国家的文化意识形态职能》;俞吾金:《意识形态论》第287—288页、第294页。)此外象哈贝马斯, 在克服传统合法性理论缺陷,以及创立自己系统的合法性理论方面确实贡献突出。但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得那样,他把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集中到合法性危机问题,而又将合法性危机最终归结为价值规范的危机,从而不可避免地回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夸大了文化、思想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注:前引陈炳辉:《试析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可见,他们一方面看到了合法性实际上是统治阶级利用意识形态宰制被统治阶级心灵、实行思想统治的结果,合法性观念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集中反映;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过于夸大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甚至把意识形态视为巩固国家政治统治的坚硬无比的“水泥”。和马克斯·韦伯等其他合法性研究者一样,他们也或多或少地抱持一种“社会一体”的假设:似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为全体社会成员一致接受,似乎只要统治者有了合法性“要求”,被统治者就会产生合法性观念,给予“积极服从”。(注:笔者此处有关“社会一体”假设的批评,来自于泰尔朋和帕金的启示,见前引泰尔朋:《政权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政权》,第102页; 帕金《马克斯·韦伯》,第112—113页。)于是,被统治阶级成了可以由统治阶级随意塑造的作品,他们的精神世界被浇铸成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水泥”,他们总是根据统治阶级强加给自己的、错误虚假的、于己不利的观念在思考和行动;从而在历史和社会政治发展中,大众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要求和意识,没有主体性、能动性,只是被动、“失语”的“意识形态动物”。这显然失之于简单化、绝对化。
结束语
综上所论,为了推进合法性研究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既要大胆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尊重他人的学术劳作,又要注意对其方法论前提进行必要的反思,冷静分析已有的研究在哪个层次上是合理的、有说服力的,在哪个层次上又存在着缺陷和不足、给我们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追加自己的劳动与创造等等。大体而言,恐怕今后应从两个方面寻找着力点。其一是利用已有的合法性研究成果具体分析中国的政治法律问题,不仅利用对中国问题的个案研究充实、印证已有的结论,更要运用自己独创性的研究去丰富它,矫正它。其二是在方法论原则上,迫切需要突破和跳出那种单就政治制度、思想观念角度讨论合法性问题的封闭的思维模式和认识层次,把目光延伸到社会的经济生活、物质关系层面,用一种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总体分析眼光去考察我们面对的问题,即: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利益机制方面把握合法性的实质与“原始起因”,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者相互关联的角度,整体地、全面地考察合法性问题。这也意味着必须坚持一种历史和逻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统一的思考方法,至于如何秉持以上原则,具体“重构”中国的合法性研究,则既已超出本文的主旨,又非笔者一人力所能及,自不能在此详论。
标签: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学理论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