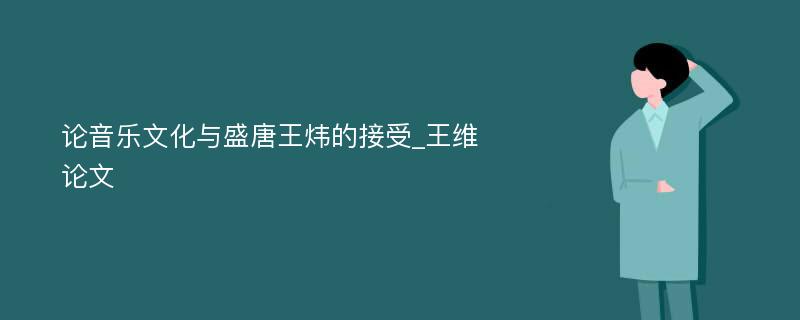
论音乐文化与盛唐王维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文化与论文,音乐论文,王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王维是唐代著名的诗人,近年来王维研究的热点之一便是王维的接受研究。但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其明显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对盛唐王维的接受关注极少,二是对唐代王维接受差异原因的解释,往往都聚焦在诗学上,视角的单一使研究很难有新的突破。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是源与流的关系,第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彻底理清,第二个问题自然很难有新的进展。有憾于此,本文将重点就盛唐王维的接受作深入考察。
提到盛唐王维的接受,人们不能不关注唐代宗。这不仅因为他贵为帝王的身份以及他对王维“天下文宗”的美誉,而且还因为他道出了王维在盛唐为人们所接受的主要方式。唐代宗对王维诗的论述主要见于《旧唐书·文苑传·王维》和《新唐书·文艺中·王维》,内容大致相似,主要是说他曾在天宝年间诸王宴会上听过王维诗的演唱,登基后仍不能忘怀。正是在他的关注下,王维的文集首次被朝廷辑集。唐代宗后来还就此颁布了《答王缙进王维集表诏》,其中有“诵於人口,久郁文房,歌以国风,宜登乐府”①。可见,王维的诗篇在唐代宗的心中就是歌辞,而且是具有典范意义的歌辞。由于唐代宗亲历过盛唐,此种评价又发表于登基不久,距离盛唐并不遥远,因而他的评价与盛唐王维的接受历史是一致的。可见,诗篇被选入乐曲中演唱,是王维在盛唐被人们接受的主要方式。关于这点,唐代其他人亦有叙述。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序》言及卢象有“始以章句振起於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於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②,既然将王维与卢象并提,那么“传贵”于“乐府”的自然也包括王维的诗。事实上,这一方式还贯穿于整个唐代王维的接受。如中唐刘禹锡《与歌者诗》与白居易《对酒诗》载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曾被选入《渭城曲》(亦称为《阳关曲》)中演唱;白居易《听歌六绝句·想夫怜》中注王维《和太常韦主簿五郎温汤寓目》被选入《想夫怜》中演唱。如晚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条中亦有“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等③。
因此要考察盛唐王维的接受,实际上就是要着力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王维的诗为何会在盛唐被视为歌辞广为传唱。而无论是歌辞还是传唱,都属于音乐文化的范畴,故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盛唐,揭示其音乐文化的特点,进而考察王维与它所形成的密切关系。
一、盛唐音乐文化的主要特点
盛唐音乐以宫廷为中心发展。这与唐玄宗有密切关系。唐玄宗不但酷爱音乐,而且精通音乐,会作曲、表演,甚至还会教授乐工。同时他崇儒任贤,十分注重发挥音乐在治人心、化民俗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故登基不久便组织朝臣对音乐进行了积极建制,内容包括:修定雅乐的乐章与歌辞、强化太常寺典礼作乐的传统职能、增设教坊与梨园等新的宫廷音乐机构、对民间音乐进行严格的约束等。另外,唐玄宗还大力鼓励皇室成员纵情声乐。《旧唐书·睿宗诸子·皇帝宪》载:“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④受其影响,盛唐皇室成员好乐、习乐蔚然成风。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逸文》云:“而诸主贵主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奏曲毕,广有进献。”⑤
这种好乐之风到了盛唐晚期又进一步波及权臣及一般朝臣。上有所好,下必效之。唐玄宗与皇室成员对音乐的热衷,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唐书·礼乐十二》:“帝又好羯鼓,而宁王善吹横笛,达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⑥但从现存史料来看,盛唐前期朝臣好乐之例并不多见。到了盛唐后期,朝廷会派遣或赏赐宫廷乐人给权臣以示恩宠。如唐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王鉷、杨国忠选胜燕乐,必赐梨园、教坊音乐,贵妃姊妹亦多在会中。”⑦权臣们因而留情声乐、热衷蓄妓。如李林甫,《旧唐书·李林甫》:“晚年溺于声妓,姬侍盈房。”⑧不仅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等亦如此,相关史料屡见不鲜。同时朝廷还增设节日,赏赐钱物,以此激励朝臣参与宴乐。如《新唐书·礼乐十二》:“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⑨,如《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开元十八年)二月,癸酉,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⑩结果一般朝臣也得以跻身于好乐之列,《新唐书·文艺中·孙逖》:“时海内少事,帝赐群臣十日一燕。”(11)盛唐后期,群臣留意声乐风气之盛,已经严重影响朝廷职能的正常运作,后人因此对之有过批判。如《旧唐书·穆宗》:“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则是物务多废。”(12)
好乐之风造成了两个结果:第一,上流社会和长安成了盛唐音乐的繁荣地。关于上流社会音乐的繁荣,我们从盛唐乐人李龟年兄弟的生活状况可以看出。作为当时著名的音乐家,他们不但活跃于宫廷,而且还出入于贵族之家,深受上流社会的青睐,过着富比王侯的奢侈生活。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歌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13)关于长安音乐的活跃,仅举中唐元稹《连昌宫词》就足以说明。此诗描述了盛唐的繁荣,其中有“力士传呼觅念奴,念奴潜伴诸郎宿。须臾觅得又连催,特敕街中许然烛。……李谟擫笛傍宫墙,偷得新翻数般曲”(14)。从元稹对这些诗句所作的注来看,念奴是长安青楼著名歌手,曾被唐玄宗频频召入宫廷中演唱;李谟是长安市井吹笛少年,因为隔墙听到宫廷新制的乐曲,随即翻唱,结果使此曲很快传遍长安,此举引起了玄宗的诧异,李谟差点因此被捕入狱。此诗所言及的长安乐人音乐水平之高超、长安追随宫廷音乐步伐之紧凑,足见盛唐长安音乐的繁荣。
第二,盛唐文士与歌辞创作关系空前密切。盛唐音乐以宫廷为中心发展,导致了大量新乐曲的产生,仅唐代崔令钦《教坊记》一书所载教坊乐曲就高达248首,而大曲又高达46首。这样一来,人们对于配合新乐曲演唱的歌辞需求自然会激增。盛唐宫廷乐人对旧歌辞已失去了演唱的兴趣,《旧唐书·音乐三》:“又自开元已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孙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通,相传谓为法曲。”(15)盛唐人对新歌辞的热望以唐玄宗的言论最具代表性。唐代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载玄宗在宫中与杨贵妃听音乐时,对高力士道“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16);如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中载玄宗对李龟年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17)。前者是说玄宗不再满足于纯音乐的欣赏,对歌辞有了期待,后者是说玄宗不再满足于旧歌辞的欣赏,对新歌辞有了期待。
在唐代,歌辞的来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依乐填词,一是选诗入乐。唐代元稹《乐府古题序》:“斯皆由乐以定词,非选调以配乐也。……后之审乐者,往往採取其词,度为歌曲,盖选词以配乐,非由乐以定词也。”(18)从相关史料来看,选诗入乐是初盛唐歌辞产生的主要方式,因而精于诗篇创作的文士自然成了初盛唐歌辞的创作主体。初唐文人虽然也会参与歌辞创作,但由于宫廷音乐仍然相对沉寂,且封闭发展,因而歌辞的需求并不是很多。这样一来,初唐文人参与其中的机会自然很少。从相关史料看,参与歌辞创作的文人在身份上往往很特殊,不是朝廷要员就是依附权贵的高级文士。前者如《旧唐书·音乐二》中受旨参与《破阵乐》歌辞创作的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药;后者如唐代孟棨《本事诗·嘲戏第七》中所载的应旨创作《回波乐》歌辞的沈佺期与崔日用等。到了盛唐,情况大不一样。不但官僚中的下层文士会普遍地参与歌辞创作,连布衣文士也频频涉足于此。前者如元德秀,是鲁山令,《新唐书·元德秀》载朝廷曾在东都组织大酺,曾“命三百里县令、刺史各以声乐集”(19),结果他创作了《于蔿于》,让乐工们演唱。后者以康洽最为著名。他曾经活跃于长安与洛阳两地,所作歌辞在宫廷和上流社会广为传唱,李颀《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戴叔伦《赠康洽老人》、李端《赠康洽》及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等对他多有述及。从李端《赠康洽》:“同时献赋人皆尽,共壁题诗君独在”(20)来看,在盛唐,文士们对歌辞创作持有普遍的热情。
在盛唐,歌辞创作已经融入文士们的日常生活。如《旧唐书·文苑中·王澣附王浣》:“登进士第,日以蒲酒为事。并州长史张嘉贞奇其才,礼接甚厚。(王)浣感之,撰乐词以叙情,于席上自唱自舞,神气豪迈。”(21)同时,歌辞创作还成为他们实现入仕理想的捷径之一。如李颀《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西上虽因长公主,终须一见曲陵侯。”盛唐很多诗人都曾被卷入其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旗亭赌唱”中的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等以外,连倍受后人推崇的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也不例外。任华《寄李白》:“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22),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文场供秀句,乐府待新词”(23)。
同时,盛唐音乐中俗乐尽管迅速繁荣,但雅乐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由于朝廷对民间音乐实行严格的打击和限制政策,故盛唐民间俗乐相对沉寂。在宫廷,前文已言,唐玄宗登基不久,便先后设立了教坊与梨园等新的音乐机构,以负责宫廷俗乐的表演与管理,故俗乐得到了迅速的繁荣。但是由于朝廷执行的是尊儒重礼的文化政策,所以俗乐虽然有了空前的发展,但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雅乐。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如盛唐宫廷音乐表演的顺序,一直是雅乐在前,俗乐在后。《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府·县散乐、杂戏;又以山车、陆船载乐往来;又出宫人舞《霓裳羽衣》;又引犀象入场,或拜或舞。”(24)又如在盛唐宫廷乐人中,连最富有娱乐性的俳优也保持着讽谏帝王的传统职能。唐代高彦休《唐阙史》卷下“李可及戏三教”:“开元中黄幡绰,明皇如一日不见,则龙颜为之不舒。而幡绰往往能以倡戏匡谏者。”(25)
对此,我们还可以从盛唐胡乐的发展状况看出来。不少学者依据中唐的一些诗篇,认为胡乐在盛唐已经一统天下,由于胡乐隶属俗乐,如果这种结论成立,那么俗乐在盛唐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唐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创作者会根据特定的创作动机而作出虚构、夸张等艺术处理,因而它们所言的盛唐音乐发展状况与真实的历史并不是完全的等同关系。虽然胡乐在唐代宫廷中一直存在,如九部伎、十部伎中就有好几部是胡乐,但它们只是作为以华治夷、华夷和谐相处的象征而存在,仅在一些仪式场合如祭礼、朝会等表演。在盛唐绝大部分时间里,胡乐的发展状况依然如此,仅是仪式性的、政治点缀性的。此时,胡乐一旦作为艺术在朝廷之上进行表演,上流人士就会高度警惕,并强烈抵制。如唐代郑棨《开天传信记》有:“西凉州习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上召诸王便殿同观,曲终,诸王贺,舞蹈称善,独宁王不拜”(26),面对玄宗的疑问,宁王的回答仍然是严华夷之辨的儒家传统言论。直至盛唐晚期,胡乐才获得与其他音乐样式同等的、在朝堂之上表演的合法身份。《新唐书·礼乐十二》:“开元二十四年,升胡部于堂上。……后又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明年,安禄山反,凉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27)即便如此,它仍然要面临着被雅化的命运,这包括更改它们的乐曲名称,以及改造它们的乐章等。如唐代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唐玄宗看到龟兹曲名后,“深恶之,……遂令诸曲悉改名”(28);如《霓裳羽衣曲》,最初是由西凉节度使杨敬述进献,但它进入宫廷后,玄宗对它进行了改造。宋代王灼《碧鸡漫志》卷三记载:“西凉创作,明皇润色,又为易美名。”(29)关于胡乐在盛唐社会仍然处于被压制、被排斥的地位,泼寒胡戏的被禁最足以说明。此戏源于外域,是一种载歌载舞的音乐艺术,初唐时曾在市井中一度流行,后来因为中宗的喜爱而受到朝廷的重视。但是在盛唐初期,当朝廷因为吐蕃入朝而打算表演此戏来作接待,结果张说认为不合礼仪,上书要求禁止,从此泼寒胡戏便消失在公众视野中(30)。
这对盛唐歌辞造成了重要的影响。雅乐占主导地位,必然会重视歌辞的内容,要求它们在国民的精神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以助帝王治政;俗乐的繁荣发展,必然会重视歌辞的形式,要求它们带给人以纯粹的艺术享受,以助娱乐。这样一来,盛唐歌辞必然会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均有积极的追求。由于选诗入乐是初盛唐歌辞产生的主要方式,故盛唐歌辞的这种特点,时人常常用评价诗的术语概括之,即“声律”与“风骨”兼求。对此,我们可以从芮挺章在天宝年间所编订的《国秀集》看出来。人们一般将《国秀集》视为诗篇选集,实际上它同时也是一部歌辞集,因为编者选诗旨在将它们入乐演唱,《国秀集·序》:“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31)从芮挺章述及当时有识之士回顾诗史时用“绮靡”与“风雅”等术语,并对于当时“虽发词遣句,未协风骚。而披林撷秀,揭厉良多”之现状不甚满意,以及最终所选出诗篇等来看,他显然致力于兼顾两者。
对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在当时的宫廷及上流社会广为传唱的歌辞看出。其一是李白所创作的《宫中行乐词》10首和《清平乐》3首,这些都是李白任翰林学士时为宫廷创作并被乐人传唱的歌辞,分别见载于唐代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与唐代李浚《松窗杂录》。虽然李白倡导诗歌的“大雅”精神,以复古自居,对齐梁以来的近体诗持批评态度,但是当他奉旨进行歌辞创作时,却没有融入这些理念。首先在体裁上,它们都是近体诗。如《本事诗·高逸第三》:“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律度对属,无不精绝。”(32)其次,在内容上,它们所描写的是李、杨二人身处深宫歌舞升平的快乐生活,以及对杨贵妃美貌的颂扬。最后在技法上,主要以赋为主,讲究辅陈,较少运用比兴,并没有寄托深远的情思。玄宗对李白的这些歌辞给予了褒奖,如《清平乐》3首被誉为“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可见,它们擅长在“声律”上。
其二,元德秀所创作的《于蔿于》。前文对之已有讲述。从所载史料来看,此次大酺热闹非凡,元德秀作为带队的县令,最终能够吸引玄宗的关注,并获得赞扬,并不是所带乐队阵容的庞大或音乐的新奇,而是“乐人数十人”所演唱的歌辞,这些歌辞为元德秀亲自创作,从史料中盛赞元德秀“善言辞”以及玄宗称赞这些歌辞是“贤人之言”等来看,这些歌辞应当是内容朴素、思想纯正,具有感动人心的强大力量,故它们擅长在“风骨”上。
其三,大家所熟悉的“旗亭赌唱”中的4首歌辞,具体见于唐代薛弱用的《集异记》“王之涣”条(33)。虽然文中将王之涣的胜出描述成由最出色的宫廷乐人演唱的结果,可仔细分析会发现他胜在诗的“风骨”上。史料中所提及的诗有4首,均为绝句,其中王昌龄有2首诗,1首是送别诗,1首是宫怨诗,高适有1首,是羁旅诗,这些诗篇所描写的均是唐人生活的一个侧面,并没有太多触及当时的朝政。但王之涣的诗却不同,它表面上写边塞生活的一个场景——将士吹笛,却由此展开了丰富的联想,继而写到朝廷的皇恩不及边疆将士的现状,并以笛声烘托出将士们内心哀怨的情怀,因而最终表达的是对皇帝及朝廷的委婉讽谏。其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显然运用了传统的比兴手法,以“春风”喻皇恩。王之涣的这首诗显然是儒家诗道精神的践行,极富“风骨”。其实,王之涣之所以在盛唐诗人中非常独特,也是因为这点。唐人靳能在《唐故文郡文安县尉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有:“尝或歌从军,吟出塞,曒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至夫雅颂发挥之作,诗骚兴喻之致,文在斯矣,代未知焉。”(34)由此则史料可知,宫廷乐人口中所传唱的均为绝句,而最优秀的宫廷乐人演唱的是极富“风骨”的绝句。故在盛唐,那些“格律”与“风骨”兼擅的诗篇最受欢迎。
总结上文,盛唐音乐文化的主要特点如下:上流社会与长安成为盛唐音乐的繁荣地,盛唐文士与歌辞创作关系空前密切;盛唐歌辞呈现出“风骨”与“声律”兼求的发展走向。
二、王维与盛唐音乐文化的契合
以上就是王维所处时代的音乐文化背景。受其影响,盛唐很多士人纷纷涌至长安,出现在上流社会的各种宴会场合,进献歌辞,以企博得时人的关注和赞誉,或以此寻求入仕的捷径。王维处于其中,如鱼得水,这与他的音乐才华、社会活动及诗篇特点等密切相关。
首先,他有着杰出的音乐才华。他不但会演奏琵琶,而且还会作曲。如唐代薛弱用《集异记》“王维”条有“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闲音律,妙能琵琶”(35),并记载王维是带着自创的乐曲《郁轮袍》出现在贵公主的宴会上。王维对音乐的精通,有一个事例最能说明,这则史料曾被多则唐宋笔记小说反复转载过。说他曾看到一幅奏乐图,断言画中所表演的是《霓裳羽衣曲》,而且还说出了表演的具体章节,结果好事者验之,《旧唐书·文苑传·王维》:“一无所差”(36)。《霓裳羽衣曲》是盛唐宫廷著名的法曲,最初由地方节度使进献,后来在唐玄宗带领下,宫廷音乐机构对之作了艺术改造,因而水平极高。王维对此如此熟悉,足见他在音乐方面惊人的造诣。另外,王维还曾做过大乐丞,后因私舞黄狮子一案被罢免。大乐丞,是唐代专门负责朝廷礼乐表演的太常寺中的一个官职,王维能够得到它,极有可能与他的音乐才华有关。王维对于自己的音乐天赋亦颇为自得。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10卷载他作诗言:“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捨余习,偶被时人知。”(37)这为他参与当时的音乐活动提供了先天条件。
其次,他一直生活在长安、且与上流社会交往密切。从陈铁民《王维集校注·王维年谱》来看,王维从十五岁离家赴长安准备科举到安史之乱爆发,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仅九年离开过长安,其中被贬到济州与淇上任职七年、到河西节度使幕府任职一年、出使岭南一年,可见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长安。王维在长安一直与上流社会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旧唐书·文苑传·王维》:“维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昆仲宦游两者最,凡诸王驸马豪右贵势之门,无不指席迎之,宁王、薛王待之如师友。”(38)这种密切的交往不仅是在他入仕以后,此前他为布衣青年时,就受到过上流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最为时人津津乐道的是与岐王的交往。唐代薛用弱《集异记》载歧王在科举考试前曾为他出谋划策,使他博得权倾一时的贵公主举荐,最终在科场上春风得意。虽然这则史料作为笔记小说可能有虚构夸张的成分,但是从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对王维诗篇所作的编年来看,王维在开元年间所作的诗篇最少有3篇与歧王有关,它们是《从歧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足见他与歧王交往的密切。
前文已言,长安是盛唐音乐发展的繁荣地,上流社会又好乐成风,因而王维的社会活动使他一直居于盛唐音乐活动的中心。又由于他精通音乐,故处在其中自然非常活跃。又由于“选诗入乐”是盛唐歌辞产生的主要方式,而王维又精于诗篇创作,故他的诗篇自然易为乐人们所熟悉。相关事例颇多,现略举一二。如《息夫人》,宋代王谠《唐语林》卷6载它曾被选入《簇拍相府莲》中进行过演唱。从唐代孟棨《本事诗·情感第一》对此诗撰写过程的叙述来看,它最初产生于宁王的宴会,起因是宁王将一位卖饼者的妻子夺走,但该女子不能忘怀于丈夫,一年后当她与丈夫重逢时仍伤心不已,于是“(宁)王命赋诗”,王维在众文士中先作成诗篇。故最初见到王维这首诗的除了宁王、众文士、卖饼者夫妻以外,还有宁王的宠妓,“宁王曼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隔障歌”条有“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39),并载“外客”之一的李白还向宁王请求将最出色的乐妓宠姐给大家演唱,宁王欣然同意,结果众文士因此大为欢快。由此可推断,在《本事诗·情感第一》这条史料中,“绝艺上色”的宠妓中定然包括乐妓。故王维的这首诗也是在第一时间为乐人们所知晓的。
再如王维的《相思》与《失题》。唐代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载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曾在宴会上演唱过它们。前文已言,李龟年是盛唐著名的歌唱家,曾出入于上流社会,李端《赠李龟年》:“青春事汉主,白首入秦城。遍识才人号,多知旧曲名。”(40)他与歧王的交往甚密。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有:“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41)如唐代冯贽《云仙杂记》转载《辨音集》之“辨音秦楚声”条(42),言他到歧王家,因为能够通过琴声微妙的差别而准确地判断出表演者的籍贯,所以受到了歧王的赞誉和恩赐。前文也言,王维与岐王交往也很密切。由于盛唐乐人与文人经常会同时出现在宴会上,并时有合作,故李龟年对王维应当并不陌生。从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79所载来看,王维《失题》是大曲《伊州》的第一首歌辞。而《伊州》是天宝年间极其流行的乐曲,宋代王谠《唐语林》卷5“补遗”:“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43)作为当时著名的歌唱家,李龟年显然对《伊州》及其所配的歌辞非常熟悉,其中当然包括王维《失题》在内。同理可推,李龟年对王维《相思》亦是如此。正因为如此,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和人生苦难后,他才会在江南触情伤景,演唱昔日所熟知的歌辞。
当乐人们熟悉王维的诗篇时,这些诗篇便有了得天独厚的传唱的便利条件。同时王维的诗又富有“雅秀”特点。唐代殷瓃《河岳英灵集·序》:“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44);明代唐汝询《唐诗解》评《酬郭给事》:“起语闲雅,三四深秀,五六峻整”等(45)。所谓“雅”,是指其诗体现出儒家的诗教精神,清代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序》:“右丞崛起开元、天宝之间……其为诗……亦复浑厚大雅,怨尤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46),表现的是儒家所倡导的温柔敦厚的审美特点,如清代张谦宜《絸斋诗谈》评《息夫人》:“体贴出怨妇本情,又不露出宁王之本情,真得《三百篇》法。”(47)故人们有时亦以“正声”、“正调”等代替“雅”来评价王维的诗。在王维诸多诗作体裁中,最能体现“雅”这一特点的要算他的应制诗,清代吴烶《唐诗选胜直解》亦曰:“应制诗庄重典雅,斯为绝唱”(48)。可见,王维诗的“雅”实际上与建安诗篇的“风骨”精神一脉相承,如清代邢昉《唐风定》:“绝去雕组,独行风骨,初唐气运至此一变。”(49)所谓“秀”,主要是针对王维诗的体裁,赞誉他在近体诗上的突出成就。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编》卷4《近体上·五言》中就有“王、韦五言,秀丽可挹”、“排律……太白、右丞,明秀高爽”、“七言律,唐以老杜为主,参之李颀之神,王维之秀,岑参之丽”等(50)。王维在近体诗方面的成就,自唐代开始就受公认。唐代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沈、宋既殃,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51)
当人们用“雅秀”来评价王维的诗,实际上是指王维能够运用当时极为流行的近体诗,传递出盛唐健康明朗的时代精神风貌。清代黄子云《野鸿诗的》:“高、岑、王三家,均能刻意炼句,又不伤大雅,可谓文质彬彬”。可见,王维的诗也是“风骨”、“声律”兼具的。如唐代殷瓃《河岳英灵集·序》言“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时,王维赫然居于所举诗人之首,“粤若王维、昌龄、储光羲等二十四人,皆河岳英灵也”。这显然与盛唐歌辞的发展走向完全一致。这样一来,王维的诗自然深受时人欢迎,熟悉它们的乐人自然也乐于传唱。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26《谈丛二》:“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王维为多,中、晚李益、白居易为多。”(52)
总结全文,盛唐音乐文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上流社会与长安是盛唐音乐的繁荣地,盛唐文士与歌辞创作关系空前密切,盛唐歌辞“风骨”、“声律”并求。从王维的音乐才华、社会活动及诗篇特点等来看,他与盛唐音乐文化极其契合,这使得其诗深受时人欢迎,并广为传唱。可见,音乐文化是盛唐王维接受的基石。
注释:
①②(51)[清]董诰等:《全唐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46第220页,卷605第2708页,卷388第1842页。
③⑤(13)(16)(25)(26)(32)(39)《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5页,第975页,第962页,第1247页,第1350页,第1224页,第1247页,第1739页。
④⑧(12)(15)(21)(36)(38)[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11页,第3241页,第486页,第1086页,第5039页,第5052页,第5052页。
⑥⑨(11)(19)(27)[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6页,第477页,第5760页,第5564页,第477页。
⑦(17)(28)(43)车吉心:《中华野史·唐朝卷》,[济南]泰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550页,第565页,第555页,第410页。
⑩(2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788页,第6993页。
(14)(18)[唐]元稹:《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70页,第254页。
(20)(22)(40)[清]彭定求:《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07页,第2895页,第3247页。
(23)[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0页。
(29)[宋]王灼:《碧鸡漫志》卷3,《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第124页。
(30)参见柏红秀、李昌集:《泼寒胡戏之入华与流变》,[北京]《文学遗产》2004年3期。
(31)(44)《唐人选唐诗(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6页,第58页。
(33)(35)(37)(42)[唐]薛弱用:《集异记》;王汝涛编校《全唐小说》,[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0页,第792页,第1250页,第3179页。
(34)周绍良、周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49页。
(41)[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60页。
(45)(47)(48)(49)陈伯海:《唐诗汇评》,[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第338页,第328页,第294页。
(46)(50)陈铁民:《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281页,第1270页。
(52)[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