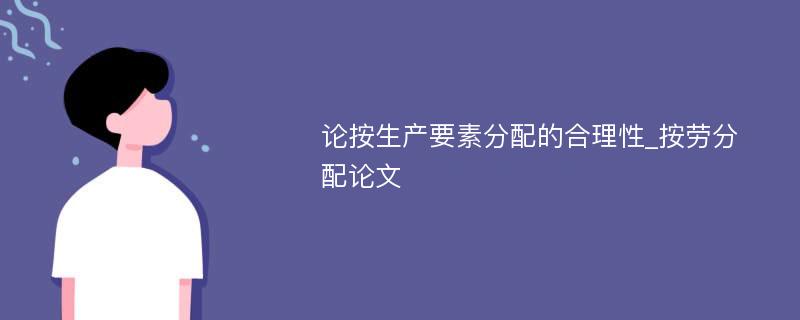
论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合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生产要素论文,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提出,我们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是我国分配模式的重大突破,分配理论的重大发展。这不是某种权宜之计和临时性政策,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发展的合理性。
1.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全社会的生产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的盲目状态,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时,有产者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侵占劳动者的一部分劳动。市场竞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剥削等等,导致社会两级分化。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资本家所持有的原始资本来源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中的血腥掠夺,资本在使用过程中并不创造新的价值,只是用来剥削工人的手段。所以,以资本、设备等生产要素获取收益是不合理的。代替资本主义新的社会制度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这个理想的社会中,每个生产者根据自己提供的劳动量,取得与之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即“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只能按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为计量根据,不存在也不允许有其他的分配方式。
2、在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 教条式的理解,特别是由于“左”的思想统治,我们脱离实际地不断强化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一大二公”。通过多次政治运动,强行建立了基本上只有全民和集体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大一统的纯而又纯的经济模式。从形式上看,由于社会只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全体劳动者是国家或集体的主人,他们掌握着生产资料,劳动收益的分配就只能按劳动的质和量进行,而且,生产资料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也为实行按劳分配提供了理想化的条件。
但问题是,第一,劳动者的劳动怎样计量?社会生产形式纷繁复杂,没有任何专门机构能够准确计量每个劳动者在各种生产活动中付出的劳动;而且,劳动的性质千差万别,很难有统一的标准准确计量。
第二,即使劳动能够计量,等量劳动也不一定创造等量产品,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由于劳动者的素质,生产条件、掌握的知识信息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非但不是等量劳动创造等量产品,反而是等量劳动创造不等量的产品。
再次,等量劳动更不一定能创造等量价值。在现代社会,由于生产成本和满足社会需要的情况不同,等量劳动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特别是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活动,不但少创造或不创造价值,而且创造负价值,这样的劳动付出越多,对社会造成的损失就越大。
所以,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无法准确计量个人的劳动量,理论上又必须以劳动量作为分配的依据,只好人为地脱离实际地把劳动力分为不同的级别。在农村分为强劳力和一般劳力,男劳力和女劳力等;在城市则把劳动者分为不同的级别,决定级别的主要是资历,而不是实际的劳动能力。这样,就把劳动者和他在具体劳动中实际付出的劳动的质和量割裂开来,劳动的计量不可能反映劳动者的能力特点和在劳动中的实际付出。再者,这种单纯计量劳动量的办法把劳动活动与劳动结果割裂开来,只强调劳动过程的参与,不考虑也不计算劳动对劳动结果的贡献率,即劳动的效率,所以,出工不出力,干与不干,干好干坏报酬一样成为普遍现象。另外,这种办法还把劳动结果与社会需求割裂开来,从而无法确定劳动成果的价值,自然也无法确定劳动创造和实现的价值情况,无论劳动创造的价值大小,也无论其创造的是正价值还是负价值,只能不加区分地去分配个人所得。这是一种名义上的“按劳分配”,实际上的平均主义。
3、实践证明, 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所谓的按劳分配只能导致平均主义、大锅饭和低效率、低效益,真正的按劳分配从来没有得到切实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是正确的合理的,社会主义应该实行按劳分配,但这就要求实际地准确地计量劳动的质和量。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联系劳动活动的成果,而对劳动成果的价值状况的确定又不能脱离社会需求,又必须联系它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就是说,只有将劳动与市场相联系,才能计量劳动对劳动结果的作用以及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才有可能实行按劳分配。
在市场经济中,劳动者、劳动活动、劳动成果都被纳入到客观的经济运行之中,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得到实际的确定。具体而言,由于市场主体要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他会主动关心经营成本,自觉地把劳动与劳动结果相联系,计算具体劳动对劳动结果的贡献率。由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由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各种劳动力的价值得到客观准确的衡定。在劳动中,又以契约的形式得到明确认定,从而使素质不同的劳动者获取不同的报酬。由于竞争和选择的作用,劳动力资源处于流动之中,这就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其所创造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使得即使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其实际创造价值的不同而获取不同的报酬。
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才可能切实得到贯彻执行。而市场经济是以产权形式的多样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投资形式的多样化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为基本前提和特征,这就必然存在按生产要素分配,也必须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不允许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也就不会有真实的按劳分配。要实际地而不是形式地实行按劳分配,就必须同时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
4、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首先, 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客观要求。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在生产和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的科技含量已达到80%以上。特别是在当代,世界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的信息产业值已占GNP45%—65%。 科学技术信息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创造着越来越多的经济价值,允许科学技术、信息参与分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实际。同时,也会有效地引导我国的科学技术、信息产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接轨,有力地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次,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扩大生产、发展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个人收入的增加,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将会有数额不等的剩余资金。如果不允许资金投入经济运行以获取收益,那么这部分资金或者被消费掉,或者闲置,这将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允许投资参与分配就会有效地鼓励人们把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活跃经济生活,促进全社会的经济发展和财富总量的增加。
再次,允许和鼓励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有利于促进国民自主意识的形成和民主意识的增强。以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到经济运行之中,并获取收益,会使社会成员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和责任者,热情地关心和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培养其自主和责任意识。如果仅靠劳动收益,虽然也会使人们关心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但必竟不会产生强烈的主体意识。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无论我们怎样强调“全体劳动者都是国家的主人,”可到头来大多数劳动者的行为却怎么也不象是主人。植根于经济生活之中,由对自身基本经济利益和自主事业的关注而培养起来的主体意识,是社会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条件。公民的主体意识使他们更为关心社会政治权力的形成和使用,关心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关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对公众权力起到制约和保证作用,从而促进民主政治建设。
最后,允许和鼓励按生产要素分配,有利于促进国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由于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投入及合法经营获利,能够引导和培养公民积极向上,通过诚实劳动追求幸福生活的良好素质,形成勤劳、节俭、积极、乐观、健康的生活方式。反之,当人们贫穷落后而又没有出路,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则可能一方面片面依赖社会,不思变革安于贫穷落后;另一方面则可能产生某种暴民心态,仇视富足,试图掠夺他人和社会的财富,满足物欲,而一旦占有了一定的财富,又只会山吃海喝低俗消费。由于社会保障公民的投资和经营的合法收益,使得社会的公共生活对社会成员来说成为休戚与共、利害相关的,他人的行为也与自身处于有机联系之中,从而产生对社会、国家的公共生活的归属感,增强公德意识,改善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由于可以从生产要素的投入中获取利益,社会成员就会自觉地思考投入和获益的方式和结果,关注社会现实。为了适应社会需求,实现自己的目标追求,人们要自觉通过接受教育,参与竞争等途径,提高自身的素质,发现和发挥自身的潜能和特长。在这个过程中,使社会成员的素质得到提高,潜能得到发挥。
5、允许和鼓励按生产要素分配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总量,并且能够促进社会成员素质的提高,促进他们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和思想道德的提高。同时也有利于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这些无疑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进步。
按照流行的观点,以生产要素,特别是以资金、设备的投入来获取收益,是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典型的剥削行为。实际上,如果从实质上而不是从名词概念上看问题,就会理解,是否存在剥削现象,并不取决于分配方式,不在于是否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而在于分配是否公平合理,对这种合理性的判定,既有经济利益的因素,又有伦理道德的因素;既有社会现实的因素,也有文化心理的因素。所谓剥削和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归根到底是利益分配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产生有多种原因。但事实证明,过去我们不按生产要素分配,并非就不存在这种不合理;只不过由于“左”的统治的宣传和教化,人们对此视而不见或者巧妙地加以掩饰。现在这种不合理的存在,也绝不是因为实行了按生产要素分配。比如,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指令性定价,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使得农民的一部分劳动被无偿占有,通过社会的计划使另一部分人受益,这实际上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夺,毛泽东也曾讲过这个问题。由于社会的民主法制不健全,监督制约不力,代表国家对资源行使管理权的一部分管理者,可以利用职权,大肆挥霍和占有本属于全民的资源,这些资源的所有权名义上是国家的、他人的,但其使用权支配权是管理者自己的,因而他们对他人劳动的无偿占有也更隐蔽,更“无偿”。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腐败现象突出说明了这一点。
在一个法制健全、公平、正义的社会体制中,社会成员的资金、设备、知识、技术的获取应该是勤奋劳动及合法经营的积累,即各种劳动付出的积累。当他们把以往劳动的积累再次投入于经济运行之中以获取利益时,从根本上说是劳动的回报,而且这种回报的数额是由市场规律和市场主体之间的契约决定的。社会法律、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以及社会的文化、心理、观念等会自然地确定和接受一种公平合理的收益水平。我们不应该把剥削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必然联系起来。
同样道理,消除两极分化,也决不能否定按生产要素分配。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是我国加快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当然,按生产要素分配会使一部分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经济收入中先富起来,拉大收入差距,但这是必然的,正常的。不切实际地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一齐致富,只能是共同贫穷。就现实而论,收入差距的急剧拉大主要是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导致的非法收入造成的,靠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致富应该得到社会认可。所以我们要坚持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鼓励和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大力发展经济,鼓励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去获取收益,以此增加社会的经济总量。同时,通过税收和社会再分配及政策调节等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兼顾社会公平,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