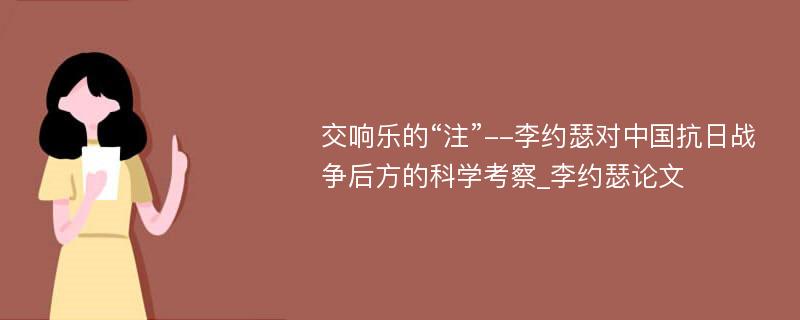
交响乐的一个“音符”——李约瑟对中国抗日大后方的科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后方论文,科学考察论文,交响乐论文,中国论文,音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中国抗日大后方的科学技术工作,长期为人们所忽视,资料缺,论著少,实为憾事。笔者认为,李约瑟博士撰写的宏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部交响乐,而他对中国抗日大后方的科学考察成果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音符”。在战争峰烟弥漫,民族存亡之秋,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抗日大后方的众多科技工作者坚持不懈地进行研究活动,取得杰出的成果,为延绵数千年的祖国科学技术发展链条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环节,为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交响乐谱写了一个新的“音符”。
在战争彤云下保存科技实力
中国科技发展史显示,19世纪末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科学研究方法先后传入我国,到本世纪50年代中叶,从学科设置到研究设施,从科技人才培养到学术研究成果,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随着日本对华全方位侵略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主义”政策,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大片国土沦丧,广大民众流离失所,山河破碎,经济凋蔽,疮痍满目,哀鸿阵阵。在兵荒马乱的大动荡中,东部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相继内迁,科学实验室破败,研究设备和科技图片大量散失;日伪集团文化特务使尽威胁利诱的伎俩,骗走一些科学文化研究人才,为其侵略战争效力;还有一些科学工作者远走异国他乡,到条件较好的研究机构里继续完成其研究课题。当后来李约瑟博士踏上这个古老大国的土地时,“她正处在艰苦的抗战之中,多年的内扰外患使国家处于危境,政府疲倦不堪,经济全面萧条,一贫如洗,一切知识、文化生活紊乱无章。这时的中国,远离了汉、唐、宋、明各个朝代的光辉业绩”[1]。在这种情况下,初具规模的现代中国科学技术体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初生的中国科技事业陷入了艰难困境,曾经是光辉灿烂的祖国科学技术发展面貌顿然暗淡了,其发展链条似乎中断了。
实际上,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科学研究活动并未停止,中国科学研究成果并未化为0,中国科学发展长河并未断流干涸。正如著名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40年代中期对中国抗日大后方进行科学考察时所见所闻、搜集整理的大量资料、所描述的科学研究活动情况表明的,在众多科学工作者身上仍然保持着中华民族的艰苦奋斗精神,在他们坚持不懈的科学活动中仍然体现着中国人民的科学创造能力,他们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杰出成果,实实在在地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谱写了一个新的“音符”。
在内扰外患的民族存亡之秋,在日本侵略战争乌云密布,“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急关头,中国广大科技工作者高擎爱国主义旗帜,为国分忧,为民除昧,为祖国科学事业尽心尽责。有些人投笔从戎,血战沙场;有些人历尽千辛万险,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走上抗日战争第一线;而众多科技工作者则在国民党政府开明官员和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赞助下,随同大学、科研机构和文物图书资料分期分批地内迁,经受颠沛流离,劳累困顿,饥寒交迫之苦,在道路质量极差和交通工具奇缺而陈旧的条件下,辗转数千里向祖国大西南迁移,寻找新的立足之地。需要指出的是,有不少大学、科研机构在内迁过程中,或因战乱,或因匪盗肆虐,或因经费不济,被迫停办、被解体、被摧毁了,实为民族千古遗恨。
根据有限的资料表明,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设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各所,在国民党政府匆忙命令下陆续西迁,中央研究院总部随同政府迁往重庆;气象所经汉口转成都,再迁北碚;地质所经汉口转桂林,再迁沙坪;物理所、心理所、动植物所,经桂林迁北溶;社会科学所经阳朔迁至昆明;工程所、化学所、天文所、历史语言所均经湖南转迁昆明。设在北平的科研所,大多数迁往昆明……。这一搬迁工作多数单位于1939年结束,少数单位迟至1944年才完成。我国科学研究的另一方面军——高等院校,除辅仁大学等少数教会学校保持中立外,都从祖国东部沿海地区被迫匆忙内迁,迁往祖国西南、西北地区,或就近迁入山区。北京、清华和南开大学迁长沙,再迁昆明合组成“西南联大”;北洋、北平大学和北平师大迁至陕西,合组成“西北联大”;中央、复旦、武汉、东北、山东、东吴和金陵大学等31所高校迁至四川各地城镇……这次高等院校大搬迁运动,断断续续地进行了8年之久。
在这次高校和科研机构大搬迁过程中,或因乱机轰炸,或因匪盗抢劫,或因仓忙慌乱,图书资料损失很大;科技工作者受到各种干扰,精神上受到打击,研究活动被中断,其损失是无法估量的。但是,在科学家们的精心组织和广大爱国同胞的帮助下,科研的骨干力量,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文物图书资料的主要部分保存下来了。经过调整,重新布局,形成以昆明、重庆、成都为中心的科研配置新态势,科研人员各就各位,在特殊环境里继续进行研究活动,大学也在新的条件下重又开学上课。这是我国科学事业的基本实力,是祖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起点,是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希望!
在艰难环境里坚持科研活动
1942年,当中国人民处于灾难深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英国科学界代表、英国驻重庆大使馆科技参赞李约瑟博士出使中国,以实际行动赞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实地考察中国抗日大后方的科学活动状况,以便发展中英两国的科学文化合作事业。
科学研究工作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40年代的中国科学家们则必须在战争乌云密布、政治腐败和经济凋蔽的条件下搞学术活动。李约瑟博士在中国进行科学考察的四年多时间里,研究设备和生活条件比牛津大学差多了,遇到的麻烦事和困难问题也大得多了。然而,以他在科学界的地位和英国大使馆参赞的身份,能够到英国驻华机构弄到所需要的东西,在与国民党政府所属机构打交道时也顺利得多,因为他们不敢得罪这位有强大国家支持的“洋博士”。而身处大西南的中国科技工作者没有李约瑟博士那样的政治背景和学术地位,其环境之艰难,工作之辛劳,精神之创伤,简直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李约瑟博士进行这次科学考察的所见所闻,亲身感受和理论升华,集中体现在谈论中,讲演里,生动地凝聚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国的科学》摄影集、《科学前哨·中英科学合作馆文件集》的字里行间,对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艰苦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对其杰出的科研成果给予高度的评价,对其顽强的学术探索精神表现出由衷地敬佩,刻画出一幅惨淡悲伤的科学技术活动图景!
政治环境险恶。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除对养生之道的医学和供达官贵人享用的建筑学等少数学科予以支持外,而对有利于国计民生和促进社会文明发展的科学技术则往往看之为“雕虫小技”、“奇器淫巧”,加以抑制和摧残。偏安于大西南的国民党政府也是如此,对战争需要的军用技术、对政治宣传有利的部分社会科学学科予以支持,而对有利于社会经济进步的现代科技和学术活动相当忽视,甚至加以压抑。国民党当局利用抗战之机,极力进行思想控制,加强思想宣传,鼓吹“拥护党国”、“服从领袖”和“以党治校”等口号,扼杀进步思想,压制科学精神;政府实行恐怖统治,警宪肆虐,特务横行,加紧迫害进步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在当局的纵容下,地方势力、黑社会组织和流氓地痞之流抢掠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财产,滋扰科研活动和教学秩序……李约瑟博士时常对各种腐败现象大感恼怒,对竟然容忍“合法的暴行”公开存在的不公道制度感到震惊[2]。这样,就使得本来已经十分愚昧落后的大西南地区又被笼罩在重重愁云惨雾之中,本来就相当落后的祖国科技事业又陷入了新的“严冬”。
物质条件极差。抗日大后方的科研活动处境十分悲惨,物质条件极差,生活环境恶劣,简直达到难以言状的地步。政府不关心科学事业,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投入的财力物力极其有限,其支出不足国库支出的20,而科研经费更加短缺,中央研究院的每年经费仅为130万元,其他较小科研机构的经费就更可怜了。在物价飞涨的条件下,只能勉强维持与抗战有关的少数项目,而对社会进步和国家未来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则难以颇及了,致使这些单位买不起图书设备,更谈不上购买先进科学仪器了。科技工作者实际上沦为难民,薪金菲薄,还经常拖欠,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无法进行正常的研究活动。恩格斯早就指出,人们必须首先确保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科学技术,这是物质生活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历史发展规律[3]。迟至20世纪40年代,已经进入高度工业文明时代,自然科学在非欧几何、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论和计算机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科学家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不断提高,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了。然而,抗日大后方的中国科技工作者却在自然经济环境里,运用原始研究设备,采用手工作业方法,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搞科研,“缺乏设备的情况是任何其他民族都会吃惊的”[4];大学迁入祠堂,学生寄宿破庙,每天坚持上课,教授在烛光下做实验,写文章,实在可叹,可悲,可恨!!!
很多科学家,包括从国外归来的科学家,怀着一颗赤诚的报国之心,不畏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险,前往大西南参加“科学救国”工作。为了共赴国难,科学家们忍受清贫,甘愿吃苦,即使是著名教授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每月只领到一些混杂糖壳、沙子的糙米,有时还要变卖衣物度日,但不能动摇他们搞科研的决心。30年代末从德国归来的化学家黄鸿龙,赴昆明前给友人的信中说:“弟此次归来,立志为国服务,待遇多寡本不置念,说困难时期,更不当论薪资厚薄……”[5]。读之令人涕下,令人感奋,充分体现了科学家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科研工作继续进行。身居大西南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坚韧不拨,排除万难,因陋就简,始终坚持科研活动,为祖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长河,为中华民族他日的崛起,做了许多实实在在、奠基性的科学理论准备工作。曾跟随李约瑟博士进行科学考察的黄兴宗先生描述着,四川小镇李庄,聚集了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所、社会学所、考古博物馆、中国建筑学史所和同济大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同济大学的主要校舍设在大禹庙中,历史语言所设在一座简陋的农舍里,而到这里考察的李约瑟博士则被安置在一座“结构简单、设备不佳”的新建招待所内。这里集合了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专家,也可能是当时全世界这个领域研究的中心,李约瑟先生提出的关于中国科技史的问题“引起了普遍的骚动”,竟相搜寻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6]。在战争阴云笼罩下的大西南穷乡僻壤,科学家们却以顽强的毅力,大无畏精神去战胜困难逆境,将古旧寺庙、破落宗祠略加改造而成为学术研究机构,用原始简陋的工具,自制的玻璃器皿,少量的化学药品,用桐油作汽油的替代品,用旧汽油筒做抽炼焦厂的管道,用废弃汽轮的引擎作为轧钢厂的动力……坚持不懈地进行科学研究。西南联大的赵忠尧、张文裕教授对宇宙线的研究,王竹溪、黄子卿教授对热力学的研究,杨石先、曾昭抡教授对有机化学的研究,都是在实验设备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的;孙云铸教授对云南地质构造的研究,清华大学的矿冶所对云南丰富矿产的勘察,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在重庆,翁文灏先生为主任委员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拥有十六万多名职工,进行多课题的经济研究;生物所的王家楫教授领导下进行多项目的生物学研究,都是在重重困难中进行的。在成都地区,金陵大学物理化学家李云洲博士关于伊洪热温高、伊洪容积水化作用等课题十分出色,李约瑟称之为“最突出的一位科学家”;武汉大学高尚荫教授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主持创建了当时中国唯一的微生物研究室。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在艰难的环境里,自然科学期刊,《科学农业杂志》、《气象杂志》、《科学新闻通讯》和《中国生物学会会议录》等依然出版,促进学术交流,向国外输出科技信息。李约瑟博士在考察这些科研单位时,看到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意外地坚强,继续进行着研究,使工厂坚持生产,异常感佩,深受鼓舞。他写道:“来自东部大城市的中国科学家对于中国西部的原始状况,及他们被迫而在技术上因陋就简,其惊异程度不亚于我们。在四川嘉定有人在可以遥见西藏山峰的一座宗祠里讨论原子核物理;在广西山洞中有大规模发电厂,若干工程师正力竭声嘶地向外来的工程师作着讲解;在大理土著部落中有人帮助一个浮游生物学家在五华塔下的洱海边推船下水”[7]。
科研成果卓著。大后方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保和发扬中华民族长于创造的科学能力,在艰难困苦条件下搞科学研究,不断有新的发明创造,写出高质量的优秀论文,取得了常人不敢企求的杰出成就。迁至昆明的天文所,在这里创建了中国西部的第一座天文台,从事测算彗星轨道,证解赤道仪校正法等研究工作;严密地组织了1941年9月21日的日全食观测,覆盖了黄河、长江流域的西部广阔地区,组成北、南两个观测队,摄取日珥和日冕的照片,拍摄日全食电影,观测日食时的天空亮度,观测日食时对地磁的影响等珍贵资料,观测电影转播到英美等国,中国民众为之振奋。在昆明筹建的数学所,聚集了姜立夫、陈省身和苏步青等知名数学家,专注于数学前沿重大课题的研究,其中有抗战伊始从英国归来兼任西南联大数学系教授的华罗庚,撰写有《堆垒素数论》一书和20多篇数学论文,被李约瑟博士誉为“很出色的青年数学家”。在此期间,北京大学吴大猷教授著有《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的专著和十七篇科学论文,获得教育部第一等科学奖金;同济大学童第周夫妇主持的胚胎学研究,给李约瑟博士“很深的印象”;中央大学张宗燧教授对统计物理和量子场论的研究,撰写多篇论文在英、美学术刊物上发表,某些方面“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黄鸣龙还原法是天然有机化学上的重大突破”,“候氏制碱法”是世界化学工业中的重要发明,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从松节油中提炼汽油,从当地植物中提炼橡胶;还有对川康古迹的考察,对敦煌千佛洞考古都取得重大成果……。这些,表明了中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条件下能做出卓越的科学成果,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具有不逊于其他民族”的创造能力。李约瑟博士将这些科研成果的一部分在伦敦进行展览,选出138篇论文推荐到欧美学术杂志上发表,为中华民族在世界科学之林增添了应有的荣誉。
抗战期间,内迁到大西南的各高等院校,也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坚持教学活动,共培养大学毕业生77000多人,不仅为抗日战争输送了大量专门人才,而且为新中国建设事业造就了一批科学大师或学术带头人,为中国跻身于世界科学殿堂而培养了杨振宇、李政道等“科学精英”人物。需要强调的是,原来是刀耕火种、断发文身的愚昧贫穷的大西南地区,通过内迁科研单位的科技开发,内迁高校的文化灌输,经济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在社会文明进步征途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一九四六年初,李约瑟博士离华去联合国总部任职,在大西南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又重新东迁,在另一种社会环境里继续进行科学研究活动。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成型上的贡献
青年时代的李约瑟博士,接触了一些中国科技史资料,有了撰写关于中国的科学与文化的著作的大体计划轮廊,渴望揭开被无知和偏见的厚厚面纱所覆盖的旧大陆东部的古代文明真面目。然而,这毕竟还是肤浅的认识、零散的资料,也还未摆到他科学活动的主要议事日程上。而李约瑟博士战时的中国之行,为搜集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物资料所倾心,为看到的中国科学家们在极端艰难条件下迸发出来的巨大科学创造力所感佩,发生了科学生涯的“分水岭”,从此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把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科学文化优秀成果介绍给全世界,让它在全人类科学宝库中占据显著的位置。可以这样说,他的卷帙洁繁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动机和决心产生于此次中国之行,是在对中国之科学考察基础上,在众多中国科学家的有力帮助下成型的。
从1942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时期李约瑟博士率“英国科学家访华团”出使中国起,到1946年3月离华去巴黎就任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的第一位主持人之职止的数年时间里,有很多时间和机会实地考察中国西南、西北和东南部辽阔地区,访问三百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与上千名学术界和科学文化界知名人士会晤交谈,亲自了解他们的科学见解和学术研究计划,亲眼看到他们在无法描述的艰难困苦条件下,坚持各自的工作岗位,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活动,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李约瑟博士为了获得第一手中国科学研究新材料,广交学者、专家朋友,而中国科学家们对这位来自西方科技发达国家的学者表现出特别的热情,对他提出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重大问题感到浓厚的兴趣,共同探讨了许多新颖的学术问题。一个炎热的夜晚,在广东坪石河旁阳台的烛光下,与王亚南先生讨论中古时期中国封建官僚社会的实质;在广东曲江的茶馆里,与吴大琨教授探讨社会学发展新趋向;在四川乐山,与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博士讨论中国思想史,了解到旧儒教的教义精髓;聆听郭本道、黄云刚教主关于艰深的道教思想的阐释;与钱临照博士研讨《墨经》,钱先生对书中的物理学原理所作的解释使李约瑟博士“惊叹不已”;在陕西宝鸡的河南大学疏散地,与李相杰教授讨论《道藏》,李先生介绍了其中的炼金术问题,是使李约瑟博士“终生不能忘记的”事情;在广东坪石中山小学,看到蒲蛰龙教授从事把生物学方法用于控制害虫的开拓性研究,给李约瑟博士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与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由好友黄兴宗先生介绍到“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的曹天钦研讨葛洪《抱朴子》一书中关于铝汞化学问题;与著名学者傅斯年、陶宣和谈论中国科技史料的真伪问题。李约瑟博士还多次深情地提到,在对中国的科学考察中,得到了考古学家郭沫若、博学多才的财政专家冀朝鼎的“指导”,结识了当时在重庆做抗日统战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通过这些学术上的交往,李约瑟博士眼看到这一伟大民族从传统农业——半封建文化出发,精通近代科学和工程技术,还有多种发明创造,甚至在日本侵略战争的重压下,仍然保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和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保持着中华民族的科学创造力,认为这是中国明天的希望所在,并对此与中国人民一样“引以为荣”[8]。
李约瑟博士此次中国之行,是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指派和生产部的资助,其使命和初衷是打破日军对中国科学知识方面的封锁,保持和加强中英两国科学文化领域的合作,为当时在难以想象条件下勉力进行科研活动的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医务人员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他在重庆创造“中英科学合作馆”,制订计划为中国科学界购置英版图书期刊、科学仪器、化学药品,接受科技咨询和邀请英国学者来华讲学,资助中国学者、学生去英国考察或留学,推荐中国科学家撰写的论文到欧美学术刊物上发表等,为我国在世界科学园地争得不少荣誉。在这些工作中,给他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结识了许多中国科技界知名人士,游历了中国辽阔地区,惊喜地发现大量中国科技史宝藏,搜集到众多的中国科技中资料,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李约瑟博士在科学考察过程中,最为关心的是到古旧书店购置古代中国科技图书。途经成都时,因汽车坏了需要修理,就邀同农学家何文俊教授进城买书;到福州考察时,到古旧书店购置了两大藤篮的古代中国科技书籍,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色”。与李约瑟博士交往过的中国学者们,被他提出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新见解所吸引,被他的科学探索精神所感奋,非常乐意地帮助他“走上正确的途径”,纷纷向他赠送自己珍藏的古代中国科技图书。竺可桢教授赠送了铝字排印本《古今图书集成》巨帙,黄子卿博士赠送了一部《齐民要术》,唐钺博士赠送了一部《天工开物》,不少学者还向他奉送了自己的科学史研究成果。在巨著的整个准备时期,得到王铃先生在研究古籍方面的帮助,“花许多时间去查找,选取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些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们再从科学史的观点仔细地审查,然后确定它的价值”,因此成了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位同伙人[9]。抗战期间李约瑟博士在中国搜集到的这些古旧科技图书,成了他后来于伦敦创立《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基本资料。附带一提,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博士五次访华,学术界朋友们又向他赠送了很多古代中国科技图书,周恩来总理也向他赠送了珍贵的古代中国科技书籍,使得撰写伟大科学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资料准备更加充实丰富了。
科学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尚未出齐,该书内容于何处终止尚不清楚,然而,从此大部头著作的写作决心和资料准备来自李约瑟博士对中国科学考察的结果看,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历史长河的事实看,应当包括中国抗日大后方的科技活动部分,否则是不完备和不公允的。李约瑟博士曾经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比作一部交响乐[10],那么他战时中国之行所目睹的抗日大后方科学活动和卓越成果就是这部交响乐的一个“音符”。我们坚信,在改革开放的环境里,在经济振兴的基础上,中国科学技术将会迅猛地发展,将会谱写出更多更美的“音符”!
注释:
[1]黄兴宗:《李约瑟博士1943—44旅华随行记》,李国豪等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8页。
[2]黄兴宗:《李约瑟博士1943—44旅华随行记》,李国豪等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4页。
[3]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4]许立言等:《抗战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活动》,见《自然杂志》1981年第9期,第650页。
[5]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下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3页。
[6]黄兴宗:《李约瑟博士1943—44旅华随行记》,李国豪等主编:《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7]许立言等:《抗战时期李约瑟在中国的科学活动》,见《自然杂志》1981年第9期,第650页。
[8]胡升华:《李约瑟与抗战时的中国科学》,见《科学》1994年第6期,第52页。
[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27—28页。
[10]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