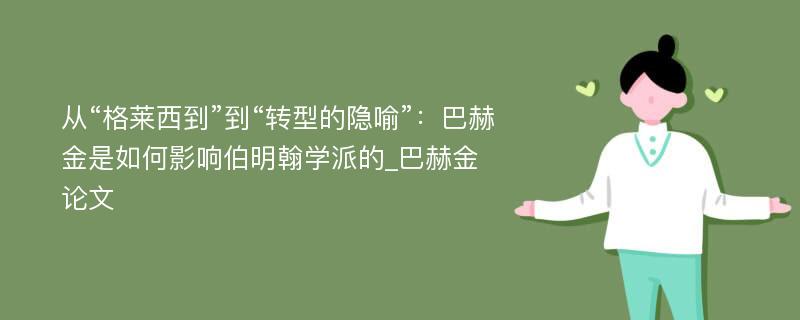
从“葛兰西转向”到“转型的隐喻”——巴赫金是如何影响伯明翰学派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伯明翰论文,巴赫论文,学派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4-0013-09
巴赫金文论在近半个世纪里已经成为中西方文论竞相引征的理论资源,其所具有的理论活力有目共睹。但是,它们彼此之间究竟是如何发生理论上关联的?巴赫金受到重视的那些理论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到各门各派思想之中的?被改头换面后的巴赫金文论自身独特性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不仅对研究巴赫金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切入西方文论发展的肌理,去辨析其中的奥妙。而这又需要以英国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简称CCCS)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为切入点,因为由它所倡导的文化研究已经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写了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的面貌。
一、影响的可能性:一个“小组”和一个“学派”
在真正进入巴赫金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研究之前,首先要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影响的可能性,而这需要从三个方面考察辨析。
其一,学术生产的群体性。
即使是平行比较,我们也能很容易发现巴赫金与伯明翰学派在学术生产方式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尽管俄苏学者在近半个世纪里将巴赫金“奉若神明”、尊崇为学术大师,尽管巴赫金在其大半生时间里孤苦伶仃、学术无援(其30年代的小说理论和40年代的拉伯雷研究均是纯个体性的学术行为),但是真正决定巴赫金思想面貌和理论取向的却不能不说是奠基于从1918年开始持续到20年代中后期的“巴赫金小组”①。在那个“苦茶谈辩到天明”的时期,巴赫金小组展开了大规模的学术辩论,所涉及领域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从俄国形式主义到弗洛伊德主义,从洪堡到索绪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学术氛围使得巴赫金不再期待“‘从孤独遁向孤独’来寻找上帝,而是从人与人的彼此相对,从人与人之间来寻找上帝”②。这是一种全新的基于对话主义的学术生产方式。伯明翰学派也具有类似这种学术生产群体性的特征。如果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处于草创阶段的霍加特时期(1964—1968)还属于个体学者独立撰著结集的话,那么在霍尔接任中心主任之后,中心便进入到“集体学术生产”时期。尤其是在整个70年代,霍尔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系统学术规划和集体研究项目,分别在媒介研究、亚文化研究和语言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1979年以后,该中心虽然在理查德·约翰逊和乔治·洛伦两任主任的主持下努力实现学术转型和突破,但这种群体性研究的因素仍然存在,学者间彼此的合作也频繁。③
也许正因为伯明翰学派对这种学术生产的组织性、群体性的认同,使得他们并不特别在意70年代开始的围绕巴赫金小组的著作权之争,而是以相对宽容而灵活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在伯明翰学派的不同时期、不同学者那里,存在各种策略性的描述方式。比如说,在雷蒙·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最早版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中,威廉斯称《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为“一直同巴赫金合作”的V.N.沃洛希诺夫,而在1989年该书的重印本中,则改为“V.N.沃洛希诺夫是巴赫金的笔名”④;霍尔除最早的《编码/解码》中直接引用“沃洛希诺夫”之外,以后一直以客观介绍的方式对争议“存而不论”;而约翰·费斯克则对“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平行引述,并不混淆。由此也可以看出,伯明翰学派学人更关心的是“巴赫金小组”(托尼·本内特也称之为“巴赫金学派”)思想的相关性和解释的有效性。
其二,问题意识的相关性。
如果没有基本相似的问题意识,彼此间的影响便很难发生。20年代的“巴赫金小组”在其理论构建中面对着国内的庸俗社会学和形式主义两种迥然相异的学术思想的交锋;同时,20世纪早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也成为其展开学术论辩的对象。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阶级”的关心,形式主义对“语言”、“符号”的青睐,精神分析对“心理”、“意识”的强调,共同构成了“巴赫金小组”的学术语境。而“巴赫金小组”的学术努力正是力图克服彼此的缺陷,以便将三者整合成全新的理论体系。正因为如此,《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才会一方面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以“意识形态科学”为名恢复“内容”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则以批判形式主义方法为名,肯定“材料”和“手法”的价值;《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才会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弗洛伊德,将之归入“主观心理学的变种”行列,但另一方面又利用弗洛伊德主义对个人意识的发现去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而发现“日常思想观念”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同样,《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借助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强调来克服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忽视“言语”的弊病,而其“意识形态符号”的独特概念不失为打通“社会”与“符号”、“意识”的绝好途径,其“多重音性”虽系语言学术语,但其更具有应对现时代纷繁复杂多元交融的社会现实的能力。
事实上,从60年代开始,如何沟通“社会意识”和“语言符号”便成为伯明翰学人努力的方向。约翰·希金斯注意到,“在读到米哈伊尔·巴赫金关于理解小说中的意识形态和体裁动力的著作成为流行倾向之前很早,威廉斯就已经努力将它们视为一个作者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结果或表达来理解它们间的相互关系了”。⑤ 威廉斯文学研究方面的思考方向可谓与巴赫金不谋而合。70年代,在霍尔的主持下,该中心展开了系列研究,但其面对的更为重大的问题在于中心面临着日益激化的“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之争。比如,媒介研究更多借鉴结构主义思路,从文学文本到视觉文本到社会文本;而亚文化研究则以社会学、人类学方法,注重社会调查,采取民族志的方式进行。所有矛盾的焦点便集中到了如何处理语言和言语的关系、如何处理主体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处理社会意识和语言符号的关系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当伯明翰学人一旦读到巴赫金小组在20年代面对相似甚至同样的问题已经有了重大理论突破时,其亲切之感油然而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三,著作英译和私人交往。
除了纯学术上的相关性之外,影响研究最为重要的是关心彼此间事实上的接触和交往。就巴赫金对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来说,还应包括巴赫金著作的英译和介绍情况、巴赫金与伯明翰学派间是否存有人际接触和私人交往等问题。
从巴赫金著作的英译情况来看,早在巴赫金被“第一次发现”时期,其研究拉伯雷的著作就已在1968年被译成了英语。70年代以后,巴赫金小组的著作陆续被译成英文,如1973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1976年的《弗洛伊德主义批判纲要》、1978年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80年代以后,则以巴赫金文集的形式将其各个时期的单篇论文结集出版,如1980年的《小说中的话语》、1981年的《对话的想象》、1986年的《语言类型及其近期论文》等。同时,大批巴赫金的研究、介绍和传记也在英语世界中出版,比较有代表性的如1979年托尼·本内特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980年舒克曼的《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巴赫金文体》、1983年舒克曼的《巴赫金学派文集:俄国诗学翻译中的特别主题》、1984年托多洛夫的《巴赫金:对话的原则》以及同年由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合著的《米哈伊尔·巴赫金》等。这些文集的出版,为英语世界的接受提供了基本的文献。
从人际接触和私人交往情况来看,巴赫金逝于1975年,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巴赫金在有生之年曾与伯明翰学人有过正面接触。但颇有意味的是,巴赫金的哥哥尼古拉·巴赫金在30年代来到英国,在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之后先后执教南安普敦大学和伯明翰大学。尽管尼古拉早在1950年就已去世,但是巴赫金兄弟对语言哲学有着共同的偏爱,而且在巴赫金有生之年,70年代早期还曾收到由尼古拉在伯明翰的朋友们搜集的一包材料,给巴赫金带来了尼古拉迟到的问候。尽管这种私人性的联系并不可能对伯明翰学人接受巴赫金产生什么影响,但是,此等机缘巧合足以让伊格尔顿在80年代兴奋异常,令霍尔直到90年代仍然对巴赫金兄弟欷嘘不已。⑥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辨析巴赫金与伯明翰学人之间的学术交往和思想影响过程时,我们不能把两者的关系进行简单化的处理。因为从伯明翰学派自身的学术发展来看,来自以德、法为代表的欧陆思想的影响都是举足轻重的,而巴赫金和他的巴赫金小组同样也是最初经由雅各布森、托多洛夫、克莉斯特瓦等人的介绍才进入欧陆学术视野的。因此,一方面,只有将巴赫金与伯明翰学派的关系放在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理论思潮的总体背景下,我们才能更为准确地呈现巴赫金的影响和意义;另一方面,在强调巴赫金的影响因素时,也千万不要过分夸大这种影响——当然,指出巴赫金对伯明翰学派影响的这种有限性并无损于双方的伟大。
二、最初的接受:霍尔、“语言和意识形态”小组以及威廉斯
尽管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拉伯雷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有法、英译本,但是目前还没有材料证明伯明翰学人那时已经开始受到巴赫金的影响了。目前可以查到的对巴赫金小组的最早引用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而被引用的最早文字是以巴赫金/沃洛希诺夫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于1973年被翻译为英文,这在巴赫金对西方文论影响史上是个关键性的事件。对此,托多洛夫用“戏剧性的变化”来描述这一年前后出现的巴赫金研究状况⑦。也正是在这一年,霍尔写出了《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在目前最流行的版本《编码/解码》(即霍尔在前文的基础上于1980年所作的修订本,被收录在《文化·媒介·语言》一书)中,出现了霍尔对巴赫金小组的最早引用。在论及意识形态在话语中对话语的积极介入问题时,霍尔特别指出,“用沃洛希诺夫的术语来讲,完全进入到争夺意义的斗争之中——语言中的阶级斗争”⑧。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早在1973年就已经阅读、接受了巴赫金小组的影响,因为《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最早的也是最终的版本至今还处于蜡版油印本状态。霍尔在修订本中不仅对前文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写、润色,而且增添了不少内容,其中有关沃洛希诺夫的这段话就属于其1980年版本的新增部分。⑨
从目前可以查到的材料来看,伯明翰学人对巴赫金的最早引用见诸于文字的是1976年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报告”第九辑(WPCS.No.9)。在该卷中,查尔斯·沃森的《工人阶级语言的符号学》和约翰·伊利斯的《意识形态和主体性》标志着伯明翰学人对巴赫金的正式接受。这两篇文章是“语言和意识形态”小组的阶段性成果,此外还有1977年出版的由罗莎琳德·考沃德与约翰·伊利斯合著的《语言和唯物主义》一书。在《工人阶级语言的符号学》中,沃森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阅读指出,“阶级社会的连续形式……每一种都具有将语言转变成其对立面的具有生成性的意识形态超结构;从一种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去理解客观现实的社会努力转变成对少数人利益的努力遮掩”⑩。但是,沃森并没有进一步去追问影响人们所闻所感的意识层面之下的无意识因素,无法分析语言中的“梦境内容”。作为对沃森阅读《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回应,伊利斯在《意识形态和主体性》中指出,沃森在分析中没有注意到一种与辩论形成对照的特殊对话形式——即“内部对话”。正是内部对话,更明确地将意识形态与心理学的问题提了出来。而在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看来,“凭借意识形态符号统一的、能包容它们的理论,心理和意识形态的相互界限问题可以得到解决”(11)。因此,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语言哲学不仅有效地克服了形式主义仅仅关注语言符号的结构形式的弊病,同时也克服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生物学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将语言与客观现实简单对应的缺陷,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将“内部语言”和“外部语言”结合了起来(12)。
1977年,被视为伯明翰学派的“精神领袖”或“学术顾问”的雷蒙·威廉斯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在该书第一章“基本概念”第二节“语言”中,威廉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的理论有两个特点值得特别重视:一个是它强调语言是活动,另一个是它强调语言有历史。在回顾了从18世纪以来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相关的知识谱系,特别是分析了斯大林主义语言观之后,威廉斯把目光聚焦到了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认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找到了一条足以超越那些影响巨大但又甚为偏颇的表现论和客观系统论的途径”。正因为巴赫金/沃洛希诺夫“把整个语言问题放到马克思主义那种总体的理论格局当中加以重新考虑”,“这使他能够把‘活动’(洪堡特之后的那种唯心主义强调之所长)看作是社会活动;又把‘系统’(新的客观主义语言学之所长)看作是与这种社会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不是像某些一直被人们袭用的观念那样,把二者看得相互分离。……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由此开辟了一条通往新理论的道路,对于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学术来说,这种新理论一直十分必要”。(13) 70年代中后期,威廉斯一方面已经注意到自己所提出的“情感结构”因为各种原因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则面临着对阿尔都塞—拉康式的对主体和符号问题的反思的回应压力,《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在语言层面转向对以巴赫金小组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重视正是这种压力下的产物。威廉斯在此所展现的对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关注,足以证明巴赫金小组对英国学术界的影响,而威廉斯的态度也可以成为伯明翰学派接受巴赫金思想的佐证。
三、“主要的文本”:“多重音性”与伯明翰学派“葛兰西转向”
尽管伯明翰学人之间对巴赫金小组语言哲学的了解、定位以及借鉴略有差异,但大体方向是基本一致的。在《转型的隐喻》中,霍尔从伯明翰学派“葛兰西转向”的高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启示性意义。霍尔指出,“葛兰西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主要的文本无疑是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该书由研究会出版社在1973年翻译成英文,并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深远影响”。霍尔将该书的意义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它确立了意识形态终归散漫的特征”;“第二,它标志着各阶级间的联系和各自独立的、自洽自足的‘阶级语言’、意识形态世界,或者用卢卡奇主义的术语来说是‘世界观’的断裂”;“第三,它进一步推进了这一关键性讨论:既然不同的口音在相同的符号中关联,那么,意义的斗争就不会以一种形式替代另一种形式,用一种自足的阶级语言取代另一种,而是在同一种符号内部,不同的意识形态口音相互脱节和重新接合”;“第四,《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一种意识形态的‘运作’,可以说不是将一种已经定型的阶级看法强加给另一阶级,与其说是施以更多权力,不如说是插入对话性的流动性的语言之中,通过语言无限的符号‘游戏’去影响意识形态的‘切割’,去解释‘散漫的构造’的局限,调整它的秩序,以便武断地固定语言的流动,把语言固定、凝固、缝合为单一的意思”。由此,霍尔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在普遍的理论转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即从对‘基础/上层建筑’的修正版本的黏糊调情转向彻底的体现话语/权力概念的意识形态”。(14) 霍尔的这番表述,可视为伯明翰学人正式接受巴赫金十八年之后所作的理论总结。在这段时期,霍尔本人已经经历了从阿尔都塞到葛兰西、从福柯到萨赛义德等一系列的理论重心转移。因此,尽管霍尔明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与伯明翰学派的“葛兰西转向”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但是他对该书的影响仍带有部分“事后诸葛亮”的成分,尤其是其中所包含的福柯式的味道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在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结构主义范式中,来自索绪尔、罗兰·巴特和阿尔都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中,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方式重读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并非虚幻的面纱(错误的意识),而是“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的观点对伯明翰学人以极大的启发(15),以至曾一度成为占据了伯明翰学派“完全正统的位置”(16)。但是,文化主义范式主张更多地关注与支配性结构(语言)的实际斗争,而在这方面,阿尔都塞因为对“系统”(system)和“结构”(structure)的过分倚重而没有留给“活动”(agency)以足够的空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因此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中成为争论的焦点,甚至成为文化主义批评的靶子。不过,这种理论转向与其说来自外在压力,还不如说来自内在需要,当霍尔意识到需要在理论上作出努力以便调节社会差异、大众传媒、权力和抵抗间的问题时,霍尔便开始了摆脱阿尔都塞的努力,其结果就是通过接合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实现“葛兰西转向”。
与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大众意识的压制不同的是,霍尔发现,很难认定在话语中只有统治意识形态能够被再生产,“因为如果语言中的社会斗争能够被引向相同的符号,我们便可由此断定符号(在更宽泛的领域里,包括所有能指和话语)不能被以一种确定性的方式永久性地给定给斗争中的任何一方”。(17) 而在这一理论转换中,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多重音性”概念再次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多重音性”是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展开其“意识形态符号”理论时最为重要的术语。在他们看来,社会意识和语言符号之间并不存在——对应的关系,语言符号所反映的社会意识不是一种简单的反映论,而是“符号的折射”,而这种折射“是由一个符号集体内不同倾向的社会意见的争论所决定的,也就是阶级斗争”。不过,语言符号内的阶级斗争与现实生活中的截然不同,因为“阶级并不是一个符号集体,即一个使用同一意识形态交际符号的集体。例如,不同的阶级却使用同样的语言。因此,在每一种意识形态符号中都交织着不同倾向的重音符号。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由此,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得出结论:“意识形态符号的这种社会的多重音性是符号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其实,正是由于重音符号的这种交织,符号才是活生生的、运动的,才能发展。”(18) “多重音性”概念在三个方面拓展了伯明翰学派在反思社会意识和语言符号关系时的理论空间:其一,语言符号不是对社会意识的简单反映,由此区别于简单的反映论;其二,同一种语言符号在不同的社会意识中会产生极大的差异,甚至“符号的阶级斗争”,因此索绪尔式的对语言体系的追求无济于事;其三,因为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的存在,在社会意识和语言符号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权力关系。正是这第三方面,与伯明翰学人正在重新接受的葛兰西“霸权”(hegemony)理论一拍即合。在葛兰西那里,“文化霸权”的实质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19) 很显然,葛兰西的“霸权”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关心上是相同的,但不同于阿尔都塞简单地将统治意识形态视为单纯的压制、灌输与强制,葛兰西更多地注意到了统治阶级在实施文化领导权时的策略。例如,一方面要求获得赞同,但另一方面又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一方面要遏制异己,但另一方面也并非一定要“斩草除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正是以这样一种既支配又协商的方式实施文化领导权的。在此,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意识形态符号”理论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正好对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作了最好的证明。
伯明翰学派“葛兰西转向”带来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在《解构“大众”笔记》中,霍尔比较了三种“大众”的定义:基于文化工业和消费文化的“大众”、人类学意义上的“大众”和居于统治关系之中的“大众”。其中,第三种定义是霍尔所欣赏的,即“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来说,最关键的是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用持续性的张力(关系、影响和对抗)来界定‘大众文化’。……它的主要焦点是文化间的关系以及霸权问题”。那么,这种文化斗争究竟如何展开?有何特点?当霍尔展开这一具有葛兰西式的“大众”定义时,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很自然地成为其极具说服力的理论资源。在引述了该书一段长长的文字之后,霍尔的结论是,“文化斗争有很多形式:吸收、歪曲、抵抗、协商、复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巴赫金/沃洛希诺夫成为葛兰西有关“民族—人民”文化、“霸权”理论的有力注脚。依据由巴赫金/沃洛希诺夫所注释的葛兰西理论,霍尔实现了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型——从“阶级分析”转为“权力分析”。“人民与权力集团相对,而不是‘阶级与阶级相对’,这是对立的中线,文化领域沿着它分开。大众文化尤其围绕着大众力量与权力集团的对立建构起来。这赋予了文化斗争领域自己特有的性质。”(20) 霍尔对“大众”的解构由此也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如果说伯明翰学人在60年代关心的是“工人阶级文化”、70年代更多关心的是“亚文化”的话,那么,到了80年代则转变成了葛兰西、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式的“大众文化”。
四、“转型的隐喻”:巴赫金式“狂欢”与福柯式“越轨”的理论纠葛
当伯明翰学人试图通过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实现对结构主义范式的超越时,其实已经内含了“巴赫金对形式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的问题。但是,“语言和意识形态”小组只是将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定位,而忽略掉了巴赫金小组与俄国形式主义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于1997年的本内特的《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书正是一个有力的补充。该书分为“重返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从美学到政治”两个部分,而对巴赫金则以“巴赫金的历史诗学”为名置于了“形式主义之后”的章节之中。这是与沃森和伊利斯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角度进入巴赫金完全不同的理论视角,显示了伯明翰学人将巴赫金置于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双重视野予以理解的努力。本内特指出,俄国形式主义的极端倾向完全消解了美学对历史的关注,他们只是抽象地提出问题但无法历史地去解决它们。而在这方面,巴赫金学派在20年代后期通过历史诗学的途径超越了形式主义,“在他们的著作中发生了俄国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尽管这一对话如谢顿所说的‘无法终结’,但也正显得格外有活力”。在历史诗学的范畴下,本内特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体裁的历史诗学,并在“作为历史体裁的‘文学’”一节中对狂欢化理论进行了介绍。不过,本内特在此并没有将“狂欢化”放在文化理论中看待,而只是从历史诗学的角度强调了民间文化对狂欢化文学的影响,尤其注意到“巴赫金更关心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文学文类的‘狂欢化’成为当代欧洲‘纯文学’(belles lettres)诞生的标志”。(21) 不难看出,70年代末本内特对巴赫金的接受基本上是在形式主义及其超越的问题域中进行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伯明翰学人中,接续了霍尔80年代初期对“大众”的“葛兰西转向”式的思考并进一步将之“发扬光大”的当属约翰·费斯克。80年代中期,正是费斯克直接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整合进了大众文化研究。在1987年出版的《电视文化》一书中,费斯克用巴赫金的“多音性”(即“多重音性”)来描述电视文化,将电视节目视为“杂语”性的文本,而电视节目则是各种观点、不同立场间“对话”与协商的结果。(22) 不仅如此,巴赫金的“狂欢”概念正式作为电视节目的风格形态被费斯克引入分析过程。费斯克将《摇滚与摔跤》节目称为“电视上的身体狂欢节”。在这里,身体的中心地位、过度、夸张、丑怪荒诞和“大众奇观”构成了节目形式的狂欢化;而在节目中摔跤场面的混乱取消了奇观与观众之间范畴意义的区别,摔跤游戏对体育运动的戏仿形成了对“公正”的亵渎,参与摔跤节目的身体不再指涉“健康、强壮”,而以其“怪诞的男性的身体”为观众制造快感。值得注意的是,费斯克在此所作的分析与其说是巴赫金式的,不如说是罗兰·巴特式的。他虽然运用了“狂欢”概念,但分析手段却是罗兰·巴特式的符号学。真正将“狂欢”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分析工具的,是两年后即1989年出版的著作《理解大众文化》。在该书中,费斯克认为,大众的反抗“主要由快感所驱动:即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社会体验的意义所带来的快感,以及逃避权力集团的社会规训所带来的快感”(23)。这两种快感,费斯克分别命名为“生产的快感”和“狂欢的快感”。在“狂欢的快感”中,身体及其快感成为至关重要的权力与逃避、规训与解放相互斗争的场所,大众通过狂欢的快感释放被法律、道德等社会行为规范所控制的身体而获得逃避的快感(24)。由此“狂欢”经过费斯克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改造而成为正式的大众文化研究术语。
其实,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进入伯明翰学派的理论视野并非仅有霍尔——本内特——费斯克一条途径。比费斯克出版《电视文化》还要早一年,由皮特·斯塔利布拉斯和阿伦·怀特合著的《越轨的政治学和诗学》更显示了影响的“正途”。在该著中,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进行了将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嫁接到当代大众研究的大胆尝试。他们不同意某些社会历史学研究所认为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和钝化的中产阶级趣味已经成功地压抑了狂欢和其他大众意识的共同表达,相反,他们认为狂欢仍然以碎片式的、边缘化的、升华的和被压抑的然而有时也压抑不住的方式呈现。巴赫金虽然抓住了狂欢的原始动力,但是没能区分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普通的对世俗快乐的追求中高级趣味与低级趣味的混和,另一种是中产阶级式的对肉欲和商业的杂交。于是,他们通过从英国文学、文学批评和对社会历史现象解读的文献中来描述狂欢在当代文化中的转型。尽管他们也是从当代大众文化现象,比如说第一章就是从广场开始切入的,后文中还广泛涉及了诸如丑怪身体、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冥想(25)、城市、家庭罗曼司之类的现象,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指向费斯克式的大众的文化抵抗,而是转向了当代文化中“高雅/低俗”、“大众/中产阶级”、“社会/审美”之间的“越轨”。
如果《越轨的政治学和诗学》还只是停留在将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简单套用到当代大众文化现象的分析之中的话,那么,它很可能只会是一部平庸之作。直到阿伦·怀特去世五年之后,亦即1993年,当霍尔重读这部著作时,他才开始疑惑为什么当初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部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文本”。事实上,《越轨的政治学和诗学》最重大的理论贡献在于以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为基础为文化研究确立了福柯式的“越轨”观念。“越轨”一词还可译为“逾越”、“僭越”、“越界”等,也有人将之译为“违犯规章”、“逆行”等。这个词并非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独创,而是来自拉康和福柯。在《康德和萨德》一文中,拉康将力主仰望道德星空的康德和纵欲虐待加变态的萨德等同视之,认为“萨德即康德”,并借此将道德和欲望联系起来,认为“越轨的观念将一种涉及我们要求于道德的东西明显联系了起来,这就是欲望之意”(26)。在《越轨的序言》中,福柯则进一步提升了“越轨”的意义,强调“在为我们的言行提供支持的文化领域,越轨不仅规定了唯一的发现它的没有中介物的神圣性的行为,而且提供了修改它的空洞形式、它的缺席的方法,这样,文化就闪烁出了炫目的火花”。越轨并不同于一般的颠覆、反抗、革命之类的行为,在福柯看来,“越轨并不寻找一种东西去反对另一种东西,也不试图通过嘲笑或忧虑基础的坚固来达到它的目的;……越轨不包含任何否定,但是肯定受限制的存在——肯定无限的跃进,就像它第一次敞开其存在的领域一样”。(27) 不过,福柯在文章中分析的主要对象是癫狂和性,主要涉及人类文明对癫狂的压抑以及当前性行为超越了自然繁衍的功能而泛滥之类的问题。这篇文章也可以视为其后著作《癫狂与文明》和《性史》的“先声”或“总纲”。但是,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在《越轨的政治学和诗学》中则试图将这种极限性的“越轨”引入现代社会对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并在此论域中实现与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对接。在他们看来,“现在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狂欢’正在成为一种模式、一种理想和一个分析范畴”。他们发现,“在最近运用狂欢理论的社会历史著作中,狂欢的政治维度显示出巴赫金或他的贬低者所难以想象的复杂程度”。根据这种狂欢化的理解,他们认为,“只有把狂欢置换进更为开阔的符号倒转和越轨的概念中,现在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成为分析范围的狂欢观念才有可能变得更加富有成效”。(28) 其中,“符号倒转”的观念来自芭芭拉·巴波科克(Barbara Babcock),而“越轨”则是受福柯思想的影响。经由“符号倒转”和“越轨”改造后的“狂欢”不再只是对现存秩序的简单的镜像式的倒转,或者是矛盾双方对称式的否定对方;狂欢不可被现存的法律所预知,因为它不能够由现存的象征意义来表示,却能够从新的象征资源中生成。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同时也发现,“要描绘一幅令人信服的狂欢转型的地图涉及对迁徙、藏匿、变形、分裂、内在化和神经性升华”;但是,“除非作为一种令人感伤的景观,狂欢却因过于厌恶中产阶级生活而无法忍受”。(29) 很显然,“狂欢”在进入“越轨”后,自身也面临着理论的限度。
如果说当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撰写《越轨的政治学和诗学》时还处在伯明翰学派的“福柯影响”时期的话,那么,到了90年代,当霍尔重读这部著作时,福柯的影响已经逐渐淡去,面对着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60年代末期以来的当代文化变局,霍尔此时也更有感慨。于是,在霍尔那里出现了一次重大的理论逆转:斯塔利布拉斯和怀特成功地将“狂欢”注入了“越轨”,霍尔则反向地将“越轨”引入了“狂欢”,从而将“狂欢”提升为当代文化“转型的隐喻”。在霍尔看来,转型的隐喻必须至少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要“允许我们在现行的文化价值受到挑战、旧的社会阶层被推翻、老的规范标准消失或者被视为‘革命的节日’时,想象一种新的意义、价值、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出现”;二是“它们必须设法为我们提供在这种转型过程中社会与其符号域关系的途径方法”。(30)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已经成为一种经典的转型的隐喻,而像“革命的节日”这类词就属于那些对激进想象而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隐喻家族。霍尔引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31)。证明转型在此已非常典型地按照翻转和替代来“思考”了。但是霍尔发现,时代已经变了。这种思维方式已不再为人们所认可,文化理论已经果断地与这类戏剧式的简单化和二元式的翻转拉开了距离。因此,必须寻找到一种新的隐喻来替代它。霍尔意识到,巴赫金的“狂欢”正是替代马克思的“革命”的最合适的“转型的隐喻”。巴赫金的“狂欢”正是对二元区分的逾越:“低文化侵入了高文化,模糊了被强制接受的等级秩序;它所创造的,不是简单地用一种美学战胜另一种美学,而是那种不纯的、混杂的‘怪异’形式;它暴露出低文化之于高文化的相关相依,显现出所有的文化生活不可避免的混杂和矛盾的本质,文化形式、象征、语言和意义的可逆性;揭露出文化权力的武断和简单化行为,排除作用在每一种限制、传统和经典形式的建构和每一条文化闭合的等级原则之上的运行机制。”尽管在霍尔的表述中,福柯式的思维方式仍然存在,但是“狂欢”已经不再像福柯逾越癫狂、监狱和性时那样“惊世骇俗”和“特立独行”。在“狂欢”成为替代“革命”而成为新时代的“转型的隐喻”后,巴赫金式的对话主义开始逐渐成为霍尔处理文化问题的思维方式。
至此,巴赫金思想经历了二十多年时间的漫长转换,终于从隐藏在欧陆思想身边的影子走到了学术话语的前台,从理论论争中被援引的资源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思想,而其与文化研究、文化理论、文学理论之间关联的复杂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体现。从伯明翰学派接受巴赫金思想影响的途径、方式及效果来看,我们很难说巴赫金思想的全貌已经得到全面的呈现,甚至即使到了霍尔将“狂欢”确立为当代文化“转型的隐喻”的阶段,我们也很难说这是伯明翰学派对巴赫金进行了最准确的把握和最正确的运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影响和接受的过程确实发生了,巴赫金独创性的“多重音性”(与之相关的还有“杂语”、“多声部”、“复调”概念)、“狂欢”、“对话”理论已经经由伯明翰学人的创造性发挥而获得了更大的生机。
[本文为2007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巴赫金对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研究”(07CZW00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 其实,“巴赫金小组”共分为两个时期,即早期的“涅韦耳小组”时期和后期的“维贴布斯克”小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巴赫金都堪称为核心人物。在这两个小组中,形成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其中就包括日后发生“署名权之争”的沃洛希诺夫、梅德维杰夫和卡纳耶夫等。
② 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第80页,语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③ 如《媒介·文化·社会》(1980)、《非大众教育》(1981)、《制造历史》(1982)、《帝国反击》(1982)、《英国危机》(1985)等以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报告”(CCCS Working Papers)为载体的学术成果;霍尔在调到开放大学之后,组织编写了大批教材和主题论集,如已译成中文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和尚未被翻译的《文化身份问题》等。此外还有《文化研究》杂志的创办等。
④ 这一问题是由王尔勃在翻译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过程中发现的。相关引文引自该译著的未刊稿,特此致谢。
⑤ Raymond Williams,Ed.by John Higgins:The Raymond Williams Reader,Oxford:Blcakwell.2001.p.92.
⑥ 相关文献可参见:Terry Eagleton:Wittgenstein's Friends,New Left Review,Sep-Oct 1982,pp.64—90.Stuart Hall:“For Allon White:Metaphors of Transformation”,Ed.by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pp.297—298.
⑦ 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第79页,王东亮、王晨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⑧ 斯图尔特·霍尔:《编码/解码》,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第3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⑨ 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部分蜡版油印“工作报告”一直没有再版,后来部分文章在新结集时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甚至有的面目全非,因此不可简单地以印刷文本来引证其油印文本时期的思想。相关文献的影印件由章戈浩提供,才使得两个文本得以比较。特在此致谢。
⑩ Charles Woolfson,The Semiotics of Working Class Speech,WPCS.No.9.pp.165—166.
(11) 巴赫金/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周边集》,第383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2) John Ellis:“Ideology and subjectivity”,Culture,Media,Language.Ed.Stuart Hall,Dorothy Hobson,Andrew Lowe,and Paul Willis,London:Hutchinson,1980,pp.186—194.
(13) Ray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本译文引自王尔勃对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未刊译稿,在此致谢。
(14) Stuart Hall:“For Allon White:Metaphors of Transformation”,Ed.by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1996.pp.295—297.
(15) 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见《保卫马克思》,第201页,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
(16) James Procter:Stuart Hall,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4.p.45.
(17) Stuart Hall:“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Ed.by M.Gurevitch,T.Bennett,J.Curran and J.Woollocat,Clulture,Society and the Media,London:Methuen,1982.p.79.
(18) 巴赫金/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见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周边集》,第365页。
(19)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38页,曹雷雨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0) 斯图尔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见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第41—5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
(21) Tony Bennett,Formalism and Marxism,London:Routledge.2003.p.61、67、166.
(22) John Fiske,Television Culture,London:Methuen & CoLtd.1987.p.90.
(23) 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第58页,王晓珏、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24) 非常有意思的是,费斯克在《电视文化》中分析的“《摇滚与摔跤》节目”一节被完整地挪到了《理解大众文化》一书中,成为第四章“冒犯式的身体与狂欢的快感”中的一节,由此可见这两本书在理论上的关联性和延续性。
(25) 史密斯菲尔德是位于伦敦西北部的一个市场。
(26) Lacan:“Kant avec Sade”,Desiring Whiteness:A Lacanian Analysis of Race,by Kalpana Aeshadri-Crooks,p.109.
(27) Michel Foucault:‘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30、35.
(28) Peter Stallybrass and Allon White:“From Carnival to Transgression”,The Subcultures Reader,Ed.By Sarah Thornton,Ken Gelder.p.293、297、299.该文是《越轨的政治学和诗学》(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Transgression)的导论部分,因该书没能在国内图书馆查到,目前只能通过谷歌图书(Google books)及其他网络书店查询到部分章节,目前收集到的有导论、第一章和第五章,但全书总体思想倾向已能够明了。
(29) Peter Stallybrass and Allon White:“Bourgeois Hysteria and the Carnivalesque”,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Ed.By Simon During.London:Methuen,1986.p.388.该文属于《越轨的政治学和诗学》中的第五章。
(30) Stuart Hall:“For Allon White:Metaphors of Transformation”,Ed.by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 and New York,1996.p.287.
(3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