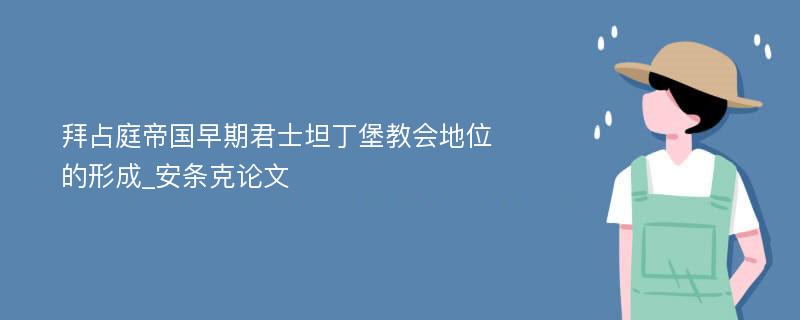
论拜占廷帝国早期君士坦丁堡教会地位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君士坦丁堡论文,帝国论文,教会论文,地位论文,论拜占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66-07
基督教化是早期拜占廷帝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和重要内容。基督教在该时期的高速发展不仅表现为多神教的衰落和基督教取得了国教地位,还表现在4—5世纪,通过四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和三次对重大神学异端的斗争,使基督教正统教义得以基本明确。①与此同时,教会内部的组织关系也逐渐形成,在这一层级分明的组织体系中,居于教会最高层的是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为代表的五大教区。然而,与我们较为熟悉的罗马教会相比,目前国内对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关注尚显薄弱,尤其对于其在4—6世纪地位初步形成的过程更缺乏系统性的研究。笔者认为,对该问题加以分析探讨,有助于我们完善早期基督教会史和拜占廷史的研究体系。同时,对当今基督教世界内与罗马教会(天主教)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东正教)进行研究,对我们认识基督教现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君士坦丁堡教会在4—6世纪地位的形成是与基督教会内部组织体系逐渐完善的大背景密不可分的。在基督教向西传播,进入罗马帝国腹地之初,基督教会内部并没有明确的教职制度,随着信徒的增加和传教工作的需要,从2世纪初期开始,在一些基督教文献中出现了“长老”“监督”和“执事”等头衔。2世纪中叶,出于管理的便利,一些教区开始出现独掌大权的主教,到60年代后,主教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了。②至公元3世纪时,主教成为教会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以至于当时的教父西普里安提出:“教会的合一在于主教制……主教在教会里,教会也在主教里。因此谁不与主教在一起,他就不在教会里了。”③
与此同时,主教下属的一些神职也逐渐确立起来。尤西比乌斯在《教会史》中记载到,公元251年,罗马主教科尔尼里乌斯在写给安条克主教的一封信中提及,自己属下有“46名长老、7名执事、7名副执事、42名襄礼员以及52名驱魔人、诵经员和看门人”。④这些职位在同时代和稍后历史学家的作品中也多有涉及,时至今日的天主教和东正教会中,还保留了很多当时的神职名称。
然而,与各地方教区内部结构日益完善相比,基督教会的诸教区之间在3世纪时尚未形成比较清晰的组织关系。在此时期,教会内的主教们虽然辖区大小贫富不一,但是从地位来看基本上保持平等。尽管罗马主教因为管理着“使徒彼得的教区”而广受尊重,但是并未取得凌驾于其他主教之上的权力。正如强调主教重要地位的西普里安所言:“教会的合一并不包括臣服于一位‘众主教的主教’,而是在于所有主教之间的共同信心、爱心与交通。”⑤
然而,随着公元313年后基督教逐渐取得合法地位和皇帝对基督教会给予了越来越多的优待,许多民众选择了皈依基督教,教徒人数的大量增长对教会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国家与基督教会之间的联系也比先前更为紧密,为了保证基督教成为帝国的精神统治工具,拜占廷统治者需要一个组织严密,层级分明,利于控制的教会。再加上如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等教区的主教因为驻节在帝国的大都市内,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希望能够在教会中拥有更多的权力。因此,像先前那样由所在教区主教全权管理本区事务,教区之间互不统属的体制已经很难维系,更为复杂的组织体系的建立势在必行。
这种趋势在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上已经有所体现,会议通过的第4条教规对省区内主教任命的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一个主教必须由同省区的其他主教选举产生……但是,每一项任命都必须交由省城批准通过。”⑥这一规定实际上给予了省城主教在人事方面的特权。接着,在341年召开的安条克宗教会议在第9条教规中规定:“各省的主教必须承认驻节在省城主教的权力,后者应主持全省教会的事务……无论何处他都应名列该省主教之首,其余主教不得超越其而行事。”⑦显而易见,这项教规比尼西亚会议的决议更进一步,它使得各省城主教不仅在人事方面,同时在各个领域都拥有高于该省其他教区主教的特权。这些驻节在省城的主教被称为“都主教”以和普通主教区别,原先主教之间平等的关系就这样被逐渐打破。
与此同时,在都主教之上,拜占廷基督教会内还逐渐出现了权力更大的宗主教区。在这几大宗主教区中,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教会主要是凭借其使徒教区的身份和罗马时代作为基督教中心的传统获得这一地位。这三大教区在拜占廷帝国建立后地位不断上升,至4世纪末已获得了高于一般都主教的地位。君士坦丁堡教区则是因为帝国首都的身份才获得此尊荣。在君士坦丁大帝刚刚迁都君士坦丁堡时,君士坦丁堡教区只是色雷斯地区赫拉克里亚都主教治下的一个小教区,影响力十分有限。然而,随着首都地位的确立,它在基督教会中的地位也节节高升。公元381年的第2次基督教大公会议通过的第3条教规宣布:“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地位仅次于罗马主教,因为君士坦丁堡就是新罗马。”⑧这一教规使得君士坦丁堡主教获得了和上述三个使徒教区宗主教同等的身份。耶路撒冷教会在451年的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也取得了宗主教区的地位。至此,拜占廷帝国的五大宗主教区正式形成。五位宗主教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帝国的西部地区的教会归罗马教区统辖;首都君士坦丁堡教区对希腊部分地区、色雷斯、黑海地区和小亚细亚大部拥有管辖权;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则是埃及和附近利比亚部分地区的宗教领袖;安条克和耶路撒冷教区分别享有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以及阿拉伯地区教会的领导权。⑨
在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之后,拜占廷教会已经逐渐形成了以五大宗主教为核心的一套比较成型的组织体系。五大宗主教对各自属下辖区在诸多方面进行统辖。大致看来,宗主教和都主教对下属教会拥有以下几类管理权。
首先,他们拥有对下级教会的人事任免权。按照规定,任命省内教区主教应由本省区其他主教推举,再经省城的都主教批准后方能通过。这一传统被延续下来并得到完善。宗主教都拥有一套自己的咨询机构,主要由其下属都主教和其他一些重要神职人员组成。比较重要的人事问题,如都主教的任命往往由该机构向宗主教提出候选名单,并由后者最终选择任命。各都主教区也有类似的机构,其确定下属主教的方式与此大体相同。⑩
除此之外,宗主教和都主教还拥有召开地方宗教会议,处理本教区内教义纠纷的权力。尼西亚第1次大公会议的第5条教规要求,各省教区每年必须举行两次全体会议以商讨本省教区内教义和人事问题,一次在大斋节前,一次在秋季到来之前。(11)这一教规后来被作为传统延续下来,各宗主教和都主教也相应地获得了本教区内宗教会议的领导权,上级主教不仅能够召开会议,还可在会议上对本教区内的教义和人事问题进行裁处。
最后,宗主教还可处置本教区经济事务。这种特权在该时期的史料中屡见不鲜。6世纪的历史学家,担任安条克宗主教格里高利顾问的埃瓦格里乌斯就多次在著作《教会史》中提到安条克宗主教任意使用教会财产的情况。如“当皇帝查士丁二世批评安条克宗主教阿纳斯塔修斯滥用教会财产的时候,后者公开辩称这是为了避免让可恶的(皇帝)查士丁挪用教产”。再如,“安条克宗主教格里高利经常慷慨地捐献金钱,在所有场合都表现的极为大方”等。(12)格里高利的教友,以弗所主教约翰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批评格里高利主教利用教会的财产满足公共享乐,甚至还“准备大量的金银和无数贵重的服饰作为礼物”用于行贿。(13)这也在侧面表明,宗主教拥有处置教会的财产并决定其如何使用的权力。
正是因为拜占廷教会内部开始出现了层级分明的等级制度,因此随着主教间平等关系的打破,宗主教与下级主教之间开始表现出明显的隶属和主从关系。在后者与前者发生矛盾时,很多情况下下级主教会选择委曲求全,尽量避免与宗主教发生直接冲突。埃瓦格里乌斯就记载了5世纪末安条克宗主教塞维鲁和下属主教之间的一件趣事。当时安条克治下的埃比法尼亚主教科斯马斯和附近的一些主教反对塞维鲁的基督一性论主张,因此他们联合撰写了一封申诉信,但是因为害怕宗主教的权势,却没人敢将信交给塞维鲁。最后,“他们将传递这份文件的任务交给埃比法尼亚的第一副执事奥勒良。但是因为他畏惧塞维鲁宗主教的高贵身份,因此在到达安条克城之后他穿上了妇女的衣服来拜见塞维鲁。他(奥勒良)忸怩作态,在伪装掩护下将这封信递交给他。之后趁人不备他离开了人群,并且在塞维鲁看到信的内容之前安全地逃跑了。”(14)这种下级教士对宗主教地位的畏惧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五大教区的最终形成和层级分明的体系虽然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教区之间平等的地位,并压缩了其自由发展的空间,但却产生了严明的纪律和更为高效的管理,这对基督教会在这一时期的高速扩张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如上所述,君士坦丁堡教会伴随着拜占廷帝国五大宗主教区的形成逐渐兴起。但它最终后来居上,取得帝国东部宗教中心的地位,还与拜占廷帝国早期基督教会内部的教义争端密切相关。基督教教义在形成发展与稳定的过程中曾经出现多次重大神学争论,君士坦丁堡教区一直积极参与乃至引导这些争论,最终借助5世纪重大的基督一性论争端,成功地战胜了东地中海基督教世界的神学中心亚历山大里亚,奠定了自身的地位。
拜占廷帝国的宗教中心在帝国建立之初位于西部地区。罗马教会凭借其使徒教区的身份和悠久的传统在基督教世界获得了首屈一指的地位。它不但能够直接领导东至塞萨洛尼基在内的帝国西部的诸教会,同时和东部的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也有传统的联盟关系,并可借此对东部其他诸教区施加影响。
然而,在公元381年召开的第二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影响了罗马作为宗教中心的地位,会议通过的第3条教规宣布:“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因为君士坦丁堡就是新罗马。”(15)这一决定标志着君士坦丁堡教区开始走向争夺基督教世界领导权的道路。
显而易见,君士坦丁堡教会地位飞速的攀升是对罗马教会的一大挑战。因此,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地位,从4世纪末到5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罗马主教一直试图和其东部的盟友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联手遏制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发展。罗马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都以使徒教区著称,且有着深厚的传统关系。在君士坦丁堡主教获得仅次于罗马主教地位的同年,罗马主教达马苏斯就指使治下的塞萨洛尼基主教阿斯科里乌斯联合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提摩太攻击德高望重的君士坦丁堡主教格里高利,最终迫使其辞职。(16)此后,它们又多次攻击君士坦丁堡教会。公元404年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塞奥菲鲁斯利用君士坦丁堡主教“圣金口”约翰与皇后的矛盾使他先后两次被皇帝放逐,(17)直至客死他乡。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大公会议上,面对聂斯托里神学争端,足智多谋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在罗马主教凯莱斯廷的协助下联合其盟友以弗所主教门农,罢免了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托里,(18)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的联盟不断取得胜利。这一事实表明,直到5世纪30年代时,尽管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地位不断提高,但是罗马和亚历山大里亚宗主教依然是众主教中最有影响力的主导者。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在以弗所大公会议结束之后,东部诸教区中率先对罗马教会进行挑战的并非君士坦丁堡,而是罗马的传统盟友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在第三次大公会议后,君士坦丁堡教会和罗马教会的关系在其后的20余年间波澜不惊,没有进一步的冲突出现。东部的另一大宗主教安条克主教则只是希望确保自己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地位,对于争夺基督教会的最高领导权没有表现出兴趣。反而是罗马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密切的关系随着政治利益的变化最终改变。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主教西里尔于444年去世后,其继任者狄奥斯库鲁志大才疏,一心追求基督教会的最高领导权,这使罗马主教产生了不满,进而开始调整对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态度。双方逐渐积累起来的矛盾最终在基督一性论争端中爆发。
当亚历山大里亚神学家尤提克斯发展了西里尔的神学思想,提出“基督一性论”的观点后,狄奥斯库鲁立即加以支持,然而罗马主教利奥却对此严加反对,并暗中支持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于公元448年召开宗教会议谴责尤提克斯。这无疑是罗马对狄奥斯库鲁的警告。然而,狄奥斯库鲁对此视而不见,在一年后的第二次以弗所基督教会议上,他依仗皇帝塞奥多西二世的支持拒绝宣读罗马主教利奥提交的信件,更将得到罗马教会支持的弗拉维安放逐后迫害致死。(19)他甚至得意忘形地宣称:“与其说国家是皇帝的,还不如说是我的!”(20)这样,罗马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长久以来的联盟正式破裂,与此相对,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在反对基督一性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共同利益。在451年召开的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罗马主教利奥的特使和君士坦丁堡主教一起与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狄奥斯库鲁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埃瓦格里乌斯在作品中记录了利奥的特使宣读的一篇针对狄奥斯库鲁的檄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矛盾已然不可调和:
恶贯满盈的亚历山大里亚主教狄奥斯库鲁……我们不谈其他事情,而来看看他的罪行,他凭借自己的权力公然对抗教规,并且和尤提克斯走到了一起……这些人应该对最神圣的利奥主教和神圣的大公会议保持恭顺,这样他们就可以被我们看作信仰上的同伴。但是这个家伙固执己见,甚至做出了应该令他痛心疾首并且跪在地上请求饶恕的恶行。此外,他甚至拒绝宣读受主祝福的罗马主教利奥写给被看作圣徒的弗拉维安的信,之前他已经被那些送信人再三劝告,要求他宣读这封信……但是,尽管他做了这么多恶行,我们还是可以宽恕他之前不虔诚的行为,因为连其他那些权力不如他大的主教们都是上帝所钟爱的。但是他又犯下了更大的罪行,他居然胆敢宣布罢免最神圣的罗马主教利奥……同时,他屡次践踏教规,因此他现在是自食其果。最神圣和受到祝福的伟大的罗马主教利奥通过我们和现在的这次会议,与被多次祝福和盛名远扬并且是正统信仰基石的彼得教区一起剥夺他主教的职位以及所有作为教士活动的资格。(21)
通过这段记录,我们不难看出,罗马主教真正的不满并非是狄奥斯库鲁接受了尤提克斯的神学理论以及迫害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而是在于他拒绝服从利奥的命令,甚至挑战其现有的地位。因此,在卡尔西顿大公会议上爆发的罗马教会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冲突也绝非仅仅因为教义上的异见,而是一次争夺基督教区领导权的政治斗争。最终,在君士坦丁堡主教的协助下,利奥的意见得到了皇帝马西安的支持,狄奥斯库鲁和尤提克斯都被处以放逐。从塞奥菲鲁斯开始,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们就一直试图成为帝国东部地区基督教会的最高首领。然而,卡尔西顿会议后,他们的这一理想彻底破灭,亚历山大里亚再也无法获得宗教领袖地位。(22)东地中海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教会手中。
但是,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在对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斗争中形成的短暂合作关系却未能保持长久。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失败使得拜占廷基督教会内部的政治关系由三足鼎立演变为两强对峙的局面。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成为了争夺基督教会最高领导权的竞争者。
尽管君士坦丁堡教会在卡尔西顿会议后名义上获得了和罗马教会平等的地位,但是与后者相比,依然有一些明显的劣势阻碍其成为帝国的宗教中心。首先,从宗教传统来看,罗马教会相传由圣彼得和圣保罗建立,是高贵的使徒教区,而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没有这种背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号召力。例如,卡尔西顿会议给予君士坦丁堡教区与罗马平等的地位让罗马主教利奥极为不满。他严词表明这一决定是“与教父们确定的教规相矛盾的,是对抗圣灵的地位和古典时代传统的表现”。(23)452年他更是在给君士坦丁堡主教阿纳托里乌斯的信中表示:“君士坦丁堡甚至不具备都主教的资格,因为即使它是皇帝所在的城市,也不能使其成为使徒教区。”(24)
其次,从4世纪末到5世纪上半叶各宗主教区的势力范围来看,罗马教会是整个西部基督教世界的领袖,同时东部部分教区,如塞萨洛尼基教会也归其管辖,在所辖区域内,罗马主教在宗教问题上有绝对的权威。反观君士坦丁堡教会虽然不断壮大,然而此时也仅是对色雷斯、黑海地区和小亚细亚地区大部具有管辖权。在东部其他地区,除罗马的下属外,亚历山大里亚等宗主教区,乃至以弗所这样的都主教区都不同程度地保持着独立性。在这一时期的宗教会议上,如前文提到的第二次以弗所宗教会议,经常出现君士坦丁堡教会被其他一些教区孤立的情形。因此,君士坦丁堡要想挑战罗马并取代其帝国宗教中心的地位,必须依赖另一个重要的条件。
君士坦丁堡教会最大的优势在于绝大多数拜占廷皇帝的强力支持。尤其是5世纪后,当帝国政治中心逐渐稳定地确定在君士坦丁堡之后,皇帝对远在意大利的罗马主教越来越难以控制,而对卧榻之侧的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管理则要容易许多。当罗马教会的独立性日趋明显时,为了维护基督教作为帝国精神统治工具的作用,拜占廷君主们需要扶持一个便于控制的宗教领袖,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便是最好的选择。因此,君士坦丁堡教会每一次地位提升实际都与皇帝的意志有密切关系。
凭借皇帝的支持,君士坦丁堡教会从诸多方面加强了自身的地位。首先,卡尔西顿会议后,君士坦丁堡教会开始改善同东部其他教区,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关系,同时极力维护自身在东部教会中的领导地位。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在卡尔西顿会议之后地位迅速下降,至少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构成对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实质威胁。这样,二者一度因为争夺东部基督教世界领导权所造成的尖锐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从主教阿卡西乌任内开始,君士坦丁堡教区逐渐调整了对亚历山大里亚教区的敌对态度,并在皇帝的支持下有计划地改善了双方的关系。这一政策的标志即是482年的《联合诏令》。(25)这一诏令是阿卡西乌促使泽诺皇帝颁布的有利于实现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和解的宗教政策,旨在调和支持《卡尔西顿信经》的基督徒(君士坦丁堡教会支持这一信经)与支持基督一性论的宗教势力(主要为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之间的矛盾。它回避了基督性质这一争论焦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君士坦丁堡与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之间紧张的对立局面。阿卡西乌对诏令的颁布起到了重要作用,除了向泽诺皇帝提出建议外,按照埃瓦格里乌斯的记载,他还派特使赴亚历山大里亚与刚刚上任的主教彼得·蒙古斯和谈,最终使后者接受并对全亚历山大里亚教徒宣读了这一诏令。(26)尽管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并没有因为这一诏令而放弃自己的一性论信仰,但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没有发生如第二次以弗所宗教会议上那样的剧烈冲突。
除了对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缓和政策外,君士坦丁堡主教还极力维护对所辖教区的控制和管理权。在卡尔西顿会议后,君士坦丁堡主教尤其反对罗马教会干涉东部教会事务,为此不惜与其发生正面冲突。双方在《联合诏令》颁布后爆发的激烈对抗将这种冲突推向极致。罗马主教菲利克斯在得知诏令的内容之后勃然大怒,因为在其眼中,这一诏令实质是对罗马教区主导的《卡尔西顿信经》的背离。因此,埃瓦格里乌斯记载到,菲利克斯“给阿卡西乌写了一封信,并且在信中宣布因为与彼得联合的问题而罢黜阿卡西乌。阿卡西乌对此并不接受,因为他认为这种行为不符合教规……这之后,菲利克斯要求泽诺皇帝确保卡尔西顿会议的决定依然是官方信仰,并且要求阿卡西乌去罗马为自己辩白。”(27)
一向倾向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泽诺皇帝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菲利克斯的要求,于是后者发表了宣言:“罗马教会不接受异端信仰者彼得,他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被神圣的教会谴责、开除并且诅咒了……这件事情表明君士坦丁堡的阿卡西乌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28)
罗马教会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这次冲突在基督教会史中被称作“阿卡西乌分裂”。这是东西部教会在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分歧。尽管直到1054年,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东正教会方才最终正式分裂,但是“阿卡西乌分裂”事件后,“普世的”罗马教会和“正统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隔膜逐渐加深。罗马教会内部对《联合诏令》是如此愤恨,以致当498年新主教的选举过程中,倾向部分接受这一诏令的候选人尽管得到了皇帝阿纳斯塔修斯的强力支持,但是还是被坚决拒绝妥协的西马库斯击败。(29)罗马教会此后与拜占廷东部教会渐行渐远。至553年查士丁尼召开第五次基督教大公会议时,罗马教会在这次会议中并没有起到先前四次,尤其是卡尔西顿会议中主导性的作用。不但罗马主教本人拒绝出席会议,而且意大利等西部地区的主教出席会议的人数也很少。(30)罗马教会自此逐渐倾向于脱离拜占廷政权的控制,并最终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教会也无力干涉西部教会事务,只是在皇帝的协助下取得了某些原属罗马所辖的东部教区,如塞萨洛尼基的控制权。在罗马教会逐渐远离了拜占廷教会体系的同时,君士坦丁堡主教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帝国内最有权力的宗教领袖。
此外,为了与历史悠久,宗教圣所众多的罗马教区相抗衡,皇帝还在首都建造了许多重要的宗教设施,这也为君士坦丁堡的宗教中心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壮丽的圣索菲亚教堂。这座教堂是尼卡起义后,查士丁尼皇帝在毁于战火的同名教堂的原址上重建起来的,工程历时25年之久。圣索菲亚教堂从落成时起就成为了拜占廷民众心目中的圣殿。它不但是君士坦丁堡主教的驻节地,而且也是帝国举行大部分宗教活动的场所。每当有重要宗教活动,帝国各地的基督徒都会蜂拥而至,而每年到此参观的外乡人更是不可胜数。圣索菲亚教堂对于拜占廷人来说是如此的神圣,以至于直到帝国灭亡的那一刻,城中幸存的民众还是选择躲避到这里,乞求上帝的显圣。
除了圣索菲亚教堂之外,据普罗科比在《建筑》中记载,仅查士丁尼皇帝就在君士坦丁堡修建或重建了33座教堂,其中就包括了规模略逊于圣索菲亚教堂的圣使徒大教堂,历代拜占廷皇帝和君士坦丁堡主教的陵寝都安放在这座教堂之中。(31)当罗马教会为历史悠久的圣彼得大教堂等宗教圣地自傲的时候,这些新建于首都的雄伟建筑则使新兴的君士坦丁堡教会毫不逊色。
这样,在5—6世纪,凭借拜占廷皇帝的支持,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影响与日俱增,通过在多方面与罗马教会的竞争,最终取代后者,成为了拜占廷帝国新的宗教中心。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君士坦丁堡教会获得的地位也有明显的弱点,即这种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皇权作用的结果,这恰恰为拜占廷皇权介入教会事务提供了良机。从拜占廷的历史来看,皇帝在绝大多数时间都把持着召开基督教大公会议的权力,同时极力控制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和一些其他重要神职的任免权,这也正是拜占廷教会最终未能完全摆脱皇权控制而独立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君士坦丁堡教会在4—6世纪地位的形成,是该时期拜占廷帝国社会转型的产物,体现了基督教化进程与拜占廷皇权作用的双重结果。
[收稿日期]2013-08-12
注释:
①可参见拙作《5世纪基督教会的两次基督论神学争端探析》相关内容,《历史教学》2008年第22期。
②[美]威·沃尔克著:《基督教会史》,朱代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52~54页。
③威.沃尔克:《基督教会史》,第83页。
④Eusebius Pamphilus,Church History,NPNF2-01,New York 1890,VI.XLIII.11.
⑤[美]奥尔森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6页。
⑥H.R.Percival,ed.,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NPNF2-14,Edinburgh 1988,p.44.
⑦H.R.Percival,ed.,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NPNF2-14,p.165.
⑧H.R.Percival,ed.,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NPNF2-14,p.250.
⑨G.Every,The Byzantine Patriarchate 451-1204,London 1962,p.23.
⑩陈志强:《拜占廷帝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30页。
(11)H.R.Percival,ed.,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NPNF2-14,p.46.
(12)Evagriu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Liverpool 2000,V.5-6.
(13)John of Ephesus,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Bishop of Ephesus,Oxford 1860,V.17.
(14)Evagriu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III.34.
(15)H.R.Percival,ed.,The Seven Ecumenical Councils,NPNF2-14,p.250.
(16)J.H.W.G.Liebschuets,Barbarians and Bishops:Army,Church 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tom,Oxford 1991,p.161.
(17)J.H.W.G.Liebschuets,Barbarians and Bishops:Army,Church and State in the Age of Arcadius and Chrysotom,pp.204~207.
(18)Evagriu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ns Scholasticus,I.5.
(19)Evagriu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II.2.
(20)J.Lindsay,Byzantium into Europe,London 1952,p.199.
(21)Evagrius Scholastic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II.4.
(22)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Vol.1,New York 1958,p.358.
(23)(24)W.H.C.Frend,The Rise of the Monophysite Movement,Cambridge 1979,p.146.
(25)可参见拙作《拜占廷帝国〈联合诏令〉出台的政治原因初探》,《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
(26)Evagri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III.13.
(27)Evagri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III.18.
(28)Evagri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111.21.
(29)W.T.Townsend,"The Henotikon Schism and the Roman Church",Journal of Religion,Vo1.16(1936),pp.84~85.
(30)Evagrius,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Evagrius Scholasticus,IV.29.
(31)Procopius of Caesarea,Buidings,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1914-40,1.IV.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