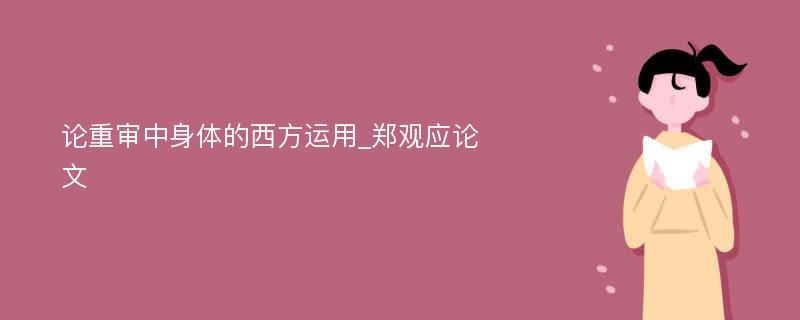
重审中体西用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体论文,西用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割体用,采末固本,变器卫道,“用夏变夷”,是甲午战争以前魏源、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张之洞、左宗棠和李鸿章那代人〔1〕文化变革的核心内容,也就是在19世纪40至90 年代十分流行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这一代文化变革者依据“中体西用说”,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切实推动了中国第一度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外沿部分的变革。这种文化观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其悖谬之处,还有必要对它进行重审。
中体西用说
首倡“中体西用说”的并非张之洞,与他同倡此说者,大有人在。
据有的研究者探查,最早出现“西学”字样是在晚明,那时有本书就叫《西学凡》。到了清朝的康乾盛世,西学已在上层人士中比较流行。但那时西学的地位并不高,西书被打入《四库全书》的另册,西学被认为精于天文推算、工匠制作而拙于学理,其道变幻支离,莫可究诘。〔2〕所以稳固世道人心者,非穷理尽性的中学莫属。 这大约就是“中体西用说”的“原型”。
魏源的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便无疑关乎这一原型。“夷之长技”正是历来为中国人所鄙弃的“天文推算、工匠制作”之类的“雕虫小技”,不过,承认技不如人,而且还要“师夷之长技”,肯定也算向前跨了一大步。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自序》中自白:“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不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至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3〕话说得很委婉,点出己意而不致招惹是非,可见当时言论背景之险恶、言路之特色。他的本意无非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以“驭夷为天下第一要政”〔4〕。
幕僚薛福成代其主子李鸿章撰文,大胆断言“中国之洪荒,以圣人制度文物辟之;外国之洪荒,以火轮舟车、机器电报辟之”,认为“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伦于不蔽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5〕。此论极偏,竟大得李鸿章的赏识, 誉为“精凿不磨之作”。薛福成如此出论的意图在于“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也”〔6〕。
邵作舟较中西短长,论来更不近情理:“中国者神灵之域,而声名文物远所从出者也,五帝三王以来四五千岁,圣贤英智之徒,继起而辈出,相与创政立教,讲述损益,穷乎天人之奥,而极于性命之微,一事一理至明且备”;“夫泰西者独器数工艺耳,奈何惊其末而遽自忘其本乎?”于是他恳请“陛下深观祖宗立法之意,与吾所以为国者,必力持而毋变,去繁就简,本末粲然,然后择泰西之善修而用之……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7〕。
总之,“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8〕;“中学为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9〕;“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10〕。清府位高权重的孙家鼐在《议覆开办京师大学堂摺》中规定:中国五千年来,圣神相继,政教昌明,决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芸人,尽弃其学而学西法。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辅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是立学宗旨。”立学宗旨如此,立国宗旨又何尝不是如此!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一流的洋务大臣立德、立功、立言无不本此。张之洞操办时务,于戊戌年写、刊风行天下的《劝学篇》,死守“中体西用”规范。《劝学篇》分成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恰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11〕的守本开新的文本格局。他写道:“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于经义。如其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12〕又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13〕“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政制和道统双修互通,乃是他的固本之原。“伦纪”、“圣道”、“心术”,都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义理根基、驯驭民众的“旧学”,是万万不能变的;可变者仅仅是“法制”(当为加固政制、道统的某些形式手段,与今义无多大关系)、“器械”、“工艺”之类微不足道的“新学”。
两种理论预设的冲突
“中体”何所指?人言言殊,不可能完全一致。特指“三代圣人之法”者有之(如薛福成),泛指中国有史以来政制、道统者有之(如邵作舟),明指“五帝三王”和“汉唐及明”之“圣教”而有意略掉秦制者有之(如张之洞)。“西用”所指也不尽相同,或者专指器物、科技,或者并指器物、科技和制度文化实用的外沿部分,例如“法制”和教育、科举体制等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分别位于文化的表层、中层和深层,“中体”与“西用”正好各占一半。这表明第一度文化变革未能触及中国制度文化的内核和思想文化。冯天瑜所下判断是比较准的:“文化保守主义反对全变,坚持《易传》的变易与不易的统一,认定文化的某些层面(如器物层面及制度层面的某些外沿部分)是可以变,必须变的,某些层面(如伦常层面及制度层面的核心部分)则不可变,不应当变。”〔14〕
体用、道器、本末,一物两极,相反相成,有主辅之分,断无中西各据一极之理。中国有中国的体用、道器、本末,西方有西方的体用、道器、本末。“中体西用”论者的要害就在于违背道器合一、“体用不二”的古训,强行作出不合古训的推理,不能自圆其说。深通西学的严复批判“中体西用说”,即据此立论:
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有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之为异也,如其人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5〕严复以人性、种族差异论批判“中体西用说”,一味顺着古人的眼光看问题,着眼点在中西各自的特殊性,指出“中体西用说”理论上的毛病,一针见血。但是,严复没有也不可能注意到中西文化还有共通的一面,故而也就忽视了“中体西用说”固有的有限合理性。
依我看,体用、道器、本末,在古人心智中是互异互涉的等级结构,体、道、本居先、位上、为大,用、器、末居后、位下、为小,二可同一,一可为二,等级秩序井然,不可颠倒。第一代文化变革者之所以不惜违背古训,分割体用、道器、本末、将体、道、本派送给中国文化,将用、器、末扔给西方文化,将中西视为一体,把中上西下这个等级结构扩大、套用到中国文化上面,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巩固这个等级秩序。运思方式倒不失为“辩证”的,运思材料却是两种文化,推论哪有不偏之理!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外沿部分可以通融,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核心部分则无一点儿调和的余地,否则,国将不国,成何体统!
“中体西用说”的理论预设是正相反对的普遍人性论与人性、种族差异论。主张中西各有体用时,“中体西用”论者的理论预设是人性、种族差异论;主张中有体西有用时,“中体西用”论者的理论预设则是普遍人性论。这里的普遍人性论,指的是无视尘息在不同地域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把全人类文化看成没有人性、种族差异而普天同一的一种理论。而与之对立的人性、种族差异论则只强调生息在不同地域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无视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这两种理论同为“中体西用”论者的理论预设,互克而不互补,“中体西用说”岂能圆融!
从前一理论预设出发,得出中有体西有用的结论,合情合理。然而,“中体西用”论者并未始终贯彻普遍人性论,而时常在两种理论预设之间摇来摆去,置论自然自相矛盾。郑观应明明在《盛世危言》中说过“中学为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偏偏又在同书自序中赞同相反表述:“善夫张靖达公云,西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乎!”〔16〕郑著《盛世危言》屡经修改,有多种版本行世,且内中夹杂他人文字和观点(如王韬的道器合一论和孙中山的策论),也许不足为据。但郑观应在1884年7 月11日的日记中分明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捍格,难臻富强。”〔17〕既然知道中西各有体用,那么何以又说“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一会儿视中西为一体,一会儿视中西为两物;一会儿讲普遍性,一会儿讲特殊性,这理不知从何说起!
说白了,“中体西用说”原本就不是一种自洽的理论学说,而是一种有悖常理却行之有效的“以守成之势治天下”的文化应对方略。依了这两种理论预设,守本又要开新,固道又要求器,顾此失彼,调适得了吗?至于说中学兼有体用,西学有用无体,而且即使是西学的用也是中学失传的,源于中学——“中源西同说”——就更是无根之谈了。假如只求物质文化之同,还不致离事理太远,事实是“中体西用”论者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们时而在异中求同,时而在同中存异。这种理论矛盾深刻地反映着中国社会转型、中西文化最初冲撞的时代特点,无法排解。要守本固道,不得不奉普遍人性论为圭臬,抑西扬中;而要开新求器,体察到变器不协以变政的症结,又不得不以人性、种族差异论为理据,等视中西。欲开新求器又怕丢了老本旧道,欲守本固道又不可能不开新求器,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理论上不能圆融,践行起来势必困难重重。只在制度文化的外沿部分和物质文化层面做文章,就是说,动末不动本,文章注定是做不好的,开头容易终篇难。
这一代文化变革者中已有先觉者注意到这个关目,前引郑观应的话即是确证,他先于康有为呼吁在中国实行宪政。更先于郑观应对“中体西用说”进行质疑的是郭嵩焘。“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先欲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18〕钟天纬推究西方国家致强趋富的“大本大原”,直抵西方制度文化的核心部分:“究其本原,不外乎通民情、参民政而已。盖泰西通例,国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但能奉法而行之,不能权威自恣。而国之律法,则集亿光公议而定;君之权威亦本公助而成,是以君虽有所限制,反能常保其尊荣。民情得以自伸,不致受困于虐政,则不必袭揖让之虚名,而阴已得天下之实际。此则国势强弱,民生休戚之大关键也。”〔19〕此外如王韬、陈恕、陈炽、汤寿潜、陈虬、胡礼坦、何启和宋育仁等,都曾不同程度地建议变政。西政为体,西器为用,中国变革当依西体西用谋本末俱变,这已成为80年代以后众多执意变革者的共识。
倡言开议院、定宪法、君民共主,旨在富国强兵,变政不过是为了顺利变器,替新兴资产阶级在政界争得一席之地,并无彻底颠覆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意思。
郑观应可谓一语道破天机:“政治不改良,实业万难兴盛。”〔20〕他提议“定宪法”,限制君权,扩大民权,骨子里是要求扩大势单力孤的工商资产阶级的权势范围。照他看来,议院的功能仅仅是办日报,公举官员、议员,裁减冗员之类。他虽然同情康有为和梁启超,但对他们的改革行动很不以为然,认定“康、梁办事毫无条理,不知度德量力,将来必有风波”〔21〕。康有为在觐见光绪皇帝前询于郑观应:“政治可变否?”郑观应摆出一副老谋深算的模样,告诫他“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22〕。他与他所属阶级一样单薄、谦卑和软弱。
蒋智由的《风俗篇》也道出了端由:中法战争以后,朝野渐知洋务新政之不可为,渐知“工商之世,而政治不与相宜,则工商不可兴,故不得不变政”〔23〕。钟天纬推尊西政、西法,结穴处却是为皇上献策:“不必袭揖让之虚名,阴已得官天下之实际。”等而下者更把议会仅仅当作打通上下之情的手段。
他们构想的议院仍由王公大臣把持,君权仍然至上,所谓君民共主,实则是君臣共主,换汤不换药。因此,当90年代中叶新一代激进的文化变革者呼啸而至、历史迈向一个新阶段的时候,他们便大都几乎噤声不语。陈炽在甲午前还口口声声称道英美各国富国强兵、纵横四海之根源在于实行合君民一体、通上下一心的议院之法,一俟康梁派崛起、兴中会成立,他立马改口,声称“议院民权,不可再说耳”〔24〕。梁启超至京城大讲民权,他便以“善言”相劝。研究戊戌变法很有成就的专家汤志钧深谙其中奥秘:陈炽“恋栈封建,归本‘圣道’,实与有为有异。盖有为心中之孔子,资产阶级之孔子也;陈炽之‘舍孔子何法’则植根于封建”〔25〕。兴许他们过多从策略上考虑问题,不赞成变政操之过急,深思慎行,这容易理解,但究其实,他们的变政仅停留在口头上,与康梁派动真格的变政根本不是一档子事,更不好与孙中山等人发起的革命相提并论。理论武库储备不足,死抱着老祖宗的道统成法不放,变器、变政唯恐改了旧制,变政与变器不协调,行动起来瞻前顾后,进一步退两步,怎能指望他们捣毁旧制度的老巢!
颠倒道器 重释体用
要开创新局,必先实施对中体西用论的批判,为变法扫清道路。
康梁派攻击洋务派,问题抓得很准。康有为在《敬谢天恩并统筹全局摺》中指出:“今天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周公思兼三王,孔子损益四代,乃为变法。”他进而建议“皇上统筹全局,商定政体,自百司庶政,用人交外,并草具纲领条目,然后涣汗大号,乃与施行,本末并举,首尾无缺,治具毕张,乃收成效”。梁启超宣扬乃师高论不遗余力,说:“中国自同治后,所谓变法者,若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交涉之有总署使馆也,皆畴昔人所谓改革者也。”〔26〕梁启超指斥对象为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藩、沈葆祯之流,责难他们“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支支节节以变之……则于中国之弱亡之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27〕。守本开新,开新不拿政体开刀,“变事”而不“变法”,枝枝节节以变之,改革势必难收良效。
康梁派和严复对“中体西用说”的攻击极为猛烈。严复的批判已见上文。谭嗣同必欲置“中体西用”论者于死地,不留丝毫回旋余地。依从王衡阳“道不离器”之说,他翻转体用、道器,将道置于器下,使道依器而存,器大道小,器重道轻,真意在“用夷变夏”。请看:
窃疑今人之所谓道,不依于器,特遁于空虚而已矣。故衡阳王子有“道不离器”之说,曰:“无其器则无其道,无弓矢则无射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又曰:“道之可有而且无者多矣,故无其器则无其道。”诚然是言也。信如此言,则道必依于器而有实用,果非空漠无物之中有所谓道矣。〔28〕
故道,用也;器,体也。体立用行,器存则道不亡。〔29〕这岂不是降形上之道为形下之道,将“中体西用’论者蔑视的、处于下位的器、用升到道、体的高位了么!“故变法者,器既变矣,道之且无者不能终无,道可有者自须亟有也。”〔30〕这是明目张胆为变法作理论铺垫。谭嗣同的理论推断很有中国特色:
圣人之道无所不包,岂仅行于中国而已哉!观西人之体国经野、法度政事无不与“周礼”合,子思子曰:“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虽不尊亲,其人亦自不能不由其道也。盖亦不自天降,不自地出,人人性分中之所有,故数万里初不通往来之国,放之而无不准,同生覆载之中,性无不同,既性无不善,是以性善之说最为至精而无可疑。〔31〕把中国懦学的“尊亲”推及全世界,用性善概人类,实际上是把儒学中对立于荀子性恶论的孟子一路的性善论加以改塑,搬来批驳中西各有体用的谬论。谭嗣同的要文《报贝元徵》和《上欧阳中鹄书》立意均在此。他这般设问:“中国今日之人心风俗,政治制度,无一可比数于夷狄,何尝有一毫所谓夏者?即求列于夷狄,犹不可得,乃云变夷乎?”〔32〕侯外庐评道:“按此说,西人是夏,我反为夷,变法所以仿效‘西人之夏’变‘中人之夷’,以复古为名,而公然在内容上倡用夏变夷之说。”〔33〕可谓一针见血。与“中体西用”论者共有一个普遍人性论的理论预设,却得出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的结论,肯定与他颠倒了道器的位置有关。而他所公然倡用的以夏变夷之说,则相当接近“五四”“西化派”的中西文化等级观。谭嗣同的确如李泽厚所说,是康梁派中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左翼,其最激烈的理论主张不一定弱于“五四”。不过,谭的中西文化观还不可与“五四”一代同日而语,从上引“圣人之道,无所不包……”那段文字就可以看出,他还是等视中西的。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是攻击“中体西用说”,康有为的理论预设却是人性、种族差异论。他未能将他的性善论贯彻到他的中西文化观中去。在1888年《与洪给事右臣论中西异学书》中,他就辨别过“中西本末绝异”之“势”、“俗”二大端,反对“以中国之是非绳之”。在他看来,中国自三代以来一直是个大一统国度,地广邈,君日尊,君民隔,君权不可能不有所限制,故法治趋于保守和疏漏;西方之“势”则反之,自罗马帝国以后就“散为列国”,各“列国”争雄竞长,地小,下情易达,“争雄则人有愤心”,君民不隔,故法治易变而密实。中西“俗”差在于前者崇等级而后者尊平等:“中国义理,先立三纲,君尊臣卑,男尊女卑……故君尊其国,男兼数女。泰西则异是,君既多则师道大行而教皇统焉,故其纪元用师而不用君也。君既卑,于是君民有平等之俗,女既少,则女亦不贱,于是与男同业而无有别之意……”因此,他判定“各有本末,中国泰西,易地皆然”。康有为不通西文,接触的西书有限,恐于西学多皮相之见,托言谬悠自不可免,不过此论以地缘差为据,有一定道理,还不至于一无可取,不可全盘否定。
另一耐人寻味之处是他虽仍循“中体西用”论式,却置换了这一论式的语义。循“中体西用”论式,必定据以普遍人性论。戊戌年他替人代笔上奏,明言:“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34〕这里的“中学”实指中国的经史,“西学”实指西方的各种时务知识。他说“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35〕,是想打通中西学问,培养兼通中西二学的治世良才。梁启超的论式同于康有为:“舍西学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36〕据梁启超回忆,康有为甲午战争以前讲学“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37〕,此为一说。又一说是他以“由宋明理学与公羊学所结合的义理”为体,以“经世之学,西洋制度与中国历代沿革与学术变迁”为用。〔38〕两说立足点不一,有些出入,各有各的理由。两说也有共同点,即都以为康的体全是中国传统的义理,康在用中才掺进了西学,这无异于康自己的表述。全面看,概言之,他所谓体,是经由他创造性转化的传统的安邦济国的义理之学——思想文化,并非只有中学;他所谓用,是会通旧学新知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中学西学互渗共存在体用之中。他的论式虽一仍其旧,然而,老树新花,确已超迈前代。他与谭嗣同殊途同归,一起冲毁了前代人设置的思想藩篱。
注释:
〔1〕史家惯例是将张之洞等清府大臣称作“洋务派”, 将冯桂芬等幕僚、郑观应等买办称为“早期维新派”或“早期改良派”。在我看来,这两类人的文化构成和文化立场并无太大的质差,与他们有明显文化质差者倒是后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变法派和以孙中山、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
〔2〕请参见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时期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3〕《校邠庐抗议·自序》。
〔4〕《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
〔5〕《庸庵文集·文编》第2卷。
〔6〕《筹洋刍议·变法》。薛福成出洋考察归来后, 思想为之一变,认为中西各有体用,靠近了康、梁。
〔7〕《邵氏危言·纲纪》。
〔8〕王韬:《杞忧生易言·跋》。
〔9〕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
〔10〕沈寿康:《匡时策》。
〔11〕《劝学篇·外篇·设学》。
〔12〕《劝学篇·外篇·会通》。
〔13〕《劝学篇·内篇·变法》。
〔14〕冯天瑜、何晓明:《张之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冯天瑜手迹插页。
〔15〕《报〈外交报〉主人书》。
〔16〕《盛世危言·自序》。
〔17〕转引自夏东元《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18〕《福建按察使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
〔19〕《综论时务》,转引自丁伟志《“中体西用”论在洋务运动时期的形成与发展》。
〔20〕《盛世危言·自序》。
〔21〕转引自《郑观应传》,第298页。
〔22〕转引自《郑观应传》,第300页。
〔23〕转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58页。
〔24〕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第158页。 本文中的康梁派,特指维新变法和本世纪头10年这两个时期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变法者,并非专指对立于革命派的流亡日本的康、梁那帮人。
〔25〕转引自《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第159页。
〔26〕《戊戌政变记》第3卷第3章。
〔27〕《戊戌政变记》第3卷第3章。
〔28〕《上欧阳中鹄书》。
〔29〕《报贝元徵》。
〔30〕《报贝元徵》。
〔31〕《报贝元徵》。
〔32〕《上欧阳中鹄书》。
〔33〕《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778页。
〔34〕《奏请经济岁举归并科举并各省岁科试即改试策论折》。
〔35〕《奏请经济岁举归并科举并各省岁科试即改试策论折》。
〔36〕《西学书目表·后序》。
〔37〕《康有为传·修养时代及讲学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