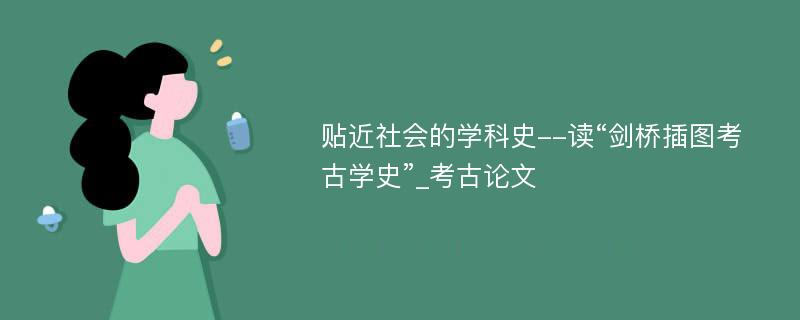
一本亲近社会的学科史——读《剑桥插图考古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剑桥论文,一本论文,插图论文,亲近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大名鼎鼎的阿克敦爵士于20世纪初主编的《剑桥近代史》问世以来,“剑桥”就成了国际历史学界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随后陆续出版的冠以“剑桥”的断代史、地区史与国别史,卷卷堪称学术精品,始终被知识界置于有关专题的主要参考读物清单之列。
“剑桥”成了出版界的名牌,自然引来了不少刻意仿效的东南北施,甚至剑桥的姊妹校和老竞争对手牛津也搞出了一套“牛津”史书系列。但迄今为止,就通论性质的大型历史书系而言,没有哪家的产品胜过剑桥。究其原因,不外是剑桥史书编纂难度相对较大,编纂周期较长,一般急功近利的出版社不愿也没有能力仿制。以作者队伍来讲,剑桥史书的主编和撰稿人均为欧美史学界某个研究方向的带头人,都是货真价实的一流学者。比如20世纪20年代出版的多卷本《剑桥古代史》,主编是饮誉国际史坛的伯里、库克和阿德考克三位史学大师,各卷章节的撰稿人无一不是欧美学界已经成名的专家。待时钟转到50年之后,新版多卷本《剑桥古代史》同样集合了欧美各国的史学骄子,包括牛津大学的路易斯、鲍德曼、哈蒙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奥斯瓦尔德,多伦多大学的格雷森等人。剑桥史书不以是否剑桥教授取人,而外校的众多大教授又愿意应召到剑桥旗下,这种肚量和巨大的号召力是国外大多数出版社难以企及的。有了一流的作者,也就意味着拥有了一流的学术资源,包括前沿性的知识,如果再佐以足够的编写时间(如二版《剑桥古代史》的编写时间长达20多年)——而不是像我国众多大书的编写那样,弄到一个选题,拉上几个名流充当挂名主编,再凑成一批半生不熟的写手,一两千万字的庞然大物,如催命般两三年便能搞定——焉能写不出笑傲史坛的大作。
此外,讲究质量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对品牌的爱护也值得一提。出版社的老总显然懂得名牌来之不易、倒牌子却是轻而易举的道理,所以近一个世纪以来,该出版社推出了成千上万种史书,能在书名上标示“剑桥”字样的也不过十来部。剑桥的这种名牌战略和策略,应该受到苦心孤诣地试图创出名牌的我国众多出版社的高度重视。
但以往的剑桥史书也有它的局限,就是过于专业,书中充满了繁琐的考据和引证,到处是普通读者望而生畏的专业术语、符号以及精致的图表。加之每部书都篇幅巨大,即使是专业人员,若无相应的对某个研究方向的知识准备或全面的兴趣,耐心读完全书或读懂全书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所以这类史书通常只能在象牙塔里流行,或者装饰在附庸风雅的购书者的书架当中,其印数和社会价值因此也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这种现象无论对剑桥大学出版社还是历史学科而言,都不能说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因为历史学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应当负起广泛的人文主义关怀的社会责任。
然而,至少到20世纪90年代初,剑桥大学出版社似乎更注意提高,而忽略了普及。整个西方史学界,也没有对普及工作给以应有的注意,这同自然科学界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知道,世界各国的自然科学家都很重视向普通民众传播科学知识,他们把这项属于人文主义关怀的工作视为科学家应尽的义务。许多科学家,甚至是超一流的大科学家,如爱因斯坦等人,均能够俯下身来,运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为普通读者撰写科普文章或书籍,充当科学知识和理性火种的播撒者,担任“院士科普图书”系列或《十万个为什么》之类书籍的撰稿人。而在至今尚被人怀疑并非属于科学家族的历史学的研究者们,却鲜有从事科普活动的要求,并且倘若有某些专业史家撰写一些通俗历史读物,还可能受到同行的所谓不务正业的指责。
这种“正业”意识当然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自19世纪开始,历史学便随着人类自我认识的速度加快,程度的加深,国民普通教育的需要,逐渐变为少数专业人员的领地,形成了一整套自身的学术范围、认识论和方法论体系、评价标准和表述术语。其历史后果之一就是曾经在两千年里驰骋史坛的业余历史家先后被专家学者排挤出局,以专著和论文为代表的史学成果代替了业余史家的叙述性史书,成为人类社会中极小部分懂行者的精神食粮,历史学因此也从常人之学堂而皇之地上升为历史科学。这当然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因为人类的自我认识需要日益准确、深入、系统和精致,而缺少系统训练的业余史家是很难胜任这一使命的。但人类史上也很难找到没有副作用的进步,人类能力的局限决定了她的任何行为均或多或少地会带来有害的后果。比如史学的专业化、概念化是以传统史学所具有的文学审美和常人之学的丧失为代价的,这就使专业化的史学始终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即如何像前专业化时期的史学家那样,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读者或公众保持血肉的联系。实际上,没有通畅的社会联系和公众的理解支持,任何学科、尤其是人文学科,都不会拥有持久的活力。所以,任何学科都需要承担或者说必须承担向社会公众普及学科知识的责任,将本学科的价值及研究所带来的对自然与社会的各种新的理解,用通俗的语言转达给群众。这种科普活动不是一种单向的人文主义的关怀,它还是学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国外的史学界中的少数有识之士比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比如20世纪最杰出的思辨历史哲学家之一汤因比,就曾在30多年前亲手把他那部艰涩难懂的大作《历史研究》(12卷本)改写成单卷的插图本,以飨普通读者(注:据悉,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在今年下半年出版该书的中译本,这无疑是我国读书人的一件幸事。)。我们知道,配图的论说文图书是深受读者欢迎的一种编写方式,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准备的读者对形象思维的表述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汤因比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插图本中指出图片的重要意义:“配合文字说明的各个插图赋予这部书以新的内容。图片不仅增强了文本的效果,而且能传递大量文字所无法充分表达的信息。”通过深入浅出的文字表述,再结合恰如其分的画面(其实大部分插图本身就是珍贵的史料),汤因比把自己的深刻历史意识传递给了普通读者,众多西方的专业史家也是通过这部普及本才真正结识汤因比思想的。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史书编辑也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自90年代始,他们开始调整“剑桥”史书的编写方针,首次采取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继续推出脍灸人口的剑桥国别史、地区史和断代史,另一方面开始了亲近社会的名牌战略,10卷本《剑桥插图史》丛书的问世便是他们的最初尝试(注:包括《剑桥插图考古史》、《剑桥插图天文史》、《剑桥插图医学史》、《剑桥插图战争史》、《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剑桥插图大英帝国史》、《剑桥插图法国史》、《剑桥插图德国史》、《剑桥插图中国史》、《剑桥插图英国戏剧史》。)。
国内外科普图书的出版经验表明,优秀的普及读物的作者,必定是某个学科的专家,但某个学科的专家,却不一定是好的普及读物的作者。这是因为普及读物需要综合性的知识和技能,除了通识学科的知识之外,还应具备一定的哲思能力和深入浅出、生动流畅的文字表达能力。所以,写科普读物不是件易事,出版社在选题确定之后,往往要花很大气力罗织合适的执笔人。现在看来,《剑桥插图史》在这方面还是相当成功的。该丛书的作者群体尽管仍是西方世界有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但所有的作者都能够放下架子,努力抛弃艰涩难懂、枯燥无味的专业术语、数据和图表,避免莫测高深的宏篇大论,娓娓讲述各个学科以及国家、地区的形成和发展史。而且叙述的对象尽量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的人和事上,而不是专业史家习以为常的抽象的群体。再加上书内几乎每一页都有精心挑选的插图和照片,使得一个没有多少相关知识准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通过阅读文本和品味插图,便能顺利地理解书中的内容。所以,尽管这套书价格不菲,在图书市场上却反映甚好。这自然引起我国一些对国外图书市场行情颇为敏感的出版社的注意。山东画报出版社便是其中之一。该社在普及历史学知识方面已做出了一些抢眼的成绩,《老照片》等“畅销产品”便是明证。而《剑桥插图史》的配图形式又同该出版社的专长极为吻合。因此该社老总和编辑再次显示出他们的眼力和决心,迅速购买了《剑桥插图史》丛书中的《剑桥插图考古史》和《剑桥插图中国史》两书的版权。
现在《剑桥插图考古史》中文版的翻译、编辑、印刷等工序均已完成,即将投入市场,据说征订情况喜人。笔者有幸先睹为快,感到这的确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好书。它采取叙述体的表述形式,依时间和空间的顺序叙述考古学的缓慢进步:从早期古物收集者们盲人瞎马般的摸索到当前高技术、多学科项目的研究,从博学家的时代到高度的专业化阶段,从一窝蜂地争挖奇珍异宝到为解决特定问题而进行的探寻。这是一部有关人类对自身过去的兴趣和认识在不断深化的长篇故事,具有很大的信息量。
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考古史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这些考古故事中的精采情节,如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的发现,埃及法老土坦哈门陵墓的发掘,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墓葬的出土,考古学家如何从一块陶瓷碎片上提取多种多样的信息(它的年代、装饰、原材料及其来源、烧制的温度、盛过什么食物)等等。通过读书品图,广大读者还会进一步知道考古学家不是离群索居、专门在田野上打洞的少数怪人。他们有常人的个性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他们当中有高尚的君子,也有卑劣的小人,有亲密无间的合作,也有尔虞我诈的竞争甚至敌视。而无法无天的盗墓和文物走私活动也曾经是、现在仍然是正常考古发掘的伴生物。普通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将了解更多的有关考古学的知识,最终将结识他们所很少知晓的考古学。
但本书绝不仅仅是关于探幽猎奇、取悦大众好奇心的考古故事的集锦。它有清晰的编纂思路,既记述不同时代考古学家的非凡贡献,又介绍考古学家对考古学科本身的理论反思,这就使该书对我国专业考古工作者和史学工作者也有一定的阅读价值。
由于我国待发掘、抢救的考古遗址为数众多,国内考古工作者多年来忙于田野发掘工作,相当多的从业人员对国外考古学发展状况以及世界考古史所知甚少。虽然在这本《剑桥插图考古史》问世之前,文物出版社曾出过一部近似世界考古史纲的著作,即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的中译本,但由于该书内容简约,结构失之于琐碎,且重点在欧洲和近东考古,编年范围又偏重20世纪50年代以前,所以还算不上是世界考古通史的全景介绍。《剑桥插图考古史》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其编年上限位于考古学的发轫时期,下限迄于20世纪90年代,最后一章还专门讨论国际考古学界存在的论争问题,并对考古学发展的未来趋向加以展望。其空间范围覆盖整个地球表面,而且各个地区考古发生、发展过程所占的篇幅和插图的数量也比较均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在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和人们所知甚少的事物之间、在考古学的一些伟大突破和有时并不引人注目但却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些事件或发现之间,力求找到一种平衡。所以该书的作者很自信地说:这本书是“第一部在真正的世界范围内对考古学的发展进行考察的书”。
书内的许多事实陈述和价值陈述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比如,作者指出考古学认识并不因其认识基础是实物史料便不存在主观性,这一学科的理论发展已使人们意识到,考古学家不只在重新发现过去,而且在不断地创造过去。这是因为从地下挖出来的各种史料必须由人来解释它们,而考古学家正是它们的解释者。尽管大多数考古学家力求客观地再现过去,发现过去“真正”发生了什么,但由于他们没有能够穿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机器,他们所能做出的最佳成果仍是一种可以为人所接受的虚构的故事,一种根据无法验证的资料所推演出来的故事。作者列举了考古史上出现的一些习见的误解,譬如关于尼安德特等古人类化石的错误复原图,关于在苏卢特发生的所谓野马从山崖上被驱赶下来、成群摔死的假设,关于莫须有的德国考古家谢里曼从小就矢志挖出特洛亚城的传说,关于英国巨石阵的错误解释等等。在作者看来,这些学术误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科学正是在“这种文学的偏颇”中,通过话语和视觉形象为世人所知的。所以作者认为考古学史是一部颇为复杂的历史,它不单讲述关于考古发现和各种新的研究技术的历史,而且还涉及到新的、不断更新的解释范式。正因为如此,我们虽然都由过去塑造而成,但我们实际上又通过考古实践在为我们自身创造着过去,不断改写着考古学的历史,人类的历史也因此一代又一代地被人改写或创造出来。有鉴于此,人类对自身过去的认识是无止境的,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从而发现终极结论的做法是幼稚可笑的。
再如,作者提出要警惕考古学变成新古物学的危险,提倡考古学家注意探讨古文物中人的情感和思想;考古学要不断吸取人类学、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考古学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能够促进人种或种族的和谐,因此它是服务于人类的学科。考古学不是学界精英的智力游戏,它需要与社会保持血肉联系,需要公众的支持、考虑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兴趣。这些见解对我们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当然,前面讲过,写作一部世界范围内的史书不是容易的事。由于知识分工越来越细,通英国考古,未必懂中国考古;懂中国史前考古,未必懂秦汉考古,所以内行的人在这本书中能看到少量的史实错误,某些价值评估也有不尽合适的地方。此外,书中仍有某些技术语言的痕迹,且书成众手,内容选择、组织和表达的质量参差不齐,但这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是英语世界第一部内容比较全面的考古学通史,为我国考古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如何亲近社会的范例——学科史原来也是可以这样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