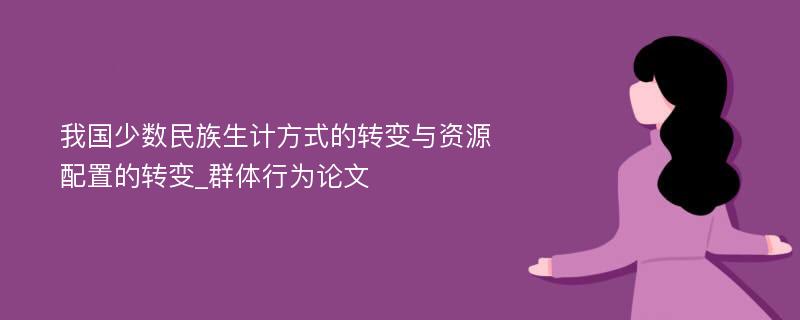
中国少数民族生计方式转型与资源配置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生计论文,少数民族论文,中国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5)01-0023-08 资源作为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交换互动的核心中介,乃是生计方式中至关重要的基础性核心要素[1](61)。围绕资源,各人类群体在长期实践中发展出特定生存技术,构建了风格各异的采集渔猎、农耕、畜牧等谋生方式。基于此,生计研究重点关注资源环境与人类的技术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围绕谋生能力(Capabilities)、资产(Assets)和活动(Activities)等要素所展开的[2](296),各类资源的选择、获取、转换与积累等。而资源不但应当包括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3](378),同时还必须囊括借由宗教信仰、文化价值观念、生产生活习俗等共同构建的文化符号体系。进而,资源的流动与配置方式不但组织了生计活动的全程,贯穿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所有环节,而且还与社会结构持续地深度互动。中国少数民族生计方式因而呈现为紧密关联生态资源、技术行为、宗教与习俗及社会组织制度等的一种整体性。而其现代转型也就展现为由国家和市场所主导的、支配资源配置的权力制度及其组织架构的对应过程,该过程同时也引发了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 一、维系期中的民族生计形态与资源配置结构 中国各民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契合各自生存环境的生计方式,它们可大致概括为采集渔猎、农耕与畜牧等方式。如果把1840年视为我国近代史的开端,那么由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便可以被界定为各民族生计缓慢变迁的维系期。近代变迁的首推力当属清代“改土归流”以及20世纪初移民政策的实施,此后便在畜牧与农耕区域之间形成了持续扩大的半农半牧区域[4](20)。随后西方列强对边疆的殖民与盘剥,使他们在不平等的市场资源配置中被迫卷入全球商品流通体系。但由于未能改变既定结构之根本,各民族生计只能以衰落之势缓慢运行于传统轨道之上。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却显现出如下共性。 第一,各民族传统生计绝非通常所认为的单一或封闭,而是在采集渔猎、畜牧、农耕等宏大概念的掩盖下,附生了众多辅助生计。它们共同构成了高度互补的、多样化的整体结构。采集渔猎的内部构成便纷繁至极。如19世纪前的鄂伦春人主要以狩猎狍、鹿、野猪、熊等为生,同时还饲养驯鹿、捕鱼等;辅以种类达四十余种的植物、鸟蛋等的采集;还有制作皮制品、毛织品、桦皮制品、骨制品等手工业,以及与周边其他族群的交换活动[5](42,92,105,143~144)。他们的生计因此关联到吃、穿、住、用、行等所有生活层面。 而作为人类积极利用有限资源环境的游牧,同样伴生了大量的辅助生计。如历史上藏族的狩猎采集;嫩江流域扎赉特旗努图克蒙古人以牧业为主,兼以狩猎、耕种蒙古糜子及制作牛车等为副业;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人的季节性种植青稞、小麦和玉米,部分哈萨克人兼营农业等。进而,还有常见的对外贸易、掠夺乃至战争等,都需视为其外部补偿性的辅助生计[6](34~39)。 再从农业来看,景颇族、德昂族、部分哈尼族的3~20年不等的刀耕火种,包含着棉、稻、玉米等多种复合作物的轮作,乃至各种杂粮、药物等。其休闲地同样不可或缺。如基诺族的休闲地不仅是木料产地,同时还兼营放牧、采集和狩猎。在定居农业群体中,虽然生计的复杂性有所削弱,但耕织结合是普遍现象,此外通常还兼有林业、家庭养殖业、手工业、采集渔猎等。如侗族单是糯稻品种便达数十种,另外还发展出在稻田里蓄水养鱼的技术,在近代甚至还兼营经济林。 在某种主导方式下,民族传统生计因此容纳了千差万别的具体方式组合,并以森林、水流、草原、耕地、动植物、劳动力等资源的复合性配置构成了高度互补的整体性结构。这种内部多样性不仅源于人们对生存风险的规避及其外部交换的有限性,同时也根植于他们保护自然环境资源的考量。 第二,各民族构建了低度的但同时也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生计方式。它们经由资源的动态平衡配置来实现,并通过文化体系来给予保障。我国少数民族大多置身生态脆弱的边疆地带。在长期适应的基础上,各民族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维护人类与自然之间均衡互动关系的技术方式。如蒙古族采用多种家畜在不同草场之间季节性地轮流放牧,不但保证了家畜生产率,同时也对草原实施了严格保护。瑶族对耕地的有意识利用和保护,则采取一是就地取种;二是林粮间作;三是不营纯林[7],以此保证生态环境与生计之间的有机平衡;早期苗族的食物来源多达数百种,虽产量不高,但恰是不断改变取食对象及其方式,保护了喀斯特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与之相较,他们在近代前后开荒营造梯田,却导致了栖息地的严重石漠化,最终陷入生态破坏与生计困难的长期恶性循环[8]。可见,在脆弱生态环境中采用浅表的、低度的、可持续的生计方式,当是维持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能量持续交换的必要路径。 此外还有与之配套的文化系统的重要作用。它们体现为系统性的习俗、习惯法、宗教及超自然力量等,所实施的对自然环境的强制性保护。如藏族围绕神山崇拜所产生的狩猎禁忌,并延伸至对草原、动植物、水源等核心资源的保护[9],违者视情况处以罚款、鞭打甚至被永久歧视。宗教因而是各民族保护生态资源的常见关键因素。 可见,各民族群体以其特定生计技术与文化保障体系,使之在低度但却可持续地发展本土生计时,在资源的复合利用与消耗的强制限制中,避免了单一生计对某些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破坏。当然,这是以人们的制度性协作为前提的。 第三,各民族传统生计均包含各类资源的群体互惠配置,它们具体体现为共同体内部的各种互助和社会保障。虽然近代以来中国各民族的生计活动与资源配置单位,大多都已落实到了个体家庭之上,但基于土地、森林、草场、水流等资源不同程度的公共享有,使之仍保持着不同形式联合的生计互助。如云南各民族中常见的“共耕”,便包括氏族共耕、家族共耕、兄弟共耕、亲戚共耕、氏族之间的共耕,以及基于买卖关系的共耕等多种样态[10](121~146)。此外更为常见的,是在秋收、盖房、修路等重大活动及各类仪式活动中,共同体成员都会相互帮工,共同分享食物。如云南省西盟县岳宋佤族寨1954~1957年剽牛874头,然后便是众人分享食物。他们每年该项花费占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11](81)即便是在阶层分化明显的群体中,人们依然会以公共事务管理、公共设施建设、危机保护等方式,在资源的再分配中着力实现共同体的整体生存安全。资源的互惠配置实质上构建了小共同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在共同体外部。长期的族际往来推动着各民族生计方式的缓慢演化。如处于农业、牧业交接地带的部分土族、藏族等,较早便形成了兼具农业、牧业生计二重性的特点。而1840年以来的近代商品化、市场化进程,并未真正推动各民族生计的发展,反而是在外部不平等力量的挤压中,大多巩固了他们的传统生计,同时又使之不断趋向凋敝。其根源在于,当时基于畸形不平等市场交换的资源配置,并非指向商品交换本应有的差额积累目标,而仅是将其兑现为当地人日益萎缩的基本生存所需。结果便是空前加剧了各民族传统生计边际效益递减的过密化现象,并最终将其推向崩溃边缘。 综上,至20世纪中期,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生计仍呈现出较突出的整体性——资源的复合性配置所构建的多样化、互补性的整体;资源的平衡性配置及其文化保障,所秉持的低度的但却可持续性的生计方式;资源的内部互惠性配置所构筑的共同体保障制度体系等。而其基础在于,共同体自身掌控着生计资源配置的支配权,即采集渔猎群体的血缘氏族组织依然主导着共同体资源安排;游牧群体多样化的家庭联合仍是畜牧生计的最普遍组织方式;定居农耕群体依然高度重视基于亲属与地缘关系的资源共享与流通。而其间的商品化进程,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外部力量,对他们的资源配置权的全方位侵蚀和剥夺。该历程开启了各民族生计方式的初步缓慢转型,并呼唤着随后的根本转变。 二、重塑期的资源配置调控与生计集体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少数民族生计方式转型的第二阶段。国家对各类资源的强制性配置,推动了生计方式前所未有的整体重塑。但它还可以细分为两个时期,即1949~1958年的以土地改革为重点的过渡期,以及1958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全面集体化时期。 在第一个时期,新生的共和国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了渐进式的生计变革。结合具体实际,除了北方牧区较早对牧主实行缓和的改造和赎买政策外,其他区域以普遍较晚且有所差异的方式完成了改革。如在农耕民族中实行土地改革。即将地主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大致平均地配置给个体家庭;藏、傣、凉山彝族等,在和平协商的基础上开展了民主改革;采集渔猎群体只是进行了援助与部分变革,直至1958年前后才直接过渡到公社公有制。 该时期最突出的生计变化,当是资源向个体家庭的私有配置,其结果是极大消除了曾经的田租、劳役等负担,显著推动了各民族生计的发展。如我们曾调查过的湖南省永顺县双凤土家族村,1951年贫雇农人均水田仅0.068亩,至1952年6月土改完成后,人均分得水田1亩多,村民生产热情高涨,粮食困难问题得到较好解决。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新生村的鄂伦春族,该时期也发生了从游猎经济向定居生产的转变。但直到1956年,猎业收入仍占其总收入的62%,其间甚至还成就了其狩猎史上的“黄金时期”。可见,该时期各民族生计显著发展,但很大程度上并未改变其传统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方式。相应地,人类与自然环境资源之间的协调平衡,特别是文化保障体系与共同体的互惠系统等同样得以延续。如该时期四川阿坝的嘉绒中等户藏民,仅向寺院供奉的青稞一项就占全年粮食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当然,其前提在于各民族共同体依然保持着资源配置的较高自主权。 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至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要求农业在短期内快速增产,并希望通过工农产品价格之间的“剪刀差”,实现工业化初期的资本积累。国家因此从技术、组织、配给等方面实施了统一改造。该进程对各民族生计的影响直接而重大,但同时又是有所差异的。 首先,在资源要素的高度统一配置中,各民族生计方式从多元趋向单一。生产资料的全面公有化调控,以及伴随其间的集体劳作、食品的统购统销、人口与商品流动的严格限制等措施,特别是在“以粮为纲”路线下的种植业的极力推广,实质上取缔了传统生计中的诸多亚类型。 先从农耕群体来看。重塑期种植业主导性极度突出,使得几乎所有资源都偏向了该领域的单一化配置。而家庭饲养业、手工业、林业、商贸交易等,则被纳入统一的集体运作。笔者曾调查的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箐口哈尼族村,1967年时为116户533人;671亩田地,当年粮食总产量约38万斤;猪82头,黄牛20头。与之比较,1979年时为142户726人;田地632亩,粮食共约31万斤,每人平均分配300斤;猪116头,牛66头,此外便只有零星的林业等①。历经12年后,该村人口显著增加,但生产方面除了牲畜有所增长外,粮食总产量反而下降近20%。因此该时期最突出的,一是各民族生计的单一化及其资源复合性配置的弱化,二是国家基层政权对传统家庭、共同体资源配置功能的取代。它们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农耕生计的显著困难。 与之相比,该时期对牧业群体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定居农耕的推广。其中最突出的,当属60年代期间开展的、为期三四年的草原开垦浪潮。如内蒙古115万多公顷草原的开垦,造成1976年比起1965年来牲畜10.7%的下降[12](206)。加之副业、商品交换的停滞,以牧业为主导的传统生计结构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而刀耕火种、采集渔猎群体,则在“直接过渡”政策下,通过“消灭刀耕火种”“农业学大寨”等,实施了定居农业改造。其后果不仅是他们的传统生计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整体变迁,还随之衍生了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 其次,资源配置向种植生计高度增产的单方面侧重,加之宗教仪式等活动的停止所导致的环境资源强制性保护功能的缺失,削弱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机制,产生了部分民族地区的生态破坏问题。这方面的影响集中体现在非农业群体中。 如新疆富蕴县恰库尔图河段的阔斯阿热勒村,1960年至80年代因为土地的盲目开垦与定居人口增长,急速破坏了平衡、稳定的生计系统。其间粮食产量虽然获得短期提高,但却让沙漠面积迅速扩张[13]。再如50年代以后云南苦聪人(拉祜西)的毁林烧荒,其根源是在定居定耕的导向下,管理者硬性划分了国有林范围。虽然在短期内保护了部分林木,长期而言却切断了他们传统的螺旋式的刀耕火种序列,结果便是无序的毁林烧荒,以致很多山地至今荒芜[14]。这一悲剧的实质,乃是当地人将本该循环游动、浅表开发的刀耕火种技术,改之以固定的、深度开发的方式来实施,其结果便是生态环境的破坏。 另一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于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的禁止,以及相关保护自然的观念、管理制度与惩罚措施等的消散。如在笔者曾调查的云南省红河州河口县桥头乡老刘寨苗族村,村民们认为:“以前每年‘祭龙’,风调雨顺的!集体时候不准搞,寨子连水都某得(没有)喝!”经实地勘察与访谈后可推知,当是因为那时禁止砍伐神山禁忌的骤然空缺,致其水源系统受到极大破坏所致。 最后,在该时期除少量群体外,资源的高度公有化配给取代了大部分民族共同体的传统互助体系;进而,基于外部市场交换的生计及其资源流通也大多被阻断。但必须强调的是,不同生计类型的群体反映差异较大。 农耕群体所受影响尤为突出。以双凤村为例,1958年进入高级社后,虽然仍以村寨为基本单位,但土地、林地、劳动力等核心资源均由公社统一支配。共同体自身的互助保障功能被彻底切断,加之相关因素的作用,导致了1959年饥荒的爆发,村民们大多得了营养不良的水肿病[15](68~71)。再从我们长期调查的信仰基督教的云南省昆明市富民县芭蕉箐苗族村来看,约从70年代中期开始,生产队其实已经默许了村民们的宗教活动,并且还与教会合作,来共同组织生产、安排资源配置。究其实质,当是在与新兴基层权力长期博弈后,资源的配置权相当程度地重归了共同体本身。 但牧业群体却与前者的遭遇又有不同。1965年前,有限度的集体化使牧业总体上呈现为稳中有升的态势。如内蒙古1957-1965年,畜产品、商品流通量等都实现了约1倍的大幅增长,特别是东苏旗,在以畜群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探索了规划轮换放牧、按劳分配、畜股报酬、生产责任制等制度创新。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牧业的下降,主要便是因为之前灵活的资源配置方式被高度简化的全面公有化所取代;加之统购统销对市场交换的替代[16](64~92)。可见,建立在个体家庭多种形式联合基础上的一定程度的公有化,是适应畜群的迁徙游动等特点,并能抵御生产的不确定性风险且促进牧业生计发展的。 与之相比,采集渔猎群体更能适应该时期的高度公有化。如1958年的变革,并未改变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景洪市补远乡基诺族的土地公有、共同劳动经营与平均分配的根基,他们“原有的社会组织及制度。仍部分地寄存在新集体经济的‘躯壳’之中”。鄂伦春族、部分鄂温克族、怒江福贡的傈僳族,以及苦聪人等,同样对公有制持高度肯定态度[12](76~79)。在国家援助下,他们在该时期中传统生计的良好态势,正是源于此时高度的公有制,实质上重归了其“原始”公社集体协作的传统。由此可见,公有或私有并非某种社会进化发展阶段的标识,不同类型的生计方式内在地吁求与之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方式。 由上可知,从1949年至70年代末,国家通过对资源的公有化调控,对各民族生计实施了全面改造。其核心一是各类资源向定居农业生计的单一化引导,一是推行生计资源全面的公有化配置。各群体生计曾经的整体性结构就此被极大地解构了。但需要强调的是,如在农耕群体中,其生计技术并无实质改变,关键是资源的全面公有化配置违背了个体小农的生计传统,从而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等问题。而畜牧群体尤其是采集渔猎、刀耕火种群体,却不同程度地适应与其传统生计内在契合的公有制。他们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向并不熟悉的定居农耕转变,各民族的生计方式及其资源配置结构由此在该时期被重塑了。 三、从加速到迟滞期间的生计方式与资源配置市场化 上个阶段国家在资源计划配置中的生计改造,特别是定居农业的推广,让各民族生计方式渐趋相近。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该领域发生了更具根本性的变化。纵向来看,1999年少数民族村寨人均纯收入1264元,比80年代增长15倍[17]。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95年的3055元至2009年增至18133元,增长近6倍②。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各民族群体的传统主导生计普遍表现为两大阶段的不同发展态势,即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加速发展期,到2000年前后逐步下降甚至大幅衰减后进入了迟滞期。与之相应的则是三类新兴生计的快速拓展,及其对生计结构及资源配置方式的彻底改变。 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先后在各民族群体中落实。尤其是对农耕群体而言,其主导生计并未变化,关键在于资源配置的主导权重新回归了拥有长期历史经验的个体家庭,从而快速推动了生计发展。再以箐口村为例,1985年该村当年耕地播种面积769亩,粮食总产量39.79吨。较之1979年,粮食产量增长2.57倍。至2000年水稻总产量更比1985年增长7倍还多。资源配置家庭化的有力促动,加之新品种作物、种植新技术及农药、化肥等的引入,使得农耕生计实现了空前增长。该时期因而可谓之各民族生计发展的加速期③。 2000年前后,传统主导生计普遍步入了迟滞期。如2007年箐口村粮食产量仅为322吨,7年仅增长1.17倍。更具代表性的是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府村的蒙古族,至1992年超过70%的家庭已经完全放弃畜牧生计,转而依赖占据25.2%的农业,以及35.9%的养殖、种菜、外出务工等其他生计[19](53~57)。人们因此极大缩减了劳动力、资金等向传统主导生计的配置。传统辅助生计同样如此,如纺织品、手工艺品、家用品制作等因为难以与工业产品相抗衡,从而出现了普遍的消亡现象。各民族传统生计的整体互补结构及其复合性资源配置模式,因而在当代已经基本解体了。与之相伴随的,是90年代以来基于市场经济的三类新兴生计的蓬勃兴起,它们彻底改变了各民族生计的基本结构及其性质。 第一类为基于本土资源和技术调适的新兴作物的种植、牲畜的规模化养殖等。如1994年后的四川省汶川县龙溪乡阿尔羌族村,莲花白、青椒等经济作物的增长尤为迅猛。该项收入占一般家庭总收入的60%~70%,有的家庭甚至高达90%[19](655~672)。显然,这只是保留了传统种植业的形式,而其实质已发生质变。在牧业群体中,则是除了商品化的牲畜规模养殖外,苜蓿、玉米、小麦等的种植正成为很多群体的新兴副业选择。它们引导了生计方式的结构性转变,而且其目标已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保障,而是明确指向差额利润的积累。 第二类是基于外部市场的以务工为代表的劳动力资源向外部配置的方式。如甘肃省宕昌县河坝风景区新坪藏族村,1990年外出务工青壮年劳动力人口的比例为2.7%,至2005年便增至36.8%[20],它已成为当地人获取现金收入的最重要方式。各民族群体均与之相似,外出务工甚至已然将他们的当代生计改造为一种“半耕半工”的二元结构[21]。这种新兴方式表明少数民族生计及其资源配置方式正在被市场经济加速整合并结构化,从而与汉族群体日趋同质。 第三类为依靠当地民族文化、土地等优势资源,在市场经济中探索新兴生计的方式,包括当前兴起的乡村旅游、民族手工艺、乡镇企业及土地出租等。如云南省通海县纳古镇回族,凭借其机械制造传统,2005年工业占据全镇总收入的91.32%,15%的家庭每年收入达数十万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9年后,定居下来放弃狩猎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托扎敏乡的部分鄂伦春村民,因为难以掌握种植技能,只能靠出租土地间以采集等维生,甚至出现了返贫现象[22]。通过对比可知,这类新兴生计转型成功与否,取决于民族特色资源以何种路径进入市场体系,即究竟是本土资源的资本化运作,还是局限于生存保障的被动目标。本土生计的隐退与获利性新兴生计的拓展,在该过程中因此是一体两面的,它们共同解构了传统的复合性资源配置方式。 此外,在市场资本原则主导下,资源向能够带来快速增值的现代生计的单向度配置,加之传统生态保护诸多强制性内容的消散,打破了自然资源与人类消耗之间的平衡配置机制,随之引发了相应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为了追求更高的产量和利润,青海省玛多县藏族“围栏封育”等的实施,违背了传统的“不动土”生产、转场浅牧、多畜种放牧、保护野生动物等有效规避生态脆弱环节的文化规则,冲击、破坏了黄河源区生态系统的关键枢纽。至2000年,全县沙化面积可能已达64.7%[23]。生态环境受到更广泛影响的是牧区以农改牧的推广。如在内蒙古地区,抛荒后的地表快速风蚀,致使沙化严重。据统计,近年来内蒙古2/3的旗县和60%的垦殖农田,都受到沙漠化威胁[24](168~174)。生态环境资源显然同样被纳入到资本利益攫取的运行轨道上来了。进而,那些高利润的、深度开发的、高消耗性的现代生计,被普遍用来改造他们低度的、但却可长期持续的生计方式。其结果则常常是诱发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长期尖锐矛盾。 另一保障民族生计与生态安全的重要因素,即经由习俗、习惯法、宗教禁忌及超自然力量等所构建的生态保护文化体系,进一步减弱乃至消弭了。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勐罕镇的傣族,橡胶生计所伴生的经济理性扩张,让曾经涵养水源的神林“奄林”被不断砍伐,人们对土地的尊重与珍爱也转变为一种掠夺关系[25]。与人类具有内在生命关联的自然,已然逐渐对象化为工具性的资源,从而使其发生了“符号性死亡”[26](229),并由此内在地解构了曾经的资源平衡配置机制。 再次,80年代以来资源配置的个体家庭化与市场化,在推动生计的独立性、巩固以个体为基点的全新生计结构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解构了传统的互助互惠体系。 资源配置的家庭化得到绝大部分民族群体的认同接纳。但对于采集渔猎群体来说,其反应却有所不同。如滇西北的独龙族因为承包制的到来,一度遗弃了辛劳开垦的江边田地,居住和生活更为分散;甚至直至90年代,还有最多时达38户的苦聪人家庭重返森林[12](77,67)。类似的极端反应,根源于个体化终结了他们传统的、高度集体互惠的生计方式。 在其他群体中,互惠生计同样极大地弱化了。但它们并未完全消亡,而是得到不同方式和程度的存留。如新疆昌吉市阿什里乡胡阿根哈萨克村,1984年实行牲畜折价归户、草场使用权承包到户后,村民仍以10户左右的牧组为单位来组织牧业生产。而其他各群体的互惠依然在农忙时节、盖房等的帮换工中,在各类仪式及日常礼物流动中得以延续。 互惠生计的意义主要在于本土社会保障功能。而它的当代消亡,不但可能助长因贫富分化过快等诱发的社会矛盾,甚至还会如芭蕉箐村那样,因为强调公平、公开、互利的互惠机制的失效,从而直接阻断共同体新兴生计的拓展[27]。反之,如果互惠生计运用得当,则不但能够帮助个体家庭分担市场风险,降低政府的社会保障成本,还可能像纳古镇回族的股份制那样,在新型互惠方式的缔结与本土资源的整合中推动当地生计高速发展。 80年代以来的宏大历史进程,实现了各民族生计的空前发展及生计结构的彻底变革。在这一时期,生产技术、环境资源与社会文化制度等关键生计要素的实质,均已发生了彻底改变。而其核心动力,除了资源配置的家庭化制度变革外,更重要的是来自市场经济的结构化整合。如果说以往各民族生计是基于生存所需,并在注重人类与自然、个体与群体关系平衡基础之上的,借助互惠流通来实现的一种整体性模式的话;那么当代各民族的生计,则是在独立个体的基础上,逐步转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并以货币为主要收入方式来构筑的全新复合形态。当然,这一快速而激烈的变迁,在持续提升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配置在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失衡,以及共同体资源互惠配置弱化等问题。 四、结语 中国少数民族生计现代转型的波折历程揭示了生计绝不仅仅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而是围绕资源配置为核心展开的一种人类与自然环境,以及人类之间相互交流、交往的最基本活动。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呈现,其变迁也必然牵连到人们生产生活实践的全面变革。在国家与市场两大力量的驱动下,它集中表现为各民族群体资源配置机制的结构性变迁,即从本土共同体的复合性、平衡性与互惠性配置方式,先后转变为国家控制下的、资源高度集中支配的实践,再到当代以资本为原则的、以市场运作为主导的基本模式。对这段宏大历程的回顾表明,各民族的生计目前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但其间的跌宕事实也揭示了,要实现他们当代生计的顺利转型,一方面除了重视技术能力提升、新兴生计方式的探索外,同样还必须强调环境资源保护与关联文化制度的建构;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生计内在地要求与之适配的资源流通脉络,因而需要在充分考量传统资源运作机制的基础上,探索更具弹性的生计资源配置方式。 收稿日期:2014-10-17 注释: ①箐口村数据资料为笔者从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档案局查询,并结合田野调查整理获得。以下其他调查过的村寨的相关数据同理。 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相关数据测算,见http://www.stats.gov.cn。 ③该时期采集渔猎除了在鄂温克族、赫哲族、鄂伦春族等群体中还有部分残留外,作为主导生计已经在我国基本绝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