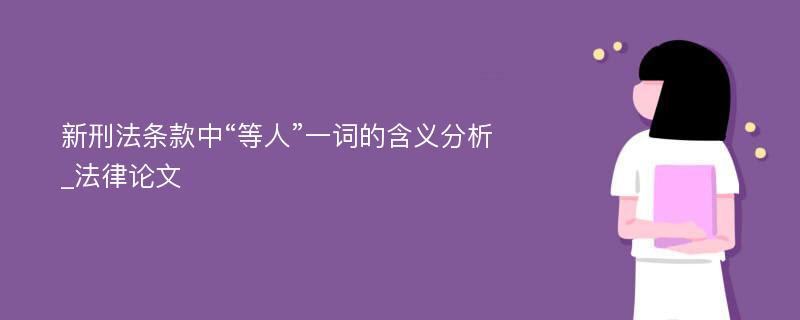
新刑法条文中“等”字意义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中论文,意义论文,新刑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及其意义
1997年刑法中共有29个含“等”字的条文,计35个“等”字。这些“等”字都用于列举之后,例如第56条“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如果“等”字的这种用法只有一种含义,绝无引起歧义之虞,对此辨析也就毫无意义。事实上,“等”字用于列举之后有两种相反的含义:一是“表示列举未尽(可以叠用),如京、津等地、纸张文具等等”;二是“列举后煞尾,如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等四大河流”。(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出版社1992年版,第277页。 )对刑法中的“等”字应作何理解呢?是一律表示列举未尽?还是一律表示列举后煞尾?抑或两种情况兼而有之?司法实践中确实提出了类似疑问。
有论者说:凡如第56条列举后加“等”字的,都表示列举未穷尽;而如“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等四大河流”的表述形式,之所以表示列举后煞尾列举已穷尽,是因为从前后文可以推断出列举已穷尽。刑法中“等”字的表述形式皆如第56条,故一律表示列举未穷尽。但此论也存在反对者。
众所周知,“在法律中,有时一句话或一个字就能影响到人的生命财产,企业的活动,机关的职责,法律用语发生错误,会影响到法律的权威性,并导致破坏法制。”(注:吴大英、任允正著:《比较立法学》,法律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35页。 )对“等”字的理解也概莫能外。比如在适用刑法第56条时,如果将“等”字理解为“列举后煞尾”,则对于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之外的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就不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反之,将“等”字理解为“表示列举未穷尽”,则可以对前面列举的五种犯罪之外的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比如故意伤害、盗窃)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在此,对一个“等”字两种不同的理解,就决定了一部分犯罪分子政治权利的予夺。而在有的“等”字条文中,两种不同的理解,却决定着一个人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重大问题,其所涉罪名有时甚至是可处死刑之罪!一字之义,即关乎公民权利予夺,甚至关乎死生大事,真是不可不审慎详察啊。
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法律解释方法,对“等”字意义加以辨析并予明确,希望于司法实践稍有裨益。此外,对于此种歧义的产生原因及预防方法,笔者力图通过立法与司法两方面加以考察并提出建议。
二、辨析结论:“等”字均表示列举未尽
法律解释学认为,任何法律条文之解释,均须从文义(文理)解释入手。(注: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45页。)因为法律的语言文字是立法意图的直接载体,立法者在一个法律规定中使用了什么样的词语,运用了何种语法规则,都体现了立法者对该规定意义的取向,因此,要阐明法律规定的含义,必先运用文义(文理)解释方法。(注:参见李希慧:《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32页。 )如在文理解释后含义明确,不存在歧义的,就无需再运用论理解释法;如果有复数解释结果存在之可能性,应继之以论理解释。(注: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第245页。)如前所述,“等”字单纯从字面解释看,存在着相反的两种含义,因而就必须继之以论理解释,(注:论理解释的特点是:在解释刑法的某一规定时,不拘泥于该规定的字面意义,而是联系一切与之有关的因素阐明其含义。论理解释具体可分为系统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等八种。同前引参见李希慧:《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10页。 )以明确其含义。
(一)系统解释的结论
系统解释法就是将被解释对象置于刑法系统之中阐明其含义的方法。其功能之一是,在法律用语含义歧义时,通过系统解释明确法律用语的含义。因为从逻辑上讲,从应然角度看,同一刑法规定中的同一用语应用同一含义。(注:同前引参见李希慧:《刑法解释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21、123页。另,刑法系统具有层次性,其最大系统是由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非刑法规范中的刑法规范三要素构成,此三要素又各有若干构成要素。(同前引参见李希慧:《刑法解释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10页)本文所涉刑法系统仅限1997 刑法典。而关于同一规定应有同一含义的应然性, 可参阅吴大英、任允正所著《比较解释学》第235页。)
我们先看看“等”字含义明确的刑法条文。如第352 条中的“罂栗等毒品原植物或幼苗”,至少包括大麻这类毒品原植物或幼苗,其“等”字显然表示列举未穷尽。因为第357 条已明确规定本法所称毒品包括鸦片、大麻。并且其邻近条文第352条“非法种植罂栗、 大麻等毒品原植物”,除罂栗外,还列举了大麻植物。如果第352 条中的“等”字表示列举后煞尾,而不表示列举未穷尽,就有三个疑问产生。首先,单从语法看,也没有必要使用“等”字,为什么不直接表述为“罂栗种子或幼苗”?其次,为什么对大麻这种毒品,立法者要在两个邻近的条文中采用如此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处罚)标准呢?最后,既然第357 条已明确规定本法所称毒品包括鸦片、大麻,为什么第352条会是例外? 显然,持“列举后煞尾”论者无法回答这几个问题。因此,第352 条中的“等”字表示列举未穷尽是毫无疑义的。
根据系统解释方法关于“同一用语应有同一含义”的应然性设定,上述结论,似可推诸整个刑法中相同形式的“等”字。比如第351条, 除已列举的罂栗、大麻原植物外,根据毒品常识和法定毒品范围,至少还包括“古柯树”这一毒品原植物,其“等”字表示列举未穷尽。又如,第364条中的“等”字也表示列举未穷尽。因为在现实中, 音像制品除电影、录像两种形式外,客观上还存在录音带、幻灯片、激光唱盘、激光视盘、电脑磁片等多种形式。不仅如此,音像制品的形式还将随着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日新月异,层出不穷。此处用“等”字,也是为了适应这种词义的易变性的原故。(注:关于词义的易变性,可参阅《刑法解释论》第103页。相同的例证可见刑法第360条、第286条, 等等。)
依次征诸刑法中所有31个“等”字,笔者大都可列举出尚未列举穷尽的内容。据此,上述关于“等”字表示列举未穷尽的结论似乎可以成立了。但是,有人却对“同一刑法中的同一用语应有同一含义”的应然性设定的提出疑问,并列举出我国刑事立法中与此相违背的反例论证。(注:见李希慧:《详刑法解释论》第63~64页、第123页。 如“致”字,在1979年刑法中有两种意思:(1)过失引起;(2)既包括过失引起,也包括故意引起。又如,“处罚”在有的条文中是“量刑”的意思,而在有的条文中又是“定罪量刑”的意思。)事实上,1997年刑法也仍存在同一语不同含义的状况。(注:这一现象在1997年刑法中同样存在。如,“处罚”在第26条中表示“定罪”,而在第339 条中则表示“量刑”。参见陈兴良:《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4 月第2版,第108~109页、第407页。而据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罪名推理,第239条中的“处罚”是指“定罪量刑”。可见, 违反同一用语应有同一含义的规范,必然造成理解上的混乱。)所以,单纯依靠系统解释法能否最终确定“等”字均表示列举穷尽的结论,仍要以别的解释方法来检验。
(二)比较解释的结论
据法律解释学定义,比较解释法是指在解释刑法的某项规定时,将刑法的其他相关规定或者外国立法例作为参照资料,借以阐明该规定含义和内容的解释方法。本文意图通过与其他国家刑法和我国其他法律中“等”字含义的比较,来推断刑法中“等”字含义。(注:本文所用比较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比较解释方法。关于可比性及其意义,笔者考虑到,与我国其他法律法规中。“等”字含义比较,应具有可比性,因为法律制定者遵循的是相同的语法规范;而参照的外国刑法也是中文译本,译者所遵循的也是相同的语法规则,同样具有可比性。)
1.与我国其他法律法规中“等”字含义比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有8个“等”字,其含义均表示列举未穷尽。如序言中“教育、 科学、文化等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明显还包括未列举的医疗卫生、体育等事业,这些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共有11个“等”字,均表示列举未穷尽。如第25条中的“等”字,表示除已列举者外,明显还包括未列举的“迷信”;第50条中的“等”字表示还包括电子出版物。(注:第25条:“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等毒害未成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第51条:“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等出版的,依法从重处罚。”)又如《化妆品广告管理办法》第8条第5项“(禁止)使用最新创造、最新发明、纯天然制品、无副作用等绝对化语言”,我们自然会想起诸如“誉满全球”、“全球第一”之类曾风靡一时、泛滥成灾的绝对化的广告用语。再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大全》中一些法规等标题中的“等”字。如《国家税务局关于乳胶、涂料等五种化工产品在1993年内继续减免产品税的通知》、《最高检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等法律的通知》(总共是四部法律,还有《科学技术进步法》、《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字均明显表示列举未穷尽。
2.与外国刑法(注:在此将香港刑法典归于此类,是考虑到其刑法渊源的特殊性。)中“等”字含义的比较。
《韩国刑法典》(注:金永哲(韩)译、韩大元校对、赵秉志专业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中“等”字多不胜数,其基本形式都如“第158条(妨害葬礼等)妨害葬礼、 祭典或者传教的,处3 年以下劳役或60万元以下罚金。”很明显,“等”字表示列举未尽。
《香港刑事罪刑条例》(注:杨春洗等编著:《香港刑法与罪案》,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58页以下所附法定语文(中文)真确本。 )中“等”字多用于概括性的小节标题中,一般形式如《盗窃罪条例》中“盗窃罪、抢劫罪、入屋犯法罪等”,随后列举了8种犯罪, 从上下文很容易就可判断出“等”字表示列举未穷尽。
《法国刑法典》(注:罗结珍译、高铭暄专业审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中“等”字则很少,只有2个。(注:分别见第227—25条“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施以猥亵行为未使用暴力、强制、 威胁或突然袭击等手段的”,第434—15 条“在诉讼程序进行中或者为了在法院起诉或应诉,采用许诺、奉送、馈赠、施加压力、威胁、殴打、诡计或骗术等手段,以期促使他人提交伪证”。数量少,或许与法国奉行绝对罪行法定原则有关。)其“等”字含义因缺少资料,尚不可断定是否表示列举未穷尽。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注:黄道秀等译,何秉松审订,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尚未发现“等”字, 不知是译者文风问题,还是客观上没有“等”字,其条文多采用“列举后加‘或其他’”的方式,以此使表达更加严密,规定更具周密性和概括性。
例子当然举不胜举,其结论是:“等”字表示列举未穷尽。当然,由这种不完全归纳法得出的结论的弱点在于,反对者只要列举出一个相反例证,这个结论的可靠性就不攻自破。但所幸的是,笔者发现,凡“等”字表示列举已穷尽,列举后煞尾的,都可从上下文、前后文轻易推断出来,诸如“赵钱孙李等四人”,除此之外,“等”字均应理解为表示列举未穷尽。
(三)目的解释的结论
德国人欧特曼说:“立法目的之探求是开启疑义之钥匙”。目的解释法就是根据刑事立法之目的,阐明刑法规定含义的方法。(注:李希慧:《刑法解释论》,第129页。)通过统计对比我们发现,1979 年刑法只有第142条采取了列举之后加“等”字的表述方法,而1997 刑法竟然有35处之多,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立法者的目的何在?对这种变化原因和目的的探求是否有助于“等”字含义的明确?
有人认为,我国刑法已确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者之所以大量采用在“等”字前列举的表述方式,完全是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79年刑法过多的概然性条款,给予了司法机关过大的司法裁量权,其后果是不仅易使立法权受到司法权的侵夺,而且容易造成法外定罪处刑,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比如,79年刑法第14条第2款关于已满14岁不满16 岁的人应负刑事责任的罪名,除列举外,还加上“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这样的模糊用语,在实践中容易引起扩大解释的弊端,不利于对这部分未成年人的保护,所以,97年刑法在第17条第2 款中已将其改为完全列举。对于“等”字前进行列举的表述方法,以此推定,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也应理解为列举已穷尽,而不能理解为列举未穷尽;否则,又将重蹈覆辙,容易作出扩大解释,而这是立法机关已予注意并加以防止的。
诚然,我国刑法第3条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并且,罪刑法定不是一条简单的法律标语,应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中得到切实的贯彻。尤其是在刑事司法中,应当转变观念,加强刑法的人权保障机制,严格依法定罪量刑。(注:陈兴良:《刑法疏议》,第32~33、75页。)但是否可单纯以罪刑法定为依据即确定“等”字含义表示列举穷尽?笔者认为不能。首先,如为贯彻罪刑法定原则而需要列举穷尽,完全可与前述第17条第2款的表述方式一致。比如第56 条可表述为“对于犯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罪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或者表述为:“对于下列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而完全没有必要采取这种不统一的、易于引起歧义的表述方式。再者,如表示列举已穷尽,则有的条文间(如第53条和第57条)不可避免会出现矛盾。比如一个犯故意伤害罪或盗窃罪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无期徒刑,按第57条规定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是如按“等”字表示列举穷尽的观点,依据第56条,就不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立法者竟会忽视而让其存在吗?显然,“‘等’字表示列举穷尽”论者在此误解了立法者的意图。
笔者认为,增加刑法条文的明确性是立法者在97年刑法中所着力体现的。明确性是罪刑法定的题中之义。97年刑法以明文列举性规定替代了诸如“其他”之类的概然性规定,分则中列举罪状大量增加,正体现了刑法在明确性上的进步。97年刑法大量采用“等”字前列举的表述方式,同样体现了立法者在增加刑法明确性上的努力。法条明确性一旦增加,则既利于司法机关适用法律,同时又限制了司法裁量权的滥用。立法者之所以增加“等”字前列举表述方式的条文,正是基于此种目的。
有人要问了:你既已认为“等”字表示列举未尽,则尽管“等”字前已有列举,该条文仍是不完全确定的,何以说这种表述方式增加了条文的明确性,利于法律的适用和利于限制司法权的滥用呢?要回答此问题,须从立法语言学入手。立法语言学认为:“立法语言所表述的法律和法规是调整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因此,不仅需要准确、具体,同时还要求周密、完备。”(注:华尔赓:《法律语言概论》,第200~201页。)“等”字前列举的表述方式,正是为兼顾准确具体与周密完备而采取的。这种表述法既有包容,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体现。列举丰富了概念的内涵,增加了法条的明确性。如能全部列举,使法律的明确性达到完全的无疑义的程度,当然求之不得;但是,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有时一个概念的外延是无法用列举穷尽的方式来划定的。比如对破坏选举的非法手段,97年刑法增加列举了“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两种,但却仍未穷尽,故只好保留“等”字。然而即使仍保留了“等”字,前者也显然比后者更为明确,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重要的是,因为增加列举使其内涵丰富了,司法机关就不仅会注意而且必须按列举的内容适用法条,同时在一定意义上(注:也只能是在一定意义上,至少这些已列举的内容,司法机关必须毫无争辩地予以执行。)也限制了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综上,笔者认为,从文义解释和论理解释综合起来看,我国刑法中的“等”字都表示列举未穷尽。至于“为什么不用列举后加‘其他’这样的模糊用语表示规范的周遍性,而要用‘等’字这样易于引起歧义的表述方式”的问题,笔者认为是一个立法语言学上值得研究的问题,限于学识和篇幅,在此就不展开论述,但希望能就教于有识之士。
三、结语:引发的思考
尽管“等”字意义存在的疑问,通过法律解释学方法辨析可予解决,但此过程却引发了笔者关于立法与司法等相关问题的思考。比如司法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为法律院系学生增设法律解释学课程,等等。但笔者在此更想强调的是关于立法语言与技术、立法与司法解释工作这几个问题。
(一)立法者除应重视刑事立法语言文字、立法技术水平的提高外,还应加强刑事立法解释工作。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一个法律成功与否,科学与否,固然与立法的条件成熟与否,与立法者思想水平、知识水平以及对法律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了解的深度如何直接相关,但无庸置疑也与立法者的语言文字水平如何密不可分。(注:周旺生著:《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7页。)因为成文法律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之一, 在于它由文字以及由文字构成的语言排列、组合而成。语言文字是一切成文法律最基本的要件。”(注:周旺生著:《立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页。)
正因为如此,为了提高法律质量,许多国家在每一项法律草案提交立法机关审查之前,事先都要组织一些法学家、语言学家、逻辑学家和其他专家对法律的用语和逻辑结构进行仔细的推敲。比如前苏联,1939年即专设一个由法学家和语言学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任务是:(1 )仔细研究现行立法的文字,并找出其中缺点;(2 )对法律的文字提出有科学、有根据的建议。(注:吴大英、任允正著:《比较立法学》,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又如罗马尼亚,在1976 年就公布了《规范性文件草案的制定和系统化的立法技术方法》。在此规定中,为保障立法语言的高质量,专条规定了一些有关立法语言应遵循的规则。(注:比如“第101条:在规范性文件草案中, 对于同一个概念只能使用一个词汇。”等等。)
在立法技术的提高上,有学者甚至认为,控制论方法和机器的采用大有作用。因为它可使大量分散的法律资料迅速加以整理和系统化,并发现法律文件中的矛盾和重复,甚至可以使法律文件从一种文字译为另一种文字的过程实行机器化。(注:吴大英、任允正著:《比较立法学》,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我国立法作为全国人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它同时也应该是运用民族语言的最高典范。总体看,我国立法符合这个要求。但是,在现行的法律条文中,我们仍可发现有待完善之处。比如有的语言学者指出,有些法律条文,包括刑法条文中的一些句子,违反了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则,从而有损于法律语言的严肃性和庄重性,有损于民族语言的纯洁与健康。虽然其中有些意见1997年刑法已予采纳并据此作了相应的修改,从而使法律语言更为规范;但是,有待完善之处仍有不少。由此看来,立法语言、技术水平的提高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立法机关应更积极地借鉴国外这方面好的经验,以期使我国立法在立法语言、技术上更加完善。
卢梭指出:“制定法律的人要比任何人都要清楚,法律应该怎样执行和怎样解释。”(注: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中文版,第87页。)但是,我国刑法立法解释却一直处于贫乏薄弱状况。有的学者认为这种状况与刑事立法空前活跃的现状不相适应,背离了宪法和法律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使命,与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所处的特殊地位不相协调,与司法实践对其需求相去甚远。(注:参见《刑法解释论》,第154~156页。)该学者分析了这种现状的成因后(注:参见《刑法解释论》,第156~157页。主要内容有4点:(1)有关立法解释的法律不健全;(2)缺乏专门的立法解释的工作机构;(3)立法工作任务繁重,使全国人大常会难以顾全法律的立法解释工作;(4)立法解释主体对专门的刑法解释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并对现状的改进谏言直陈。(注:参见《刑法解释论》,第158~163页。主要内容有4点:(1)完善法律立法解释的立法;(2 )设立负责该项工作的专门机构;(3)增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干部队伍;(4)提高对刑事立法解释重要性的认识,使之落到实处。)笔者认为,上述论述确是言之确凿且直中肯綮,实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予采纳实施。但此言已出数年,而刑事立法解释工作现状仍未有太大起色。
(二)最高司法机关应重视刑法司法解释的主动性和及时性,并为此建立起一个自下而上的调研系统。
由于我国刑事立法的不成熟以及刑事立法解释的贫乏薄弱状况,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只得求助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起着不可缺的作用。近年,我国刑法理论界对刑事司法解释的研究比较活跃。最高司法机关对刑事司法解释工作也日益重视,除对司法解释进行编纂整理外,还重视从理论研究和实践两方面加以完善,司法解释工作也日趋主动、及时、规范。如最高法院1997年6月23 日已作出了规范司法解释工作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并下发本院各部门。但是,刑事司法解释工作仍待完善之处还有不少。笔者在此想强调的是主动性与及时性方面完善的重要性,以及为保障主动性与及时性的实现而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功能强大、反应敏捷的调研系统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因为我们看到,仍有一些重要的实践中急需的司法解释(比如犯罪数额标准、大量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界定)付诸阙如,或年久未改,落后于社会的发展,满足不了实践的需要。
笔者认为,加强高、中级法院调研系统的建设是改变现状的首务(除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外,尤其是要加强定期的频繁的纵向联络)。另外,省际及区域横向交流的薄弱状况应予以改变。这样,就能为最高司法机关尽快制定发布实践中急需的司法解释,积累经验,提供素材,创造条件,进一步完善刑事司法解释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