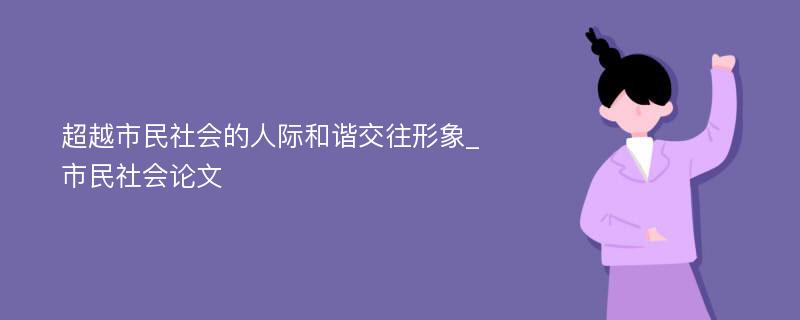
超越市民社会的人际和谐交往图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景论文,人际论文,市民论文,和谐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07)10-0032-04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双重论域
从词源学上看,“市民”(Bǖrger)的德语原义为居住在中世纪城堡(Burg)中的居民,他们摆脱了封建领土的控制而拥有市民权,基本上都是商人和手工业者,具有转变成资本家的可能,顾名思义,市民社会是由政治上和经济上相对独立的市民组成的社会。对市民社会的论述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由来已久,亚里士多德将市民社会(Koinóniapolitiké)视为城邦,该概念“在14世纪开始就为欧洲人采用,其含义则是西塞罗在公元1世纪便提出的。它不仅指单个国家,而且指也已发达到出现城市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1](P125)应该说,城市文明形成以来的政治社会可以被看做广义的市民社会,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及“旧市民社会”、“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狭义的市民社会则专指私有观念发生作用特别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马克思市民社会批判的着力点。[2](P93-94)
在颠倒黑格尔政治哲学思辨逻辑的过程中,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它“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以及“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5](P41)失去“一切物质交往”的国家当然只能是思辨领域的空中楼阁,黑格尔的逻辑悖谬恰在于此,他忽视“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殊不知,正是“家庭和市民社会使自身成为国家。它们才是动力”,即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来说正是必要条件”。[14](P11-12)马克思高度肯定市民社会的历史价值,认为较之突出“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的历史观”而言,重视市民社会的历史观才真正值得称道,因为“市民社会是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5](P41)
马克思从双重路径审视市民社会,从物质基础层面而言,市民社会是政治生活的前提,在中世纪时代,“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市民等级和政治等级的同一就是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同一的表现”。[4](P90-91)在封建社会,“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性质,就是说,市民生活的要素,例如,财产、家庭、劳动方式,已经以领主权、等级和同业公会的形式升为国家生活的要素。”[4](P186)在现代社会,“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5](P145)但从价值诉求层面而言,马克思看到市民社会并非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成为可能的社会,因为它“以商品交换关系为核心”,使“人们的社会交往采取了异化和物象化形式”,甚至成为“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抗为核心的资产阶级社会”,[6] 这样的社会当然是要加以扬弃的。
既然市民社会是政治生活的物质前提,对其做纯粹的哲学批判难以产生现实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为此钻研穆勒、斯密、萨伊等国民经济学家的市民社会理论,因为“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经济解放进行的”。[7](P251)也正是在理解国民经济学家关于市民社会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市民社会的物质力量,同时戳穿了市民社会的政治哲学神话,指出市民社会是“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8](P32)使人们走出市民社会阴影的遮蔽。如果说人们的政治生活具有两重内涵,即“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的话,那么,“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4](172—173)
如何扬弃市民社会的价值误区?这是政治哲学不能忽略的问题,马克思以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种价值进路加以说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摧毁了专制统治,“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组成为普遍事务,就是说,组成为现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同业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是人民同自己的共同体相分离的众多表现。于是,政治革命消灭了市民社会的政治性质。”[4](P187)但资产阶级革命的限度决定其不可能完成对市民社会的真正克服,因为政治解放离人类解放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对市民社会政治性质的消灭仅仅使其脱离政治形式,其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仍然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
换言之,市民社会问题的实质在于资本的统治,“市民社会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自由与平等就已经流于形式。因为,随着以占有他人劳动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即资本的出现,市民社会中拥有平等权利的市民早已发生分裂,一部分人转化为无产者,而另一部分人则转化为资产阶级,自由与平等被阶级差别与剥削所取代,市民社会已经变质为资产阶级社会。”[6] 资产阶级革命致力于消除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而非扬弃资本的统治,而仅仅就对市民社会的等级差别的消除而言,当时也只有法国革命完成了这一点。无产阶级革命则“为消灭[Authebung]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9](P238)因为市民社会与私有观念共存,当私有观念得到扬弃,人际交往达到无功利的和谐状态,市民社会自然为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社会所取代。
在对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切批判中,马克思高度肯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意义,认为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社会不仅具有市民社会的物质基础,同时扬弃了市民社会的异化状态,是政治理想与价值诉求得以实现的途径。当然,市民社会的扬弃并非一蹴而就的,或曰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还是必需的,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赢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仍然要在纠偏价值误区的轨道上加速市民社会的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当市民社会的物质生产生活达到最高水平,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当然地扬弃社会生活的异化状态,为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创造近乎完备的条件。
二、作为唯物史观的市民社会历史观
上面已经提到,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前,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并没有清晰的划界。之所以得到清晰的划界,在于现代国家以政治革命或市场经济的方式确立了市民社会的重要地位,即资本的统治催化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在这个意义上,狭义的市民社会是18世纪的产物,“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3](P130-131)现代政治国家不再是市民社会的代名词,而为市民社会所左右,这种“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对上层建筑当然具有基始意义。
应该说,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它深刻地反映了城市文明形成以来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形成以来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存在方式。可以将唯物史观的市民社会范畴称为市民社会历史观,[6] 市民社会历史观并非立足于市民社会,探讨资本的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以市民社会批判的方式论述政治实践视域的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状态,“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P57)当“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成为政治哲学的全部价值旨归,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市民社会批判贯穿马克思哲学—经济学研究的始终,而马克思对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市民社会的批判也当然地成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线索。
为了深入地阐述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作用,马克思认真研究了国民经济学家的鸿篇巨著,并肯定经济基础之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意义,但马克思绝非经济决定论者,他看到市民社会背后的资本的统治的事实,继而戳穿了市民社会的神话。尽管现代市民社会已经消灭了政治性质,但“消灭了政治性质的市民社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特殊性与普遍性相分裂的私人活动的领域,这一领域的特征是特殊性、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市民社会中,实际的欲求和利己主义是驱动市民社会前进的动力,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意味着市民社会成员仅仅成为了利己主义的人;市民社会的人被政治国家夺去了自己的类本质、共同性和普遍性,沦为利己的孤立的个人,他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10] 即市民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给具有自由个性的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空间。
马克思市民社会历史观是其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基本规律,市民社会则是现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样态,是现代政治国家确立的基础,马克思市民社会历史观深刻地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何以发展及消亡,与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及其现代性视野内在一致。市民社会历史观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视为相互作用的存在,“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私人生活的领域,固然以经济交往活动为基本内容,但同时也包含着丰富多彩的其他社会交往活动;政治国家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固然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但同样也是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利益的活动领域。”[11] 在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批判与现代政治国家批判是一体的,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哲学—经济学批判,上升到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学批判,并将政治发展的目的还给人本身。
之所以将马克思市民社会历史观视为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并将市民社会理论视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重要线索,在于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其对共产主义理论的生成也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产生他们的过程。”[3](P92)“这种历史观”即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将市民社会视为“整个历史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审视“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
可以说,马克思终结了旧市民社会的观念,论述了现代市民社会的运作模式,深刻地指出“现代发达国家的基础,并不像批判所想的那样是由特权来统治的社会,而是废除了特权和消灭了特权的社会,是使在政治上仍被特权束缚的生活要素获得自由活动场所的发达的市民社会”。[5](P148)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历史考察,马克思看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都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结果,却并非人类政治生活的目的,它们完全可以超越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而独立存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4](P170)这种价值缺席的场景在资本主义社会比比皆是,以市民社会历史观审视资本的统治的现实,可以看清“一切龌龊事物的温床”,[12](P662)摧毁这张温床,必然要彻底地扬弃私有观念,而只有人类解放才能完成这场革命。
换言之,当阶级消亡的时候,市民社会历史观才完成其历史使命。因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存在是以阶级对立的存在为前提的,当社会中不再存在阶级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根本对立也将不复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将同时消亡。因此,马克思坚信,消灭阶级既是政治国家消亡的现实途径,也是市民社会消亡的现实途径”。[2](P106)阶级的消灭正是为了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成为现实的可能,为了抵达“尘世生活”的彼岸,马克思慎重对待这一问题,在揭示阶级差别产生的根源的同时,他指出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和致力于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同样重要,当前者极大丰富的时候,必须使后者成为可能;当后者提前发展的时候,必须致力于发展前者,即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只有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达到极高的和谐发展水平的时代才能得到满足。
三、市民社会的扬弃与人际和谐交往
市民社会是现代政治国家确立的基础,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仍有积极意义,对其加以扬弃乃是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对市民社会的扬弃缘于人类解放的需要,“现实的个人”生活在市民社会,并非抽象的政治符号的化身,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是现实的存在,它不同于抽象的政治人或法人,但其自由个性还有待实现,“现实的个人”要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则必须放弃其“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身份。他不再忍受资本的统治,而要在摧毁“旧世界”的锁链的彻底的“现实的运动”中获得“新世界”,诉求自由与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以愤世嫉俗的口吻批判市民社会造成人性异化的现实,在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学之后,他以更为辩证的方式客观地评价市民社会在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终将扬弃的内在原因。市民社会的生产生活是现代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没有饮食起居等基本的生活条件,道德、宗教、文化等上层建筑都是空中楼阁,但隐藏在市民社会背后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政治制度,它以资本的统治的合理性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的勤劳工作并不能成为生活幸福的源泉,相反,他们工作得越多,生产的劳动产品就越不属于他们,他们就越深重地遭遇异化,而他们在合法的框架内采取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这个意义上,致力于人类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他们的必然选择。
马克思通过对交换价值或货币的阐述说明资本的统治与人们的交往,“毫不相干的人们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才成为他的活动和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是“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的前提,而他们的“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3](P106)。由于价值与实体的分离,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货币持有者之间的关系,劳动的目的不再是人的幸福,而成为对货币的索取,或曰对货币的索取成为人生幸福的全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人学审视让马克思看到,“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3](P479)为什么物质生活丰富的现代阶级社会不如古代社会崇高呢?私有观念发生作用的结果。为此,马克思将消除私有制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任务。
当读到政治哲学家或国民经济学家对人性的抽象论述时,马克思曾将革命视为无产阶级最为重要的人性表达,并认为这种表达乃是历史的火车头。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状况而进行反抗,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感情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要在这种反抗中显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了。”[5](P501)这种“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情的特性”在资产阶级法律框架内是无法显示也无法得到认可的,无产阶级以生命为代价参与了政治解放,而政治解放的成果却为资产阶级所独享,资本的统治的面纱遮蔽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异化得到合理化,马克思揭穿了资本的统治的全部秘密,一旦将剩余价值还给工人,资本家就失去了投资的全部动机,工人有权索取自己的剩余劳动所得,这种索取必将变革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转模式,使市民社会走向终结。
资产阶级拒绝支付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却开出了空头支票,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现代社会具有同样的人权。事实真的如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人权与公民权在政治国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不同于droits citoyen[公民权]的droits de l' home[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就是说,无非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人的权利。”[4](P182-183)这样的人权只能是抽象的存在,用以维持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和谐,殊不知,“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作为退居于自身、退居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与共同体分隔开来的个体的人”,[4](P184-185)这样的人并非“现实的个人”,因封闭且脱离社会整体而无法生成为“有个性的个人”。
为了获得真正的人权,无产阶级必须进行终结市民社会的“现实的运动”,使个体性的实现成为可能。“要成为现实的公民,要获得政治意义和政治效能,就应该走出自己的市民现实性的范围,摆脱这种现实性,离开这整个组织而进入自己的个体性,因为他那纯粹的、明显的个体性本身是他为自己的国家公民身份找到的唯一的存在。”[4](P97)终结市民社会,必须汲取市民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成果,并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加丰富的物质生产生活成果,同时变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一方面,积极探索使每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成为可能的现实道路;另一方面,以政治实践的现实力量描绘人际和谐交往图景,使人际关系走出资本笼罩的时代,使人与人的交往真正成为人性生成的需要,即真正使每个人的自由与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与发展的条件,这是扬弃市民社会的价值目的所在。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以往政治哲学家论述市民社会的基础上,颠倒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结论,确定了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意义,认为市民社会是城市文明形成以来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确立以来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它深刻指出市民社会的价值误区,认为资本的统治是社会不和谐的深层原因,为了摆脱资本的统治,扬弃剩余价值被无偿剥削的异化状况,无产阶级必须进行人类解放,在砸碎旧社会锁链的过程中获得整个世界。在砸碎锁链之后,要在市民社会的物质基础及其精神废墟上发展生产力,完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只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手段,而真正的和谐要通过建构共产主义社会来完成,因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4](P81)应该说,重温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这段话与深入领会其《资本论》中对人在资本的统治中的现实境遇的客观分析是能够获得内在一致的。
标签:市民社会论文; 政治论文;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