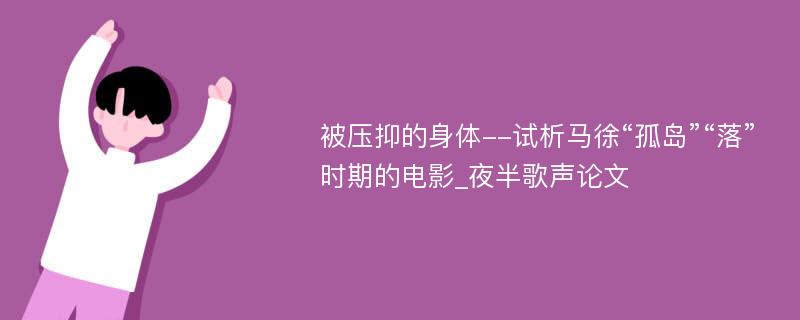
压抑的身体:“孤岛”“沦陷”期马徐维邦电影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孤岛论文,身体论文,电影论文,徐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马徐维邦民国时期的电影实践活动的论述随着重写电影史的浪潮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例如,李道新教授的《马徐维邦:中国恐怖电影的拓荒者》一文采用历史梳理的方法,清晰地介绍了马徐维邦来上海直到南下香港之前这段时间的恐怖片创作,阐明了马徐维邦恐怖片拓荒者的地位。黄望莉的《变容·分裂·生死:马徐维邦影片的叙事特色》,以马徐维邦1943年的《秋海棠》为分析文本,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挖掘出马徐维邦作品中“自恋的伤痕”和“残酷命运观”的主题。通过对马徐维邦从影经历的梳理,笔者认为他的创作经历一般可以分成四个阶段:1923-1937年间,马徐维邦经历了中国电影的初创期——商业类型电影的形成和第一次繁荣的时期,最终成就了《夜半歌声》这一经典恐怖片;1938-1945年间,马徐维邦在上海“孤岛”时期和“沦陷”时期中的创作极大地体现了当时中国电影创作的复杂性:“藉神鬼怪谈以泄其忧愤”,①隐晦而曲折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第三个阶段是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的短暂创作期;第四个阶段是马徐维邦离沪南下香港后的创作和生活。 “孤岛”和“沦陷”时期的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而马徐维邦在这个时期的电影实践也是最为丰富的。他既拍摄了《古屋行尸记》(1938)这样集侦探恐怖于一身的影片,其中老仆的僵尸形象可谓是中国电影史上僵尸片的鼻祖。《冷月诗魂》(1938)则是他拍摄的第一部鬼片。他还从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中获得灵感,利用毁容制造恐怖的《麻疯女》(1939)以及别具一格的古装片《刁刘氏》(1940)。此外,他以平均每年两部以上的作品确立了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如1941年的《夜半歌声续集》、1942年的《现代青年》《鸳鸯泪》《寒山夜雨》《博爱》(合导片)和1943年的《万世流芳》(合导片)、《秋海棠》(上下)。1945年他除了《火中莲》《大饭店》之外,还联合拍摄了贺岁片《万户更新》。《博爱》《万世流芳》等一些影片至今仍然存在争议。“孤岛—沦陷”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马徐维邦的创作,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上海电影创作的复杂情境,然而,隐含在作者独特的影像和人物身体的展现中,又凸显了作者压抑的精神一种外在的曲折表达。 一、《夜半歌声续集》:“孤岛”时期的“不合时宜” 马徐维邦在长年的恐怖片创作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他看来,一部恐怖片并不一定要有离奇神秘的剧情,一个平淡的故事也能通过各种手段营造出恐怖气氛,牢牢控制住观众的情绪。马徐维邦用恐怖的空气概括了恐怖片的核心,并从自身的创作实践和好莱坞电影中总结出了一套营造恐怖气氛的手段,即将摄影、音响、置景、灯光及演员的演技和化装多种手段进行有机组合:“譬如拍一个地窖里突然出现怪人的场面,在摄影和灯光上,先便是一条黑影映在墙壁上,然后用推镜头使黑影渐近渐大,而在配音上,用先缓后急的音响,杂以急促的鼓声,使观众的心情为之紧张起来,再加上屋外的雷声和闪电之光,使空气格外恐怖。而在置景上,例如墙角满布着蜘蛛网,破坏的桌椅倾斜地放在一角……同时配上演员恐怖的化装或是惊骇的动作……”②这些出自他口中的场景设计几乎就是一个恐怖段落精准的分镜头。在马徐维邦的诸多电影中,黑影、雷雨、动物意象(尤其是蛇),惊恐的脸是必定出现的几个视觉符号,这种视觉风格完整地出现在《夜半歌声》及其续集、1942年的《博爱》等影片中,延续至南下香港后拍摄的《琼楼恨》③皆是他的本色之作。马徐维邦被称为“恐怖侦探电影作家”④的原因之一正是他影像中对人物身体的独特而夸张的呈现,他在“孤岛”后期的《夜半歌声续集》(1941)不仅保持这一风格,而且其手法上更加成熟。 《夜半歌声续集》承接前作,讲述了跳海的宋丹萍获救后,再次被怪医生毁容,重新回来寻找爱人李晓霞并双双死去的故事。该片秉持马徐维邦一贯的特色,运用一切手段来制造影片的恐怖效果。首当其冲的还是马徐维邦对脸部化妆术的奇观制造。在这部影片中,不仅宋丹萍的脸部做出了与上一集截然不同的效果,还制造了“怪医生”的脸部造型。洪警铃饰演的怪医脸形扭曲,眉毛残缺不齐,一脸的肉疙瘩,兴奋地欣赏着宋丹萍可怕的脸,尤其他在卧室中摆放了许多裸女像,可谓是早期中国电影中最独特的变态狂形象。很明显,绘画出身的马徐维邦对德国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的电影语言的运用是一以贯之的。在摆放着试管、量杯、烧瓶的实验室中,宋丹萍躺在病床上,等待着怪医通过手术恢复他原来的面貌。马徐维邦通过实验室窗户的光线由暗至明的一个空镜头暗示手术时间之长。当头上的纱布取下,装满水的玻璃箱中映照出一张骷髅般的脸,恰如旁边矗立的骷髅骨架。宋丹萍在狂怒之下杀死怪医,逃出那个怪异的小岛。很明显,马徐维邦对人物脸部“伤痕”的恐怖感不仅仅是化妆术的效果,更多的是通过表现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像的呈现来强化的。此外,马徐维邦还大量地运用声与影来营造故事的恐怖效果。如,他对宋丹萍人物形象的强化上。马徐维邦以一双沾满泥巴的脚行走的特写交待了他的下一个出场:一个披着黑斗篷、戴着黑帽、蒙着脸的神秘人跌跌撞撞穿行在烟雾弥漫的小树林中。接下来是宋丹萍出现在小酒馆引起人们恐慌的场景,画面中只有从酒馆内传出的单调的念经的人声,混合着鼓声和铁片撞击声,喝酒的人们皆朝馆内注视。黑衣人由画面左侧入画,背对镜头,慢慢向人群靠近。酒馆中的人全无察觉。镜头切成门边一人背对镜头朝里望的全景,此人身后是放在酒馆前的饼摊,前景中黑衣人弯腰取饼。门边人不经意转头一看,望见一张骷髅般的脸。马徐维邦巧妙地借助了声音(开始单调的念经声和随后的喧嚷声)与人物动作(统一的注视—慌乱)的静与动的对比来表现恐怖,远比早期作品中(比如1930年的《空谷猿声》)表现人物反应单纯使用簌簌发抖的身体或惊恐的脸要高明复杂得多。 这些极度风格化的身体展现固然是为了吸引观众的观赏趣味,然而被迫害的身体也明确地与叙事核心冲突“反抗专制、争取个人自由的爱情”勾连在一起。与上一集鲜明的“左倾”激进的意识形态表述略有不同,抗日的呼声变得更加的隐晦和曲折,所有的社会批判表面上都指向反对封建压制。例如,影片在开端是从安琪儿剧团在南山之麓为绿蝶举行葬礼开始,墓碑上刻着剧团全体同人写的墓志铭。影片一开始便奠定了高昂的基调,前来吊唁的李晓霞(谈瑛饰)一下马车便直面观众,处于画面的中心。近景将她从背景剥离出来,她代表了编导的意图说明这里记载了这位为反抗封建压迫而牺牲的时代女儿(指绿蝶),祈祷她的灵魂能伴随他们得到最后的光明,她是时代洪流中充满革命激情的风云儿女。这种刻意营造的仪式感显然是导演在借她之口痛斥黑暗的社会,昂扬青年身上的力量,表明继续革命事业的思想。影片中表面上设置了自由与专制的二元矛盾,压迫李晓霞的黑暗势力仍旧是封建的家庭,晓霞追求的自由与父亲代表的专制一再地产生激烈的矛盾。但是,其中的很多细节也不乏对时代的影射。影片将李晓霞塑造成一个具有独立的个人意志、勇于反抗的新女性。例如,她与父亲争论“汤俊之死”时,先从道德上认定“害人的人终究会被人害”,接着大声呼喊出“我有我个人的自由”的时代强音。 电影这种面向大众的通俗媒介,自诞生起天然地承担着商业功能和社会教化功能,很容易受到来自电影工业之外的力量的舆论导向作用。在“孤岛”上海,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三方力量纷纷办起报刊争夺话语权。在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下,宣扬抗日的报刊一度兴盛,激发包括电影界在内的“孤岛”民众的抗战意识。1938年12月8日,51位激进的文艺工作者联名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敬告上海电影界书》,批评的对象就是当时流行的神怪片热潮。这些影片既包括重映的张石川在明星公司拍的“火烧红莲寺”系列,同时也有当时新拍摄的借梦境“而至于居然人鬼交往”的影片,这封联名书尽管并没有点名哪位导演或者电影,但是,借梦境人鬼交往的表述恰好符合《冷月诗魂》的剧情,而作为新华公司拍摄恐怖片的首席导演,马徐维邦显然在此批评之列。《敬告上海电影界书》认为这种表面上反封建、惩恶扬善的神怪片,“骨子里恰好是(不管是有意或无意)帮助敌人麻痹自己的同胞!”敬告书在喷薄的爱国热情中定了一个极端的公式,拍摄神怪片即等同于麻痹民众的汉奸行为。与此同时,日本人控制的报纸也讨论起神怪片,他们认为《冷月诗魂》反映了中国人的厌战情绪。虽然中日批评界出自各自的政治目的批评马徐维邦所代表的影片创作,但是两者观点都基于发现神怪片脱离现实的不合时宜。 将马徐维邦的作品置于当时的舆论场中,就能看到其系列作品面对复杂的历史情境中所面对的窘境。《夜半歌声续集》的结尾处,李晓霞在宋丹萍的《夜半歌声》中含笑而逝,宋丹萍自刺毒针殉情。这样的悲剧收场似乎不应该是一个在影片中多次强调反抗精神以及对民众负责的革命志士所为,正如当时的一篇评论所说,宋丹萍不应“牺牲革命工作和自己的前途”而“用死来结束一切”。⑤今天看来,我们不难发现,马徐维邦影片中,即使是惩恶扬善的鬼神故事,也隐射了日本侵略者(恶人)和受侵略的中国民众(善良的人),借助非现实的鬼神的力量以激发起现实中身处“孤岛”中人们的抗日意识。这些做法或许收效甚微,但是左翼批评者们在这篇慷慨激昂的联名书中所阐述的反抗就是爱国,反之则是汉奸这样极端的二元对立的观点,事实上是不符合当时特殊时期的宣传策略的。而对《夜半歌声续集》恰是“透过被毁的容颜,来揭示他的自我因失去所爱的人,而留下‘自恋之伤痕’,乃导引自卑感而自杀的过程”⑥才是马徐维邦影片中借身体的扭曲和压抑所表达的反抗意图。 二、《博爱》:娱乐与政治的混杂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就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早上,日军接管了上海租界。租界内的报社和出版社被关闭,上海的电影业被继续保留,其目的是为了恢复上海的大都市正常状态,成为推行大陆政策的工具。⑦为了加强与上海电影业的合作,日军找来了熟悉中国与电影的川喜多长政,作为日方的代表,接管上海电影界。川喜多长政在1939年6月就创立了中华电影公司,作为日本对华电影工作的国策机关。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与上海电影业的张善琨等人就有过接洽,将“孤岛”时期最为著名的《木兰从军》发行至沦陷区的人正是川喜多长政所为。日军报道部辻久一记录了12月8日川喜多长政与中国电影公司老板接洽的目的:“我们是去见制片人的,目的是想用最和平的手段将租界内有力的支那电影制作者均置于日本的统治下,丝毫不损坏他们的机构,让他们继续工作,只是将其内容置换。”⑧川喜多接洽的正是当时上海最有名气的电影大王张善琨。在日军提供胶片等电影拍摄所需的物资,并且不干涉拍片的条件下,张善琨同意与日军合作。⑨ 1942年4月,新华、国华、艺华、金星等上海12家私营电影公司合并成立了中华联合制片公司(简称“中联”)。成立资本为中储券300万,其中中华电影公司占51%,其余各公司占49%。⑩同年9月,“中联”公开向社会招股,资本额达到中储券1250万(原资本额300万),日方资本份额不到10%。这家新成立的官商合办的电影公司,由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为董事长,川喜多长政为副董事长,也是实际的掌控者,张善琨任总经理兼制片部经理。高度集中的“中联”拥有三家制片厂,以及三个临时摄影场,共有摄影棚16座,沪上男女大明星、大导演以及各专门部分的技术人才大多数罗致麾下。实权在手的川喜多长政出于拍摄不触及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意识形态上无关痛痒”的电影能获得商业利益及拉拢上海电影创作人员、观众的考量,坚决贯彻1938年在北平召开的“日本电影的大陆政策及其动向”座谈会的会议精神,即“今后,日本电影如要以中国电影市场为目标而做活动的话”,那么“在日本电影上千万不能加上日本或满洲的名义,最好用大题材的中国电影的姿态出现”。(11)由于川喜多长政在管理上坚持故事片和新闻片分家,“中联”和“华影”只负责故事片的创作。(12) 此时,多年的制片经验使得张善琨保持着对市场和观众趣味的敏感,他多次强调娱乐片的商业价值。(13)在电影商人的角色之外,他同时有着敏感的政治嗅觉,同多方力量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张善琨将自己制作的所有的电影剧本都向日本军、南京政府及重庆的地下政府申请”。(14)尽管如此,编导们在题材的选择上仍然如履薄冰,“只求无过,不求有功”,“凡是稍为硬性一点的就都在各自小心之下不拍”,不约而同地转向与政治无涉的爱情主题。(15)在轻快的爱情片充斥影坛之时,马徐维邦也正当适宜地继续恐怖类型片的创作。 马徐维邦在拍完《夜半歌声续集》后离开了张善琨的中国联合影业公司,成为艺华公司的特约导演,并交出了两部作品。一部是根据张恨水同名小说改编的《现代青年》,另一部则是他编导的侦探片《鸳鸯泪》。(16)两部影片都是在上海沦陷后的1942年才上映的。《鸳鸯泪》完成时,上海电影界面临大转变,艺华公司也在合并之列,私人制片随着“中联”的成立而宣告结束。(17)从“中联”到“华影”,马徐维邦导演的作品有7部,其中合导片占了3部,分别是1942年的《博爱》、1943年的《万世流芳》和1945年的《万户更新》。 《博爱》集“中联”全体创作力量完成,是一部紧密围绕“博爱”主题的集锦片,形式与30年代的《女儿经》相似。影片分11节,分别是“人类之爱”“儿童之爱”“乡里之爱”“同情之爱”“父女之爱”“兄弟之爱”“互助之爱”“夫妇之爱”“朋友之爱”“团体之爱”以及“天伦之爱”。再加上片头片尾,分别由13位导演完成,全体明星联合演出,时长三小时零九分。(18)马徐维邦导演的“乡里之爱”一段,在恐怖的氛围中强调爱应该超越本乡与外乡的界限。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黑夜,是马徐维邦酷爱的经典环境。树在风雨中狂舞不止,屋顶的瓦片吹落,断裂的声音让人惊心。屋内一家人静悄悄,小男孩缩在母亲怀里说“鬼,鬼影来了”。母亲赶紧捂住他的嘴。在表现恐怖上,马徐维邦惯用自然的天气和声音来表现,大人是默然不语,只有惊骇的脸的特写。而孩子似乎能与自然的神秘相通。一对赶路的父女突遇大雨,敲门求助。倒吓坏了屋里的一家人,赶忙将桌子搬过来抵住门。父女只好来到一座破庙(侧面全景俯拍),人物压缩在边缘。梁上掉落一条蛇,在地上蠕行,女儿惊声尖叫。父亲大声询问,镜头慢慢由双人中景推近至父亲脸的特写,仿佛与隐藏在黑暗中一双逼近的眼的视点重合。闪电明暗交替中僵尸出场,一个高大的黑影时隐时现,慢慢靠近,出画后,接脚移动的特写。马徐维邦还用了一个特殊的镜头来表现僵尸的可怕,固定近景镜头中,鬼一步步靠近,头和下半身皆在画外,只留一个上身。等鬼走到父女身后,追赶开始。村民们为是否去救两个外乡人发生争执,一个正义的年轻人(高占非饰)与自私的老人(洪警铃饰)据理力争,在千钧一发之际打跑了僵尸。最后在警察来到后,撕开披在鬼身上的衣服,露出囚犯的号衣,真相大白,原来是一个越狱的强盗在装神弄鬼。尽管这只是片段式的一个小故事,但是依然保持了雷雨天气、破败的建筑、黑影、蛇、惊恐的脸等马徐维邦恐怖片中惯用的视听元素。这些光影音营造的紧张气氛再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观众识别其导演身份的标签。(19) 1942年“双十”节,“中联”出品、由全体导演与演员合作的《博爱》在上海大光明、南京、国泰、美琪、大华五大西片首轮戏院同时献映。(20)就在上映前一天为了配合宣传,参演该片的男女四十大明星在大光明戏院做慈善献映,登台演唱片中主题歌《博爱》,(21)影片在影院的映期上也颇费周章,“双十节”起在五大戏院各映三天后,从十三日起由大光明、南京大戏院两家同映四天。十七日起,大光明单独再映三天。考虑到首轮西片戏院的票价较贵,《博爱》同时在两家国片首轮戏院上映。(22)噱头大王张善琨精于此道,强大的宣传攻势,让“一般感觉物质缺乏的影迷似乎错过了这张片子,比丢失了宝贝似的还要难过”。(23)从《博爱》的广告宣传来看,观众更可能是冲着“十六大导演,十六大明星”的豪华阵容去观影的。 这种颇耗人、财、物的强大阵容,在日本和其附庸汪政府方面是作为宣传国策的工具,《博爱》和《万世流芳》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日本“大东亚秩序”的意识形态,成为批判其他同时期纯娱乐片的典型。学者傅葆石先生在《双城故事》一书中,已对《万世流芳》的创作者们如何以远离历史的才子佳人结构,架空鸦片战争的政治意义,淡化日本“大东亚秩序”宣传的反英意识形态做了精彩的分析,不仅为我们认识《万世流芳》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同样有助于我们对《博爱》的认识。《博爱》拍摄时间不足一个月,是“中联”为了迎合汪政府反英美的国策而交出的命题作文。影片通过“天伦之爱”故事中演员徐立之口,“博爱之为仁”,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连接,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日本鼓吹的“大东亚秩序”,即强调中国的文化传统以驱除英美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根本目的则在于借孔教这一东方传统从文化上确立中国与日本的亲密关系,将中国人的民族仇恨从日本转向英美,从而共建大东亚共荣圈。意识形态上的附敌正是《博爱》此后被诟病的原因所在。台湾和大陆的官方电影史不约而同地认为《博爱》的创作者在影片中宣扬顺民哲学和中日亲善。(24)而据张善琨的妻子童月娟与参演者李丽华所说,《博爱》是“沦陷”时期电影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全体影人秉承严肃创作态度下的艺术结晶。(25)事实上,意识形态宣传的效果并不是单一而固定的,在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面前,“中日友好”本身就具有莫大的反讽意味,或者,片头中“人类生存,端赖互爱”可以置换成呼吁沦陷区的同胞互相爱护,共渡难关。正是由于文本的多义性使得我们不能对影片做一个简单的评判。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一段“人类之爱”中陈燕燕与舒适饰演的兄妹与母亲逃难到上海,面临失业问题;第六段“兄弟之爱”与最后一段“天伦之爱”中,两次出现民国三十一年日历的特写镜头,说明《博爱》中的人物都是生活在“此时此地”上海沦陷区的普通人。他们是患难与共的朋友(“人类之爱”),破镜重圆的夫妻(“夫妇之爱”),相濡以沫的家人(“天伦之爱”),冰释前嫌的邻居(“互助之爱”),甚至连小偷也有一颗善良的心(“同情之爱”)。影片借儒家的仁爱思想建造了一个乌托邦,在这个世外桃源中,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压迫在善与爱的感化下消解于无形,而这种乌托邦,或许也正迎合了沦陷区观众渴望安定的心理,满足他们在压抑现实之外的娱乐需求。 三、《秋海棠》:弱者的反抗 一部作为“生平心血纪念”的《秋海棠》上映后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可谓马徐维邦巅峰状态的代表作。1942年的马徐维邦年过四十,自电影初创期进入电影圈,在不断的拍片实践中电影语言与风格日臻成熟。一向以恐怖片权威导演著称的马徐维邦在《寒山夜雨》尚未完成时,就对刚刚出版单行本的小说《秋海棠》产生兴趣,开始与作者秦瘦鸥商量电影改编的计划。(26)同年12月24日,《秋海棠》由上海艺术剧团搬上舞台,卡尔登影戏院连演四个月,观众的空前热情使得此话剧一票难求,直接促成了话剧的商业繁荣。此后仍在众多剧团长演不衰。与此同时,因“中联”拍摄的包括《博爱》与《万世流芳》在内的影片并没有达到日本人所要的宣传效果,为了加强对上海电影的垄断,日本指使汪伪政权颁布所谓《电影事业统筹办法》,实施所谓“电影的总体战”,把“中联”“中华电影”(管发行)和“上海影院公司”于1943年5月合并为“中华电影股份公司”,简称“华影”,使影片、发行、放映一元化,所谓“实施三位一体之电影国策”。 电影《秋海棠》因为男主角“秋海棠”的人选迟迟未定,直到1943年初才开拍。(27)“耗时年余,耗资二百万元,通力合作动员一千余人的《秋海棠》于1943年12月21日在大光明、南京、大上海三家戏院同时上映”,“从首轮至二三轮影院,直到2月28日方才落幕”,创下了不俗的票房成绩,可谓是马徐维邦一生中观众最多、最为卖座的电影。(28)可以说,《秋海棠》的诞生正值“华影”成立前后,因此,影片文本创作内外都体现了这个时期艺术创作的复杂与含混之处。《秋海棠》时长三小时半,分上下两集。以京剧名伶吴玉琴(秋海棠是他出科后的艺名)的命运沉浮为主线,时间横跨二十余年,从民国十一年到民国三十余年,影片前二分之一讲述了吴玉琴和被军阀袁宝藩霸占为姨太太的罗湘绮相爱并生下一女,后被袁宝藩发现在吴玉琴脸上画上一个十字。余下二分之一讲述吴玉琴与女儿梅宝相依为命,因为水灾由天津农村逃到上海谋生,面貌已毁,昔日的名旦秋海棠只能扮演满脸油彩的武行。梅宝与母亲相逢,一家团圆终偿夙愿,秋海棠不愿意罗湘绮看到自己的残破面容而跳楼身亡。 当时不少在上海的日本人也十分喜欢这部“曲折离奇,哀婉动人”的电影,(29)然而由于语言文化的隔阂,以及最重要的处在入侵者的立场,往往只能看到故事的最表层,或者对片中的隐喻避而不谈,他们的热情与中国的观众“持万钧之力,刺向了众人的肺腑”的感受不可同日而语。(30)那么处于动荡时代中的“半新不旧的人”如何与这个“半新不旧的故事”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31)以及在这部心血结晶的《秋海棠》中,马徐维邦如何借残缺的身体来将一个传奇悲剧与沦陷区人们的日常生活贴近的,并隐晦地表达其爱国意识和反抗精神呢? 在秦瘦鸥最初的连载小说中,对“秋海棠”名字的来历有一番详细的介绍:中国的地形,整个儿连起来,恰像一片秋海棠的叶子,而那些有野心的国家,便像专吃海棠叶的毛虫……“秋海棠”成为一个符号,象征着中国,以及对中国觊觎的“野心国家”的指涉,显然是原作者对日本侵略中国现实的不满而有意为之。对于“秋海棠”的政治意蕴的所指不仅有原作小说的白纸黑字说明,还与1937年的《春闺断梦》中的海棠叶形成互文。马徐维邦坚持使用象征中国版图的“秋海棠”作为片名,其隐喻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影片中还有一处明显的隐喻,在外跑码头的三哥突然来找秋海棠,秋海棠在重逢的喜悦之余总是忧心忡忡,但又不好开口,为了向毫不知情的三哥解释清楚,便拿出一本记述自己与罗湘绮相爱经过的日记让他看,扉页上写着四个字:自由日记。这是一处颇具匠心的改编。对于生活在沦陷区的人们,自由是一个敏感而充满政治风险的词汇,此时此刻“自由”的内涵已经超出了银幕上弱者反抗军阀的故事,直接与日本侵略、大后方形成链接。 影片中,秋海棠被毁容后,带着女儿逃离战乱和水灾,一路从天津逃到上海,他所承受着的天灾人祸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以及秋海棠城市—乡村—城市这种往来穿梭的生活,作为一种集体记忆重新又引起多少因战事背井离乡涌入上海讨生活的人们的共鸣?马徐维邦借秋海棠的迁移经历慰藉了乱世中艰难生存的人们。吕玉堃在上海沦为“孤岛”后才开始电影演员生涯,他清秀、瘦小、文弱的外在形象,符合名旦秋海棠俊美的外形特征,而俊美本身就混杂着一丝女性气质。正是这种亦刚亦柔的气质,秋海棠既能在舞台上反演明代名妓苏三,情到深处还能为红粉知己慷慨一曲《罗成叫关》。这种女性气质在秋海棠被毁容后,内化为一种母性,他既是父亲,又是母亲,带着残破的面容,含辛茹苦地抚养着自己的女儿,承受着命运的痛苦,坚强卑微地活下来。人们被这个容貌尽毁、贫病交困的秋海棠身体上的韧性打动了,那种坚韧正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性格中积淀下来的底色。就连日本报道部的久一也隐约感受到了影片中“秋海棠这个人物象征的一种中国人的性格”。(32)正如张爱玲所说:“切身的现实,因为距离太近的缘故,必得与另一个较明澈的现实联系起来方才看得清楚。”(33)“秋海棠”身体所承受的灾难犹如一面镜子,使得观者在同情的泪水中产生共鸣、建立认同,黑暗境遇中求生存便成为弱者的一种反抗方式,它的触角深入到沦陷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孤岛”到“沦陷”时期的创作不仅是马徐维邦最多产的时期,也是他导演生涯中最为复杂的一笔。隐含在马徐维邦作品中的“鬼怪”、受害的革命者(如宋丹萍)和戏子(秋海棠)身体中的压抑与当时的压抑现实形成呼应,使得马徐维邦一方面更加强化其恐怖/侦探类型创作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隐藏在《夜半歌声续集》《博爱》与《秋海棠》等影片中的呐喊在今天看了也是很明显的。其后,这段经历深刻地影响了他此后的导演生涯和个人生活,在战后初期惩治汉奸的呼声中,服务于敌伪电影公司的事实成为马徐维邦的一个污点,被排除在主流的电影格局外。1949年2月25日,马徐维邦与摄影师董克毅搭乘油船赴港。(34)他先后在长城、永华、新华以及许多小电影公司拍片,《琼楼恨》(1949年长城影片公司出品)重现《夜半歌声》的视觉风格,《毒蟒情鸳》(1961年香港新华影业公司出品)(35)则是一部男女角色倒置的现代版的《麻疯女》(1939),都显示了马徐维邦试图在香港重振上海辉煌的野心,可惜更加不得志。马徐维邦可谓是南来导演人中最水土不服的一位。昔日的大导演迫于生活压力,一度只能去拍低成本的厦语片。马徐维邦在上海解放前赴港时并没有久居香港的打算,解放后曾回到上海希望能在新的国营电影制片厂体制中拍片,然而没有作品问世,之后只身再次前往香港,直到1961年2月14日因车祸离世。(36)驰名海上的一代大导演就此陨落,东方郎却乃,恐怖片权威导演,附逆影人,慢车导演,南下影人等等混杂的身份标签在时间的流逝中叠映出马徐维邦的个人传奇。 ①参见《介绍〈寒山夜雨〉》文章中马徐维邦的《导演者言》,载《新影坛》1942年第一期。 ②《与马徐维邦谈怎样处理恐怖片》,载《太平洋周报》1942年第1卷第41期。 ③见“第14届香港国际电影节”专刊《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中陈辉扬《传奇的没落——马徐维邦香港时期的启示》一文对《琼楼恨》几场恐怖戏的场面调度的分析。 ④佐藤忠男《中国电影百年》中专设一节介绍马徐维邦及其作品,称之为“恐怖侦探电影作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6月第一版,第47页。 ⑤周达《新片评介〈夜半歌声续集〉》,载《华商报》文艺副刊,1941年8月2日。 ⑥同③,第40页。 ⑦[美]傅葆石《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2月第一版,第164页。 ⑧辻久一《租界进驻记》,原载《新映画》1942年2月,引自邵迎建《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⑨张善琨与川喜多长政谈合作,见黄爱玲《童月娟:新华岁月》,《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南来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电影资料馆胶片来源断绝。上海的制片公司所存胶片数量不多。新华公司的张善琨意识到胶片来源关系着电影业的生死存亡。见《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经过》,载《中联成立一周年纪念特刊》以及辻久一《租界进驻记》。 ⑩《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经过》,载《中联成立一周年纪念特刊》,中华·中联联合宣传处编辑出版,1943年4月12日。 (11)艾以《上海滩电影大王张善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9页。 (12)《一年来的中国电影界》,载《华文每日》1943年1月1日,第10卷第1期。 (13)俊生《张善琨发表谈话》,载《新影坛》1943年第4期;张善琨《中联一年》,载《新影坛》1943年第7期。 (14)[日]川喜多长政《父子世界主义者》,引自邵迎健《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第202页。 (15)《本刊总编辑与朱石麟先生对谈制作倾向及其他》,载《新影坛》1943年第6期。 (16)《马徐续为艺华导演两部新片〈最后的一幕〉〈寒山夜雨〉》,载《中国影讯》1942年1月16日,第2卷第41期。 (17)《上海电影界一大转变》,载《中国影讯》1942年4月3日,第二卷第51期。 (18)《一年来大事记》,载《中联成立一周年纪念特刊》,中华·中联联合宣传处编辑出版,1943年4月12日。 (19)《〈博爱〉(影评)》,载《华文每日》1942年11月1日,第九卷第九期,以及《影评〈博爱〉》,载《太平洋周报》1942年12月23日,第一卷第四十期。 (20)[日]川喜多长政《父子世界主义者》,引自邵迎健《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第202页。上海沦陷后,中外影片发行权集中于中华电影公司,“中联”制作的优秀影片由中华公司配给在以往专映西片的一流电影院上映,《博爱》即为一例。 (21)《胜利灌收〈博爱〉唱片》,载《中联影讯》1942年10月10日。 (22)《〈博爱〉创新纪录》,载《中联影讯》1942年10月21日。 (23)《观〈博爱〉后》,载《中国艺坛》1942年10月15日第5期。 (24)见杜云之《中国电影史》第二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5月初版,第62页,以及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117页对《博爱》的评价。 (25)黄爱玲《童月娟:新华岁月》第31页;朱顺慈《影坛长青树李丽华》第167页;转载自《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南来香港》。 (26)《秋海棠搬上银幕马徐维邦秦瘦鸥会谈》,载《中联影讯》1942年8月19日。 (27)《〈秋海棠〉秋海棠之谜》,载《中联影讯》1942年12月16日;以及《中联〈秋海棠〉十六日起开拍李丽华吕玉堃主演》,载《电影周报》1943年1月17日第三期。 (28)邵迎健《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第216页。 (29)参见《岡崎宏三》,邱淑婷《港日影人口述历史化敌为友》,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页。岡崎宏三是上海沦陷时期“华影”中日合作片的日方摄影师之一,曾参与《春江遗恨》的拍摄,在此期间看了不少中国影片,《秋海棠》是他印象最为深刻的电影之一。 (30)佐藤忠男《尴尬的妥协和艰难的反抗》,载《社会观察》2005年第六期,第37页。 (31)《〈秋海棠〉三部曲》,载《文友》1944年第二卷第五期。 (32)辻久一《马徐维邦与〈秋海棠〉》,载《新影坛》1944年第4期。 (33)张爱玲《洋人看京戏与其他》,兰云月主编《民国才女美文集》(上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360页。 (34)《名导演马徐离沪》,载《青青电影》1949年3月5日,第17卷第6期。 (35)《毒蟒情鸳》虽在马徐维邦死后于香港公映,但是完成时间应该是在1957年。影片完成时间可参考公孙鲁《中国电影史话》第二集,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出版日期不详,第177—179页;影片上映时间见香港电影资料馆网站《香港电影片目1914-2010》。 (36)《王为一访谈》,陆弘石《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月版,第168—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