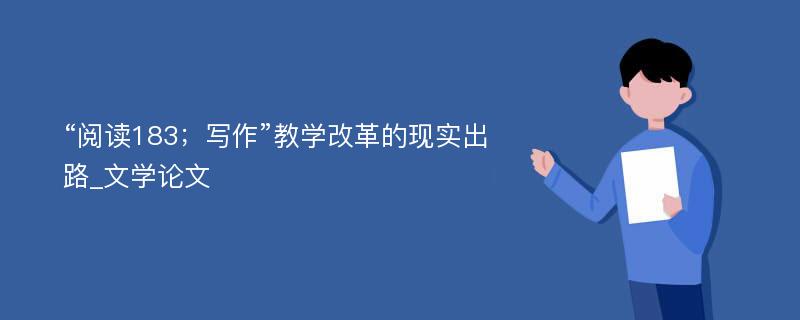
“阅读#183;写作”教学变革的现实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拒绝“有感情地朗读”
“荷叶圆圆的,绿绿的”,谁来读?你读的荷叶不圆,也不绿。谁来读?圆是圆了点,还不够绿……
就一句话,读一次,再读一次,读出感情来,读出感情来……
当前这种“以读促悟”、“以读悟情”的课堂似乎是语文回归的路标了。殊不知,在长达九年的语文学习中,如此“有感情地朗读”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试问,一千次没有内容的朗读能让孩子学到什么?拯救阅读教学,首先要对课堂中无休止的“有感情地朗读”说“不”。
如果语文是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统一是无可非议的,那么,阅读教学也理应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工具性就应直接体现在“阅读能力”上,为生活实践受用,比如能根据文本提炼主题、概括内容要点,能根据主题选择有效材料等等,这样的能力在写论文、写报告中极为常用,但是阅读教学并没有教这样的“能力”,而且这样的能力似乎和当前“阅读”中的“感悟”、“朗读”是不相关的。我认为阅读教学的工具性体现为以阅读能力为指征的独立训练体系,而“概括能力”是这个体系之核心,它可以从指代和还原、筛选和整合、提炼和归纳、推断和补充、质疑和批判、譬喻和类比等角度构建训练体系。从目前的现实性角度出发,应在“教材中编制单元”,根据不同能力点选择难易程度不同的实用类文本进行训练,实用类文本须有指向人文素养的质性结构。
阅读教学的人文性则主要体现在“文学类文本”的教学上,而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把“文学作品”和“实用类文本”教学功能相混淆,形成了并不实用的一些奇怪的阅读能力(王荣生教授语)。
文学作品的教学是读者和作品意义生成的媒介,教师所做的就在于架构起“体验”之桥梁或者路径,无论多么美丽的理论只有找到实践范式才能有教学意义。
之一,体验,从生活经验出发。梅洛庞蒂说,生活经验如同意义的呼吸。转向对生活体验的研究意味着通过再次唤醒对世界的基本体验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由此体验文本的重要路径则是打通生活经验的通道。心理学家普遍认为,一个人的故事会暴露其生活中的重要倾向和主题。于是运用主题分析法是尝试打通生活经验通道的重要方法。它要求被试者根据卡片上的情境(图片)编故事,故事内容向度应该包括:(1)图中显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即发生了什么事?(2)什么原因导致此情境的发生?(3)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4)当事人的思想感受如何?(马一波、钟华《叙事心理学》)被试者在看图编故事时,图片刺激的和故事情节中的正是其重要的需求、愿望、冲突等,通过描述和解释就会不知不觉地将内在的人格表露出来。于是《风筝》教学中,我首先要求学生根据主题分析的四个向度讲述童年的悔事。然后提供类似“风筝”故事的情景图片,要求学生根据主题的四个向度编故事,通过言说暴露作为读者存在的学生的人格,为建构学生的精神世界提供客观依存。最后,请学生根据四个内容向度讲述鲁迅的“风筝”故事。同一种结构在三次“叙述”中完成“我”和“鲁迅”精神意义的“吐纳”,设计前两次故事讲述其意义在于生活经验的获取和重新认识。
之二,体验,从作者的心路历程出发。现象解释学认为,传记、自传、个人生活史都是生活体验素材的潜在来源。然而,我们应该知道,传记通常用于记录个人生活中的隐私或其独特经历;我们阅读传记,可以接近经验,因为作品是以卓越的形态表现的生活经历。((加)马克斯·范梅南著,宋广文译《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人教社教材七至九年级教材共选了鲁迅作品九篇,从课后练习的价值取向看是被当作“应试阅读技能”训练的文本,这和是“鲁迅”的作品无关。如果把《风筝》作为鲁迅的作品进行教学,那么要“理解文本”,必须有“背景文本”,进行完整意义建构性的阅读,而阅读鲁迅的书信、自传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比如:当时的“我”为什么会对弟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难道“我”没有和弟弟一样爱玩的天性吗?这样的问题难道可以通过反复朗读解决吗?而从《鲁迅传》中的家境变迁等史实中是可以找到理解的背景的。
之三,体验,从理解知识出发。课程哲学家玛克辛·格林说:“仅仅接触艺术作品是不足以引起美感体验的,还要有一种能够发现艺术作品中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能力。即使是学术性的认识,也完全不同于在想象中创造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并从感知、情感和认知方面进入这个虚构的世界。要使人们达到这样的参与境界,就得在帮助学习者注意作品(形状、样式、声音、节奏、修辞、轮廓、线条等)和放手让他们自由地觉察作品的意义之间达成微妙的平衡。”在荣格看来,个体的精神成长需要神话、艺术、宗教这些象征“超越的”、“更高的”、“神秘的”“整合”,而领悟“原型”则是整合的典型模式(冯川《神话人格——荣格》),每个作品的“象征”则是“原型”的图式或者说样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作品的教学必须揭示作品那些超越的神秘的象征意义,以“整合”个人精神的成长。比如鲁迅作品中的“香炉和烛台”、“华夏”、“人血馒头”、“阿Q”等无不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由此教学《风筝》,为何不能从“象征”切入,通过激发生命唤起想象“风筝”、“小屋”、“游戏”这些物象的境界,把人带入意义更加充实、内容更加丰富的生命存在呢?
之四,体验,从写作表达出发。写作把我们与我们的生活世界分离开,又吸引我们更接近生活世界,并由此使我们发现了体验的存在结构。以一种文本形式无法言表的体验往往能够以另一种文本形式表达出来。比如对于爱的体验,行为科学的阐述很难令人满意,诗歌、音乐、美术这些形式却可以将其全貌呈现出来。对真理的体验,可以通过诗歌、小说、美术、音乐、电影技术等手段成为可能。((加)马克斯·范梅南著,宋广文译《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那么我们教学《风筝》是否可以通过改写成诗歌、绘本、剧本等形式表达阅读的体验呢?写作的过程是内化和重建对作品的“理解”的过程,作品则是体验和理解的表达。
之五,体验,从场景游戏出发。英国思想家斯宾塞发展了席勒的“游戏说”,在生命目的论的基础上把游戏和艺术审美统一了起来。作为教育学意义上的“场景游戏”,我们不妨把它视为一种“表演”,从剧场、服饰、语言、道具以及表演过程中实现和文学作品的意义对话与建构。如此把《风筝》改编成课本剧进行表演不正是一种“体验”吗?学校本身就是剧场,在苏珊·朗格看来,剧场是一个透人灵魂、可以对人进行全面地征服与改造的场所。(李政涛《表演:解读教育活动的新视角》)
象思维:语文之根
然而,文言文教学的工具性似乎又“过”了,我们把培养学生“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力”的目标建立在实词、虚词、用法、翻译这样一个知性解剖的模式上,这从中高考题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文言文教学的现状就是不断地总结和归纳各种知识,训练大量的题目。当然我们的教材是大致根据文言深浅来选编文章并分散在各个年级的,即使同一年级选文也缺乏内在思想脉络建构,更不用说整个初高中阶段了,这在客观上造成文言文的学习变成纯粹的肢解而失却了“人文性”。
汉字的根基是象形,“以象尽意”是我们民族思维的根。这种“象思维”在《周易》中就是象数符号,卦爻之象,在道家那里就是“无物之象”的道象,在禅宗那里就是回归“自性”的开悟之象。中国先哲正是以“立象”、“取象”、“象以尽意”的“象思维”打通了宇宙体悟的本真本然方式,创造了生命世界的诗思境界。庖丁从“见全牛”到“未见全牛”,再到“官知止而神欲行”,正是一个从具象、意象到“大象无形”的象思维过程。“象思维”中“象”的最本源是“大象无形”,这是“原象”,就是“有生于无”的“无”,就是“太极”,就是庄子的“无待”之自由之境,其具体表现可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达到思想与精神完全自由的境界。“象思维”让我们回到了自身本真本然之境界,它是非实体的,非对象的,非现成的。从《诗经》、《楚辞》到魏晋诗,再到唐诗宋词,从书法、绘画等等其抒情写意精神构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之象”,从本质上说“象思维”之“象”乃是“精神之象”。(王树人《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象思维”和西方文化之根的“概念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概念思维是主客二元的对象化思维方式,它把一切进行规定对象化,从而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却为物所累,为物所役,甚至陷入“殉物”的悲惨境地,人的存在陷入深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概念思维”不可能使人回归到“本真之我”之生命和宇宙息息相通的境界。海德格尔对实体论形而上学的批判认为两千年来人们把本来意义下的“存在”忘记了,这种“存在”就是非实体的一种表达,并且从诗歌中寻求“诗意”的倾向,他在解读荷尔德林“人诗意地栖居”时说:“作诗首先把人带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进入栖居之中。”
其实《易经》的比兴、类比这样一些“象思维”表征形式在老子、庄子、孟子、韩非子、荀子以及魏晋、唐宋元明清等时代的大师的作品中处处可见。庄子用“鲲鹏”、“庖丁解牛”、“浑沌”等这些寓言之“象”隐喻生命和宇宙之思。象思维是整体思维,我们不去较为完整地阅读这些先哲们的著作怎能体悟这其中的象之精神境界?仅靠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我们能打开老子伟大的诗境吗?由而,我想,要弘承文言文的人文价值,至少我们的教材要作如下之变革:
之一,文言选文应以作者为单元。初高中六年至少有十册教材,如果每册教材仅选编一位作者的作品,至少有十位作者的作品。六年中能真正较为完整地阅读十位大师的经典,就能运用“象思维”体悟大师们的生命哲学,这个过程比任何一种知识归纳的概念思维更具有人文意义。文言文应在小学教材中就编排。
之二,文言选文还应以“意象”为单元。神话中的“夸父”、“女娲”、“精卫”,诗文中的“酒”、“梅”、“菊”这些“精神之象”都是“象思维”之“象的流动和转化”。阅读“意象”主题的作品,就是“象思维”的“象的流动和转化”,既体悟“精神之象”中融合的“大象无形”之道,又是自我确证天、地、人贯通一体的生命存在的“我象思”。
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在五岁时就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诵读,上中学时就喜欢读《老子》和《庄子》,他对粒子研究的发现就是得益于庄子寓言的启发,“如果证明物质竟有三十多种的不同形式,那就是很尴尬的。更加可能的是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它可能是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还未分化的某种东西。用所习用的话来说,这种东西也许就是一种‘浑沌’。正是当我按这样的思路考虑问题时,我想起了庄子寓言。”这段文字生动证明了诵读经典对培养“象思维”的重要作用。诚如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从1929年起在芝加哥大学推广从荷马史诗到弗洛伊德的443部经典著作时所说,“不管这些18岁的学生以后干什么,做什么工作,他们都不该没有这一传统的筑防。这些书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教养的一部书。”
虽然没有人对语文教学回归经典质疑,但不是“象思维”视野下的回归是否能带着孩子走向生命的诗思?
“记叙文”让写作教学走入歧途
写作也必须体现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基本价值取向。现行以“记叙文”为主要取向的写作教学一方面要求作文具有真情实感,要写生活中发生的事,然而由于学生现实生活之境域,必然导致千篇一律的“假、大、空”;另一方面又要求作文要有新意,诸如各类故事新编,这和“记叙文”文体要求不是自相矛盾的吗?“记叙文”这一“文体”写作混淆了写实和虚构,弃置了写作本体的一些基本要求,从一开始就让学生不明白“作者我是谁”、“读者他是谁”、“为什么而写”,从而,它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活动,丧失“文体感”的写作是不存在的。现在所说的“记叙文”的作文形态只存在于应试作文教学中。换句话说,学生十多年的写作训练都是缺乏“文体感”的训练,按王荣生教授说是“应试性的小文人语篇”,这种文章体式的“作文能力”与我们意欲培养的适合于社会应用的作文能力之间有着严重的冲突。
如果说现在充分重视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和事、关注自己的生活并以“记叙文”这样一种文章体式来表现的写作形态是人文性体现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写作教学的工具性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写作教学体现“人文性”的体式,我认为是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而不是什么“记叙文”,还要加上个“诗歌除外”。写作教学的工具性应直接体现为“实用性”。
所谓“实用性”就是要为学生未来的生活和学习服务,不仅指一种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写作能力的外显表征,更是在思维等内隐层面具备深度和广度的倾向性特征。个人记事、日志记载、事件报告、读者来信、对作品的回答、用法说明、短评、读书文摘、求职书、简历、课文复述、作品阐释、图表描写和阐释、内容提要、记录、专题性报告等等都应该是实用性写作的内容。(《当代外国语文课程教材评介》)
从现在中高考试题关于“实用性写作”的考查来看,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实用性写作能力的考查在试题分值上需要加大,至少和“话题作文”应有合适的比例。二是考查提供的情境应以图表和文字情境为主,而不是笼统的所谓“生活情境”;特别要加强“体”的提示和要求,让学生知道写作的对象。三是应有考纲条目,对各个能力点进行明确。
除此,在各年级教材中应增加一个“实用性写作”单元以推进实用性写作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