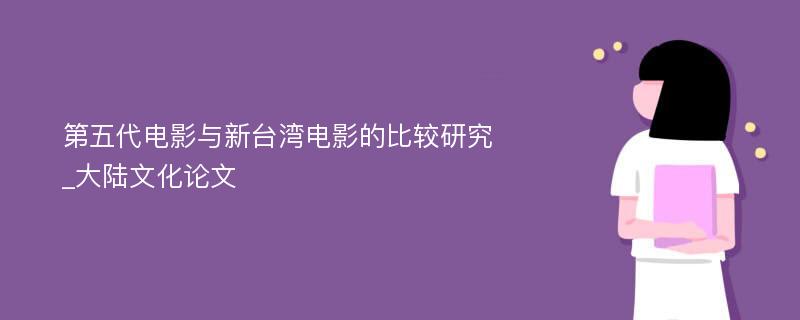
“第五代”电影和台湾新电影之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第五代论文,新电影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语 旅美学者陈犀禾先生的这篇文章对80年代两岸新电影运动的异同作了比较,其中关于成因及变化前景部分的观点尤有新意,这对人们展望下世纪的中国电影走向可能是一个有益的参考。
大陆电影和台湾电影本出一源。他们植根于同一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1949年以前的上海电影传统)。1949年以后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到八十年代,大陆由于经济和政治的开放,文化呈现一新的面貌;台湾亦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文化进入一新的境界,两地在电影中都有一个“新潮”。两个新潮都由年轻的新生代领头,都打破了各自传统的电影规范,而且很快都驰誉世界影坛。但是透过这些相同点,究其所呈现的影象和文化心理内涵,它们又是十分不同的。
“第五代”和其“逆文革情结”
大陆第五代导演创作的滥觞可追溯到1983年底、1984年初出现的《一个和八个》(张军钊)。紧接着,陈凯歌导演了《黄土地》(1984)。此片不但在大陆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亦在同年香港国际电影节上引起轰动,并很快吸引了国际影坛的注目。同年,吴子牛亦导演了《喋血黑谷》。次年,第五代的其他重要成员又推出了《猎场扎撒》(田壮壮)、《黑炮事件》(黄建新)、《绝响》(张泽鸣)、《女儿楼》(胡玫)等重要作品,第五代于是蔚为潮流。在以后几年内,第五代不断有新作品和新作者出现。第五代新浪潮的高峰是在八十年代中期。1988年以后,随着大陆电影工业向市场经济体制靠拢,娱乐片成为强势潮流。这种压力使得第五代的某些导演试图在个人创作追求和市场商业压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最后的疯狂》(1987,周晓文)、《疯狂的代价》(1988,周晓文)、《顽主》(1988,米家山)、《摇滚青年》(1988,田壮壮)。第五代导演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其活动一直持续到今天,并不断有重要作品出现。如张艺谋的《红高粱》(1988)、《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秋菊打官司》(1992)、《活着》(1993),大多制作于八十年代晚期和九十年代,另外还有《血色清晨》(1990, 李少红)、 《大磨坊》(1990,吴子牛)、《霸王别姬》(1992,陈凯歌)等。但从其所体现的文化特征,它可以被划分为“第五代”和“后第五代”两个范畴。电影学者倪震对此作了如下界定:“如果说第五代电影强调美学概念的表达,并且把故事架设于较为原始、自然的时空,那么‘后第五代’电影的时空是都市,它的主题则是现代社会人与人的冲突。”
第五代导演在题材内容方面大多回避了直接的个人成长经验。它们或来自于历史,如《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或来自于域外之城,如《猎场扎撒》、《盗马贼》;或来自于当代,如《黑炮事件》。而他们自身成长经验中重要的一段经历——文化大革命,在他们的作品中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
在表现风格上,第五代作品带有表现主义的色彩。他们有许多真实的场景,但这些场景在特定的构图、光影、色彩、剪辑和叙事中变得带有强烈的象征和隐喻意味。例如《黄土地》中的土地、河流和窑洞,《黑炮事件》中的会议室和挂钟,《红高粱》中的高粱地,《大红灯笼》中的深宅大院;在情节方面也是如此,如《黄土地》中的翠巧之死,《红高粱》中“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故事,都是极富戏剧性和隐喻意味的。
其间,第五代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中国经验”。这种“中国经验”中充满了进步和落后、文明和野蛮、理性和疯狂、独立和盲从、科学和迷信、压迫和反抗、个体生命和社会传统、封建主义和反封建主义之间的激烈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几乎总是消极的方面:落后、野蛮、盲从、疯狂、迷信、压迫、传统和封建主义占了上风;而无数的普通人,常常是最无辜的生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第五代的电影中,中国的现实常常过于痛苦而难以接受。事实上,第五代的影片是他们文革经验的表达。但是,它并不是对文革的事件和人物的直接表现,而是把文革经验(有意无意地)再现在历史的隐喻之中,并藉此表达对文化大革命一整套名为革命(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实为封建(迷信专制、摧残人权)的观念体系以及根据这一观念体系制造出来的神话体系的激烈批评。正如陈凯歌在谈到《黄土地》时所说的,他的影片是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重复延续这个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第五代电影所再现的文革经验对文革时所流行的观念和价值体系是一种逆向关系。对第五代电影的这种文化心理特征,我以“逆文革情结”名之。
台湾新电影和“本土意识”
台湾新电影始于1982年《光阴的故事》。该片以时代的演进为线索,包括四个独立的故事,分别由四个青年导演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执导。四段故事虽然风格不同,但都摆脱了传统的电影模式,被称为“浊流中的清泉”。次年,又有由侯孝贤编剧、陈坤厚导演的《小毕的故事》推出,叫好又叫座,并赢得数项金马奖,影评誉之为新电影开创时期的代名词。随后,《儿子的大玩偶》(1983,侯孝贤,曾壮祥,万仁)、《看海的日子》(1983,黄春明编剧,王童导演)、《海滩上的一天》(1983,杨德昌)、《油麻菜籽》(1984,万仁)、《老莫的第二个春天》(1984,李佑宁)等片均获票房和评论肯定,新电影遂成潮流。在以后几年里,新电影的重要作品和作者不断出现。这些影片题材贴近现实,风格清新,迥然不同于传统的政教片和商业片,被认为是台湾八十年代以来电影创作中一个最重要的新现象。但是,由于新电影并不以商业卖点取胜,在电影市场竞争中始终面临巨大压力。1987年新年伊始,由五十多位作者(包括许多新电影的重要作者)具名的台湾电影宣言:“给另一种电影一个存在的空间”,即反映了这种情况。宣言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但并没有解决新电影所面临的问题。1987年以后,新电影势头渐弱,所以台湾不少电影作者和学者认为台湾新电影在1987年以后已经结束。事实上,1987年以后,一些新电影的重要作者仍在原来的方向上继续努力、并有重要作品出现。如侯孝贤的《悲情城市》(1989),王童的《香蕉天堂》(1989)。特别是《悲情城市》,根据台湾电影批评家焦雄屏的观点,“标示着台湾新电影的真正成熟阶段。”
在题材内容方面,新电影不同于台湾传统的政教片和娱乐片,而把现实主义带进了台湾电影。他们从日常生活和现实环境中寻找题材,许多都是所谓“个人成长模式”的电影,例如《光阴的故事》、《小毕的故事》、《海滩的一天》、《青梅竹马》、《油麻菜籽》、《我这样过了一生》和许多自传体式的作品,如《童年往事》、《恋恋风尘》、《冬冬的假期》、《阳春老爸》。这些个人的成长经验,呈现了新电影作者为台湾几十年来的变化所作的集体式记录,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台湾现代变迁图。而在此之前,真正的“台湾经验”在台湾电影中则是“一片空白”(台湾学者王玮语)。
为了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经验,台湾新电影在风格上也刻意追求现实主义。他们舍弃了传统的戏剧性故事结构,而采用情节淡化的叙事结构,将人物置于社会现实的脉动中,以非戏剧性的、更接近常人生活经验的方式审视社会和人物两者的互动关系。他们大量运用长镜头、深焦镜头、实景拍摄、非职业演员及内敛含蓄的表演方式,使新电影的外观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叙事电影的写实风貌。
通过这些题材和风格,台湾新电影直接地呈现了他们的本土经验。在这种呈现中,新电影对于台湾社会的本土现实大多取一种接受的态度。虽然在总体的接受中有反省、批判,但他们都把这一现实看作是自己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台湾新电影的基本特征,不少台湾学者以“本土意识”加以概括。
“逆文革情结”和“本土意识”之比较
“逆文革情结”和“本土意识”显示了大陆和台湾新一代寻求新的文化身份的努力。在这种寻求中,大陆第五代和台湾新电影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他们前辈的、属于他们自身的独特文化经验。这是他们的相同点。但是,这种相同也意味着他们的差异。因为他们都是“二战”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成长于(大陆和台湾)两个分裂的地理文化空间。这使得他们所呈现的文化经验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方式。第一,大陆第五代呈现的是大陆的文革经验,台湾新电影呈现的是台湾的本土经验,两者没有联系和交叉。这不像上一代台湾的“反共影片”和大陆的革命影片(主要是描写1949年以前内战的影片和1949年以后的和美蒋特务斗争的影片),两者都从各自的视角呈现了自身和对方,从而创造了完整的、然而是互相对立的两种“中国经验”。第二,第五代的电影是他们自身文革经验的非直接的呈现,台湾新电影则是直接地呈现了他们的本土经验。第三,第五代电影对文革的经验(或中国的经验)持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而台湾新电影对他们的本土经验基本上持认同的态度。第四,第五代电影更倾向于的是集体的经验。他们关注个人的生命和价值,但他们创造的个人,常常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人”,是在历史中的个人。他们的影片常常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一般思考。而台湾新电影呈现的是个人化的经验,其中充满了具体的、微观的个人生活的记忆和痕迹,表达了对个人的独特存在的不可重复性及其价值的关怀。其观察角度常常是聚焦于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变化。第五,第五代的“逆文革情结”是一种纠结的心理状态,对与之相对的文革观念和中国神话执着不舍。他们试图通过“改写”历史来重塑今天。而“本土意识”的出现,意味着它已经从旧的经验和心理状态中脱身而出,努力塑造一种新的文化经验。
和传统文化、现代化以及政治的关系
在进一步把两者的文化内涵作比较时,我们发现他们还有以下差别。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第五代持明确的、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延续。而台湾新电影对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持回归的、认同的态度。对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来的传统文化的失落,表现出一种怅茫、失落、怀念的态度。但在深入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五代对传统文化的批评集中在政治和体制方面,台湾新电影对传统的认同则偏向于伦理和人情方面。
在对现代化(西化)的态度上,第五代是认同和肯定的。事实上,他们是站在现代化的立场上批判传统文化。他们认同和肯定现代化的态度还特别明显地见之于“后第五代”的“城市电影”,他们以乐观和期待的心情表现了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现代城市生活,如田壮壮的《摇滚青年》。相比之下,台湾新电影则对现代化持保留态度,他们常常怀疑、甚至批判随现代化而来的台湾社会中消极和病态的人际关系,如杨德昌的《恐怖分子》。
第五代电影具有强烈的政治批评意识,他们试图用一套新的文化价值系统来取代文革的泛政治价值系统,并以此来塑造一种新的中国经验,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身份。台湾新电影早期的大部分作品对政治层面的经验存而不论。这种情况在后期作品,如《悲情城市》、《香蕉天堂》中有所改变。
这种文化内涵的差异揭示了今日台湾和大陆社会环境及成长于其中的新一代观念之差异。台湾已进入发达社会,它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来看待传统和现代化的问题,故对现代主义有所批评和对传统有所回归;而大陆属于发展中社会,它是站在前现代的立场看待传统和现代化的问题,故对传统多有批评而对现代化多有向往。另外,大陆的政治动荡激化了年青一代的政治意识;反之,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及其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淡化了其政治意识。总之,“逆文革情结”和“本土意识”处理了各自的社会现实。这不同于上一代的电影,例如大陆的革命电影和台湾的“反共”影片。
成因
台湾新电影的作者大多是“战后新生代”,台湾经验是他们主要的成长经验。这种作者方面的条件是“本土意识”成因的一个起点。另外还有社会方面的条件:第一,七、八十年代以来“战后新生代”成为社会中坚,为注重本土现实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社会基础。第二,台湾近几十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相对稳定,为肯定、认同本土现实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现实基础。第三,随着七十年代大陆和美国建交以来一连串的外交挫折,使台湾社会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意识。他们在把注意力转向本土现实时(外部的变化似乎是难以逆料和控制的),倾向于在本土现实中找到一种积极的、足以肯定自我的基础。这为认同本土现实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心理基础。
文化大革命在大陆是一种普遍的否定性的社会经验,应无疑问。新老几代导演的影片都对文革有批评性的表现。但第五代和其他导演的反思模式不一样,他们把一个全球的、文化比较的观点作为他们思考文革的前提。这样,他们不是把文革和中国历史的某一点相联,把它看作一个局部问题,而是把文革现象和整个中国历史相联,把文革中的问题看作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从而对中国文化提出了疑问。由此,他们不仅处理了历史,而且呼应了开放后的现实。和台湾新电影的作者一样,大陆第五代也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在他们思想形成最关键的十年,他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然后,他们又进入了新时期开放年代并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两种不同的经验和背景使两者新观点的形成成为可能。
前途和可能性
虽然1987年以后,具有独特美学风格的新电影已不再是台湾电影的主流,但其所呈现的“本土意识”依旧强调,似无疑问。一些近期的优秀影片如《饮食男女》(1994),承接和发展了这一主题;许多通俗影片也将“本土意识”所强调的“台湾经验”变为一种商业性时尚,例如《暗夜》(1991)。就大体而言,“本土意识”在意识形态上会维持目前的格局。但也有另一种倾向出现,它涉及到以前新电影甚少涉及到的层面,并强化了其批评意识,如《悲情城市》和《香蕉天堂》所显示的倾向。
大陆第五代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已成为大陆电影工业的中坚,这种情况将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其文化内涵“逆文革情结”亦面临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强化,甚至浮向表面。如《菊豆》、《大红灯笼》、《霸王别姬》所显示的。但未来更大的可能是随着大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而逐渐淡化。其淡化有两种形式:一,转化为对新的生存环境的认同,正如“后第五代”在其“城市电影”中所显示的,并生成一种意识形态(第六代?)。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在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可能会和“逆文革情结”有不同的表现,如非政治化、对传统和现代化关系的重新思考;并在关注重点上转向城市个人生活。二,继续呈现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主题。但“逆文革”的旨趣已悄然隐去,而变成一种中性化和距离化的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展示。
1949年以后,大陆和台湾电影走向不同的方向。不管两岸之间的关系今后如何发展,文化的多元化似乎已成趋势。这种情况不但表现在两岸之间,在大陆和台湾内部也是如此,因为新电影和第五代正是文化多元化的产物。与此同时,它们共同的、内在“中国文化情结”(不管批评或认同)则又使他们共处于同一个大文化现象之下。
标签:大陆文化论文; 新电影论文; 黄土地论文; 霸王别姬论文; 红高粱论文; 悲情城市论文; 菊豆论文; 黑炮事件论文; 香蕉天堂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台湾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