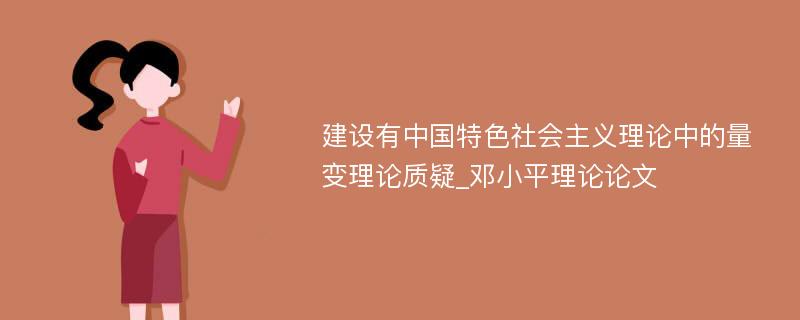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量变论”的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量变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仍有少数人坚持认为,毛泽东是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先驱,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所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仅仅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方面量的变化。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在外延方面的延伸,其理论的内容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范畴,其理论的特色只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一些细微枝节和具体的方法方式上的变化,并没有突破毛泽东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对此,笔者就这种“量变论”提出以下质疑。
第一,具有相同的思想核心,是否一定产生相同的理论内容?
“量变论”认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立足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而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和核心也是实事求是,在这种相同的核心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和理论也必然是相同的,所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相比较没有质的突破。诚然,实事求是确实贯穿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始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起指向作用,在理论的确证过程中作为必要条件起约束作用。但是,具有相同的实事求是理论核心,是否就一定会形成相同的理论内容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同样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但对问题观察的方位角度不同,所处的时代、条件不同,个人的主观思维方式不同,也会产生出不同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从中国遭受几千年封建压迫,人民急于摆脱贫困和剥削的客观实际出发,提出了“工农商学兵合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好一种组织形式,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在此阶段,将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论断。
而邓小平从中国由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落后,经济不发达的实际状况,提出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实行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
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老一辈共产党人都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就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出含义迥异的观点呢?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众所周知,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在当时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把国内有限的资源集中用到急需发展的有限目标上,这就决定了实行毛泽东所倡导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但是,理论和思想的产生又是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的。当国家的工业化基础和相对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立,作为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按照社会再生产的规律,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必然被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所取代,数量速度型经济必然被质量效益型经济所取代。这样,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所主张以价值规律的调节为动力的市场经济理论,也就有其应运而生的必然性。所以时间和条件的变化,必然导致理论和思想的变化,这既是正常的社会意识运行规律,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同于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理论依据。
第二,理论中有相同的部分,是否就一定不会产生质的突破?
“量变论”的第二个论点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些观点、思想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所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没有超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只是在一些细微的枝节上有部分量的变化。应该承认,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相比确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具有相同的内容是否就没有质的突破呢?回答仍然是否定的。
党的十四大指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为飞跃,不是量变,而是整体性跃进的质变。同时,飞跃必须有对象,无对象的飞跃是不可能实现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表现为对马、恩、列、斯理论飞跃的同时,主要表现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飞跃。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限制商品生产发展的生产方式等方面。他同时认为上述基本特征之下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必然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在邓小平看来,本质和特征是不能简单混同的,本质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内在规定性。而社会主义特征则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外部表现,是本质的要求和反映。于是他并没有拘泥于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认识,在分析特征的基础上,实现了认识上的飞跃,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念,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内容相比,前者是对后者的升华,具有全新的内容和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他明确回答了长期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未能解决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关键性问题,所以社会主义本质论带有明显的质的突破性和相对的独立性。
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继承和发展是否仅仅是量的扩涨?
“量变论”的第三个论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老一辈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历史经验的总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毋庸置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实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中的许多合乎客观实际的有益东西。但继承并不意味着全盘吸收,而是有目的、有选择地对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扬弃”。所以,我们在看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继承方面的同时,亦应注意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发展。
所谓发展,其涵义则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这种新事物的产生就不仅仅是量的扩涨,而反映着质的突破。作为理论的质变,一般有三种形式:完全取代、同质归并和归并取代。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应是第三种形式。其质的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突破了超越阶段、急于过渡的“左”倾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改革为标志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其二,突破了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是纯而又纯的社会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多样性特点的社会。其三,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其四,突破了片面强调独立自主、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提出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既然“量变论”承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那么就不能不承认上述邓小平建设理论必然有着代表质的突破的新的思想内容。这种新的思想内容相对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也必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否则,“量变论”自身就具有逻辑上的矛盾,当然,也就不可能很好地解释“发展”二字的确切含义。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同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有继承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建设理论的发展、突破和创新。那种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量变的观点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只有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和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所作出的历史性重大贡献以及这一理论创立的伟大现实意义,才能更好地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完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