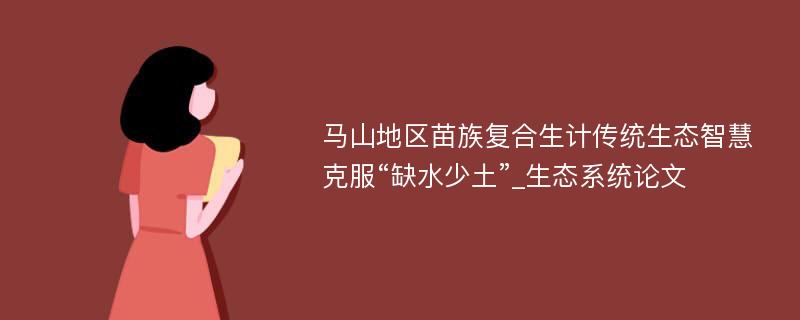
麻山地区苗族复合生计克服“缺水少土”的传统生态智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苗族论文,山地论文,生计论文,生态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5/Q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1)01—0034—06
一、引言
学术界早就提出了“脆弱生态系统”[1][p.6-8]这一概念,并明确提出所谓脆弱生态系统具有抗逆性差这一特点,脆弱生态系统一旦受到了不合理的人为损伤就很难自我修复和自我恢复。麻山喀斯特山区的生态脆弱环节在哪里?其实就是“缺水少土”。如何保存这里的“水”与“土”就成为文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麻山地区石漠化灾变已经酿成,原生生态系统的延续就会造成时间上的断裂,蜕变后的生态系统只会按另一种运行方式去延续,以至于原先行之有效的办法现在完全不适用了。不认识到生态恢复的手段、技术和技能需要改弦易辙,那么,好心的支持和麻山地区人民的长期努力都会落入生态陷阱,花了钱办不成事。有幸的是,麻山乡民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他们也曾受过石漠化的打击,对付石漠化他们有从头做起的经验和技术,也有配套的技术技能,凭借这样的经验和技术他们可以把断开的时间重新链接起来去展开生态建设,并收到理想的成效。[2]麻山地处喀斯特地貌发育区,地表破碎、土石混杂,自然与生态环节中最容易受损的原因处在水土流失上。在这里由于重力侵蚀、流水侵蚀和溶蚀作用复合并存,很容易诱发水土流失。实行复合生计,地表植被的覆盖能长期保持高密度的稳定,因而能够高效地抑制各种形态的水土流失。
二、苗族复合生计方式的基本样态
据史料记载,麻山苗族长期以来一直实行刀耕火种。刀耕火种大多选择在山体的溶蚀坑开口或裸露石山的山脊区段,实施多种农作物的复合种植,并且将农、林、牧、狩猎、采集有机地整合起来。在这样的复合经营中,几乎可以做到不翻动表土。播种作业需要针对耕作区段土石结构的特点,灵活采用不同的操作方法。[3]当地苗族民谚说:“刀耕火种种小米”,但更通用的说法是将这种做法称为“烧小米”。谈起“烧小米”,当地年长一点的乡民对耕作细节记忆犹新,并且对这种几近消失的农耕方式充满向往和依恋。
其具体做法是,农历二月间,先齐地面砍倒灌丛、杂草,然后将它们架空在岩缝上,摆放成有规律的“过火通道”。经过连续几个晴天后,砍下的柴草已经彻底干透。在清明前后即将下雨的前一天下午,从山脊下方点着柴草,火势就顺着预先摆好的火道能自然烧遍所有架空的柴草,并确保能烧透土石。大火熄灭后,岩石、土壤和灰烬开始转凉时,就把准备好的小米直接撒播到过火山脊坡面的灰烬上。撒完后,一般都会有大雨来临,不久小米就会发芽生长了。明人江进之的诗歌有云:“绝壁烧痕随雨绿”,即是对这一操作的生动写照。
“烧小米”根本不需要动土,加上在这一过程中,由于野生植物地下部分没有被触动,还能发挥固土作用。因而即使是最陡的山岩,遇上再大的暴雨,表土都不会冲下山来。用这样的办法种植粮食作物,才能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
除撒播小米外,还可以混种天星米、红稗、高粱等其他农作物。天星米可以和小米一道撒播,红稗需要移植,高粱则直接点种,但点种的高粱也只是戳洞点播而已。只有那些种粒较大的农作物,如豌豆、饭豆、扁豆、南瓜等则需要开穴播种,但这样的开穴都是看具体的土石结构而定,也不需要挖翻土地。因而有理由将这样的耕作称为少动土耕作,目的都在于抑制水土流失。将他们的农田作物构成与原生生态系统相比,不难发现其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当地原生生态系统是亚热带藤蔓丛林,攀援类和匍匐类的植物密集生长,匍匐类作物在生态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在农田中,丛生状态的豆科植物也占有很大比例,因而他们的作物种植是一种模拟原生生态系统的耕作办法。原生生态系统靠植物多层次、高密度的覆盖,能有效控制水土流失,这种农耕也自然具有等同功能。
除了播种不动土外,麻山苗族还不实行中耕,收获也尽可能避免动土。不中耕同样是为了少动土,听任野生植物继续生长,但却要不断地对这些野生植物加以“收割”,目的是为牲畜提供饲料,同时又起到避免野生植物疯长的功效。明人田汝成所说的“耰而不耘”,[4]就是针对不必实施中耕而言。
麻山苗民实施多种农作物混合种植,每一块土、每一处洼地,适合种植什么,老乡们非常熟悉。甚至祖辈在哪一小块田土上哪一年种了什么、卖到哪里等相关故事,他们都如数家珍。种植物即熟即收,即收即用,先熟先收,后熟后收。收获后根据数量和价值决定其用途,质量好、数量少的作为人的食物,质量次、数量大的供作牲畜饲料。以至在他们的耕作区段内能终年保持多层次、高密度的作物覆盖,这也是能够抵御暴雨淋蚀的适应对策。农作物、野生植物的混合并存,使他们的耕作区成为百宝囊。各种用途的生物资源同时并存,因而正如葛兹比喻的那样,这里的耕地也是周围自然生态系统的“人工缩版”。[5][p.107]
同一种生物资源在麻山苗族手中,可以做到多层次、多手段、多内容的复合利用,这也是他们复合生计的特色之一。天星米在麻山苗族的农田中就具有特殊的意义。天星米属于苋科植物,是在麻山地区苗族的烧畲地上普遍生长的一种半驯化的野生植物。它的嫩叶从四月开始到七月,一直是当地苗族的家常蔬菜。七月以后,长老了的叶、杆连同正在开花的穗,又会被割来充作猪的饲料。等到十月到十一月,被割掉顶端的天星米照样可以结实。这时候,麻山苗族又会陆续用摘刀割下成熟的穗线集中晾晒,再用联枷拍打脱粒后收集籽实,作为粮食储存。脱粒后的穗线用作牛和猪的饲料,割掉果穗后的残株,在冬季通常被用作燃料。这样去利用天星米,同样是稳定地表植被高密度覆盖的举措之一,在利用的同时也是在有意识地兼顾对水土流失的控制。[2]
麻山的传统生计中,还要实施农牧兼营,农牧兼营的最大好处也在于能高效抑制水土流失。麻山牲畜和家禽喂养也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宗地花猪肉质鲜嫩,是有名的特产。猪、羊、马、黄牛、鸡等都实行开放或半开放性放养,由于山坡陡峭,牲畜放养在山上以后,地形所限它们几乎都不能乱跑,因而麻山的乡民从不惧怕牲畜走失。在作物生长期间,将鸡放入农田为农作物消灭害虫,但对会妨碍农作物生长的食草大牲畜则禁止进入农田。在收割以后农田又转化成牧场,烧畲地休耕时也改做牧场,这就使得种植与和牲畜的放养融为一体。与此同时,农田中不断收获的家种和野生植物又都是作为大型食草动物的饲料使用。牲畜排放的粪便还会增加土壤中有机质的含量,加快表土的物质循环,刺激野生植物生长速度,从而发挥更强的保水固土作用。由于当地生物种类极其多样,不同生物会均衡取食,在牲畜取食过程中,地表覆盖度和覆盖密度也都能保持长期稳定。[2]因而同一块土地不管作农耕还是畜牧,都能高效抑制水土流失。
麻山林业也实施多层次利用。用材树主要有松、杉、枫香、椿树等,经济树种有油桐、杜仲、厚朴等,还有纤维树种棕榈树、构树。对构树的利用,就是一个多层次利用生物资源的典范。构树的浆果是猪的肥育饲料,猪取食构树复果后,由于其种子具有坚硬的外壳不会被消化而随粪便一道排出,便在土地边角和草坡上分散开来,这些猪粪就成了构树种子的培养基,大雨过后其中就会长出一丛丛的构树苗来。构树树叶可以喂猪、喂牛、喂羊,必要时还可以喂养柞蚕。构树树皮纤维长且韧,早年被苗族群众用来制作衣物,还作为优质的造纸原料,是当地重要的外销产品。剥下树皮后的枝干可以作为柴薪,成材的构树又是当地首选的建筑用材。在当地乡民眼中,构树浑身都是宝。林地更新时,一般都要转化为烧畲地使用,再用作牧场一段时间,然后又恢复为森林。这种周期性扭转,同样是为了保持地表高密度覆盖,以便有效地控制水土流失。而且这种农、林、牧用地的互换,加快了物质运行,同时产出多种物质产品,满足人类的多种需要。
在烧畲地上,麻山苗族乡民们还会有意识地留下一些高大的乔木与庄稼一起生长,烧畲时不触动它们。火焚后,灌木、木质藤本植物地下根及地上茎的残段,还能发芽再生,和作物一道生长。对于那些长在烧畲地边缘上的乔木和灌木也不触动,仅是在它们遮蔽作物阳光后,才实施修剪。这些野生、半野生植物是乡民的采集对象,在提供产品的同时又增加了地表的覆盖密度,使得麻山地区稀缺的土壤在乡民手中几乎看不到明显的流失。
他们用一个专用的术语“护”来称呼当地所有伴生的野生植物,意思是对有采集价值的乔木、灌木、木质藤本植物,在实施刀耕火种或放牧时,都尽可能少动或不动,保证在烧畲时不死去,并根据它们的价值来控制长势。不彻底清除这些植物,同样是为了避免深翻土地造成水土流失。
麻山苗族的复合生计还包括狩猎采集。当地直接利用的生物物种极其丰富多样,除高大乔木以外,还有灌丛、地表的菌类和地下的竹笋等,早年麻山苗族生活中的蔬菜来源主要仰仗对竹笋、蕨菜和菌类的采集。据调查,他们不仅拥有同一地带其他民族都有的农作物和家畜品种,还能够利用当地野生的数十种植物提供食物、纤维、饲料和油料等;采食数十种不同的昆虫;驯化二十几种野生动物,其他的狩猎采集对象更是不胜枚举。当地的野生植物群落和动物种群规模虽然不大,但种类丰富。由于他们实施的是均衡取用狩猎采集的结果,因而生物的多样性照样可以得到稳定的延续。这样一来,不仅人工密集使用区段水土流失能有效控制,人类没有利用的原生植物群落也能长期高密度稳定。[2]因而他们的复合生计不管在哪个方面,都能对当地容易发生的水土流失做到高效控制。
纵观麻山的复合生计模式就会发现,首先,不动土或少动土种植是整个传统生计的精髓。其次,这样的生计方式高度地因地制宜,做到了地尽其用。再次,就是仿生性的生计模式,有效地规避了自然风险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特征。[6]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下的人群和不同的地区理应互有差异。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并存是生态环境良性运行的基础与前提,多样文化对生物资源的不同层次利用可以使生物群落的内在结构复杂化。只有特定文化与生态系统的耦合状态下,才能经受住自然和社会巨变的冲击,显现其抗逆能力,这样一来,就使得生态系统的稳定延续。麻山苗族乡民传统复合生计能够较好地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就在于苗族的这种麻山复合生计能够有效地规避了该区域的生态脆弱环节,从而使其生计方式与其生态系统达成耦合演进关系,成为人地关系和谐的范本。
三、文化干预意在重建文化与所处生态系统的耦合
有学者认为,贵州麻山石漠化灾变区成为当地的“土地癌症”,进而认为这已经“癌症”,就是不治之症了,即在这样喀斯特山区一旦出现了石漠化灾灾变,就只能听之任之,任其存在。这就意味着人力包括文化在内的其他科学技术在恢复喀斯特石漠化灾变区的生态系统都将无效的。但在我们二十余年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喀斯特山区的“石漠化”既有地质特征结构运动的因素,但也有民族文化行为的因素,而且人为的文化因素在当代该地区的“石漠化”进程中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地质运动造成的后果我们无从改变,但人类的文化行为所引发的“灾变”后果,是可以通过“文化”去加以“改变”的。
只要人类在活动中能够避开该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对特定民族的文化事实与生态系统的对应关系进行全面的清理,使其文化事实的运行能够绕开该区域的生态脆弱环节,该区域的生态系统不仅可以得到很好的维持,即使生态环境发生了灾变,也是可以恢复的,以对当地生态资源实现可持续的利用。这一过程就是“文化干预”所体现出来的对生态系统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的价值所载。
在我国西南喀斯特石漠化荒山要实施生态恢复,首先要对其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进行科学甄别。在麻山地区,其生态脆弱环境就是少土缺水。虽然这里的降雨量丰富,但由于地面几乎没有泥土,降下的雨水会立即被蒸腾挥发,而不会较长时间滞留在地面上,针对这一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当地居民的生态智慧就在于巧妙地利用木质藤本植物以及匍匐类的植物,来加强对地面的覆盖。[7]这些藤本植物和匍匐类植物可以将自己的根系扎生在岩缝中,从岩缝中吸取营养,而一旦存活就会将裸露的岩石进行包裹,在岩石上铺上一层地毯一样,使降下的雨水得以滞留,这不仅有效地降低了地表的温度,同时控制了水资源的无效蒸发。
因此,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苗族乡民从生计活动时,就对苔藓类、蕨类植物,蕨类植物的倍加珍惜。乡民的这一做法,其本质就是在于给地面以加厚来贴近地表植物的密度和厚度。这一智慧既可以稳定喀斯特山区基岩,以免山石的下滑,更主要的是增加了地表植物层之间的水蒸气饱和气层。乡民在长年累月的生产活动发现,只要有遮阴与水蒸气饱和气层稳定的地带,就会有苔藓类植物的生长,而一个地带一旦有了苔藓类植物的生长与蔓延,该地带就可以种植庄稼,庄稼就可以有收成。原因在于苔藓类植物将裸露的基岩包裹起来以后,就可以部分地代替土壤发挥水资源储养能力,缓解了喀斯特荒山既缺土又缺水的生态恢复障碍。与此同时,乡民在作物种植时,还必须辅以大量的丛生类植物,我们知道,丛生类植物同样可以发挥降低高温,滞留降水的过渡作用,维护藤蔓植物和蕨类植物的生长。乡民种植丛生类植物,还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招来食草类动物,通过动物的粪便和对子实的采集来替植物传播种子或花粉,使喀斯特山区的植被覆盖得以加速。除此之外,乡民种植丛生类植物还可以加快腐殖质的增长,还原成无机肥料,缓解喀斯特荒山土地贫瘠。
在喀斯特山区也有零星或者是成片高大的乔木,这些高大的乔木凭借其强大的根系,从岩缝的深处将无机养分吸收出来,一年四季的循环,在秋冬季节的落叶堆积在地表,腐烂而转化成肥分催生那些贴近地面的藤蔓植物和苔藓植物健康的生长。
可见,这种藤蔓/丛林生态系统生物之间本来所呈现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属性,其本身就是对该区域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的保护。这些层次不同的植物和动物都有自己的作用和贡献,同时也都依赖其他动植物生存。
凭借我们在麻山20多年的田野调查,我们都注意到石漠化山区的坡面上,尚残存有禾本科、菊科和苋科的植物。这些植物大部分可以凭借风力和流水传播的植物;在我们的观察中进一步发现,仅存的土壤都储存在岩缝中,而岩缝的开口又很小,加上这些岩缝往往又被种子小的植物先行填满,在生物的种间竞争中,种子颗粒较大需要动物携带的植物,根本没有机会自然落入岩缝中,而获得生存的机会。可见,藤本植物、苔藓类植物、蕨类植物都会成为喀斯特荒山生态恢复的必备物种。而这些植物的种子进入不了喀斯特荒山,这一缺环也只有仰仗人类帮它去克服。当然这样的藤蔓植物、苔藓类植物的长成,还不会乖乖的布满整个裸露的基岩,它们还会依照自己的生物本能走它们的路。
笔者在这一地区通过连续5年的调查研究和实验印证,发现如下三个环节是限制生态系统自力恢复的关键,而必须依靠人为的文化干预才能实现生态修复。首先,能支持植物群落成活的土壤都隐藏在地表以下的溶蚀坑中,而溶蚀坑的开口十分狭小,植物种子落入岩缝中的几率极低,不到1/100000。只有鸟类和特种啮齿动物藏匿食物的时,才能满足这一播种要求。但当前由于地表生态恶化,这些动物稀缺,因而失去了生态系统自然恢复的“播种机”。其次,由于当地土壤稀缺,对大气降水的截留能力极为低下。裸露的岩石在日照下会急剧升温,不仅导致水资源的无效蒸发,还会杀伤植物。只有藤本植物成活后,并将基岩覆盖,直立的乔木才能顺利长大。而当前的植树造林仅种乔木,不种藤本植物,因而生态系统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可能。再次,苔藓类和蕨类植物能够在裸露的基岩表面或砾石缝中生长,只要上部有藤本植物覆盖,就可以正常的生长,全部覆盖裸露基岩,并部分地替代土壤,发挥截留和储养水资源的能力,满足植物群落生长的需要。但这些非被子植物,只能靠孢子繁殖,而孢子又只能随水流向下传播,以至于石漠化灾变一旦形成,植物群落在石山陡坡坡面就不可能自行恢复。除非以苔藓植物为生的鹿科和灵长目动物存在时,才能将这些植物的孢子向上带到山脊和陡坡上。而现在,这些动物已经绝迹,因而生态系统就不可能自行恢复。
因此,类似地区生态系统恢复的上述三个关键环节的断裂是人为干扰导致的产物。当此情况下,要加速类似地带的生态恢复,只有依靠人为的文化干预,在岩缝开口处实施多植物物种混合播种,替代野生的动物完成播种使命,这样的石漠化灾变地带,才可能恢复为原生形态的藤本加丛林复合生态系统。
四、结语
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我们认为要治理麻山地区的石漠化,如下基本认识需要理清。
首先,界定需要治理的生态区,麻山的石漠化灾变显然与现行的水土流失概念无关,但石漠化灾变却最为严重。由于导致石漠化灾变的主因是山体的崩塌,因而应当正确地称之为“山体崩塌类型”的石漠化灾变。从这样的生态背景出发,对该区域内并存民族文化进行全面梳理,寻找这些民族的生态智慧作为利用生态资源和维护生态环境的出发点,来框定相关各民族的生态知识与智慧在有效利用和维护的自然生态系统耦合程度,确立各民族间相互信守的生态利用与保护意象界缘。
其次,在喀斯特山区,其石漠化程度不一,甚至其形成历程也不一致,其表现形态也不尽相同。因此,在制定生态治理目标上也应该是多元的,首先要确认该不同生态位的具体生态复位目标,这一目标一旦确立后,就需要民族学工作者对该区域内相关民族文化事实进行分析研究,寻找其与自然系统耦合的历史过程与表现方式,作为以后制衡格局达成的远景追求目标。
最后,民族学家在通过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从全人类的相关文化事实中制定一系列菜单,向相关各族村民以及科技工作人员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方案。这样的选择方案包括历史上人类曾经使用过的和现代科技正在使用的技术技能,不论是生物资源利用办法,还是生态维护办法,抑或世界各民族利用与维护类似生态环境的传统做法,我们都应该鼓励乡民和科技人员选择试用。
总之,我们认为时下的对喀斯特山区石漠化灾变成因分析的时候,过度地相信自然科学的结论,忽视了社会科学的价值和作用,这就会导致对不同类型的石漠化灾变的成因都会导致理解上的严重曲解,并会干扰这些类型石漠化灾变的治理。我们在麻山20多年的田野实践发现喀斯特山区的“石漠化”从特定意义或是其本质而言是文化所为的结果,是汉族农耕文化在喀斯特山区误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在对该区域生态灾变的治理时,我们也必须惟文化是问。因此,我们认为,只要喀斯特山区石漠化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使该区域的民族文化在其运行中科学地绕开其生态脆弱环节,不对其生态系统造成冲击,该区域的生态恢复就可以实现,而特定文化智慧在对生态资源的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中得到升华。
[收稿日期]2010—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