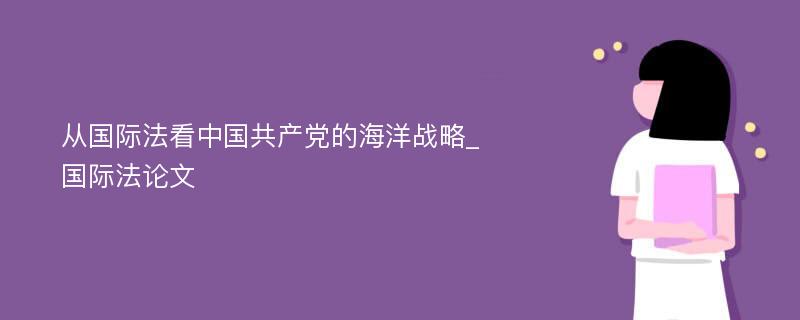
国际法视野下的中共海洋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法论文,中共论文,视野论文,海洋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3)04-0004-10
海洋问题关涉我国的核心利益。建国以来,历代中共领导人领导全国人民,在海洋问题上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斗争。海洋问题首先是战略问题,解决海洋问题应从战略高度加以审视;其次,当今的国际社会是崇尚法律的社会,维护海洋权益应更充分地运用国际法的法理和规则。本文试图在国际法的视野下,从战略的高度对建国以来中共海洋战略的发展进行考察和总结,并为今后我国更好地使用国际法武器维护海洋权益提供参考。
一、建国初期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战略
“战略”(strategy)一词,最早意为对军事斗争全局的策划和指导。近代以来,这个概念被引申至其他领域,泛指统领性的、全局性的、左右胜败的谋略、方案和对策①。本文中的海洋战略,指我国几代领导集体在海洋问题上的决定全局的策略,其内容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外部局势和险恶的海洋安全环境。一方面,朝鲜战争牵制了我国的战略布局,美国第七舰队借机侵入台湾海峡,“使中国的海洋战略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②;另一方面,我国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有损中国主权的在中国领土上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要求,使得我国海军的建设无法寄希望于苏联的帮助③。囿于这种严峻的局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果断采取以反侵略反霸权为中心的海洋战略,有力地行使了国家基本权利,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行使国家基本权利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首先谋划的海洋战略。国家基本权利(fundamental rights)是国家作为国际人格者所固有的、国家不可缺少的生存攸关的权利④。国家基本权利源于国家作为一个国际法实体所具有的性质,“较之习惯和条约创造的实在国际法规则具有更大的拘束力”⑤,是不可剥夺、不可侵犯的。国家的基本权利包括独立权、平等权、自卫权和管辖权。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战略,主要体现在对管辖权和自卫权的行使上。
管辖权(right of jurisdiction)是国家依据主权对特定的人、物、事件进行管理和处置的权利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属地管辖权(territorial jurisdiction),又称属地优越权,即国家对其领土范围内一切不享有特权和豁免权的人、物、事件进行管辖的权利⑦。解放后,西方列强在中国仍然保留着残存势力,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仍未完全改变。因此,我国首先采取行使管辖权的方式,来巩固新中国的独立地位。1949年4月3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要求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海陆空军“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海、领水、领土、领空”⑧。1951年5月26日,根据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驻旅顺口的苏军撤回苏联⑨,自此中国政府收回了外国在中国的驻军权;此外,在海关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要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⑩,建设新的人民海关。1951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正式收回了海关管辖权。
自卫权(right of self-defence)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有“使用它的一切力量从事国防建设的自由”(11);二是对于外来的侵犯,国家有进行抵抗的权利。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陆军部队已初具规模和战斗力,那么当时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则较为弱小。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海军的建设和发展。1951年10月,《中央军委命令》指出:“海防为我国今后主要的国防前线。”次年2月,毛泽东视察海军舰艇部队并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泽东曾指示新中国海军首任司令员肖劲光:“海军应该是一个战略决策机构,是一个军种,应单独成立司令部”(12)。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决定中断对华技术援助,并对我国进行核技术封锁。对此,毛泽东在《赫鲁晓夫访华破坏技术援助后的指示》中指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周恩来也表示:“就是没有裤子穿,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核力量,我们要搞尖端国防。”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高度关心下,从1955年到1960年,由海军东海舰队、海军南海舰队和海军北海舰队组成的中国海军主力三大舰队相继建成,我国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也于1974年下水。中共对海军建设的指导,是我国在海洋问题上行使自卫权的战略体现。
行使领土主权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谋划的另一海洋战略。领土主权(territorial sovereignty),是国家对其领土本身以及领土范围内的人和事物的最高权力,包括平时领土完整和战时不可侵犯(13)。在海洋问题上,我国行使领土主权,从确定我国的领海宽度开始。在联合国于1958年、1960年召开的两次海洋法会议上,与会各国对领海宽度这一议题进行了持续而激烈的争论。出于国防安全和维护自身海洋权益的考虑,发展中国家普遍主张较大的领海宽度。(14)我国于1958年9月4日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首先从国内法的形式确立了行使领土主权的依据。《声明》的主张完全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15)此外,我国还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行使领土主权。1951年8月,周恩来在《关于英美对日和约草案及旧金山会议的声明》中指出:“西沙群岛和南威岛正如整个南沙群岛及中沙群岛、东沙群岛一样,一向为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主权。”1958年10月,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指出:“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并号召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理西太平洋。(16)对于入侵我国领海和领海上空的军舰和飞机,党中央均指示坚决予以还击(17)。1974年1月,中国海军进行了有限的自卫还击,收复了被越军侵占的甘泉、珊瑚和金银三岛并就此声明:“为了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自卫行动。”(18)1988年3月,我国海军在赤瓜礁再次击退越南海军的进犯,捍卫了我国的领土完整。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战略,概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相对于陆地防御,海洋权益与岛屿主权的维护被迫居于次要的地位,海军发展的战略停留在近岸防御的层面上(19);二是以政治、军事的内容为主,几乎没有涉及海洋经济建设的构想。这是由建国初期的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我国海洋力量的客观状况和我国当时的战略任务所共同决定的。不难看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战略,有效地维护了新中国的基本权利和领土主权,完全符合国际法的法理和原则。
二、改革开放后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战略
随着“文革”十年动乱的结束,饱经患难的中国百废待兴。对内改革经济体制,对外经济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为此创造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成为了党和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围绕这个任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宽广务实的胸怀和态度,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国际海洋斗争的成果,提出了新时期的海洋战略。这一时期的战略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在军事上提出了“近海防御”和建设“精干顶用”海军的战略思想;二是在处理海洋争端上提出了“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20)三是经济上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建立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沿海开放格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和海洋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高度、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广度和经济科技因素上升的深度”(21),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海洋战略提出了高度而全面的思考:在对海洋地位的认识上,提出了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在对海洋内涵的理解上,确立了以海洋经济为核心的综合海洋观;在对海洋安全模式的选择上,提出了以合作关系取代“零和”关系的新主张;在对海洋权益维护途径的探索上,提出了综合手段与多种措施并举的方略。(22)
中共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战略,在实践层面具有高度的连续性。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后中共海洋战略的突出特点,体现在海洋争端的解决和海洋经济的开发上,这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密不可分。20世纪60年代末,跌宕起伏的民族解放运动致使国际政治力量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海洋权益的斗争也日趋激烈(23)。在此背景下,联合国于1973年召开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此次会议是“当时国际关系史上会期最长、与会国最多的一次外交会议”(24)。会议于1982年表决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法公约》的诞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懈斗争的成果,本质上是对国际海洋权利格局的再分配,大体上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权益保护。我国一直积极参与《公约》的制定工作,并分别于1982年12月6日和1996年5月15日签署、批准了该公约。(25)
《海洋法公约》的产生,对中共第二、三代领导集体的海洋战略有着借鉴作用:其一,公约从国家管辖的角度,明确了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其二,公约从经济开发的角度,对国家在其管辖范围内外的海域的经济权利进行了列举;其三,公约对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作出了规定。国际海洋争端主要体现在对各类海域的划界问题上。《海洋法公约》对沿海国的领海、群岛水域、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法律制度和界限宽度都进行了概括性的规定,并对相邻国家之间的划界问题从实体法层面进行了规定。比如,对于领海的划界问题,《海洋法公约》规定适用“等距离/特殊情况规则”(26)。然而,实体法层面的解决办法未必能在所有国家之间有效适用。因此,《海洋法公约》又从程序法上予以补充。例如公约第74条第1项规定:“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所指的国际法基础上(27)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在达成协议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做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并在此过渡期间内,不危害或阻碍最后协议的达成。”又如公约第279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三项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之间有关本公约的解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并应以此为目的以《宪章》第三十三条第一项所指的方法求得解决。”(28)
改革开放后中共领导集体在海洋争端解决方面的战略思想,和《海洋法公约》倡导的解决办法相一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坚持主权,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首先是坚持主权。邓小平曾表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29),我国外交部也多次声明:“任何国家未经中国许可进入中国领土从事勘探、开采和其他活动都是非法的,任何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在上述区域进行勘探、开采等活动而签订的协定和合同都是无效的”(30);其次是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关于海洋争端,邓小平认为“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可以在不放弃主权的前提下,“搁置争议,共同开发”(31)。1979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本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1986年6月,菲律宾副总统劳雷尔访华时,邓小平向他提出,“南沙问题可以先搁置一下,先放一放,我们不会让这个问题妨碍与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1988年4月,阿基诺总统访华时,邓小平再次阐述了这一主张:“从两国友好关系出发,这个问题可先搁置一下,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32)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海洋争端解决原则。首先,江泽民提出要以“先易后难,分区解决”的步骤解决海洋争端。他认为,我国和周边国家不仅有岛屿、海域的权属争议,还可能涉及海洋资源利用等各个领域的争议。对于这些争议,应循序渐进加以解决。这在本质上和邓小平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其次,江泽民提出了以合作模式替代“零和”模式的思想。江泽民认为,海洋争端问题不是哪一国家可以单独解决的,必须抛弃冷战时期的“零和”思维,并开展国际合作:“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33)必须以信任取代猜疑,以对话取代对抗,以和谈取代冲突,以互谅互让取代争夺,以人类共同安全取代联盟集团安全。(34)
《海洋法公约》对海洋经济开发作出了多方面的规定。根据《海洋法公约》以及先前制定的《日内瓦海洋法公约》(35),国家在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都有进行海洋经济开发的权利。其中,国家在领海内拥有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专属权利;在专属经济区内拥有勘探、开发、养护、管理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的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在大陆架内拥有开发海床和底土上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36)改革开放后中共第二、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海洋的经济开发。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主要从海洋问题解决的程序层面,就海洋经济开发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为后人的海洋经济开发创设了较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则沿着前人指引的发展道路,开始从实体经济层面引导海洋经济的开发。1994年7月,国家海洋局成立30周年之际,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分别题词道:“管好用好海洋,振兴海洋经济”、“探索海洋奥秘,发展蓝色产业”。1996年10月,江泽民为中国海洋石油工业题词道:“开发蓝色国土,发展海洋石油”。(37)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我国在海洋经济开发方面取得的进步,主要在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开始显现。首先,在共同开发这一程序问题上,我国开始与周边国家达成共识:1995年8月,中菲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在争议解决前为在南沙地区确立行为准则而遵守和平友好解决等八点原则(38);1997年和1998年,我国先后和日本、韩国签订了渔业协定,就东海海域和南黄海海域划界前的渔业活动做出了临时安排(39);2000年12月,中越签订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2001年11月,中国和东盟签订了《南海各方行动宣言》,东盟实际上承认了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其次,在行使开发权利这一实体问题上,我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开始运用国际法对本国海域行使权利:我国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1992年2月颁布)、《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规定》(1993年5月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1998年6月颁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2001年10月颁布);再次,在战略高度上,我国制订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发展规划:我国于1995年制定了以1996年~2020年为规划期的《全国海洋开发规划》,并于次年发表了被称为“第一个海洋发展纲领”的《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1998年,我国发表了《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并于2001年编制了第一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一系列较为密集的由政府发布的法规和规划性文件,表明了我国对海洋经济的开发已经提升到一个战略的高度。正如江泽民所说,“开发和利用海洋,将对我国的长远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40),“我们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海洋,增强全民族的海洋意识”(41)。
三、新世纪中共领导人的海洋战略
进入21世纪,中国的国家力量和周边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的海洋战略,在实践中遇到了挑战和困难。在军事建设上,近海防御已经不能有效地保护我国的海洋利益,“精干顶用”的海军力量也不足以掌控我国周边海域的海权;在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上,单纯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走到了一个瓶颈的阶段,中国海域周边的国家开始不断地蚕食我国海域,挑战我国的领海主权,这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海洋经济建设。
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状,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与时俱进,提出了新的海洋战略,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坚持主权毫不动摇。2012年11月,在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强调:“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42)第二,将海洋战略扩展到远海甚至远洋,建设海洋强国。2008年12月,我国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派遣海军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任务,标志着我国首次将国家力量扩展至远洋。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更表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43)。第三,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2006年12月,胡锦涛在会见海军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时指出:“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在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中,海军的地位重要,使命光荣。要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44)2009年5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60周年之际,时任海军司令员吴胜利、海军政治委员胡彦林也撰文表示“要大力推进建设强大海军的历史进程。”(45)
面对海洋问题等我国周边环境出现的常态化问题,2013年1月28日,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46),首次阐明了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原则底线。习近平从战略的高度指出:“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决不在国家核心利益上退让(47)。习近平的讲话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广泛关注。美国《纽约时报》评论道,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亚洲邻国因海事主权争端导致关系不断紧张”,对此习近平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中国的外交立场,“包括致力于世界和平的承诺,以及对某些要求中国做出让步的警告”(48);英国《金融时报》则指出,“通过添加有关权益和核心利益的表述,习近平似乎在暗示,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强硬的姿态”(49);台湾《联合报》更是坦言:“因和平发展易造成‘西线无战事、捋中国虎须也没关系’的误解,故习(近平)再次明白敬告有所图谋的相关国家,特别是与大陆有领土与领海主权纠纷的周边国家,日后该有所作为,将依法据理绝不隐忍。”(50)国际社会将习近平的战略总结为“刚柔并济,强势而不强硬”。(51)习近平曾有言:“打铁还需自身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52)。在坚定宣示我国战略的同时,新的中共领导集体十分注重军队建设。自从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先后完成了对海陆空、二炮部队和武警部队的视察,体现了中共对新时期军队作用的重视。
新世纪以来,我国周边各国对我国海洋领土主权的挑战和侵犯不断增多,这些争端有的已经超越了局部海洋争端的范畴,演变成为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的全局性的国际争端,比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中菲之间的南海争端(53)。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国际争端(international disputes)产生于当事国在事实、法律或政策等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其中一方提出的主张遭到另一方的拒绝或否定的情形(54)。解决国际争端,有强制与和平的方法(55)。进入新世纪,当前“搁置主权”的原则受到邻海诸国挑衅时,以胡锦涛、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采用了灵活的海洋战略,综合运用强制与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保障我国的权益。
解决国际争端的强制方法与战争不同:“强制方法即使在最坏的情形下,也只限于采取某些伤害性措施”(56)。因此,“虽然强迫解决方法也使用武力,但争端当事国和其他国家不认为其是战争行为,因而一切和平的国家关系保持不变”(57)。强制方法一般有反报、报复、平时封锁和干涉四种。在国际法上,后三种都属于国家不法行为,都受到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禁止,而我国在实践中采用的强制方法,主要是反报。反报(retortion),是一国以同样或类似的行为对另一国采取的不礼貌、不友好或不公平行为作出的反应(58),不是国家不法行为。
新世纪以来,周边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对我国的挑衅愈演愈烈:菲律宾于2009年2月通过所谓“领海基线法案”,将我国黄岩岛等8处岛礁及相关海域划为菲律宾领土;日本则于2012年9月,通过“购岛”方式,将钓鱼岛“国有化”。面对这些挑衅,以胡锦涛、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在海洋问题的国际争端上,逐渐采取了较为强硬的立场,对某些周边国家的不友好、不礼貌行为进行了反报。在钓鱼岛问题上,我国从2012年底开始,向钓鱼岛附近海域派遣海监船、军舰和军机,对钓鱼岛进行巡航;在南海问题上,我国于2012年6月在南海设立三沙市,并派遣军舰赴黄岩岛海域巡逻。此外,我国还适时向外界展示新发展的军事力量:2012年9月25日,我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正式入列服役;2013年1月26日,我国自主发展的大型运输机“运-20”试飞升空;2013年1月27日,我国再次进行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2013年1月31日,我国海军舰艇编队赴西太平洋训练。上述反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威慑对方的作用。我国采取的强制方法,是在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框架下实施的,在本质上是为了制止对方的不礼貌、不友好和不公平的行为,促使对方重新回到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轨道上来。
解决国际争端的和平方法,可以分为政治解决和法律解决两种途径。政治解决方法包括谈判与协商、斡旋与调停以及调查与和解(59);法律解决方法则包括仲裁、司法解决以及在联合国组织主持下解决。(60)以胡锦涛、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灵活运用解决国际争端的和平方法,来处理我国目前面临的海洋问题。
我国采取的政治解决方法主要是通过外交途径,直接谈判,协商解决。谈判(negotiation)与协商(consultation)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为使有关问题得到解决、达成协议或获致谅解而进行国际交涉的方法。其中,直接谈判是争端各国最普遍使用的一种做法(61);协商则是在谈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外交方法。协商不受谈判双方的限制,允许非争端当事方的参加,并且强调和谐友好的气氛和灵活的和解精神(62)。建国以来我国的外交实践直接推动了协商作为外交谈判的特殊形式的适用和发展。在1954年5月12日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首次提出了协商的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63)此后,协商的方式已被成功适用于我国与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国家的问题解决(64)。新世纪以来,我国更加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和平谈判和友好协商。2011年6月26日,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会见越南领导人特使、越南副外长胡春山后,共同表示要“积极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通过谈判与友好协商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海上争议”;2011年6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南海争议是相关当事国之间的事,应由当事国通过直接谈判和友好协商来解决”;2012年9月8日,胡锦涛在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时指出:“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南海问题符合有关国家共同利益”。(65)
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通常包括仲裁(arbitration)与司法解决(judicial settlement)。前者是各当事国将争端交由共同选任的仲裁方处理,并约定服从其裁决的办法;后者是当事国将争端提交给国际法院,由其根据国际法作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判决(66)。此外,在特定领域的国际法公约,也经常规定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比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专门设立了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以解决“具有极高之科学性及技术性”的划界问题(67)。据此,大陆架超出200海里的缔约国必须将本国大陆架界限的有关情报提交该委员会并征求其建议,只有在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划定的大陆架外部界限才具有确定力和拘束力。近年来,我国逐渐主动地使用法律解决方法,来处理国际争端。在东海问题上,我国根据《海洋法公约》、《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议事规则》和《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科学和技术准则》的有关规定,于2012年12月14日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了东海部分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对于该申请,联合国表示将于2013年晚些时候予以审理。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多表明该划界案在实体法的层面具有足够的法律依据(68)。另外,我国对于他国提出的法律解决方法,也应有足够的自信加以应对(69)。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就南海主权与中国的争端提交联合国仲裁,希望以此途径解决两国争端。然而在中国宣布中国渔政船和海监船将继续在黄岩岛进行巡逻和执法之后,菲律宾官员也承认了在实体法层面,“黄岩岛在中国有效控制之下”,因此法律解决方法对菲律宾较为不利(70)。在强制方法辅助与配合之下,我国更多地使用法律解决方法,将更加有利于今后海洋问题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
当然,无论新时期我国采用何种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其根本目的都是要维护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71)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而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维护这个战略机遇期。“战争对于军人来说,是唯一选项;对于国家来说,则是最后选项”(72),我国在海洋问题上的强制解决方法,根本上是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确保我国的战略机遇期,捍卫我国的核心利益。
四、中共海洋战略的发展与国际法的关系
中共的海洋战略与国际法具有紧密的联系。从本质上说,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73),从国际法产生以降,它就为国家处理相互之间的国际关系服务(74)。国际关系的基础是政治关系(75),而决定一国政治关系的便是一国的战略。中共海洋战略与国际法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共海洋战略始终遵守国际法的规范框架。在国际交往中,各国应当遵守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然而在实践中,“发达国家对待国际政治问题,主要是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来考虑”(76),当其感到利益受威胁时,可能“不顾及国际法而去干涉另一国家的内部事务,虽然这并不表明它有权这么做”(77)。而我国的在海洋问题上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行使权利,并恪守不侵犯、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国际法原则,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其二,中共海洋战略积极借助国际法而得到实施。国际法是实施国家战略的重要途径(78)。国家可以援引国际法原则和规则,为自身战略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发展中国家和处于弱势的国家与民族,在现代国际法中所受的保护,“远比以前任何时代更多”(79)。从建国初期的国家基本权利和领土主权的行使,到改革开放后海洋经济开发权的行使,到新世纪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尝试,我国的海洋战略积极通过国际法规范的适用而得到实施。
其三,中共海洋战略的发展推动了当代国际法的发展。综观国际法发展史,从公元前13世纪的埃及与赫梯同盟条约,到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再到20世纪的《巴黎非战公约》和1945年《联合国宪章》,每一个国际法发展标志性事件的背后,都有国际政治和国家战略的身影(80)。国家战略会促进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形成(81)。建国以来我国的海洋战略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国际法的发展。我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在解决陆地领土问题上起到了作用,更为发展中国家所广泛认同,并作为解决海洋争端的原则;我国提出的和平协商的国际交往方式,更补充了当代国际法理论关于解决国际争端的内容。
中共海洋战略的发展历程,是我国国家实力发展成长的缩影。综观建国以来历届中共领导集体的海洋战略,可以看出,其在空间上经历了从近岸、近海,到远海、远洋的发展过程;在内容上经历了从海防建设与主权维护,到发展海洋经济和拓展国家利益的发展过程;在手段上经历了从军事手段,到军事与政治、法律手段并举的发展过程。其在总体上是逐渐扩展、丰富,并不断升华的。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中共海洋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建国初期,中共的海洋战略侧重于国家自卫权、管辖权和领海主权的行使;改革开放后,则转向了搁置争端,并开发海洋经济;新世纪以来,则注重于综合运用强制与和平的手段,来维护我国的主权。可以肯定的是,建国以来中共的海洋战略,都是在国际法的框架内实施的,都在有形与无形之中借助着国际法的法理与规则而得到实施,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代国际法的发展。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453页。
②刘中民、桑红:《新中国海洋防卫思想史话之防御下的强大——第一代海洋防卫思想》,《海洋世界》2007年第1期,第54页。
③参见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386页。
④邵津:《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⑤[美]汉斯·凯尔森:《国际法原理》,王铁崖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5页。
⑥[英]J.G.斯塔克:《国际法导论》,赵维田译,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198页。
⑦属地管辖权古已有之。在近代国际法传入中国的时期,其被称为“内治之权”。参见[美]惠顿:《万国公法》,[美]丁韪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88页。
⑧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页。
⑨王历荣:《建国后毛泽东的海权思想与实践》,《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1页。
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4页。
(11)周鲠生:《国际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95~196页。
(12)肖劲光:《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13)白桂梅:《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页;邵津:《国际法》,第99页;[英]J.G.斯塔克:《国际法导论》,赵维田译,第139页。
(14)马呈元:《国际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8页。
(15)王铁崖:《在海洋法研究所第十六届会议午餐会上的讲话》,《王铁崖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35页。
(16)吴士存:《南海问题文献汇编》,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0页;《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页。
(17)毛泽东:《坚决打击入侵海南岛上空的美机》(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3页。
(1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人民日报》1974年1月21日,第1版。
(19)王历荣:《建国后毛泽东的海权思想与实践》,《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63~64页。
(20)孙立新、赵光强:《中国海洋观的历史变迁》,《理论学刊》2012年第1期,第95页。
(21)刘永路、徐绿山:《从“零和对抗”到“合作共赢”——中国特色海洋安全观的历史演进》,《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128页。
(22)刘永路:《江泽民新海洋安全观的理论新贡献》,《政工学刊》2006年第2期,第14~15页。
(23)赵理海:《海洋法的新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3~76页。
(24)会议于1973年12月召开,于1982年12月结束,共举行了11期会议,会议总天数达585天。共有167个国家以及作为观察员的50多个非独立领土、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见马呈元:《国际法》,第123页。
(25)在国际法上,签署和批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签署(signature)是在条约谈判结束时认证约文的方式,仅在某些只需签署即表示受约束的条约中具有拘束力;批准(ratification)是国家权力机关对其谈判代表所签署的条约的认可,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的行为。国家可以通过批准程序,对条约进行全面审查,并为制定必要的国内法提供时间。参见[英]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曾令良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73~674页。
(26)在此规则下,相邻或相向两国中任何一国都无权将其领海延伸至一条两国领海基线之间的中间线以外,但如因历史性所有权或其他特殊情况,可不适用上述规定。参见[苏]苏联科学院国家和法研究所海洋法研究室编:《现代国际海洋法——世家海洋的水域和海底制度》,吴云琪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7~304页。
(27)《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规定国际法的渊源包括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和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可以作为确定一般法律原则的辅助资料;“公允及善良”原则可作为国际法院裁判依据。参见王铁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28)《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3项规定:“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宪章》第33条第1款规定:“任何争端之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判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办法,求得解决”。See Tim Hiller,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Carvendish Publishing Ltd.,p.229(1999).
(29)邓小平:《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5页。
(30)杨金森、高之国:《亚太地区的海洋政策》,海洋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页。
(31)邓小平:《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0页。
(3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搁置主权,共同开发》,2000年11月7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iliao_611306/wjs_611318/t8958.shtml。
(33)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二○○○年九月六日),《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
(34)江泽民:《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35)1958年4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海洋法会议上制定了4个公约:《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大陆架公约》和《捕鱼与养护公海生物资源公约》,合称《日内瓦海洋法公约》。参见马呈元:《国际法》,第123页。
(36)See Mark W.Janis,A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Citic Publishing House,p.221(2003).
(37)李明春:《海权论衡》,海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163页。
(38)唐家璇:《中国外交辞典》,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751页。
(39)万霞、宋冬:《争议海域的共同开发制度——从邓小平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外交思想说开去》,《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6期,第36页。
(40)章示平:《中国海权》,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41)吴纯光:《太平洋上的较量——当代中国的海洋战略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4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二○一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页。
(4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二○一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36~37页。
(44)参见新浪网:《胡锦涛:锻造适应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民海军》,2006年12月27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06-12-27/1814422755.html。
(45)吴胜利、胡彦林:《锻造适应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的强大人民海军》,《求是》2007年第14期,第33页。
(46)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2013年1月29日,第4版。
(47)《习近平首谈战略定力不寻常 新国际观渐显》,《文汇报》2013年1月30日,第6版。
(48)See Chris Buckley,China Leader Affirms Policy On Islands,New York Times,January 30,2013.
(49)See Jamil Anderlini,Xi Strikes Strident Tone On Foreign Policy,Financial Times,January 29,2013.
(50)《昭告世界和平与利益都不放弃》,《联合报》2013年1月30日。
(51)《强势不强硬习近平外交策略》,《香港经济日报》2013年1月30日。
(52)《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共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出台一月综述》,《人民日报》2013年1月5日,第4版;《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复兴之路的启示之四》,《人民日报》2012年12月4日,第1版。
(53)See Lee Joyman,Islands of Conflict,History Today,May2011,Vol.61,Issue 5.
(54)See J.G.Merrills,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3r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1998).
(55)周鲠生:《国际法》,第757页。
(56)[德]奥本海:《奥本海国际法》下卷,第二分册,王铁崖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93页。
(57)邵津:《国际法》,第411页。
(58)王铁崖:《国际法》,第454页。
(59)白桂梅:《国际法》,第525~527页。
(60)[英]J.G.斯塔克:《国际法导论》,赵维田译,第390页。
(61)参见[德]奥本海:《奥本海国际法》下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第3页;[苏]Ф·И·科热夫尼科夫主编:《国际法》,刘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74页。
(62)马呈元:《国际法》,第322页。
(63)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发言》(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二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62页。
(64)周鲠生:《国际法》,第760~761页。
(65)参见新浪网:《中越称将通过谈判与友好协商和平解决海上争议》,2011年6月27日,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627/160010053873.shtml;新华网:《外交部: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解决南海争议》,2011年6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6/28/c_121597109.html;人民网:《胡锦涛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2012年9月9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2/0909/c1024-18956399.html。
(66)参见[英]伊恩·布朗利:《国际公法原理》,第781~783页。
(67)傅崐成:《海洋法专题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285页。
(68)参见张新军:《权利对抗构造中的争端——东海大陆架法律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124页;See Zhongqi Pan,Sino-Japanese Dispute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The Pending Controversy from the Chinese Perspective,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12,No.1,2007,p.80-83; Ivy Lee & Fang Ming,Deconstructing Japan's Claim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The Asia-Pacific Journal,Vol 10,Issue 53,No.1,December 31,2012; Gavan McCormack,Small Islands-Big Problem:Senkaku/Diaoyu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and Geography in China-Japan Relations,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 9,Issue 1 No.1,January 3,2011.
(69)See Kimie Hara,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nd Frontier Problems in the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A Sixty Year Perspective,The Asia-Pacific Journal,Vol 10,Issue 17,No.1,July 7,2012.
(70)参见凤凰网:《菲律宾称已将中国“告上”联合国要求修改南海九段线》,2013年1月23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nanhailingtuzhengduan/detail_2013_01/23/21483004_0.shtml;凤凰网:《菲高官承认中国已有效控制黄岩岛 菲再也不能进驻》,2013年1月21日,http://news.ifeng.com/mainland/pecial/nanhaizhengduan/content-3/detail_2013_01/21/21417876_0.shtml。
(7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二○一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5页。
(72)刘源:《确保战略机遇期,战争是最后选项》,《环球时报》2013年2月4日,第14版。
(73)See Black's Law Dictionary,West Publishing Co.,p.816(1990).
(73)周鲠生:《国际法》,第8页。
(74)张乃根:《国际法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76)杨泽伟:《国际法析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77)[美]W.迈克尔·赖斯曼著,万鄂湘等主编:《国际法:领悟与构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78)刘志云:《当代国际法的发展:一种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的分析》,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79)杨泽伟:《国际法析论》,第13页。
(80)参见[苏]Ф·И·科热夫尼科夫主编:《国际法》,刘莎等译,第1~4页;[德]奥本海:《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王铁崖等译,第58~61页;白桂梅:《国际法》,第9~14页。
(81)[美]路易斯·亨金:《国际法:政治与价值》,张乃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