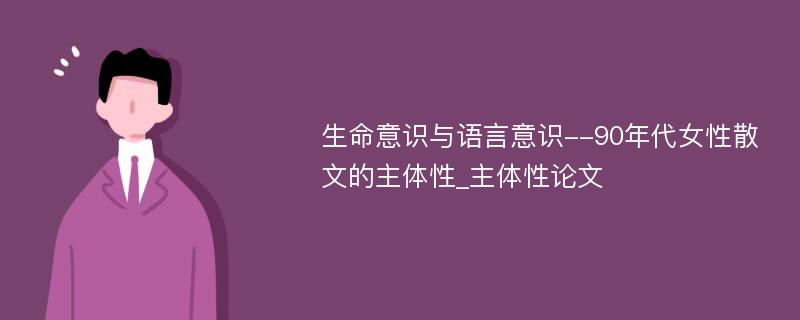
生命与语言的自觉——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中的主体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问题论文,散文论文,主体论文,自觉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4—0088—07
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汇集了从世纪初出生的世纪老人直到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整整四代女人的散文,作者人数与作品之多,为20世纪其他任何年代所未见,也是同时期的女性小说、女性诗歌所未有。① 本文尝试着以生命与语言的自觉为起点,从大量女性散文文本中发现思想,并用思想阐释文本,抓住“主体性”这个思想理论的生长点,将女性主体性问题放在生命哲学的理论框架和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一次初步的理论的梳理与整合。
生命、语言、主体言说
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中,不止一代人写到了对衰老与死亡的直接面对。这是生命中最后的两个阶段,衰老意味着死亡的临近,而死亡意味着生命的消失。对衰老与死亡的恐惧与直面,成为生命意识觉醒的起点,这也就是哲人所说的向死而生的意志和决断,“是创造性的和自觉生命的一个有益的瞬间”。[1]172 正是在这样的“瞬间”里,女人鼓起勇气克服对死亡的恐惧,直面自己这只有一次的生命的每一天,珍惜筹划自己的生存,在普遍的死亡结局面前创造自己生的意义和价值,意识到普遍的死,是拥有一个创造性的有意义的生的前提。对死亡的自觉意识,是一种生存的勇气和智慧,而对死亡的无知无觉便是对生的无知无觉,是一种生命的混沌和蒙昧。因此正是死亡意识导向了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成熟。一个世纪以来女性文学中对“我是谁,我向哪里去”的追问和对主体性的探寻和建构,便有了沉甸甸的生命价值论和生存论的分量。
黄宗英的《上了年纪的禅思》和张晓风的《近照及其他》,捕捉的正是这样一个“自觉生命的有益的瞬间”。60多岁的黄宗英意识到自己“上了年纪”就要“做一点‘上了年纪’该做的事儿”。[2]25 张晓风从一张应牙医要求所拍的自己的X光侧面头像,看到了自己生命的结局:和天下所有众生“同其形的枯骨”。这个众生平等的,也是无情的生命的终点,对于还活着的“我”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对“我是谁,谁是我”这个生命意义的追问,由于“死亡”的提醒而导向了积极的对生的意义的承担。这样的向死而生的追问,便是一种直面死亡而生出的强烈的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价值诉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人人都会经历的生老病死为经验内容的“生命哲学是对主体性或自我经验这个话题所做的重要的贡献”。这是因为生命哲学“服从一个简单的观点,即我们所拥有的生命是唯一的一次”。[1]2
她们在这一生命结局的背景下为自己找到了生的价值:“也许,真正能留住我容颜的,是这些美丽的方块字的魂魄吧!”[2]81 这就涉及到生命与语言文字的关联,生命的自觉与语言的自觉的关联。
生命哲学认为,生命本身就具有语言性,或者说,生命要求语言,语言来自生命。“现象学对生命哲学的所有回答都是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语言。因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以一种符合现代理性的方式来澄明生命哲学的直观性。”[1]191 生命在语言中敞开,语言使生命得到澄明。“生命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进入语言而塑造自我。这是因为在生命与语言之间,在感情世界和文字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关联”[1]191,因而生命意识的自觉必然导向语言意识的自觉。生命的无意识也就是语言的无意识。这也是90年代四代女作家在女性散文中表达的共识。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存在以语言之家为家”,表达了女作家对语言的贴己的亲切温暖的感觉。“语言是一种神迹……它如日月之光给予我生命的抚慰”。[2]269 林白则把她的写作看做是让生命作为语言的翅膀飞翔,语言唤醒了她生命的想象力和身体语言。②
语言与生命的另一面是遮蔽、是牢笼、是窒息、是欺骗、是暴力,尤其是当语言与政治强权相结合的时候,语言便是一种“巫术”。识破语言的这一面同样需要生命与语言的自觉,需要作为言说主体的独立的思想和生命的良知。王小妮在《遍地天使》中说“语词”是一个“无法加锁的工具库,比路边任何一个‘便民箱’还容易打开”,“我曾经一次次为语言的遍地行骗而惊讶”。[2]354—355 筱敏在《语言巫术》中以敏锐犀利的语言批判了法西斯政权的“语言的暴力”,认为这是一种摧残人的心智和灵魂、剥夺人的独立人格和尊严的“巫术”。“一套一套装备完好的语言网一样张开,守候在所有日常生活的过道上,随时随地向你喷射而来,随时随地切断你思维的线索。不断地切割,使你的大脑不再能生长一株你自体的思想的胚芽”。“在我们生存的世界到处存在着蜕去生命的语言硬壳”。[2]309—310 小宛《月正中天》、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写的“父亲”和“母亲”,就是被这样的脱离人的真实生命经验的“语言的巫术”所击中,被这样的“语言的硬壳”所囚禁,最终又被这样的语言所驯化,完全失去了人的主体性的可怕而又可怜的政治僵尸。他们发射出一粒粒“语言的子弹”,从中收获一点虚幻的、可怜的革命道德满足感和政治成就感。于是,语言成了他们“躯体的形状”,他们成了徒有其表的“语言的空壳”。
筱敏分析“语言巫术”的尖锐性在于,她以自己的主体性言说,看到了人被语言操纵的危险后果,便是生命的异化,是人被占有、被奴役和人不成其为人。看到并说出这一点需要生命与语言的自觉,需要对语言欺骗性的洞察,需要由此而来的对自由的渴望,需要生存的勇气和智慧。90年代女性散文在这方面所达到的思想的高度与深度,不仅标志着一个世纪以来女性以主体性言说反抗失语,反抗被言说、被塑造,自我言说、自我创造的艰难历程,已达到了一个时代所能够达到的高度,而且在思想的敏锐度和深度上远远超过了同时代那些男性散文家的散文。遗憾的是女性散文的这些从来也不事张扬的空谷足音,至今未能被当今思想界与当代文学研究界所发现、所理解。
父权制·他者·偶像
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由生命与语言的自觉而达到的主体性言说,对于女性命运和女性文学来说都是划时代和破天荒的事。这件事在中国发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的发现与女性的发现,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曲折历程之后,终于在90年代女性散文中达到了思想理论上的成熟。这是一个与20世纪中国历史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社会现代性与人的现代性同命运和相始终的历史进程,而这里的“传统”也就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概括与确证的,以人对人和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占有为特征的等级制的统治秩序。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根据《左传》中“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所阐释的人与人、男人与女人的统治关系,道出了父权制统治秩序的秘密,即男人与男人间、男人与女人间等级制的人伦秩序,是以家庭中男女性别统治为起点和基础建立起来却又不止于性别统治,所谓夫为妻纲、君为臣纲,男性的君与臣及臣与臣之间,也是等级森严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崔卫平的《宦官制度、中国男性主体性和女性解放》论述了“阉割”这一父权制剥夺男性性权利的制度性、结构性举措,对男性人格与精神的无形阉割造成了男性主体的消失,只是在人与人和男人与男人一级压一级的关系中,被压在最底层的是比所有男人更卑、更弱的女人而已。林丹娅《遥望祖母之名》以对祖母的怀念,道出了妇女在父权等级制结构中,无名无语的一生。祖母在世时,祖父叫她“咳”或者“窑下”,街坊邻居们叫她“窑下婶”,孩子们叫她“窑下婆”,死后墓碑上刻着“林氏窑下之墓”。“窑下”是一个地名,取代了所有从这里嫁出去的女人的称呼。她们成为“无名的一族”。这也正是女性在父权制的群体性、结构性命运。她们没有自己的名字,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没有言说自己的话语权。女性由被言说到作为言说主体这一历史性巨变,发生在父权制统治秩序出现变裂,而女人对自己被占有、被言说的依附性、被动性地位有所觉醒,并力求摆脱这一地位而由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历史进程之中。在这个历史进程之前或之外,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没有真正的主体性可言。
据研究主体性哲学的学者考察,“主体性”、“自我”这两个概念出现于近代,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萌发于14—16世纪欧洲以“人的发现”为特征的文艺复兴运动,而文艺复兴运动就其思想实质而言,属于以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独立和自由为特征的人文主义思想。人意识到自己生命价值此岸生存的不可替代性,也就同时意识到外在于自己生命、凌驾于自我生命之上的种种“绝对理念”的不合理性,主体意识与自我意识,就这样从严密的父权等级秩序的硬壳中破土而出了。自我意识是个人主体性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个人还没有真正分化出来的早期人类群体中,没有个人主体,也就没有自我、没有自我意识。只是有了从群体中分化出来的个人主体,个人对他人来言才成为自我。这说明主体意识与自我意识,都是在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中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中形成的,二者在语言中可以互相说明与互相通假。“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即主体,必须是在人对自己的主体身份有了自我意识的时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主体不可能是真正的主体”。主体与“自由”“独立”“民主”等亦如是。“自由这个概念,当它意味着人的主体状态时,其实就是指人的主体性,自由的人即具有主体性的人”;“自由其实是主体的同义词,自由主义者不过是以理论方式表达的个人主体性”。[3]32 没有主体性的人便没有自由,以及与自由相关的独立、平等可言。人只有成为主体才可能是自由的。所以所谓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自由、能动和创造的特性”。[3]30—31 卢梭所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而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句话的第一个分句应理解为自由的潜在性,由潜在的自由转变为现实的自由,是一个主体性的人对自己生而为人的权利的争取,也是从种种“枷锁”中突围而出、用个人的主体性活动创造自己的人生价值的人,即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人”。这是人的主体性交响乐中最激昂、最美妙、最动人心魄的乐章。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体性不是历史进步对女性的慷慨赐予,而是女性在历史进步中吸取的对独立、自由的渴望和用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选择与承担,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生成、建构的过程。
“主体”、“自我”都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现的,这是因为人的世界是一个人与人“共在”的世界,“此在本质上是共在”。女性主体性的生成与建构过程,应该历史地放在从父权制人与人关系的转变过程来看,这个转变过程,正是从被统治的依附性的“他者”身份到“主体”身份的转变。关于“他者”,这个与“主体”相对而言的重要概念,目前还用得比较混乱。“他者”不等于“他人”,“他者”是“非主体”,作为他者的人只有摆脱“他者”地位才能成为“主体”。这一点,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译者陶铁柱纠正了萨特的名言“他人即地狱”的错译,应译为“他者即地狱”,并辨析了“他者”(the Other)的真正含义,即“是指那些没有或丧失了自我意识,处在他人或环境支配下,完全处于客体地位、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他者即地狱”是指“一个人如果丧失了主观意志,任凭他人与环境,及异化了的自我摆弄,就等于走进了地狱”。[4]5 这里的解释仍有不准确之处,从前述“主体”与“自我”的关系来看,“失去了主观人格的被异化了的人”,应为“失去了主体人格的被异化的人”;“丧失了主观意志”应为“丧失了主体意志”;“异化了的自我”应为“异化了的人”。因为被异化了的人已不成其为“自我”。这样的如同生活在地狱中的“他者”,正是父权制中处于被统治、被奴役、被剥夺了生命主体性的大多数男人和作为一个性别整体的一个个女人。鲁迅在《伤逝》里代子君说出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之所以石破天惊,正是因为他说出了五四时期知识女性的自我意识与主体意识。
女性主体性成长中,最难的是以爱情婚姻为关联的两性关系中的主体性。这是因为几千年制度性的男主女从、男尊女卑,已经内化和驯化到女人心理的深层,成为她们很难摆脱的性别集体无意识。男性成为她们心中一个庞大的阴影,同时也是一个高大的偶像,体现在爱情婚姻中,便是一种偶像崇拜式的爱。蝌蚪的《家·夜·太阳》、张玲的《偶像》写的都是自己的偶像崇拜式的爱情婚姻的破灭,区别只是前者至死仍在这样的爱中徘徊流连,后者已从这种爱的“创伤性经验”中醒悟但为时已晚。人的有限性是生命的普遍定律,无论女人或男人。把自己所爱的男人当作偶像崇拜,这本身就反射出女人还没有长大,反射出自己的矮小和愚昧。偶像的“伟大”、“英明”是因为人还跪着,正是女人的自我贬抑、甘愿为奴为仆制造了以男人为偶像的神话。发生于1993年10月8日的顾城杀妻并自杀案,见诸报端的种种议论,完全无视被损害、被剥夺了生的权利的女人谢烨的主体性人格,甚至把她的惨死说成是“凄艳绝美,万古流芳”。文昕的《最后的顾城》,甚至颠倒是非认为以顾城为中心的两个女性谢烨、咪儿两星捧月式的“天国花园”的倒塌,是因为两个女性背叛了“孩子般纯洁的顾城”。
在众多议论中,唯有赵玫的《女人·诗·仇恨》和蒋丽萍的《谢烨之死》,以清醒的女人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为谢烨鸣不平:“谢烨作为女人为什么不能反抗?”“谢烨她自己呢?她的独立人格呢?”[2]343“报章上满是对失去一个朦胧诗人的婉惜”,“而谢烨呢?一个被野蛮地夺去了生命的女子,似乎就只能成为顾城的最后一首‘绝美诗’中的一个符号”。[2]300 顾城案启示我们,一个被作为“偶像”崇拜的男子,他的统治欲、占有欲会恶性膨胀到什么程度!男性人性中的自私、专横、暴力倾向的无节制发展,使他根本无视曾经爱他的女性对自己命运的自主性、主体性选择的权利,而把她作为背叛他的“他者”而残忍地剥夺了她要求生命的权利。波伏娃也分析过女人要改变自己“他者”处境“在依附的地位上恢复独立的要求”的天然合理性,“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个主体自我的基本抱负都同强制性处境相冲突,因为每个主体都认为自我(self)是主要者,而处境却让她成为次要者”。[4]25—26 文昕文中所说的谢烨对顾城的“背叛”,不过是一个意识到自己的“他者即地狱”的处境的女子对选择新的生活权利、爱的权利的争取。而自由就是选择,剥夺了她的选择权利也就是剥夺了她的自由、她的主体性。然而她面前自由选择的路被顾城给彻底封锁和粉碎了。这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争取自我主体性的悲剧。
谢烨之死以最为残酷和极端的形式,昭示出女人由父权等级制两性关系的“他者”成长为主体的艰难。《最后的顾城》的作者虽身为女性,却在顾城已经暴露出其自私凶残的暴君式真面目之后,仍然于偶像崇拜的迷宫里痴迷不返,说明性别为女的人并不具备主体成长的天然的优先性和必然性,也说明作为个人的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差异,并不亚于作为个人的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差异。倒是从激流岛噩梦中惊醒并毅然抽身而去的咪(英儿,后以麦琪笔名写作),在经过多年的自我疗救、自我启蒙之后,成长为一个经济上与精神上独立自主的女人。她曾经与谢烨一样把顾城作为偶像(领路人)崇拜,但谢烨永远失却了说出她的醒悟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麦琪比谢烨幸运。
代·个人·他我
女性生命与语言的自觉,是以时间意识为起点的。生命时间的一次性与普遍的逝而不返,使女人对时间有一种如刀如剑的感觉。然而,作为生命的孕育者与抚养者的真切温馨的生命经验,又使她超越了时间的空幻感和虚无感,导向了呵护珍惜生命、肯定人的此在生存、认同女性家庭角色价值的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这个意义上,我用“代”这一概念来阐释女性的主体意识。“代”包括历时态的代际关系与共时态的代属关系,是一个人与人生命时间相互关联的时空范畴。在“代”的范畴里,彰显出具体的一代又一代人,此在生命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的过程。成为在“代”的范畴里生存的女人(家庭角色为女儿、妻子、母亲、外婆或奶奶的递进),可以直观性体验与领悟到贴己的生命时间之流,并在这样的时间之流中肯定自我的生存位置与对生命的责任与承担。母亲的宽厚与博大,正是在“代”的范畴里获得了永恒的价值。在“代”的接续与共在的结构里成为女人亲历过的时间之镜与生命之鉴。社会学家把“代”比喻为“社会岩层”,它同时也是“家庭岩层”、“代”便是岁月在女人生命流程上雕刻出来的刻度,女人凭借“代”的提醒和感悟,无师自通地领悟并承担自己对前辈母亲/父亲与同辈兄弟/姐妹,后辈子/女及外孙/孙女的爱和责任。周小娅的《岁月如圆》、蒋子丹的《岁月之约》、林丹娅的《心念到永远》等,表述的以女儿/母亲双重“代”身份出现的“代”的自觉,便是女性在“代”的范畴中认同生命的缘份和生命的契约,逝而不返的时间流程在“代”的递进、交接中转换成女性对家庭角色的自觉承担。
家庭不是社会历史的绝缘体。相反,作为社会历史的最基本的单元,家庭与社会历史存在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父权等级制社会结构有所松动,女人有了外出求学、求职的机会,有了家庭角色之外的社会角色,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的知识女性大批出现,为女性主体性的成长提供了历史基础。90年代女性散文中表现出来的四代女人的主体性追求,不仅完全超越了传统的、依附性的贤妻良母,而且也结束了五四时代与80年代“做人”还是“做女人”的二律背反怪圈,自觉潇洒地认同与承担家庭角色,同时在社会角色的认同与承担中,表现出相当普遍的出自自我生命体验的对社会历史的独立思考和对超越民族国家的人类命运的关注。30年代出生的戴厚英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中,反思了青年时代受到红色恐怖的“洗礼”,意识到自己因恐怖而驯从,因驯从而认同了“驯服工具”、“齿轮和螺丝钉”的命名。正是对自己这样的社会角色的反思,她渐渐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善正在被恐惧和野心压缩,恶却慢慢膨胀起来”,意识到“如果这就是阶级斗争,我以后再也不参加阶级斗争了”。她从残酷的政治权力斗争的历史长河中抽身而出,再也不做一颗被抛来抛去的“石子”,这是告别依附性工具性的生存,自己创造、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性生成的前提,也是女性拥有独立的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前提。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女性散文四代女作家,在20世纪末这同一时间平面上,通过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与生命感悟,同时拥有了这个作为一个独立的和完整的主体性女人的前提或日起点。
从这条“历史长河”中抽离出来的女人是什么呢?她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个人”和“女人”这两个命名,也就是作为女人的个人和作为个人的女人。她们既认同“女人”这个性别又认同“个人”这个身份,性别意识与个人意识不再相互对立排斥而成为“代”的范畴中女性生命意识土壤中开出的并蒂莲,由五四时期“为人和为女的双重自觉”递进到“为女和为个人”的双重自觉。这是女性文学一百年以来关于人是什么和我是谁的追问的一个大幅度跨越。筱敏的《血脉的回想》,就是在三代女人(外祖母、母亲、女儿——即隐含作者“我”)的历史比较中,突出了自己作为个人的独立选择。在“代”这个很容易无视或抹杀女人个人的独立与尊严的范畴里,强调了女人“独立成株”的主体性诉求。外祖母是一个勤劳勇敢的女人,然而她辛劳一生不过是无数代女人不能更改的命运的又一次重复。她“生前与身后的梦中都空无一物,然后就这样空无一物地被埋葬了,成为囚禁她一生的墓园中一抔同质的沙土。”母亲虽然念书求学成为穿上了双排钮扣的站在革命队伍里的知识女性,可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却“只学会了忠诚和服从,学会了融入大众,学会了删除自己”,从而丧失了对自己、对社会、对历史独立思考的能力。对外祖母与母亲的这种深刻的理解,成为筱敏为自己预设的超越祖辈、母辈的起点。这就是要以“独立成株”的形象挺立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拒绝。拒绝千百年来女人“代”的重复或轮回,拒绝被任何“虚幻的集体”所吞没所遮蔽,选择独立和自由,选择有性别而又超性别的作为人和女人的“个人”。筱敏的“独立成株”这个意象,代表了90年代女性散文中四代女人主体精神之旅壮丽的飞翔,飞翔到以自由、独立为价值理念的人文主义思想的高度,也是安然的降落,降落到以人之为人价值支点的个人生命存在的大地。
主体性哲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主体的个人与他人的关系问题。西方主体性哲学正是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经历了从认识论的主体论到本体论的主体论的转变,从而超越了最初的“唯我论”局限进入了“主体间性”哲学。如前所述,主体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产生的,这就会出现对他人主体性的排斥和盲视,就会遇到他人不是客体,他人也不会永远安于“他者”地位的困窘。所以,波伏娃把“唯我论”的主体性称作“帝国主义意识”。胡塞尔的“主体间性”这个概念,从理论上走出了唯我论的主体性,而把自我与他人都看做是主体。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所以“主体间性”又译作“互主体性”或“主体际性”,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互尊重、理解的关系。这是因为人与人组成的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共在”而不可能是“独在”的,从生命哲学来看,便是生命与生命的相关性,“我”与“你”与“他”“她”的相关性。“处于主体与主体关系中的人的存在是自我与他人的共同存在,人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独在。正如黑格尔所说,不同他人发生关系联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3]237 由此,我们把主体间性中的“他人”称作“他我”。在生命价值论层面上看,与主体性的“自我”相对而言的不是“他人”,更不是“他者”而是“他我”。所以,主体性哲学仅有主体性而没有主体间性是不完整的。这个道理对于以生命与语言的自觉为起点和以生命经验为基础的女性散文作家来说,并非一种逻辑推理而是一种生存的体验与智慧,是她们为人处世、安身立命的原则,是推己及人对他人命运遭遇的将心比心,感同身受。王小妮《目击疼痛》记述的全是60到90年代自己在不同时间、地点所目击的庸常百姓的生存之痛,“疼痛”既是目击的宾语又是省略主语“我”的谓语。这种独特的构词方式,准确地表达了目击者与被目击者生命疼痛的息息相通,是生命与生命相关性而出现的心理痛感的通感结构。周小娅《挨着打工妹汗粘粘的手臂》写的是“我”与打工妹们相遇在车间楼道里手臂挨着手臂的感觉,“打工妹们热乎乎粘腻腻的手臂”,使她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血汗钱”这个词的分量。由此主体对主体的尊重理解和主体与主体间天然的相通相联,只有“他我”这个词才能胜任。
90年代女性散文中与“主体间性”相关连的“他我”这个概念,还表现在女性散文作家在承担“作家”这一社会角色时,对关乎人类命运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的勇气,也就是把这些问题看做是“自我”和“他我”,本民族与全世界全人类命运攸关的问题来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南京大屠杀、“文革”十年等全人类的大劫难进入她们的视野,她们思想的触角,已经伸展到世界范围内,主宰了20世纪历史的几个宏大话语,如“革命”、“群众”、“阶级斗争”、“暴力”等曾经是不容置疑的未经深思也不容你深思的“绝对理念”。筱敏的《群众汪洋》、《成人礼》、《两个女性》,龙应台的《小城思索》、《巨人之死》,斯妤的《真实梦境》,崔卫平的《宋江为什么要杀阎婆惜》、《幽深的没有阳光的日子》等,其犀利的思想锋芒,已经穿越了20世纪而指向了21世纪人类思想的盲区,指向了人类在新的世纪里战胜暴力、战胜恐怖,战胜种种狭隘种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斗争。
费迪南·费尔曼在他的《生命哲学》首页上,引用了一位智者的话:“我在。但我没有我。所以我们生成着。”第一句的“我在”指的是人的生物性与“他者”性的非主体的也就是非人的“在”,是自我消遁的没有“我”的在。而由这样的“在”到真正的主体性“在”是一个生成的而且是艰难的和非必然性的生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被看做是近代主体性哲学先声的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以同时说成是“我思我说故我在”或“我在我思故我说”。这也是中国90年女性散文主体性问题对我们的启示。西方后现代者们“消解主体”,认为“所谓的主体性只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种虚构而已”,“事实上真正的主体并不存在”,现在是“主体性的黄昏”。我国的“后现代”们亦步亦趋在90年代也曾刮起“消解主体”、“批判启蒙”之风,把正在生成中的“主体性”、“人文主义启蒙话语”看做是“霸权话语”、“声名狼藉”等等。笔者坚信90年代这新旧世纪之交是女性“主体性的黎明”。
收稿日期:2007—05—1O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052JZD00030)。
注释:
①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1999年出版的女性散文集有400多本,女作者约200余人;仅《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选读》中入选的人以年龄顺序排列,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的苏雪林到70年代初出生的周晓枫共126位。
②参见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置身于语言之中》、《语词:以血代墨》、《空中的碎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