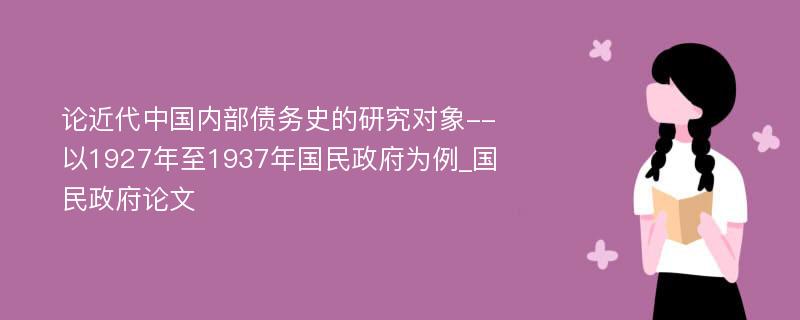
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以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债论文,刍议论文,国民政府论文,为例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的内债,是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问题。绝大部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教材和作为断代史的中华民国史著作,以及相关时段的经济史、财政史、金融史教材、著作,都涉及内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还做了专题性述评。但是对近代中国内债问题做整体性观照的成果,仅有千家驹主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中华书局1984年1月新版),其中的“代序”《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一文,另刊于《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又以《论旧中国的公债发行及其经济影响》为题,发表于《文史哲》1983年第6期。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以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材和专著问世。不过,近年来旧中国内债史资料已有较多刊布,如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的有关财政经济分册里,以及若干金融机构资料集里,都可以较方便地查到(注:这方面的资料集见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1912-1949》(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交通银行史料第一卷1907-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上海市档案馆编《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些档案部门已对馆藏史料进一步整理开放。在阅读了上述著述和资料文献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关于内债史研究对象的若干思考,以就教于学界同仁。由于旧中国政府举借的内债债项甚多,情况不尽相同,本文以1927-1937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举借的内债为例进行讨论。这不仅在于资料颇为集中,而且相关的研究成果也较丰富,笔者的探讨可以有明确的比照。
一、内债与公债
千家驹《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一文,把研究对象概括为“旧中国发行公债的历史过程和它的影响”。在《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的附录统计表中,有债券名称、发行定额、实发行额、担保品、利率等要件。从该《资料》所收入的大部分公债库券条例中,还可以看到关于发行主体、票券面额、是否折扣、是否记名、还本付息日期、清偿期限、票券其他功能等要件,以及关于票券发行机关、还付付息经理机关、基金保管机构的规定。这些当然都属于研究对象。附录统计表的最后一栏“其他”,给出了某些债款要件改变的情况,提示内债关系本身是一个过程。近年来关于内债整理的成果问世(注:参见王晶《1932年的公债风潮:国民政府与上海金融界关系述评》,《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表明已有研究者关注内债关系的延续性和阶段性,把与债项各要件有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的内债风潮和理债问题列入研究范围。
研究内债史往往要对许多债项进行梳理和统计,得出相关结论。但是如果未关注某些性质不同的债项,或者将这些债项混同于常规债项,得出的结论就可能是不周全的,可能只注意到内债问题的共性而未达及特性,没有揭示内债问题的某些重要内涵。如果确有上述疏漏,那么与较长时期以来对“内债”与“公债”两个词的混用、误读有关。
在近代中国财政史上,内债与公债的区别是清楚的。公债即国家公债,包括内国公债和外国公债,“内债”与“外债”则是相应的简称。内债,指中央政府在国内以信用方式向个人或团体筹措资金,其债权—债务凭证的形式可有公债票、国库券与合同、契约之分。反之,在国外举借、或向外国债权人举借的,便是外债。在给定研究范围内,用“公债”来表示“内债”并不会导致理解上的歧异;但是,有些著述在对“内债”、“公债”做统计或统计性评述时,只列入采用公债票、国库券形式的债项,省略、忽视非债券形式的内债,混淆了不同形式债项之间的区别;对于债券形式的债项,公开发行谈得较多,以债券抵押借款甚少提及,语焉不详。这就容易对复杂的内债问题做简单化的理解。
1927年至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举借了大量内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举债总额,几种研究成果的记载有所出入。千家驹记为:“综计自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十年之内,南京政府正式发行了二十六亿元以上的内债”(注:《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第124页。)。杨荫溥的遗稿《民国财政史》谈道:“本期十年内(1927-1936年)先后发行了内债二十三亿二千一百万元”(注: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页。)。与以上两个统计数字出入较大的是《民国社会经济史》:“综计1927-1936年间,共举内债43.42亿元。”(注: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新近问世的研究成果中,也有沿用此说的:“1927年至1936年间,国民党政府发行有担保的内债总额43.42亿元。”(注:刘克祥、陈争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12页。)千家驹明确把1936年发行的统一公债14.6亿元定义为“调换旧债”,未计算在新发行各债的总额内(注:《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第124页;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307页也明确指出统一公债与其他新债的区别:“1936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各种公债208200万元,除统一公债14.6亿元是旧债外,新债发行额达62200万元。”);而且也没有把1928年的5亿元“国民政府财政部建设公债”计入(注:据建设公债条例第三条,该公债发行期限及办法未定。(《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7页)千家驹把1928年的发行总额计做1.5亿元(同上书,代序言,第19页),显然未计入该建设公债。但是“建设公债”的要件列入该书附录之统计表中(同上书,第370页)。)。那些大大超出千家驹统计数的结论,很可能把统一公债与“建设公债”一并统计在内了。笔者认为,举借新债与整理旧债,拟发而嗣后实际未发、或虽发但名称和数额已与最初条例不同之债项,都应列入1927年至1937年期间内债史的研究范围;但如果都计入各债项总数,宜对有关情况加以说明。
笔者要着重指出的是,一些著述往往只把公开发行公债票、国库券的债项列入研究范围,忽略了对非债券形态的内债债项和以债券抵押借款的研究,这是对“公债”一词的狭义使用。仅基于公开发行债项的统计以及相应的评判,会导致对内债问题所包含的财政和政治关系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片面性。全面考虑内债的各种形式和内债问题的复杂性,这是笔者主张在泛指和统称场合使用“内债”一词、进而区别“内债”与“公债”、“举借内债”与“发行内债”的不同含义的主要理由。
事实上,千家驹对公开发行的债券与非公开发行债项之间还是有所区别的,如:“这一年(指1932年)虽未正式发行公债,国民党政府仍向银行借了一亿数千万元。”“除公开发行的债券之外,国民党政府复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以意国退回庚款为担保向上海银行团(由中央、中国、交通、浙江兴业、上海商业、中南、金城等七家组成)借了国币四千四百万元。”(注:《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第120、123页。)收入《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的“财政部无确实抵押内债各表计算总说明”,把北洋时期内债分为公债、借款、库券三类,借款又分为盐余借款、内国银行短期借款、各银行垫款三项(注:引自《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01-102页。)。但千家驹又往往不区分“内债”与“公债”。他一方面把“旧中国发行的公债分为四个时期来研究”,而在对各时期做概述性说明时,又屡屡使用“内债”,如“清政府举行的第一次内债是一八九四年”,“北洋政府之大量发行内债是从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开始的”,“综计自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一年这五年之内共发行了内债债额达十亿五千八百万元之巨。”他把南京国民政府“筹措反革命的战费”方法归纳为“增加附税”、“借外债”、“发钞票”、“借内债”4种,这里的“借内债”当指广义的举借内债,包括公开发行与非公开发行的方式。但前引“综计自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这十年之内,南京政府正式发行了二十六亿元以上的内债”,显然仅统计了公开发行部分(注:《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第107、111、120、124页。)。《旧中国公债史资料》所附《旧中国的公债统计表》,只收入公开发行的债票库券,也使人易产生“内债”即“公债”的印象。
1927年至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举借内债主要方式有:第一,发行公债库券;第二,政府以债券向金融机构抵借;第三,直接与债权人发生关系,既不通过中介方,也不采用债券抵押方式。《旧中国公债史资料》所列出的主要是第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的借款事实上不少,如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前中国银行提供的几笔借款,1927年4月上海银钱业两笔垫款共600万元。在《交通银行史料》便见有:1933年中国、交通、中南、金城等行向铁道部垫款450万元;1935年中国、交通、中南、金城、盐业银行向铁道部垫款486万元;1936年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向铁道部透支借款300万元;1935年和1936年南京当局以湘岸盐税做抵,两次向中中交三行举借现款充做军费,每次为200万元;1936年财政部以粤桂闽区统税收入向中中交三行借款1200万元(注:《交通银行史料》上册,第398、405、385-386、388页。)。在业已出版的中国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史料中,都可以见有关于非债券抵押借款的记载。
从1928年开始,第二种情况即以债券抵借的次数颇多,情况最为复杂。30年代的研究者曾有如下描述:“政府发行公债,多当需款孔殷之求,等不得债票拿去发售,预先就以债票向银行抵押借款,然后由银行陆续按市价而出售,等到债券售出,再行结帐。”(注:佳驹:《国民政府与内国公债》,《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直接发售(购买)债券与作为抵押品的债券之间是有区别的。作为抵押品的债券所有权尚在国民政府,政府方面按实际获得的押款支付利息,其利息率与作为抵押品的债券并不完全相同。如果国民政府清偿押款本息,债券即需归还政府。通常押款届期或逾期而又无法以现款偿付本息,国民政府便会委托银行钱庄在市面上出售债券以抵付借款本息,或以债券按市价折抵。顺便指出,国民政府不仅向银行业而且也向钱庄业多次以债券抵借。某一债券可能若干数额直接向市场发售募集,其余部分向金融机构抵借,但最终又以所抵债券按市价清偿,这样被清抵的那部分债券实际是在二级市场上易手。对债券抵押借款的研究不仅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也是全面研究相关债票库券发行实际情况之所需,是1927年至1937年期间内债问题中难度较大但极具研究价值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看抵借个案的概况。1928年3月2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向上海市钱业公会借款100万银元,以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200万元为抵押(后抽回50万元)。在这笔抵借中,国民政府承担债务额是100万元,而不是作为抵押品的数额200万元或150万元;清偿期由起初规定的3个月两次展期,实际为7个半月;最初3个月利息率为8厘,以后展期内增至月息9厘。在国民政府最终明确授权清结之前,钱业公会对作为抵押品的库券并无处置权;因此不能把抵押品的押借折扣率,简单地视做发行折扣和计为债权方的收益率。这笔100万元的抵押借款与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本身在利息率、期限等要件上,都有所区别,应视为两笔借款。换言之,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的一部分初次发行时便被认购,但其余部分被充当押借抵押品,最终才被清抵的。如果对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进行专题研究,除了公开发行之外,还应搞清楚其余部分的库券是向哪些债权方、以何等条件进行抵借的,最后是怎样清抵的。
在谈到公开发行债券与抵押借款的区别时,不可不提到美国学者小科布尔的著作《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书中写道:“在1928年3月至1931年11月期间,上海钱业公会在十三笔交易中所购入的债券是三千零六十万元,而实际所贷出的款是一千五百六十二万五千元(见表5)。”书中表5为“上海钱业公会购买政府债券项目表(1928年3月—1931年11月)”,共列出13项,且注明“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1961),第207-209页。”(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79-81页。)但经查上引《上海钱庄史料》有关页码,所列表格是“1927-1935年钱业认购反动政府债券、借垫及押款明细表”,是把认购债券、借垫及押款3个方面的共30项按时间顺序分别排列;而《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所见的13项,都应属于押款即以债券为押品的借款,在这13项中钱业得到的债券都只能说是政府方面提供的押品而非“购买”债券本身,各项折扣率都只是抵押品与垫款额直接的比率,而不是购买折扣;这13项“购买”,无论从金融史和还是经济史的角度来看,都不是“购买”而是抵押借款。在《上海钱庄史料》中确实列出并注明为真正“购买”的,如1929年5月1日认购续发卷烟库券、11月2日认购上海市公债,但《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项也没有摘引。《上海钱庄史料》还记有1930年11月国民政府以民国19年善后短期库券(注明数目不详)押借200万元,《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表格中也没有收入。笔者查阅了《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的英文原著,发现上述问题发生在英文版,其中表5的标题是“购买”(purchase),表中又标明钱庄提供的是“贷款”(advance),获得的是“证券”(securities),并有以下一段话:"After the formal date of issue,the bonds would either be placed directly on the market at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and the Shanghai Chartered Stock and Produce Exchange or retained by the banks."(注:Parks M.Coble,Jr.,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1927-1937,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pp.70-72.)需要指出,从整体来看,金融业持有的债券分为两部分,即自有部分(直接从国民政府方面承购或购自市场)和抵押部分,可以自由向证券市场出售的是已经真正购买的自有债券;至于政府抵押借款的那部分债券,只有在政府方面授权清结的情况下,作为债权方的金融机构才能处置。但英文版只字不提国民政府的授权。中译本没有注明英文版与所引《上海钱庄史料》的出入(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44页表5为“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购买政府债券的条件”,所列13项同《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译本。)。国内的某些著述也提出了与小科布尔完全一样的结论:上海钱庄业确实以极大的折扣分13次“购买”、“购得”了上述债券。不知这些著述是直接对《上海钱庄史料》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后而得出统计结论的,还是采用了小科布尔著作中译本未加说明的直译?
除了钱庄业外,国民政府还多次向银行业押借。如财政部和交通银行之间,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5次抵借共2580万元,押品合计为民国20年赈灾公债426.09万元、民国22年和23年关税库券共3548万元;1936年3月和7月以复兴公债2915万元共押借2040万元,9月又以统一公债和复兴公债票面共4300万元押借3000万元(注:“交通银行行务纪录汇编”(三),《交通银行史料 第一卷 1907-1949》上册,第380-387页。)。还可以举出许多押借个案。这类个案绝大部分没有列入千家驹的统计或统计性评述。不少著述虽然提到有非正式发行的借款、抵借,但实际上几乎都没有如同公开发行的公债库券那样做直接的研究。把国民政府公开发行的各公债库券按其条例上的数额,按阶段、按时期进行统计和比较,当然有其科学性、学术价值和意义。《旧中国公债史资料》出版后,不少研究成果运用该书代序和附录统计表中给出的实发数额进行阶段、时期的内债发行额的统计,或照搬该书的统计结果。但该资料的“例言”中有说明:“本编后附一统计表,其中‘实发行额’一栏,凡官书档案有记载者概以列入,其无特殊记载者,即以‘发行定额’为‘实发行额’,这可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仅以供研究者的参考。”该书没有注明统计表中发行定额与实发行额相同的许多债项,其中哪些是“官书档案有记载”,哪些并无记载。因此在运用该书资料进行统计时,应加以说明,不能只是简单地按该时期各债项的条例将发行额相加计算。
迄今为止关于国民政府非公开发行内债尤其是以债券抵押借款的研究成果甚少,这主要是受到资料刊布状况的限制,也与对内债内涵缺乏周全的把握有关。不过,准确理解和使用“内债”一词,明确内债不仅包括狭义“公债”即在国内发行的公债票、国库券,还包括直接借款和抵押垫借,进而搞清它们之间的区别,这还是应当而且可以做到的。
二、债务方与债权方
如同近代中国的外债问题一样,内债关系的确立无疑要有债务和债权两个方面,然而在为数不多的涉及内债的研究成果中,实质上都是从债务方(通常指中国政府)的角度出发,叙述内债政策的制定以及内债的发行、使用、本息的偿付等环节。这一视角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且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研究1927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发行的内债,“债务方”问题还有必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吗?
笔者以为,从研究内债史的要求出发,有必要搞清所论及债项的直接举借主体,即是由“国民政府”还是由其直属部门出面发行或洽借签约的。而在做统计性、概述性表述时,如果仅提某时期“国民政府”共发行若干数额内债,理应把该时期经国民政府批准或授权的由各直属部门出面举借的各债项都考虑在内。前文提及的《民国社会经济史》有如下表述:“1927年至1931年的5年间,国民政府发行的有担保的内债共25次,总债额共10.58亿元……(略去以下列出各年度债项数和年度总额)”(注:陆仰渊、方庆秋主编《民国社会经济史》,第256页。)该书注明这一统计引自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代序,但笔者查核这一版本的千家驹原文,在按年度列出25项内债及给出总额10.58亿元后,注明:“上表未把伪交通部、建设委员会所发行的各种债券计算在内,仅以伪财政部发行者为限。”(注:《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代序,第15页;而中华书局1984年第一版《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的代序中(第19页),仍保留了此段注文,仅略去了两处“伪”字。)事实上,同期国民政府直属的其他部门也公开发行了若干债券,如:1929年铁道部收回广东粤汉铁路公债2000万元:同年和次年交通部两次电政公债各1000万元;1930年建设委员会电气事业长期公债150万元和电气事业短期公债250万元;同年铁道部北宁铁路机车设备短期公债500万元(注:《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87、189、191、194页;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4),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340、341页。)。上述这些借款的具体用途、担保品和基金保管机构都不同于财政部所举借各债,是评价该阶段“国民政府”内债政策和整体意义上内债问题全局时,应当予以关注的;在做相应统计时,如果是考虑到非财政部门发行内债的特殊性而分列分述,当然是可以的,不加说明而略去,显然不妥。
1927年至1937年期间公开发行各债券的具体发行者,究竟是财政部还是其他部门,或者是财政部与其他部门共同发行,应当有较准确的表述。30年代财政部与国民政府所属其他部门共同发行的公债为数不少,如1931年财政部与实业部共同发行过江浙丝业公债;1935年与交通部发行过电政公债;与铁道部在1934年共同发行玉萍铁路公债,1936年发行过第三期铁路建设公债,1937年发行过粤省铁路建设公债和京赣铁路建设公债。研究内债史既要指出各债项之间的共性,也要揭示其区别,包括具体债务方的不同。把1927年至1937年期间各项公债的发行主体都简称为国民政府,固然有助于使相应的经济关系和财政关系的本质更为凸现,但在做统计性的表述时必须考虑到具体债务方的周全。
至于非公开发行之借款(包括押借),财政部之外的其他部门有多项举借。如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举借的就有:1930年9月外交部以民国19年关税库券50万元抵借20余万元;建设委员会1934年以淮南电气公债押借90万元;同年交通部以西安电话局收入担保,借款22万元,海军部借款50万元,等等(注:《本行政府借款之研究》(1934年12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06-609页。)。又据金城银行1937年6月统计,对政府各机关放款情况为:财政部7057227元,交通部放款329580元,实业部放款61450元,军事机关放款216946元(注:《金城银行史料》,第484页。)。可以认为,国民政府通过财政部出面举借内债的数额大于其他部门;但是如果把财政部所借内债等同于国民政府举借的全部内债,这样的结论难免不周全。
除债务方之外,构成内债关系还有另一方即债权方。应当明确:谁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债权方?南京国民政府向哪些机构、团体和个人承担有还本付息的义务呢?进而言之,在论及的债项中,债权方为什么要对南京国民政府提供债款?债权方对款额、利息率、担保、期限等要件持何态度?债权方对国民政府的内债政策及其他重大政策持何立场?从现有研究成果的实际情况来看,强调不仅要从债务方、也要从债权方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更为客观、全面地研究旧中国内债问题本身,从而使近代中国内债史得以确立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地位;也可以拓宽近代中国工商史、金融史、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同时,相对于近代中国外债史研究中的外国债权方,研究内债史的债权方问题的资料条件要有利得多,就整体而言具备了研究的可能性。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承了北京政府时期所发而未清偿的若干内债债务,还承认了广州和武汉时期发行的部分公债。当时这些债票库券的持有者何止成千上万。这些人当然也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债权方,但由于债券并非南京国民政府所发行,故不列入本文考察范围。本文提出应加以关注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本身所举借内债的债权方问题。
以往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实际上都涉及债权方及提供债款的目的等问题。千家驹指出:“金融资产阶级为了它本阶级的利益以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它们一方面从国民党政府胜利的果实中分润其剥削劳动人民的赃物;一方面通过了对南京政权的财政支持,从而加强了它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使南京国民党政府更忠实地为它服务。国民党政府和金融资产阶级的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在公债发行上是表现得很突出的。”他还指出,当时的“持票人会”,“事实上即上海的银行团,也就是中国的金融资产阶级。”(注:《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代序,第18、20页。)杨荫溥则称:“控制着上海金融经济命脉的江浙财阀”、“买办财阀”,“以承购公债的方式支持反动政权”(注: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61页。)。上述提法虽然过于绝对化和简单化,毕竟还涉及了债权方问题。然而,千家驹在《旧中国的公债统计表》中收入了1927-1937年期间发行的50余项公债库券,分别给出“债券名称”、“发行日期”、“发行定额”、“实发行额”、“担保品”、“利率”、“其他”共7个要件,但没有列出债权方或者经销、代销机构(注:《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0-375页。)。这是十分典型的以债务方为本位,尽管列出的各要件对于债权方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其他一些著作简要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内债的发行对象是银行与公司;大量的公债都是由银行包揽或承购(注:《民国社会经济史》,第255页;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史》,第268页。)。可以明显看出,论者的重点所在实际是作为债务方的南京国民政府。近年新问世的关于江浙金融财团的研究成果,则进一步明确指出,购买南京国民政府公债的不仅有银行钱庄,还有“民众自愿认购”,“有部分公债是因民众购买而得以顺利推销的”(注:姚会元:《江浙金融财团研究》,第268页。)。南京国民政府所发债票库券的持票人数额之多,当不少于北京政府时期。
下面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举借的几笔内债为例,来探讨与债权方有关的几个问题,即:1927年5月1日开始发行的江海关二五库券3000万元,1927年7-8月间的盐余库券垫款828万元,1927年10月和次年2月两次发行的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4000万元。
1927年4月4日和25日分别签署的上海银钱业两次垫款共600万元,属于直接举借。当时上海银行公会有25家会员银行共承担了400万元;钱业公会的84家会员钱庄共200万元,每次每家认购11900元,公会每次出400元(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89-90页;《上海钱庄史料》,第207页。)。这两次垫款的债权方,既有少数的“财阀”,也有百来家银行钱庄的相关股东、投资人。从债务方蒋介石当局出发,这两次垫款可以认为是来自上海金融界的重要支持;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到在南北之间、宁汉之间、国共之间,上海银钱业的垫借不无政治上选择的意味。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垫款合同和相关文件,可以解读出别的含义。如第一份垫款合同对不少问题都有明确规定:垫款数额:银行公会各会员银行垫借200万元,钱业公会各会员钱庄垫借100万元;利息率:月息7厘,“自交款之日起算,陆续收款拨还,利随本减”;担保和偿付方式:“以江海关收入二五附税作抵,由银、钱两公会自借款日起,派员监收,逐日由收款行照数分派各行庄,至垫款本息还清之日为止。但本垫款本息未还清以前,如库券已销售有款,得以销售之款,尽先归还之。”(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57-58页。)银行公会要求派往江海关二五附税局监收的代表,“所有每日收入附税若干,暨每日分派各行若干,拟请逐日开单见示,以凭备案存查。”(注:上海银行公会执行委员叶扶霄、胡祖同致沈服周函,1927年4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以下简为上海银行公会档),档号S173/1/28。)在上海银钱业看来,与蒋介石当局还有着债权方与债务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严格按照商业原则,才能保护债权方的利益和要求。而加入垫款的各行庄作为不同的债权人,相互之间亦是“在商言商”,铢厘必较。
江海关二五库券是南京国民政府首次公开发行债券,如果仅知道发行定额和实际发行额都是3000万元,这只能笼统的说,南京国民政府得到了工商界的支持。而搞清具体是谁(商会、银行、钱庄、工商企业等)、各承募多少库券,显然有助于认识的深化。对于自行购买库券的公众数及其具体情况,尚难以明了;但有关档案显示:这笔库券自1927年5月1日起开始发行,至5月9日,上海市商业联合会所属的交易所联合会、纱厂联合会等32个会员,共认购190.7万元(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85-87页。)。而其中大部分会员各自又有若干个工商企业。再从上海金融业来看,到5月19日共承购504万元,其中有25家银行和100多家钱庄(注:《上海钱庄史料》,第207页。)。各行庄的资力不一,与国民党方面关系密切程度也有区别,但承募并不踊跃,如上海聚兴诚银行就曾表示:“此项库券,敝行最多只能认购票额2万元。”(注:引自上海市银行公会致聚兴诚函,1928年5月23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档号S173/1/28。)到后来只能统一规定,各行庄须按前两次垫款额的84%认购江海关二五库券。在购买、承销江海关二五库券的“债权方”中,上海中国银行颇引人注目。当时蒋介石曾强令其购买1000万元,上海中行总经理宋汉章只同意垫借400万元,代销600万元,结果与蒋介石发生正面冲突,引起上海金融界大哗,甚至连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都站在中行一边,向蒋介石据理力争。虽然最后江海关二五库券如额被购买和抵借,但金融界在政治高压和商业利益直接冲突情况下如何应对处置,是研究这一时期内债问题时应当注意的。
紧接着江海关二五库券之后的盐余库券结局,体现出债权方的态度对国民政府举债数额的制约。财政部原来宣布将发行盐余库券6000万元,蒋介石致电上海银钱两业,要求“设法垫募”。财政部次长钱永铭亲赴上海商催垫款,但金融界反响冷淡,中国银行担任额度最大,也仅246万元,且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分4批解款。居第二的交通银行垫借额只有120万元,以下北四行共100万元,南三行共80万元,四明银行40万元,再往下20家银行,每家认额多的为8万元,少的仅5000元。钱业公会总共只肯承担200万元,下派到各庄时,85家会员每家2万元,共170万元;公会出面与20家元字庄商议,希望每家承担1万元,元字庄方面统一口径:“如此巨数万难担任”,最后每家只认垫5000元,余下的20万元只得以钱业公会名义借垫。结果,到8月中旬蒋介石宣布下野时,上海各行庄解交款项总共才828万元,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与财政部代表就这一数额匆匆达成垫借合同,两业且要求财政部在合同中写明:“在本借款未清偿以前,国民政府为顾全市面金融计,允不再向两公会借款。”(注:上海市钱业公会常会议事录,1927年7月16、30日,上海钱业公会档,档号S174/1/2;《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33页。)上海金融业的最终认定数与盐余库券原定6000万元的发行额相差如此之远,以至于接任财政部长的孙科只好中止发行盐余库券,到同年10月以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换回作为押品的盐余库券。
至于续发二五附税国库券,大部分也是由金融机构购买或提供抵押垫款。值得注意的是金融业对利息率的计较。1928年初,继孙科之后出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宣布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加发1600万元,利息率由月息7厘增至8厘。两同业公会便向财政部方面提出,两业所认1340万元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在1927年12月底以前便已缴款,在预约期内应行加给1厘之利息,要求财政部查照各户预约券内载票额及缴款日期,核明补发。财政部拖到8月份才予答复,称该项库券自加发劝募之日起利息已增至8厘,而原预约券已分散,无从补息。12月中旬,上海银行公会得悉财政部直属机关认购该库券者,已领到补息,遂再度向财政部交涉,要求同一待遇;并指出“预约券分散”不能成为财政部拒绝补息的理由:“查敝会各银行之认购该项库券,与钧部俱有契约关系,与普通认购者不同,按图索骥,似不难复查……务乞俯念下情,准予补发。”这样,财政部不得不同意上海金融业关于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预约期内补息1厘的要求(注:关于这次交涉情况,可详见上海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1928年2月20日致宋子文张寿镛函、宋张同年8月4日复函、上海银行公会12月13日和17日致宋子文张寿镛电、12月17复上海银行公会电、上海银行公会12月22日致财政部函、宋子文1929年1月5日致上海银行公会函,上海银行公会档,档号S173/1/29;上海钱业公会档,档号S174/1/44。)。在筹募加发续二五券时,财政部长宋子文以加息、担保确实等条件和应为完成北伐“军事统一”尽义务相号召,不可谓不精明;但是作为债权方的上海金融业显然认为,在对国民政府尽义务的同时也决不可以忽视商业利益。
还应指出,当时财政部曾要求国民政府所辖各机关及省、市、县政府所属职员,一律以一个月薪俸应募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社会方面,凡行号商店及厂家,均须以职员一个月薪水为标准认购。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首次要求以薪俸、薪水额摊发债券,财政部要求上海银钱业在1928年3月15日前交款,未果;后来由上海商界劝募江海关二五库券协会出面,展至当月底,结果上海钱业南北各庄95家的职员,以一个月薪水为标准认购库券共72500元,并在月底前如额交款(注:宋子文张寿镛致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函,1928年3月8日,上海钱业公会档,档号Q174/1/44;林康侯致钱业公会函,1928年3月26、31日,上海钱业公会档,档号Q174/1/47。)。尽可能搞清各级政府和各厂商行庄职员应募与认购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的情况,是从债权方出发研究这一债项的必然要求,有助于深入揭示债项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内涵。
张嘉璈曾经指出,到1931年底为止,“估计未偿债券余额7亿余元中,银行之发行准备占2亿余元,个人与团体所有占4亿数千万元,外人手中六七万元。个人与团体所有之债券,一部分押于银行钱庄。”(注:《中国银行史资料汇编 上编 1912-1949》(1),第631页。)如果按行业区分,金融业尤其是上海金融业无疑是这一时期内债的最大债权方。较长时期以来流行一种看法:“金融资产阶级以承购公债支持蒋介石政权,同时他们也由公债买卖中发了财。”(注:《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代序,第26页。)就整体而言,这种看法并不错。但是,如果由此而认为,任何情况下金融业都乐于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供借款、购买或承销债券,那就把作为债权方的金融业的态度简单化了。1927年4月25日,上海银钱业公会与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达成的第二次垫款合同中,就有这样的规定:“自此次加垫后,不再续行垫借,并各地支行联号,亦不再加借。”(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59页。)国民政府推销加募续发江海关二五库券之初,1928年3月6日上海钱业公会委员会议通过的决定是:如以印就正式库券2万抵借1万,按照抵借手续办理,似不能推卸,但抵借之数愈少愈好(注:上海钱业公会档,档号S174/1/3。)。同年9月,财政部商议以善后公债票面150万元向上海钱业公会押借100万元现洋,钱业公会讨论的结果,仅允以100万元票面押借现洋50万元,“并要求财政部,将来本会会员倘有募到是项公债,不论数目多寡,应随时扣除。”(注:上海钱业公会第16期常会纪录,1928年9月26日,上海钱业公会档,档号S174/1/3。)1931年8月,财政部向上海钱业公会提出以新发行之盐税库券抵借200万元,遭到钱业公会的拒绝,结果财政部只得同意先结清此前的统税库券押款200万元,即由钱业公会代为售出作为押品的统税库券票面300万元之后,再以400万元的盐税库券重新抵借200万元的现款(注:上海钱业公会第15、16期常会纪录,1931年8月2、16日,上海钱业公会档,档号S174/1/5。)。待到1932年以上海金融业为主体的持票人会与财政部谈判公债整理案时,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政府不再向各商业团体举债为内战及政费之用。”(注:“持票人会对于内债之宣言”,《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26页。)还可以举出不少的例子。在较高的利息率和有抵押的情况下,为什么金融业对于向国民政府提供借款依然持谨慎态度,这是值得研究的。从某些债项来看,其政治意义较突出;但从整体来看,金融业把向国民政府提供借款或购买债券,看成是商业投资行为,追逐利润和规避风险,是题中应有之义。
三、起中介作用的团体和机构
进一步考察1927年至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的内债问题,可以发现:无论公开发行还是非公开发行债项,在债务方国民政府与真正的债权方之间,往往有某些团体和机构在起着中介作用。如上海商业联合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以下简称江海关二五券会)、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蒋介石当然也派出军需官为筹饷直接催款奔波,国民政府财政当局也时常会亲赴上海与金融业接洽借款,即便如此,在这一时期的内债机制中,某些团体和机构的中介作用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从内债史角度来研究相关的团体和机构,或者说通过研究这些团体和机构来考察当时内债问题的特殊性,是拓宽内债史研究领域的需要。
从概括商界、金融界与国民政府的关系而言,把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等团体直接说成债权方,把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直接说成债务方,并无原则性的不妥。1927年共600万元的两次垫款合同,确实都是由上海银钱业公会与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签署的。但是,如果仔细查阅有关史料,便可以发现,不仅这两次垫款、而且嗣后各次上海金融业承购承销债券、直接提供债款或垫款,真正的供款者是各行业商会(甚至工商企业)和具体的银行、钱庄;商业联合会和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的实际作用,一方面是把国民政府的各次相关举债额落实到下属行业商会和行庄,另一方面是作为债权方的代表,向国民政府进行交涉。而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虽然受权于南京当局,但金融工商界的代表为数不少,该委员会并不等同于国民政府本身,它的性质和在内债机制中的作用宜做具体分析。同样,对江海关二五券会和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也应做较深入的研究。
上海商业联合会与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都曾在1927年为南京国民政府募集内债,但二者的作用有较大区别,均值得做个案性研究。
商业联合会仅承担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400万元,在此额度内向所属各业商会、公所和同业公众摊派和催缴。1927年4月下旬起,分别致函有关下属团体,又召集部分会员团体会议,下达和确定认销额。至5月6日,商业联合会解款150万元,其中80万元是下属团体所缴,70万元是向交通银行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垫的。商业联合会固然打算完成所认定的承销额。但是,在催缴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商业联合会也会把矛盾上交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开列各团体名称、摊认款额,要求财政委员会直接“通函催其从速认销”(注:上海商业联合会致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函,1927年5月14日,《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101页。)。商业联合会成立于1927年3月,同年11月解散,存在时间短,且基本上没有营业性收入,可支配的仅为64家团体会员一次性缴纳的会费共15900元,完全不可能直接向国民政府提供借款(注:据上海商业联合会结束时的报告,会费支出各项为:捐款6591.28元,杂项5507元,邮电1400余元,薪工2000元,广告器具等300元左右,余存75元。见《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26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业联合会后期对替国民政府募款的态度明显趋于消极:“国军莅沪以来,我商民习处于憔悴呻吟之下,乃始而垫款,继则库券,竭商人之全力,以供绞脑沥血之金钱,无非促进政治……乃自清党以还,应有清明之望,而前辙依然,故吾犹是。虽曰训政方当期月,责备未可过严。然人寿究有几何,枯鱼先已入市。所谓内谋保障者,更不过如是如是。”(注:上海商业联合会结束宣言(稿四),1927年11月,《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第30-31页。)商业联合会包括上海工商业的数十家商会、公会、公所,江海关二五库券的发行对商业联合会范围内(除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之外)的各个阶层究竟有什么具体影响,如何全面看待商业联合会对南京当局内债政策所持态度;进而言之,1927-1929年的上海总商会、1930年之后上海市商会对各项内债的态度,都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与上海商业联合会“以互助精神维护商业为宗旨”大为不同,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虽然以上海金融界工商界人士为主体,但却是蒋介石直接授意设立的官方机构,有支配江苏境内一切财政收入之权,和筹拨“驻苏军队月饷及其余各费”之责(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财政经济》(1),第3页。)。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虽然存在的时间比商业联合会要短,却直接筹集了上海银钱业公会的两次垫款共600万元和发行江海关二五库券3000万元。在筹款过程中,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首要角色是国民政府的代表,在两次垫款合同中,财政委员会都是以债务方的身份签约的,江海关二五库券也是国民政府委托其发行的。然而,与日后直接出面接洽借款的国民政府财政当局(如1927年的孙科、1928年以后以及1932-1933年的宋子文、1931年底1932年初的黄汉梁、1933年10月之后的孔祥熙)不同,陈光甫等人当初之所以愿意以银行家身份出任财政委员会委员并为蒋介石筹款,更直接的考虑还是为了商界特别是金融界的利益。因此,当上海金融界与国民政府在内债问题上发生分歧甚至冲突时,财政委员会往往出面协调解决。1927年5月,蒋介石为使上海中国银行预垫江海关二五库券1000万元,多次与上海中行经理宋汉章直接信函往来,待到出现僵局,便由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陈光甫出面斡旋,最终由中行垫款400万元、承销库券600万元(注:关于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在此次风波中的态度和作用,参见吴景平《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述论》,《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4部分。)。这样既保护了中国银行,又使国民政府举债的基本目标得以达到。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最终结束,除财政部和江苏省财政厅业已正式运作外,还有两方面的客观原因:第一,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已经与南京国民政府有较多的沟通,财政当局可以直接向两公会提出借款、垫款的要求,由两公会再向众多行庄摊派、收款;第二,金融界工商界代表人物已经在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这一新的专门机构中有了相应的地位。
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虽然是商业联合会会员,在内债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商会和其他各业的同业组织,正是通过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蒋介石当局获得了最初的两笔垫款共600万元,以后发行的债券,大部分都在两业公会参与承销和押借。在国民政府财政当局看来,除了可以直接向中国、交通等大银行交涉垫借、押借之外,两业公会无疑是金融业债权方的代表,否则的话直接与数以百计的银行钱庄打交道,举债过程就会变得十分复杂和琐碎而难以操作,所需时间之长、募债成本之高,都会使国民政府难以承受。不过,无论在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时期还是在此后,银行公会本身通常不直接提供借款,钱业公会有时会承担各庄摊派后的余额,而它们的作用主要都在于把国民政府各次所要求的垫款,押借和债券发行数额分摊到有关行庄,并直接汇集缴付债款,参与内债基金保管和管理事宜,实际上成为1927-1937年期间国民政府内债政策运作机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另一方面,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首先和最直接代表了会员行庄的利益,或就新借款的数额、期限、利息率、担保抵押、或就已发行债券的还本付息和整理,与国民政府财政当局多次进行交涉。正因为如此,银钱业公会还成为上海非会员金融机构、沪外金融机构甚至所有内债持票人公认的代表。这在1931年底至1932年初的债券停付本息风潮中,以及尔后内债整理方案达成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与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相比,江海关二五券会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要少得多(注:宋时娟的《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始末》(刊于《档案与史学》2000年第3期)是公开发表的关于江海关二五券会的第一篇论文。)。江海关二五券会是南京国民政府自1927年公开发行第一笔内债起便成立的内债基金保管机构,主要由上海银钱业公会及商会的代表所组成,以后到1932年改组为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为止,江海关二五券会陆续保管有21种公债库券的基金,基金来源包括关税、盐税、统税、内地税、煤油特税以及庚子赔款退还部分,与相应的征收机构甚至财政部有着直接的关系;更与基金存放机构、还本付息经理机关、华商证券交易所往来密切。应当指出,江海关二五券会不仅对内债基金负有保管之责,还在不影响还本付息的前提下,适当运用基金现款贷放与金融同业。如1928年5月,为调剂上海金融,江海关二五券会决定以余存现款150万两贷放上海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由两公会转放与同业行庄(注:上海钱业公会会议纪录,1928年5月28日,上海钱业公会档,档号S174/1/44。)。这就使江海关二五券会具有了一般营运性金融机构的某些性质。不过,正如江海关二五券会的名称所示,该机构的基本职能是保管公债库券基金,而随着所经管债项的增加,江海关二五券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也时而发生。在1932年1月停付公债库券的风潮中,江海关二五券会主要成员以“头可断,基金绝对不可动摇”的原则相勉,进而公开以此昭告国人,终于使当时的孙科政府不得不放弃挪用内债基金的打算;但当上海银钱业公会决定接受宋子文的展本减息整理方案后,江海关二五券会又表示“应以一般持票人之意思为意思”,同意了整理方案(注:江海关二五库券基金保管委员会会议纪录,1932年1月13日、2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第一编 财政经济》(1),第516、519页;《银行周报》第16卷第1号,1932年1月19日。)。总体上看来,江海关二五券会的存在和运作维护了金融工商界持票人的利益,使内债发行有所节制,对国民政府债信的维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客观上也符合国民政府的利益。由江海关二五券会改组而设立的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除了保留上海银钱业、商会的代表之外,现任公债司长、关税署长和总税务司都作为当然委员,一方面使得组织上更臻完备,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该委员会的控制。1932年4月5日,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后,除接收原有江海关二五券会所保管的基金外,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还对新发行之跨地区、全局性的共12项公债库券的基金加以管理。除江海关二五券会和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这样的多种债券基金保管机构外,同时期还有一些专项内债的基金保管机构,如津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基金保管会、疏浚河北省海河工程短期公债基金保管会、铁道部收回广东粤汉铁路公债基金保管会、交通部电政公债基金保管会,等等。
指出上海商业联合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江海关二五券会、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机构、团体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决不意味着可以低估这些机构、团体在内债问题中的作用,而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它们的地位与影响,无论是在募款还是在理债方面。例如,由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出面就内债问题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正是各成员行庄把两个公会推向前台的结果。忽略“中介”机构与债权方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不利于揭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内债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有碍内债史研究的深入。
以上谈到的三个方面,都与内债本身直接相关,自然都应列入1927年至1937年期间内债史的研究范围。但从更广的视角考察,还有一些问题应引起关注。如北京政府遗留未清偿的对内债务,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债政策究竟有何影响;国民政府本身所发行的各项债券的上市情况,某一债券的上市与日后行情,是如何影响到现有其他债券行情,进而影响到以后的发行的;公债库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公债库券风潮的起因及其对债务方和债权方的影响;1932年和1936年两次公债整理案,对相关债权方的影响究竟如何(注:整理案涉及之债券,利息率降低,期限延长,有的甚至延长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才能清偿。这样,就投资角度来考察,1927-1937年期间相关债权人最终从购买债券中获得了多少利益,收回了多少本金,都需要具体分析。);如何评价地方借款与中央借款的关系;金融业对政府借款与对工商业放款的比较;特定债项中的外债部分与内债部分的共存问题;政府当局的内债政策与金融工商界有关主张的交互影响,等等。在掌握史料和搞清事实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内债史的研究领域,有助于构建较为完整和科学的内债史研究体系,同时也有助于对1927年至1937年期间的某些重大问题,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标签:国民政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 南京国民政府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银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