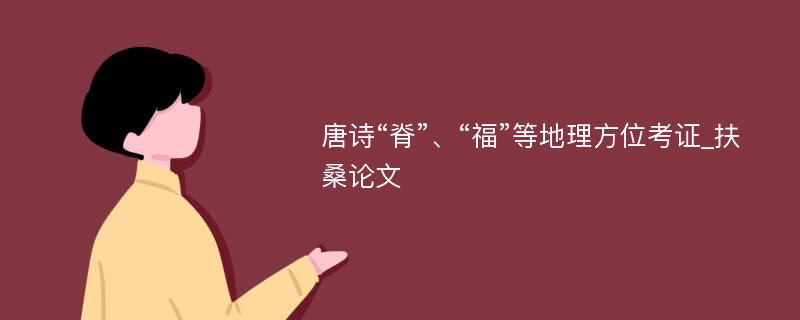
唐诗中“日东”“扶桑”等地理指向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扶桑论文,地理论文,唐诗中论文,日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2)03-074-07
《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收有唐人与新罗、日本和渤海人员交往的诗歌111首,在这111首诗歌解读与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每首诗所赠或所写的对象究竟是哪一国人员?就这些诗逐首加以考察,多数是明确的。但其中也有部分诗歌没有清楚标明对方国籍,只是在诗中出现了“日东”、“海东”、“东海”、“扶桑”等词语。这些词语在诗中究竟何指,不经过细致深入的考释,是得不出准确的结论的。经笔者统计,111首唐与东邻诸国交往诗,题中以“日东”等词指示地域的共15首(按:其中《赠日东鉴禅师》被《全唐诗》重收在司空图和郑谷名下,实为郑谷诗[1](P644),其中“日东”7首、“海东”6首、“东海”2首。迄今为止,对这15首诗赠与对象的国属,严耕望[2](P425-48)、谢海平[3]、戴铁栓[4]、张步云[5]、柳晟俊(韩国)[6](P231-247)、党银平[7]等中外学者都曾分别作过推测和判断。但有的只是简单的猜想,有的间或出现错误,其中张步云的《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错误最多。在他之前,严耕望、戴铁栓等先生虽有正确解释,张书亦未能吸收,说明仅猜测正确还不够,还要列举充分证据,才能让后来学者信服和采用。本文打算对前人的成果加以鉴别吸收,先就本身可以获得确证的9首诗歌作个案考察,继而再联系相关个案材料对“日东”、“海东”等词语的使用情况作历史考察,最后得出确定这些词语地理指向的事实和理论依据,并指出某些诗歌传本中词语出现讹误的原因。
一“日东”等词地理指向的个案考察
1、杨夔《送日东僧游天台》(卷763,此表示该诗在《全唐诗》中的卷数,下同):
一瓶离日外,行指赤城中。去自重云下,来从积水东。攀萝跻石径,挂锡憩松风。回首鸡林道,唯应梦想通。
诗题中的“日东”,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以下简称“严文”)谓“此可能为新罗人”,戴铁栓《“日东”“海东”何指》(以下简称“戴文”)、柳晟俊《罗唐诗人交游之诗目与其诗》(以下简称“柳文”)、党银平《唐与新罗文化关系研究》(以下简称“党书”)亦均谓为新罗人。张步云《唐代中日往来诗辑注》(以下见简称“张书”)收此诗,谓为“日本人”。按,朝鲜古籍《三国史记》云:“(公元六五年)春三月,王夜闻金城西始林树间有鸡鸣声。迟明遣瓠公视之,有金色小椟挂树枝,白鸡鸣于其下。瓠公还告。王使人取椟开之,有小男儿在其中,姿容奇伟。上喜,谓左右曰:‘此岂非天遗我以令胤乎!’乃收养之。及长,聪明多智略,乃名阏智(笔者按:阏智即新罗王金氏始祖)。以其出于金椟,姓金氏。改始林名鸡林,因以为国号。”[8](P9)公元三○七年,复改国号为新罗[8](P31),五○三年始定新罗为国号[8](P49)。《资治通鉴》载:“(龙朔三年四月)乙未,置鸡林大都督府于新罗国,以金法敏为之。”[9][P6335)唐授新罗王为鸡林州都督自金法敏始。“鸡林”在唐诗及唐代文献中指新罗。皮日休《庚寅岁十一月新罗弘惠上人与本国同书请日休为灵鹫山周禅师碑将还以诗送之》(614):“三十麻衣弄渚禽,岂知名字彻鸡林。”刘得仁《送新罗人归本国》(卷544):“鸡林隔巨浸,一住一年行。”李昌符《送人入新罗使》(卷601):“鸡林君欲去,立册付星轺。”刘禹锡《送源中丞充新罗册立使》(卷359):“身带霜威辞凤阙,口传天语到鸡林。”例证甚多,兹不一一列举。故据“回首鸡林道,唯应梦想通”可定题中“日东”指新罗。张书(第82页)注“回首鸡林道”之“鸡林”云:“鸡林:新罗。唐代中日交通途径,分南北两条。日东僧这次从北路走,故途经鸡林。”戴文则指出:“据《新唐书·新罗传》记载:唐高宗咸亨五年……‘诏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由此可见,新罗除被称为‘鸡林州’之外,还曾被称作‘鸡林道’。‘回首鸡林道,唯应梦想通’是写这个日东僧来到中国之后对故土鸡林的怀念。”张、戴两家之说对照,张说显然是曲解,戴说可取,但如果细加考究,谓“鸡林道”为行政区划之名,又显拘泥,“鸡林”即指新罗,“回首鸡林道,唯应梦想通”一联之中,“道”与“通”上下呼应,“道”乃道路之义。
2、曹松《送胡中丞使日东》(卷716):
辞天理玉簪,指日使鸡林。犹有中华恋,方同积浪深。张帆度鲸口,衔命见臣心。渥泽遐宣后,归期抵万金。
戴文据“辞天理玉簪,指日使鸡林”认定题中“日东”指新罗,且说:“曹松是唐末人,诗中所说的‘鸡林’当指新罗无疑。”然较戴文后出的张书竟亦将此诗收入中日往来诗中,并谓胡中丞所使乃日本,其误显然。拜根兴《朝鲜半岛现存金石碑志与古代中韩交往》[10](P47-53)引《三国史记》(卷11,第154页)“夏四月,唐懿宗降使,太子右谕德御史中丞胡归厚,使副光禄主簿兼监察御史裴光等,吊祭先王”,以及崔致远《大崇福寺碑铭并序》“遂于咸通六年,天子使摄御史中丞胡归厚,以我乡人前进士裴匡,腰鱼顶豸为辅行,与王人田献铦来锡命曰……”指出“胡中丞”系咸通六年(865)出使新罗之胡归厚,则是进一步从当时出使之人和出使之国证实题中“日东”指新罗。
3、许棠《送金吾侍御奉使日东》(卷604):
还乡兼作使,到日倍荣亲。向化虽多国,如公有几人。孤山无返照,积水合苍旻。膝下知难住,金章已系身。
“金吾侍御”出使对象,戴文谓为新罗,张书收此诗,谓为“日本”。戴文以诗中提及“还乡兼作使”,而引唐宪宗元和时期在唐为质子的新罗人金士信事迹为证。金士信《请充本国副使奏》云:“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尝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蕃,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今在城宿卫质子,臣次当行之。”又引《旧唐书·新罗传》《唐会要》等相关材料,谓:“唐时新罗质子常有在唐宿卫的,中国也常派使到新罗去传达朝命,即以宿卫的新罗质子充当副使,几乎成为惯例。”还进一步指出:“日使回国,中国出于外交礼节,有时也派使伴送到日,但现在能确知的使人,全部都是中国人,无一日人。虽也有阿倍仲麻吕曾充任使人的传说,但既不能证实,也未成事实。且自公元七七九年以后,中国再没有派出过赴日使人。所以从时间及历史背景上看,许棠是晚唐诗人,他诗中所说的这次使节,应是出使新罗而不是日本。”戴说可信,除他所举例证外,以新罗质子充当赴新罗副使的史料还可以举出许多,如金忠信[11](P11433-11434)、金允夫[11](P11466)等。而从唐代中日交往史方面考察,日本“自公元八三四年第十八次遣唐使之后的六十年间,日唐之间的正式关系等于中断”[12](P37),八三四年许棠约十三岁[13](P23-24),其赠使者诗无疑在八三四年之后,故题中“日东”必非指“日本”。又,唐禁军有左右金吾卫,然其官属无侍御,故笔者认为题中“金吾”应为人名,《旧唐书·新罗传》载新罗“国人多金、朴两姓”[14](P5334),由此可推定“金吾”为新罗人,题中“日东”指新罗。
4、沈颂《送金文学还日东》(卷202):
君家东海东,君去因秋风。漫漫指乡路,悠悠如梦中。烟雾积孤岛,波涛连太空。冒险当不惧,皇恩措尔躬。
严文谓“惟此金文学必新罗人无疑”,柳文、党书均谓“金文学”为新罗人,张书收此诗,谓为日本人。按,“文学”为官名,掌雠校典籍,侍从文章,唐朝太子司经局、亲王府都设有此职;此人姓金,当为新罗人。题中“日东”当指新罗。
5、雍陶《送友人罢举归东海》(《全唐诗补逸》卷7):
沧沧天堑外,何岛是新罗?舶主辞蕃远,棋僧入汉多。海风吹白鹘,沙日晒红螺。此去知提笔,须求利剑磨。
严文、谢海平《唐代诗人与在华外国人之文字交》(以下简称“谢书”)、柳文、党书皆收此诗,谓题中“友人”为新罗人,张书未收此诗。据“沧沧天堑外,何岛是新罗”,知题中“东海”定指新罗。
6、张乔《送朴充侍御归海东》(卷638):
天涯离二纪,阙下历三朝。涨海虽然阔,归帆不觉遥。惊波时失侣,举火夜相招。来往寻遗事,秦皇有断桥。
唐诗人中,张乔所作的与外邦人员交往诗歌最多,共7首,分别是《送新罗僧》(卷638)《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卷638)《送宾贡金夷吾(一作鱼)奉使归本国》(卷638)《送朴充侍御归海东》《送僧雅觉归东海(一作海东)》(卷638)《送人及第归海东》(卷639)和《赠头陀僧》(卷639)。《送人及第归海东》有“自笑中华路,年年送远人”之句,可见他与外邦人交往之多。从他的有关7首诗看,7诗中前两诗题中用新罗直接指称,无须辨析。上引《送朴充侍御归海东》中的“朴充侍御”是哪国人?“朴”为新罗国姓。又,尾联“来往寻遗事,秦皇有断桥”提到“秦皇断桥”。“秦皇石桥”本为神话传说,但到唐代确有把唐至新罗道中某处称为“石桥”者,《新唐书·地理志》载:“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15](P1147)李昌符《送人入新罗使》云:“愁约三年外,相迎上石桥。”可见此类诗歌中“石桥”与新罗相关。题中“海东”指新罗可定。严文、柳文均谓朴充为新罗人,党书引朝鲜文人朴趾源《热河日记》:“朴充、金夷鱼皆新罗人也,入唐俱为宾贡进士”,以及朝鲜李朝末期编纂的《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五《选举制附宾贡科·制科总目》,亦谓朴充为新罗人。张书未将此诗收入中日往来诗中。
7、张乔《赠头陀僧》:
自说年深别石桥,遍游灵迹熟南朝。已知世路皆虚幻,不觉空门是寂寥。沧海附船浮浪久,碧山寻塔上云遥。如今竹院藏衰老,一点寒灯弟子烧。
严文收此诗,谓:“此僧当自海外来。唐中叶以后,海东人浮舟多先至吴越,而乔又多友海东人,则此盖亦海东僧也。”严文只说“海东”未点明何国。党书曰:“此新罗头陀僧亦不详所指,然据‘遍游灵迹熟南朝’句知其多漫游于江南之地,‘沧海附船浮浪久’似指离开新罗时间已久。”按:党书解说可取,据上文对“石桥”之考证,结合此诗“自说年深别石桥”句,“头陀僧”亦来自新罗无疑。
8、张乔《送宾贡金夷吾(一作鱼)奉使归本国》:
渡海登仙籍,还家备汉仪。孤舟无岸泊,万里有星随。积水浮魂梦,流年半别离。东风未回日,音信杳难期。
严文、谢书、柳文、党书皆以“金夷吾”为新罗人,张书未将此诗收入中日往来诗中。“金”为新罗国姓。又,唐以新罗留学生或质子为副使出使新罗为惯例。“且自公元779年以后,中国再没有派出过赴日使人”(参见上文),张乔为晚唐诗人,其生活年代唐日已无官方往来,故从时间及历史背景上看,“金夷吾(一作鱼)”出使的不是日本,其为新罗人可定。
张乔7诗中,以上考清了5首诗的归属,所赠对象皆为新罗人,张乔跟新罗人有密切交往,当与乡里及经历有关。乔为池州青阳人,曾隐居于青阳界内九华山十年[13](P302),九华山是著名的佛教胜地,而新罗国王金氏近族金乔觉(圆寂后被尊为地藏菩萨)则是九华山佛教的开山祖师。金乔觉于唐玄宗开元末年来华,其时正是新罗佛教鼎盛时期。新罗佛教本传自中国。唐时新罗留学生、僧人、商贾大量涌向中国,“不绝于长安道”。金乔觉在九华苦修,由刺史张岩上奏,获唐德宗赐“化城寺”匾额,影响及于中外,宋代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唐池州九华山化城寺地藏传》载:“本国(笔者按:指新罗国)闻之,率以渡海相寻,其徒且多,无以资岁。……”[16](P516)金乔觉卒于贞元十年(794)[17](P7129),在他生前,新罗人来九华山学法者已多。其后,九华山香火更盛,到晚唐新罗僧人有增无减。张乔隐居九华十年,交往许多新罗僧人乃至其他新罗人是很自然的事。以上确定归属的张乔5首赠新罗人诗,内有2首赠僧侣,1首赠棋待诏,2首赠官员。可见张乔与新罗僧侣以及其他类型人士有广泛接触。又,(高丽)释子山《夹注名贤十抄诗》尚收有崔致远《和进士张乔村居病中见寄》[18](P109),证明张乔与新罗人崔致远亦有交往。崔致远擅长诗文,兼通佛道,在唐与新罗两方面都曾为官,并有重要影响[7](P99-132)。这些事实表明,在晚唐中日交往中断的背景下,张乔赠外邦人士的作品,其对象当皆属新罗人。他的七首赠外邦人诗剩下的两首《送僧雅觉归东海(一作海东)》《送人及第归海东》题中“东海”“海东”亦应指新罗无疑(按:严书、柳书、党书均谓两诗赠送对象为新罗人,然皆未说明理由;张书未将两诗收作中日往来诗)。
9、林宽《送人归日东》(卷606):
沧溟西畔望,一望一心摧。地即同正朔,天教阻往来。波翻夜作电,鲸吼昼为雷。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
张书收此诗,谓林宽所送系“日本人”,严文、谢书、戴文、柳文、党书均以题中“人”乃新罗人。其中戴文作年早,且论述最为充分,云:“新罗受唐册封,奉唐正朔是一种义务。诗中说‘同正朔’,正是指此而言。日本就不同了,它虽也采用中国历法,但非强制性质,……有时正朔同于中国,有时则并不相同。……最后一联:‘门外人参径,到时花几开。’新罗自古盛产人参,而日本却非人参产地。”戴说甚是,但张书仍不取。兹继戴说再补充数证: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卷506):“想把文章合夷乐,蟠桃花里醉人参。”顾况《送从兄使新罗》(卷266):“鬓发成新髻,人参长旧苗。”可见此类诗歌中的“人参”与新罗相关。《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四》:“(开元)十一年四月新罗王金兴光遣使献果下马一匹及牛黄、人参……”[11](P11407)同书同部又载:“(开元二十二年)新罗王兴光……遣其侄志廉谢恩,献小马两匹、狗三头、金百两、银二千两、布六十疋、牛黄二十两、人参二百斤……”皆可证新罗以人参为其特产,故贡之于唐。而《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新旧《唐书》从未记载日本与渤海以人参贡唐者。又,诗中提到“正朔”,新罗本自有年号,永徽元年(650)始用唐年号,奉唐正朔[8](P72),其后皆然,而日本、渤海虽表面上“正朔本乎夏时”[19](P1288-1289),然皆私有年号。从这个角度看,“地即同正朔”亦可说明诗题之“人”乃新罗人,题中“日东”指新罗。
二“日东”“海东”和“东海”在唐诗中出现和使用情况的历史考查。
以上确定了9诗题中“日东”、“海东”等词所指示的地域,余下尚有6诗待确定:张说《送梁知微渡海东》(卷89)、刘昚虚《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卷256)、张籍《赠海东僧》(卷384)、项斯《日东(一作本)病僧》(卷554)、杜荀鹤《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卷691)、郑谷《赠日东鉴禅师》。杜荀鹤生于846年[13](P264),其赠诗当作于公元834年中日之间无官方往来之后,因而所赠对象当为新罗人。张籍集中未见有与日本人交往诗歌,但有《送新罗使》(卷384)《送金少卿副使归新罗》(卷385)两诗,可见张籍与新罗人交往较多,再加上下文所讲的唐代典籍中狭义的“海东”、“日东”等特指新罗的用语背景,其“海东僧”之“海东”当亦指新罗。去此2首之后仅剩张说、刘昚虚、项斯、郑谷诗各一首,要确定此4诗所送外邦人的国属,须对“日东”、“海东”、“东海”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情况作进一步考查。“日东”、“海东”、“东海”在唐人与新罗、日本和渤海人员交往诗歌中的用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放在诗题中,用以特指新罗,如:
题中用“日东”特指新罗者:①沈颂《送金文学还日东》②林宽《送人归日东》③许棠《送金吾侍御奉使日东》④曹松《送胡中丞使日东》⑤杨夔《送日东僧游天台》
题中用“海东”特指新罗者:①张籍《赠海东僧》②张乔《送朴充侍御归海东》③张乔《送人及第归海东》④杜荀鹤《送宾贡登第后归海东》
题中用“东海”特指新罗者:①雍陶《送友人罢举归东海》②张乔《送僧雅觉归东海(一作海东)》
二是放在诗句中,指代新罗或渤海:
①诗句中用“日东”指代渤海。
徐夤《渤海宾贡高元固先辈闽中相访云本国人写得夤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赋家皆以金书列为屏障因而有赠》(卷709):“肯销金翠书屏上,谁把刍荛过日东。”
②诗句中用“海东”指代新罗或新罗地区:
窦常《奉送职方崔员外摄中丞新罗册使》(卷271):“帝命海东使,人行天一涯。”
姚合《送源中丞赴新罗》(卷496):“谁得似君将雨露,海东万里洒扶桑。”
张乔《送棋待诏朴球归新罗》:“海东谁敌手,归去道应孤。”
三是放在诗句中指日本:
①诗句中用“海东”指日本:
法进《七言伤大和尚》(《全唐诗补逸》卷18):“大师慈育契圆空,远迈传灯照海东。”(按:此诗出自日本真人元开的著作《唐大和尚东征传》,题中“大和尚”指名僧鉴真,“远迈传灯照海东”赞扬鉴真往日本传教之功,“海东”自指日本无疑)
陆质《送最澄阇梨还日本诗》(《全唐诗续拾》卷19):“海东国主尊台教,遣僧来听《妙法华》。”
朱千乘《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全唐诗续拾》卷22):“去岁朝秦阙,今春赴海东。”
②诗句中用“东海”指日本:
贾岛《送褚山人归日本(一作东)》(卷573):“东海几年别,中华此日还。”
综上可知:“日东”、“海东”、“东海”可以放在诗题中特指新罗,也可用以在诗句中指新罗、日本、渤海。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发现“日东”、“海东”、“东海”用在诗题中特指日本和渤海的诗作。由此当可以推知:唐代典籍中狭义的“日东”“海东”、“东海”特指新罗,广义的“日东”、“海东”、“东海”则可指新罗(高丽和百济灭亡前,两国也应包括在内)、渤海和日本(按:有一例特殊,即朱千乘《送日本国三藏空海上人朝宗我唐兼贡方物而归海东诗》,此诗为送日僧归国时作,盖为了避免与前面的词语重复,才用广义的“海东”进行复指)。
“海东”出现较早,陈寿《三国志·夫余传》载:“夫余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20](P848)《三国志·公孙度传》载,公孙度为辽东太守时曾“东伐高句丽,西击乌丸,威行海外”[20](P252),东汉辽东郡辖区大约在今辽东半岛[21](P13-14)。《三国志·夫余传》之“海东”约指以今辽东半岛为中轴,向北、向东延伸的一段区域内。到了唐代,辽东半岛为唐所取,“海东”的地理指向也相应东移,用以指朝鲜半岛高丽、新罗、百济。《旧唐书·东夷·百济传》载,永徽二年唐高宗降玺书给百济王义慈曰:“至如海东三国,开基日久,并列疆界,地实犬牙。”[14](P5330)知唐太宗时朝鲜半岛就已经被称为“海东”,而日本与唐遥隔大海,贞观时期只向唐派出过一次遣唐使[14](P5340)。至于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高丽灭,徙居营州。万岁通天中,契丹反,其首领率众东走,保险自固,恃荒远,乃得建国。建国后因受阻于突厥和契丹,它和唐的交往也很少,因而长期未被唐廷承认,直到睿宗先天二年(713),唐廷封其首领大祚荣为“渤海王”,唐与渤海才真正建立起联系[14](P5360)。所以唐初“海东”系指朝鲜半岛上的高丽、新罗和百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灭百济,总章元年(668)灭高丽,虽尽有两国之地而不能守,新罗乃乘机扩张势力,侵占高丽、百济故地,逐渐统一朝鲜半岛,致使“海东”在唐高宗灭百济和高丽后成为新罗的专称。约中宗、睿宗、玄宗时期,日本与唐的交往逐渐频繁,渤海国也与唐建立联系,两国方逐渐进入唐人的视阈,才被包括在“海东之国”内,到了王维送晁衡归国时广义的“海东”已经形成,故其《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曰:“海东国,日本为大。”把日本视为海东诸国中之一国。虽然“海东”的词义在扩大,但是由于词义有相对的稳定性,又由于新罗离唐较近,与唐官方、民间的交往更多,关系更为密切,就使得用以特指新罗的“海东”的词义继续存在,唐人在指称新罗时还沿用“海东”这个词,如马戴《送朴山人归新罗》(卷556)之“新罗”,《全唐诗》注:“一作海东”,“新罗”与“海东”其实是由于同义互用而产生的异文。“东海”显然是“海东”的变称,如张乔《送僧雅觉归东海》诗题之“东海”,《全唐诗》注“一作海东。”乃倒置所致。而唐人意识中,新罗与“海”“日”“扶桑”(参见下文)固相联系,变“海东”为“日东”往往只是修辞做法。
上文分析了“海东”在唐诗中的用法及其词义的演变过程,可见“日东”、“海东”、“东海”可特指新罗,这样题中以“日东”、“海东”作为指称、不能确定归属的4诗皆可视为唐人所作与新罗人员交往诗歌。因为除上述理由外,还应考虑到新罗与唐关系更为密切等情况。
三 唐诗中“扶桑”的用法
“扶桑”在唐人所作的与新罗、日本和渤海人员交往诗歌中也经常出现,有两种用法。
诗句中用扶桑指示新罗地域或作为其地域标志:
李端《送归中丞使新罗》(卷286):“东望扶桑日,何年是到时。”
顾况《送从兄使新罗》(卷266):“扶桑衔日近,析木带津遥。”
刘禹锡《送源中丞充新罗册立使》(卷359):“想见扶桑受恩处,一时西拜尽倾心。”
姚合《送源中丞赴新罗》:“谁得似君将雨露,海东万里洒扶桑。”
张乔《送新罗僧》(卷638页):“永向扶桑老,知无再少年。”
贯休《送人归新罗》(卷829):“积愁穷地角,见日上扶桑。”
陈光《送人归新罗》(《全唐诗续拾》卷36):“扶桑归到后,万里梦长安。”
诗句中用扶桑指示日本地域或风物:
方干《送僧归日本》(卷652):“大海浪中分国界,扶桑树底是天涯。”
吴顗《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全唐诗续拾》卷19):“扶桑一念到,风水岂劳形。”
全济时《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同上):“家与扶桑近,烟波望不穷。”
许兰《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同上):“归到扶桑国,迎人拥海壖。”
幻梦《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同上):“劫返扶桑路,还乘旧叶船。”
可见,扶桑在诗中既可以指示新罗,也可以指示日本,要特别指出的是,诗人用这个词指示新罗往往直接使用,而在指示日本时,虽有直接指示的,如上举方干、吴顗、许兰和幻梦的诗,却往往又有人谓日本在比扶桑更远的地方:
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刘长卿《同崔载华赠日本聘使》(卷150):“遥指来从初日外,始知更有扶桑东。”
徐凝《送日本使还》(卷474):“绝国将无外,扶桑更有东。”
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卷695):“扶桑已在渺茫中,家在扶桑东更东。”
四诗将扶桑与日本联系,但不认为扶桑就是日本,而认为日本更在扶桑之东。换言之,扶桑乃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其意念当为中日之间的大海或新罗。从“扶桑”在典籍中出现的情况看,人们在使用时逐渐把神话中的扶桑落实到新罗,然后再逐渐东移落实到日本。王元化《扶桑不是日本的旧称》、《扶桑为东方理想国说》两文[22](P280-284)指出《辞海》“扶桑为日本旧称”的错误,认为扶桑最早出现于《离骚》,本义是东方神木,以其为日出之所,因而张衡《两京赋》、王充《论衡》等均用它泛指东方,至于以扶桑为国名,始于唐初姚思廉《梁书·东夷传》,但此国并非日本,而是日本以东的另外一个国家,即东方理想国。王文也有疏误,即认为用扶桑指日本始于近代,如王国维、梁启超等人诗作中都以扶桑为日本。对此,初国卿《称日本为“扶桑”始于唐代》一文[23](P93-94)作了纠正,但还应指出,“扶桑”在唐诗中并非固定指示日本,亦可指示新罗或中日间大海里的神话之地,且指示新罗与东部海域的用例更多(共11例)。
在唐诗的阅读中,根据上文“日东”可以特指新罗之说,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一些校勘上的疑难问题。如钱起《重送陆侍御使日本》(卷237)题中“陆侍御”系指陆珽,他于大历三年(768)二月作为归崇敬副使往新罗册立金乾运;先是,钱起写过《送陆珽侍御使新罗》(卷237),故题曰“重送”,陶敏《全唐诗人名汇考》谓“‘日本’乃‘新罗’之误”[24](P424-425),确为的论,但“日本”、“新罗”字形迥异,如何讹误呢?据上说,即可推知题中“日本”之“本”当为“东”之讹,“日东”与“新罗”在转换上是不存在障碍的。又无可有《送朴山人归日本》(卷813),柳文、党书均谓题中“朴山人”为新罗人,张书收此诗,谓“朴山人”为日本人,上文已及,朴为新罗国姓,故柳文、党书是,张书误,题中“日本”之“本”当亦为“东”之讹。又齐己《送僧归日本》(卷847):
日东来向日西游,一钵闲寻编九州。却忆鸡林本师寺,欲归还待海风秋。柳文谓此僧为新罗人,党书曰:“据原诗‘却忆鸡林本师寺’句,鸡林为新罗国名别称,此无名僧必为新罗僧,疑‘归日本’原应作‘归日东’。”张书收此诗,谓此“日僧可能在鸡林寺院学过佛”。柳文、党书是,张书曲解诗意,题中“日本”之“本”亦应为“东”之讹。这种“东”与“本”的讹误还表现在项斯《日东(一作本)病僧》(卷554)、贾岛《送禇山人归日本(一作东)》和钱起《送僧归日本(一作东)》(卷237)诗题中,需要根据上述理由加以校正,并准确确定赠与对象。
总之,“日东”、“海东”、“东海”、“扶桑”,在唐诗中并非固定指新罗、渤海或日本,而要结合具体作家作品和赠送对象,方可确定。确定的原则,一是作品本身可能提供的证据,再一就是要对这些词语进行系统的历史性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