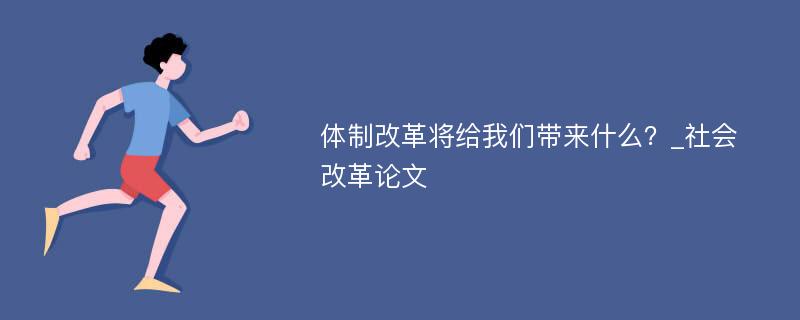
机构改革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给我们带来论文,机构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不久前闭幕的九届人大会上,人们盼望已久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终于亮相。基本原则是:机关干部应精简一半。目前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干部有4.8万人,将有2万人被精简,坐惯了办公室、动惯了笔杆子和动惯了嘴的人,今后将以何谋生?
几天前,国家计委某研究所的一位朋友说他们所可能要取消,而他们这些人就需要找后路。尽管他已经联系外贸部的一个部门,可这位先生仍顾虑重重:新调的这个单位将来是否也有可能被减掉?
没有铁饭碗了!不要说二三十岁这代人,就是四五十岁的人也面临新的考验。这次机构改革,先拿中央、国务院机关“开刀”。不过,国家机关再“砍”也就是2万来人。 在这么大的北京市消化个万把千人并不困难。可明年轮到省一级,那人数就多了。现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这一级机关党政干部人数大约近20万人。如果也是照着一半的标准精简,那就是10万人。在近30个省、市、自治区里消化这10万人也不算什么难事。
难的可能是第三年,轮到省级以下的各级政府部门。这一批干部的数字是多少?800万。要是“砍”去一半的话就是400万人。这400 万人如果一时得不到妥善安置,就只有加入待业和失业大军。而目前我国失业率已达到什么状况了呢?1997年社会登记失业率达3.2%, 登记失业人数为589万人,加上上年遗留下来的600万,全国实际等待就业的总人数为1189万。按1996年末国有经济单位、城镇集体经济单位、其他经济单位、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合计数1.755亿推算,我国1997 年的城镇实际失业率为6.77%。
如果今后3年不能消化掉近1200万的失业人口, 并继续增加300 ~400万人,那么3年后当失业人数达到1500万时,我国城镇失业率将达到8~8.5%。这基本是中国社会可承受的上限。如果实际失业率超过10%,城乡之间、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之间等多方面利益的矛盾就可能激化,社会就可能出现较严重的不稳定。因此,8 %的失业率是社会承受力的上限,而9%的失业率应当视作政策警戒点。
压力下的选择
于是就有人问了:既然机构精简将加重社会失业压力,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动荡,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让这些干部再呆在机关里不行吗?的确不行。应当这么说:机构改革精简人员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形如同当下的企业减员增效。如果不精简不改革,出现的问题可能还要严重。先算个帐吧,目前我国吃财政饭的人数有多少?总计3300 多万! 其中800万是各级党和政府机关干部,其他2600 万是各类事业单位及教育、医务等部门的工作人员。
干部在中国社会中的比例有多大,以至造成的财政负担有多重?财政部部长助理提供过这样一个数字: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总人口与财政负担人员的比例(即供养关系比例),汉朝时大致为8000∶1, 唐朝时为3000∶1,清朝为1000∶1,而今天为40∶1,即使按800万党政工作人员计算,这个比例也为156∶1。这就是说,今天1000个中国人里有6.4 个官员,20个吃财政饭的人,清朝时1000个人里只有1个官员, 唐朝时只有0.3个,在汉朝,1000个人里平均不上0.13个官员。请问:1000 个人供养一个官员轻松,还是40个人供养一个干部轻松?
让我们再横着做一比较。克林顿总统在90年代初上台时,美国联邦政府文职人员近300万人,占全国劳动力的2.8%。而德国和日本政府的这个比例只有1.4%,英国为1.9%,因此克林顿认为应当大力削减。五六年下来,美国政府的机构改革成绩斐然,财政赤字从1500多亿美元变成几十亿盈余。
而我国目前3300万靠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事业人员,占全国7 亿总劳动力的比例大约为5%。也就是说, 我国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吃国家财政饭的人员与国家劳动力人口的比例是西方发达国家的2到4倍。现在的中国,每100人里有2.75个人靠财政供养。
英联邦国在裁减政府公务员方面曾取得过显著的成就。从1979年到1996年的十几年时间里,英国政府的公务员人数减少了1/3,仅此一项政府就节省了大量的行政开支。国家财政出现连年盈余。
财政负担过重的恶果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今天中国国民负担沉重的程度了。如此庞大的干部队伍,如此众多的脱产人员,都要国家财政来供养,工人和农民的付出该有多大!不仅国家财政支撑不了,连整个国民经济都支撑不了。
看看这几年的中央财政,连年赤字近600亿元。 全国近一半的县财政吃紧。一共90多个县的陕西省,约60个县发工资困难。某些乡镇干部也常常数月半年拿不到工资。为了弥补额外的开支,财政部的国债发行量只好逐年增加,90年代初仅为几百亿元,到了1996年和1997年发行额增大到2000亿和2500亿元,今年的国债发行额加上银行特别债券总数要高达5200多亿元。历年积累下的国债加上国企的各种债务,国家总债务实际上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已达到西方国家的债务率警戒线。
债务率一高,便意味着金融风险。东南亚一些国家的金融危机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不尽早将这些危机的苗头化解,日后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财政费用紧张,是滋生许多弊病和歪风邪气的温床。正如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所说,现有机构重叠庞大,人浮于事的现象严重,不仅滋生了文牍主义和官僚主义,也助长了贪污腐败和不正之风。许多地方官员和干部,每遇财政困难,便巧立名目,乱摊派乱收费,不仅损坏了政府形象,也恶化了党群关系。1995年我国地方财政预算外的收入达到3800亿元,1996年和1997两年大约也在3000多亿元。预算外收入占到财政总收入的一半,这个问题说明了什么?人们可以细心去思索。
从经济建设角度来说,由于财政经费被大量的“人头”所侵吞,许多地方财政成为名副其实的“吃饭财政”。政府难有能力提供“公共产品”。不仅一些公共设施基础建设工程难以实施,甚至连基础教育和社会治安等任务也难以执行。
干部到底是什么?
机构改革势在必行。除了财政的原因,机构改革的意义更多的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方面。我国建国以来,先后进行了6 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国务院所属部门从35个最高增长到100 个,现在又要缩小到29个。尽管部门数目不断在变动,但机构人员却有增无减。1993年的机构改革不但没将人员压缩,反而又增加出100万人。 并且,到1994年为止,全国与财政挂钩的事业单位已达130万个。 这种屡增的原因何在?现在需要从根本上挖掘。中国当今有一词语需要重新进行审视,这就是“干部”。干部的准确含义是什么?长期以来,它的含义没有准确的界定。历史地看,干部是革命战争年间遗留下来的概念,凡是革命队伍中的大小负责人,有一定行政级别和军阶级别的人都被称作干部。
建国后,干部这一概念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它的涵盖面不仅包括政府机构,也被运用到厂矿农村大街小巷。从词义上讲,干部好象应该是群众的管理者,但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干部的应用面相当大。大专和大学以上的毕业生都纳入干部行列。上了大学,便有了干部身份。不管你当不当官。譬如报社的编辑记者、大学的教师和医生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都在干部行列。
从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情况看,干部已成为社会中相当大的一个群体。“提干”和“转干”曾经是口头禅。只要成了干部,就有了一定的权力,便被划入财政供养的范畴,有了一切的生活保障,即工资、住房、医疗福利、养老退休金等等。也就是说,只要成了干部,此人便有了终身的铁饭碗,国家要对此人包到老,包到死。
事业单位也要变性
此外,在干部成堆的地方,如国家中央机关、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和医疗卫生等部门的勤杂维修和后勤服务人员,几乎是所有在国家政府部门和机关事业单位里工作的人,全都需要由财政部里开出工资。
问题在于,任何一种概念和制度一经形成,便具有自我繁殖和衍生的功能。建国后干部群体日益增多和机构日益庞杂,是与官本位和等级制逻辑力量密切相关的。这种逻辑的具体表现便是:由于干部身份这一特殊的优越待遇,使人们想方设法往干部队伍里钻。越是在那些贫困地区,政府机构中养的干部就越多,机构也就越庞大臃肿。所以,如果不从理念上认清和纠正干部体制的弊端,机构改革和精简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因此,今天“干部”这一名词似乎要用官员和国家公务员这一类名称来代替,许多人的身份和称呼要改变。譬如,医生就是医生,教授就是教授,记者就是记者,研究员就是研究员,用不着再加上一个干部的身份。
如此看,“事业单位”这种称呼和含义也需要改变,像医院、学校、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完全可以经济自理,完全是独立经营的生产实体,没必要将它们挂在财政开支行列,划为事业单位。从现在开始。有计划地将一些吃财政饭的事业单位推向市场。同时,培养一批从市场中冒出的非财政开支的科研、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健身和广告媒介机构。
机构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另外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例如,机构改革是不是政治改革?如果仅仅把它看做是简单的机关人员增减,这种“量”的改变还谈不上政治意义的改革。准确地说,人员的增减只是机构改革意义的一部分,只是更大范围的改革即政府治理机制和治理能力等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从质的方面来看,机构改革应该是政府职能职权的调整和合理化,应围绕着政府职能职权决定组织机构的设置。这才是机构改革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权划分看,要明确哪些是政府该管的,哪些是政府不该管的,削减政府不应有的权力,界定政府权力的界限。要重视机构改革的法制化,应当制订编制法,坚持党政分开,党群编制与政府编制应该彻底分开。
邓小平同志早已指出,政府体制改革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党政分开,第二步是权力下放,第三步是精简人员。但是,我们今天是在倒着走,迟迟不能触及问题的核心,这说明中国体制改革的艰难。
这次机构改革会不会遇到阻力,机构精简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有句话说得好,改革已改到改革者的头上,已触及到某些改革者的切身利益。多少年吃惯了官饭的人猛地可能转不过弯来,抵触情绪肯定会有。另外,当前社会上下岗待业和失业的人数已经不少,如果再从政府机构中又增添出一批失业待业者,会给社会带来相当的心理震荡。
迎接巨大的经济增长
机构改革必须要有经济建设的有力发展,如此一大批脱产人员精简下来,必须要开辟新的就业岗位。从今年开始,要加大某些生产领域和基本建设领域的投资。3年之内,国民经济增长率不能低于8%。为了配合新一轮经济增长,银行利率还有下调的余地。
另外,各级机关分流出的大批干部实际上是一笔宝贵的人力资源,这些人从宏观到微观,使两者相结合,必然在将来的中国经济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机构改革使干部充实到基层生产领域,在战略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全面综合这一轮机构改革的意义之后,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机构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要获得巨大增长,要跃上一个新台阶,最终获益的是中国人民。因此,置身于这一改革洪流之中的人们,要及早做出明智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