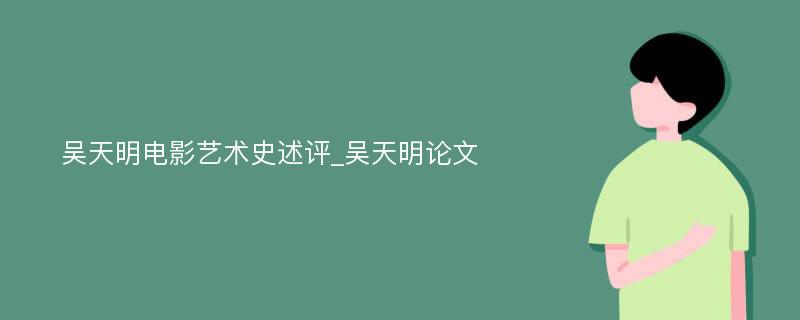
对吴天明电影的艺术史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史论文,电影论文,吴天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吴天明的电影成就,可以跻身于世界级大导演之列。然而从全球华语电影的研究成果看,吴天明研究并不突出,也就是说,学术界对于吴天明的评价,还远未达到这一位艺术家应有的地位。这源于国际学术界(甚至包括国内学术界)对存在于吴天明电影中的世界观探索、艺术观追求的认识和评价不足。本文的任务,即在于对吴天明代表作《人生》、《老井》与世界艺术史之间的联系予以揭示,以此证明导演试图立足于世界电影之林的艺术抱负,也证明导演的代表作是完全可以与世界电影杰作比肩的。 一、《人生》与新中国民族文艺传统 电影《人生》在中国新时期电影史上的地位,决定于该影片所展示出的乡村生活的真实、叙事格局的宏阔和电影语言的丰富。然而,这一切成就并非是吴天明及其创作团队的发明。吴天明的功绩,在于他首先在创作中融会了他自己的时代所可能吸收的中国电影、中国文学以及陕西地方文艺传统的所有成就。 就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地理路径看,在其创作中心离开延安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陕西文艺在全国的版图中似乎并不特别突出。就电影生产看,在北京、上海、长春等地的电影制片厂已经生产出奠定中国电影叙事的基本范式的代表作品的1950至1957年间,西安电影制片厂还尚未完成筹建工作,但这也许只是问题的表象,因为延安文艺及其观念,在走向全中国的同时,亦未离开陕西。柳青《创业史》所描写的新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的魂牵梦绕、生死相依的关系,它所塑造的具有特殊精神气质、行动方式、感情状态以至语言习惯的陕西农民形象,既是新中国文学的代表性成就,也是几代陕西作家的精神楷模。路遥、陈忠实等作家的创作实践与柳青之间的继承性关系,显而易见。吴天明选择路遥小说《人生》作为改编对象,其所借助于路遥小说的,必然首先是新时期中国农民问题这一着眼点。这当然是延安文艺以来中国文艺创作的主流传统,同时携带着鲜明的地域特色。 就电影本身的发展历程而言,将《人生》与《白毛女》做一适当勾连也许是有意味的。排除这两个故事当中的诸多差异因素,其共同点最少表现在它们都在探讨: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中,中国乡村青年女性的命运问题。如果将《白毛女》看做是新中国电影叙事传统的奠基性作品,那么《人生》则表现出了对《白毛女》所秉承的艺术理念的深层继承和跨越式发展。所谓的继承指的是:《白毛女》这一电影文本虽然历经由歌剧到电影之间若干次的情节修订、细节完善和形式探索,但它与新中国文艺应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艺术宗旨从未脱离。而《人生》从小说到电影,其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也依然牢固①。小说《人生》中写到高加林被迫离开城里的工作岗位,回到故乡,正在他为了个人的自尊担心乡亲嘲笑他的时候,“许多刚下地的村里人,却都从这里那里的庄稼地里钻出来,纷纷向他跑来了”。作者继而感叹道:“当你跌倒了的时候,众人都伸出自己粗壮的手来帮扶你。他们那伟大的同情心,永远都会给予不幸的人。”②而电影《人生》中所塑造的数量众多的“恋土”者形象,也都首先是基于影片创作者对土地和劳动者的由衷敬意。 路遥在谈电影《人生》改编时所提到的六种意见,涉及小说题旨的表现,可感的生活的呈现,由陕北的人情、民俗和大自然所承载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以及哲学的内涵,雄浑、博大、深沉的风格,以及艺术理念上的“土洋兼备”③。吴天明在电影《人生》的导演阐述中对上述创作观念也做出了更符合电影媒介特性的说明。这些说明,尤其是路遥所强调的“土洋兼备”,都形象地道出了艺术家在创作理念上放眼世界范围的可接受性,力求有所突破的努力。所以,相比于“十七年”时期农村题材的电影,《人生》对于人物故事、乡村生活以及生产劳动过程的呈现,更真切、更感性,视野也更宏阔。一种生动可感的乡村生活的场景和气息在电影《人生》中处处可见。抛开那些被观众所熟知的情节和细节,一些从未被批评家分析过的事物也能穿越银幕时空,借助摄影机背后发自肺腑的情感,成为诗意书写的出色段落。 影片中高加林的父亲所经营的一小块白菜地,它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刘巧珍给高加林送完甜瓜,高加林在回家路上,看到父亲在白菜地劳动,说:“爸,回家了!”④这时候,时间正是夏末,白菜苗刚刚长高;第二次是巧珍爹跑到白菜地找到高加林的父亲要求他出面管教自己的儿子,不要再和巧珍来往,一向内向的高玉德站起来大声说:“你要是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我就把你的脑壳劈开!”这时候,白菜苗儿长得大一些了,这似乎意味着,高加林和刘巧珍的爱情,在长辈的关注和同龄人的羡慕中,开始成长了;而当高加林和巧珍在水窖边商议一起去城里买漂白粉,之后两个人一起骑车经过起哄的孩子、村里的妇女和地里正在劳动的年轻人时,高加林的父亲正在白菜地里劳动,他老人家害羞地背对着观众,急速地蹲了下来:他恨不得要将自己藏在这大而浓密的白菜的叶片当中。设想一下,如果高玉德的故事全部发生在窑洞里,那就太沉闷了,尽管窑洞的背景和他的脸庞之间气质相近,但却没有张力。如果高玉德的故事发生在像德顺老汉经常耕作的高高的山梁上,那样又太高远宏阔,与他的性格不符。电影画面安排高玉德这个既内向又有着毫不迟疑的舐犊深情的老汉,细致入微地耕作在自己的生机盎然的小块自留地里。这一块白菜地,事实上可以看成是高玉德老汉美好的内心世界的一个外化,它也寓意着故事主人公的爱情事件的成长和变化。“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⑤。这一从20世纪80年代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借以描摹理想生存状态的诗句,用来比附高玉德老汉的存在状态,也是十分贴切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在极易被观众忽视的人物和事物那里,《人生》电影的创作者也赋予了他(它)们以艺术发现的光芒。 真实并且具有诗意,这是新时期中国电影借助于语言革新所期待的艺术观念革新的目标。电影理论探讨和创作领域不断辨析蒙太奇和长镜头这两种电影语言在写真实这一艺术目标上的利与弊,并且在某一阶段里似乎选定了长镜头才是贴近真实的这样的一种认知立场,发表了大量的以探讨长镜头、纪实美学以及巴赞等人的电影理论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拍摄了大量以实践长镜头为目的的电影作品。作为这一次语言革新和艺术观念革新潮流中的当事人,吴天明对上述论争深有了解,并且拍摄过《没有航标的河流》这样的包含了大量无目的长镜头的影片,但吴天明很快便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其争论的漩涡,他在《人生》中流畅使用多种视听语言,借鉴丰富的艺术传统,完成了故事的讲述。像影片片头交代高加林家庭环境的画面、集市上的热闹场面、高加林初到县城工作的场面、暴雨中救灾的场面、巧珍婚礼的场面,这些信息量大、人物情感冲击强烈的段落,影片使用了比较快的剪切方式,而在田间劳动、恋爱抒情、山川风物的展示段落里,影片则较多使用了长镜头。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吴天明在创作过程中并未在戏剧性和纪实性、蒙太奇和长镜头之间做出有倾向的选择,他秉持了一种融合和超越的艺术理念。融合是在说对于各种论争的兼容并包,超越是在说他不以实践某种艺术理念为其创作目的,而是以写生活、关注人生和传递文化为其创作任务。 至于写生活、关注人生,上文已经在新中国文学和电影观念的演进基础上做出大致描述,而至于传递文化,这一任务的设定和出色完成,也是《人生》之所以能够在80年代初的中国影坛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在其流传过程中畅通无阻、深入人心的原因。 作为首先以影像存在的艺术媒介,电影《人生》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既能获取各种人物“类”的共性,又能体现某一个人的“个别性”,在认同度和感染力两方面,完成的是经典的现实主义创作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艺术理念。同时,《人生》的人物形象设计,更融会了新时期中国艺术的先锋气息,比如《人生》中高加林父亲的形象与罗中立油画《父亲》(1980)之间的可辨识的共同点⑥。作为80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罗中立在这一幅绘画中挖掘了“农民”这一形象的典型性、当代性、崇高和卑微共存的特性。这种卑微感,是新中国“十七年”银幕形象所没有的,因为即便是像杨白劳这样的被压迫者的典型,作为一种艺术形象,其卑微感也没有像高加林的父亲和罗中立的《父亲》那样强烈。杨白劳、祥林嫂,他们在阶级关系中是受压迫者,但是他们的银幕形象却并不卑微。相反,由于创作者赋予他们的被压迫者的愤怒,这些形象具有着相当明显的自足和骄傲。然而,在新时期的艺术家这里,农民的形象增添了卑微而怯懦的性格特征,这种卑微感就是观念的跨越,是吴天明和罗中立他们对于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处境的真切体认。因此,在影片《人生》的开头,当高加林要为自己的不公命运“写状子”告高明楼,他的父亲说:“好我的小老子,人家通着天呢。”这一句话显示着人物的极度虚弱感的台词,放置在80年代初这个被看作是中国农民最有希望、最具幸福感的时代的银幕上,获得的则是令人振聋发聩的效果。这就是艺术观念的跨越中所体现出的干预社会的勇气。 《人生》作为西部电影的开创性作品,其对中国西部黄土高原的山川风物的展示,在中国电影中也是第一次。影片中所使用的多首陕北民歌,由于其韵律经典、与故事情节紧密关联,在声音层面上为影片《人生》的艺术成就增添了不少分量。带着一身黄土气息,风尘仆仆地走进观众视野,就好比一个农人走进了艺术殿堂,《人生》在其公映之初带给观众和评论界的震惊,至今仍为人所称道。在《人生》以后的中国银幕上,持续不断地存在着以黄土地作为故事发生背景的影片,以至于黄土地已然成为了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本身的象征性符号。由黄土而大漠,由大漠而奇观,这个序列的影像元素已经作为景观式电影的流行元素,成为了特定类别的商业电影的符号,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视为商业成功的可能。然而,尽管黄土高原在《人生》以来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由农民的劳动场所蜕变成为了影像元素,但这个蜕变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一条道路。换句话说,在富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乡村生活以及民族文化传统中,吴天明获得了讲述《人生》故事的语汇和思想;而同时,电影《人生》所提供的视听语言和故事题旨,也已经成为了中国电影历史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已经成为了传统。 二、《老井》与现代艺术观念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电影的创作和理论领域,各种“新颖的”理论和风格风云际会,一种为艺术而燃烧的创新的激情鼓荡着艺术家和评论家的灵感和方法。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其巅峰时期所生产的代表影片,同样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既能够在形式上大胆创新,其立意题旨又能深植于生活本身。这也许与吴天明当时所主导的西影厂的整体创作氛围和他本人的艺术观念有关⑦。邵牧君在《老井》公映时就曾对吴天明与理论的关系发表过看法:“他重视理论,认真研读,认真听讲,观点不论新老,一律兼收并蓄。不过他脑袋里有个过滤器,胸腔里有根主心骨,哪些该身体力行,哪些仅供参考,哪些留作己用,哪些转送他人,纹丝不乱……他有意改编《老井》之后,曾在已故钟(惦棐)先生家里面,隆重召开座谈会,首开剧本一字未写,先向理论请教的先例。”⑧而我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老井》,不仅是因为这部影片对于吴天明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因为影片所表现出的内涵与西方当代艺术理论和实践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关联表现在“身体”、“对话”和“凝视”等三方面。 《老井》使用大量的篇幅、镜头甚至是故事情节,探讨了创作者对“身体”这一表现对象在银幕上进行艺术突破的可能。 《老井》的片头是一名男性身体的上半身,他抡起铁锤,敲打一个凿子,在凿石头。通过各种视角的拍摄,镜头缓慢接近,从半身近景渐渐推进为臂膀处的特写。这一组镜头持续四分钟左右,整个影片的片头字幕就写在这样的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凿石头的过程中。这样的以身体展示为主要内容的片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次。同时,这样的片头是一个预示,它引导着观众首先要从身体及其赞歌的角度上理解这一部影片的深层次的立意。所以,尽管《老井》同样拥有一个农村知识青年孙旺泉及其艰辛人生这样的一个故事框架,但渗透在故事发展过程中隐秘的“身体”问题,才更值得我们进行挖掘和辨析。 从故事表层看,孙旺泉的身体是一个劳动者的身体,他在段喜凤家里帮忙凿猪食槽子,他从山间背着一块大石板郁郁而行。他的身体,也是一个恋爱者的身体。在影片开始不久,孙旺泉和赵巧英结伴去挑水,途中休息,两人“喊山”,孙旺泉脱去上衣,露出健美的身体,而从他的视角看去则是赵巧英因长时间挑水负重而红扑扑的脸蛋。几次正反打,观众能够体会到孙旺泉和赵巧英这一对恋人之间对于对方“身体”的爱慕。一点一点地,电影将作为描写对象的身体,拓展成了作为艺术理念实践对象的身体。也就是说,《老井》的创作者们,在对于身体展示这一问题上,找到了具有突破性的发现点。 孙旺泉受到水利专家孙总工程师的邀请,到县水利学校去学习。为此,孙旺泉的爷爷在家里设宴,为其送行。爷爷对他的这一次学习寄予厚望,认为“兴许咱老井村,能出个把神来”⑨,这个由新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赋予“知识”的“神力”,不仅表现在《老井》的整体叙事动力中,而且毫无疑问地塑造了“爷爷”这个人物形象中面向未来的那一面。三十多年过去,“科学技术”和“知识”到底在今天中国民众中的地位还是否能够具有与当年一样的“神力”,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我们关心的是爷爷在讲这一番话的时候,他、二爷、弟弟旺来和孙旺泉,这一家四个男人,坐在一张被安放于狭窄的堂屋门里的小方桌上举行的“家宴”。 喝着廉价的烈性酒⑩,桌上摆着几样家常炒菜。四个男人穿着20世纪80年代初山西太行山区的农民的典型衣着。爷爷回顾了自己的豪迈历史,因为求雨不得而“吊打过龙王爷”,二爷由于打井受伤,“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精神有问题),而弟弟旺来,“性子弱”,所以,“出个把神”的指望,就落在孙旺泉身上了,因为“你们这一辈人,眼界宽”。这是一个豪迈的段落,爷爷大段的演说让孙旺泉感到责任重大。画框包着门框,紧紧地框着四个坐着的男人,似乎他们的动作稍微有所变动,就会出画一样。画框所给出的狭窄的范围,固然可以让我们感知到这四个男人之居所的逼仄,但我们却更愿意相信,这一个段落的目的是导演和摄影师要让观众对这些男人的身体所散发出的力量感到难以抗拒。这就是吴天明的态度,是他对待自己在那个年代所塑造的银幕形象的态度:生活是艰苦的,但充满了希望,希望存在于健壮的身体中。这当然也是一种时代精神、一种对劳作在大地上的农人无限崇敬的时代精神。二十年后,贾樟柯在《三峡好人》(2005)中,用同样的手段塑造了三峡轮船上的移民群像,以及在奉节县城的简易旅馆中工友们的饮酒畅谈,在这些画面中,人物的身体也都几乎撑破画框。贾樟柯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对劳动者的崇敬。这时候,我们再次意识到,吴天明和张艺谋(影片《老井》的摄影师之一)在拍摄《老井》时所体悟到的描写“人的身体”的方式、理念和态度的超越性功绩。 然而,如果仅仅塑造了一种有力量的劳动者的形象,《老井》并没有完全完成自己在艺术追求上的抱负。仅就上述这一个段落来看,爷爷在大段演说后,又满怀柔情地表示,他不该管孙旺泉和赵巧英恋爱的事。爷爷的柔情直接让孙旺泉泪奔,他的眼泪说明他在现实的境遇中原谅了爷爷,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并且决意与命运进行一次正面的抗争。就在这个时候,爷爷对弟弟旺来说:“旺来,拿土豆来。”旺来伸手从旁边的大锅里端过来的是一大碗煮熟的完整的土豆。爷爷掰开一颗土豆,咬一口在嘴里。干面的土豆和烈性的酒在人物的嘴巴里相遇:这就是80年代中国北方乡村的一场豪迈家宴中的一个瞬间。它的中国性和地域性是如此地强烈,它的历史性和现场感也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它立即获得了穿越时空的锐利,永驻我们的眼底。然而进一步,我们也知道,这一画面的“素材”和呈现方式并不是中国电影所发现的,甚至不是中国艺术所发现的。“在清澄光华的映照中,是桌上的面包和美酒”(11)。这一句诗,来自于格奥尔格·特拉克尔的诗作《冬夜》,海德格尔的名篇《语言》,解读的就是这一首诗。只要观众熟悉这一句诗,那么上述画面立即就笼罩了诗意的光辉。 1885年,梵高完成了他的杰作《吃土豆的人们》。画面中,一家人围坐在狭小的餐桌旁,桌子的上方悬挂着一盏灯,成为画面的焦点。灯光洒在农民的脸上。房顶低矮,空间拥挤,但这一切都不妨碍我们看到灯光,看到餐桌上的土豆所冒出的热气,看到被灯光所照亮的农民的脸和裹在衣物当中的农人的身体。梵高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他描绘了人物境遇的艰辛,更在于他描绘了存在于这些人物内心和生活境遇中的光辉,还在于,他向我们展露了他在描绘这些人物的过程中,存在于他内心中所赋予这些人物和事物的光辉。就这一点而言,梵高如此,吴天明如此,张艺谋也是如此。将存在于画作当中的19世纪80年代荷兰“吃土豆的人”,置换为存在于银幕上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太行山区“吃土豆的人”,这展现的是优秀的艺术家在面对“农民的身体”这同一种对象时所共有的感怀。拍完《红高粱》,张艺谋坦言自己深受《梵高传——热爱生命》一书的影响(12),这可以看成是我们将影片《老井》中的“吃土豆的人”这一画面与梵高画作直接联系的注脚。这种联系让我们体会到吴天明和张艺谋在创作《老井》时意欲比肩世界艺术高峰的抱负和雄心。 《老井》还以一种极具民族风格的方式实践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这是中国电影叙事手段的大胆创新。 1985年,西安电影制片厂颜学恕导演的作品《野山》公映,评论界反响热烈。这部影片中有一个段落,是四个主人公在画面上二人一组同时说话,但又互不干扰,成为刚刚在中国文艺理论界传播开来的巴赫金“对话”理论在电影艺术创作中应用的典范。钟惦棐对《野山》的艺术成就的评价,认为它“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在传统的基础上上升到一个新的美学层次”(13)。这个新的美学层次,既包括影片中大量同期录音的使用(14),不动声色的长镜头和景深镜头的使用,也包括上述将戏剧性蕴涵于场面调度中的大胆尝试。 在《老井》中,也有一段类似的镜头。孙旺泉、村支书和爷爷陪着水利专家在崇山峻岭间勘测井位,村支书抱着红色的暖水瓶,爷爷怀里抱着两瓶水果罐头,孙旺泉拿着两个搪瓷茶缸子。休息时,爷爷用菜刀开罐头,后来孙旺泉接过来继续开,用菜刀在罐头盖子上划开一个十字口,爷爷接过孙旺泉划开的罐头瓶子,用手指将口子掰开,爷爷的手指被划伤了。而在画面的后景中,是两个水利专家端着倒了热水的茶缸子,边喝水边谈话(讨论将孙旺泉吸收进水利讲习班的事)。这一组镜头,也是几个人在前景和后景分成两拨,同时说话,然后两个水利专家走到前景,爷爷用自己的衣襟擦勺子,将勺子递给水利专家,专家说:“呀,手都破了!”旺泉、支书和爷爷三个人,满含笑意地看两个专家吃罐头,爷爷将流血的手指放进嘴里吮吸着:五个人又混在了一起。这个段落,与上述《野山》中的场面调度相比,它也实践了理论上的“对话性”,也自然地运用了景深,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这个段落中看出,最卑微的事物、最普通的食物,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传递,在艺术家爱的光照中,散发出了动人的光辉。 所以,对于“对话”理论的使用,如果说在《野山》那里还停留在一种叙事手段的尝试的话,那么在《老井》中,这一新颖的艺术手段已经与艺术家的爱的胸襟完全融合。艺术家的爱的胸襟,隐藏在摄影机背后,那就是体现在镜头中的各种层次的“凝视”。在上文所述“村民山间款待水利专家吃罐头”那一个段落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艺术家在不动声色、又十分努力地挖掘着蕴藏在村民行为习惯中的美德,将浓烈的情感投射在微小的事物和人物上。因此我们最后要探讨的是,《老井》所具有的沉思性风格和气质,与镜头的“凝视”这一既是拍摄手段又是艺术理念的问题之间的关系。 作为20世纪西方思想史的重要话题,萨特在视觉压抑体制的层面上探讨过“凝视”的问题,而拉康的镜像理论、福柯的权力理论以及穆尔维的性别理论都有非常重要的有关凝视的探讨。然而,就1986年《老井》筹拍以及1987年《老井》公映时中国电影的历史语境看,影片中我们称之为“凝视”的段落,其从艺术理论和观念的资源看,更多应来自于中国电影界对巴赞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长镜头的美学分析、对法国新浪潮电影、对西方现代主义电影实践成果的学习。上述艺术潮流及其实践,从语言上看,是尊崇长镜头和景深镜头,从艺术理念上看,是隐藏拍摄者的思想和情感,发动观众在生活流的呈现中解读影像内涵。这样,摄影机背后的“凝视”的态度就成为一种必需。在我们认为所有的镜头尤其是长镜头都具有凝视功能的前提下,我们要特别论证的是,在《老井》中,存在着一个特殊又隐蔽的结构,它既体现了创作者的表意意图,又超越了其最初的设想,从而赋予了影片《老井》以某种形而上的沉思风格和气质。 在已有的《老井》评论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孙旺泉“在喜凤家入赘,死心塌地端起了尿盆盆”这一剧情的分析,认为这是孙旺泉“屈从的象征”(15)。这一认知一直代表着中国电影研究对《老井》的立意分析的主流。尽管评论界对于《老井》所描绘的孙旺泉精神世界的成长历史也十分肯定,但是这种由人物对环境屈从入手,继而升华到“英雄气概”的切入点,并没有穷尽吴天明在刻画孙旺泉这个人物形象、描绘“老井村”人民的生存状态时所倾注的所有艺术激情和抱负,也对这一剧情所具有的解读的延展性缺乏认识。从剧情上看,孙旺泉第一次倒尿盆,是他和段喜凤第一次结合后的早晨;第二次倒尿盆,是段喜凤告诉他,自己已经“有了”之后的那天早晨;第三次,则是在旺才因打井而死,孙旺泉和赵巧英在这一次事故中受伤康复后,他和支书以及打井的乡亲们决心继续打井,来到井边看到旺才母亲在井架上系满了辟邪的红布条之后的第二天早晨。这三次倒尿盆,意味着孙旺泉作为一个人物形象,在命运和环境的压力中、在渐渐获得的生命之美好的体验中、在日常生活本身所携带的巨大力量中、在一个有抱负的农村青年的价值追求中,他一点一点介入了人生越来越深刻的本质内容。尽管人们很少对三次倒尿盆之间导演所赋予的人物精神世界的推进做出详细的分析,但意识到这一点,应该已经是《老井》的观众和研究者的共识。 我们要进一步关注的是,在三次倒尿盆之后,影片所“附着”的三个非常有意味的段落: 第一次倒尿盆之后所附着的段落:孙旺泉和段喜凤结婚后,段喜凤终于忍受不了孙旺泉在感情上的“冷淡”,哭了。孙旺泉安慰段喜凤。两人第一次结合后的第二天早上,金色的阳光照着小屋的门口,也照着厕所的一角。穿着新的学生服的孙旺泉端着尿盆走进厕所。接下来的镜头,是白雪轻覆中的村庄远景,继而切换成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用铁马勺在地上舀雪的近景,她专注地舀着,一马勺,一马勺,她的眼睛专注地看着雪,襁褓中的孩子似乎也在安静地参与这一个过程;之后是喜凤妈,她跪在地上,用一个小的木簸箕,往一个大的藤条簸箕里“搜集”雪,一下,又一下,十分专注;然后是支书和他的妻子,共同用铁簸箕往一个大筐里装雪;之后镜头拉成中远景,画面中是不少村民都在搜集雪的场面。在这个“搜集雪”的段落中,没有台词,影片只是细腻地描摹人们如何搜集雪的过程。人们的体态和雪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虔诚迎接、俯身感恩的关系。在一个以寻找水为主要故事的影片中,雪的到来,人们搜集雪的段落,并未介入故事的讲述,而成为时间上的一次停顿。孙旺泉并未出现在搜集雪的人群中,他的出现,需要等到这一次时间停顿结束。当我们的观影时间重新与故事时间重合时,孙旺泉出现了,几个年轻人从远处跑来,向村支书报告在双泉井发现石碑的事。如果说,在这个段落中存在着凝视,那么除了摄影机背后创作者的眼睛,事实上,影片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类似“上天”那样的视点。因为,只有在上天看来,这些作为水的化身来到老井村的村民身边的雪,才是最具有爱的恩赐。而且,这一场雪,既可以是当下剧情的需要,也完全可以超越剧情,成为老井村村民、北方世代农民与雨雪之间的恩情关系的永恒写照。雪的段落与此前阳光照耀的信息之间的断裂,说明导演有意赋予了雪以及“搜集雪”这一行动以象征性目的。 第二次倒尿盆之后所附着的段落,是在与喜凤给未来的孩子取名字的第二天,穿着变旧了的学生装的孙旺泉端着尿盆走出了家门,也有一抹阳光在他的肩上晃出了金黄的影子,他走进阳光照着一角的厕所。接下来的镜头,是冬日的户外,孙旺泉和段喜凤在铡草,他一下一下地压着铡刀,每铡一下,他的身体就有节奏地弯一下,而喜凤则跟着他的节奏,一点一点往铡刀下送干草;接下来是喜凤妈从树上取下金黄的玉米棒子,拿到摆在院子里的大箩筐那里,祖孙二人坐在那里剥玉米;秀秀轻咳一声,然后继续认真地剥。镜头再次回到孙旺泉和喜凤铡草的画面,由近景拉成中景,喜凤妈和秀秀剥玉米的情景就成为旺泉和喜凤铡草的后景。整个段落中,没有对话,一下又一下有节奏的铡草声与画面相始终。这也是一次脱离了故事讲述的时间的停顿。孙旺泉第一次作为家庭成员,与段喜凤的母亲和女儿一起劳动。这一处的凝视,体现的是创作者对于孙旺泉渐渐习惯了的婚后生活的祝福,也是对乡村日常劳动的美学观照。 第三次倒尿盆之后所附着的段落:依然是晨光熹微的冬日早晨,阳光照着以矮墙围起的厕所,披着黑棉袄的孙旺泉端着尿盆走进厕所。接下来的画面依次是:女儿秀秀在鸡窝那里看着鸡们一只一只走出来,孙旺泉蹲在屋子门口,抽着烟,看秀秀放鸡;段喜凤喂猪,装在铁皮小桶里面的猪食,被她认真地倒进猪食槽;喜凤妈扫院子,脸部特写表明她扫得专注,扫得认真;秀秀拿着一个原本是扫炕的小笤帚,和奶奶一起,也认真地扫着,一缕头发遮住了她的眼睛,她捋了捋头发继续认真地扫;喜凤和喜凤妈磨面,小毛驴拉着石碾子,喜凤妈扫着碾子上的麦子,喜凤坐在旁边,用箩子箩面。镜头再次回到孙旺泉凝视的目光。这说明,上述一切人和事,都在他的视域中。他似乎无动于衷,但又似乎是百感交集,深吸一口烟,烟雾遮盖了他的眼睛。在这个段落中,孙旺泉成为了喜凤、喜凤妈和秀秀的凝视者。与前两个段落不同的是,孙旺泉的凝视,体现的是他与生活之间既在又不在的特殊关系,他似乎既融入了生活,又特意与生活保持一定距离,进入了一种“哲思”状态。 我们看到,在这三个脱离了剧情发展、有意让时间停顿下来的段落中,表现出了吴天明早在80年代中期就试图有所跨越的艺术理念,他从单纯的写实叙事,走向了对人物、生活和人物与生活之关系的诗性沉思。这种沉思赋予了吴天明电影以强烈的现代性特征,而这一特征则是研究他的人很少进行充分探讨的。 三、由《变脸》而从中国西部汇入世界电影潮流 1995年,在阔别影坛、羁旅美国五年之后,吴天明拍摄了《变脸》。尽管该影片获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认可,但在吴天明研究中,很少有论者将其当做典范的“吴天明式”的电影进行讨论。究其原因,结合上述我们对于《人生》和《老井》的分析,可以看出,《变脸》离开了吴天明的代表作所具有的展示一种宏阔的历史画卷的抱负,它也不再关注作为群体存在的“人民”;从艺术观念上看,实践某一种艺术手段,也已非它的创作动力。《变脸》以一种淡化时代、淡化社会立场和形式特征的冷峻气质,完全将问题的核心聚焦在对命运本身的探讨上。不过,当我们想到吴天明在美国的生存基础是在洛杉矶开设的一家叫做“南山影视”的录像带租售店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他回国后每天的生活,只要条件允许,是必须要看最少一场电影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位艺术家从未中断过对世界艺术和电影发展过程的关注。在《变脸》公映前一年,正是吕克·贝松新作《杀手莱昂》风靡全世界的年份,片中女主角怀抱一盆绿植在大街小巷阔步行走;而在《变脸》中,女孩狗娃也拥有着一种同样的镇定自信、崇尚情义的气质。当狗娃病后,变脸王爷爷背着她卖菜,她抱在怀里的是几棵叶子新鲜的莴笋。由于《变脸》整体的影调是灰暗的,所以这几棵莴笋显得十分明丽。这时候,我们也许可以会意,吴天明之所以离开“吴天明式”的电影,是因为他已经离开中国西部,汇入了世界电影的潮流。 挖掘吴天明电影和中国民族文艺传统与世界艺术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要证明他“借鉴”了什么,而是要说明,他的作品所启示给我们的民族性、诗性、爱的胸襟和沉思的力量,使得他的作品已经达至世界艺术杰作的领地。 对中国西部电影的研究,多年来更注重的是对其地域特色、文化元素和特定时代精神的研究,缺少的是对存在于西部电影中的思想探求之超越性、艺术观念之先锋性、社会介入之深刻性的强调。今天,中国西部电影作为一个创作群体,似乎处在一个相对低沉的时期;中国电影整体上在多元发展和市场运行成功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艺术创新不足、社会问题介入不足的缺陷。总结中国西部电影巅峰时期在以上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不仅有利于对中国西部电影的已有成就给予充分评价,而且有利于今日的中国电影在其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再攀艺术观念和思想探析的高峰。 ①这种观点代表着《人生》小说读者和电影观众的普遍认同。在电影改编和拍摄的过程中,导演吴天明和路遥均首先强调文艺为“广大观众”服务的宗旨。批评家阎纲在与路遥的通信中,将小说《人生》评价为“现实主义”以及“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在新时期的生命力的表现(阎纲:《关于〈人生〉和路遥的通信》,《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5页)。 ②《路遥全集·人生》,第181页。 ③路遥:《关于〈人生〉电影的改编》,《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第185—186页。 ④本节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电影《人生》台词。 ⑤该诗句作者为荷尔德林,可见于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郜元宝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93页。 ⑥作为亲身经验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西部艺术创作之崛起的评论家,萧云儒认为,吴天明的电影《人生》和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代表的都是这一时期西部文化蓬勃发展的最重要成就。文献可见于2014年3月6日《西安晚报》所发表的纪念吴天明的访谈。 ⑦2014年春天,吴天明导演辞世。在许多纪念文章和访谈中,曾经与导演共事合作过的艺术家,都谈及了吴天明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时期锐意革新的创作理念、兼容并包各种思想的艺术生产管理经验。文献可见于2014年3月4日至11日的《西安晚报》,其中包括张艺谋的访谈文章《头儿改变了我的一生》。国内亦有多家媒体发表相关信息。 ⑧(15)邵牧君:《〈老井〉品析》,王人殷主编《吴天明研究文集:梦的脚印》,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第224页。 ⑨本节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电影《老井》台词。 ⑩确实是廉价的烈性酒。吴天明在与罗雪莹关于《老井》的谈话中,讲到了这一个信息:“由于实拍时饮的是劣质白酒,艺谋很快就醉得眼球发红了。”(王人殷主编《吴天明研究文集:梦的脚印》,第116页)。 (11)转引自海德格尔《语言》,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页。 (12)马驰:《〈梵高和阿姆斯特丹的画家们〉来华展出》,载《新京报》2011年9月8日。 (13)这是1986年电影金鸡奖评选揭晓时,钟惦棐为西安电影制片厂的两部作品《野山》和《黑炮事件》的成功所写下的备忘录中的一段。仲呈祥《赵书信性格论》(载《电影艺术》1986年第5期)一文对该备忘录有完整引用。 (14)《野山》同期录音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六,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如此大比例使用同期录音的影片;到《老井》拍摄的时候,吴天明已经表示不能忍受后期配音。这两种材料可见于《野山》录音师李岚华和《老井》导演的创作谈当中。文献可见于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野山——从小说到电影》(1990)以及吴天明与罗雪莹关于《老井》的谈话(《吴天明研究文集:梦的脚印》,第120页)。标签:吴天明论文; 老井论文; 艺术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白毛女论文; 人生论文; 高加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