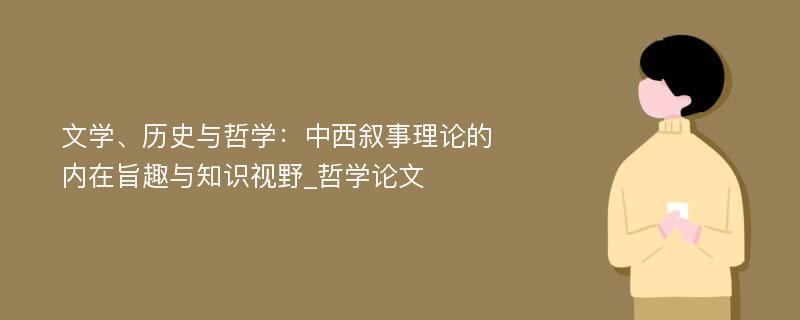
文史哲:中西叙事,理论的内在旨趣与知识眼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旨趣论文,文史哲论文,眼界论文,中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批评的剖析》中,弗莱曾说:“文学位于人文学科之中,其一侧是史学,另一侧是哲学。由于文学本身不是一个系统的知识结构,因此批评家必须在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找事件,在哲学家的观念框架中找思想。”〔1〕弗莱的论断十分中肯,文学不是一门学科知识,文学之为文学恰恰在于它的前学科性和超学科性,因此,批评家不可能在文学自身找到观照文学的观念框架,他只能求助于特定的人文学科,给它一种视野,一套可操作的批评语汇。史学和哲学作为最古老的人文学科正是传统批评可依赖的“知识”。
不过,严格说来,弗莱的论断只对传统批评有效,因为现代批评不再寄生于史学和哲学,而是位于语言学之上,并就是一种本源性的语言学实践。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文学被认为是一种最为基本的语言活动,因此,对史学和哲学的本真理解反要借助于文学的参照才有可能。
不管怎么说,弗莱的论断都是我们进入中西叙事诗学,并反观其现代转向的路标。
诗史之分:志与事、一般与个别
中西传统诗学是在“语词与实在”的关系中入思的,对叙事诗学而言,“实在”即“事”,因此,诗(言、文)与事的关系是中西传统叙事诗学的基本视域与可能之论域。由于传统工具论语言观和实在中心论的支配,中西传统叙事诗学基本上是一种遗忘了“言”之本体功能的“事论”,而对“事”的理解又是在“史学”和“哲学”的眼界中进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诗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未能注意到“事”对“诗”的意义,故而其叙事诗学发生迟缓且难产;西方诗学则一开始就注意到“诗与事”的特殊相关性,因而其叙事诗学早发而且早熟。
此一情形可在中西远古思想对诗与史的区分中见出。
在中国,“诗言志,”〔2〕“史,记事者也。”〔3〕“志”与“事”分别是诗与史的言说对象、也是区别诗与史的标志。
此一区分意义重大、因为它暗含了一个判断:诗叙事是非法的,“事”是史的言说对象,诗的本职是“言志”,诗如叙事则“不务正业”、“不守诗道”,非诗而史了。
虽然中国诗论也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4〕之说。但“事”毕竟只是哀乐之缘起,即所谓“触事兴咏”,诗所咏唱者不在“事”而在哀乐之“志”。此外中国古人虽在释诗时也好寻“本事”,但对正宗诗论而言,寻本事只是手段,察兴寄之情志才是目的。
与之相较,西方的情况则有根本的不同。亚里士多德指出诗与史的区别主要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5〕不管怎么说,诗与史的言说对象都是“事”,只不过是不同的事罢了。诗与史各言其事,各行其事,并行而不悖。在今天看来,亚里士多德这些言谈几近“陈词滥调”,但它对建立西方叙事诗学的意义却一直隐而不彰。
话还得从柏拉图说起。在柏拉图眼中,诗歌叙事也是非法的,只不过理由与中国古人有异。依柏拉图之见,诗叙之“事”是个别事物的影子,与真理(一般理念)隔着三层;此外,诗模仿的事物影子是为了投合读者卑下的情欲,败坏了人的理智,因此应将诗人逐出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重新解释了古希腊流行的“模仿”说,他认为诗之“模仿”是模仿自然造物的方式,即像自然造物那样将形式加在质料上以制成诗作和艺术品。其次,亚里士多德重新解释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认为柏拉图式的一般(理式),即那种先于个别而独立存在的一般理式是不可思议的,任何一般(理式)都只能依附于个别而存在,个别才是第一实体或本体。因此,诗不仅可以叙述个别之事,而且只有经由个别之叙述才能揭示那依附于个别的一般。再次,亚里士多德基于以上见地认为诗虽叙述个别但却意在一般,故而它高于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因为历史为写个别而写个别,它不关心一般。
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这一论断非同小可。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哲学”被认为是对一般理念的表达,因而它意味着真理、知识、道德和存在的权利,说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就是说诗比历史更有价值、更有存在的权利。因此,这 一论断为诗歌叙事奠定了强有力的合法基础,同时也就为诗歌叙事理论开了绿灯。
与此相反,中国诗学长期安于“诗言志”,“史叙事”的分野而不曾为诗之叙事争得一席之地位,只是到了唐宋之后,文学叙事在传奇小说戏剧中自然发展而蔚为大观时,文学叙事的合法性问题才得到关注。即便如此,对文学叙事的思考也大都是在戏曲和小说论之中,而与诗话、词话无甚关系。
俗常以为,中国的叙事诗学发生迟缓是因为中国远古的文学经验主要是抒情诗,西方叙事诗学早熟而丰饶是因为古希腊的文学经验主要是史诗和戏剧。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一概而论。问题可能还在于,中国古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找到区分诗歌叙事和历史叙事的理论依据,尤其是在古老的诗史区分之后,如何将诗歌叙事从历史叙事中剥离出来并确立诗歌叙事的合法性就成了一个特别困难的事情,在此不仅需要相当发达的诗歌叙事经验,更需要一种强有力的理论尺度。遗憾的是,在古代中国这两者都贫乏。此外,由于中国古代的尊史传统,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唯我独尊,因此,诗歌叙事和叙事诗学最初是寄生在历史叙事和叙事史学中的。事实上,中国的叙事诗学是从诗之外的小说戏剧等写作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而小说戏剧的母胎更像是史传而非诗歌。因此,以小说戏剧论的样式而出现的中国叙事诗学的形成史就是既依存又偏离史传叙事理论的历史。
文史哲:历史旨趣与哲学意味
“历史”作为文学叙事评价自身的唯一尺度长期支配着中国文学叙事理论的发展,文学叙事只有不断证明自己的“历史性”才有存在的理由。所谓“文参史笔”、“班、马史法”和“良史之才”乃是对文学叙事的最高评价。“历史旨趣”乃是文学叙事的最高标准和目的。
这种“依史论文”的倾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支配着人们对传奇、戏曲和小说的看法与鉴赏。诚如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所言,“在中国的明清时代,作者与读者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对小说本身更感兴趣。最简略的故事只要里面的事实吸引人、读者也愿意接受。……职业性的说话人一直崇奉视小说为事实的传统为金科玉律。《三言》中没有一则故事的重要人物没有来历,作者一定得说出他们是何时何地人,并保证其可靠性。……讲史的小说当然是当作通俗的历史写,通俗的历史读,甚至荒唐不稽附会上一点史实而不当作小说看。所以描写家庭生活及讽刺性的小说兴起时,它们显然是杜撰出来的内容,常引起读者去猜测书中角色影射真实人物,或导致它们作者采用小说体裁的特殊遭遇。前人对《金瓶梅》既作如是观,《红楼梦》亦然,被认为是一则隐射许多清代宫廷人物的寓言。……他们不信任虚构的故事表示他们相信小说不能仅当作艺术品而存在:不论怎样伪装上寓言的外衣,它们只可当作真情实事,才有存在的价值。它们得负起像史书一样化民成俗的责任。”〔6〕
其实,不唯小说传奇,即使对叙事诗的评价也依这一把“历史”的尺子。比如有关杜甫的评价,孟綮《本事诗·高逸》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另为‘诗史’”。宋祁《新唐书·杜甫传赞》云:“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糜相矜……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旧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杜甫之为“诗圣”而高过“诗仙”李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杜甫史笔之沉郁真切。
相较而言,西方文学叙事理论则是另一路数。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史之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区分是借助于哲学之参照来进行的。在亚氏眼中,史离哲学(关于一般理念的知识)很远,它是关于个别事物的记录;诗离哲学很近,它是关于一般事物的“准知识”。因此诗比史更有“哲学意味”。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是“依哲论诗”的。
“依哲论诗”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主要生发出后世的古典主义诗学,这种诗学在根本上以哲学为“诗性叙事”的参照和样本,诗之为诗就必须像哲学那样去叙述有关一般理念的真理或知识,不能像历史那样去叙述个别偶然的事物,更不能虚构怪异和非理性的事物。
贺拉斯在《诗艺》开篇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画家作了这样一幅画像:上面是个美女的头,长在马颈上,四肢是由各种动物的肢体拼凑起来的,四肢上又覆盖着各色羽毛,下面长着一条又黑又丑的鱼尾巴,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缘看见这幅图画能不捧腹大笑么?皮索阿,请你们相信我有的书就像这种画,书中的形象犹如惊人的梦魇,是胡乱构成的,头和脚可以属于不同的族类”。〔7〕贺拉斯觉得这样一幅画可笑是因为画面事物的各组成部分“属于不同的族类”。所谓“族类”正是个别与事物的“类一般”,这“类一般”规定着个别自然机体的类别部分及构成秩序,画面构图只能根据这种个别与一般的归属关系来进行,不然就违反了“必然律”和“可然律”,就是“胡乱构成的”,就是“可笑的”。在谈到人物的性格描写时,贺拉斯谆谆教诲要注意“不同的年龄的习性……不要把青年写成个老人的性格,也不要把儿童写成个成年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永远坚定不移地把年龄和特点恰当配合起来。”〔8〕,在此,年龄是一个“类一般”的标志,它不仅是检验某年龄阶段的人物是否写得合适的尺度,也是通过写某年龄阶段的个人而必须揭示的东西。对于古典主义者来说,个别只是一般的例证,写个别是手段,揭示一般才是目的。
十分显然、西方古典主义这种“类型说”理论正是“以哲论诗”的产物,它将文学叙事引向所谓“普遍事物”的模仿;相反,中国古人“以史论文”的思路则将文学叙事引向所谓“个别事物”的实录。从中西文学叙事理论的建构可见各自传统文化的最深层的价值座标。不用说,古代中国最高的文化样式是“史”,古代西方最高的文化样式是“哲”。因此,在中国,别的文化样式必得近于“史”,模拟“史”、追求“历史旨趣”才有价值;在西方,别的文化样式必得靠近“哲”,追随“哲”,获得“哲学意味”才受人敬仰。
不过,在“依史论文”和“依哲论文”的逻辑终端,“文”都难免不被“史”和“哲”所消融或排斥。因为文毕竟不是史,也不是哲,较之史与哲它终归等而下之。
其实,文学叙事的实质既非史之“实录”,亦非哲学之“真理”,要确立独立的文学叙事理论只有摆脱史论和哲学的学科性束缚才有可能,事实上,中西文学叙事理论正是从寄生于史与哲到摆脱史与哲的限制中确立起来的。
文学叙事:文与事
有意思的是、中西文学叙事理论在摆脱史学和哲学眼界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路。中国文学叙事理论借助一种“哲思”摆脱了“史论”的限制,却陷入了类似于西方早期叙事理论的泥坑;西方文学叙事理论借助一种“史论”摆脱了“哲学”的束缚,又走上了一条靠近中国早期叙事理论的道路,并且双方都主要以小说理论的样式出现。
具体而言,中国小说叙事理论之所以能偏离历史叙事理论主要借助了“理与事”这对范畴,这对范畴颇类似于西方之“一般和个别”这对哲学范畴。
脂砚斋在《石头记》第二十九回有段批语曰:“清虚观,贾母,凤姐本意大适意大快乐,偏写出多少小不适意的事来,此变天然至情至理,必有之事。”(庚辰本)第二回写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脂批曰:“官制半遵古名亦好,余最喜此等地有半无,半古半今,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极幻极玄,荒唐不经之处”(甲戌本眉批)。所谓“事之所无,理之必有”指的正是小说所叙之事的特点,这种事虽不是已有之“实”事,但必是合理之“真”事。在此,“事”被一分为二了,已有之实事是个别已然之事,它是史传叙述的对象;合理之真事是普遍必然可然之事,它是小说叙述的对象。为此,小说有理由虚构,只要它依理顺情,造必有之事就行。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它使文学之叙事有别于史传叙事而别开一面。
显然,这一区分与亚里士多德的理由大体相似,虽然脂砚斋并未明言什么哲学但暗含一种哲思。正是凭借这种仍嫌朦胧的哲思,小说叙事才得以为其非史之虚构辩护。
有趣的是,当中国的小说叙事理论借助于一种朦胧哲思力图摆脱史论之约束时,西方的小说叙事理论却借助于一种史论来摆脱哲思之束缚。在西方文学中,小说(novel)是一种在18世纪后期才正式定名的文学形式,它因其特定的历史内涵而区别于前此的准小说样式“散文虚构故事”(fiction)。伊恩·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小说兴起于现代,这个现代的总体理性方向凭其对一般概念的抵制一—或者至少是意图实现的抵制——与其古典的,中世纪的传统极其明确地区分开来。”〔9〕在瓦特看来,兴起于18世纪英国的“小说”确立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传统的现实观。在传统文论中,真正的“现实”是那种普遍性的、类别性的、抽象性的事物,而18世纪的小说家则认为“现实”是特殊的、具体的、个别的事物。
瓦特将18世纪的小说对个别事物的表达技巧概括为人物个性的塑造和环境的详细展示。在人物个性化描写方面,瓦特仔细分析了18世纪小说给人物“取名”的问题。瓦特指出:“古代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观念与其文学实践相符合,偏爱的都是历史的或类型化的名称。”〔10〕而18世纪的小说家对传统进行了极有意义的突破,“他们为他们的人物取名的方式,暗示那些人物应该被看成是当代社会环境中特殊的个人。”〔11〕“它所应象征的是,人物被看作了一个特殊的个人,而不是一种类型。”〔12〕“从逻辑上讲,个人的特殊问题是与专有名称在认识论上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的,因为,用霍布斯的话说,‘专有名称只能使人想起一件事情;而全称命题却使人想起许多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专有名称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同样的作用,它们是每一个体的人的特殊性的字面表达形式。但是,在文学上,专有名称的这种作用是在小说中最先得到充分确认的。”〔13〕
瓦特指出:对特殊环境的具体描述也是基于抵制一般化而追求个别化表达的需要。他认为早期的虚构故事出于对一般普遍性事物的迷恋而不在意事物存在的时空性,“事件的先后顺序被设计在一个非常抽象的时空连续统一体中。”〔14〕柯勒律治就曾指出斯宾塞的“《仙后》中奇异的独特性和准确的想象完全缺乏特定的地点时间。”〔15〕瓦特说:“洛克所承认的‘个体化的原理’,是时空中某一特殊点上的存在。正像他写的那样,因为‘如果把理念从时空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它就变成了一般性的东西,’因此,只有时空环境都是特殊的,理念也才是特殊的。同样,只有小说中的人物被置于某种特殊时空的背景之中,他们才是个性化的。”〔16〕瓦特认为笛福是第一位使其全部事件的叙述具体化到如同发生在一个实际存在的真实环境中的作家。为此,瓦特说18世纪的小说“向我们展开了一种发展的,而且是意外的,特定的个人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获得的特定经验的聚合体。”〔17〕如此之小说正如时人评论笛福的小说所言:“像在法院宣读证词。”
作为“证词”的小说是“信史”,作为“信史”小说才是有价值的。华莱士·马丁在《当代叙事学》中指出,“绝大多数的十七、十八世纪作者都或明或暗地否认他们在写小说或传奇。他们为自己的作品加上‘历史’,‘传记’,‘回忆录’等等名称,以便将自己从小说传奇的无聊的、空想的、未必然的、有时甚至不道德的那些方面开脱出来。‘这并不是一部小说/传奇/故事’这类说法经常以各类形式出现于前言之内。理查逊说《克拉丽莎》不是‘一部轻浮的小说,也不是一部昙花一现的传奇,’而是‘一部生活与社会风俗的历史。’”〔18〕以历史论小说的风尚在巴尔扎克那里表现得最突出,他那句尽人皆知的名言是“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学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19〕”。而直到享利·詹姆斯还坚信小说家必须“视自己为历史学家,视自己的叙事为历史。”〔20〕
如此看来,西方18世纪以来的小说观念离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越来越远,离中国古代的叙事理论越来越近了。不过,无论是西方小说理论在一种史论意识中使小说离开哲学而靠近历史,还是中国小说理论在一种朦胧的哲思中使小说离开历史而靠近哲学,小说都还未在理论意识中真正独立起来。
因为文学叙事的本质特征在根本上并不取决于文学叙“一般之事”还是“个别之事”, 而是取决于文学为何叙事,“事”与“文”的关系如何?是从“事”出发设定“文”呢?还是从“文”出发去理解“事”?简单地说,文学叙事的突出特征是为自身的目的而“造事”或“生事”,“事”是“文生之事”、“文内之事”。文学叙事的“自我目的性”是其本质。故而倒是金圣叹一语道破了天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为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说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21〕金圣叹的“文”当指叙事“艺术”,或叙事之“叙”。简言之,史书为事而文,小说为文而事。在金圣叹的叙事学说中,我们首次看到一种根本的颠倒,在他那里,文学叙事理论不再是变相的“事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论”。
将叙事之“事”作为展示叙事之“叙”的手段也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叙事理论的观点之一。什克洛夫斯基就认为,对文学而言,叙事之事也是“形式”因素之一,是“叙”之艺术的结构性成分,只有通过研究语言和艺术结构的成规,才能理解何以这事而非那事,什克洛夫斯基这一思路被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所发展,叙事之“事”最终被看成是“叙”出来的,是“叙”的产物,是永远不可能与“本事”重合的“事”。
华莱士·马丁指出,传统叙事理论对小说的非难主要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知识信念,即认为语词可以准确无误地对应于客观事物,哲学和历史都自以为可以达到这种“准确无误”而获得“真理”。“在这一语境中,‘小说’意味着词与物之间的错误联系,或者是对不存在之物的言及……更晚近的哲学家们已经不把真理设想为陈述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而把它设想为语言运用中包含的种种成规的一个衍生物。陈述一个真实的命题最终只是言语的一次运用”。〔22〕
“更晚近的哲学家”显然是指J.L.奥斯丁这样一些哲学家。奥斯丁在《论言语有所为》一书中提出一种“言语行为”理论,这种理论的关注重心不再是“言语说出了什么?”“什么存在着?”“什么是真实的?”而是“怎样言说才有意义?”“我们通过运用它们实现了什么?”“哪些成规决定着它们的使用?”从奥斯丁提问的角度可见小说的问题不能在“语词和事物”的关系中提出,而只能在“语词和语词”的关系中提出。就此之见,小说对语词的运用不是为了直接叙述事物以达到实际行动的目的,它只是以语词模拟日常语词的运用以达到非实际行动的目的。因此,对小说而言无所谓虚实真伪的问题。
受奥斯丁影响的理查德·奥曼就认为戏剧是以语词模仿日常言谈,为此他说:“文学作品是悬置了通常的言内规则的话语,是没有通常结果或影响的行为……作者制造模仿的言语行为,但让它们好像是正在被某人所做的行为。”〔23〕受奥斯丁影响的巴巴拉·赫恩斯坦·史密斯则认为小说是以语词模仿史传的言说,为此她说:“小说的本质上的虚构性不应在被提及的人物、事物、事件的非实在性中寻找,而应在提及行为本身的非实在性中寻找。”〔24〕
在这些批评家看来语词与事物的关系不是文学语用的关系域而只是日常语用的关系域,文学语用的关系域在语词与语词之间,在此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学言说“真的”说出了什么,而是它是否真像日常语言那样表达着。简言之,这些批评家把文学表达看作是日常表达而非对事物本身的模仿。值得注意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的看法与此相反,他们认为文学表达不是对日常表达的仿拟而是对此的“陌生化”或“歪曲”,不过,他们与上述批评家一样都把文学表达看作与日常表达的关系而不是与事物本身的关系。
从文学表达与事物本身的关系入手来看待文学叙事并以此为基础为文学叙事辩护,在理查德·罗蒂看来一开始就错了。因为它源于这样一个哲学传统,“这个传统一直致力于保证真与伪、现实与想象/虚构之间的区别坚固可靠。这一传统本身就是一个在有关概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顽固信守一种模仿图画观的传统。与其让自己屈从于这种观点或与之正面战斗,罗蒂建议我们不如干脆忘掉它。我们以各式各样的方式运用语言;只要我们在谈论电子、社会习俗、小说或历史时相互理解,实现了我们的目的,那么,为下述事实——夏洛克·福尔摩斯在一种意义上存在着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又确实不存在——大绞脑汁就毫无意义,而且事实上也是很奇怪的。如果我们完全接受下述观念,即词语的意义取决于它们如何被使用,那么剩下来的唯一问题……将是有关组成我们的话语的种种不同的语言游戏中所包含的成规的问题。”〔25〕
当这样一种思路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语言理论中被推向极端之后,文学表达的问题不仅被看成与事物本身无关的问题,也被看成一个与日常表达无关的问题,它成了一个自足性的语言结构问题,即纯粹的语词与语词间的关系问题,或文本与文本间的关系问题。
正是从以“事”为中心对文学叙事理论的阐述到以“叙”为中心对文学叙事理论的阐述,标志着文学叙事理论的“现代转向”。此一转向虽然也萌发在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之中,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而流失;相反,西方文学叙事理论因倚靠20世纪现代语言理论的充分发展而完成了此一转向。
作为文学叙事的历史与哲学
没料到,转向后的西方叙事理论竟导致了这一结论:历史叙事和哲学叙事在本质上都是文学叙事,这真是一种历史性的反讽,因为中西传统文学叙事理论都在勉力将文学叙事说成是历史或哲学,以此为文学叙事的合法性存在辩护。
我们知道,叙事理论的现代转向之所以可能,主要基于“事”(本事)的悬置,即不再相信任何叙事能说出本事。叙事之事并不在叙之先而是在叙之后,是叙之结构性产物。这一原则不仅对文学叙事有效,对历史叙事和哲学叙事也如此。说历史叙事和哲学叙事在本质上是文学叙事,就因为文学叙事明显地体现了上述叙事原则,因此,事情发生了倒转,不是文学叙事要凭哲学和历史来理解,而是相反。
在谈到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的关系时华莱士·马丁先分析了两者的种种不同,然后说:“尽管上述种种不同,但两种叙述者面对同样的问题:阐明一个时间系列的开始的局面怎样导致该时间系列终端的不同局面。能否确认这样一个系列呢,这首先有赖于下列先决条件,如阿瑟·丹托和海登·怀特所阐明的那样:(1)被牵涉的事件必须全部与某一主体有关,如一个人,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2)它们也必须在与某种人的利益的关系中统一起来,这一利益将说明为什么;(3)这一时间系列必然始于和终于它开始和终结的地方。给定这些条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的任务就开始显得类似起来。”〔26〕
在《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现象》一书中,海登·怀特认为历史文本作为一种话语样式涉及三大要素:素材、理念和叙述结构。历史叙事总是以一定的理念去解释素材,并总是将这一切安排在一个语言叙述结构之中。历史叙事的深层动机是以话语叙事的“自然性”来对应性地表述历史事实,让历史事实在语言序列上看起来就像是那么回事。但怀特指出在这种历史文本制造的表象之下有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这个结构从本质上看是“诗性的”和“语言性的”。所谓“诗性的”是说历史文本在根本上基于“想象”,所谓“语言性的”是说历史文本中的事物之秩序在根本上基于语词之秩序并依存于语词的解释。此外,怀特还指出,历史著作总是体现出一些文学性的情节(喜剧的、悲剧的、传奇的、讽刺的),这些情节的秩序与其说基于一种认识论立场不如说基于某种美学和伦理立场。在《话语之诸比喻》一书中,怀特还进一步分析了历史话语的比喻性。据此,怀特认为历史在本质上是一种话语虚构,因而与小说没有什么两样。
“文史不分家”本系中国传统,但所谓文史不分在中国传统中大都是以史观文的,真正对史之诗心剖析较深者大约还是今人钱钟书先生。
在《管锥编》中,钱先生如此写道:“虽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大事书策,小事书简,亦只谓君廷公府尔。初未闻私家置左右史,燕居退食,有珥笔者鬼瞰狐听于傍也。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警咳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心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27〕钱先生将之概括为“史有诗心、文心之证”。遗憾的是,钱先生的洞见仍只是一种学术性直觉经验之谈。其后有杨周翰先生《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一作为文学的历史叙事》一文开始借鉴现代西方叙事理论来谈历史叙述的文学性问题,虽言简而意赅,但终因孤掌难鸣而未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深入的讨论与思考。
将哲学叙事还原为文学叙事是20世纪最有启发性的思想成果之。在西方传统中,哲学作叙事常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文学无论怎样巴结和依附于哲学都无济无事,因为在哲学看来,文学无论怎样努力都摆脱不了它自身语言的缺陷,这种缺陷就是文学语言本质上的隐喻性和非指称性。哲学以为唯有哲学所使用的纯逻辑化的指称性语言才能充分表达真理,因此,唯哲学是有关真理的叙事而文学则是一种修辞性叙事,它最多只能审美而不能表达真理。
对这一古老的偏见予以致命打击的是德里达。德里达在70年AI写作了一篇著名的论文《白色的神话》,副标题就是:“哲学文本中的隐喻”。在德里达看来,“隐喻”并不是哲学用来辅助性地说明某些慨念以加强概念指称性的可有可无的工具,隐喻就是哲学话语的深层结构。不管哲学在表面上将隐喻清洗到何等程度,哲学表达的基本结构都只能是隐喻性的,因为任何抽象的观念表达都以潜在的类推和类比为基础,并且一些基础性的哲学语词,诸如“理论”、“理式”和“逻各斯”等都有其古老的隐喻来源,并作为隐喻在哲学表达中起作用。在此意义上,哲学话语就是文学话语,不同仅在于,文学是一在于,文学是一种明目张胆的隐喻性神话,哲学则是一种遮遮掩掩的隐喻性神话;文学是一种具有自知之明的神话,哲学则相反。德里达将这种隐喻性的哲学神话名之为“白色的神话”。所谓“白色的神话”是说哲学这种隐喻神话是用隐形的白色墨水写成的神话,它隐蔽在哲学文本之中,通常难以看出,但稍许细察就可以看破天机。,
为此,乔纳森·卡勒说:“哲学依赖于比喻,使之成为文学,即使当它们标榜同比喻的对立来界定自身时也如此”。“哲学因而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28〕德里达称之为“原型文学”。
在本文行将终结的时候,我以为开头所引弗莱的那段话似乎该颠倒过来了:文学位于人文学科之中,其一侧是历史,另一侧是哲学。由于文学最充分地体现了言语的本性和语言运用之成规,文学成为历史和哲学重新认识自身的基本参照。于是事情发生了倒转:不是文学凭借历史和哲学来理解自身,而是历史和哲学凭借文学来发现自身的真理。
“反者,道之动”。〔29〕
诚哉斯言!
注释:
〔1〕N·弗莱N批评的剖析》,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7年,第12页。
〔2〕《尚书·尧典》,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页。
〔3〕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78年,第65页。
〔4〕班固《汉书·艺文志》,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141页。
〔5〕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28—29页。
〔6〕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导论》,见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6页。
〔7〕〔8〕贺拉斯《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37、146页。
〔9〕〔10〕〔11〕〔12〕〔13〕〔14〕〔16〕〔17〕 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第4、12、13、14、12、18、15、26页。
〔15〕见波特编《作品选》,伦敦,1993年,第333页。
〔18〕〔20〕〔22〕〔23〕〔24〕〔25〕〔26〕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第4、12、13、14、12、18、15、26页。
〔19〕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序》,见段宝林编《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300页。
〔21〕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见(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三册,第245页。
〔27〕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84年,第164—166页。
〔28〕乔纳森·卡勒《论解构),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第120页。
〔29〕老子《道德经 四十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