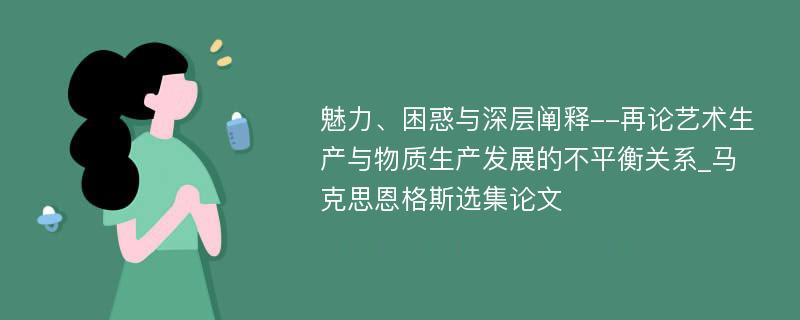
魅力、困惑与深层解读——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再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衡论文,困惑论文,物质论文,魅力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论题的导入
马克思主义美学区别于他种美学体系的质的规定性是:隶属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受制约于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这一始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见著于《共产党宣言》,最终以严密的科学逻辑体系确立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典思想,成为我们研究美学、文艺学的性质与意义的理论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谁若漠视马克思这一论断,或颠倒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谁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信奉者。
但马克思并非孤立地考察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两者的关系。他强调:“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即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点上,从特殊的历史形式中,来考察物质生产活动。如若“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18世纪法国人的幻想。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伏尔泰写《亨利亚特》之所以成为莱辛嘲笑的对象,原因就在于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的、历史地发展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例如没有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6页。)这一历史形式,而仅从18世纪科技生产力超越古希腊时代这一简单的生产形态对比、类推,产生以新的史诗《亨利亚特》代替《伊利亚特》的“幻想”。在马克思看来,伏尔泰的失误是来自简单化的经济决定论的“庸俗的见解”。
脱离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关系的庸俗经济决定论,曾一度风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以至使晚年的恩格斯不得不在他的多封通信中力图扭转这一偏误。例如,1890年,他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写道:“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经济因素决非“历史过程”的唯一决定性的因素,不能简单、机械地在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之间划上等号,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逻辑所论定的。由此,我们方可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会在确立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制约的基点上,又从另一侧向提出了“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的论题。(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而对于这一论题的研究,则涉及到美学、文艺学研究中的方法论等根本问题,从而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二 已有的三种看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2页。)对此,国内学术界(特别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美学教学领域)较有代表性的解读有如下三种。
第一种认为,“马克思探讨这一问题,目的还是要指出艺术最终必然受物质生产的制约”,“马克思强调的是,艺术的一定繁荣期能创造出一种对后人说来高不可及的艺术形式,可当时的物质生产较之以后可能相当落后,待到后来社会物质生产水平提高了,整个艺术生产也前进了,那种划时代的、古典的艺术形式反而创造不出来了。”(注:董学文:《马克思与美学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这种看法仍把“不平衡性”问题归结于单一的物质生产的制约。其论证逻辑是,一定物质生产水平上只能产生与其相适应的艺术形式(其中包括一些对后人来说是高不可及的);当物质生产水平变化了,那些艺术形式再也无法创造出来了。如随着火药、铅弹、活字盘、印刷机这些现代器械的出现,代替了弓箭、刀枪及口头语言的传达等,产生古代歌谣、传说、史诗等必要条件便消失了,这些艺术形式也就渐之消亡。在这个向度上,论者是对的。但正如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论者没有对马克思所强调的“困难”作出正面的回答,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其论析的不完满。
第二种看法侧重于从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来分析“不平衡性”问题。他们主张社会结构系统由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四个层次构成,这四个层次从不同侧面、以“合力”形式作用于艺术,由于各种作用力不均等,便出现不平衡的状态。而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是必然的,是规律;其二者不相适应,是偶然的,是现象。因此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也属于偶然的现象。“相适应的内在本质,不平衡的表现形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一般发展’的不平衡观,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艺术发展论。”(注:陆贵山、周忠厚:《马列文论导读》,作家出版社1991年版,第307页。)这种看法,虽然论析的途径不同,但得出的结论与第一种是相近的。即“不平衡性”属于现象、表现形式,是偶然的,它归根结底仍服从于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一必然的规律。同样,他们也回避了这一论题的关键点——对马克思强调的“困难”问题的解答。
第三种看法正面触及了马克思提出的“困难”问题。他们这样分析:“古代希腊艺术何以会具有不朽的魅力?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作了科学的回答:因为希腊艺术再现了人类童年的‘真实’。”但对这一“真实”的概念内涵,论者把它转化成“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文学的魅力也在于‘真实’。希腊艺术把人类童年的真实生动地再现出来了,这就是它具有永久魅力的根本原因。”(注:纪怀民等:《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7页。)这里便出现一个逻辑推演过程的间隔,文艺理论范畴中的“真实性”内涵能否类同于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上人类童年时代的“真实”呢?因为在文艺领域中,像左拉之类的自然主义的“真实”未必能使其作品产生不朽的魅力。
可以看出,以上的三种解读各有其合理的地方,但也都有其不尽完善之处。
三、论题的再解答
那么,该如何分析马克思提出的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呢?如何解答马克思作为实例提出的古希腊艺术何以会显出永久魅力的问题呢?笔者认为,除了上述的三种解读之外,以下两个方面的探讨,将会有助于本课题研究的进展。现提出求教于学界的同行,企盼使问题得到更完满的答案。
1.“一般的表述”与“‘特殊性’的确定”。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
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末,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既然马克思把矛盾的焦点缩压到“一般的表述”这一问题上来,那么其内涵是什么呢?这必须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文的语境中加以论定。在《导言》“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部分,马克思区分了两种生产的概念,一种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一种是“生产一般”。前者的概念已明确;对于后者,马克思强调指出:“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7~88页。)这就是说,我们对包括精神生产在内的“生产”的考察,可以从两个层面上入手,一是特殊历史阶段的生产,它是具体、明确的,例如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生产。所以马克思说:“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指的就是这种特殊阶段的精神生产,它容易得到明晰的解释。另一层面是“生产一般”,即“抽象”的生产,马克思阐释道:“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8页。)这种包括精神生产在内的“生产一般”、生产的“抽象”,它有多种超越“特殊”的形态,其最高度的抽象是“属于一切时代”。我觉得马克思这一提法尤为重要,他告知我们,对物质生产和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的考察,人们应该从两个向度进行。把它们纳入一定的特殊的社会阶段考察,人们已习以为常了;但从“属于一切时代”这一“抽象”、“一般”的向度着眼,人们却似乎是忽略了,特别是庸俗的经济决定论者,更是如此。因而,若从“生产一般”这一思维向度出发,马克思论析希腊艺术和史诗时所作的评价:“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它属于“发展得最完美的”、“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就不难理解了。显然,马克思是从“属于一切时代”、作为人类整体的族类“一般”性来看待希腊艺术和史诗的。它属于人类的美好童年时代的作品,这已超越了具体的、阶段性的、特殊的社会形态范围。
对精神生产这两个向度的考察,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也能找到类似的范例。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注:刘勰:《文心雕龙》,《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83~285页。)每一时代、朝政的治乱盛衰的交替,促使着文学产生重质或重文的变化;文学的变化受一定的社会风气的薰染,文学的盛衰和一定的时代动向相联系。显然,刘勰对文学发展的考察,属于马克思所说的,纳入“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特殊性”的范围内论析。但钱钟书的考察就不同了。《谈艺录》开篇“诗分唐宋”章曰:“余窃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注: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与刘勰相反,钱钟书认为文学的发展不必尽与特殊的社会阶段,与具体的朝政治乱盛衰相吻合,它有着本身的审美自律,即文学艺术是“属于一切时代”的,是人这一族类的“一般”本性、“一般”的精神所外化的对应物。像以丰神情韵擅长的唐诗,是人类处于“少年才气发扬”时的精神对应产品。这与马克思把古希腊艺术和史诗论定为人类“一般”本性“发展最完美”时的“正常的儿童”——古希腊人的精神对应产品,有着惊人的一致。由此,笔者认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学体系,就应当在内在的思维向度上,把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古典美学联系起来考察,方能使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
2.“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
马克思在《导言》中,以希腊艺术和史诗为例,说明它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符合物质生产对精神生产、经济基础对意识形态的制约这一“平衡”原理;但另一方面,它又超越“一定社会发展形式”,越过两千多年的时空,“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个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形成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其原因何在呢?马克思紧接着作了以下的具体论析: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自己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为什么马克思会以“儿童”以比喻希腊人呢?其“儿童的天性”中的“真实”、“天真”、“纯真”、“固有的性格”等的内在涵义又是什么呢?这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回到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的理论前提——德国古典美学的语境中去寻找。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对《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等观念)产生巨大影响的席勒美学就曾在类似的语境中使用过这一比喻。席勒主张,人有着一种自然本性,即处在自然状态的人性,例如对着自然风景、儿童等,他都会产生一种喜爱的感情。因为“这些对象就是一种意象,代表着我们的失去的童年,这种童年对于我们永远是最可爱的”(注:席勒:《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页。)。但在现代文明中,国家机器的等级和职业区分,科技理性及劳动分工的片面宰割,使人变成“碎片”、“异已”的存在,即“异化”的存在。因此,“我们的童年是在文明所造成的人性中保存着的、完整的、未被玷污与肢解的自然。”(注:转引自毛崇杰《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0页。)在《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席勒还写道:人是“自然”时所表现的人性就是素朴。素朴作为人的本性,历史范本就是古代人——希腊人;在现实中的范本就是儿童。现代人只有在童年时代才是素朴的,历史上只有希腊人才是素朴的。因为“希腊人没有失去人性中的自然”(注:转引自毛崇杰《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页。)。与席勒同时代的美学家让·保尔在他的《美学入门》中也写道:“像故去的伟人一样,希腊人在我们心目中也显得神圣与高尚。他们对我们必然产生比对他们自己更强烈的影响;因为使我们倾慕的不单是他们的诗,还有诗人本身;因为一个孩子的天真纯朴不会对另一个孩子有魅力,而只能使已经失去了童年的人着迷;因为当代文化的酷暑造成树叶萎缩,这就正好使我们能比希腊人自己更清楚地看清他们那孕育着累累硕果的一个个花蕾。”(注:让·保尔:《美学入门》,转引自《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可以看出,把希腊人比喻成未被沾污的、自然的、素朴的、天真纯朴的、令人倾慕的人类“童年”,是德国古典美学语境中较常用的例子。显然,马克思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的比喻源自这一历史语境,其间的脉胳贯连、意蕴延续是明晰的。
那么,作为“人类童年”的古代希腊人为什么会令人倾慕呢?马克思从人类的历史发展进程考察。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论析到这个问题:“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6页。)也就是说,就人类生产活动的目的性而言,古代是以肯定人的自由自觉的内在本质为目的;现代却以积敛财富为目的,人反而变成了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因此,在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6页。)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内在本质,在以积敛财富为目的的现代世界中,即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已普遍“物化”了,全面“异化”了,他已牺性了自己的目的本身。在这种“一般”的人性、人的本质的历史考察中,当异化的现代人性和素朴的古代人性两相对照时,自然就显出以希腊人为代表的人类“儿童”阶段的“天真”、“真实”、“纯真”等“天性”的美好,它“使成人感到愉快”,甚至感到“崇高”。就像席勒在《美育书简》“第六封信”中所描写的那样:古代希腊人“既有丰满的形式,又有丰富的内容;既能从事哲学思考,又能创作艺术;既温柔又充满力量。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想象的青年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的人性。”(注:席勒:《美育书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9页。)其人性中对立面构成了和谐完美的统一体,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希腊人有如“正常的儿童”的内涵所在。若依此类推,在民族苦难中创造出不朽的人类精神的经典——《圣经》的希伯来人,则应称之为“早熟的儿童”;而那些处在荒僻地域的、未开化的原始部族,则又可以称之为“粗野的儿童”。
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在“生产一般”的向度上,它又是人的精神对应化的产品。因此,人类发展得最完善的童年时代——古希腊人,其艺术和史诗便产生了“永久的魅力”,它实际上也是人类对自身的“永不复返”的美好阶段的追忆和怀念。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家厄恩斯特·斐舍尔论析道:“重要的是,马克思把一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的受时代限制的艺术看为人类的一个要素,并认识到正因为这样,这种艺术才能超出历史的瞬间而继续起作用,才能显示出永恒的魅力,即使受时代限制的艺术还是反映人类的一些永恒不变的特征。”(注:转引自柏拉威尔《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89页。)他所提及的“人类的一个要素”、“人类的一些永恒不变的特征”,和前述马克思所论析的“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抽出来的共同点”,即“一般”的人的族类本质特性,内涵是相近的。也就是说,除了从一定的社会发展形式、物质生产状态这一向度,来观察古希腊文学艺术之外,我们还可以同时从“生产一般”、“一般的表述”这另一向度来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全面地理解古希腊文学术作品所具有的超越历史时空的永久魅力,及其所包含的人文精神的永恒之美。
标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政治经济学批判论文; 艺术论文; 西方美学史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希腊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