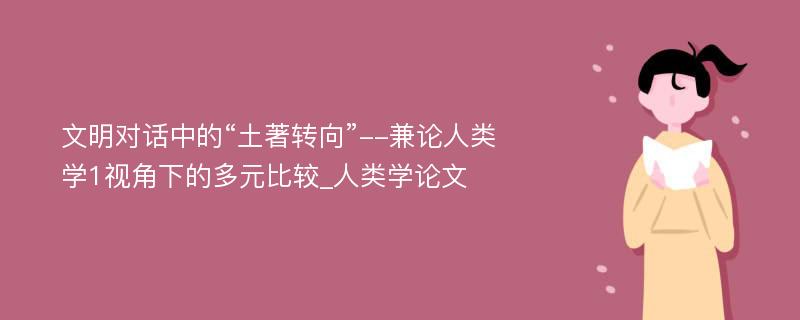
文明对话中的“原住民转向”——兼论人类学视角中的多元比较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原住民论文,视角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平、发展以及如何与自然长久共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如何诠释并解决却众说纷纭,思路万千。进入现代化时代以来,主流的思想界大多把关注点集中于被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文明”②圈里的精英层面,企图从中找寻能普世适用的终极关怀或一劳永逸的最后斗争与历史终结。在这种单面向的过程中,“西方中心论”起了主导作用,以至使人们要么一味地追求价值和路径的一致性,无视人类存在的多元、多样从而纠缠于对话语霸权的争夺和掌控;要么不断地彼此攻击,相互贬损,把人类社会的联系推向支离破碎、不共戴天。
面对这样的困境,如何克服既有范式的局限,走出精英话语的阴影就成为世人不得不深思的议题。本文结合在不同地区和族群间开展“文明对话”的讨论,围绕“原住民知识”的时代意义展开,目的即在于为打破上述僵局而强调一种新的资源与途径。通过对新儒家学者的关注与原住民对话的事例分析,可以看到这种新途径在实践中的尝试。笔者把这样的实践视为文明对话中的“原住民转向”。其意味着以往被忽视的原住民不仅在政治上得到尊重,而且开始作为一种人类珍贵知识的载体和传承者,加入到全球的多元对话之中。
当今世界的不同力量和价值资源
自1980年代中期起,在为“儒学第三期”坚韧开拓的努力中,杜维明先生一再呼吁要开展全球性“文明对话”,并逐步强调对话的成员应当包括原住民文化——因为在原住民文化中,蕴藏着反思现代性弊端的源头活水。由此之故,在1990年于“夏威夷东西中心”筹办具体的对话项目时,杜先生特别指出,文明对话的重点之一就是发掘并整合非启蒙范式的人类资源,亦即“探讨轴心时代的精神传统和本土宗教之间健康互动的可能”。谈到个人的切身感受,杜先生还举例说明在和夏威夷的原住民首领(多半是女性)进行持续而多样的沟通中,通过她们的“诵诗、舞艺、祭歌和礼仪”等生活细节,获得了最大的启发。③
多年来,迫于“文明冲突”在理论和实际方面的压力,人们越来越重视并参与到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之中;然而相当多的人却忽略了其中理应包含的原住民成员,不习惯也不理解“文明”之中为何包括原住民,感受不到与之对话的重要和紧迫。
结合对发展陷阱、生态危机及国家冲突等相关现象的考虑,我认为杜维明等吸纳原住民文化的呼吁和整合具有突破性价值,意味着对既有以西方现代性为中心之知识构架的挑战,在超越“科学主义”、“经济主义”及“国家主义”等现代取向的前提下重构了当今人类思想谱系的新划分和新可能,同时也为原住民文化的传承及研究提供了与外部兼容的新思路和新空间。
按照杜先生的解释,影响当今世界的力量主要有两种,一是globalization,一是localization。前者的含义可以理解为全球、一体和扩张、变异的,代表着“现代”。后者则是本土、多样和自在、根源的等,也可称为“寻根”(search for roots)。此两种力量各有资源。globalization主要出自西方的启蒙理性和科技现代化,localization则包括了中国、印度、阿拉伯等众多非西方的“轴心传统”以及美洲“印第安”、大洋洲“毛利人”和夏威夷“土著”等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文化。④这样的观点不但使原住民文化得以作为受尊重的成员与其他“轴心传统”平等并置,而且有助于打破数百年来在“进化论”影响下对人类世界所做的文明与野蛮之分,继而在“复数文明”的基础上重新看待人类价值的多元性。⑤
接下来需要讨论的话题便有很多,比如:谁是原住民?他/她们在历史和当下的状况如何?若要与之对话,怎样的方法和语境才能促成?
“原住民”含义及其内外表述
对于汉语表述而言,“原住民”是一个外来的现代用语。其对应着西语的indigenous一词,在不同的文本里也被译为“土著”、“土人”或“原著民”等。Indigenous词根indigen的主要含义是指土生、本地、固有等,与外来、移植、引进等相区别。在用指人群时,indigenous的意图在于一种分别,即以生长和居住地的来源为准区分内和外。对于被数世纪以来一波又一波殖民化浪潮深刻改变了的人类格局来说,这种区分的突出作用在于强调殖民者与殖民地的关联和差异。也就是说,“原住民”其实是一个两边看的相对概念:对于通过地理“大发现”而向全球扩张的殖民者而言,世界上所有被征服与待征服地的人群都是Indigenous;而在后者的眼光里,他/她们始终是自己故土的世居者和主人,而殖民者们则是外来者、异己和陌生的人群。
在早期,由于受进化论等影响,西方“原住民”概念的使用带有把殖民地人群视为“落后”、“野蛮”的显著贬义。Indigene一词虽然也指“土著”、“当地”,实际上是以殖民者自我为本位,把殖民地当作外地、远方或异邦来看待的。因此所谓“原住民”就几乎与“原始”(primitive)或“蒙昧”(obscuration)相等同,意味着比殖民者低一等、无文化,是文明的对立面。直到进入后殖民时代,在“民权运动”、“多元主义”及“身份政治”等潮流的冲击下,原有的殖民本位观点才发生改变,“原住民”概念也才逐渐获得以当地世居人群为主体的新转向。只有在这样的转向里,作为文明多样性之地方性传统的体现,分布于全球各地的“原住民知识”亦才有可能被当作人类文化整体系统中不可分割的共同财富而受到敬重和珍惜。
自20世纪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把目光投向原住民及其文化传统。相关的论述与实践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对“原住民”含义及特性的界定也处在不断的修整之中。总体说来,这些不同论述可大致分为两类,即来自外部的看法和原住民的内部认知。比如,在一些影响广泛的国际组织里,这种外部表述如下:
“原住民”,也称“土著少数民族”(indigenous ethnic minorities)或“部落人”(tribal groups),指的是拥有与主流社会不同之社会及文化身份的人群。这些群体每每因其独特的身份而在发展过程中处于弱势而且易于受到伤害。
在此类表述中,“原住民”还被列举出如下特征:
1.拥有世代传承的土地和自然资源;
2.自认和被视为独立的文化群体;
3.拥有自己的“土话”,其通常区别于流行的“国语”;
4.包含有习惯的社会与政治结构;
5.保持着较为原初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⑥
根据这样的界定和区分,即便在日日变异、文化流失的当代世界,全球“原住民”的总数据统计也仍有3亿多。其中包括数量为5000之众的族群,分布在70多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⑦
与此同时,来自原住民内部的表述则把自身强调为地球母亲的儿女。他/她们与大地和自然同在,虽然正因外部强力的冲击而陷于困境,却仍不懈地为生存权利和传统继承以及环境保护等奋起抗争。1992年,危地马拉的曼楚女士(Rigoberta Menchú)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原由是其“为冲破不同种族、文化和社会疆界做出了巨大努力”。作为美洲原住民的一员,曼楚强调了族群的政治因素。她说自己好比历史的残存物,孤独地在这个世界上挣扎行进,目的是不得不向世人揭示故土的不幸和创伤。⑧
同样在1992年,体现原住民话语的历史性文件《原住民“地球宪章”》(Indigenous Peoples Earth Charter)面世,全面阐发了与原住民相关的诸多观点。对于“原住民”(indigenous)一词的使用,《宪章》提出要祛除一切旧有偏见,提升其内在含义,那就是族群传统的主体性及其与大地和自然的关联。它说:
我们原住民踏着先辈的足迹走向未来。经由最大和最小的存在,造物主用空气、土地和大山,从四方把我们创造。我们原住民依存于地球母亲……⑨
以人类学的常用术语来讲,上述内外互补的陈述,一个代表“客位”(etic),一个代表“主位”(emic)。⑩惟有二者结合,方能全面理解“原住民”及其文化传统的意涵和层面。
“原住民运动”的兴起和演变
作为一种诉求多样且形态不一的世界性潮流,“原住民运动”的起因可谓由来已久。其中主要背景是19世纪晚期以来殖民主义的瓦解和进入20世纪后原住民族群的自我觉醒。在这两股趋势的合流中,对原住民地位、处境及其文化传统和命运的关注逐渐成为波及深广的全球运动。其从弱到强、此伏彼起,震撼着人类社会既有的身份区分与利益等级。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此运动的重点也经历了从争取政治平等到要求经济振兴再到参与文化互动的顺次延伸。在这过程中,各种各样与原住民诉求相关的国际组织纷纷成立,旨在保护原住民文化的若干“公约”和“宣言”跟着问世。在这当中较具代表性的如“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印地安条约委员会”(IITC)和“世界原住民委员会”(WCIP)等。ILO分别在1957和1989年发布并修订的《原住民及部落族群公约》,在后来成为了联合国颁布《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1993)及《保护和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2006)等文件的主要依据和来源。这些文件一方面反对人种歧视,承认原住民与其他群体一样,“有权充分享有《联合国宪章》、《人权宣言》与国际人权法中承认之所有人权与基本自由”;同时强调族群间的政治和文化平等,即“所有民族对构成人类共同遗产之文明与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均有其贡献”。(11)
如果说这些公约的发布,标志着人类社会对待原住民文化的积极改进的话,所有这些都与原住民自身的卓越奋斗密不可分。在北美、澳洲和亚、非、拉美,无数原住民人群自被殖民以来的反抗与联合,谱写了无数为自由和解放而战的动人篇章。正如一些敏感的国际观察者所描述的那样,除了前面提到的危地马拉的曼楚,因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成为“象征土著人权利之战的国际性偶像”以外,从厄瓜多尔的原住民联盟到玻利维亚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加拿大道格瑞普族人土地斗争和墨西哥恰帕斯州的起义,世界性的原住民运动已获得了日益广泛的政治影响。在观察者们看来,该运动之所以在近来发展迅猛,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全球化与本土化被有效结合。也就是说,尽管无可避免地受到其巨大冲击,但事实上“全球化”依然使原住民“连为强大的整体”,从而让全世界听见他们“比以往更有力的声音”,并为改变本土社会的状况发挥出更大作用。(12)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趋势使人们对全球化后果的一种担忧被随之打破,即人类社会的未来会日益趋同,文化的丰富多彩会因全球化而迅速消失,等等;恰恰相反,原住民运动借全球化之力的蓬勃发展说明,越来越多边缘人群与文化在此过程中觉醒,开始主动地乘全球化势头来争取本土和自身的权利,继而有可能以独特的声音加入到世界性的文明对话之中。
“原住民知识”的多重意义
距今150多年以来,一封据说是原住民首领致美利坚总统的信广为流传。为了答复白人领袖的土地要求,这位叫做“西雅图酋长”的印第安长老站在与自然共存的立场陈述了原住民的大地观。信中提到:
这里的每一块土地,对我们人民来说都是神圣的。哪怕是一颗发亮的松针,一块沙砾的海滩,一片林中的云雾,一颗清晨的露珠,还是一只鸣唱的小虫,所有这一切,在我的人民的记忆和现实中都是神圣的。
我们熟悉树液流过树干,正如血液流经我们的血管一样。我们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也是我们的一部分。
基于此,西雅图酋长对白人总统购买土地的要求深感惊奇和不安。他反问说:“土地怎么能够买卖呢……正如不能说新鲜的空气和闪光的水波仅仅属于我们而不属于别人一样,又怎么可以出卖它们呢?”(13)可惜这样的反问在那时不仅不起作用反而被当作无知而受到嘲讽。
一百多年后,事情终于发生变化。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它们的正式文件里慎重宣告了原住民知识的权利和价值:
·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而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
·尊重原住民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文化与传统做法可促进环境之永续、合理的发展与适当的管理。(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1993)
·原住民是人类重要而富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他们的遗产、生活方式及其对地球的关爱和宇宙论知识,对所有地球生命都是无价之宝。(世界银行,2005)
在跨越三个世纪的一百多年里,影响世人对“原住民知识”改变看法的原因很多。简略说来,一个重要因素是全球的生态恶化:来自大自然汹涌莫测的报复迫使人们反思工业化、现代化乃至“文明”本身的困境和桎梏,从而转向未受“污染”的地区和族群求援。尽管这种转向带有实用和功利的色彩,但毕竟标志着人类社会价值系统和权力格局的重大改变。过去被视为落后、野蛮的“土著”人群非但恢复着应有的权利和地位,而且将成为世界新秩序中的一极,参与到关涉全球命运的协商对话之中。
从人类学对文化多样性的比较研究来看,我把上述这种变化称为文明对话中的“原住民转向”。该转向的意义重大深远,标志着人类知识与价值领域的一场变革。它既挑战了“科学至上”的宇宙观,使自然和万物重受尊重;也挑战了“轴心文明”的划分体系,使众多被排斥在外的“前轴心”传统和“非轴心”族群再度彰显,从而为扩展人类知识的整体资源创造出新的基础,使之有助于应对日益加剧的全球危机。
人类学可以说是一门最关注原住民的学科。在西方,从摩尔根(L.H.Morgan)最早撰写《易洛魁联盟》以来,其他许多著名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泰勒(E.Tylor)、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owski)和博厄斯(F.Boas)等,都对原住民进行过深入研讨,发表了一系列描写“异邦”、“蛮夷”和“他者”的民族志作品,并且影响巨大(14)。不同的是,随着时代观念的演变,他们的研究可以说经历了从单一进化论到文化相对论的变革。如今,在殖民解体和文化自觉的交汇下,人类学领域又出现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其对“原住民知识”(15)的评价也进入了关键的转型时期。这一点不仅在米德(M.Mead)与弗里曼(D.Freeman)有关“萨摩亚人的青春”的不同阐释以及奥贝塞克拉(Obeyesekere)同萨林斯(M.D.Sahlins)围绕“库克船长”象征的激烈争辩中有所体现(16),更通过卡斯塔尼达(C.Castaneda)与印第安“巫师”的对话和师承以及吉尔滋(C.Geertz)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论阐释得到充分展开。(17)
这样的转变有何意义呢?在我看来,其意味着越来越强调“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人类学成果将有助于文明对话在不同族群间的多向展开。与此同时,尽管还有许多学科的相关看法或许仍停留在小说《鲁滨孙漂流记》塑造土人“星期五”那样的水准上,在当今世界,“原住民知识”会作为人类价值的重要部分呈现出来将不再是虚构或幻想。并且,对于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轴心文明”而言,与“原住民知识”的对话将不仅是政治民主或思想宽容的体现,而必然会深入到对自然、世界、生命乃至人生意义等根本问题的终极思考之中。
在这样的对话里,逐步渗入到人类知识整体的“原住民转向”,其效果将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标志着原住民运动在争取权利上的推进,即已从最为基本的“生存权”延伸到了更为重要的“身份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它也同时使作为原住民对立面的一方获得明镜,在不同宇宙观、生命观的对比中照见自身的局限与残缺。
由此观之,讨论人类社会的公平与发展,不能不关注这种讨论的前提和基点。正如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地球当今的气候恶化与工业化大国的废气排放等有关而众多的发展中小国和民众却不得不照样承受相同的恶果一样(18),对于一个未考虑其全体成员及知识体系的世界而言,公平和发展的含义都是有缺陷的。
本文开头说过,进入近代以来,世界的主流思想界大多把关注点集中于被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文明”圈里的精英层面,留下了难以把握人类整体资源的结构性残缺。正因如此,杜维明先生以儒学第三期立场,呼唤在文明对话中引入“原住民知识”,便具有打破僵局的意义。在杜先生的具体设计中,以宗教系统为例,这种新类型对话的原住民指向是多层的,不但有“轴心文明”(如印度教、佛教、儒家、道家、犹太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与其内部“本土宗教”的互动、各原住民“本土宗教”之间的对比[如夏威夷、美国印地安各族、太平洋的毛利、非洲、印度的森林地带居民(forest dwellers)以及爱斯基摩等原住民的精神传统],还包括由这些对话所体现的“世界精神的新方向”(World Spirituality、New Directions)。(19)
作为“轴心文明”的一种反思,这种设计或许回应了早期儒家“礼失求野”的传统和马克思学说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探求,同时亦为突破“单一进化论”及其所派生的科学主义话语提供了新框架和新前提。在此之中,西方与其他地区的文明“大传统”不再是唯一的中心,所谓“现代性”也不能继续自称为绝对标准;而若要深入论说公平与发展的话,就必须考虑人类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和全球生态的未来前景。
并且,作为人类历史上又一次“原住民转向”,以知识和话语为主对原住民文化的“发现”,决不仅关涉社会关系上的民族解放,而将意味着人类每一成员的自我复归。在此意义上,“原住民”指的是与地球亲近的人类,“原住民知识”则指基本的经验和常识。其间的关系,就如多年以前西雅图酋长在与白人总统的对话里说过的“人类属于大地,而大地不属于人类”,因为:
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就像血液把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连接在一起一样。生命之网并非人类所编织,人类不过是这个网络中的一根线、一个结。但人类所做的一切,最终会影响到这个网络,也影响到人类本身。因为降临到大地上的一切,终究会降临到大地的儿女们身上。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世界是多民族整体。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我们需要反省习惯中以权势和技术为中心的“文明”及其固有之局限。
注释:
①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中国俗文化研究所”重点项目“藏彝走廊的民俗遗产研究”成果(批号07JJD840190)。其中的内容曾在2007哈佛-燕京国际学术研讨会“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演讲。此处有所修改。
②雅斯贝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4),德国史学家、思想家。所谓“轴心理论”主要出自其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参见中译本,(北京)华夏出版社,魏楚雄、俞新天译,1989年。
③杜维明:《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读书》(三联书店),1995年第10期。
④杜维明:《全球化与本土化冲击下的儒家人文精神》(1998年6月21日在新加坡的演讲,后收入《第四座桥——跨世纪的文化对话》,新世界出版社,1999年10月),以及《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第1~41页)。
⑤关于“复数文明”的讨论,笔者曾以《文明的复数》(Civilization of civilizations)为题在哈佛-燕京校友论坛上提交过讨论。当时主要是为回应亨廷顿所提的“文明冲突论”而作。其中的诸多方面还有待展开。
⑥参见世界银行的相关网页:"Indigenous People":http://go.worldbank.org/6P8N1L4QA0。
⑦资料来源:"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United Nations Office at Geneva.以及Indigenous issues.International Work Group on Indigenous Affairs.Retrieved on September 5,2005.转引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Indigenous_peoples#_note-1。
⑧参见Rigoberta Menchú Tum,Crossing Borders:An Autobiography.New York:Verso,1998。
⑨引自《原住民“地球宪章”》(Indigenous Peoples Earth Charter),资料来源:http://www.tebtebba.org/tebtebba_files/finance/susdev/earthcharter.html。
⑩人类学所说的“主位”是一种特别的研究方法。它主张跳出研究者的偏见,努力站在本地人(当事者、原住民)立场,通过“参与式”观察,来理解被考察对象的文化和价值。参见吴泽霖主编:《人类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黄平等编:《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参见《原住民及部落族群公约》、《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草案》等相关公约。
(12)Moisés Naím,An Indigenous World:How native peoples can turn globalization to their advantage,美国《外交政策》2003年11月12日(http://www.foreignpolicy.com/story/story.php?storyID=13996%20)。
(13)关于西雅图酋长的言辞有许多不同的版本和说法。其中被引述最广的是一封他致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的信和一次演讲。信的英文版在不少原住民网页里都有链接,演讲则有中英文对照本出版。参见http://www.indigenouspeople.net/ipl_final.html及《感动一个国家的文字》(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第279~286页)等。
(14)相关著作的中译本已有不少,可参见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重译本,连树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药等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博厄斯:《原始人的心智》(项龙等译,国际文化出版社,1989年)等。
(15)关于“原住民知识”(Indgenours Knowledge——简称IK),2006年在四川大学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的培训项目里,我们曾有过讨论。有学者强调其“属于地方性知识”、特点“经验的”“口传的”和“实践的”;有的则突出其“族群性”、“非现代性”以及与自然的“亲和性”……总之看法不一,还有待展开。
(16)可参见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周晓虹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德里克·弗里曼:《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李传家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史船长为例》(张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及马尔库斯和费彻尔主编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等。
(17)关于卡斯塔尼达(C.Castaneda)与印第安“巫师”的对话,可参阅卡斯塔尼达:《寂静的知识——巫师与人类学家的对话》,中译本,鲁宓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吉尔滋的论著可参见其《地方性知识》一书,王海龙、张家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18)最近以来,有关气候恶化与人类行为关系以及全球资源配置和消耗不公等问题的讨论,已逐渐由科技领域转向政治、文化和哲学领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07年8月号的“气候丕变与环境危机”专栏可参阅。
(19)杜维明:《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载《读书》(三联书店),199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