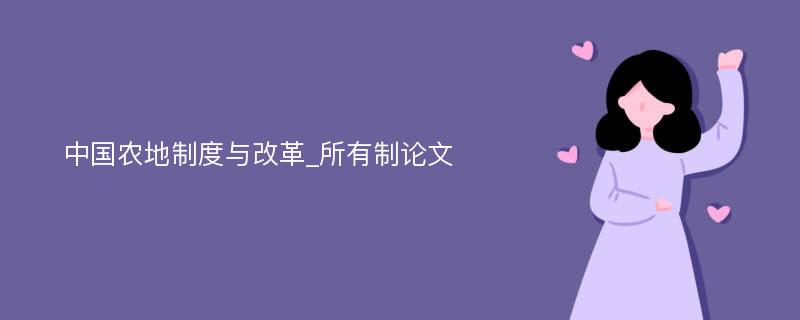
我国的农地制度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地论文,制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农地制度,包括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个层次也是最基础的层次,即所有制度,第二个层次是占有制度,第三个层次是经营制度。这三个层次是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农地制度,主要是就第一、二两个层次而言,即论述我国现阶段的农地所有制度与产权制度。
一、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地制度的变革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土地改革阶段。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面进行的“土改”运动,从1951年开始,到1952年结束。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向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根本变革。通过土改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包括封建国家所有制与地主所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这是我国农地制度最伟大的一次变革,彻底解决了我国长达近三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从西周算起)。
第二阶段是农业合作化阶段。从1952年开始,到1956年基本告一段落。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从农民个体土地所有制变为农民集体土地所有制。通过农民土地入股,初级农业合作社变为高级农业合作社,基本上实现了这一过渡。
第三阶段是所谓的“人民公社化”阶段。从1958年开始至1978年基本结束,延续了近二十多年。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成功的实践,是我国农地制度的一次畸形变革。
第四阶段是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从1978年土地承包制开始,到人民公社制度解体。
二、我国农地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现阶段的农地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还很突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我们认为主要问题有五个:
(一)关于农村土地所有制度
这是农村最基本的经济制度,是“三农”问题的根基。没有土地,就没有农业,农民也就不成其为农民,农村也就名存实亡了。
如前所述,我国现阶段的农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这似乎是很明确了,其实不然,问题是由谁来代表行使农地的所有权。我国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上是由人民公社时期相当于生产队(或大队)的村级组织来代表,而村级组织的大权掌握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归根到底是掌握在村支书和村长手中。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许多问题。
一是村一级组织既不是一级政权组织,也不是一级经济组织,它既不能代表政府,也不能代表本村农民集体。因此,它们代表集体来行使所有权职能,既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客观经济依据。
二是村一级组织行使农地所有权职能,给一些村干部提供了“寻租”的机会,成为农村干部腐败的经济根源。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一些村干部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在调整土地承包时为自家或亲友分好地或多分地,而在分配国家和各级政府的税费负担时,则尽量派给一般农民;村办企业虽名为集体所有,但实权完全操纵在村干部手中,成为他们安插亲属、化公为私的私人企业;特别是近十年来,一些城郊村国家征用土地的收入,成为村干部大吃大喝的财源,甚至被少数人瓜分或私人侵吞,使一般农民连名义上的农地所有权也不存在了,成为真正的“无产者”。
(二)关于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
这是指对农地的占有和支配的权利,本来这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核心,但是在上述农地所有权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农民对承包土地的产权也名存实亡了。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经常变动,村干部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理由”进行调整,后来虽然规定了承包期30年不变,但事实上年年都有小调整;再加上在承包期内,农民不能将土地产权出租和转让,更不能将产权出卖和入股,也没有规定产权可以由法定继承人继承。这样一来,农民就不可能将农地视为自家的“恒产”,正如孟子所说的:“无恒产则无恒心”。农民就不愿意在农地上长期投资,来改善农地的环境和生产条件,只是搜刮地力、靠天吃饭,以致农地肥力不断下降,有的农地出现盐碱化、沙化,甚至荒漠化。
二是,由于农民丧失了对农地的产权,因此其使用和支配的权利也大大弱化了。乡村干部以致县市领导部门,可以硬性规定农户可以种什么,不可以种什么,以致那些农产品可以卖并卖给谁,都由上面说了算,农民自己不能做主,而由于瞎指挥造成的损失却无人负责,后果由农民自己承担。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三)关于对农地征收税赋制度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农地所有制度与产权制度的根本变化,国家政权性质的根本改变,国家对农地征收税赋的性质也根本改变,它不再是剥削阶级对劳动农民的掠夺,而是农民对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一种义务。
但是,我国在对农村征收税赋的形式上,却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过去封建制度下的税赋制度,即按土地和人丁征收。这对我国现阶段农地制度的状况来说,这种税赋制度就很不合理了,因为农民既未掌握农地的所有权与产权,凭什么向农民征收土地税赋呢?至于按农民家庭人口来征税,那就更没有道理了。
(四)国家征收和征用农地制度
根据国家修改后的《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总结了过去二十多年在征收和征用农地制度的经验与教训后所作的修改。
教训之一,就是忽视了农地集体所有制和家庭承包制产权的性质及其权利,政府往往采取强制的行政手段,不和农民协商,不向农民讲清道理,就把农民的土地占用了,因而引起了农民的不满,甚至采取激烈的反抗形式,使农民与国家的矛盾尖锐化。
教训之二,就是补偿的价格大大低于农地的价值,根本弥补不了农民因失去农地而造成的损失。据有关专家估计,近几年由于国家低价征用农地而使农民少收入2千多亿元,这是对农民的变相剥夺,也加深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矛盾。
(五)关于村级自治组织制度
关于村级自治组织的性质,顾名思义,它是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一个群众性组织,它既不是一级政权组织,也不是一个经济管理组织,同时也与过去的农民协会的性质不同。
但是,由于村级组织实际上掌握了村上农地的所有权和一定程度的农户承包土地的产权,再加上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制度的遗留影响,因此,村组织实际上成为一级政府,同时也是一级经济组织。
这样就产生了以下问题:一是村级组织包办了村里一切事务,农民无权参与,成为名副其实的被统治者,根本谈不上是主人;二是村于部利用政权组织所赋予的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甚至作威作福,欺压农民,农民有话无处说,有冤无处诉;三是村级组织恶性膨胀,村干部人数急剧增加,据有的专家估算,全国乡镇一级建制4.37万个,乡镇干部约400万人,如以每个乡镇10个村计算,村级干部将近4000万人,这对农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难怪有的农民愤怒地说:“旧社会我们村只要养一个保长,现在我们要养10几个保长。”四是村级组织既然掌握全村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权力,所谓“村民自治”,实行“民主制度”,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我们的对策与建议
总的设想是:农村土地同城市土地一样,全部归国家所有,实行全国土地国有化;农村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其占有、使用和经营权(即产权)应归承包的农民家庭,这种产权可以出租、转让、抵押、赠送、遗传,承包期不限定年限;与此相联系,国家应及时调整对农村的财政政策和征用农地政策,加大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坚决取缔对农民的繁重税收,逐步免征农业税,实行农村所得税制;坚决制止村民自治组织政权化,大力精简县、乡(镇)、村的机构与人员,一个村只应保留两名办事人员(党村各一);逐步取消城乡隔离的各种制度,缩小工农产品的不合理“剪刀差”价格,保证农民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上学与就业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机遇,具体论证如后:
(一)关于农地国有化问题
1.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
2.列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以上思想,在十月革命以后签署的第二个法令就是《土地法令》,宣布苏维埃国家的全部土地均属国家所有,后来写进苏联的历次宪法中。二战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曾宣布过土地国有化法令。
3.19世纪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乔治·亨利也曾提出过土地归国家所有的主张,认为这样可以消灭绝对地租,有利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孙中山先生非常欣赏这一论断,并写入他的《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两书中。二战以后取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中,也有采用土地国有化方针的。实践证明,即使实行资产阶级土地国有化方案,也比封建土地所有制要好得多,因为它可以消灭私有的垄断,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
4.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进行土改运动中,党中央也曾考虑过实行土地国有化方案。但是由于我国当时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农民希望得到土地所有权的强烈愿望,不得不采取农地归农民家庭所有的方针,并通过合作化使土地成为集体所有。
5.根据我国现阶段农地所有制现状和问题,如何妥善加以解决呢?不外乎三条道路:一是维持现状,略加修改。看来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农地集体所有的名存实亡,也就是说由谁来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很难解决好;二是走农地私有化道路。这是西方一些学者所提出、我国有的学者积极宣扬的道路,其中张五常教授就是突出的代表。他在《分成租佃论》一书和《私有产权与分成租佃》一文中,就是宣扬他那一套私有产权与土地租约安排理论。我们认为,他的这一套可能对资本主义制度下适用,但对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是不符合的,理所当然地为中央政府所拒绝。因此,我们现在只剩下农地国有化的这条路可走了。
6.我们认为,实行农地国有化的好处:一是可以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持久性,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可以合理解决国家征用农地中与农民的矛盾;四是可以消除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产生腐败的经济根源。
(二)关于农地产权家庭化
1.关于所有制、所有权和产权的联系和区别问题。
所有制,一般是指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是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不同的基本经济制度。所有权是指所有制在法律上用语,是属于法学上层建筑的范畴。产权,按照马克思的论述,是指人们对财产的占有、使用并支配的权利,也是属于法学范畴。按照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产权也就是财产的所有权,它是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和实现形式,其核心是所有者对所有物的排他性独占,其一般定义是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与产权可能发生分离,但核心问题还是产权。
2.关于农地产权的家庭化问题。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农业产业化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农业产业化的前提首先是农业市场化,而农业市场化,农户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就必须具有使用和支配承包土地的权利,即具有实实在在的产权,农户可以自由转让、出租、入股、遗传甚至买卖的权利,而且这种权利不应当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化和规模经营。同时,也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向农民征收所得税的权利和理论依据。为此,就必须对当前农村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进行改革,明确承认承包农户对承包土地的产权,废除承包年限和区域限制,坚决禁止各级地方政府对承包农户的土地经营权的侵犯和剥夺,违犯者必须坚决绳之以法。
3.关于农地所有权与产权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关于所有权和财产权的涵义,在自然经济和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这两者是完全结合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土地的占有、使用和支配当然也归私人;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两者可能发生分离,即土地的所有者不一定是土地的占有和使用者,其实这也是一种结合的方式,只不过这是两个不同的主体通过商品关系,形成外在结合方式而已。例如在土地国有制的条件下,根据国家的性质可能形成多种不同的外在结合方式,如我国古代的井田制方式、封建制度下的地主与农民的结合方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主、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之间的关系等。如果我们实行农地所有权国有化与产权农户家庭化,就会形成一种新型关系,即人民的国家与几亿农户的结合关系。
4.必须区分不同性质的国有化与农民的关系。
在奴隶制度下,土地归奴隶主国家所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当时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奴隶,连当“王臣”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当牛做马的一种“会说话的工具”而已。在封建制度下,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下面还有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完全垄断了土地的所有权,同时也控制了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农民只不过是变相的奴隶而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土地所有权仍在地主手里,农业资本家租种地主的土地,也只是取得有限的土地占有使用权,而农业工人则是雇佣劳动者,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曾颁布过《土地法令》,宣布全国土地归苏维埃国家所有,农村土地由集体农庄使用和支配。但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土地国有制下不可能形成土地的产权,因此也就谈不上所有权和产权的分离了;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实行农地制度国有化,则必然要形成农户的产权制,并与农地国有化相分离。
(三)与农地国有化、产权家庭化相关的问题
1.关于农地国有化与农户产权家庭化,同国家对农村土地的征收或征用问题。
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名不副实,农户对承包土地的产权不明,因此国家在征收或征用农地中出现了不少问题,至今仍不能合理合法加以解决,以致成为现阶段“三农”问题严重存在的原因之一。因为土地征收首先涉及农地所有权的转移,而土地征用主要涉及农地产权问题;其次涉及征收或征用农地的补偿问题,如所有权的转移应当补偿多少、产权的转移应补偿多少等。因此,如果我们实行农地所有权国有化、产权农户家庭化,国家对农地的征收或征用就只涉及农户的产权及其补偿了,也就是只涉及产权交易费用与级差收益的分配了。
2.关于农地所有权国有化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
根据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颁布的《矿产法》规定,全国地下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由国家开发和经营管理。这一规定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则不完全适用了,因为它形成了国家与地区以及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特别是与老少边穷地区之间的矛盾,成为影响我国安定团结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在过去曾提出:在坚持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废除国家全部垄断产权和经营管理权;除极少数如黄金白银等贵金属、铀矿、石油等战略资源以及某些稀有金属外,其他的矿产资源的开发经营权应交由各省(市、区)统一安排和管理;产权应由各类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外资等企业)掌握,在国家法定的范围内自由经营,国家按照规定对其征收税费。
3.关于农地所有权国有化与农业税赋制度的改革。
我国现在的农业税赋制度是从古代逐渐演变而来的。仍然是以土地所有权作为征收农业税赋的依据。在漫长的封建制度下,实行的租、调、庸三位一体的农业税赋制度就是如此。其中的“租”主要是指实物地租,这是由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决定的;“调”是指对农村家庭工业剩余产品的征课;“庸”是对封建国家的劳役地租但以实物交纳。总之,都是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给国家缴纳的税赋。如果我们现在农地制度不变,还是土地所有权名不副实,产权不全,国家就失去了对农民征收农业税赋的依据,我们现在提出的五年之内免征农业税也就名不正而言不顺了。为此,我们提出农地所有权国有化,首先就可以免去绝对地租,因为废除了土地私有权的垄断,绝对地租也就不可能存在了:至于级差地租因涉及土地经营权的垄断,也就是涉及土地产权问题,如果农户家庭真正掌握了土地的占有以及使用和支配权,国家征收一些级差地租还是合理的。但为了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国民待遇,可以改收所得税的形式,即与城市居民一样,农户月收入超过800元以上交纳所得税,并采用累进所得税的制度以缩小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
4.关于农村的政治民主化问题。
这也是与农村的土地所有权与产权紧密相连的问题。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下,农民既没有土地的所有权,也没有土地的产权,因此根本谈不上农村政治的民主化,这是几千年来的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了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土地成为国家所有或农民集体所有,才为农村的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但是,由于我们过去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被扭曲,农民也未真正掌握承包土地的产权,因而农村民主化的经济基础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这也正是我国农民的政治权利得不到保证,甚至人身自由权和劳动权也经常受到侵犯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曾经建议:1)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建立各级农民自己的组织,真正实现农村的“村民自治”;2)撤消村一级建制,更不应赋予它一级政权机构的责任与权利,以杜绝农村基层干部的“寻租”活动;3)逐步废除乡镇一级建制,首先要坚决压缩乡镇干部的人员编制;4)逐步推行农村各类各级组织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评议制度,使干部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人民的“老爷”,更不能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土皇帝”。
标签:所有制论文; 农民论文; 土地所有制论文; 土地产权论文; 所有权的转移论文; 农村改革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论文; 家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