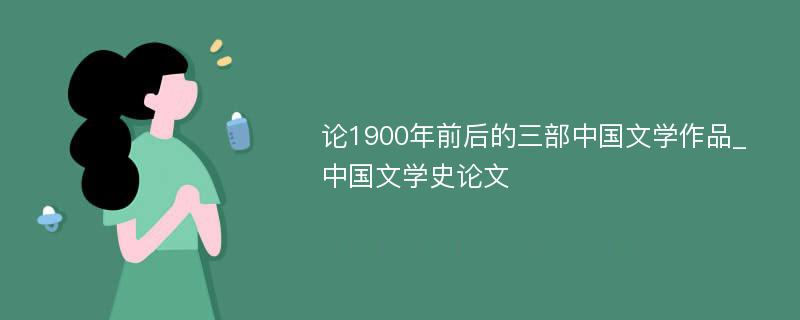
谈谈1900年前后的三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著作论文,年前论文,中国文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目前所知,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是俄国人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接着,1882年日本的末松谦澄出版了一本先秦的断代文学史《支略古文学略史》。之后稍沉寂了一段时间,到1900年前后,则形成了一个编纂“中国文学史”的热潮。假如从1891年到1904年作一统计的话,中外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有十馀种(参见拙作《日本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5期)之多。在这期间,国人有三部都是作为“讲义”的文学史著作问世: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1897-1906)、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1910)、黄人的《中国文学史》(1904-1911后)。当时是中国文学观念大变化的时期,今就这三部著作,从三个方面来看不同文学观念的介入与文学史编纂的演变。
一、传统文学观的瓦解
中国古代是文与学不分,见之于文字的都可称之谓文学。后来尽管有文笔之分,以及文章、词章等不同的概念出现,但直至晚清,总体上还是沿袭了一种“大文学”或“杂文学”的观念,而至20世纪初,西方“纯文学”及美学观念的引进,使整个20世纪从“杂文学”走向了“纯文学”。这在最初的这三部文学史著作中即可见其端倪。
我们先看最早的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他的“文学”,即包括经、史、子、集。其正文内容为五部分,依次为“志文字原始第一”、“志经第二”、“叙史第三”、“叙子第四”、“叙集第五”。他对经、史、子、集的基本看法是:
学必由文字始,兹叙文字为发端。立纪纲,厚风俗,使薄海内外之人相协而不相离,可强而不可弱者,莫备于经,故次之以经。上下古今,成败得失之道,一览了然,得所依据,莫善于史,又次之以史。凡人情事理,以至农工商贾,虽世变日新,有百变而不能出其范围者,莫详于子,又次之以子。从古硕德通才,奇谋伟略,以至文人学士,亦各有著作,以抒其见,悉载文集,又次之以集。兹择其恒见而切要者录之,间附末议,虽所见孤陋,然窃谓会而通之,有益之学,大致备矣。
他论“文”是以“理”为核心的:
文以明理,文以述事。理明则著为事而不至于纰缪。士大夫握管为文,必有其关于理之是非、事之利害而始可言文也。何谓利?凡守先民之道可以遂民之生、蓄民之财者,则谓之利,何谓之害?凡背先王之道以致贼民之生、妨民之财者,则谓之害。
其“叙集”部分尽管接近于后来的“中国文学史”,但还是从“集”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述的。先论集部之始,由《诗经》到《楚辞》的“总集”,论到贾谊、董仲舒之后的“别集”。然后,他对集部的内容作了如下的概括:
兹录集部,以奏议为冠,然强半已入史部。曰散文,曰诗词,若妃青俪白之工,揣摩应举之作,乃文学之蠹,儒林之害也,急荡涤而摧廓之。
这说明他还是以理与利放在首位,而不是所谓文学性。不过他在论词之后,还是用三行字、以肯定的态度论及了曲,从元曲《西厢记》、《琵琶记》,到汤显祖、徐渭、洪昇、孔尚任,再到李渔、杨潮观、蒋士铨,一一点到为止。当然,这种肯定基本上还是不脱传统的看法。对小说则只字未提。
再看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他的文学观,比之窦警凡,有进步处,也有倒退处。他虽然也从文字论起,顾及群经、史传、诸子,但毕竟突出了“文”。全书十六篇,从第十二篇“汉魏文体”到第十六篇“骈文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很大一部分是在论古代的散文,且史与论相结合。从这一点上看,它比之窦著更像一部文学史。但它对诗、词、曲、稗等其他文体,或三言两语带过,或根本不予论述,甚至对小说戏曲加以全盘否定,其《元代文体为词曲说部所紊》云:
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变乱陈寿《三国志》,几与正史相混;依托元稹《会真记》,遂成淫亵之词。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文之《虞初》。若载于风俗史犹可。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而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
要知道,1904年,梁启超等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运动早已如火如荼,人们的文学观念正在发生巨变,而此时的林传甲竟还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小说、戏曲,这只能证明其本人的“识见污下”。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他受了当时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的规定,以及京师大学堂的禁令的影响,因为当时《奏章》等“以学生购阅稗官小说,垂为禁令”。这当然可以理解,但他对《奏章》变通之处甚多,为什么这里不向积极的方面变通呢?为什么同样在这年开笔的黄人,同样为大学堂写“讲义”而不是这样的态度呢?这主要还是反映了他的文学观念的落后,不容讳言。
黄人在当时较注意吸收西方的新鲜观点,因此他的文学观与窦、林有着很大的区别。1911年,他在《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文学”条下说:“文学虽与人之知意上皆有关系,而大端在美。”这与窦警凡认为在“理”就大相径庭。黄人在《中国文学史》的卷首,即开宗明义地指出:
人生有三大目的:曰真,曰善,曰美。……文学则属于美之一部分,然三者皆互有关系。……故从文学之狭义观之,不过与图画、雕刻、音乐等。自广义观之。则实为代表文明之要具,达审美之目的,而并以达求诚明善之目的者也。
当然,在整部文学史中,是否彻底地贯彻了这一思想,看来还要有一个过程,但应当说,他还是努力贯彻了这一文学思想的。从全书来看,尽管所选的文体比较庞杂,制、诏、策、谕,乃至金石碑帖、音韵文字,包罗极广,但毕竟跳出了经、史、子、集的框框,他把制、诏等都是作为“文学”来看待的,更何况他还注意并高度评价了小说、戏曲,乃至“闺秀”作品,这在当时说来都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对于小说的评价,应该说是当时检验不同文学观的一块试金石。窦警凡不屑谈,林传甲诋毁之,而黄人在《略论》中说:“小说为工细白描之院本,院本为设色押韵之小说。小说能扫荡唐宋历来之稗官家,犹院本之能扫荡汉魏以下一切乐府焉。……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尔、索士比亚专美于前也。”这样的文学观明显地具有时代的先进性。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窦警凡,到林传甲,再到黄人,对于“文学”究竟是什么?“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什么?已经有了显著的变化。传统的文学观正在瓦解,新颖的纯文学观正在确立。
二、西方进化论的介入
以上是从文学的本质特征来加以考察的,再从文学发展观来看,三部文学史也不相同。
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也有史的观念,他在描述经、史、子、集各体文章时,也注意论述其源流变化。如云:
大抵六代文风,自曹子桓、吴季重等开之,晋以前尚以意运词,晋以后则词胜于意,梁陈之后,靡丽而益之轻艳,虽秀逸如谢明远、庾兰成,亦所不免,而江南之文运终矣。
至于为什么变化,与时代什么关系,均未关注,只归结于“运”而已。
林传甲在论述文学的演变时,也注意到历时性的变化,并注意这种变化与时代的变化联系起来。他曾说,“言语亦随时代而变”,“孔子亦随时,此其所以为圣之时”等。这是“一代有一代之体制”的传统看法。但他又强调“文章难以断代论也”。他说:
然以文体细研之,则汉之两京各异,至于魏而风格尽变矣;六朝之音宋与齐梁各异,至于陈隋而音节又变矣;而唐四杰之体,至盛唐晚唐而大变,至后南唐而尽变矣;宋初杨、刘之体,至欧、苏、曾、王而大变,至南宋陆游而尽变矣。……必欲剖析各家文体而详说之,非举《四库》集部之文尽读之,不能辨也。
实际上,他对文学的发展有所注意,但并未深入地思考,也无特别的理论指导。
黄人的文学发展观显然比前二书有很大的进步。全书有上世、中世、近世之分,又有文学胚胎期、全盛期、华离期、暧昧期、第二暧昧期及文学之反动力等说法,把整个文学看成是流动的。这种流动变化,又是与世运的进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经常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政治、风俗决定了一代的文学。例如,他在论述“明之新文学”曲本时就说道:“一代之文,每与一代之乐相表里,其制度虽定于瞽宗,而风尚实成于社会。”他在当时进化论的影响下,还认为文学在前进过程中常常出现曲折,所以其发展往往是螺旋形的:
文治之进化,非直线形,而为不规则之螺旋形。盖一线之进行,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轨。故历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后却者,又中止者,又循环者。及细审之,其范围必扩大一层,其为进化一也。
进化后的文学便“自成新种”。显然,黄人的这种文学发展观,比起窦、林来既具体,又深入,有了很大的进步。
三、编史功利观的增强
编史都有一定的目的。窦警凡当初编写《历朝文学史》可能就是作为南洋师范的课本。其人政治上比较守旧,反对维新,但他面对着国家的衰微,也希望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以达到“转弱为强,转衰为盛”的目的。他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国之败不在财力之贫弱,而由上下之离心;国之胜不在兵力之盛强,而在士民之协力。”他分析了宋、元、明来的情况之后又说:“由此而观,成败之故,固莫备于文学矣。”他就是希望通过学习文学的历史来知“理”明“事”,振兴国家。正是在这意义上,他说:“知事本于理,理原于文,古今天下非一文之所维系哉!”
林传甲先后受知于张之洞、严复等,思想上比较开通,但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仓促间受聘于京师大学堂,需马上赶编讲义,“奋笔疾书,日率千数百字”,到年底学期结束时共完成十六篇。显然,他编此书完全是为了应付教学,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遵照1904年1月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的原则来编写的,换句话说,他基本上是清政府官方教育的一部分,顺手还参考了1903年刚翻译过来的日本笹川种郎《历朝文学史》,故其独立的编史意识并不十分明确。翌年,他即奉调广西任知县,同年又赴黑龙江搞教育,兴趣转移到地理学方面去了,对“中国文学史”事也就搁置不论。
与窦警凡、林传甲不同,黄人编《中国文学史》并不仅仅应付教学之用,而是有明确的人文目标。他在《总论》一篇中专辟“文学史之效用”一节,详论了编写文学史的目的。第一,是为了煞住盲目崇洋的不良风气,用事实来证明我国文学发达最早,且连绵不断,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之相比,改变那种“过华屋而叹凌夷,窥明镜而羞老大”的自卑感,增强民族自尊心。他说:“有文学史,厌家鸡爱野鹜之风,或少息乎!”第二,为了激发爱国热情。他把弘扬中国文学,提到了保种还是灭族的高度上来认识。一部《中国文学史》,可以使人窥知祖国文学遗产的光辉灿烂,“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第三,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他不满封建社会“常统于一君主一法律之下”,特别是对汉武帝及明代社会的专制予以猛烈的抨击,认为文学是“言语思想自由之代表”,通过学习中国文学史,则可以使人相信“此言语思想之自由,政治习俗未尝明为限制,而亦不能为之制限也。”第四,为了“障翳抉则光明生,糟粕漉则精华出”。他说:“史者,人事之鉴也,美恶妍娸,直陈于前,无所遁形,而使人知所抉择。”通过学习文学史,懂得去糟粕、取精华,国民才能进步。总之,他写《中国文学史》,并不仅仅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传授文学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为了陶冶爱国精神,宣扬民主革命。黄人的这一思想,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这不仅是关系到文学史著作的编纂,而且与整个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精神也是相通的,特别在当前,当与文学沾边的相当一部分人的人文精神失落的时候,重温一下黄人的话,还是很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