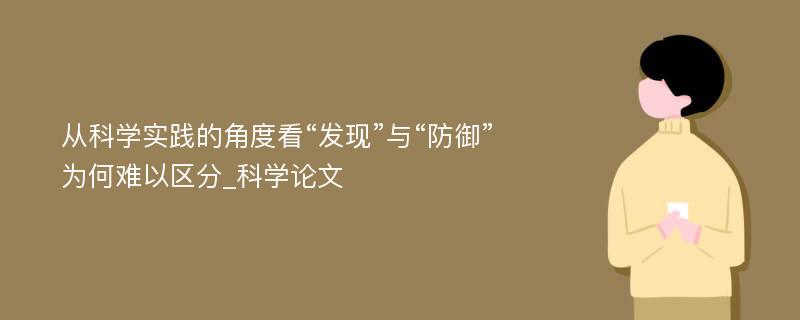
“发现”与“辩护”为何难以二分——从科学实践的观点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观点论文,发现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05-0086-06
一 问题的由来及其演进
“发现”与“辩护”的关系是科学哲学中一个重要问题。按照经典归纳主义的观点,归纳法是科学发现的一条重要途径。归纳是由特殊到一般的过程,其结论的范围有可能超出前提,因此具有一种扩散和创造的可能性。逻辑经验主义继承了古典经验主义的观点,但只保留了归纳的辩护功能,却抛弃了其发现功能。赖辛巴赫① 对“发现情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情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作为科学理论的发现过程,是一个未知的心理过程,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不应该包括在知识论的研究范围内;知识论的任务只应关心辩护情境,只能研究如何从理论推导假设、如何验证假设、如何对理论进行辩护问题,而不必考虑科学理论的发现或来源。这一主张受到大多数逻辑经验主义者的赞同。由此形成了“发现情境”与“辩护情境”的二分。
“发现情境”与“辩护情境”的二分带来了两个最直接的后果:第一,“发现情境”在科学哲学中被存而不论。站在这种规范性的立场来看,科学是对客观实在的表征,其来源或产生存在种种偶然性,科学发现可能归因于科学家的直觉、灵感等非理性因素,应该交由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来研究。第二,“辩护情境”则完全是规范性的,科学辩护应在认识论意义上、在表征层面进行探讨,于是逻辑经验主义采取一种语言分析的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和合理性重建。可以说,两种情境的相分一度决定着科学哲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内容。
此后,对两种情境相分问题的研究大致沿两个方向发展:其一,一批学者在科学哲学中重提科学发现,② 认为“发现”应包括在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这种研究在20世纪70-80年代早期成为科学哲学的主题。③ 他们认为科学发现是理性的,其研究关注科学发现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经得起检验的。这一研究方向在当今认知科学和生物学哲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试图通过对认知和生物属性的研究找到科学发现所遵循的逻辑。另一个研究方向来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经验研究。这部分学者认为,两种情境相分事实上是将历史学和社会学排除在科学哲学之外,但这是一种不成功的努力。他们采取一种描述性方式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辩护过程进行经验研究。SSK的强纲领、实验室研究都是在两种情境不能相分的前提下做出的。
2002年,在德国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召开了“重访发现与辩护(revisiting discovery and justification)”的学术会议,同名论文集于2006年出版。文集中收录了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考察。其中,有学者从历史出发,重新考察了赖辛巴赫提出两种情境相分的政治社会因素,以及这种区分今天是否有效,由此来回应两种情境的相分;有学者通过对“发现”与“辩护”的含义和区分不同适用范围来重新考察两种情境是否相分、在何种意义上相分的问题;还有学者从具体的物理学实验出发来论证“发现情境”与“辩护情境”的不能相分。文集向我们传达了如下两个意图:第一,对“发现情境”和“辩护情境”是否相分问题的研究不能局限于科学哲学内部,而要充分吸收当今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研究成果;第二,科学社会知识学(SSK),特别是强纲领过于经验化的方法忽视了认识论的内容,并不能真正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很好的思路。相反,只有多角度融合的研究方式才可能为我们更清晰看待这一问题提供帮助。
对两种情境的相分问题,我国多位学者在阐述SSK,特别是实验室研究采用情景化策略对科学知识产生进行研究时都有所涉及,但由于文章主题所限并没有进行进一步阐述。④ 他们将两种情境的相分看做从社会学角度介入科学研究的前提。
本文运用实验室研究、新实验主义以及科学实践哲学的研究成果,尝试从科学实践的角度对两种情境相分的问题进行回应。这一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上述第二个研究方向进行的。通常认为这一研究进路始于库恩。在库恩看来,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方法对科学知识进行逻辑分析,用牛顿力学的观点审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将会发现后者毫无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我们承认两者的价值,那么只能理解为两种知识体系是遵循不同范式构造的,知识的内容和准则只是在不同时期的共同体内部得到辩护。由此库恩的科学革命与范式转换理论就为“发现情境”与“辩护情境”的不能二分开启了一扇大门。
在此之后,SSK的强纲领派和实验室派采取了一种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方法对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进行分析,以表明两种情境的不能二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都将自己的研究聚焦于具体的科学实践过程,共同汇聚成一股新的趋势——从传统科学哲学一直关注的表征转移到具体的科学实践当中。⑤ 尽管他们关注的旨趣、所用的方法不同,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的研究共同勾勒了一幅科学知识何以在具体的语境(实践)中产生和辩护的图景。他们的研究表明,科学知识产生和辩护无法完全脱离产生它的地方性语境。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科学活动过程之中来看科学,就会发现将“发现情境”与“辩护情境”相分,事实上就是将知识与认识行为分离开来,这是不可行的。
二 独立的发现情境是否存在
如果我们承认“发现情境”与“辩护情境”的二分,那么首先必须承认有独立的“发现情境”和“辩护情境”存在。按照传统科学观,科学发现就是人类阅读自然之书,发现隐藏在事物背后的规律,并将其表征出来,经过辩护而形成真知识的过程,是科学家对已有规律的发觉。因而,“发现”一词暗含了一种实在论和符合论的科学观。然而从科学实践的观点来看,这个假设并不成立。实验室研究表明,科学知识并非被发现,而是被生产和制造出来的。对此,新经验主义者有更客观的论述。按照新经验主义代表人卡特赖特的观点,科学定律并非发现,而是在人工构造的特定语境(一种受控环境)中展现的,是科学家通过各种实践活动构造出来的。用卡特赖特的话说,“自然定律得到承认是因为能力(capacity)⑥;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因为具有能力的系统组分在特定的幸运情况下重复运作”⑦。定律是律则机器产生的,也只在律则机器中才起作用。自然定律只是相对于律则机器的成功的重复运作而成立。⑧
所谓律则机器就是“对组分或要素的(充分)固定安排,有着(充分)稳定的能力,该能力在适当(充分)稳定的环境中,将通过重复运作来产生我们用科学定律表达的规则行为的种类”⑨。它有两种形式,一种存在于自然界中,是自然发生的;另一种存在于实验室中,这是律则机器起作用的更通常的情况。律则机器由概念、特殊安排、以及屏蔽条件构成。最终保证其有效性的还有一点是其他情况均同定律,它通过特定情境的转移来保证定律的有效性。
构成科学理论的最基本要素是概念,以“力”这个概念为例,自然中并没有一种实体与之对应。它之所以被理解是通过一种特定的形式,只有将其置于一定的特殊情境中,通过建构特殊的力学模型,力的作用才能展示出来,这个抽象概念才能形象化地表现出来。由此来看,构成科学理论的概念并非是对自然界的“反映”,而是一种具有语境依赖性的建构。
宇宙运行规律通常被看做是最经典的科学发现,没有人否认开普勒定律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是对天体本来属性的一种真实反映。然而,在卡特赖特看来,这些定律也只是自然界中律则机器发生作用的情况,并不具有普遍性。例如,开普勒第一定律告诉我们:每一个行星都沿各自的椭圆轨道环绕太阳,而太阳则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中。牛顿所做的工作就是如何运用一个力学描述来表达行星的运动状态及受力情况,也就是如何找出说明这一规律的律则机器。最终牛顿发现了组建律则机器所需的能力。产生开普勒定律的律则机器的组分是:质量为M的质点——太阳,质量为m的质点——行星,它们以距离的方式被安排,把行星保持在椭圆轨道上的力为F=GMm/r[2]。⑩ 而要使律则机器发生作用,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屏蔽条件,这里的屏蔽条件就是二体必须是在没有额外的巨大物体及其他可能干扰因素的情况下相互作用,才能确保椭圆轨道。由此来看,即使被我们视为自然界之本来规律的行星运动律,其发生作用也是有条件的,它只能在排除一系列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才能被抽取或展现出来。人们在观察天王星时,发现其运行轨道与牛顿原理预测并不相符,后来发现是由于海王星的存在干扰了天王星的运行。“这表明了牛顿行星机器在特定情况的描述失败了,而海王星的发现则正是来自于对屏蔽条件的修正。”(11)
在卡特赖特看来,实验室是更多律则机器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场所,因为人工可控的环境更容易实现对干扰因素的屏蔽。在实验室中,科学家往往针对一个想要得到的结果,设计一套完整的实验流程,把可能引起干扰的因素屏蔽掉,将研究对象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再进行跟踪和介入来获取想要的结果。这些严格设计的实验事实上就是构建律则机器来得到定律。为了构建一台合适的律则机器,通常会使用分析方法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科学家往往先对分割成更基础部分的自然能力有所了解,然后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和需要构建一个情境,在这个人工构建的情境中,将每一部分重新组合起来,重新进行安排,将那些能带来希望出现结果的因素留下,干扰因素屏蔽掉。屏蔽本身并非自然界的真实情形,只是特定情境中的人为安排。在一个情境中的干扰因素在另一个情境中也许是希望得到的结果。在特定情境中产生的科学定律具有很强的情境依赖性,它只在产生它的这一律则机器中发生作用。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众多科学定律表现出的普遍性隐含了一个重要条件——其他情况均同。不同情形中同一定律发生作用是因为其有相同的律则机器,科学理论的“普遍性”事实上是一种地方性情境的移动。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之所以强大并非因为它的普遍性所带来的演绎功能,而是通过构造相同的律则机器使其在人为的操控下展现。理论与现实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反映与被反映关系,而是通过模型连接起来的,模型成为连接世界与理论的中间桥梁。“如果没有模型,那么存在的仅仅是抽象的数学结构,漏洞百出的公式,而且与实在没有任何联系”(12)。
由此来看,科学的“发现”过程往往是:科学家根据已经掌握的事物的能力(本性),构造一个具体情境,在此情境中,按照自己的研究需要设计实验环节,运用拼凑的定律,选择恰当的模型,屏蔽干扰,让想要得到的事物的能力展现出来。它们所用的抽象概念仅在具体的情境中才有意义。那么,科学发现事实上是以一定的科学创造为前提的,没有情境的构造就没有发现。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可以独立存在的发现情境。
三 科学发现和辩护中的语境因素
如果我们承认没有独立的发现情境存在,那么对科学知识合理性的重建也就必须突破语言表征的层面,回到科学实践的过程之中,这正是朝向科学实践的学者们所共同强调和关注的。(13) 通过对科学实践具体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知识产生和辩护过程中充满了大量非逻辑的因素。对此,科学实践的观点与其说是强调社会利益因素,倒不如说它强调的是一种地方性。所谓地方性,盛晓明曾做过如下概括:“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14)。笔者认为,在科学实践的视野中,地方性更多是指一种对特定语境的依赖性。
以现代实验室这个科学知识最集中、最典型的生产场所为例,它不仅是作为场所的存在物,更重要的是作为语境的存在物。实验室包括如下一些物质性要素:拥有特定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观察、介入和操控自然现象的实验设备以及被研究人员和实验设备所重构的自然。这些要素及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共同构成了知识得以产生的语境。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渗透着科学家的选择、商谈和决定,同时也受制于实验室研究资源、仪器设备、人员背景等条件,整个过程中充满语境因素。
第一,从研究选题来看,科学研究往往并非源于“问题”而是始于“机会”。“问题”与研究选题之间具有一种非必然的关系。通常认为,研究选题来自于现有理论中的困难或者矛盾,然而通过对科学实践的研究表明,许多科学研究的开展并不源于科学家想要解决当前理论中已知的难题,而是因为他们希望利用现有的资源:设备、技术、训练有素的人员以及相关的科学成果。因此,科学家更关心我们在现有条件下可以做什么,而不是为了克服当前理论中存在的矛盾我们必须做什么。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研究机会,也正是由于机会才使问题凸显出来。在这期间,资源、兴趣或合作者、实验人员的背景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问题由于缺乏上述条件而不能成为一个研究选题,而另一些按照某一实验室的特定背景、兴趣和资源建构出来的“问题”最终会成为这个实验室的研究选题。
第二,从科学研究所用的方法来看,对同样的研究课题,不同实验室会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案,方案的选择中渗透了大量语境性因素。对此,塞蒂纳用“科学研究方法的索引性(indexical)”(15) 来指称这种语境中的偶然性,而皮克林则用“语境中的机会主义(opportunism in context)”(16) 来指称相同的事实。一个特定实验室在开展研究时,一定会考虑哪些技巧适合于自己的研究方案,这是一种基于自身地方性的语境考虑。这种语境性包括实验室和个人两个层面:从个人角度讲,某一科学家提出一种研究方案一定是基于之前自己所受的专业训练、已取得的成绩,同样也会考虑到目前已有的实验条件。比如在DNA发现的案例中,由于不同的学科背景,研究小组所处的不同地位,对研究局势的不同判断使得由威尔金斯、富兰克林和戈士林组成的皇家学院(伦敦小组)和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沃森和克里克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案。(17) 这个案例说明,“研究战略是根据科学家个人以享有的资源在不同的语境下做出创造性探索的机遇而定的”(18)。“不可能存在对研究机会的‘理论性’、‘客观性’的评估”(19)。事实上,如若存在这种“客观性”评估,应该所有的科学家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都得到同样的方案和同样的认识。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决定是非理性或主观的,而是说评估的理由不可能脱离关于对象和实践领域的需要,因为这也是处于地方性语境中的。
每一个实验室就是一个具体的语境,在这个具体语境中产生的知识不可避免会受到这个语境中研究人员的背景、研究方法的影响,这就是一种地方性的特征。“这种地方性的理解将告诉我们哪些相关的知识、实践和设备是必要的,将为我们弄清什么样的数据是充足的、什么样的理解是贴切的、什么样的器械室是‘好的’等而提供特定的、必需的基础”(20)。
四 科学文本中语境性的部分隐退
对科学的辩护往往是通过对其载体——科学文本的考察进行的。科学知识在实验室中的生产过程最终要通过科学论文的形式呈现出来。由于学术规范要求,论文在公开发表时,往往以一种非索引的语句出现。论文以严格的实验证明保留了“律则机器”起作用的核心条件,换言之,只要你按照论文中所用的方法、材料和步骤可以在另一个实验室构建起一个同样适用的律则机器。这里也正体现出传统科学哲学与科学实践的分歧所在。在传统科学哲学看来,实验的有效性、可重复性源于一种普遍性;而从科学实践的观点看,实验的可重复性源于一种地方性情境的移动,这否认了普遍性但并不否认客观性,只是这种客观性是有条件的。事实上,科学论文的形成与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高度相关,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科学论文在公开发表时,科学家就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去语境化了”(21)。这种去语境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实验室中研究活动的基础与科学论文中所表达的研究活动的基础有很大区别。实验室中研究活动充满语境性和偶然性,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特质,而科学论文中展现的则是一幅循规蹈矩且高度规范的理性行动过程,这种理性也体现在论文采取的标准格式上(包括内容摘要、简介、材料、方法等等各部分)。实验室中的发现和推理错综复杂,而科学论文中则以划分段落的形式把不同问题清晰地陈列出来。“论文中摒弃了个人利益和环境偶然性,将工作置于新的理性框架内”(22)。大量研究的真实理由(包括个人的利益等等)被隐去了,而仅仅变成了科学论文中的一行论证。(23) 这并非是科学家有意歪曲或掩盖实验室活动的真相,而是论文的规范形式使得语境性必须被隐去。
第二,实验室中的方法和材料与科学论文中的方法和材料有着明显不同。具体操作中,方法和材料的选择过程充满着利益融合与分裂,也渗透着科学家之间的商谈,但在论文中,方法不具备其自身的动态结构,更像是公式的背诵,步骤的简明核对表,是一系列被剥离了语境和理论基础的连续性操作。“总而言之,因为缺乏相关的语境化,方法呈现给读者的是非选择伪装下的选择流程图”(24)。
由此可见,科学知识从实验室中的生产到科学论文的展现,事实上经历了一个部分去语境化的过程。科学论文按照标准论文格式重新编排研究问题,方法、数据、对数据的分析和解释呈现出一种理性的过程,通过使用一些文字策略将真实过程中的偶然性和语境性隐藏起来,使自己的论述更为精确、可靠,将一种客观性的印象突出出来,将论文从其产生的语境中剥离出来,以一种部分去语境化的方式予以展现。然而,只要我们回到实验室,就可以发现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是语境性的,只有在语境中才能对其进行理解和辩护。
结语
我们从科学实践的观点来看,“发现情境”与“辩护情境”难以二分,其根本上源于科学知识与世界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反映和符合,科学知识的产生和辩护都依赖于一种特定情境,尤其是往往强烈地依赖于实验室的人工环境。从这一角度来说,科学知识本质上与其他种类的知识一样都是地方性的。逻辑经验主义之所以对“发现情境”与“辩护情境”进行区分,是为了给科学合理性一个更好的说明,那么,一旦我们承认科学的“发现情境”与“辩护情境”不能二分,是否就彻底否认了科学的合理性?对此,笔者认为并非如此。从上述对科学实践的考察来看,尽管科学知识产生和辩护具有语境依赖性,但并非怎么都行。卡特赖特的律则机器表明科学理论的适用有一定范围,仅在特定情境中事物本性才能展现,其观点的对立面不是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而是普遍性。事物的能力(capability)在律则机器中展现,模型在律则机器中与世界连接表明任何定律不具有普遍性,但具有一种实验意义上的实在论,或曰“局部实在论”。科学理论是局部为真的,这正是其合理性的体现。
实验室中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往往是自然的物质力量和研究者的人类力量的一种互动。科学家可能会根据自己已有的学科背景、专业训练挑选选题,设计实验,但人类力量并不能对自然力量完全操控。实践中物质力量表现出的对人类动机结构的脱离就是科学客观性的表现。在科学活动中,事情绝不是怎么都行。科学客观性在科学活动的个体实践层面上就已经存在了。但这种客观性并不表现为任何法则或标准。当这些标准在科学实践中起重要作用时,这些标准本身便依赖于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即皮克林所言的“缠结(mangle)”(25);社会主体所承载的不是科学知识的认识论法则,而是一些社会特性,它指向的不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而是科学知识的相对性。
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框架下,科学合理性的问题等同于遵守认识论规则和方法论规则,而在科学实践的框架下,科学合理性是由一种情境中的规范性所保证的,具体的情境决定了实践者行动的可能性选择。科学知识的产生是语境相关的,这一方面表明知识并非具有普遍性和反映论意义上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表明知识并非主观的、任意的。因为语境中的各种因素为科学知识提供了规则和约束力。此时,语境不是在一种语言层面而言,而是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正是语境与实践的关联使我们有可能在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植根于社会实践的理性。
当代对“发现情境”与“辩护情境”二分关系的探讨正沿着不同研究方向继续。客观而言,尽管以SSK为代表的社会进路对逻辑经验主义提出猛烈的批评,但其过于相对主义和经验描述的方法并不能真正得到传统科学哲学内部学者的认同。同时SSK也在发展中发生分化,一部分学者放弃“利益”的解释模式返回到对科学实践的研究中。科学实践为我们重新理解诸如观察与理论、自然与社会、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等等在传统科学哲学中“二分”的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我们提问的方式不再是决定与被决定、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变成几种因素如何在科学实践中关联起来,如何共同发挥作用。鉴于此,为了对“发现”与“辩护”的关系有更合理的解读,对科学知识的产生和辩护有更清晰、全面的了解,我们有必要对实践和具体的科学过程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注释:
① Hans Reichenbach,Experience and Prediction:An Analysis of the Found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7.
② 具体参见汉森:《科学发现的模式》;Nickles,Scientific Discovery,Logic,and Rationality,Reidel,1980.
③ Jutta Schickore,Friedrich Steinle,Revisiting Discovery and Justification:Historical and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Context Distinction,Springer,2006,pviii.
④ 具体研究参见孟强:《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12期,第563页;田小飞:《自然主义科学哲学及其规范性——基于多重维度的研究》,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08;盛晓明:《巴黎学派与实验室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3期,第65页等。
⑤ 已有多位学者对此趋势进行了讨论,具体参见吴彤:《科学实践哲学发展述评》,《哲学动态》2005年第5期;吴彤:《走向实践优位的科学哲学——科学实践哲学发展述评》,《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盛晓明:《从科学的社会研究到科学的文化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2期等。
⑥“Capacity”是卡特赖特的术语,大多情况下她用这个词表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本性。
⑦⑧⑨⑩(11) 南希·卡特赖特:《斑杂的世界》,王巍、王娜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第58页;第59页;第59页;第60页;第62页。
(12) Nancy Cartwright,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59.
(13) 这些研究包括女性主义科学哲学,以皮克林为代表的后SSK的研究,以哈金、卡特赖特为代表的新实验主义以及以约瑟夫·劳斯为代表的科学实践的解释学等。
(14) 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哲学研究》2000年第12期,第36页。
(15)(21)(22)(23)(24) 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王善博等译,东方出版社,2001,第63页;第88页;第184页;第187页;第209页。
(16)(18) Andrew Pickering,Constructing Quarks:A Sociological History of Panicle Phys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11.
(17)(19)(20) 劳斯:《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的政治哲学》,盛晓明、邱慧、孟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94-98页;第97页;第97页。
(25) 邢冬梅将其翻译为“冲撞”,参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时间、力量与科学》,邢冬梅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笔者认为“缠结”更能表达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