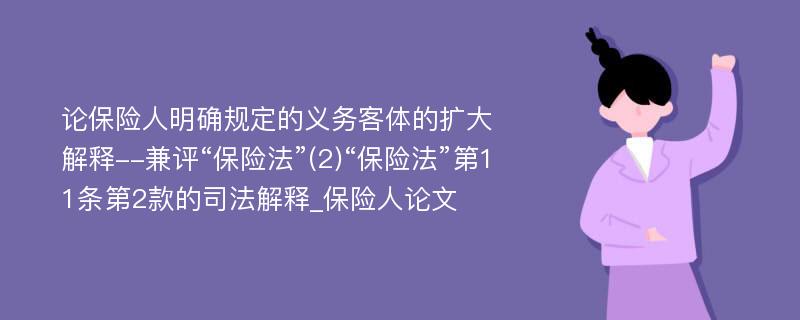
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对象扩张解释之检讨——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第2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险法论文,保险人论文,司法解释论文,义务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第2款规定,保险人应当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负担明确说明义务。①质言之,就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而言,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为三项,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与法律后果。由保险人对免除其责任条款的概念与内容作出明确说明殆无疑义,盖因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与内容属于保险产品信息之范畴,保险人较投保人而言享有信息优势,故为解决保险商品的信息不对称问题[1],有必要使保险人在其信息优势范围内对投保人负担明确说明义务。不过从该司法解释第11条第2款的规范内容来看,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不仅包括概念与内容,还包括法律后果。
然而从《保险法》新旧条文对比来看,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均为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1995年《保险法》第16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第17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2009年的新《保险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从明确说明义务条款的立法沿革中可以得知,立法者只是将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设定为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而没有进一步对内容与法律后果进行区分。基于司法解释是对现行法律进行解释的原则②,故应认为司法解释对现行立法作了相当程度的扩张,将原本作为明确说明义务对象的内容扩张为“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三种类型,且尤为强调“应对其(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法律后果进行明确说明”,[2]但是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与法律后果是否可分?保险人是否应当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一切法律后果负担明确说明义务?强行区分是否存在弊端?这些问题实值探究。
二、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中内容与法律后果的关系
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在理论上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说采实质标准,认为一切导致保险人不承担责任或减轻责任的合同条款都属于责任免除条款,而狭义说则认为倘若将一切可能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均认定为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则有加重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之虞,因此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应当解释为保险合同中所规定的除外责任条款。[3]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9条的表述来看,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了广义说,且采实质标准,认为“保险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可以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而事实上,无论采广义说抑或采狭义说,条款的内容与法律后果都是不可分的。
(一)狭义说:内容与法律后果混同
保险合同在性质上系属法律行为,乃保险人与投保人就具体的保险事务而为私法自治的工具,故在一定程度上,保险人与投保人基于有效的保险合同而结成了具体的法秩序,在该具体法秩序之下,保险合同条款之于合同双方不啻于法律条文,而从保险合同条款的写作方式来看,其也的确与法条相似。与法条内容一样,条款内容包含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两大部分。
以《机动车保险合同范本》③为例,倘若采狭义说,则该范本的第4条和第5条为明显的除外责任条款,即狭义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以该范本第4条规定为例,该条款规定,“本公司对下列事项概不负责:(1)战争、军事冲突或暴乱……(5)被保险人或其驾驶人员的故意行为”,从条文内容来看,(1)至(5)项属于具体事项的列举,系构成要件,而“本公司对下列事项概不负责”的表述则系法律后果。法学上的构成要件乃指法律赋以法律效力所必具之一切事实[4],通常情况下,法律在包含抽象的构成要件的同时也规定了法律后果,适用法律的常态为将需要审查的生活事实与法定构成要件进行比照,运用演绎逻辑,将具体生活事实作为小前提,并将之置于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要件之下,而结论则是法律后果。[5]保险合同除外责任条款与法条的逻辑结构完全一致:有关具体事项的列举事实上是在罗列可能导致保险人免责的构成要件,而一旦满足保险合同预先设定的免责事由,即符合构成要件,则发生免除保险人保险责任的法律后果;在此,条款内容包含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两大部分,条款内容与法律后果是融为一体的,故在狭义说下将内容与法律后果区分为保险人明确说明的两大对象存在事实不能的阻碍。
(二)广义说:内容与法律后果不可分
那么采广义说又如何呢?广义说之下,除了保险合同的除外责任条款以外,通常将保证条款、程序性条款和免赔率(额)条款纳入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之列[6],兹作类型化分析:
1.保证条款
保证条款与除外责任条款不同,其并不直接规定保险人在特定情况下免责,而是将保险人是否承担保险责任、承担多少保险责任与被保险人相应义务的履行情况挂钩,倘若被保险人没有履行或者瑕疵履行相关义务,则保险人有权依据保证条款的约定而部分或者全部免责,甚至获得合同解除权。以《家庭财产保险合同范本》④为例,合同第六部分为“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义务”,包括合同第15条至第18条,其中第15条至第17条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风险预防义务和防减损失及损失通知义务,而第18条则明确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如果不履行第十五条至第十七条规定的各项义务,本公司有权拒绝赔偿,或者自书面通知之日起终止保险合同”。从条文内容上看,与除外责任条款相似,保证条款的内容事实上也包含着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两大部分,只不过与除外责任条款相比,保证条款的构成要件由特定法律事实置换为了投保人、保险人义务不履行或者瑕疵履行的法律事实而已。
2.程序性条款
程序性条款是“涉及保险费的缴纳、赔款的支付办法、索赔的程序及提交的材料、争议的处理等方面”[6]的保险合同条款,其本身与除外责任条款和保证条款大相径庭,从表面上看似乎并不能将程序性条款纳入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范畴,不过从广义说之实质标准上看,程序性条款因其设定保险期间等程序性、期限性的条件以及合同生效条件等等的确可能出现免除或者减轻保险人责任的情况。以《建筑工程保险合同范本》⑤为例,其第六部分“赔偿处理”之(一)规定“对保险财产遭受的损失,本公司可选择以支付赔款或以修复、重置受损项目的方式予以赔偿,但对保险财产在修复或重置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变更、性能增加或改进所产生的额外费用,本公司不负责赔偿”。从该条文的内容来看保险公司拥有理赔方式选择权,同时又享有在保险财产发生任何变更、性能增加或改进情形下免于负担保险责任的权利,依广义说应当系属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作条款的逻辑分析,则该文除了具有赋予保险人保险方式选择权的内容外,也包含构成要件加法律后果的内容,即一旦满足保险财产在修复或重置过程中发生的任何变更、性能增加或改进所产生的额外费用的要件事实,即发生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的法律后果。在此,条款的内容与法律后果仍然不可分。
3.免赔率(额)条款
免赔率(额)条款,简称免赔条款,是保险合同载明的,保险人能够据以免除或减轻赔付保险金义务的条款[7],分为免赔率条款与免赔额条款。在条文设置上,通常保险公司会在保险事故实际损失的基础上计算免赔率或者直接规定免赔金额,并在条款中约定发生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损失的,保险公司在扣除免赔部分的基础上负担保险责任。从条文结构角度分析,免赔条款内容上仍然是由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组成的,即一旦满足保险事故发生的要件事实,即发生保险人依照免赔额度负担保险责任的法律后果。
就广义说角度所作的类型化分析来看,广义说项下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内容仍然遵循“构成要件加法律后果”的结构模式,条款内容由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组成,法律后果是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能够与内容相分离的独立的明确说明对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不管依广义说还是依狭义说,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与法律后果均不可分。在条文逻辑结构上,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采取的是类似于经典法条结构的“构成要件加法律后果”模式,奉行“只要具体案件事实S实现构成要件T,对于该案件事实即应适用法效果R”的逻辑规则,[8]条款内容包括一般法律后果,即一旦出现符合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所定之情形,则保险人即全部或者部分免除责任;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在内容之外并无独立的法律后果。当然,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不可能包含该条款所可能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如关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在合同法、时效法方面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等等,但这些法律后果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法律后果”,而属于保险合同可能引起的法律后果,而对这些法律后果,保险人不应对此负担明确说明义务。
三、强行区分内容与法律后果的弊端
(一)加重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
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的规定来看,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倾向于将法律后果作一个较为宽泛的解释,但问题在于,人为地将免责条款内容与法律后果割裂开来,使保险人分别对免责条款的内容与法律后果均负担明确说明义务则显矫枉过正。
根据前述条文结构分析,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与法律后果不可分,而强行区分二者只会令法律后果的内涵与外延均发生不恰当的扩张。倘若要求保险人必须对保险合同文本中免除责任人条款之内容与法律后果分别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则投保人不仅会要求保险人明确说明免除责任人条款法律后果的各构成要件与符合构成要件之后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还可能要求保险人明确说明该条款可能引起的其他法律后果,如诉讼时效届满、保险期间届满所引起的投保人相应民事请求权减损的法律后果[9],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发生法律效力而可能导致的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法律后果、保险人保留保险费的法律后果等等,但保险人并非法律专业人士,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所可能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而言,保险人并不必然享有信息优势,设若投保人是保险实务执业律师,则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各种法律后果可能比保险人更为熟悉,且事实上一旦因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而发生法律纠纷,该条款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是由人民法院的司法裁判决定的,保险人不太可能在纠纷发生之前便明确知道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可能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因此宽泛化地将一切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法律后果均纳入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对象的做法无疑过分加重了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强行要求保险人对法律后果负担明确说明义务一方面在实务难以实现,另一方面因保险人难以对法律后果作出明确说明,所以会有较高概率蒙受更大的因不能明确说明法律后果而引致相关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的不利性法律后果,从而造成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严重失衡,使保险人负担沉重的信息提供义务。此举可能增加保险人在诉讼中因明确说明义务履行瑕疵而败诉的风险,加重保险人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如对保险业人员进行细致的法律培训)而必须付出的经营成本,从长远看并不利于保险业的长远发展与全体投保人的利益。
(二)违反《保险法》立法宗旨
从《保险法》条文所反映出的文本信息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区分内容与法律后果的解释方式并不能经由法条而直接证成:法律后果与法条原定之“内容”并列,这种解释方法系属目的性扩张,而非狭义的扩张解释。狭义的扩张解释与目的性扩张不同,前者乃狭义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种,虽有目的上的衡量,但重在将法条隐含的含义发掘出来,且最终的解释仍然在法条文义的射程之内,而后者则为一种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其径行由法律目的出发,将符合规范意旨的某种未为法条文义所包含的事实类型解释为法条效力能够涵盖的情形。[10]最高人民法院将《保险法》第17条之“内容”细化解释为概念、内容与法律后果。概念尚可为内容所涵盖,因为一切内容都是概念组合的产物;但是将法律后果与内容并列规定的方式则在事实上割裂了内容与法律后果内在的有机联系,法律后果成为了明确说明义务对象的一种具体类型,拥有了独立的保险法律概念地位,获得了相对于内容的独立性——故司法解释对《保险法》第17条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不能为法条所涵盖的造法,一旦区分内容与法律后果,法院不仅会要求保险人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而且会要求保险人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法律后果,如果保险人对法律后果的说明没有达到明确之程度,则会引起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不发生效力的法律后果[11],这显然对保险人是十分不利的。
为了保障公民自由,法律解释应当遵循一系列的原则,尤其应当尊重立法宗旨,不能为了权宜之计而扩张法条的意涵。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法律条文进行司法解释时,应当遵循法律解释不得超越法律本身的原则,不能任意地为法律的续造活动。尽管立法者的确为了保障投保人的利益而给保险人设置了明确说明义务,但是司法者却无权为了进一步保护投保人而超出法律的意思范畴加重保险人的负担。所谓司法公正,“在裁判实体上”,应当“坚持权利标准,保护法律权利,对当事人做到有权利就保护,无权利就不支持,侵犯权利就给予制裁”[12],法院对当事人的保护不能超出法律所限定的权利义务范畴,不能对法定的权利义务格局作出较大变更以增强一方权利,加重另一方义务;司法者须在法律的框架体系下进行司法活动,而不能有所僭越。《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将《保险法》第17条中的“内容”解释为“概念、内容与法律后果”的做法是一种 违背立法者原意的不当目的性扩张,有违司法公正理念。
(三)导致明确说明对象的模糊性、宽泛性
事实上,对比2000年的《答复》与2013年的《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关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对象的规定,仍有细微差别,《答复》的表述为“‘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13]。该《答复》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相比,对明确说明义务对象的规定持更为开放的态度,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则去掉了“等”字,从而将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类型化为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与法律后果三项,对明确说明义务对象进行了限定。从前述文本比较可知,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也意识到不能将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宽泛化,否则将使保险人承担极为沉重的信息提供义务,故去掉“等”字,以使义务对象明晰化。不过从法技术角度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引入法律后果这一概念作为明确说明义务之对象,不仅没有使对象得以明晰,反而会使对象问题复杂化。
尽管根据前述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结构分析,我们会发现该条款的确蕴含着一般性的法律后果,即使保险人部分或者全部免除保险责任;这种一般性法律后果蕴含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无法与之区分,同时事实上这种法律后果也不需要作出多少明确说明,因为一旦投保人知晓条款内容,也就知道在何种构成要件下保险人会部分或者全部免责。那么,将法律后果单列为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会产生什么影响呢?首先必须澄清的是,法律后果这个概念本身具有多义性,如有学者从规范主义的角度解释法律后果,认为法律后果是立法者对社会主体所选择的行为给予的立法评价;[14]而倘若采法律现实主义的观察视角,即将法律条文视为对法官行为的预测,而将法官裁判视为真正的法律,那么法律后果应当被理解为纠纷发生之后,法院依据法律而作出的司法裁判。[15]
在笔者看来,法律后果蕴藏于法条中的预设性立法评价,但体现在立法文件,即法律文本中的法律后果是抽象的,法律后果的生成与具体化依赖于司法机关依法作出裁决,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后果事实上只存在于法院的裁判文件中。以《机动车保险合同范本》⑥为例,该范本第4条规定,“本公司对下列事项概不负责:(1)战争、军事冲突或暴乱……(5)被保险人或其驾驶人员的故意行为”,其中属于法律后果表述的文本为“本公司对下列事项概不负责”,对于该段文字做明确说明,则保险人一般会进一步向投保人解释说一旦投保人的保险事故有条款中涉及事项的,则保险人不向投保人承担保险金给付的责任,或者更为通俗地解释为一旦发生这些约定事项,保险人就不会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金。这种说明仅仅只是对寓于免责条款内容之中的抽象法律后果的说明,保险人不可能向投保人明确说明一旦发生约定事件则法院即会做出相应确定裁判的具体法律后果,因为是否支付保险金,并不仅仅取决于保险合同的约定,还受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双方权利主张的积极程度、禁反言规则、时效制度等具体情况的约束,保险人不可能未卜先知,先于纠纷之发生及法院之裁判而事无巨细地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因此要求保险人对宽泛意义上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确说明对于保险人而言是难以做到的。
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法律后果只能被限定解释为“使保险人部分或者全部免除保险责任”的抽象法律后果,且结合前述分析,这种法律后果与内容在事实上是不可分的。而强行将法律后果与内容向区隔的作法极有可能将具体法律后果以及其他抽象法律后果纳入明确说明的范畴,从而使法律后果概念模糊化、宽泛化与不确定化,极大增加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难度,既过分加重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也无端使司法裁判更加复杂且更富不确定性。
(四)破坏符合现行法律规范的司法态度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0年时便将保险人免责条款的内容与法律后果予以区分,不过从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判例来看,这种态度并未得到彻底的贯彻。各级人民法院在认定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对象时,主要由以下几种态度:
1.将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限定为免责条款的内容
实务中,很多法院通过引用《保险法》第17条(2009年修正前为《保险法》第18条),将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限定为免责条款的内容。例如在“王学兴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国县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中,江西省兴国县法院认为“根据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被告应向原告或投保人明确告知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及保险人的免责条款”⑦;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在“王凤莲诉中国人寿新郑支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应按保险合同理赔案”中主张“所谓的‘明确说明’是指,保险公司在与对方签订保险合同时,对于责任免除条款应当在保险单上或其他保险凭证上对免责条款做出能够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且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做出解释”⑧。这种将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限定为免责条款内容的解释事实上是对《保险法》条文的文义解释。
2.引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但没有实质性地区分内容与法律后果
法院在解释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对象时,还有一种通行方法是引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出台的关于明确说明的司法解释。例如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在“赵可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中认为,“法律规定的‘明确说明’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明示、告知,而要求的是解释条款的内容。具体而言,除了对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在保险合同(保险单)明显位置提示投保人(被保险人)注意外,重要的是保险人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其代理人作出明确解释,以使投保人(被保险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⑨。
该论断有趣之处在于法院认为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对象为条款的内容,但是具体而言,保险人应当明确说明的便是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仅依据简单的逻辑推理便可知法院前后的论断存在一定矛盾之处:既然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是内容,那么为什么又将法律后果等事项列为与内容并列的明确说明义务对象呢?结合该判决的语境与上下文,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该判决并未实质性地区分内容与法律后果,法律后果只能被解释为内容的一部分,而该判决之所以将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具体表述为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主要是为了引用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司法解释以增强判决的权威性,并无区分内容与法律后果的意图。
此外,在“石狮市逍遥狮服饰贸易有限公司诉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⑩、“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州中心支公司与重庆万州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11)等案例也明确认为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为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不过这种表述却并没有实质上实现内容与法律后果的区分,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事实上被统一为免责条款的内容而被法院作为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予以考量。
3.具体解释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内容的意涵,但不区分内容与法律后果
实务中也有法院即没有固守最高人民法院对明确说明的司法解释,也没有仅仅将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限定为免责条款的内容,而是自己对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作了更为具体的扩大解释,例如广东省佛山 市顺德人民法院在“张肖媚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中认为“由于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对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负有明确的说明义务,……在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其已向原告就免责条款的内容、术语、目的及适用方面予以解释从而履行了醒义义务的情况下,应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12),故可知该法院将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由法条所规定的免责条款“内容”,扩张为免责条款的“内容、术语、目的及适用方面”。不过仔细分析,免责条款的术语是内容的语料,适用则属于内容所涉及的法律效力,目的则可以被解释为构成条款潜在内容的免责条款所应发挥的在特定情况下,保险人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免除保险责任功能,故此种解释本质上是对免责条款内容的具体化,而非对明确说明义务对象的类型化。
4.形式上区分内容与法律后果
在笔者的检索中,没有完全区分免责条款的内容与法律后果的判例,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区分二者的判例还是存在的,例如湖北省汉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汉油田支公司与江汉油田联发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中认为,“财保公司对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联发公司注意外,还应对此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使联发公司明了王涛因是‘本车上的其他人员’,第三者责任险对其免责。”从此段论述中可以理清该法院的逻辑:第一,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是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第二,具体来说,保险人明确说明“本车上的其他人员”属于对免责条款概念与内容的说明,而保险公司明确说明“第三者责任险对其(王涛)免责”便是属于对免责条款法律后果的说明。不过结合本文前面的论文,“第三者责任险对其(王涛)免责”在免责条款的由“构成要件加上法律后果”所组成的内容体系下,事实上仍旧属于免责条款内容的一部分,没有超出免责条款内容的内涵与外延,故法院的区分仍然只是形式上的区分,并未实质性的将免责条款的内容与法律后果予以区隔。
因此,通过对司法裁判的类型化探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实务上对明确说明义务对象的理解事实上都没有超出《保险法》第17条所限定的“内容”之范畴,法院一般不会将免责条款的法律后果视为与免责条款的内容地位平等的明确说明义务对象,即使将内容与法律后果予以并列,也只是认为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法律后果的明确说明恰好是其对免责条款内容进行明确说明的一种具体表现方式。司法实务中区分内容与法律后果的解释未得到贯彻的主要原因在于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所做的司法解释只是一个答复,故仅具有个案效力,各级人民法院并未将内容与法律后果的区分一般化。但是《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第2款的出台使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内容与法律后果的区分变得具有普遍适用效力,极有可能破坏既有的司法惯习,并最终使保险人在司法裁判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四、明确说明义务对象应限定为免责条款的内容
从比较法角度来看,规定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是我国《保险法》的一项特色,根据学者的考证,我国保险法关于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规定属创新之举,“查外国保险立法,未见有此规定者”[16]。
作为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确有助于削弱保险人相对于投保人的信息优势,有利于投保人更加明确地了解保险产品的信息,从而令投保人与保险人就保险合同条款达成真正的合意。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较之于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立法者的确苛加给了保险人较重的说明负担。倘若在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对象的问题上区分免责条款的内容与法律后果,则可能进一步加重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增加保险人的营运成本和保险纠纷败诉风险,从长远看,不利于保险业的发展以及全体投保人的利益。故我们应当坚持对《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做文义解释,将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限定为免责条款的内容,不宜区分内容与法律后果并对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进行扩张。 须知,保险人不应当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一切法律后果均负明确说明义务,惟其如此才能维持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衡平的权利义务关系。
注释:
①参见《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第2款:“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
②关于司法解释的效力与规范位阶问题学界存在广泛争议,有学者持较为激进的看法,认为司法解释效力直接来源于宪法,具有准法律的效力,新的司法解释甚至优于法律适用(参见蔡祺燕:“司法解释效力论”,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8月期);也有学者持较为传统的观点,认为司法解释效力来源于宪法与法律,司法解释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但在位阶上应当高于行政法规(参见蒋德海:“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的法律效力应规范化”,载《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笔者采较为保守的司法解释观,即认为司法解释只能在现行法范围内对特定法条进行解释,而不能为法律之续造。
③该范本来源为:http://www.diyifanwen.com/fanwen/baoxianhetong/128502273952890.htm(第一范文网),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9月27日。
④该范本来源为:http://www.diyifanwen.com/fanwen/baoxianhetong/128502275073644.htm(第一范文网),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9月28日。
⑤该范本来源为:http://www.diyifanwen.com/fanwen/baoxianhetong/129917350276544_3.htm(第一范文网),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9月28日。
⑥该范本来源为:http://www.diyifanwen.com/fanwen/baoxianhetong/128502273952890.htm(第一范文网),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11月6日。
⑦参见“王学兴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兴国县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江西兴国县人民法院(2006)兴民二初字第601号判决书。
⑧参见“王凤莲诉中国人寿新郑支公司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应按保险合同理赔案”,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郑民终字第375号判决书。
⑨参见“赵可诉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鞍山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2007)东民三初字第762号判决书。
⑩参见“石狮市逍遥狮服饰贸易有限公司诉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泉州中心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2007)鲤民初字第33号民事判决书。
(11)参见“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州中心支公司与重庆万州区农村信用合作社财产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6)渝二中法民终字第547号判决书。
(12)参见“张肖媚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公司保险合同纠纷再审案”,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佛中法民二再字第41号判决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