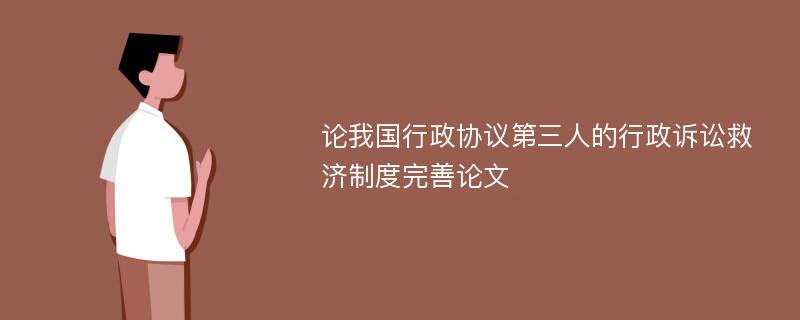
论我国行政协议第三人的行政诉讼救济制度完善
王 聪
(福州大学 法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 要: 由于我国立法的空白和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漏洞,使得司法实践中在如何保护行政协议第三人的权益这一问题上存在诸多难题和困境,如行政协议第三人的原告资格难以认定、第三人救济手段有限、行政协议争议案件的司法审查模式不确定等。针对这些问题和困境,可以通过尽快确立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采用“可分离行为”的司法审查模式和增添预防性行政诉讼救济类型等措施,在司法层面上尽快构建和完善行政协议第三人的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关键词: 行政协议;第三人;行政诉讼救济
目前,虽然我国已经明确将行政协议纳入到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对于在行政协议之外的第三人,法律和司法解释都没有作出明确和具体的规定来保护其权利和利益。因此,行政协议第三人希望通过行政诉讼来寻求救济的方法存在巨大阻碍,也同时意味着当前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重大漏洞。同时,人们在合同具有相对性的思维导向下常常会忽视第三方主体的利益。而在我国学者关于行政协议的文献中,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行政协议的类型和范围、行政协议当事人的权利保护等问题上,针对行政协议第三人的文献却寥寥无几、研究甚少。但事实上,行政协议外的第三方主体是否可以针对协议提起诉讼?如何确定该类案件的司法审查模式?行政协议第三人在受到损害后如何寻求司法救济?这些问题都是目前司法实务中面临的难题和困境。
一、行政协议第三人的涵义及特征
由于我国对行政协议外第三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立法上尚未对行政协议外的第三人作出统一明确的定义。在此条件下,部分学者参考民法领域中关于合同第三人的内涵,从广义上为行政协议第三人的概念作出了宽泛的界定,即指除协议缔约方外的其他与协议具有利害关系的主体[1],并指出相较于其他相近的法律范畴,其具有自身明显的特征。
首先,行政协议中的第三人与相对人不一样,它并非协议的当事人。因此,无论是行政机关在签订、履行协议时还是发生纠纷后法院在司法审查时,都会更多的考虑协议相对人的权益保护。但现实中,行政协议往往会涉及到第三人或是公共利益,而其因为并非是协议的当事人,所代表的权益容易被忽视,往往得不到保护。
其次,当行政协议第三人的利益受损时,他并不是只能以行政协议诉讼第三人的身份来寻求司法救济。在行政诉讼中,他也可能以原告的身份出现。同时,他也可能通过民事诉讼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再者,与行政主体相比,行政协议第三人处于弱势地位,而民事合同中的第三人仍然处于与当事人平等的地位。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协议第三人更有可能因为协议而受到侵害,但寻求救济的方法和渠道却存在更多的障碍。
因此,对于行政协议第三人的权益保护机制的设计不能完全套用民事合同的诉讼制度和行政协议相对人的相关保护制度。因行政协议第三人的上述特征,其司法救济制度也更具有特殊性,需要结合多方面的因素进行专门的考量设计。
根据山洪形成机理和灾害发生特点,各级平台建设的功能有所侧重。县级平台在获取各类监测信息的同时,强化预警信息发布和响应信息反馈功能;市级平台在充分实现各类监测信息共享的同时,强化督促、预警监视、信息汇总、信息服务和会商功能;省级平台在全面实现市级平台全部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为跨系统数据共享提供接口。省、市、县三级平台同时建设,有效地增强了省、市对各地山洪灾害预警响应情况的监督和指导作用。
二、我国行政协议第三人的行政诉讼救济困境
(一)行政协议第三人的原告资格认定困难
行政协议第三人作为一种特殊主体,当其希望通过提起行政诉讼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时,则须先获得原告资格。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明确将行政协议纳入到了行政诉讼的范围,为非缔约方的第三方主体对行政协议提起诉讼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但针对第三人的原告资格是否应被承认的问题仍存在争议。由于目前我国相关条文规定过于抽象和模糊,各个法院关于其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也难以统一。因此,尽快确立和统一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对维护和保障第三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诉讼法》第25条①规定的“利害关系标准”则是当前我国关于行政第三人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这一标准明确了第三人在其与某一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时,才会被认定具有原告主体资格。然而,这一标准十分的模糊宽泛,存在一定关系的事物间可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何况,如何界定二者具有利害关系?达到何种程度视为具有利害关系?这种判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因此,仅仅根据这一标准无法使法官在审查行政协议争议的案件时,有效地从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中识别出除行政行为相对人外的哪些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影响到行政协议第三人的权益保护。例如在哈尔滨惠民彩印厂不服道外区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与塑五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纠纷案②中,法院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相关规定,认为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被征收人应当为所有权人,而不包括租赁人。而此案中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塑五公司,原告哈尔滨市惠民彩印厂则为其租赁人,不属于被征收人和补偿对象,从而认定原告与涉案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被告与第三人塑五公司签订)没有利害关系,哈尔滨惠民彩印厂因此不具有该案的原告资格。但惠民彩印厂作为房屋的实际使用人已长达数年,而被告与塑五公司关于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将导致惠民彩印厂无法继续在该地块上经营,且相关的搬迁和补偿费用也均未给予原告,由此该协议的签订确实在实际上使惠民彩印厂的权益受到损害。但其作为行政协议第三人却因为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没有得到承认,而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寻求救济,维护自身的权益。
(二)保障行政协议第三人的司法审查标准尚未确立
行政协议具有两大明显的特征,而正是这两大特征使得法院在对行政协议的效力审查时存在诸多障碍,即行政性与契约性。行政性特征使得行政主体可以对协议进行单方变更或解除,但这是否说明其所作出的单方职权行为与协议是同时存在的?二者之间的效力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些都是司法审查中亟待厘清的问题,涉及到司法审查模式的建立、法律规范的适用和诉讼救济途径的选择等,同时也会影响到签约相对人和第三人的权益保护。
首先,协议第三人的权益受损应当与所诉行政协议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即行政协议第三人在诉讼制度上应仅限于对协议有明确利益的第三方主体。行政协议第三人所主张的合法权益应是行政机关在签订或履行行政协议的过程中依法应该予以考虑的利益。如果行政机关在签订或履行行政协议的过程中不需要考虑或根本不能考虑到,那么行政机关或行政协议相对人就不具有行政法上的可归责任。此时,该第三人也就不应该被赋予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其次,在我国目前行政协议诉讼制度仍处于初步构建的背景下,建议在原告资格的问题上采取循序渐进的态度。因此,建议对只有确有必要通过行政协议诉讼来维护自己权利的第三人,才应当给予原告资格。也就是说如果行政协议第三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来寻求司法救济,那么此时,该第三人就不应被赋予原告资格。虽然此项建议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仍然排除了一部分第三人通过行政诉讼维护权益的途径,但基于我国当前的司法现状和背景,这样的认定标准更具有可行性,也更易于操作。
事实上,行政协议的实施常常会侵犯第三人的利益。例如,在第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行政协议的内容侵害了第三人的权益,甚至行政机关根据此协议对第三人的权益进行无权处分等。而面对行政协议经常侵犯第三方和公众利益的现实,司法审查是第三方寻求救济,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在实务中,根据审判者传统的思维定式,只有行政行为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才是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况且在2014年之前,我国立法者尚未明确将行政协议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其性质尚未明确界定。因此,出现很多针对与行政机关签订的协议所提起的诉讼,法院一方面认定该协议为行政协议,另一方面却将其纳入到民事程序进行处理的现象。即便2014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和2015年最高院发布的司法解释中的部分条款涉及如何审理行政协议争议案件的问题,但也只是为协议的缔约方设计了一系列初步审查规则,而没有考虑到行政协议的第三方。并且由于行政协议争议案件审查内容复杂,各个法院的标准尚未统一,在法律适用问题上也一度陷入民事和行政两种法律规范选择混乱的状态。因此,行政协议第三人的权益在我国当前模糊不清的司法审查模式下难以得到有效的维护。
古代的士大夫书家,是不屑卖作品的。因为,士大夫们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高,不需要艺术作品来养家糊口。但是,目前不一样了,任何人都无法脱离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市场经济,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书法家在市场面前,不同的人一定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抽象化地思考这些问题。你觉得文学的商业化问题是些什么?
(三)行政协议第三人权益受损害后的救济存在诸多障碍
2.“可分离行为”的审查模式
三、我国行政协议第三人的行政诉讼救济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确立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
上述第一个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确定了可能具备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第三人的范围,而第二个必要性的判断标准则是进一步缩小了范围,即排除了能够通过其他司法途径来主张自己权利的第三人。这种判断标准一方面可以避免第三人在选择诉讼程序时可能面临的混乱状态,一方面可以避免扩大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资格的范围,将行政协议第三人的诉讼控制在行政机关可以承受的范围、避免滥诉。
TOD模式是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是规划一个居民或者商业区时,使公共交通的使用最大化的一种非汽车化的规划设计方式。例如,东京城市发展的特点是综合交通枢纽引导城市功能布局,其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和规划的依据是首都中心的发展情况,轨道交通网络规划中城际线依托枢纽、覆盖5个新城及主要新市镇的市域线网络。除此之外,政府应该借助TOD模式,在枢纽的基础上,设置相关的公共设施,如社区行政管理、文体教育、医疗卫生等,以充分发挥出枢纽在重点新市镇中的集聚作用和引导作用。
而另一特征契约性使得行政协议也同时需要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即只有当事人受合同约束。我国民法实际上是严格遵循该原则,第三人无法对合同主张权利。但我国民事合同的第三人在受到损害后有其他的救济手段,例如可选择通过侵权责任法来寻求司法救济。但行政协议则不同,它是合同方式向行政领域扩展的产物,其中的利益关系并非仅有合同的双方当事人,而是呈现出了一种多维复杂的态势,是一种特殊的合同。[1]何况与民事合同中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第三人都处于平等地位不同,行政协议第三人相对于作为协议当事人一方的行政主体来说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如果只是单纯的套用民事诉讼模式进行司法审查,那么就相当于否认了行政协议的行政性,无法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行政协议第三人和公共利益进行维护。
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和行政协议的特殊性,为了更好的保护行政协议外第三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我国还应正式确认行政协议第三人的原告资格。但是如果将原告资格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行政协议的第三方,将不可避免地降低行政机关的行政效率、浪费司法资源。因此,应当确立行政协议第三人原告资格的认定标准,只有符合一定的标准的行政协议第三人才有权利提起行政诉讼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这一问题上除了遵循上文所提及的“利害关系标准”之外,为了节约诉讼资源,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还可以确立如下具体的、可易于操作的判断标准:
(二)确立“可分离行为”的审查模式
1.法国关于行政协议第三人的司法实践
行政合同是法国行政法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项制度,多年的司法实践经验使得法国行政协议第三人权益保护体系已经建构并日益完善,而我国关于行政协议第三人权益保护的司法实践经验严重不足,因此,借鉴法国已经相当成熟的司法经验十分必要。
2.1 基本资料 患者82例,男59例,女23例,年龄18~96,平均(66.13±18.26)岁,均为汉族。其中一般脓毒症5例,严重脓毒症24例,脓毒症休克53例。平均住院时间(13.23±10.07)d。肺部感染50例,腹腔感染15例,癌症8例,糖尿病5例,外伤3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1例。54例死亡,28例存活。死亡组及存活组患者临床基本资料在性别、年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死亡组APSCHEⅡ及SOFA均比存活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在法国,诉讼分为越权之诉(客观之诉)和完全管辖之诉(主观诉讼),前者是由行政法院管辖,后者是由普通法院管辖。[2]在行政协议制度成立之初,行政协议的第三方主体没有资格提起越权诉讼。直到20世纪初,最高院通过1905年的Martin案和1906年的Croix-De-Seguey-Tivoli案才确认了行政协议第三人在自己权益受损时,可以对与协议具有关联的行为通过越权之诉来寻求救济。[3]其中,在Martin案中,最高行政法院赋予了行政协议第三人对与行政协议可分离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越权之诉的权利。所谓可分离行为,是指与合同有关联但尚未触及其内容的行政行为,比如行政机关做出的同意签订相关合同的行为。法院认为虽然这些行为与行政协议存在关联,但却是可以分离的,因此应该允许第三人对可分离行为的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
目前,我国并未对在行政协议第三人权益受损后的救济问题进行任何规定,再考虑到行政协议中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立法的空白也使得其在救济渠道的选择上存在诸多障碍。首先,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行政协议第三人权益保护的规定寥寥无几,并且保护方式也是以权利受到侵害之后的事后救济为主,而关于事前保护的立法基本没有。其次,在其他实体法律规范中,《合同法》关于认定合同无效的条款可能可以参考。但这仅仅是私法上的救济,由于我国行政协议诉讼制度才刚刚建立,行政协议第三人如何在公法上获得救济是急需解决的问题。另外,有些协议是否为行政协议存在争议,协议的相对人想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问题可能都存在一定困难,更别说在协议之外的第三人了,其想通过司法途径维权更是难上加难。
法国为了保障第三人利益而创造了“与行政合同可分离行为”的概念,即将与行政合同有关联但尚未触及合同内容的行政行为与协议相分离,这一创新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其实根据我国最高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可以发现我国制定有关行政协议争议案件的处理规则时,也有类似将行政协议拆分为两个部分的倾向。因此,结合我国现实和立法现状,参考法国“可分离行为理论”,为了使我国行政协议第三人的利益有更多的救济渠道,行政协议的效力认定可以适用“可分离行为”的审查模式。在具体操作中,可以首先将整个过程分为缔约和履行两个阶段。在缔约阶段,行政机关处于强势地位,协议的行政性特征明显突出,故应适用行政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履行阶段协议的契约性开始显现,呈现出两大特征同时存在的状态,因此,首先将行政机关的单方职权行为与契约行为分离,再分别适用公法和私法两种不同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
在我国当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下,行政协议当事人在诉讼类型的选择上基本不会遇到阻碍,通常可以选择一般给付之诉或确认之诉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是,由于法律中的相关规定言语模糊,行政协议第三人是否也能选择确认之诉或撤销之诉以寻求救济仍不明确。并且我国当前的行政诉讼制度主要以事后救济为中心,目前几乎不存在关于事前救济的规定,无法避免即将履行的协议可能给协议外的第三方主体造成的损害,不能有效保障其合法权益。因此,建议在协议的缔约阶段,增添预防性行政诉讼,给第三人提供更多的救济渠道。这种类型诉讼主要是指为了防止即将实施的行政行为给协议相对人或第三人造成重大损害,允许协议相对人或第三人在该行为作出之前请求法院阻止。这可以看作是在缔约阶段增添一种事前救济的诉讼类型,使协议相对人或第三人被侵害的可能被扼杀在协议成立之前。这一诉讼救济类型的扩增不仅可以保护行政协议当事人的权益,更有助于维护第三人和公共利益。
(三)增添预防性行政诉讼救济类型
例如,根据上述方法,典型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就可以拆分为缔约阶段和履行阶段。首先,缔约阶段则指行政审批。在这一阶段,行政主体主要利用其权力来确定和选择缔约方,是具有明显的单方职权行为性质的行政许可行为。在这个时候,因为协议尚未签订,故该第三人还并不属于真正的行政协议第三人。但其具有第三人的效力,因为行政法律等规范赋予了其保护权益的资格和手段,即第三人可以对在缔约阶段的行政许可行为提起行政诉讼或申请行政复议。其次,履行阶段则是指行政机关与其选择的合作对象实施特许经营协议。在正式签订协议后,其契约性特征开始显现并发挥功效。但即便在这一阶段契约性特征明显,也不能忽略协议背后同时隐藏的行政性特征。虽然此时行政机关看似脱下其强制性的外衣,但由于协议具有行政性,故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却一直存在其中。例如,行政机关对协议中的项目进行监管时被特许人必须配合,并且行政机关根据相关法规政策享有更多的像可以单方解除合同等强制性的权力。所以在这一阶段需要将协议的单方职权行为与契约行为分离,前者适用行政法律规范等公法调整,后者则参考适用民事法律。[4]
2.3.4 临床资料的判断:(1)是否可靠:必须判断收集的临床资料是否可靠。从患者本人处获得的病史和症状一般来说比家属可靠,但如果患者意识障碍、失忆或需要了解童年时的发病情况,家属的陈述就比本人可靠。患者口头叙述的情况就不如当年医生写的检查记录报告、出院小结等医疗文书可信。细菌培养结果的可靠性与标本来源关系很大,咳出痰培养的结果就不如防污染毛刷采集气道分泌物的结果可靠。经纤维支气管镜肺活检采集组织的病理检查结果不如手术切除标本可靠。
综上可以看出,长久以来我国学者对如何保护行政协议第三人权益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甚少,而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又在此问题上存在着漏洞,使得其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和困境。从表面看,无论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还是构建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似乎只是针对第三方主体,但从法律制度的深层建设意义来看,这一制度的完善和构建则是对多方利益进行协调和平衡的结果。
注释:
(3)浑河、苏子河的氮输入对抚顺取水口处各水质要素的影响相当,减小苏子河的磷输入能更有效地降低抚顺取水口处的叶绿素a浓度。该研究以期为大伙房水库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及水质管理提供理论指导。
① 《行政诉讼法》第25条:“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诉讼。”
水稻种子的质量影响着机械设备的调整情况,进行加工检验得到的质量较差的种子的比率,使机械设备调整的依据,工作人员可以根据这份数据,进行机械设备的相关数值的调整,使机械设备的数值符合这批种子的质量规格,能够更有效的进行种子的精选工作,选出饱满度较高的种子,从而提高种子的发芽率。
② 详见:(2016)黑0104行初20号案例。
参考文献:
[1] 邹利琴.论行政合同中的第三人 [J].研究生法学,2000(4):16-20.
[2] 杨解君.法国行政合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12-128.
[3] 陈天昊.在公共服务与市场竞争之间法国行政合同制度的起源与流变[J].中外法学,2015,27(6):1556-1657.
[4] 龚卉.行政协议第三人效力适用规则之维度把握[C]//深化司法改革与行政审判实践研究(下):全国法院第28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2017:1282-1291.
On the Improvement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nd Relief System for the Third Party in China's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WANG Cong
(School of Law,Fuzhou 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108)
Abstract: Due to the gaps in China's legislation and the loophol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system,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and dilemmas on how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ird parties in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For example,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of the third party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is difficult to identify.Third party remedies are limited,and the judicial review mode of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dispute cases is uncertain.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and dilemmas,we can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judicial level as soon as possible by establishing the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plaintiff qualification of the third party in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adopting the judicial review mode of“separable behavior”and adding types of preventiv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relief.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relief system for the third party of the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 should be improved as soon as possible.
Key words: administrative agreement;third party;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relief
中图分类号: DF41
文章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109(2019)02-0016-05
收稿日期: 2018-08-25
作者简介: 王聪(1993-),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经济法学研究。
(责任编辑:冯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