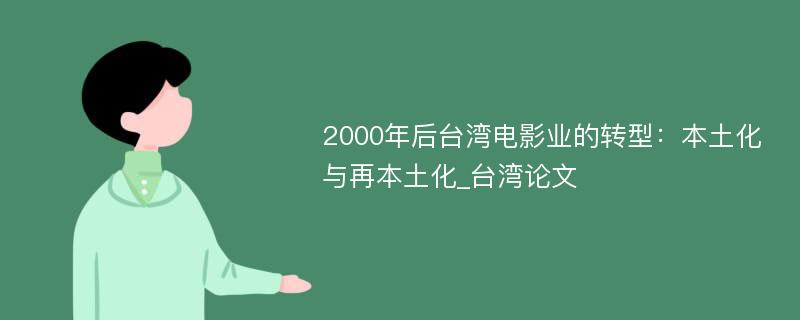
2000年后台湾电影产业的转向——去在地化与再次在地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地论文,化与论文,年后论文,台湾电影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美国电影产业与台湾地区电影产业竞合关系的流变
电影产业包括制作、发行和映演三个部分。电影在诞生之时就牵涉本体问题,它究竟是一种文化还是商品?当代艺术家安迪·沃荷①形容他自制发行的电影出现在真实世界的戏院广告牌上时,而非在艺术世界里,是教我们如痴如醉的。如同他所言:赚钱是一种艺术,沃荷的概念凸显着美国对电影产业的本体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它以全球为市场,在政府的协助下,夹带大资本的故事片、明星制度、经验丰富的电影技术及发行模式,以影视产品成为其主要出口收入之一。然而,面对经济导向的好莱坞,许多国家在地的电影工业面临其强势压境,使得各地政府与民间为因应电影工业的兴衰,而不断地陷入艺术文化保护与经济商业市场自由竞争的论辩中,加上日渐严重的文化趋同现象使各国忧心,使得文化权与传播权不断成为讨论的议题。②
70年代之后,中国台湾地区是美国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市场,但在1973年台湾地区相关电影工会组织提出“改善外片配额办法及辅导“国片”方案”,除了降低外片配额,进而从外片配额制度衍生出国片辅导金筹募办法,在“进口”外片中随片征收辅导金十万元新台币。正当与美方关系恶化后,一方面台湾地区在1982年正掀起新电影运动,拍起属于自己的故事。另一方面在1985年美国政府将保护知识产权的“著作权法案”列入“关税贸易总协议”(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促成“贸易知识产权协议”,会员国的盗版盗播都将被取缔。是年,美国电影输出协会提出301条款控诉案为要挟,要求台湾地区取消外片配额,停征“国片”辅导金及开放外片拷贝。同年10月,在“北美事务协调会、美国在台双边贸易咨商会议”上,台湾地区就美方所在意的电影管制问题大幅让步,除开放外片配额,停征“国片”辅导金,并降低外国制电影的娱乐税。此外,美国片商亦享有租税的优惠。
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媒体全球化浪潮之下,影音产品晋身为国际贸易的要角,美国成为全球影音产品最重要的输出国。而要使影音产品成为国际流通的商品,必须有良好的交易环境,除要跨越疆界之外,更要打破关税壁垒和文化保护主义,以建立成熟的知识产权之社会环境,如此一来,却间接促使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电影无招架之力。
台湾地区电影因为好莱坞电影占领各国地区领土,发行、映演通路(戏院)不得不依赖好莱坞电影的票房保证,所以排挤了本地影片的映演通路及发展空间,到了1996年,还自开门户,除了免除他们的税收,解除银幕配额和拷贝限制,敞开大门欢迎,从而形成台湾地区电影就算拍好了也几无戏院可上映,票房更是形成恶性循环,每况愈下。2003年,台湾地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为保障农业及制造产业权益,影视文化更是全面弃守。尽管在1989年之后台湾地区“行政院新闻局”为提升电影艺术水平,协同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制定了“国片”辅导金方案,鼓励兼具文化性与观赏性的电影拍摄。继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和1990年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获得国际电影节的肯定后,在辅导金的协助下,陆续有李安、蔡明亮、张作骥等导演在20世纪90年代表现亮眼,使中国台湾地区电影在国际影坛上占有一席之地。
然而,产业并没有因此提升,电影票房甚至在1997年-1999年及2001、2003年皆未达市场占有率的1%。③辅导金电影虽占台湾地区电影产量的比例提高,商业电影市场失衡同时也演变出台湾地区电影年产量减低至30部以下,2006年更仅有18部影片,荣景早已不复见,奖励政策面临相较于对外的开放政策,显然成效有限。台湾地区电影产业面临结构性上的挑战,不仅是自制商业电影市场的消解,政治上扶植的政策也效果不彰,在“外交”竞逐上亦是频频失利。国际能见度高,虽深受欧美艺术电影观众的喜爱,但曲高和寡,以电影作为娱乐消费的观众便渐行渐远。
好莱坞的兴盛当然与美国的强大有关,但我们不能忽略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娱乐的传播工具之威力,好莱坞的电影语言伴随着各地的电影院为好莱坞的天下,已成为世界观众自然而然理解与习惯的电影语言系统,使得任何的国家/民族的电影很难吸引当地的观众,便造成所谓的“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电影语言与叙境(diegesis)的构成——包括场面调度、镜位设定、剪接节奏等等皆以好莱坞为标准。④这使观众被好莱坞所奴役,在观影经验上的窥伺欲的产生、性与暴力的感官刺激、预期的皆大欢喜、邪不胜正的结局,皆源自好莱坞。反观中国台湾电影的慢节奏、长镜头、侧重小人物书写,反映现代人的孤寂等偏离感官刺激的经验,则显得无法接受,而逐渐失去自主性。
加上依照美国与世界电影产业的发展状况,跨国/地区企业在边陲/地区国家投资所得利润多半输回母国,形成经济剩余的转移,对地主国/地区资本形成毫无帮助。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其一贯的动力就是不断累积资本,藉由资本累积促成核心国家/地区的发展,同时牺牲边陲国家/地区发展。这种不平等的并存关系表现为核心国家对边陲国家/地区的支配与剥削关系,而支配与剥削的关系则以价值转运(transfer of value)为中心动力。⑤美国的好莱坞使许多第三世界的电影部门生产的失衡,经济体系脱节(disarticulation),需受美方的支配。这些依赖情境使各国/地区电影也因而必须寻求跨国合作,美其名为全球化,与国际接轨,其实也是各方条件均缺乏之不得不的方法。而对好莱坞而言,在边陲地区寻求合作拍摄方式,即透过美国的国际政治和电影技术的优越地位,到外取得相关部门与电影界的支持,运用较廉价的人力物力,藉以降低制作成本,不仅使美国在全球电影市场更具价格竞争优势,同时经由国际合作,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对其自身当然是百利而无一害。
从1989年冷战状态结束后,据统计2000年-2006年美国戏院产值约增长6%,全球戏院产值却高达46%,这使得美国主流八大片厂从主流类型影片操作转而重视参与各地特色电影制作。美国电影制作业从六七十年代的外逃摄制,发展到90年代,已形成所谓的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劳动的新国际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Cultural Labour,NICL)。⑥自此,好莱坞也转向不再隐身地区的文化之外,开始吸纳区域的工作者,或采用地区的创意。更化身为区域的电影制作者,尝试与在地文化结合。美国电影工业也藉此再度融入第三世界国家,交互影响在地的电影发展,使得物质和历史混杂(hybrid)的论述,逐渐影响东方人民对文化的认知与电影工业的发展。然而,这样的运作模式使长期被支配的国家/地区虽宥于政治的牵制看似难以翻转,但事实上却展现在地文化的拉扯效应以及民间的反动力量。这引发我们对媒体全球化、媒体帝国主义和好莱坞霸权等对台湾地区电影产业的影响有了重新的思考与讨论,似乎危机有了转机。
过去媒体帝国主义将全球化视为一种把西方的媒体产品、文化和机构散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并认为是欧美单向地将影响力投射到边缘的非西方地区。⑦这观点把全球化视为美国化,也就是经由好莱坞的特许加盟权(franchise)将文化霸权化。不过,最近有些研究修正了这个观点,将全球化视为一种复杂的过程,而非仅是文化和经济单向、强加于其身的关系,换言之,并非只是文化同质化⑧的隐忧。而是在地、本土和全球媒体之间的关系,应被视为一种多层次的地形空间,抵抗、同化、在地化、去在地化和再次在地化在此空间持续互动。⑨在地创新、更新和再次在地化的兴起,不仅是为了重新取回失去的市场,也创造西方媒体集团和在地从业人员之间更多的合作关系。⑩
那么2000年后迄今,台湾地区电影开始产生新的化学变化,正是全球化与在地化的交互吸融的最佳范例。台湾地区电影所面临的困境,逐渐隐含在电影文本之下的意识形态,同时面对好莱坞在全球化之下形成的电影新国际分工,也成为台湾地区电影工业再发展的复苏机会。尤以由徐立功的“纵横影视”和美商哥伦比亚公司等合资,于祖国大陆拍摄,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2000)的跨国/地区合作,增添了台湾地区电影制作与发行的空间。该片在国际上卖出超过两亿美元的票房,同时获得奥斯卡多项大奖的肯定,使我们能重新看待这部兼具口碑与卖座的巨片对台湾地区电影产业转向的关键影响。
美国在经济和文化的国际关系层面的统驭,以及在电影本身的范畴里,为我们提供了解第三世界电影制作的参考架构,并能透析电影产业的全貌;也提醒我们美国电影工业所带来的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应。反殖民见解加以去政治化的混杂思维,或许可以提供另一种思考路径。若全然脱离对好莱坞的依赖和宰制,对于自身的电影工业未必有所帮助,电影作为一个具有商业机制的文化产品,所面临的问题亦然不能仅以政治和经济考虑专断地处理,电影工作透过源自西方的科技与西方接触,进而促进低度发展的电影工业结构和电影工作者成就的养成,在权力脉络下透过知识,重新界定自身电影工业问题,并思考解决之道,来重新发展架构台湾地区的电影文化。观看这十几年台湾地区电影产业产生何种变化?
二、《卧虎藏龙》后的跨国/地区合制风潮
千禧年之后到今日,华语市场的开拓,欧美、日、韩多元文化的快速流通,地球村的形成,数字科技的大跃进,电子媒体的汇流,动画、电视、电影日趋合为一家,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显学。2000年,李安的《卧虎藏龙》的出现,不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在《卧虎藏龙》之前,台湾地区电影是用一种近“手工业”的方式,进行影片的制作与营销。而此种情况,至《卧虎藏龙》出现,才有另一种制片及发行模式的可能。《卧虎藏龙》在制作上结合了美国新力哥伦比亚、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等跨国和地区制作模式,在美国由Sony Classics发行,亚洲由亚洲哥伦比亚发行,中国台湾地区由博伟公司发行,在全球创下了两亿多元美元的票房纪录。另外,该片在文本上也重新建立类型的声誉,让武侠片成为文化中国的指标,除在影评和商业上的成就,也全面提升亚洲电影的地位,创新了集资方式,同时在美国也成功将电影从艺术电影院跨到多厅电影院,调整了我们对于卖座巨片和娱乐艺术的观念,在艺术与商业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11)
自此台湾地区电影产业出现两股潮流:其一是有着更大弹性并采用好莱坞拍摄模式,如市场研究和剧本发展、完片保证制度、精心设计的后期制作,及引人入胜的数字科技,这都代表商业电影直接竞争的想法。但受国族主义的趋使,并非所有人都朝向好莱坞路线,则有第二种潮流——除打造票房之外还加上其他的努力,企图活化具民族、区域和在地特色的叙事风格,是在地拍摄的新品种电影。
特别在《卧虎藏龙》成功的营销经验之后,台湾地区电影逐步试图效仿《卧虎藏龙》的“跨国合作”模式。接续的如2002年陈国富担任导演的《双瞳》,由苏照彬编剧以及魏德圣担任副导演,该片对未来台湾地区电影产业有着重大影响,同样由新力哥伦比亚公司投资,在台湾地区由博伟公司发行,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美国四地演员合作并结合国际后期制作特效等模式,在台北也创造出四千多万元新台币的票房。该片故事描述由台湾地区发生的连续三宗恐怖离奇案件开始,由于案情实在过于离奇,因此台湾地区警方请求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协助,联邦调查局便派遣Kevin(戴维摩斯饰)探员来台协助……本片不仅在票房上有所斩获,文本象征叙事与拍摄间的双轨,除了精神与经济观点、理性与迷信,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台湾实景拍摄关于台湾地区的故事和同时采取好莱坞式的管理;在营销设计上,将影片神秘叙事包装成网络上的谜题,跨文化类型结合在地主题,成功地刺激消费者进戏院观影的欲望。此种新在地主义,也间接地为其后台湾地区影史最卖座的台湾电影——2008年魏德圣导演的《海角七号》,奠定了基础与制作巨片的视野。
尽管前两部电影《卧虎藏龙》和《双瞳》的尝试为中国台湾电影制作立下了一个新典范,为中国台湾开创出一条“全球—在地”(glo-cal)生产线,运用了在地品味和技术,加上美国的资金、发行和营销。2006年苏照彬导演的《诡丝》依循雷同模式,由美商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投资,结合日本演员江口洋介、好莱坞特效等,最后再由中环集团旗下之中艺代理发行。影片再次结合惊悚类型电影的噱头,然而对中国台湾电影工作者而言,他们较习惯拍摄艺术电影,且多年来台湾地区观众养成排斥电影的习惯,要复制“全球—在地”的模式并非易事,这样的潮流随着《诡丝》的票房表现不若预期而趋缓。
虽然台湾地区观众没有顺势直接接受台湾电影,不过因受《卧虎藏龙》的影响,台湾地区兴起一股合拍片的风潮,台湾地区当局甚至于2007年修订生产电影片、电影片及外国电影片之认定基准,重修所谓的“国片”定义,期望能降低同时申请多项补助或投资的门槛,弥补台湾电影制作经费的短缺。后继接续的如哥伦比亚支持张艾嘉的《20 30 40》;2005年易智言导演的《关于爱》,由日本电影眼娱乐与天津电影制片厂投资发行;2007年李芸婵的《基因决定我爱你》,由三和国际娱乐、中影集团、中影华纳横店影视合作投资。此外,亦有如过往投资作者导演的跨国合作案例,如2006年蔡明亮的《黑眼圈》则是中国台湾、法国和奥地利合资;侯孝贤2008年的《红气球》亦由法国Margo Films公司投资拍摄。尽管票房未见斩获,电影跨国跨区域的合作模式已蔚为风气,甚至也延烧到台湾香港地区与内地之间。
三、台湾香港与内地合拍
在台湾香港地区与内地之间的合作,在2000年之前就已有人陆续敲门。以海峡两岸来说,资深影评人焦雄屏所成立的吉光电影公司在2000年所制作的《十七岁的单车》即是一先例。知名影星刘德华的“亚洲新星导”计划、曾志伟的“九降风”计划、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主办的第七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HAF,Hong Kong-Asia Film Financing Forum),甚至瑞士的卢卡诺电影节也在2009年提供Open Doors计划,辅助内地、香港与台湾地区三地的创作者电影拍摄资金。刘德华于2003年成立“映艺娱乐有限公司”,主要致力在商业及独立电影的合资制作与发行,其中“亚洲新星导”计划集合了六位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新锐导演,包括中国内地宁浩的《疯狂的石头》(2006)、中国香港地区黄精甫及李公乐合导的《家长指引》(2006)和林子聪的《得闲饮茶》(2006)、中国台湾李芸婵的《人鱼朵朵》(2006)、马来西亚何宇恒的《太阳雨》(2006)、新加坡唐永健的《爱情故事》(2006)。同样致力于发掘电影新人导演的香港演员曾志伟的“九降风”计划,也在2008年推出了三部作品:包括中国内地韩延的《摊开你的地图》、中国香港麦曦茵的《烈日当空》、中国台湾林书宇的《九降风》。此外曾参与HAF的亚洲导演多不胜数,如中国内地的贾樟柯、姜文、宁浩;中国台湾的蔡明亮、李康生、林靖杰;2009年27部HAF电影计划中,共有三部来自中国台湾,分别是张荣吉的《天黑》、张作骥的《爸,我很好…》以及魏德圣《赛德克·巴莱》。而2010年林书宇又以几米绘本改编电影《星空》获得韩国釜山影视创投的肯定与支持,之后又有中国内地“华谊”的投资等。
2005年,官方主导举办的“台湾国际影视创投会”为电影产业的一个转变契机,该创投会在以提升文化和商业市场并重的主题之下,鼓励即将完成之作品且有发行计划之影片,包括导演、制片等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内地的人才,提供高额奖金补助,首届创投会入围的47件企划案包括了王童导演的《林旺爷爷的故事》及石破天惊工作团队的《朱铭太极》两部动画片;朱延平导演的《灌篮高手》、钮承泽导演的《篮球火》;台湾地区年轻一代导演陈正道的《还魂》,柯孟融的《鬼音》、林育贤的《六号出口》、陈怀恩的《练习曲》等;2006年第二届台湾“国际影视创投会”一共有来自亚洲44件企划参加,入选17个案件,包括知名导演苏照彬描写海峡两岸核子战争的《月球的暗面》、曹瑞原的《天堂的边缘》、知名漫画家蔡志忠的《禅武少林》以及张作骥、林育贤、张婉婷、曾志伟担任制片的电影等。最后则由施文祥的3D计算机动画片《火龙果大冒险》拿下首奖。2007年的第三届台湾“国际影视创投会”,首奖由严浩导演的《南京圣诞·1937》与香港地区导演罗卓瑶的《如梦》平分,同时台湾地区林育贤的新作《翻滚吧!阿信》和蔡岳勋的《痞子英雄》也同样获得了“创投会”奖金的辅助,而后这两部影片完成在2011年暑假和2012年春节,在台湾地区都创造了7000万元新台币的票房。
虽然官方辅导金制度已行之有年,的确有效提供电影拍摄机会,但电影创投会的举办与其说是官方主导,不如说是由下而上的产业共同愿望所致,概因由李安《卧虎藏龙》所展示的制片和发行模式,为台湾地区电影产业所接受及效仿。而电影创投会因时、因地、因势地举办,刺激并整合了电影产业的动力,亦正式宣示将“国片”导向一个跨区域性合作的概念,而更重要的,是把台湾地区电影产业推向一个正规经济运作模式,而又呼应电影业界共同的愿望与需求。
四、数字化浪潮产业升级,培育新新导演
此外,在电影全面数字化浪潮之下,台湾地区自2003年起开始大量辅助戏院的数字化,2004年,更公布了“电影政策白皮书”,将数字DV纳入电影制作范畴,目的在鼓励更多新人投入电影事业。2008年,官方辅导电影产业数字升级,计有27家包括戏院与制作公司等受惠,其中包含数字后制环节的冲印公司及器材公司,辅助总金额为3800万元新台币。台湾地区电影数字化制作环节基本上已建构完成。台湾地区首部HD数字电影为2003年朱延平导演的《来去少林》,其他由HD拍摄的数转胶电影有曹瑞原的《青春蝴蝶孤恋花》(2005)、李芸婵的《人鱼朵朵》(2006)、陈怀恩的《练习曲》(2007)、程孝泽的《渺渺》(2008)等,胶卷电影已逐渐退场。
在此等结构下,纪录片和短片(包括动画片)在电影不景气时,也异军突起成为台湾电影之显学,成为年轻导演进入电影业的试脚石。新导演新电影的涌现是可以预见的,参加各类电影节累积得奖实力获得知名度,以待有大片可拍。如2004年8—10月,由台湾“文建会新闻局”与台湾电影文化协会共同举办“新导演Tailly High影展”,期藉此机会向大众引荐近年具有潜力之本土电影新秀,其中新秀导演包括剧情类的林靖杰、萧雅全、陈正道;实验类的吴俊辉;纪录类的吴静怡和动画类的马君辅等六位。激发更多有志于电影创作的学子投入前述短片、纪录片或动画制作行列,再通过参加各项大小电影节,崭露头角,博得制作下部电影的机会与投资。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电影产业也加强对新导演的培育,如2007年李安以《色·戒》获得“新闻局”颁发2000万元新台币奖金回馈台湾的“推手计划”,把这笔钱用来协助台湾新导演,第一波推手计划的种子导演为吴米森、侯季然、许明淳、沈可尚、郑有杰等五人。
此外,优秀者另有周美玲从文字记者转投入电影创作。杨雅喆在《囧男孩》(2008)之前曾与易智言合写小说《蓝色大门》(2002);钟孟宏毕业于芝加哥艺术学院,电影制作硕士,同样有丰富的广告与音乐录像带拍摄经验。林育贤毕业于大学影剧科系,曾经担任广告影片与音乐录像带制片及副导工作。陈芯宜为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毕业,较偏向独立电影创作,2000年完成首部电影《我叫阿铭啦》,并为自己的作品配乐。洪智育在电影《一八九五》之前亦有多年的影视制作经验。
总括而言,尽管这批新新导演来自不同领域,但在电影创作上都趋向一种精致质量的制作方式,其题材内容更为多元,例如《海角七号》、《一八九五》、《囧男孩》、《练习曲》、《刺青》、《诡丝》等,其作品更亲近观众。从台湾新电影以来强烈的作者个人风格,已渐转至观众电影形态。(12)
此外,数字器材的方便性也伴随微电影的广告商业效应,带动更多人投入电影创作行列,继台湾新电影后风行一时的多段式电影的风潮,再度获得观众青睐,如2009年由九把刀、黄子佼、陈奕先三人导演的《爱到底》;2010年沈可尚、侯季然、陈玉勋共同执导的《朱丽叶》;2011年由《台北星期天》的导演何蔚庭、《乘着光影旅行》的导演姜秀琼、《流浪神狗人》的导演陈芯宜和《朱丽叶》的导演沈可尚,各自执导四部短片而成的《昨日的记忆》。另一部代表作品则是由20位导演合作的《10+10》成为2011年金马国际电影节开幕片。
这群新导演中最令人瞩目的则是知名网络作家九把刀改编自己高中岁月的“恋爱滋味”、横扫华语影坛的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尽管是跨界导戏,技巧与美学仍遭受质疑,但内容贴近年轻学子却颇受大众欢迎,2011年在台湾地区创下超过四亿元新台币票房的佳绩,2012年更获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华语电影的殊荣。
多方的资金和专业企划交流,因之扶植一批所谓的台湾新新导演。(13)加以2009年台湾地区当局订定祖国大陆电影从业人员来台参与电影制作审核处理原则,为2010年6月两岸签订《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简称ECFA)双边合作铺路,全球及两岸三地的多边效应,提高了拍摄质量和叙事创新,同时也育成了这群后起之秀以及效法好莱坞炫力的营销包装,使台湾地区电影市场重新成长,变换样貌。而这一批五六年级导演,特别是七年级生等新势力导演群的加入,在2000年之后,已逐渐摆脱电影前辈及台湾新电影的影响,从剧情、纪录和动画片中走出自己的道路,他们勇于创作,并且不排斥大众文化的商业市场机制,有开阔的心胸,为台湾电影提供多元的内容创意,正踏着这新的浪头而来。
五、城市营销与电影产业结合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当局积极地提供更多资源与奖励制度之外,现各大县市也相继正式成立相关电影单位,鼓励电影制作,同时营销城市意象。2008年1月,“台北市电影委员会”成立,除鼓励协助电影工作者于台北市拍摄电影外,同时也拨款T200万元新台币来辅助七部影片。代表案例即是2010年钮承泽导演的《艋舺》,除了创造近三亿元新台币票房之外,同时也结合在地文化,剥皮寮的文物展,华西街夜市、艋舺祖师庙、宝斗里等在地风情,也成为2011年台湾地区电影复苏前哨战。“高雄县电影事务委员会”于2008年12月成立,整合高雄县电影拍摄资源与数据库建构,在此之前,已吸引并辅助多部影片拍摄,早的有2004年蔡明亮的《天边一朵云》,影片主要场景大都在高雄拍摄完成。2010年蔡岳勋电视剧《痞子英雄》的南方分局更是为高雄带来无限观光商机,电影版在2012年更是成功宣传了高雄梦时代等几个重要景点。“台中市政府影视委员会”同样于2008年12月成立。由电视转战电影的冯凯导演2012年的《阵头》,内容则结合台中文化艺术季,也成功提升与营销了城市形象,不仅如此,该片在台也创下近四亿元新台币的票房佳绩。由此可见,台湾地区各县市以更积极的态度正视电影摄制,并希望透过电影拍摄工作,强化城市营销,亦可使电影内容更加贴近在地与乡民文化,而此概念已蔚然成为风气,对电影产业本身有一定外缘帮助。
六、《海角七号》效应营销发行的再次在地化
2008年魏德圣的《海角七号》以一个在台北工作失意的乐手返回屏东老家成为邮差,以一封到不了的信,串起日据时代情怀和现代困境的跨国恋情,在台湾地区创下5.2亿元新台币的票房,再度使台湾电影环境获得世人关爱。尽管当时不少人质疑《海角七号》在票房成功的背后,是否隐示着一个整体台湾地区电影质量改变的征兆?或只是如同《卧虎藏龙》那样只是个别、短暂现象?此外,官方机构辅助与政策调整是否对电影上下游产业链连锁起了作用?这些问题随着2011年台湾地区电影票房(14)的大斩获,许多悲观主义者遂看到一线曙光。
《海角七号》所显示的票房破纪录数字,如同一般所言,数字会说话,首先必然引发我们对近年台湾地区电影票房纪录的关注。其中,2006年27部“国片”,在台湾地区总票房为4300万元新台币,占全台总票房1.62%。而2007年开始,有了显著变化,2007年39部“国片”(包含27部剧情片与12部短片、纪录片),总票房为1.982亿元新台币,占全台总票房的7.38%;到了2008年36部“国片”(22部剧情片,14部短片、纪录片),总票房为3.0542亿元新台币,占全台总票房12.09%。2008这一年的“国片”票房数字与所占百分比数,都是近十年来的最高数字。从上述数字告诉我们一个现象:从2007年开始,国片在票房上持续加温,至2008年达到近十年的最高点,且首次超过总票房的10%。2009年又降下至2.14%,一度让人以为《海角七号》只是台湾影坛的昙花一现,短暂而美丽。而2010年又因《艋舺》营销策略成功的带动,回升到7.13%;2011年由春节开始初试啼声的叶天伦导演以《鸡排英雄》在台首先开出1.5亿元新台币票房,接着林育贤的《翻滚吧!阿信》、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魏德圣的《赛德克·巴莱》(上、下)等卖座片将总票房市占率冲至近二十年来的新高点17.46%。(15)有趣的是,美片的票房总数并未减少,换言之,虽说美片市占率降低了,但营收并没有减少。从另一角度来看,是台湾地区观众对于台湾电影的接收度增加,愿意将台湾电影视为进戏院观看的娱乐选项。
笔者认为这个现象与前述所言的去在地化的跨国/地区合制和与再次在地化发行趋向有所关联,同时加以新新导演出现,摆脱包袱,影片内容和质量另具特色,联动票房的持续加温。
当然,发行公司在电影制作环节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渐显要。虽然美商涉入台湾地区电影发行在《卧虎藏龙》已展开,另外如博伟公司发行《色·戒》、《海角七号》;“纵横影视国际”与博伟公司发行周杰伦导演的《不能说的秘密》(2007)、“纵横影视国际”与“华纳兄弟台湾”、“奇霏影视”制作发行《练习曲》(2007)等,此等结合美商发行的作法,关键在于取得好的档期和增加拷贝(银幕映演数量)来提升票房,虽然利润多半受制于美商,但在这过程中也学习美商如何运用好莱坞“高概念”(High Concept)电影制作与发行模式,(16)制作质量与商业兼具的电影作品,并且更加重视产销市场的发行渠道与观众反应。所谓好莱坞“高概念”电影制作特色,在于电影作品的叙事简单明了、有特定目标的观众群以及明显卖点。用简单的文案、清楚的视觉讯息、多样化的整合营销手法来吸引观众产生消费行为。经过这几年的合作学习,师夷长技以置夷,台湾地区电影慢慢展现影片的营销创意与策略。
以魏德圣的《海角七号》来看,在台湾地区是由美商博伟公司发行,起初它并没有高的营销预算,且首周票房表现并不亮眼,但却充分利用网络BBS和博客的口碑效应,票房成长后便顺势结合文化产品的生产蓝图,增加知识产权价值,出版电影书、原声带,并与流行音乐结合,带动电影窗口效应(window effect)。有了《海角七号》的成绩之后,魏德圣以雾社事件的历史故事为主轴创作了《赛德克·巴莱》(2011),除了获得易主后的台湾地区“中影”公司郭台强3.5亿元新台币的支持,由果子电影和中环集团发行,同时在映演上也获得全民热情回应,在台湾地区分上下两集映演,首集映演也创下全台湾地区超过300个银幕同时播映的空前纪录,更带动外围产品超过200项。
事实上,在2008年,魏德圣首部剧情长片《海角七号》创下5.2亿元新台币的票房后,他决定重启拍摄《赛德克·巴莱》的计划,将筹划12年的构思付诸实行。2009年10月27日,在资金尚未完全到位的压力下,用博客来售票、网上贩卖《赛德克·巴莱》开镜纪念套票。2010年,该片获“行政院新闻局”奖励成为重点补助的电影,补助金达1.6亿元新台币以上。2011年2月22日,台湾地区“中影”公司董事长郭台强出资3.5亿元新台币,初期以营销《赛德克·巴莱》为主,这也是台湾地区“中影”公司投资的第一个文创产业。2011年8月29日,拍摄期间饱受筹资之苦的《赛德克·巴莱》将获得“行政院文建会”投资9000万元新台币“国发基金”,将使《赛德克·巴莱》成为文创创投当局与民众共同投资政策下的第一案。出版电影相关的书籍达六本之多,在2012年更是要举办《赛德克·巴莱》电影交响诗草地音乐会,将风潮延续长尾效应(The longtail)。在台湾地区鼓励投资文创产业,而文创创投又热衷投资台湾电影的风潮下,可供电影投资者与创作者共同思考。(17)
另一个重要的发行个案是由李烈监制、钮承泽导演的《艋舺》。敲定黄金档期,再开始拍片;建立清楚的投资游戏规则;为达上亿票房,卡司(演员阵容)调整成“老少通吃”,将马如龙、赵又廷等都选入出演,希望夹带《海角七号》和《痞子英雄》电视剧的高人气;抓紧制作时间以配合春节档期;精准营销,以主角阮经天带到戛纳国际电影节现场宣誓开拍等事件争取影视宣传版面,用五大策略掌握市场,成功创造了四个第一:首先,它创下台湾地区“国片”史上首日卖座最高票房,单日1800万元新台币;其次,它仅花六天,全台票房破亿,破亿速度为台湾地区“国片”史上之冠,华语片第三,仅次《功夫》、《色·戒》;再者,在当年它创下台湾地区“国片”播放厅数最多纪录,超过160个厅同步上映;此外,也是二十年来,首部挤进春节贺岁档期的台湾“国片”。(18)这部影片将台湾地区电影带入新的阶段,运用非常高超的商业操作,商业筹资手法、商业宣传手段、商业卡司,每一步都精准盘算,超越以往“国片”,不但学习美商长处同时配合在地的情境开创出一条营销活路。
回顾过去历史,中国台湾电影市场长期处于美国好莱坞电影支配,加以2002年台湾地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取消外片58个拷贝限制,以及映演厅放映外片的相关限制。(19)此种严重冲击,使得台湾地区电影几无生存空间,重要档期如暑期档和元旦档等,几乎都充斥着好莱坞大片,使得许多“国片”连上映的戏院皆无,更遑论票房。台湾地区电影生存空间狭小,就连发行和映演大都掌握在美商手中,因此,多年来业界无不苦思对策,试图提出不同意见与解决方法,改善台湾地区电影整体质量及市场运作。
在台湾地区电影产业发展风雨飘摇的过程中,好莱坞通常扮演坏人的角色,甚或是所谓的入侵者,但若仔细端详,我们会发现刻板印象中藏有可讨论的空间。台湾地区电影产业近年的新趋势,已是从手工业、摆地摊模式转向电影产业的正规经营模式,到吸取境外经营经验,寻求跨国跨区域的资金、人才、技术整合。电影制作环节中结合了发行公司和制作公司的同盟,凸显发行公司的运作,从以往“自制自销”转向“产销合一”的模式。这几年的制片发行成果,明显让台湾地区电影从“作者电影”风潮中转至“观众电影”模式。(20)伴随发展过程,十几年来台湾地区电影产业文化展现出下列几项特色:
1.电影制作资金来源多元化:首先不可讳言的,过去台湾地区电影观众真切热情地拥抱美国电影,阻碍了在地电影产业,降低产量限缩市场。但从2000年《卧虎藏龙》跨国合作成功案例开始,台湾地区电影确实产生了反弹效应,不仅开始寻求国外资金,甚至在2008年《海角七号》神迹式的卖座后,台湾地区企业主也纷纷投入电影金主的行列,如鸿海集团投资《白银帝国》(2009)、富邦金控投资《星空》。2005年台湾地区当局主导举办的“台湾国际影视创投会”,起初仅有27家公司参与比案,至2011年已经有超过200家企业加入创投会,台湾香港地区和内地更有上百件的企划案参与,投资者期望能找到好的题材,制作公司则期盼能寻获好的支持者,资金寻求不易的难关随着台湾片市场的拓展逐渐复苏,加上2010年6月两岸签订ECFA,促进两岸合拍片的运作,成功的案例如2012年上映的《痞子英雄》和《LOVE》,内地投资金额皆超过亿元新台币。
2.在地的类型电影兴起:台湾地区电影孕育出在地文化根基,拍出美国无法拍出的风格,创造属于在地的类型电影。如在2010新春上档的《艋舺》结合在地角头文化和兄弟间的义气等情节创造两亿多元新台币票房的佳作;来年新春《鸡排英雄》由蓝正龙、柯佳嬿象征台湾夜市文化的再现,夹杂当局都市更新土地征收的政商角力情节,也带出1.5亿元新台币的票房以及2012年由真人真事改编展现台湾庙会文化的《阵头》更以小兵立大功之姿用电音三太子带出超过三亿元新台币票房,超过预期强档动作片《痞子英雄》。
3.培养出观众喜爱的台湾地区电影明星:明星制度为好莱坞成功的关键之一,台湾地区长年缺乏所谓的大腕明星,香港地区还有所谓的刘德华、梁朝伟等天王级的明星,台湾地区随着几部卖座电影逐渐塑造出所谓的台湾三帅——阮经天、赵又廷和彭于晏,他们在电影票房上表现亮眼,同时演技也逐渐受到肯定,并在东亚地区也逐渐培养出一群忠实粉丝,只不过目前台湾地区女星仍还有发展空间。
4.崭新的发行空间:台湾地区电影虽在2007年之前以去在地化的方式与美商合作发行受到较大的限制,利润空间较小,随着《艋舺》、《鸡排英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赛德克·巴莱》等片的成功,摆脱美片的压制,在去在地化中增加与美商协商的空间,加上台湾地区观众对台湾地区电影的接受度增加,培养对台湾地区电影的观看兴趣,同时戏院业者也不再视台湾地区电影为票房毒药,而逐渐摆脱过去美商电影垄断戏院通路的困境,黄金档期台湾地区电影不再缺席,营销可操作空间加大,发行将可计算利润,进而创造产业价值链,有助提升整体产业结构发展。
从上可知新世纪以来台湾地区电影产业的发展,在发行映演上,台湾地区电影除了在营销的去在地化与美商相合,并产生出崭新的营销空间,有了协商筹码,同时在制作上,主题、明星和类型方面则走向再次在地化,在主题上重新展现台湾地区风土民情。不仅电影本身,产业基础内容结构也同时改变,台湾地区电影将过去的苦涩经验转化为优势,并纳入对手的公式、策略和标准,同时趁着华语市场的成长,将自己的边界地图扩大,进而重新崛起,未来期望能延续2011年起台湾地区电影在地的票房起飞之势,逐渐构成台湾地区电影与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差异性,成为制衡美国好莱坞电影商业主义在本土市场的力量,营造出更好的协商空间,进而将台湾地区电影与人才推向国际市场。
注释:
①[美]安迪·沃荷(Andy Warhol)《安迪·沃荷的波普人生》,卢慈颖译,台北三言社2006年版,第119页。
②徐挥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障及促进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对文化权及传播权之影响:以2007年欧体视听媒体服务指令为中心》,载自《新闻学研究》2009年第1期,第95—97页。
③参见台湾电影网《台北市首轮院线映演“国产”影片、港陆影片暨其他外片之票房历史统计(1999-2011)》,http://tc.gio.gov.tw/ct_131_265。
④[美]Roy Armes《第三世界电影与西方》,廖金凤、陈儒修合译,台北电影资料馆1997年版,第59页。
⑤[埃]萨米尔·阿敏《不平等的发展——论边陲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构》,高铦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英文版为Samir Amin,Unequal Development: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⑥[美]托比·米勒、尼丁·戈维尔、约翰麦·克默林、理查德·马克思韦尔(Toby Miller,Nitin Govil,John Mcmurria and Ricard Maxwell)《全球好莱坞》,冯建三译,台北巨流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⑦Dorfman,Ariel and Mattelart,Armand(1975),How to read Donald Duck:Imperialist Ideology in Disney Comic,New York:International General; Schiller,Herbert(1976),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New York:M.E.Sharp; Wallerstein,Immanuel(1974-80),The Modern World System,New York:Academic.
⑧同⑤。
⑨Lee,Chin-Chuan(1979),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Beverly Hills,CA:Sage.
⑩戴乐为、叶月瑜《东亚电影惊奇:中港日韩》,黄慧敏译,台北书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11)同⑩,转载自第40页。
(12)(13)齐隆壬《2005-2008台湾地区电影新新导演显像》,载自《电影艺术》2009年第3期,第48—53页。
(14)(15)同③。
(16)黄匀祺《从发展理论检视全球化下台湾地区电影产业发展趋势》,载自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学生论文研讨会,2009年发表。
(17)资料整理自维基百科:赛德克巴莱,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BD%E5%BE%B7%E5%85%8B%C2%B7%E5%B7%B4%E8%90%8A。
(18)李盈颖《李烈把国片营销带入新纪元》,《商业周刊》2010年3月1日(总第1162期),http://www.businessweekly.com tw/webarticle.php?id=39372。
(19)刘现成《美国及其电影业介入台湾地区电影市场的历史分析》,载自《电影欣赏》2007年第二十五卷第130期,第44页。
(20)同(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