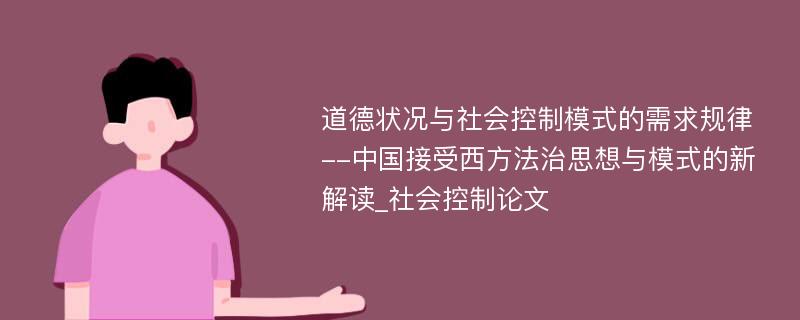
道德态势与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我国接受西方法治思想与模式原因的新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模式论文,定律论文,态势论文,法治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选择德治控制模式?西方社会为什么选择法治控制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追求法治控制模式?德治控制模式和法治控制模式的实效如何?其原因是什么?本文试图从道德估量与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关系角度来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
一 道德“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需要变量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指出:道德是不能被量化的。正如卢梭所说:“道德方面的数量是缺乏精确的尺度的,所以即使人们对于这种标志意见一致了,可是在估价上又如何才能意见一致呢?”①虽然笔者也认为道德很难被精确量化,但并非绝对不能被量化。关键是确定量化的单位或尺度。如果我们以“自我”为单位来衡量道德的话,我们会发现道德是有大小之分的。如一个人可以以自身个体为自我,从而只关心自身的利益;也可以以家庭为自我,从而只关心家庭的利益,使自身利益淹没在家庭利益之中;也可以以自身所处的利益集团为自我,从而只关心该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使自身利益和家庭利益淹没在该利益集团的利益之中。如此类推,“自我”的单位变量可以大到国家,如那些舍身家而为国捐躯的人;可以大到整个人类,如那些国际主义人士。总之,“自我”是个变量,“自我”的大小是衡量道德大小的尺度。
当然法律控制的需要也是一个变量。正如布莱克所说:“法律的量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变化跨越世纪、年代、年、月、日,甚至一天内不同的时刻。法律的量的变化也存在于所有社会、地区、社区、邻里、家庭和各种关系之中。”②而且法律控制的变量与人的道德“自我”单位变量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道德变量和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关系的角度看,一般地说,一个人的“自我”越大——越理性化——越体现公意——越崇高——越接近于圣人——越富于道德控制,而越少地需要法律控制;相反地,一个人的“自我”越小——越本能化——越体现私心——越卑下——越接近于俗人——越缺乏道德控制,而越多地需要法律控制。可见,道德的“自我”单位变量与法律控制的需要量是成反比的,即道德的“自我”单位越大,法律控制的需要量就越小。人的自私本性与法律或法治有着天然的联系,其对内的自保性需要法律权利的保障,对外的侵略性需要法律义务的约束,而理性的形态又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互惠性和权利义务的一致性。道德与法律的这种关系,正如布莱克所说:“法律本身是一种社会控制,但是还有其他多种社会控制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存在于家庭、友谊、邻里关系、村落、部落、职业、组织和各种群体中。因此,上述命题的意思是,当其他社会控制的量减少时,法律的量就会增加,反之亦然。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能够测定法律和其他社会控制的量,这样表述的命题就适用。”③本文中的道德就是布莱克所谓“其他社会控制”中的一种主要方式。
如果从便于认识的角度,我们把人类社会总体(社会中所有人和每个人的)道德变量单位进行归纳,并分别暂且界定为“小我”(个人)、“中我”(个人所属利益集团)、“大我”(整个民族国家)和“全我”(整个人类)的话,④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道德变量单位的不同的总体实现态势估价出不同空间领域所需法律控制的情况。
如果(当然只是如果)整个人类社会在总体上实现了道德“自我”单位变量的“全我”,即总体道德“自我”变量的最小单位是“整个人类”,也即在道德上达到人人以整个人类为“自我”,而没有了“小我”、“中我”和“大我”,则整个人类在道德上就实现了“天下为公”,法和国家也就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必要存在了。这样也就实现了中国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⑤
如果某一民族国家社会在总体上实现了道德“自我”单位变量的“大我”,即总体道德“自我”变量的最小单位是“整个民族国家”,也即人人“胸怀祖国”,在道德上以民族和国家为“自我”,而没有了“小我”和“中我”,则该国家的国内法控制就会很少或者根本就成为不必要。这样的国家也就是卢梭所描绘的实现了“公意”的国家,这样的国家的治理只需要很少的法律。⑥
如果某一利益集团在总体上实现了道德“自我”单位变量的“中我”,即总体道德“自我”变量的最小单位是“利益集团”,也即人人以该集团为“自我”,而没有了“小我”,则该集团内部的人际关系也就很少或者根本就不需要法律控制了。
如果某一社会的总体道德“自我”单位变量为“小我”,人人以上文暂定意义上的“小我”,即个人为自我,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最多的法律控制。
正如格兰特·吉尔默所说:“社会越好,法律就越少。在天堂里应该没有法律,狮子应与羔羊同眠……在地狱里应该只有法律,正当程序应被一丝不苟地遵守。”⑦
诚然,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社会的道德“自我”单位变量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会因时间和空间等条件变化而不同。从个人角度来说,不同层次、不同大小的道德“自我”单位可能集于一身,只是浓淡不同、强弱不同,并依时间和空间等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但不论怎样复杂和变化,某一个人身上总会有一种可被大致认知和估价的相对稳定的和主导的道德态势。如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对某人的道德态势做出一个基本的估价,从而得出结论:某人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某人是个大公无私的人。或某人是个个人主义者,某人是个爱国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等等。在前者身上,其道德“自我”单位变量的常态和主导方面是“小我”;而后者道德“自我”单位变量的常态和主导方面则是相对的“大我”。与此相适应,我们对某一民族、社会或国家的总体道德“自我”单位变量态势也可以做出大致的估价,并由此估价该民族、社会或国家所需法律控制量的大致态势,如德治或法治态势。
二 中、西方文化体系中社会总体道德“自我”单位变量走势的反向差异与社会控制模式选择及其实效的反向差异
(一)“小我”为重倾向: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自我”单位变量走势
从人性中固有的道德走势来看,至少在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尚存的社会发展阶段,人类总体道德走势相对稳定的和规律性的一面还是主要的,这种规律性可以用如下公式来表达:“自我”越大——程度越弱——人数越少——越理性化——越体现公意——越可能被评价为崇高——越接近于圣人——越富于道德控制,而越不需要法律控制;相反地,“自我”越小——程度越强——人数越多——越本能化——越体现私心——越可能被评价为卑下——越近于俗人——越缺乏道德控制,而越需要法律控制。
也许正因为在私有财产和私有制尚存的社会发展阶段,人性具有这样的规律性,有些中外思想家们才不约而同地将对人性“恶”即人的“小我”倾向的基本估价作为说明法律控制的必要性的一个主要的前提。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将法律控制的必要性归于人固有的与公心相对的私心(兽性)和与理性相对的欲望(兽性与热忱)。他认为:“某一事物被认为是你自己的事物,这在感情上就发生巨大的作用。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并不是偶发的冲动[人们对自己的所有物感觉爱好和快意;实际上是自爱的延伸]。”“谁说应该由法律遂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祗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⑧中国的韩非也是以与亚里士多德相类似的前提来说明法律存在的必要性的,只不过他将人性的“恶”即“小我”倾向绝对化,并强化了法律控制的强度,主张依人性订立赏罚规则。他认为:“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⑨因而,“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⑩“国治则民安,事乱则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轻者失事实。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11)根据这些论述,人性自私说体现了韩非对法律起源的认识。
(二)“大我”为重与“小我”为重倾向:中、西方文化体系中社会总体道德“自我”单位变量走势的反向差异
社会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中蕴涵着社会统治势力的价值追求和人性估价。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中蕴涵的价值追求注重的是集体的利益和权力,也即家族和国家的利益和权力。从价值位阶上看,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倾向于大我为重。对“自我”的侧重程度与“自我”单位变量的大小成正比,即“自我”单位越大,侧重程度越重。一般地说,这种文化体系最重视的是“大我”(个人和家族所属之国家),“中我”(个人所属之家族)次之,“小我”(个人)更次之。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角度来看,“小我”是为“中我”服务的,“中我”是为“大我”服务的,“大我”是“中我”、“小我”存在和限制的最终依据。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体系中的这种道德走势被称为“集团本位”或“国家家族本位”。从儒家伦理的“修齐治平”的要求来看,“修身”并不是对“小我”的认同,而是剔除人性中固有的“小我”,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增的“大我”,最终实现儒家伦理最高境界——“平天下”的手段。从实现的过程和条件递进来看,固然,可以按“修齐治平”的顺序来排列,但从价值位阶来看,则首重者为“平天下”,“治国”次之,“齐家”再次之。再从儒家伦理的“忠孝”要求来看,“孝”固然是“忠”的一个条件,而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则舍“孝”而尽“忠”。最能直接体现这种价值位阶的还有中国刑法史上的“十恶”重罪,其被重视和刑罚的严重程度与其所保护的儒家伦理中所要求的“自我”单位大小程度成正比。
从人性估价上看,总的来说,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对人性的估价是积极的,即倾向于人性“善”估价。虽有法家的人性“恶”(“小我”为重)估价,但法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体系中不占主流,居统治地位的还是儒家文化。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人对人性的具体关注和认识虽各有异,但基本认识是相同的,是可以“以善通约”(12)的:或认为人生来就是“善”的,或认为人具有向“善”的能力,经过后天的教化或积累可成善德(“大我”为重)。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除鄙视和否定“见利忘义”的经济人(商人)外,自然人和政治人都被以道德人的标准来要求,并认为是可以实现的。由此,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追求和人性估价体现出道德期盼和道德信任的倾向或走势,也即重视道德价值,相信和信任人的道德能力和道德规则的效力。正如瞿同祖先生所言:“儒家既坚信人心的善恶是决定于教化的,同时又坚信这种教化,只是在位者一二人潜移默化之功,其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从德治主义又演而为人治主义。”(13)
西方社会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中蕴涵的价值追求注重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该价值观认为,在社会生活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是第一位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应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14)从价值位阶上看,总的来说,西方社会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倾向于相对的小我为重。对“自我”的侧重程度与“自我”单位变量的大小成反比。即“自我”单位越小,侧重程度越重。一般地说,这种文化体系最重视的是“我”(个人),“中我”(个人所属利益集团)次之,“大我”(个人和利益集团所属之国家)更次之。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角度来看,“中我”是为“小我”服务的,“大我”是为“中我”和“小我”服务的,“小我”是“中我”、“大我”存在和限制的最终依据。西方社会文化体系中的这种道德走势被称为“个人主义”或“个人本位”。
西方社会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对人性的估价则是消极的,即趋向于人性“恶”估价,认为人最关心的是自己和离自己相对近的人和事或利益集团。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人,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等的政治人,还有亚当·斯密的经济人都是“自利”的“小我”为重主义者。(15)在西方社会文化体系中,“利他”的道德人则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由此,西方社会文化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追求和人性估价体现出道德怀疑的倾向或走势,也即不重视道德价值,不相信或不信任人的道德能力和道德规则的效力。
总的来看,中、西方文化体系中社会总体道德“自我”单位变量走势是相反的,也即体现为反向差异。
(三)德治模式与法治模式:中、西方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反向差异
文化对社会规则和控制模式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构想,文化对于生活于其中的个体的行为起到潜在的和实际的引导作用。”“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形成一个社会的基本命题,并且型塑了支配社会秩序的原则,这些原则通常是毋庸怀疑的前提。”(16)中、西方社会文化体系中的道德走势,也即其中蕴涵的价值追求和人性估价的基本趋势的反向差异影响了中、西方社会控制模式选择的反向差异。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追求和人性估价的“大我”为重倾向,是中国社会倚重道德规范、轻视法律规范和选择以人的道德为条件的德治社会控制模式的一个重要前提。可见,“普遍的人性假设,是人类构想政治控制方式的世间依据。”(17)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政治人还是自然人,在社会文化体系和社会控制模式中最终都统一于道德人,也即统一于社会文化体系中和社会控制模式中的圣君、贤相、清官、君子、良民。如果社会上每个人的道德“自我”单位变量状况都达到了儒家伦理中要求的“大我”为重的理想境界,则儒家理想的“父慈、子孝、夫宜、妇顺、兄良、弟悌、君仁、臣忠”的社会秩序,通过个人的道德自控就实现了,因而无需作为他控手段的法律。德治模式的选定,既取决于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对人性善的信念,也取决于该文化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的对道德规范效力的信任和欣赏。即相信,一方面,人有能力达到儒家伦理所要求的“大我”为重的“修齐治平”的道德境界;另一方面,既然人可以成为道德人,儒家道德伦理规范当然也有能力调控人的行为而实现理想的社会秩序。而与道德规范比较起来,法律规范则被认为具有不可克服的弊端,由此对“德主刑辅”的德治模式的选择也就不可避免。(18)如果个人都能以儒家“大我”为自我,则国家就成为“君子国”,民与民之间就不会因私利而争,互让和利他是这种关系的主要特征,因而也就不需要调整个人权利之争的民事法律;如果君和官能够以儒家“大我”为自我,则君和官自然靠贤德就可以为民做主,自然会实现“清官政治”、“好人政府”,因而也就不需要控制政府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的宪法和程序法。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民事法律和程序法律不发达,而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和宪政始终没有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辩证地看,中国传统社会所选择的德治模式并非绝对地否定和排斥法律的作用,尤其是刑法的作用。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对道德规范效力的信任并非是绝对的,由于儒家伦理与人性规律和社会上的实有道德状态存在着较大差距,因而社会统治者在道德信任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人性和道德怀疑成分,这种怀疑的程度与人的社会地位的高低成反比,即对社会地位越高的人,怀疑越小。这种比例也决定了刑法对社会地位不同的人的控制量和程度的不同,即对社会地位越高的人的控制量和控制程度越小。从“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到君主几乎完全不受刑法的控制无不体现了这一走势。
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反,西方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价值追求和人性估价的“小我”为重倾向,是西方社会倚重法律规范、轻视道德和选择以人性“恶”为前提的法治社会控制模式的一个重要前提。在西方社会,无论是自然人、政治人还是经济人,在社会文化体系和社会控制模式中最终都统一于法律人,也即享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和平等互控权利的公民。自17、18世纪后,西方的个人权利保护具备了三个维度,都是法律方面的维度,即自然法、法律和宪法。“在北美,17、18世纪宪法的发展给个人权利保护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一是体现在自然和理性法中的权利维度,二是可由立法者变更的这片土地上的法律保护的(基本的)权利维度,第三个维度被增加了:由一种反常的、远离立法者变更权力的法律保护的权利——这种法律在北美被不同地称为基本法、高级法、最高法,并且越来越多地被称作‘宪法’。”(19)既然个人以个体的“小我”为自我,则人与人之间必然形成一种以互争和利己为基本特征的关系,人的利己动机的张力和普遍性必然形成个人与个人和个人所依托的利益集团之间互控的网状模式,因而必然形成以契约精神和理性共存为底蕴和主要特征的发达的民事法律。既然执掌政府权力的官也是人,既然要求人做以“大我”为自我的道德人是不现实的,因而为保护个人和利益集团的私权利,政府的公权力也要受到限制,于是出现了限制政府公权力以保护个人和利益集团私权利的宪法和程序法。
西方的法律体系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也非常明显地反映了“小我”为重倾向,即私权利是目的、公权力是保护和实现私权利的手段。当然,西方社会在选择法治控制模式的同时,也不排斥道德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只是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来说,对其缺乏最终的信任而已。
(四)价值位阶与人性估价的理想化和现实性:中、西方所选择的主要社会控制模式实效的差异
1.中国传统文化道德走势价值位阶和人性估价的理想化与所选德治控制模式实效的缺失或不稳定
从规范内容角度看,中国传统社会德治控制模式追求和要求的儒家文化道德走势中的“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与人性规律中的“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相反并与社会实有道德态势和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也即高于人性规律中和社会实有的道德水平,因而具有较大的理想化的成分,而现实性则较差。正如有学者所言:它对人生的现实条件比较无视,多言境界,少言境遇,人生成一务虚的架势。(20)虽然存在着儒家伦理的价值位阶上的“大我”为重的理想境界,然而,中国传统社会的实有道德状态恐怕还是不能脱离人性规律的左右,其实有道德走势还是由己及人,由近及远,亲近程度和价值位阶恐怕还是“小我”为重的。“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正刻画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建构出可伸缩的社会关系圈圈,当以家为我群时,家外的人属他群,如此一圈圈扩大出去,一表三千里,然后便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似乎普天之下皆为我群,与自己同隶一个共同群体之内。但是基本上还须有立基血缘地缘初级关系的脉络可寻,全球性的同姓宗亲会,同乡会,甚至如异姓联合宗亲会,如刘关张赵四姓,还须有《三国演义》刘备等人情同手足的故事为基础。”(21)因而,德治模式因其选择所依据的前提与人性规律和社会实有道德态势和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没有做到韩非所说的“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所以人们从内心深处,不但没有动力去主动维护它,而且可能具有抵触情绪,导致其实施往往缺乏真正的社会动力,在实效方面必然大打折扣。
从规范效力角度看,道德规范的实效主要是通过有德者的自我约束机制实现的,其前提是人性善。德治控制模式中的道德规范只有与某人的实有道德观念和水平相重叠的部分才有可能实现,而高于某人的实有道德观念和水平的部分则不会有效。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德治模式所倚重的儒家伦理规范体系从人性所可能达到的最高点来估价人性,换句话说,要求所有的人都做圣人,因而其要求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远远高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由此,这种伦理规范体系的很大一部分应该是没有实效的;又由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是不稳定的,会因人、因地、因时而变化,因而这种伦理规范体系的实效也应该是不稳定的,由此必然导致儒家伦理中的许多要求或无法实现或扭曲实现。如本意是追求和谐秩序,实际上却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压制;本意是追求德治和仁政,而现实生活中却往往导致如下的蜕化链条:德治蜕化为人治,人治蜕化为专制,专制蜕化为弊政或暴政。也许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法家则完全与儒家立于相反的立场,否认社会可以藉德化的力量来维护,更不相信一二人的力量足以转移社会风气,决定国家的治乱。根本反对有治人无治法,人存政存,人亡政亡的办法。法家所需要的是必然之治,使社会长治久安,而不是这种渺茫不可期,时乱时治的办法。”(22)
也许正因为如此,统治者在主张“德主”的同时,又以“刑辅”作为德治模式的一个必要部分。“德主”体现了统治者对于人性的理想态度,“刑辅”则体现了统治者对于人性的现实态度。但由于对道德的信任居于主导方面,因而导致作为对人性恶防范手段的许多层次的法律或缺失或极不发达,如民法、程序法、宪法等,只有刑法作为对人性恶防范的单一的和最后的屏障。由于道德无效,中间又缺乏其他层次的法律作为解决矛盾的缓冲层,因而积累的矛盾一旦爆发,就很难防范,往往导致严刑峻法,而结果却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正如有的学者在谈到儒家伦理影响下的法律传统时所说:“无论国法或民俗法律,强调的都是维护群体的秩序与和谐,而非个人正义与权利的发扬。和谐被视为不易的真理,冲突是不好的,如果不能避免,最好也能迅速和解,让和谐的秩序重新恢复。一味求和的情况下,往往只促成表面的和谐,一旦积压的怨怒爆发,后果有时反而更难收拾。”(23)
2.西方文化道德走势价值位阶和人性估价的现时性与所选法治控制模式实效的真实性和稳定性
从规范内容角度看,西方社会法治控制模式维护的西方文化道德走势中的“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与人性规律中的“小我”为重的价值位阶相一致并与社会实有道德态势和水平一致或低于社会实有道德水平,因而具有较大的现实性。人们会主动维护和利用这一规则体系保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由此,该规范体系的实现或实效会具有比较坚实的社会动力支撑。
从规范的效力角度看,法治模式效力实现的主要机制是外在的强制控制,其设定前提是人性恶估价或推定,是针对人性的最底线而设定的,是对人性恶的最低防范。因而,当社会实有道德水平与其相等,也即降到最底线时,它是一种有效防范的手段,而当社会实有道德水平高于它时,则它的实效就有了法和道德、外控和内控的双重保障。因而,人类道德水平发展到现阶段,法治控制模式和德治控制模式比较起来,其实效应该是更加真实和稳定的。
三 中国当代文化体系中的“自我”单位变量走势的反向渐变与法治模式的追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文化中的“大我”为重的道德走势的价值位阶和社会控制的德治模式仍没有改变,只不过这里的道德倾向中的“大我”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工作单位”取代了“家族”,“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封建王朝”。个人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中仍没有任何地位,在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中仍体现出“大我”为重的价值位阶。这种情况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至极端:在意识形态领域提倡和捍卫的是“忠”和“公”,而“私”则成为批斗的对象。在所有制形式上则奉行“一大二公”。由此,自然人被忽略,经济人被否定,政治人和道德人合而为一,法律成为虚无,法治和法律人自然不会存在。虽然这里的“大我”已经是“人民”自己,从理论上说,“公利”和“私利”是一致的,但人们的实有道德水平与这种理想化的道德要求仍有很大的差距。这种情况也许正如卢梭所说:“每一个要使自己的利益脱离公共利益的人都看得很清楚,他并不能把两者完全分开;然而在和他所企求获得的排他性的私利相形之下,则他所分担的那份公共的不幸对他来说就算不得什么了。但除了这种私利之外,则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还是会和任何别人一样强烈地要求公共福利的。”(24)由此,德治模式的实效仍然很差或不稳定,往往导致德治理想秩序的难以实现或扭曲实现。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思想和制度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解放和改革,其重要前提和趋势之一是对“小我”为重倾向的人性规律的客观认识和承认。从思想的禁锢到解放,从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到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对自然人和经济人的忽略和否定到对二者的承认,无不体现这一趋势。当然,根据道德态势和社会控制模式需求定律,这一前提和态度也必然伴随原有的德治模式、人治模式向法治模式的转型。这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习和接受西方法治思想和法治模式的一个根本原因。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德治模式传统的深厚,我们在追求和设计法治模式的时候,不自觉地还会受到原有的德治模式传统和因素的影响。其具体表现是,在设定法律制度的时候,常将道德与法、人性善估价和人性恶估价混淆起来,以至于影响有效的法律制度的选择。当然法和道德并不矛盾。法治并不排斥道德和德化的作用,但道德和法律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机制,其前提也是截然不同的,各居人性的两端。道德是对人性善的最高期盼,法律是对人性恶的最低防范。德治是以人性善推定为前提的,而法治则是以人性恶推定为前提的。刑法规范是在假定人是罪犯的前提下设定的;侵权法规范是在假定人是侵权者的前提下设定的;程序法规范是在对人性的不信任的前提下设定的;宪法规范是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25)的推定的前提下设定的。而我们国家在设定法律制度的时候,往往以对人性善的期盼为前提来设定,因而往往不能有针对性地设计出有效防范人性恶的法律制度,尤其在防范国家工作人员权力失控方面的法律制度的设计上,往往强调国家工作人员的道德操守,而对他们人性规律的合理顺应和针对人性规律设定外在控制机制方面则较差,如我国目前高薪养廉制度、分权与制衡制度、发达的程序制度还没有完善起来即是体现。设定法律制度就像给狮子设计铁笼,在设计铁笼时,依据只能是狮子吃人的本性,而不能依据有的狮子可能不吃人或狮子有时可能不吃人这种最理想的估计来设定。法律规则的选定与人性善恶的估价又可用“木桶理论”来分析,即木桶能装多少水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而不是由最长的那块木板决定的。如果将人性比作做桶的木板,将法治比做木桶里的水的话,则判断木桶里该装多少水应该依据最短的那块木板,而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
注释:
①[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0页。
②[美]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③[美]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④当然,还可以做更多层次的分割。
⑤《礼记·礼运》。
⑥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5页。
⑦Larry Alexander(ed.),Constitution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27.
⑧[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55页、第168-169页。
⑨《韩非子·备内》。
⑩《韩非子·八经》。
(11)《韩非子·制分》。
(12)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
(13)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页。
(14)武树臣主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辞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5)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人都爱自己,而自爱出于天赋。”参见Larry Alexander(ed.),Constitutionalism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第169页。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洛克、孟德斯鸠、麦迪逊等人都以人性“恶”估价作为政治制度或宪政制度设计的前提和依据。亚当·斯密虽主张经济人的互利,但“互利”是以“自利”为目的和前提的,是“自利”理性化的结果。
(16)[美]H.W.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高鸿均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17)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页。
(18)“在儒家看来,社会行为规范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内心感情为基础的道德伦理规范;另一种则是凭借强制力保障实行的法律规范。儒家认为,自发内心的道德规范是真实的、有价值的、美好的,因而也是最有效的;而靠暴力驱使的法律规范则是不真实的、片面的、不美的,其效力是十分有限的。法律用强迫的办法迫使人们做什么,禁止人们做什么,但并不能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自觉地弃恶从善。人们一旦从内心的伦理要求出发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人们就能够自我制约。这样,法律就失去了作用。”武树臣:《儒家法律传统》,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19)Greald Stourzh,"Fundamental Laws and Individual Rights in 18th Century Constitution",in The American Founding-Essay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Edited by J.Jackson Barlow,Leonard W.Levy,and Ken Masugi(Greenwood Press,Inc.1988),p.170.
(20)任剑涛:《伦理政治研究——从早期儒学视角的理论透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1)参见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2)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4页。
(23)史布莲克语。参见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24)[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7页。
(2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标签:社会控制论文; 法律论文; 需求定律论文; 道德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人性论文; 有道论文; 利益集团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