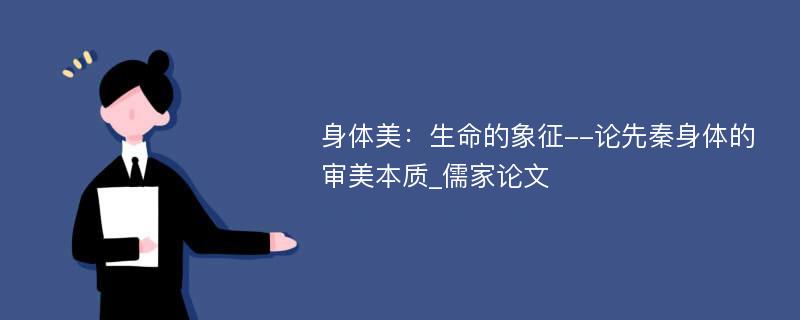
身体美:生命的象征——先秦身体审美本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体论文,先秦论文,象征论文,本质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7—018—024 一般而言,任何审美形态归根结底都是人类生命追求的象征,是一种生命之美,只是在不同审美形态中生命之美的表现形式并不一样。身体美是人类生命追求的肉身象征与表达。一部先秦身体审美史就是先秦人生命追求的历程。随着先秦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生命追求形式与主题的历时展开,体现这种生命追求主题的身体象征形式,即身体美也表现为不同形态,主要有:丰产之美、展现之美和自然之美。 一、丰产与生殖崇拜文化下的身体美 生殖崇拜是人类社会早期的鲜明主题。中外学者,如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理安·艾斯勒、郭沫若、闻一多、赵国华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过这一历史主题。人类社会早期炽盛的生殖崇拜现象的出现,在根本上是由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生产工具极端简陋的人类社会早期,人是第一生产力。为了物质生产的丰收,必然诉诸于人多力量大;而为了人丁兴旺,又必然高度重视人类自身生产。因此,人类自身的繁衍便成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成了人类社会能否延续的根本大事。“出于对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的严重关切”,炽盛的生殖崇拜出现了,“换句话说,生殖崇拜深刻反映了一个绝对庄严的社会意志——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人的再生产”。[1]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马克思所论述的“两种生产”(“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历史地统一于生殖崇拜的主题中。 在生殖崇拜的历史氛围中,丰产,即生殖的最大化、最优化是生命能量与生命能力最为核心的指标。生命以丰产为美,在此便构成身体审美的本质。就女性而言,陈醉在《裸体艺术论》一书中指出,在原始时代无论是我们中华民族,还是亚、非、欧、澳、美其他民族都塑造了各自民族的裸体“女神”。学者们把这些裸体的“女神”,美其名曰“维纳斯”。这些散布在世界各民族中的“维纳斯”差不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人物大多被雕刻成一个混沌圆浑的整体,诸如身体动态刻画,整体的比例关系以及脸孔、手、脚等细节的表现几乎完全未被注意,或者说,她们几乎未有能力展开自己的四肢,更未有能力去显示她们的表情。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单纯化与抽象化的倾向,明快而富有雕刻的质感”[2]8;不过,这些女性人体裸像“虽然对人体正常比例、人的脸部、五官等并未关心,但是,在造型上却具有另一些共同而显著的特色,那就是特别夸大诸如乳房、臀部、下腹等等女性特征,有的还作了明显的刻画”[2]10。简言之,丰乳、隆腹、肥臀是这类女性裸体形象最为突出的形式特征。有意味的是,在如此直露、大胆的艺术表现中却并未显露出半点淫秽的色情意味,相反,“在这些丰富的艺术作品中有一个常见的主题,这就是女性身体的神圣——确切地说,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女性生殖器、乳房和子宫的神圣”[3]63。这是因为“在文明初现之时,女性的阴门被当做奇妙的生命之门受到膜拜,它具有繁殖肉体与精神启蒙和转化的双重力量。女性的阴部三角……是创造生命的性力量的神圣体现。它不是低下的、卑贱的或肉欲的,而是后来叫做伟大女神的主要象征:生命、快乐和爱的神圣源泉”[3]17。人们对这些稚拙的女性人体裸像冠以“女神”、“维纳斯”的美学赞誉,实质上是对女性“能生育”的由衷礼赞。丰乳、隆腹、肥臀既是女性“能生育”的生理基础,也是丰产的象征。这些被夸饰的女性性征作为丰产的象征和生命的神圣源泉,它们历史地凝结为了那个时代女性身体形式美的基本要素。就男性而言,生殖崇拜下的丰产理想则表现为以“力”为特征的身体美。与女性相较稍显不同,对男性生殖力的崇拜是混杂在对男性生存能力的英雄崇拜之中的。例如,在我国考古发现的一些史前时代的狩猎岩画生动地展示了狩猎中的男性形象。这些岩画中的猎者具有差不多相似的形式特征:体魄强壮,弩弓欲射,给人力大无比的感觉,且对男根做了图案化的夸饰处理。这种“有意味的图画形式”暗示,在初民那里生存能力崇拜与生殖能力崇拜实为一事。身体魁梧、力大无比的男子既意味着生存能力的强势,也使人对他的生殖能力有丰富的想象空间。这具体表现在:“力”成为社会评价男性阳刚之美以及在两性性选择中女性选择男性的标准,“在文明状况之下,最能得女子欢心的男子往往不是最美的,说不定是美的反面的。……女子所爱的与其说是男子的美,无宁说是男子的力,身心两方面的力。……女子不作性的选择则已,否则她总会选一个强有力的男子,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男子才有希望做健全儿女的父亲和保家之主”[4]。无论是“丰乳肥臀”的女性美还是以“力”为特征的男性美,这种身体美观的出现固然也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与生殖崇拜下的丰产诉求的关系最为密切。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对人类生殖过程的形象而朦胧的认识中,凝结了最初始的身体美意识。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随着性的自制已不可避免,人类对生命的丰产理想虽然不再以大胆、赤裸的身体性征展露表现出来,但生殖崇拜思维仍然一以贯之地对身体美学发生深刻影响,形成了整个先秦时代一种主流的身体美观念:“以硕大为美”,它与前述远古时代“丰乳肥臀”的女性美、以“力”为特征的男性美观一脉相承。以《诗经》为例,它所称赞的美男美女几乎都是形体伟岸健硕者,谓之“硕人”。《诗经》赞美男子的诗,如:“硕人俣俣,公庭万舞”(《邶风·简兮》),“有美一人,硕大且卷”(《陈风·泽陂》),“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阳兮”(《齐风·还》),“伯兮朅兮,邦之杰兮”(《卫风·伯兮》),“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郑风·丰》)等。以上诗中的“硕”、“茂”、“昌”、“朅”、“丰”都为描述男子体魄雄健魁梧的赞美之辞。再看赞美女子的诗,如“硕人其颀,衣锦褧衣”(《卫风·硕人》),“彼其之子,硕大无朋”(《唐风·椒聊》),“辰彼硕女,令德来教”(《小雅·车舝》)等。无论男女,均以身体硕大为美,原因在于硕大的身体既有利于男性从事物质生产,也有利于女性从事人的生产,因而形成了共同的身体美标准,它与至《诗经》时代依然炽盛的生殖崇拜相关。郭沫若、闻一多、赵国华等学者都指出,中华民族的祖先最早情有独钟的某些物象,如鱼、鸟、蛇、蛙、凤的形象,都无外乎为男女生殖器、生殖能力的隐喻。闻一多解读《诗经》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念念不忘生殖崇拜对古人文化心理的影响。郭沫若认为,先秦典籍中的某些符码都蕴涵着生殖崇拜思维的信息,如他认为《易经》的阳爻与阴爻分别取象于男根与女阴,《老子》第六章中的“玄牝之门”为女阴之隐喻,等等。这说明,若抛开生殖崇拜主题来理解先秦文化恐怕是不完满的,也难于理解当时的身体美学观念。 今天看来,以硕大为美的身体美观,尤其对于女性而言,并不完全符合理想的形式美规则,但它寄寓了生殖崇拜文化影响下强烈的生命丰产诉求与理想。这一方面既抑制了时人对身体美的过多奢求与想象空间,另一方面也因此使以硕大为美的身体美观显得十分突出。时至今日,生殖崇拜对国人的文化心理仍有绵长的影响。受此影响,生命的丰产理想始终深度影响着国人的身体美观念,如女性的丰乳肥臀,男性的魁梧力量,这些要素已然凝结、积淀为人们对一个女子或男子身体形式美判断的基本标准。 二、展现与礼乐文化下的身体美 进入西周后,先秦时代中国人的生命意识有了新的觉悟和维度。从《左传》“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说的成立到孔子的“仁者寿”理论,都在宣示出一种新的生命哲学已然登场,即超越生理性身体的有限性,成就扩大、整全的身体,成为了一种弥漫于当时思想界深刻的时代之思。“不朽”概念的出场饱含着人们对生命有限性的无奈感受和深刻认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的喟叹生动地道出了生命如同流水一样有逝无回的怅然事实。就生命的有限性而言,人如同动物一样都会经历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在这意义上,人与动物没甚区别。人猿之异自当在生命的厚度、质量上下工夫。人们认识到,生命之“不朽”若仅仅寄托在生命的丰产理想、生理性身体的长生久视上并不完全,也不可靠,而是应在有限的生命中尽可能地攒取生的光辉和意义。 在这种新的生命哲学下,所谓身体美即人的生命的全然展现,在有限的生理性身体上展现人的生命的独特尊严和意义。逻辑地看,身体美与人的生命的展现,二者的内在关结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予以理解:其一,展现,是人之为人的独特存在方式。只要是人,不论其性别、身份、职业如何,都会展现自己,否则他(她)会感到压抑、难受。一个从不展现、表达自己生命形象、生命意义的人,只是生活在自身的黑暗世界之中。展现不是人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而它本身就是目的。人除非展现,难以成全人之为人的独特本质。动物是无法展现的,它永远只生活在自身物种的必然性之中。其二,展现是身体的展现,“因为:一、展现是身体在展现,除却身体,人无法有所展现;二、展现的向外性,和身体之作为一种生物生理的外向欲动是一致的(如饥食渴饮、目视美色、耳听好音),亦即展现作为一种活动和身体的任一活动之间,是融入为一的。身体之作为一种形,本身就是一种展现的隐存,此种隐存随着任一身体之分殊的动作而浮现、明确”[5]278。若身体美作为人的生命的展现这一命题成立,那么个体的生命状态将最终呈现为相应的身体形象、风姿乃至气象。 当然历史地看,人的生命不是抽象的概念,它的内涵在历史的过程中逐渐生成,又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从先秦史看,人的生命存在根本性地进入一个更加细腻、文明的时代,学界公认乃西周之际。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6]而其中最为关键的节目是周公“制礼作乐”。用今天的话说,礼即制度文化,乐即观念文化,礼乐文化即是一套集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于一体的系统。它的创造标志着先秦人由此进入了一个自觉地进行自我塑造的礼乐文化时代。在这一时代,人们不断重塑着自己的人学观。“在《论语》中,关于人的基本概念是:他是一个生来就要进入这个世界之中的人——更具体地说,进入到社会之中的人,具有被塑造成一个圣贤君子的潜质。一开始,他是一块原材料,一块璞玉,必须通过学问的滋养和文化的熏陶才能够得到精心制作,必须通过礼的塑造和约束。”[7]所以《论语》论人之修身养性时言必谈礼乐文化,如“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在先秦思想家看来,人的本性如同一块璞玉或原材料一样是朴野、粗糙甚至残缺的,只有经过礼乐文化的滋养与范铸,人的生命才获具有别于动物的独特规定性,才臻至完满与整全。“礼者,体也”,这一字义训诂最为深刻地揭示了身体生命与礼(乐)的本质关联。“凡用血气、志意、知虑,由礼则治通,不由礼则勃乱提僈;食饮、衣服、居处、动静,由礼则和节,不由礼则触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趋行,由礼则雅,不由礼则夷固、僻违、庸众而野。故人无礼则不生。”(《荀子·修身》)这就是说,人在血气、容貌、服饰、举止乃至日常的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等诸方面,是否接受礼的规约,是人的高雅与野蛮的分水岭。礼(乐)文化能使人摆脱朴野的自然人性而生成文化人性,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所谓“人无礼则不生”的“不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一方面指难存于当时的社会,另一方面也指一个人的价值生活的消陨”[5]267,简言之,没有礼仪,人无以生活,人做不成人。“人无礼则不生”这个斩钉截铁的全称判断意味着,与其说人外在地创造了礼乐文化,还不如说礼乐文化内在地成全了人的生命本质。生命以礼乐文化的展现为美,在此便构成身体审美的本质。 西周以来,礼乐文化下的生命展现落实到身体形象塑造上,阶段性地先后形成了四种身体美学观:威仪观、践形观、美身说和“内美修能并重”论。威仪观是春秋君子的身体美学观。《左传》有一段论述威仪观的经典话语:“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君有君之威仪,其下畏而爱之,故能守其官职,保族宜家。顺是以下皆如是,是以天下能相固也。《卫诗》日:‘威仪棣棣,不可选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襄公三十一年》)所谓“威仪”是一个体在“施舍”、“进退”、“周旋”、“容止”、“作事”、“德行”、“声气”、“动作”、“言谈”之间展现出的文雅与威严合度的整体身体美学形象。“威仪”是西周以来君子们身体审美追求的时尚。在《左传》、《诗经》等文献中,“威仪”一词频出其中。所谓“威仪三千”这一类语言就足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模态。孔子便是威仪观的忠实实践者。《论语·乡党》非常具体、生动描述过孔子在不同场合、情境中的身体仪态: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日:“宾不顾矣。”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从中可以看到,孔子在家乡、朝廷、接待外宾、出使诸侯国等场合的身体仪态是不一样的。他身之所处,随着场合的不同而变换着自己的身体仪容,其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近乎程式化的表演,具有审美装饰性。孔子的谦恭揖让、行礼如仪,此正是春秋君子“威仪”身体形象的典范。它实际上是先秦宗法等级制生存秩序要求特定角色个体所必须如此的身体仪容,所以孔子才如此一丝不苟。先秦礼乐文化的核心关怀在于建立一个上下尊卑贵贱长幼亲疏关系分明的宗法等级制生存秩序。这即是礼的精神,即“别异”,强调个体社会角色的准确定位。当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忠实地按照与其角色相一致的身份扮演相应的身体形象时,一种有秩序的生存体系便有了其感性的现实形式,才算真正建立起来。春秋君子的身体美时尚——“威仪”,不仅是一种的外在身体仪容,还在行礼如仪间范铸出一种人文化的意义空间,即宗法等级制生存秩序。“威仪观真正的内涵是礼,这是可以确认无疑的。”[8]31一方面,当人们“依礼而行,体现了礼,因此,他也就体现了当时的规范系统及价值系统,其容貌自然而然地也就有威可畏,有象可仪”[8]40;另一方面,当“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仪”时,一种理想的生存秩序自可期矣。 不过,时序进入春秋晚期后,随着“礼崩乐坏”,先秦社会步入了“后礼乐文化时代”,其突出特征是礼乐文化的形式意义越来越多于它的实质内涵。孔子关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的忧虑便流露出了对春秋晚期以来礼乐文化愈发形式化,以礼为内涵的威仪观实践陷入徒有其表的无奈感受。那么,后礼乐文化时代的个体生命展现如何呈现理想的身体形象?这有两种不同的思路和观点,即孟子的践形观和荀子的美身说。 先看践形观。“践形”一词,语出《孟子·尽心上》:“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践形”之“践”,历来注家有繁复释义,按杨儒宾的解释,可以通俗地作“实现”、“朗现”义解。所谓“践形”,“意指透过道德意识之扩充转化后,人的身体可以由不完整走向整全,全身凝聚着一种道德光辉,成为精神化的身体”[9]415。孟子的践形观不再如威仪观那样用力于身体之形,而是把人内在的德性精神作为身体美的根本。孟子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子下》),当个体通过后天修习的德性精神充盈于内时,它必显发于体貌形躯,如他所云:“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这种“睟面盎背”的躯体形色就是内在德性精神的圆满于体貌上所显象出的感性光辉。依践形观,修心就是正形,“心”可以实现对“形”的渗透与塑造,甚至能够修复、弥补身体之形的某些外在不足;一个强大的心灵能够焕发出一个巍峨的身体形象。《孟子》一书反复塑造的“充实而有光辉”的“大人”正是其践形观指导下的理想身体形象,它是学者长期“善养浩然之气”,能够“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道德凝聚与精神提撕之结果。 再看荀子的美身说。《荀子·劝学》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君子之学,以美其身。”这就是荀子的“美身说”,它明确指出“学习”渗透、染化形心的效果和作用。但学的内容是什么呢?其中最为重要者就是“礼”。“礼”是荀子学说的关键词,与孔、孟相比,荀子更为重视“礼”。《荀子》一书凡三十二篇几乎篇篇绕不开“礼”的话题,不仅专列有《礼论》,且其他篇目如《修身》、《不苟》、《非十二子》等对“礼”所论皆多。荀子认为,“人无礼则不生”,“礼”对个体身体形象的塑造有方向性的规定作用。所谓“美身”,即“以礼美身”,以学礼、习礼的方式来塑造美的身体形象。荀子笔下“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诎,而形不为劳”、“服五彩,杂间色,重文绣,加饰之以珠玉”(《荀子·正论》)的帝王之美和“冠进”、“衣逢”、“容良”、“俨然,壮然,祺然,薛然,恢恢然,广广然,昭昭然,荡荡然”(《荀子·非十二子》)的士君子之容则是其美身说兑现的理想身体形象。 应该说,在先秦儒家思想内部,践形观和美身说都阶段性地回答了后礼乐文化时代理想身体形象的重构问题。践形观认为,只有在人的身体形象中注入精神的内核,才能使其摆脱徒具形式的空心化窘境。在这个意义上,践形观对威仪观作了补充。“孟子以前,儒家传统对于身体的锻炼,主要是围绕着威仪观展开的。在威仪观的系统下,学者身体所要体现的正是生活世界中的伦理规范,在当时说来即是礼乐文化。然而,时序进入战国以后,周文衰弊、礼崩乐坏,因此,学者如再以前代之威仪自持,往往只会死守枝节、徒具形式,道德的实践缺乏内在的动力,也缺乏参与社会重构的功能。事实上,儒家的威仪观在东周时期一直受到严厉的挑战,儒者往往成为新兴思想家揶揄的对象。孟子处在这种价值解体的时代,想在礼乐形式的背后寻找其源头活水,毋宁是种非常合理的选择。我们可以说:孟子的践形观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对传统威仪观的一种修正。”[9]447而美身说则仍然坚信礼的美身作用,把践形观不大谈论的礼重新捡回来。在《荀子·非十二子》一文中,荀子奚落那些满腹仁义道德的腐儒的身体仪容丑态,如子张氏“佗其冠,神其辞,禹行而舜趋”,子夏氏“正衣冠,齐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子游氏“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就在于他们抛却了礼对人身的必要检束。在坚信“礼以美身”这一点上,美身说对威仪观作出了呼应。 从上述分析来看,先秦儒家就礼乐文化下的个体生命展现如何呈现出理想的身体形象,形成了三种身体美学观,即威仪观、践形观和美身说。逻辑地看,此三者在性质上又可归为两类:践形观属于德性身体美学观,威仪观、美身说同属于礼仪身体美学观;前者认为人的身体美根于人的内在德性扩充,后者则认为人的身体美根于社会的外在礼仪规范。二者各有所偏,又可相互启发、补充。从德性身体美学观看,一个德性精神强大的个体生命能够焕发出一种浩然的身体风姿;不过这也不能走向极端,一如礼仪身体美学观所宣示的那样,对外在身体仪容的检束仍然是必要的,否则也难以收到令人赏心、悦目的双重审美效果,毕竟粗服乱头仍不失其国色天香者,历来寥寥。同样,从礼仪身体美学观看,一个遵循礼仪规定的个体生命也能够成就出文雅与庄严合度的身体形象;但如德性身体美学观所警示的那样,一个威仪棣棣的身体形象若没有某种精神灌注其中,其很容易陷入空壳化。这说明,无论是礼仪身体美学观还是德性身体美学观,它们既有各自的价值,又有其限度。 于是,至战国后期历史地出现了对礼仪身体美学观与德性身体美学观予以取长避短、有效综合的努力,这就是屈原的“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理论及其践履。屈原的“内美”追求,甚至乎以其最后的殉道形式,把践形观所倡导的“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滕文公下》)的德性追求由口头变为现实,“儒家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只有在屈原这里,才得到了真正的落实”[10];而屈原孜孜不倦地“修能”,在把践形观的极致之境化为现实的同时,又始终没有放弃威仪观、美身说,纵观《楚辞》他终其一生留给人们的印象始终是一个峨冠博带、佩剑饰身、楚楚动人的君子形象。屈原的生命存在实现了尽善尽美的双重极境。千载以来,屈原形象仍活在我们心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形象背后蕴藏着一个礼乐文化下的个体生命展现的理想境界。 当然,上述大致历时性出现的四种身体美学观,静态地看,同时也是先秦礼乐文化背景下个体展现身体生命之美的四种基本路径。深入地看,这四种路径是共存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个体、群体上,人们选择其中何种路径的自觉、突出程度及其所占比例不同罢了。 三、自然与文明异化下的身体美 春秋晚期以来,面对“周文疲惫”、“礼崩乐坏”的危机,先秦诸子内部的应对态度并不相同。一条线索是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仍然对礼乐文化抱有充分信心,通过对礼乐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提振、释放其新的文化生命力。另一条线索则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对礼乐文化彻底悲观失望,并给予激烈批判:“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将礼(乐)文化视为乱世的渊薮。再看《庄子》中的孔子也不再是礼乐文化的守护者,而是不断自我否定:“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墮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这段对话中的孔子与颜回对礼乐文化极尽洗刷之能事,已经完全不是《论语》中的那般形象了。不过,老庄对孔门儒家所关怀的礼乐文化的批判并非出于情绪性的门户之见,而是有更为深沉远虑的关怀:“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庄子·骈拇》),“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在这些话中,庄子深深悲叹,从小人到圣人,人人都为外物所役使,为名利、家国、天下等而劳碌奔波、残生伤性。这就不止于对礼乐文化的批判了,而是掘进到了对文明的深切反思,即文明异化,“人在日益被‘物’所统治,被自己造成的财富、权势、野心、贪欲所统治,它们已经成为巨大的异己力量,主宰、支配、控制着人们的身心”[11]。在文明的发轫期,老庄道家触及到了异化主题,确乎有着无比深邃的哲学洞见。 在文明异化已然显题化的时代,老庄道家认为,如果仍然“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庄子·马蹄》)已无法收获积极效果;相反,人的生命存在无论在内在价值还是外在形态上惟务自然,才是理想选择。所以,老庄主张“绝圣弃智”、“绝礼弃乐”,赞美生命的自然之乐:“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庄子·逍遥游》);“斥鴳……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庄子·逍遥游》);“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引水,翘足而陆……陆居则食草饮水,喜则交颈相靡,怒则分背相踶”(《庄子·马蹄》);“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庄子·养生主》);“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庄子·秋水》)等等。展翅九万里的鲲鹏,翱翔蓬蒿之间的斥鴳,率性喜怒的马匹,从容出游的儵鱼,一啄一饮的泽雉等等,在庄子的心中,这才是一幅充满生机、诗意栖居的生命图景。庄子虽然赞美的是自然界生灵的活力,但其真实意图在于以物喻人,昭示人的生命之生机的奥秘所在:自然,即自然而然,不虚伪,不矫饰,顺从生命的本然逻辑而存在。 于是,生命以自然为美,在老庄道家的思想逻辑中便构成身体审美的本质。《庄子·天运》中讲述了一个故事:“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有名的东施效颦的故事即出于此。与西施邻里的“丑人”效仿西施而丑态毕露、终成笑剧在于,她对身体美的追求完全忘记了自身的本己条件而陷入了对他者的盲目崇拜之中,由模仿而矫饰,由矫饰而愈发丑态百出,甚至令人可怕到富人、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程度。所谓“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的意思是,这位“丑人”并没有弄懂西施的“矉美”在于它是西施多愁善感(病心)的生命气质而散发的独特魅力,这对于西施而言是其本己生命状态的自然流露,是自然美,但对于西施之外的任何模仿者而言就未必美。归根结底,故事里的“丑人”没有领悟到,人的生命存在及其身体形象乃以自然为美,矫饰乃至巧伪未必能带来积极效果。人人都拥有天生丽质是不现实的,但若每一个体都展示出自己生命的真实、本然状态,如同展翅九万里的鲲鹏、翱翔蓬蒿之间的斥鴳、从容出游的儵鱼、一啄一饮的泽雉等多姿的生灵那样,那么按庄子哲学,每一个体都会呈现出自身别具一格的身体风姿。自然赋予人的身体的美,比任何非自然的雕琢繁饰的作品更生动真实。对于擅长以礼乐文化精心包装、威仪棣棣的孔子形象,庄子并不以为然。在《庄子·盗跖》中,庄子借盗跖之口讥讽孔子为虚假不实的“鲁国之巧伪人”。纵观《老子》、《庄子》等文本虽然很少有对身体美的具象描述,但《庄子·逍遥游》中的一段话隐约反映了老庄眼中的理想身体形象:“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如处子……”。从“肌肤若冰雪,淖约如处子”之语看,所描写的“神人”的现实原型应是一位白嫩轻盈、婀娜多姿的少女身姿。这是一种天生丽质的自然之美,其中没有参杂半点世俗人为的修饰成分。这种身体自然美之令人动心,归根结底在于它背后蕴藏着一种如同少女般鲜活的充盈生命意识,一个未曾异化的自然健康的生命,其超越世俗、观念,而与光明同在。这正是生命异化已然濒临的老庄时代反弹出对身体自然美的渴求,即以身体生命的自然本色为美。 综上所述,动态地看,由身体的丰产之美、展现之美到自然之美,体现出先秦人对生命的理解、追求不断深化、提高的历史进程;静态地看,这又是三种平行共存的身体美形态,三者合为一体,共同构成先秦身体美形态的基本类型。它们基本上反映了先秦身体审美实践与生命追求这一主题的纵向脉络和横向布局。从中可以看到,先秦人的身体审美实践并不过分着意、拘泥于身体的外在形式美,也不刻意静态、局部地观察身体,而是看重生命整体的生机活力。丰产、展现、自然,是先秦人生命追求之生机活力的主要面相与表征,因而也就构成先秦身体审美的本质之所在。按这种本质论,人的身体的美归根结底依托于人的整体生命状态。没有一种生气淋漓的生命状态作为支撑,那么对于现实个体而言,即便他(她)的身体容貌、形体再出色,也不过是一具失血的橡皮人。认真把握这一点,对于当代社会中形式美至上的身体美创造观无疑是有参照意义的。标签:儒家论文; 生殖崇拜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诗经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荀子论文; 读书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