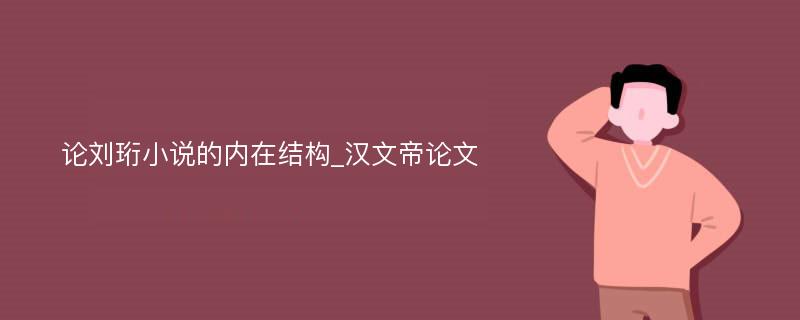
论刘恒小说的内在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论文,小说论文,刘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刘恒通常都是被当作“新写实”作家来谈论的。而新写实小说对主题的消解、对故事的淡化、对原物原汁的日常生活的偏嗜,都直接导致了小说内容的“原生态”。琐碎的生活细节的铺排成了小说内容的主体,结构安排上即是所谓生活流顺时序的自然流动,只求自然而无须考究,甚至可以说精巧的结构正是新写实作家所回避的,因为那难免与其生活化的总体特色有些不协调。如此,“新写实”作品似乎与“内在结构”不大有缘。
然而“不料主义的阔脸总有狡诈之色”,[①]刘恒可以被纳入“新写实”的麾下,但他十数年的创作恐怕远非人们最常提到的《伏羲伏羲》《白涡》所能说尽。我以为在注意其创作与新写实思潮同一性的同时也不应忽略其个性;在注意几篇出色作品的同时也应研究其创作的一贯性、系统性。本文正试图从内在结构方面考察其创作的独特风格及深刻内蕴。
我以为刘恒与其他新写实作家一个明显的不同在于他不醉心于生活的零碎,而热衷于故事,他明确宣称“有哪几篇小说不是讲老掉牙的故事呢?”[②]有故事就不能仅仅注重“过程”,它还需要结局。对死亡结局的偏好成为刘恒小说最显目的外在共性。或必然或偶然,或自杀或他杀,死亡总是刘恒小说人物的常见结局,侥幸未死的也总是以实际的失败作结局。这太多而相似的结局使刘恒在仅注意“过程”的新写实群体中显得卓尔不群,在许多新写实作家那里,“结局”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省略,因为其明显的人为性主观性有碍于“原生态”也有碍于“情感的零度”。而对于刘恒小说结局却至关重要,正是这些相似的结局使其小说具备了深层寓意,也使其简单的线性结构复杂化,从而有能力负担作品的深层内蕴。表面地看,刘恒小说也同样没有复杂精巧的结构,内在结构主要来自于人物行为的动机与结局之间明显的背离。他的小说人物总是处于一种焦灼状态,在各式各样动因的驱使下积极地消极地挣扎奋斗,在本质上这些努力的动机都是向“生”的,都意欲在或高或低的层次上实现生命的价值,而结局都是异常一致的死亡或失败,这种动机与结局之间的逆向性也就形成了小说逆向的内在结构。
刘恒小说逆向性内在结构有三种表现形态,首先表现为“求生的动机与死亡的结局”,这是其小说最常见的一种内在结构形式。《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连环套》、《陡坡》、《东西南北风》、《黑的雪》、《虚证》皆属此类,它们一个共同特点即是小说主人公常处于一种匮乏状态,追求这种匮乏满足的过程即构成小说的情节,但追求的动机与结局间却有生死的悬殊。无论是食的谋取、性的满足、金钱的需求抑或情感的沟通,动机都是为了生命的保存及生命价值的实现,可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匮乏难以满足,结果主人公行为“越轨”,以求生为目的努力却实际地将生命推向了死亡,使小说简单的情节蕴含了富于主题意义的双轨系统:主人公自以为其努力与挣扎会导向“生”,而结局却证明正是这种努力与挣扎导致了主人公的死,这就是作品逆向的内在结构。
《狗日的粮食》中的曹杏花,由于生在一个缺粮的年代,一生全副的精力与智慧都用于粮食的谋取,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言,粮食是人类保存自身及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她真可谓是谋食的天才,会偷会摸会夹带,会捋树叶、剥树皮、会跟踪追击掏鼠洞从鼠口夺粮,甚至从驴粪中找畜牲没有消化净的粮食星子,这样一个挣粮好手却恰恰死于粮食,偶然丢失了购粮本就吃了苦杏仁自杀身亡。乍看起来死得有些偶然,但实际却有其必然性;粮食对她来说太重要了,甚至超过生命本身,她自己不就是天宽用二百斤谷子换的吗?动机与结果间的严重背离使其谋食行为具有了双重性:疯狂的谋食一方面满足了其本能的需求,另一个方面却严重地异化了她的生命,以至她不知粮食为何物也不知生命为何物,她以为粮食即生命,生命即粮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她对粮食的追求在使生命得到延续的背后却使她一步步贴近了死亡。
《陡坡》中的田二道、《东西南北风》中的赵洪生、《连环套》中的兴来皆是如此,他们千方百计地挣钱,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物质享受,但更主要的是为了提高生命的质量,为了能象报纸上所写的经理们那样地生活,美好的生活需要金钱,而挣钱又谈何容易,只好不择手段,结果导致死亡或发疯。
《黑的雪》中的李慧泉比曹杏花幸运得多,因打架被强制劳动,出狱后做了个体户,衣食饱暖已不成问题,但他却有了比食更高的追求,——情感、友谊,正值青春期,他渴望结婚,但不肯与不相干的女人苟合,希望找一个他喜欢的正经女人,这样他爱上了貌似清纯的业余歌手赵雅秋,将她奉为偶象,可这偶象却走马灯似地换男朋友,最后将贞操廉价卖给了一个流氓。他进监狱就是因帮方叉子打架,方越狱后他又冒险窝藏,对马义甫那样不算朋友的朋友他多次予以资助,他希望得到友谊、爱情,可别人给他的却是欺骗和愚弄。他的死也是偶然的,在一次醉酒后被一群打劫的流氓所害,但我们以为实际上他早已死亡——情感生命的死亡,孤独、无助、冷漠早已窒息了他全部的情感,夺走了他生存的最后依据。他早已发现:人在别人眼里是无足轻重的,人们只为自己难过,人们最关心的只有自己,爱别人是假的,人们爱的是发出这爱的自身,别的人实在算不了什么,[③]追求情感生命的充实却导致了肉体生命的死亡。
在这一类型中,《虚证》有些特别,与前述作品相比,它颠倒了叙述顺序,以死亡的结局开头,而以对死因的追踪展开情节。郭普云的死真令人困惑,在“我”看来,他的“脸俊人好家贵,有官儿当有学上,能写诗会画画,他可不顺个什么?缺老婆还是眼高心不凡,老叹气是便宜得的不多,好处不完满”。的确,他三十刚出头已是一家兵工厂的宣传科长,大学文凭也即将到手,多才多艺却莫名其妙地自杀了。经过仔细的调查,“我”发现他时时挂在嘴边的不顺不外乎少年时的情感障碍,感兴趣的绘画的不成功等,而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无足轻重、微不足道,根本不足以构成自杀的理由,作者以“虚证”为题正说明死因调查的失败。但这不过是作者的艺术策略,他还是让我们看出了一点,那就是郭普云该死:他对生活对自己的要求太高太完美,他无视自己的许多成功却竭力夸大自己的失败,认定自己是小丑却看不出那些没有自杀的人只不过脸皮有相应的厚度,看不到那些自在地活着的人都是些不知礼义廉耻的家伙,对完美的追求使他不允许自己以降低生命质量为代价而苟活于人世,他对自己自杀的本质有清楚的了解,在一封信中他写道:今天翻了川端的《雪国》,不知怎的就想到了三岛由纪夫,把自己的肚子切开不就是一次惨败吗,死得那么辉煌,仍是摆脱不了对生的绝望的悲哀。[④]对于郭普云,死亡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正是对完美的生命的追求导致了他的自杀,辉煌的死恰是为了完满的生。
“表面的成功,本质的失败”是其小说内在结构的第二种表现形态。以《白涡》、《两块心》为代表。不同于第一种形态以动机与结局的截然矛盾构成内在结构的逆向,它是以结局本身截然不同的双重性质形成逆向的。表面地看,主人公通过努力而获得成功,取得一些外在于人的物质利益、权力地位什么的,而这成功却是以对生命的压抑,对人的本质的损害为代价的。周兆路本有个圆满的家庭,自己也是个功成名就的中医研究员,可自从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性闯入其生活以后,内心的平静被打破了,对女人清晰的非理性的本能冲动与理性压抑展开了激战。从一开始他就有一个纯粹的欲望,即有朝一日能得到她温软的肉体,然而理性也同时跳了出来,他不能不考虑他的事业家庭、前途。但在一次度假中他终于没能抗拒诱惑而尝了禁果,非理性的肉欲本能似乎战胜了理性,而实际上理性仍在进行有力的干扰,他企图将性与情分离开来,将女人视作自己征服的奴隶,在有意无意的自欺的帮助下,他从容地结束了这一非正常的关系,走出了困境,自己荣升为研究院副院长,而家庭也依然和睦如初。周兆路心满意足地以成功者自居,但我以为周兆路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周兆路,他将理智与情感对立起来,并以理智压抑损害情感,实际上他是个失败者,因为佛洛姆有言:由于理智成了监管人性的防卫兵,理智本身也就成了囚犯,于是人格的两方面——理智和情感都残缺不全了。[⑤]
《两块心》中的乔文政也是刘恒小说世界里极少的“成功者”之一。在现任乡长秘书的帮助提携下,他成了粮站的临时工,新的生活唤醒了他内心那已沉寂的骚动,他雄心勃勃地投入了生存的残酷竞争,可第一回合就被挑下马来。惨败的教训加上老同学的“教育”,乔文政日渐成熟,而偶然瞥见的一幕则更是让他彻悟:人什么都干得出来,人都是靠不住的,没有指望的,他所能指望的只有他自己。彻悟的乔文政一下子触摸到了人生的力量,开始独自面对人世拯救自己,最终以假装的老实和重友情成了清水乡服装厂的厂长和承包人,击败了把他当马骑的老同学和乡长。冷酷的人际关系造就了一个农民英雄,然而他失去了往日的淳朴善良,他的“彻悟”不过是把从动物进化的人又还原到了动物的水平,他抛开了诚实友情,只留下人特有的狡诈与欺骗,他因了“恶”而获得生存竞争的能力,却降低了人应有的品质,与人类进化历程背道而驰,表面的成功隐含着深刻的失败。
刘恒小说逆向内在结构的第三种形态可以称为逆转型结构,以生命力受阻后的变形与转向作为结构基础。佛洛姆认为:生命有其自己的内在动力,生命有生长及表现自己的倾向,如果这种倾向受到阻碍,以发展生命为目的的精力便会走上分解的过程,并且转变为以破坏为的的精力。[⑥]《杀》中的王立秋即是如此,在北下窑最困难的时候,他违背合同抽走股金进城搞建筑,结果全年的血汗钱被工头骗走,回村后,为了进收入颇丰的煤窑,他向原来的合伙人关大保苦苦哀求,忍受其百般污辱与嘲弄。如果说他领头开煤窑,搞建筑是生命力正向发展的话,那么到他向关大保跪下的时候,这生命力已开始变形,求生的进取变成了偷生的忍耐,仅仅为了对物质更多的占有,他可以屈辱地活着,牺牲人格尊严也在所不惜。被关大保拒绝以后,联想到那个包工头,他自然地得出结论:这世上有人不想让他活,生活力至此化成一股极具破坏力的怨愤与仇恨,他残忍地劈死了关大保,毁灭了他人生命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的生命,生命力因外在内在的阻力而发生逆转变成了以破坏为目的的精力。
如果说《杀》细腻地表现了生命力逆转的全过程,那么《萝卜套》则主要表现受阻的生命力两种不同的变态。以窑主一次偶然事故为界,窑梆子柳良地前后判若两人,此前,他贪财而胆小,为了一份丰厚的工钱,他甘于被窑主韩德培狗一般使唤,忍受其无情的耳光,甚至忍受着他与妻子的私通。窑梆子的地位决定了他的生命力难以逞正向发展,他只能忍辱含垢以做稳奴隶,但柳良地毕竟不是一条狗,他仍是人,仍有人格尊严的要求,只不过这一切暂时为物欲所掩蔽,但并没有被彻底消灭,而是在忍耐的背后变态地积聚为仇恨。在一次打猎中窑主因追逐黄狐落崖摔成废人,给柳良地提供了复仇机会,他一句“是老子把他从崖上搡下去了”就把以前不把他放眼里的老婆弄得号啕地跪了下来,并在她的秀眼里看出了自身的高大与心计,一个心造的幻影让他在心理上战胜了韩德培,通过贿赂的手段成为窑主后,他第一个决定就是雇佣只剩一口气的韩德培。不过工钱是窑梆子的身价——每月二百。韩德培占过他的女人,如今他自然不会客气,他还要建比韩家小楼更漂亮的楼房。一个偶然的事故使一个可怜的窑梆子成了一个能干的窑主,柳良地以前偷生的屈辱变成了复仇的酣畅,但这仍非生命力的正向发展,得意的复仇仍源于过去的奴隶生涯中的屈辱,这二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生命力的病态,二者互为因果又可相互转化。可以设想,当初将柳良地与韩德培调个位置,而柳良地又遭受与韩德培一样的厄运,故事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做奴隶时可以苟且偷生,做了主人必须会通过损害他人来弥补自己人格尊严的需要;做主人时视别人为奴隶,做奴隶必然为偷生而忍辱。环境的阻碍造成生命力难以恣肆,却形成恶性循环,其中自然谈不上人的健全发展。
刘恒小说内在的逆向结构清楚地昭示了其创作悲剧内涵:一切向生的努力却恰恰走向人们竭力躲避的死;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生存能力的加强却必须以对生命对人的本质的损害为代价;应以创造为特征的生命力却因种种原因的限制而难以勃发,被扭曲变形以至走向其反面,最后变成毁灭性力量。我以为对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的悲剧性的揭示正是刘恒小说的一贯性、系统性之所在,他以其差不多全部的创作多层次、多方面地揭示了这一点。首先是人在生理本能方面的内在悲剧性:人在后天被赋予的伟大、尊严、神圣却必须以动物性本能的满足为前提,否则这些本能的需求将变成生命难以承受的负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曹杏花的死亡才显得触目惊心,粮食不仅从道德观念、尊严意识方面损害了其作为人的社会性品质,粗暴地物化了本应得到丰富发展的生命,而且最后无情地剥夺了她那已严重蜕化了的生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天青的自杀才不仅仅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谴责,它还暴露了人在性方面的动物本能性与人的社会性之间矛盾的难以调和,显示了性本能对生命发展的又一重限制,属于本能的人的性需求虽因人的进化而获得了高层次的社会性,却永远保留了具有动物特点的本能的生理的内涵。杨天青叔侄二人的悲剧本质上都是性的悲剧,杨金山是性力缺乏的悲剧,杨天青则是性力过盛的悲剧,我不否认其悲剧的社会性,但以为这些社会性悲剧都是性悲剧派生的,性是小说悲剧发展的基本的内在的动力,刘恒说食性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几根柱子,其实又何尝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柱子。
欲望的无限性与其实现可能的有限性是造成生命悲剧的又一重原因。人的欲望似乎永不知足,一个欲望满足了会接着又产生一个新的欲望,而现实给定的却永远是有限的,因而欲望的满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人却并不因此而节制欲望,悲剧的发生自是难免。田二道、赵洪生本来都是老实善良的农民,企图靠诚实的劳动而过上美好的生活,但事实证明那只能是个梦想,于是修车的田二道在陡坡上撒图钉铁屑以增加补胎的机会,赵洪生则在麻将桌上押上了全部的人生,侥幸能在挑了房顶后“迎来一大轮完满的太阳”,本来田二道们的手段也有成功的可能,但作者却让他们一个因自己撒的图钉在陡坡上摔死,一个则因涉嫌杀人入狱而发疯,这明显可见作者的操纵,劝世意味不言自明:侥幸的成功是偶然,而失败才是必然的。只有死亡与发疯的结局才足以显示人欲望的无限与实现的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悲剧性。
如果说本能的负累、物质欲望的难以满足只是从较低层次上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悲剧性,那么对情感的需求与人类之间的难以沟通、生命的非理性与理性的矛盾则从较高层次上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悲剧性。人的生命存在首先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却别无选择地被置于群体之中,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此,人类总是渴望沟通与理解,然而“心外有骨、骨外有皮、皮外有衣”[⑦],于是以爱情、友谊为生命支柱的李慧泉只能以死亡作归宿,而作为个体,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理性与生命、情感又是一个带有永恒意味的话题。乌纳穆诺甚至以为:凡是属于生命的事物都是反理性的,而不只是非理性的,同样的,凡是理性的事物都是反生命的,这就是生命的悲剧根源。[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认定周兆路是个失败者,虽然他是个幸运者,因为人的健全发展至少要包括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更强的生命力更细致的生命感受以及更健全的理性。
通过对人类生命存在悲剧性的深刻揭示,刘恒的创作超越了作品具体内容的写实性,具有了某种程度的形而上的意味,而与那种对人类生存困境一般表现的作品区别了开来。的确,写实是刘恒小说一个相当明显的特色,除了那贴近肌肤的体验式描写,写实还表现在小说对故事背景的简单交待以及人物塑造上对身份的注意。背景的交待使故事因其特定的时间性而显得真实,而对人物身份的选择则为人物特定的行为奠定了真实的基础,写食、性、力气选择的是农民,以小煤窑为背景的几篇小说也以农民为主人公,而写理性、情感则选择周兆路、郭普云这样的知识分子。生活化的真实加上平静得近于冷漠的叙述使刘恒小说少有激烈的冲突,缺乏那种憾人心灵的悲剧激情,但这正与其作品悲剧内涵的深刻相适应,它不是对某种外在于人的异已力量的揭示,而是对人与生俱来的内在悲剧性的展示。本能的负累,欲望的无限与现实给定的有限,人追求完美的倾向与现实的永恒缺陷,这一切矛盾并不为某一价层所特有,而是人类普遍的永恒的矛盾。“生活化”消解了悲剧的偶然性而显示了悲剧的内在性、平凡性。冷静的叙述则显示了刘恒对人的生命悲剧认识的成熟,既然与生俱来就不必抢地呼天,而应该勇敢地面对这份欠缺,清醒地摆正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太美妙的处境,这样或许更有利于生命价值的完满实现。
通过作品内在结构而获得的悲剧内涵,更多的是给人一种悲剧启示,经由这种启示,刘恒超越了那些对生存困境无可奈何的哀叹,超越了那种对被生活击倒的人物的认同,而显示出独特的品格,写实中寄寓了一种深刻的生命悲剧意识,这正是刘恒独具的深刻。
注释:
①《逍遥颂·跋》《钟山》1989.5.P124
②《伏羲者谁》《中篇小说选刊》1988.6.P137
③《黑的雪》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
④《虚证》《开拓》1988.2
⑤⑥《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P133,P110
⑦《两块心》《小说月报》1989.5
⑧《生命的悲剧意识》北方文艺出版社,P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