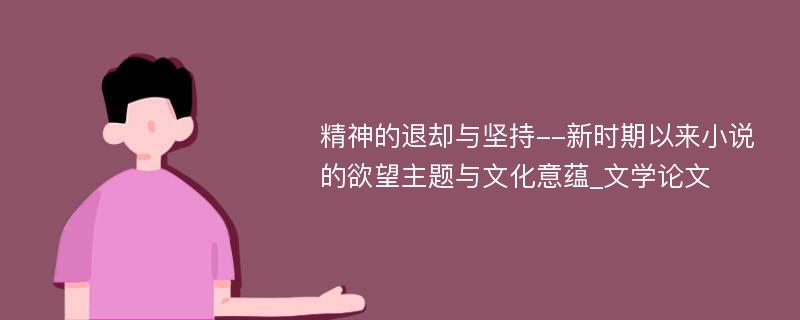
精神的退却与持守——新时期以来小说的欲望主题及其文化蕴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蕴涵论文,新时期论文,却与论文,欲望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有一个潜在的主题,即“欲望主题”,包括物欲和情欲两个方面的内容。探讨欲望主题在小说作品中的表现与发展有很重要的文化和哲学意义。
一、欲望主题的哲学意义
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1 〕孔子首先肯定了人类对富贵即物质的欲求的合理性,朱熹对这段话的解释是:“谓不当得而得之。然于富贵则不处,于贫贱则不去,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2〕朱熹的理解是正确的也是得体的,没有曲解孔子的本意。 看来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压抑人的“程朱理学”对人的基本欲求也持肯定态度。作为有意识的人类,在他具备反思自身生命的能力之时起,就开始意识到欲望对于自己的重要,但又不同于动物的本能,因而人类也开始告别愚昧,走向文明。如《孟子·告子章句上》就对道德精神与欲望的关系作了认真仔细的阐述与研究。
人类都有相同的经验,西方的《圣经》中,亚当夏娃之所以被逐出伊甸园,就是因为人类自己与生俱来的欲望,经受不住大自然的诱惑而偷吃禁果。正因为人类的原罪意识,所以人类常常犯错误,在两性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圣经》中有一段故事,约瑟在埃及逃难时,他的主人的妻子挑逗和引诱他:“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3〕
以上的举例可以说明这么几个问题,中国的哲学源头——诸子百家的理论〔4〕,是肯定人的欲望,后来中国儒学的建立, 尤其是新儒学的发展,对人们正常欲望进行了严厉地禁锢;西方对人的欲望也有禁忌,但相对于中国而言则宽松得多,东方对“欲”的表达曲折而隐晦,西方对欲的表达直露而大胆;“欲”在中国文化和文人心中的地位,中国人对“欲”的看法等都深刻地昭示着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自然观念和价值取向,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征、长处及缺陷。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当然逃脱不了传统思想的影响,将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尤其是欲望主题置于这个背景之下作一番研究,必然能探视到另外一片风景:中国当代作家和文学作品至今受到传统文化的哪些影响?这种文化是传统思想中的精华还是糟粕?这种影响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面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当代作家应持何种立场?
二、对生命本能的发现和对欲望的肯定
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其中表现欲望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80年代初期,张辛欣的小说创作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同一地平线上》、《清晨,三十分钟》、《疯狂的君子兰》等作品一问世即引起争论,争论背后的实质就是:如何认识人与社会的问题。张辛欣的小说对人的“动物”性的确认,或者说对人的“生命”属性的发现,如同一把闪光的钥匙悄悄地启动了“生命之门”。当然这种发现还是肤浅的、间接的、抽象的,还没有深入到人的生命本性之中。张贤亮的《绿化树》和《男人一半是女人》在食与性两个方面证明着人的生命属性,两部小说都认识到人是一种生命存在,人有生命的属性。
除了反映社会性问题的小说,作家对人的生命属性的认识还来自于自然律动的“生命启示”。80年代初至85年左右,出现了一批向大自然逼近、向江河湖泊迈进、向崇山峻岭挺进的小说。邓刚的《迷人的海》写出了大海的神秘莫测、变幻无穷、凶猛狂暴和自由不羁。作为海之子的大小海碰子,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征服险恶的精神、意志和力量,既是大海的性格,又是生命的天性,人海一体,海人同一,人就是海,海就是人。张承志的《北方的河》把读者带入了中国北方大地喧嚣轰鸣、蜿蜒纵横的河流之中。乔良的《陶》、孔捷生的《大林莽》、杨志军的《环湖崩溃》、蔡测海的《麝香》〔5〕、 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6〕岳建一和黎早的《荒魂》、〔7〕骆炬的《没有回音的峡谷》、〔8〕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洪峰的《脖尔支金荒原》等。这些小说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息,在精神实质上,体现出自然哲学和生命哲学的意味,但这种精神意味、这种浪漫气息是来自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土壤和情感气候,来自于一个古老民族欲重新振翅高飞的时代背景,表现了一种青春活力和生命动力的渴望。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新时期小说逐渐离开了“生命之门”,作家和文学作品的生命意识业已觉醒。人的欲望是与人的生理本能、生命意识紧密相联系的,只有生命意识彻底觉醒才能肯定欲望的合理性。如此类推,小说中的生命意识的表现其实质就是人的欲望的表现。所以,可以这么说,人类欲望由这时的一次探索性表现逐渐得到了作家和广大读者的肯定。如果说生命意识的觉醒主要是从生理上肯定了人的欲望,那么寻根中的许多小说则是从文化抑或说精神上肯定了人的欲望。其代表作有:莫言《红高梁》以及后来的作品《爆炸》、《球状闪电》、《秋千架》、《秋水》、《老枪》,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义的《远村》,郑万隆的《老棒酒店》、《野店》、《黄烟》、《地穴》、《火迹地》,张石山的《血泪草台班》,刘恒的《伏羲伏羲》。《伏羲伏羲》中,由于杨金山的年老体衰、生命枯涸,他便以虐待狂和变态心理凌辱摧残菊豆的身心。菊豆的生理本能和欲望遭到了严重的践踏和扭曲,当杨金山的侄子杨青山长大成人并知晓了男女之事,便克制不住对菊豆的欲念,而菊豆也萌发了对杨青山的青春的向往。于是,他们在生命原欲的召唤下闯入了伦理的禁区,虽然小说的结局是悲剧的,但向人们昭示着:人的欲望(包括身理和心理两个方面),如果不能得到正常的满足,人的生命将枯竭,甚至走向毁灭。
禁区已经打破,禁忌也得到解除,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得到了普遍的认同,那么新时期的小说又呈现出何种状态?
三、物欲、权欲的极度膨胀和性欲的泛滥
人的欲望很多,但不外乎两种:物欲(包括权欲)和性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的生命本源力量都是来自于人自身的欲望的存在,人类才开始对自然进行着永不歇息的征服活动,一个无欲的生命必然是一个平庸的生命、老朽的生命。文学作为作家生命律动的一种折射,是人类生命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它所直面的是人和人的生活。作为人性的基本内容——欲望,同样也是一个不可缺的表现部分。可以这么说,小说对人性的挖掘,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在终极上就是对人类欲望的深度展示。
当徐星、王朔的《无主题变奏》、《橡皮人》、《玩的就是心跳》、《剩下的都属于你》都坚持骂娘、坚持寻欢作乐的时候,当骂娘和寻欢作乐也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情的时候,小说反映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也开始日见端睨。80年代末期,肖俊志有一部长篇小说《阴阳际会》,小说毫不留情地撕下了军营神圣的面纱,还原于本来的面貌。作品以“文革”后期为背景,通过几个农村战士为争夺“铁饭碗”而采用不同的方式争取提干机会的种种行为。一方面表现了形式主义、伪饰、空话、陷害、造谣中伤等在军营中的普遍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揭示了私欲在人们骨子里头的活跃性。90年代初期,方方的成名作《风景》中七哥的恋爱婚姻——七哥放弃了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一位美丽而富有教养的知识女性,转而猛烈地追求一位大他八岁的老姑娘。为何原因呢?作品有一段精彩的描写可作为答案——
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了,她问七哥:“如果我父亲是像你父亲一样的人,你会这样追求我吗?”七哥淡淡一笑,说:“何必问这么愚蠢的问题呢?”她说:“我知道你的动机,你的野心。”七哥冷静地直视她几秒,然后说:“如果你还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你会接受这样家庭这样地位的人的爱情吗?”她低下头。
“她”接受七哥是有原因,但七哥猛烈地追求她则源于更明确的目标,即将依赖未来的岳丈大人进入上层社会,让命运完整地翻一个身。乔雪竹的《荨麻雀》叙说的是女知青(小说中的副连长)以自己的灵与肉被凌辱被摧残为代价,去换取党票和打通回城上大学的路的悲惨故事。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小说的主人公寥怀宝利用周围一切能利用的人际关系,由镇长当上农业副县长、地区副专员,最后成为市长,他沿着向上的台阶,一步一步地踏上了他垂涎已久的官座。
人们对权欲的追求还遮遮掩掩、似乎腼腆,对钱权的追求则大胆直露得多。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一些小说,何继青的《军营股民》描写了南方某大城市某军队警备区政治部一批高级军官在股票风潮中表现出的焦躁和欲望。尽管有军人不得参与股票活动的规定,但整个城市陡长的股票热还是燃起了军官们的欲望,打破了他们的机关生活。南翔的《海南的大陆人》、钟道新的《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张欣的《绝非偶然》、陈世旭的《荔蜜花苑》、陈丹燕的《吧女琳达》、莫怀戚的《南下奏鸣曲》,这些小说中拥挤着的男男女女,似乎都争先恐后地要换一个活法。对钱的无休止追求、钱欲的极度膨胀,更多的是体现在都市题材小说和“新生代”〔9〕作家的一些作品中。关于都市小说, 一位青年学者说了一段很精彩的话:“今天的中国都市既是文明的消费中心,又是文明的消解地——那里活跃着人生的各种欲望。都市,那是欲望的百宝箱、欲望的燃烧炉、欲望的驱动器。在这被驱动着、燃烧着的欲望里,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被烧毁了,一些属于文化的东西在火中生存着。”〔10〕关于“新生代”作家,刘心武有一段对邱华栋的评论的对话很具有代表性:“他写的是一种业已成功的人物,他们居住在别墅群或是豪华公寓,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那种非常考究的品味等等。”〔11〕“他还写出了另一类人,就是充满着物质的、欲望的向往,很渴望富起来的境遇中的青年,一些像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拉斯蒂涅那样的人。”〔12〕“这些新富人或是新的欲富者是邱华栋小说中相当重要的角色。”〔13〕
都市小说和“新生代”作家的一些小说,对欲望主题的表现有三种形态。一是面对欲望,被欲望诱惑,甘于沉醉此生。缪永的《驶出欲望街》,徐坤的《遭遇爱情》,池莉的《你以为你是谁》,母国政的《妻的谜语》,钟道新的《指令非法》,陈应松的《一个,一个,和另一个》,沈嘉禄的《大晴天》,彭见明的《晚唱》,何顿的《生活无罪》、《太阳很好》和《无所谓》,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时装人》、《公关人》、《直销人》、《持证人》、《钟表人》和《生活之恶》。这些小说真实、细致、具体地反映了人们充满着欲望,把自己投身于物质利益的追逐中,由此得到沉醉和幸福。《生活之恶》写一对居无定所的恋人为房子而苦恼。姑娘心平气和地用自己的初夜向一位大款换来一栋高级住房,献给自己的新郎,而觉得理所当然、物有所值。二是在物欲面前,很多人表现出一种无奈的心态。陈然的《喘息》、邹月照的《告诉我,我是谁》、肖克凡的《没戏的日子》、刘嘉陵的《焚书》、萧平的《小说二题·金窑主》、张欣的《爱又如何》等属于这一类。三是面对欲望,心理难以承受,因而逃避欲望。大约是因为欲望是痛苦之源,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说:“人的一切欲望的根源在于需要和缺乏,也即在于痛苦。因而,人生来就是痛苦的,其本性逃不出痛苦之股掌。”〔14〕邓一光的《掌声继续》、张欣的《岁月无情》、朱文的《我现在就飞》、徐坤的《鸟粪》等,这些小说传达了当代人对物欲泛滥的逃避和诅咒。
80年代末期是一个转折,这时候起,爱情文学完全忽略了民族伦理风范和东方美学气质,走向世俗化、平庸化,失却了应有的风采,小说中的性欲泛滥成为众所瞩目的问题。“近年来作品中形形色色的性描写:性本能、性冲动、性饥渴、性享受、性隐私、性乱伦……无所不包,无奇不有,步步升级,争先恐后。从内容提要到表述到书籍封面的包装,从普通的性恋情节到怪异的性爱故事,从一般动作的描写到床上细节的刻画,从挑逗到刺激性,人们的神经负荷和心理承受似乎已达到某种‘极限’”。〔15〕
有的评论家将新时期以来小说的性描写分为三个阶段:80年代末,张贤亮的小说、莫言的小说、王安忆的“三恋”以及新潮小说;93年,以《废都》为主的“陕军东征”;“晚生代”作家的一些小说和女性主义作家的小说。〔16〕我基本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关于三个阶段的性爱小说,另外有一些评论家作过很多的论述,我在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但我想简单地列举和说明一下新潮小说及“晚生代”作家的小说。新潮小说中的性爱描写将性爱本能化、欲望化和生理化,小说中充斥着乱伦、强奸、淫乱、嫖妓、宿娼、阳萎、性病等变态或病态的性爱。 〔17〕代表小说有,苏童的《米》、《十九间房》、《妻妾成群》、 《城北地带》,北村的《施洗的河》、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余华的《在劫难逃》,洪峰的《极地之侧》,孙甘露的《呼吸》等。“晚生代”作家的小说主要侧重于欲望的放逐、性本能的渲染、性经验的演示、性技术的操作。〔18〕代表小说有,刁斗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延续》,海男〔19〕的《我的情人们》、《没有人间消息》、《人间消息》,韩东的《障碍》,朱文的《我爱美元》,林白〔20〕的《一个人的战争》、《致命的飞翔》、《守望空心岁月》等。
这些性爱小说有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性与爱、灵与肉、情与欲正彻底分离,彼此没有任何纠缠,爱情的社会意义已被彻底掏空,留下的只有性,只有一种原始性的性操作的展现。
四、欲望主题的文化蕴涵
近20年来,尤其是近10年来,中国人一直在梦想一种东西,为了这个美丽的梦想也一直在刻苦追求,那就是急于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所以“现代化”成为国人的常用语,被广泛地运用于各个领域。现代化对中国目前的现实来说,的确是迫不急待的事情,它成了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动摇的历史意志,成了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的历史潮流,这种历史意志和历史潮流到了不惜代价的程度和地步,贪婪的物欲在被禁锢了多年之后被重新放归于历史潮流之中。因为我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处境,落后与贫穷激发了国人迅速致富的强烈要求,所以本来复杂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往往被提纲化、简单化,现代化最终和“钱”划了等号,人人都作着发财梦。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传统的体制、观念、信念都已不复存在,拜金主义空前盛行,官场内的钱权交易,官场外的坑蒙诈骗,法律遭到践踏,高尚的民族精神在物欲的压迫下无力呻吟。一些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这些现象作了描述:“在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莫过于腐败的滋生和蔓延……”〔21〕“在伦理道德方面,……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长蔓延,毒化着人的灵魂”。〔22〕“奉献精神、牺牲精神……诚信、正直、公平、仁慈、和谐等人类共同的社会公德,为一些人淡忘,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公然嘲弄”。〔23〕
小农经济思想一直统治着中国人的头脑,而小农经济的社会是冷淡物质、尊道德为价值尺度,而弃经济为价值尺度的。“何必曰利”、“重义轻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24〕“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络……”〔25〕小农经济社会讲求安宁、和谐,追求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意味。当富有强烈竞争色彩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化思想冲击人们的头脑时,大部分人必然感到茫然、束手无策,很多人没有认真地去思考、也来不及去思考眼前的变革,大家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这大概就是一时间物欲超出常态地膨胀的思想根源与基础。
恐怕谁也不能料到:如今的爱情文学基本上走向堕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出现了如此之多的性描写。许多学者从西方文学、西方哲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的角度作了很多扎实而有益的研究,但我认为这些研究不足以解释这一现象,还必须从自身着手作一番探讨。性既然是人类生活中客观存在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因此性描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也是不足为怪的现象,在文学批评与研究中,不存在一般地、抽象地讨论应不应该描写性的问题,只有一个应该怎样去描写性的问题以及对已经存在的性描写如何进行分析、 解剖的问题。 近20年小说性描写的陡然增多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背景,〔26〕同时也有极其深刻的文化根源。〔27〕这个深刻的文化根源首先来自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强大约束力。我们知道,儒家思想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体系和构架,在汉代定于一尊,被封为圭臬。从这时起,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中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便大为提高。这势必造成对两性间关系的严重桎梏,加上我国社会独特的家族家庭结构——父系单系制家族构成方式,这种构成方式偏重于父子间关系的密切和家族的亲密感,同时带来的是两性之间交流的隔离和族外关系的生疏。这种隔离与压抑,必然与人的正当的自然要求相抵牾,而两性的相悦与两性间情感的交流乃是遵循着自然界中“异性相吸”的这一普遍法则。人类在创造和完善自身的同时,也创造和完善了自身一个独特的东西——人类的感情,而同时也是满足两性间情的必要手段。这种外在和自律的压抑的欲望总要寻求一种解脱与渲泄。弗洛伊德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做梦与文艺就是满足被压抑的欲望的曲折的也是最好的方式之一。在此文化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唐传奇中出现大量的性描写。儒学到了宋代则成为新儒学,其中“程朱理学”是代表,“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其思想核心,他们坚持认为,物欲、杂念、邪气时时在影响人,以至人的内心欲为不善,又有羞恶之心,所以发出这样的言论:“欲之害人也!人之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强弗知,则至于天理灭而不知反……”〔28〕“天理与人欲相对。有一分人欲,即灭一分天理;有一分天理,即胜得一分人欲。”〔29〕“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30〕“身有嗜欲,当以礼仪齐之,嗜欲与礼仪战,使礼仪胜其私欲, 身得复归于理。”〔31〕“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32〕在宋明理学的文化禁锢的背景下,明代小说性描写出现了大肆泛滥的景象。〔33〕
我的以上论述,并不是研究古代文学,而是为说明三个问题:一、儒家思想中的禁欲文化思想、封建伦理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并影响着当代作家,对作家心理有一定的扭曲和戕害。二、说明了越是禁锢与封闭,性的欲望便越是要得到表现和展示。80年代以前的当代小说,性描写少而又少,而近10年却一发不可收拾,不能不说是非健康的。三、中国古代文学中,唐传奇和明代小说的两次性描写高潮,可以作为新时期小说三次“性高潮”的参照系。其次还来自于中国道教的思想。近年来,有少数学者关注到道教文化对当代小说性描写的影响。道教中的“采补术”(炼外丹)、“房中术”(炼内丹),对当今小说影响颇大,还有静坐静想、运思等,心理学上称为“幻想”和“狂想”。关于这一点,贾平凹的《废都》、《白夜》是典型的例子。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深入。
中国传统文化灿烂辉煌,同时也有许多消极因素和糟粕,如何继承其中的精华、去其糟粕,自觉抵制不健康的部份,关系到一个作家的主观精神问题。那么,当代作家该以何种精神面貌出现于文坛呢?
五、精神的退却与持守
本世纪30年代,英国诗人艾略特在他的《宗教与文学》中曾说:“当代文学作为一个整体,都倾向于堕落。”〔34〕时隔大半个世纪,在东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声音。张承志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太脏了,甚至以清洁为可耻,以肮脏为光荣,以庸俗为时髦。”〔35〕张炜怒不可遏地指出当前的文学作品:“它的制品——垃圾——包装得再好也仍然只是垃圾”。〔36〕我想,这是指当今的一些作家和作品陷入了令人困惑的欲望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热衷于欲望的展示而津津乐道,读者也沉迷于这些充满诱惑的作品之中忘乎所以。
但知识分子毕竟是知识分子,“自我解剖”意识并没有完全缺失,本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人文精神”的讨论热烈而持续。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文学应当对人类的精神处境和生存处境予以关切,并为解脱人类的精神困境投入真诚和热情,文学应表达它对人类基本价值维护的愿望和义务,在文学的娱乐功能之外,也以理想的精神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37〕“后世儒家思想将孔子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怎样做人与做怎样的人上下了许多功夫。这主要表现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宏阔胸襟;其次是‘忧道不忧贫’的终极关怀意识和现实取舍态度”。〔38〕
很多评论家和作家也纷纷发表自己的心声:“文学不仅是镜,也是灯。人类多少苦涩的岁月依然诞生了崇高的文学。文学正是因其抗拒身边的堕落博得历史的敬意,从而奠定了‘良知者’的传统身份。 ”〔39〕“‘文’之与‘道’,本如烛之与光、光之与烛,又如肉之与灵、 灵之与肉,二者无法分离。”〔40〕
近两年来,以《时代文学》和《作家报》联合开展“现实主义重构论”问题为代表,一些文学期刊都辟有较大的篇幅展开“现实主义文学现象”的论述,许多文学评论家和文艺理论工作者纷纷撰文,表现出巨大的热情。
在创作上,近几年来出现一大批敢于面对现实、批判现实、反映民生疾苦的好小说。我可以列出一串名字:张承志、张炜、史铁生、梁晓声、朱苏进、李锐、储福金、潘军、周大新、徐小斌、陈源斌、乔典运、刘庆邦、刘醒龙、何申、谈歌、关仁山、吕新、陈村、陈世旭、邓一光、阎欣宁、阎连科、李贯通、李佩甫、杨争光、陆天明、彭见明、向本贵……,其中河北的三位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同时闪耀于文坛,并引起广泛的注意〔41〕,他们的创作也启发了很多的作家:关注现实、扎根于现实土壤。
现在,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重要过渡时期,我们每天都可以目睹到,在真理与邪恶、进步与守旧、光明与黑暗、人性与兽性等等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抗争。此时此地,作为社会进步精神力量的一种来源与化身——我们的文学,理应负起特殊而神圣的使命。
注释:
〔1〕孔子:《论语·里仁》。
〔2〕朱熹:《四书集注》。
〔3〕《新旧约全书·创世纪》,引自中国基督教协会1994 年南京印发的《新旧约全书》第39页。
〔4〕我个人认为,这里还应加上《诗经》和《楚辞》, 它们对国人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都从文学的角度反映了人类的欲望思想,如《诗经》中有很多男欢女爱的诗篇:“野有蔓草,零露清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与子偕臧。”
〔5〕见蔡测海的短篇小说集《母船》。
〔6〕见《人民文学》1984年第9期。
〔7〕见《青春》丛刊1985年第1期。
〔8〕见《青年文学》1985年第1期。
〔9〕一批60年代前后出生、9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作家, 被文学界指称为文学的“新生代”。最近华侨出版社出版了“新生代小说系列”,有8位青年人的作品入选,他们是徐坤、何顿、毕飞宇、鲁羊、 张旻、韩东、刘继明、邱华栋。另外还有“晚生代”一说,与“新生代”基本同义,但这命名并不科学,缺少理论规范。
〔10〕程文超:《欲海里的诗情守望——我读张欣的都市故事》,《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
〔11〕〔12〕〔13〕张颐武、刘心武:《九十年代文坛的反思与回顾》,《大家》,1996年第2期。
〔14〕叔本华:《意欲与人生之间的痛苦——叔本华随笔和箴言集》,李小兵译,第1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15〕李复威:《新时期以来爱情文学的遭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16〕可以参见丁帆的《新时期小说三次“性高潮”后的反思》,《文论报》,1997年2月1日。
〔17〕可以参见吴义勤的《新潮小说的主题话语》,《文艺评论》,1996年第3期。
〔18〕可以参见洪治纲、凤群的《欲望的舞蹈——晚生代作家论之三》,《文艺评论》,1996年第4期。
〔19〕〔20〕海男和林白既是“新生代”作家或者说“晚生代”作家,也是女性主义作家,二者并不矛盾。
〔21〕〔22〕〔23〕俞可平:《关于现代化代价的反思》,《市场经济导报》,1995年第1期。
〔24〕孔子:《论语·卫灵公》。
〔25〕鲁迅:《安贫乐道法》,《鲁迅全集》第5卷,第53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6〕〔27〕关于社会根源,这一部的开头的一段话可以看成是这一社会根源。文化根源,这里主要指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糟粕部份,而非精华部份。
〔28〕程颐:《遗书》卷二十五。
〔29〕谢良佐:《上蔡学案》,《宋元学案》。
〔30〕〔32〕朱熹:《语类》卷十二。
〔31〕朱熹《论语或问》卷十二。
〔33〕明代小说性描写的泛滥,当然还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如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生长、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上层统治者的荒淫无耻与下层市民的靡烂堕落等。关于这些,可以参考另外许多论文和论著。
〔34〕艾略特:《宗教与文学》,这里转引自布斯著、胡晓苏等译的《小说修辞学》,第4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35〕〔36〕《抵抗的习惯》,《文汇报·文艺百家》,1993年第3月20日。
〔37〕孟繁华:《新理想主义与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光明日报》,1995年7月5日。
〔38〕畅广元等:《在世纪边缘牧歌——人文精神对话录》,《作家报》,1995年7月29日。
〔39〕〔40〕罗宏的《文学为什么不再崇高》、雷铎的《“文以载D”说》,《作品》,1996年第12期、1997年第2期。
〔41〕可以参见《靠近时代不离人民》、陈映实的《创造富有艺术魅力的时代文学》、雷达的《生活之树常青》、封秋昌的《同中有异,各具特色》,《文论报》,1996年9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