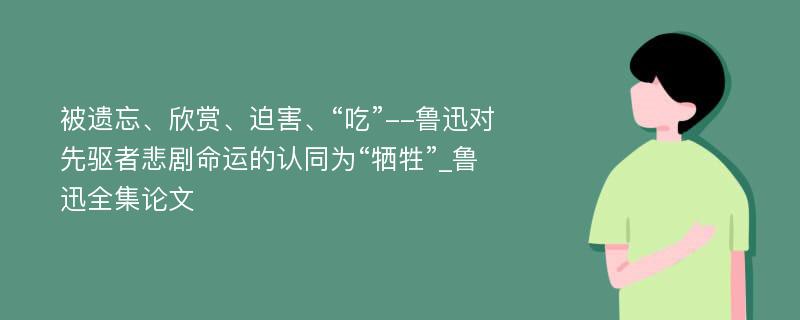
被遗忘、被鉴赏、受迫害、被“吃”——鲁迅对先驱者充当“牺牲”悲剧命运的体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先驱者论文,体认论文,被遗忘论文,悲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牺牲”:名词,古代用来指代充当祭品的牛羊等动物。鲁迅从自身的遭遇出发,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命题,即:在社会生活中,在文明发展史上,先驱者、改革者往往身不由己地陷入充当“牺牲”角色悲剧性境遇之中。
1.鲁迅本人对充当“牺牲”的体验和看法
鲁迅一生对充当“牺牲”多有体味,其中的两次遭遇尤为值得关注。1911年年底辛亥革命爆发不久,绍兴宣告光复,出任绍兴都督的是革命党人、“绿林好汉”王金发,鲁迅则担任了绍兴师范学校的校长。1912年初,绍兴师范的几名学生以鲁迅等三位社会贤达的名义创办了《越铎日报》。报纸一出版便大骂绍兴军政府和王都督,王金发立即给报社送去500大洋,以图控制报纸的舆论导向。办报的学生们背着鲁迅收下500元钱,但在报上继续骂王都督。鲁迅闻讯前往报社,批评了学生们这种不正当行为,反遭他们的指责;同时,社会上开始有了谣传,说是王金发想杀害鲁迅等人,鲁迅只好前往南京谋生。这几名心术不正的学生借鲁迅的名声办起了报纸,并且狠狠敲了王金发一笔钱,却让鲁迅背上“光拿钱,不干活,反而还骂人”的黑锅,着实让鲁迅当了一回“替罪羊”(注:鲁迅《范爱农》,《鲁迅全集》第2卷第314-3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版本下同)。)。
鲁迅另一次充当“牺牲”的事则是发生在1924年。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天花,鲁迅所任教的世界语专门学校学生大多已是20岁左右的人,却有不少还未出过天花,于是该校校医就来动员学生们去种牛痘。然而校医的进展很不顺利,因为大多数学生认为种牛痘是很疼的。鲁迅就在课堂上鼓动学生去种痘,效果并不佳。学生再三商量的结果是公推鲁迅首先去种牛痘。鲁迅此时年已43岁,并且幼年、少年时代已种过3次牛痘,大可不必去当“青年的模范”。不过他想用实际行动说服学生们,于是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往医务室。当时正值寒冷的初春,鲁迅脱衣、种痘、穿衣颇废周折,也受了一些寒。完事后鲁迅回头一看,他带来的“青年军”早已溜得一个也不在了(注:《鲁迅全集》第8卷第348-349页。)。于是,鲁迅又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回当“牺牲”的滋味。
现实生活的种种遭遇使鲁迅对充当“牺牲”角色保持着理性的认识。一方面,他指出了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某种规律,即:“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注:《鲁迅全集》第7卷第387页。)鲁迅认为,现在的人知道某些东西有毒,不可当作食物,这似乎很平常,实际上得出结论之前已不知有多少人为此而死去。所以,鲁迅认为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值得佩服的。鲁迅认为中药服用经验的积累同样也是以牺牲无数古人为代价的,牺牲的人多了,经验就上升为理论,于是有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注:《鲁迅全集》第4卷第539页。)。显然,这种牺牲是有价值的。
另一方面,鲁迅并不主张无谓地去作牺牲。当他的论敌“现代评论”派文人嘲讽他不去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时,鲁迅认为这是一种引诱他死于军阀刀枪下的诡计,他决不愿意上当。(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4页。)鲁迅更反对徒手的“请愿”。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说“请愿的事,我一向就不以为然的,”“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279页,第281页。)直到1935年底,鲁迅在他的《“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中还重申:“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张:不要再请愿!”
鲁迅的杂文《牺牲谟》值得注意,他在文中以反讽笔法刻画了一位“牺牲论”提倡者丑恶的嘴脸。作品中出现了两位人物:一位是已经得势的革命既得利益者;一位是革命胜利后仍一贫如洗的“前革命者”。他们原先曾经是“同志”,如今两人的地位已有天壤之别:一位是穿着非常体面、住宅相当豪华的“胖头胖脸”的老爷;一位是只剩一条破裤子,满身污垢,沿街乞讨的叫化子。当他们相遇后,老爷责备乞丐不去读书,不去做工;赞扬他“已经九天没有吃饭”是一种清高的行为;又批评他浑身臭味,不讲卫生;最后,老爷鼓动乞丐把身上仅有的一条破裤子捐献给“舍间一小鸦头”,并且扬言,若乞丐不肯“牺牲”这条破裤子,将有损自己的“晚节”云云。至此,这位正人君人,这位得势的老爷的“牺牲”论的虚伪本质已昭然若揭。
鲁迅一生都关注着先驱者、改革者沦为“牺牲”这一命题,他从先驱者、改革者被人们遗忘、被当作戏剧人物鉴赏,受社会的迫害,被民众当作供品而“吃”掉等角度揭示了他们的悲剧命运。
2.先驱者的被遗忘
“健忘”,是中国国民性的一大顽症。先驱者为民众所做的牺牲,改革者为社会所立的功勋很少能在民众记忆中占据永久的位置。革命成功了,人们关心和爱戴的是仍然活着的掌权者,至于那些在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中死去的先烈则很少会被人再提起。鲁迅在他的杂文、小说中反复表现着先驱者被遗忘的悲剧主题,萧条、荒凉的烈士坟墓则构成鲁迅作品一个核心的意象。
《呐喊》中的小说《头发的故事》一向不很受人重视,事实上,它的命意是很深刻的,它表现的是“忘却”这一悲剧性主题。小说主人公N回忆起清末民初的革命先驱者时深有感触地说道:“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地平塌下去了。”
鲁迅多次写到民国初年四烈士墓的荒凉。1912年1月16日,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三人试图炸死袁世凯,未成而被杀;同年1月26日,彭家珍炸清禁卫军协统兼训练大臣良弼,功成身死。后来,民国政府将他们合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又称万生园,即今天的北京动物园),在张、黄、彭三人的墓碑上都没有镌刻一个字。鲁迅在1922年写的杂文《即小见大》中为此事感到不解;他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写的杂文《空谈》中又提到四烈士坟中还有三块墓碑不刻一字的事,在文章最后,他悲愤地写道:“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鲁迅觉得“黄花岗”烈士们的命运也和四烈士相似,他曾在《辞源》中寻找有关资料,书里只作这样的描述:“黄花冈。地名,在广东省城北门外白云山之麓。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党数十人,攻袭督署,不成而死,丛葬于此。”词典对黄花冈烈士事迹只作轻描淡写,连战死的烈士的人数和姓名都不得而知(注:后来得知有72名烈士)。鲁迅发挥想象力,推想黄花冈烈士的牺牲在民众心中引起的情感反应:“当时大概有若干人痛惜,若干人快意,若干人没有什么意见,若干人当作酒后茶余的谈助的罢。接着便将被人们忘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409页。)
更令人深思的是民众对革命先驱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的冷漠和忘却。据1928年4月6日的《申报》说:“南京市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指中山陵——引注)行将工竣,石匠有摄收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市民以讹传讹,自相惊扰,因而家家幼童,左肩各悬红布一方,上书歌诀四句,借避危险。”其中有一种歌诀写道:“你造中山墓,与我相何干?一叫魂不去,再叫自承当。”这寥寥20字,将民众对于先驱者孙中山的冷漠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鲁迅发表评论说,这几句歌诀“竟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注:《鲁迅全集》第4卷第103页。)
鲁迅作品描写坟墓意象最为精心的是小说《药》:
“……这坟是草根还没有全合,露出一块一块的黄土,煞是难看。再往上仔细看时,却不觉也吃一惊;——分明有一圈红白的花,围着那尖圆的坟顶。……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
笼罩在这坟地四周的是一种沦肌浃髓的孤寂,即使鲁迅给坟顶上添加了一个红白相间的花圈,也遮盖不住夏瑜这位先驱者死后的孤独落寞。总之,荒凉萧瑟的坟墓像在鲁迅笔下成了先驱者死后被人忘却命运的象征符号。在世界文学史上,像鲁迅这样反复地描写坟墓,并把坟墓写得如此具有历史感兴趣和文化意味的作家恐怕是不多见的。
如同鲁迅经常与坟墓而我们不能说他是“骸骨的迷恋者”那样,鲁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时也去凭吊古迹,这并不表明他一味在历史情境中流连忘返。事实上,正是现实中的人和事促使他驻足于历史古迹之间。1926年9月,鲁迅从北京来到厦门大学任教,厦门山美水美,但并不怎么能使他感动,吸引他的是离他住所不远的一道城墙,这道城墙据说是明末清初的郑成功建造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丰功伟业令鲁迅景仰不已,但他也发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他告诉许广平说:“然而郑成功的城却很寂寞,听说城脚的沙,还被人盗运去卖给对面鼓浪屿的谁,快要危及城基了。”(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369页。)看得出来,民众已对郑成功的城墙十分地无动于衷,先驱者的伟业不仅被遗忘,而且遭受着破坏,鲁迅内心的悲痛在短短几行文字中隐隐透露出来。
鲁迅对现实生活中的牺牲者被遗忘现象同样十分关注。1922年10月,北京大学部分学生反抗校方征收讲义费而发生风潮。该校教授评议会议决开除预科法文班学生冯省三以示惩戒。其实,冯省三并非学潮的发动者,他只是学潮暴发后才参加的。鲁迅为冯省三的遭遇而抱不平,并联想到了社会运动中常见的牺牲者(替罪羊)的共同命运,他说:“这事很奇特,一回风潮的起灭,竟只关于一个人。倘使诚然如此,则一个人的魂力何其太大,而许多人的魂力又何其太无呢。现在讲义费已经取消,学生是得胜了,然而并没有听得有谁为那做了这次的牺牲者祝福。”(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407页。)
鲁迅还想起了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被民众所遗忘的先驱者。他以英国和法国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的拿破仑和隋那(今译为琴耶)为例,来说明人类历史上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即:一个人若想要得到后人的称赞,最好能够杀人如麻。拿破仑造成了那么多人的不幸,却被世人称作英雄;而隋那创造了牛痘接种方法,在全世界不知救了多少孩子的命,鲁迅反问道:“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杀人者在毁灭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鲁迅警告道:“这看法倘不改变,我想,世界还是要毁灭,人们也还要吃苦的。”(注:《鲁迅全集》第6卷第142页。)
3.“牺牲”的被鉴赏
人既有怜悯、同情受难者的情感指向,也有围观、鉴赏他人的不幸的丑陋的一面。据鲁迅观察,“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他推想:“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从这一幕日常生活场景中,鲁迅看见了中国国民性的一个侧面:“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注:《鲁迅全集》第1卷第163页。)
对“戏剧看客”的艺术表现,对民众鉴赏受难者所表现出的冷漠的批判,构成了鲁迅文学创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鲁迅在《孔乙己》、《祝福》等小说中描写了民众对不幸者孔乙己和祥林嫂的围观、嘲笑;《示众》一篇则通篇表现20年代北京城大街上市民鉴赏被示众者以及“看客”之间的互相鉴赏。《阿Q正传》结尾写到了阿Q被押赴刑场途中万人空巷的示众场面,面对着一群比饿狼还凶狠的看客,阿Q这位连杀头都不怕的人(他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也吓得魂飞魄散;尤其是那一双双能撕碎人的灵魂的眼睛更是彻底地暴露民众残忍无比的本性。难怪鲁迅在《随感录 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中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
当然,阿Q、孔乙己、祥林嫂他们只是一些平民百姓,并不是本专题讨论对象——先驱者。但民众对先驱者的受害与普通百姓的受害同样采取冷漠而又兴奋的鉴赏态度,这是令鲁迅非常痛心的。
鲁迅的散文诗《复仇》(其二)展现的是先觉者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悲剧。据《圣经》记载:耶稣受上帝的指令来拯救以色列人出离苦海,但大多数以色列人并不相信他。耶稣被捕后,在以色列人的要求下,罗马统治者决定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在通往刑场的路上,过路的以色列人不仅没有为耶稣的死感到悲痛,相反却冷酷地嘲笑和鉴赏着他们的救世主的死。据《马可福音》载:“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咳,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罢。”(注:参见《鲁迅全集》第2卷第176页注释⑤。)耶稣死时受民众恶意地鉴赏的一幕令鲁迅终生难忘,它在鲁迅作品中至少出现过5次(《暴君的臣民》、《寸铁》、《复仇》(其二)、《“意志之外”》、《〈小彼得〉译本序》)。
鲁迅在《复仇》(其二)中以悲愤的文字表现耶稣的死和以色列人对他的死的鉴赏:“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怜的人们呵,使他痛得柔和。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们自己钉杀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咒诅的人们呵,这使他痛得舒服。……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讥诮他。……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咒诅的。……”
鲁迅在小说《药》中以更隐晦的笔法写了先驱者夏瑜的死,以及牺牲时民众围观、鉴赏的情景:
老栓又吃一惊,睁眼看时,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一个还回头看他,样子不甚分明,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
……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
这就是鲁迅笔下愚昧、冷酷的民众。他们像赶集那样热热闹闹地去看杀人,他们是那样专注、那样兴奋地看着一位要救他们脱离受压迫境遇的革命者被处决,而眼中流露着凶残的神色。鲁迅还写到华老栓茶馆中茶客们鉴赏夏瑜在狱中被毒打的情景:刽子手康大叔讲述着夏瑜在监牢中鼓动牢头造反的故事,这令“二十多岁的人”很气愤;当讲到夏瑜遭了牢头红眼睛阿义毒打时,“驼背五少爷”很气愤;最后讲到夏瑜对毒打他的牢头说“可怜可怜”时(注意,耶稣被害时也说以色列人“可怜”),“花白胡子”、“二十多岁的人”、“驼背五少爷”接二连三大叫夏瑜是“疯了”。这就是先驱者的悲哀:他们的“造反理论”根本难以被当惯了奴隶的民众所接受,他们死后还落下“疯子”的恶名;而他们的死的价值不过是给茶馆中的闲人增加一点谈资罢了。
夏瑜死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清朝的黑暗统治时期,民众的愚昧、落后是情理中的事。令人震惊的是,到了民国已经成立17年的1928年,我们的民众仍然对砍头保持着那样浓厚的兴趣,依然是那样兴奋而冷漠地鉴赏着革命者的被杀。鲁迅的杂文《铲共大观》转引了1928年4月6日《申报》上的《长沙通讯》,它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全城扰攘,铲共空气,为之骤张;直至晚间,观者始不似日间之拥挤。”鲁迅看完这篇报道湖南长沙处决共产党人的文章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和耳闻了好几次了。”时代在变换着,而中国民众一如既往地像那闻到血腥气就聚扰过来的恶狼一样,兴高采烈而心如铁石地鉴赏着志士被砍头。鲁迅为志士之死的不能唤醒民众而深感悲哀!
4.先觉者、改革者的受迫害
先觉者、改革者与旧势力和权力集团抗争,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其目的是为了唤醒和救助生活在被奴役状态中的民众。照常理来说,群众应该理解和配合先觉者、改革者的行动才是;然而,事实却常常是群众不仅对先觉者的事业无动于衷、麻木地鉴赏先觉者走上牺牲的祭坛,而且很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到统治者迫害先觉者和改革者的行列中去,这才是真正的悲剧之所在。
鲁迅对民众参与迫害先觉者、改革者的悲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供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457页。)外国文化史上,可举耶稣来说明问题。据《圣经》载:耶稣被捕送到罗马帝国驻犹太总督彼拉多那里时,彼拉多觉得耶稣并无大罪,想释放他,但遭到犹太祭司长、文士、长老和民众的反对,彼拉多只好判耶稣死刑。(注:参见《鲁迅全集》第1卷第367页注释④。)鲁迅在《随感录》第六十五中提到这件事时指出:“……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怎样呢?
鲁迅在《寸铁》一文中指出:“先觉的人,历来总被阴险的小人昏庸的群众迫压排挤倾陷放逐杀戮。中国又格外凶。”鲁迅说,中国人对于那些“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法:将他压下去,或者将他捧起来”;他进一步解释说:“压下去就用旧习惯和旧道德,或者凭借官力,所以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140页。)而以“捧”的方法将先觉者谋害的手段则更毒辣阴险得多。鲁迅说“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背了“战士”的招牌,被人们“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446页。)
鲁迅在文章中多次提到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革命者绥惠略夫,这是一位工人出身,信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革命家。鲁迅说“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20页。)
1922年5月,鲁迅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他回忆译介这部旧俄时代的小说动机时曾说过:“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点记不真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到1926年8月,鲁迅重新翻阅这部作品时发现“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356-357页。)后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一再证明,鲁迅的关于改革者在将来也要吃苦、受迫害的预见是多么的准确;而鲁迅这类预言越是具有现实性、准确性,便越能显现中国社会改革的悲剧色彩。
在鲁迅本人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中,先觉者、改革者受迫害也是较常见的主题。《药》、《孤独者》等小说都写到强大的社会势力对孤独的改革者的迫害。而《狂人日记》的主题虽然有多种解法,但也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篇记录整体的社会势力迫害单独的先觉者“狂人”事件的作品。据“狂人”自己反省,他20多年前曾经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使得古久先生很不高兴”,并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对他的仇视。据“狂人”推测:赵贵翁虽然不认识古久先生,但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并约定路人同他作对。看得出来,“狂人”年轻时代曾经是一名大胆地向陈腐的封建文化发出挑战的先觉者,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老百姓仍十分愚昧落后,虽然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但却不觉悟,“狂人”成了一名孤军奋战的战士,独自面对统治者和庸众的围攻和迫害。迫害“狂人”的社会势力有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懦,狐狸的狡猾”。他们不肯也不敢直接杀死“狂人”,因为这样做“怕有祸祟”;据“狂人”观察和分析,他们互相联络,布下了罗网,想逼他自戕,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这样,他们害死了“狂人”,了偿了心愿,又没有杀人的罪名,自然都会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这就是鲁迅曾在《坟·题记》中提到过的、明代木皮散人(贾凫西)所说的“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的杀人方法。在现实中,改革者被“软刀子”害死的恐怕不比直接被害死的少见。
鲁迅的散文诗《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值得注意,作品把社会上的人分为四类,即:奴才、主人、聪明人和傻子。作品中的奴才过着极端恶劣的物质生活,有一日,他遇见了聪明人,便开始向他诉说自己的痛苦。聪明人同情他的遭遇,并安慰他说:“我想,你总会好起来”。听了这番安慰,奴才心理感到舒坦了许多。但没过几天,奴才又不平起来,他碰到傻子,开始诉说自己生活的如何连猪狗都不如,自己住的一间小破屋如何又阴、又湿,满是臭虫,而且秽气冲鼻子,四周又没有一个窗子。傻子让奴才带他去那间小破屋,刚到屋外动手就砸泥墙,他想给奴才开一个窗子。不料,奴才不仅没有协助他干活,反而大喊大叫起来:“来人呀!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他一边嚷着,一边在地上团团打滚。接着,一群奴才都跑了出来,齐心协力把傻子赶走了。最后,主人夸了奴才一句“你不错”,于是这奴才就非常满足了,以为今后一切都会好起来。这篇作品其实颇有象征意味,如果把中国社会比作那间小破屋,那么傻子在泥墙上开窗洞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先觉者要给长期生活在黑暗屋子中的民众(奴才)进行启蒙(带来光亮)的尝试。然而,已经做惯了奴才的人,并不想使自己的生活有什么改观,“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所以傻子的启蒙和改革工作注定是要失败的,在一群奴才(民众)的合力围攻下,傻子只好逃之夭夭。
傻子的遭遇集中体现了一切先觉者、改革者的悲剧命运:他们为唤醒和救助民众,作了种种的努力和牺牲,最后却落了个为民众所不容,所迫害的下场。
5.享用“牺牲”(先驱者的被“吃”)
民众不仅鉴赏着先驱者的牺牲,不仅参与迫害先驱者,而且还从精神和肉体上“吃”掉先驱者,这才是古往今来一切先觉者和革命者最深层的悲剧。
鲁迅作品中多次写到了先驱者牺牲后,鲜血和心肝被吃的事件。小说《药》里的革命者夏瑜死后,刽子手康大叔用他的血做成人血馒头,卖给平民华老栓。鲁迅写老栓得了人血馒头后的心理活动值得注意:“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我们再看小说写华小栓及其父母在小栓吃烤熟了的人血馒头时的情状:“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革命志士夏瑜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下,而与他生活在一个城市的乡亲华老栓夫妇却迷信邪说,用开茶馆辛辛苦苦攒起来的一包洋钱,买了用夏瑜的血制成的人血馒头,为生了痨病的儿子小栓治病,但最终小栓还是命丧黄泉,先烈的血不仅白流了,而且白吃了,这是双重的悲哀!!
鲁迅在《狂人日记》及散文《范爱农》里都写到了清末革命者徐锡麟心肝被吃的事。徐锡麟是革命组织光复会的主要成员,1907年7月6日,他以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身份为掩护,乘学堂举办毕业庆典之机刺死了安徽巡抚恩铭,后被捕惨遭杀害,他的心肝被恩铭的亲兵炒食。
先驱者肉体被吃毕竟不多见,他们更多的是在精神上被民众所“吃”和所利用,鲁迅把这种现象称作“散胙”。“胙”指祭祀所用的肉;“散胙”原指旧时祭祀仪式完成后,发给参加者祭祀用过的肉;鲁迅把“散胙”引申为先驱者牺牲后,民众从精神、心理上对他们的利用。鲁迅在《热风·即小见大》和《两地书》(二十二)中都提到北大讲义风潮结束后,冯省三成了替罪羊的事件。他在前一篇杂文结尾写道:“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而他在后一篇文章中再次表示了类似的看法:“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之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鲁迅多次提到“散胙”的事,可见他心里盘缠着一个多么深的悲剧情结。鲁迅本人在帮助青年人的时候也曾有过这种精神上被“吃”的体验,他曾对许广平说:高长虹等青年人“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注:《鲁迅全集》第11卷第212页。)
鲁迅在他所景仰的那些反抗沙皇暴政的俄国志士牺牲后的遭遇中同样看出了“散胙”现象,他说:“以前的俄国的英雄们,实在以种种方式用了他们的血,使同志感奋,使好心肠人堕泪,使刽子手有功,使闲汉得消遣。总是有益于人们,尤其是有益于暴君,酷吏,闲人们的时候多;餍足他们的凶心,供给他们的谈助。……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这倒实在是很可诧异的”(注:《鲁迅全集》第7卷第304-305页。)。
的确如此,先烈之死除了引起为数极少的亲人、友朋的悲伤外,还能引起数量也不多的敌人的快意,而更多的人既非亲朋,亦非敌人,他们对烈士的死基本上是无动于衷的,充其量只是获得更多的餐桌旁闲聊的素材罢了,烈士的血恰好可以给这些过着灰色、平庸生活的闲人着一层红色,增加一点刺激,充当他们无聊人生的调味品。先烈们的精神还是被闲人、庸众们所利用了。鲁迅在“三一八”惨案不久写的《记念刘和珍君》中悲愤地写道:“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
鲁迅还注意到了另外一种情形:某些先驱者牺牲或逝世后,社会各界开展了隆重的纪念活动,这当然可以让九泉之下的先驱者感到一些安慰;然而,鲁迅那双锐利的眼睛透过各种纪念活动表面上的庄重和热烈,看见了主持和参加纪念活动者内心的心思——他们有些人是借纪念活动而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社会声望;有些文人把纪念会当作了他们比赛写挽联和诗文水平的场合;而另一些人则因为活得太寂寞了,他们像赶集一样来赶纪念会的热闹来了。总之,先驱者的纪念会倒成了某些人可资利用的机会,而阐扬先烈精神遗产、继承他们遗志的纪念宗旨早被抛在一边。
鲁迅谈到了他在北京所见的孙中山先生纪念日的情景:“在学校里,晚上来看演剧的特别多,连凳子也踏破了几条,非常热闹。用这例子来推断,那么,黄花节也一定该是极其热闹的罢。”接着鲁迅带着嘲讽的语调写道:“我想,恋爱成功的时候,一个爱人死掉了,只能给生存的那一个以悲哀。然而革命成功的时候,革命家死掉了,却能每年给生存的大家以热闹,甚而至于欢欣鼓舞。惟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注:《鲁迅全集》第3卷第410页。)鲁迅在他的杂文《论睁了眼看》中提到了沪汉烈士追悼会场出现的丑剧: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6月11日汉口群众的反帝斗争遭镇压,6月25日,北京各界群众数十万人举行示威,并在天安门召开沪汉烈士追悼会,在这么庄严的场合,一些无聊的民众竟然在两丈四尺高的烈士灵位下互相谩骂、大打出手、驰聘威风,鲁迅挖苦他们是“借死人获得最上的光荣了”。
鲁迅在杂文《忽然想到(十一)》里再次提到这次追悼会,他从这次纪念活动中看出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即:“即使上海和汉口的牺牲者的姓名早已忘得干干净净,诗文却往往更久地存在,或者还要感动别人,启发后人”,“这倒是文学家的用处。血的牺牲者倘要讲用处,或者还不如做文学家。”
1927年4月,鲁迅在黄埔军校作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说时,仍以烈士追悼会上的诗文为例,批评文学家如何获得虚名的,他说:“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通过烈士追悼会上文人的表演,鲁迅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文人的寄生特征。
鲁迅晚年所写的《病后杂谈》以更锐利的文字揭穿了文人是如何借追悼先烈而自利的,他指出:追悼会“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为了造语惊人,对仗工稳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
在鲁迅笔下,先驱者被利用和他们从精神上被“吃”的悲剧命运,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尤其是他对文人寄生性的看法堪称是“诛心之论”。
6.总结:先驱者生前、死后的不同命运模式
从古往今来的社会史、文化史来看,所有的先觉者、改革者的命运模式不外乎四种,即:(1)生前有名,死后仍有名(如牛顿,生前总结发现了三大定律,享受极高的声誉,85岁寿终正寝,直至今日还被看作自然科学领域伟大的变革者;又如中国近代的蔡元培);(2)生前无名,死后仍无名(这种人或许不少,但其事迹不大可能留传下来,鲁迅认为明末某些抗清的烈士就是这类人,鲁迅在《半夏小集》中指出:明朝末年有三类人值得注意,一类是汉奸,他们活得最舒服;一类是“逸民”,他们痛骂汉奸,活得最清高,被世人尊敬,但后来他们去世后,儿子不妨去应试了,而且各有一个好父亲;第三类人是“默默抗战的烈士,却很少能有一个遗孤”,而且连姓名也没能留下。)这两种先驱者的命运模式比较不多见,在此不作展开。(3)生前有名,死后受曲解、受攻击;(4)生前受尽磨难,死后声名显赫。这后两种模式才是最常见也是最有悲剧意味的先驱者命运模式,可略作展开。
首先看“生前有名,死后受曲解和攻击”的那类先驱者。这类先驱者一生在社会变革或文化科技等领域历尽坎坷而做出巨大的贡献;然而在他们死后,各种社会集团、各种政治势力或各类人从各自的需要出发,曲解先驱者的精神遗产,甚至对他们横加苛责。鲁迅认为,孙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的许多先烈就是这类人,他们死后“反受奴才们讥笑糟蹋”。(注:《鲁迅全集》第7卷第264页。)鲁迅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就提到了那些对孙中山“说风凉话”的论客。1925年3月12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奔波了一生的孙中山在北京病逝,4月2日北京《晨报》就发表了一篇署名“赤心”的《中山…》一文,说什么“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为‘中山洲’,……最干脆,最切当。”而梁启超也在3月13日的《晨报》上答记者问,攻击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所以“无从判断他的真价值”。鲁迅把类似的议论说成是苍蝇的嗡嗡。
尤其令鲁迅愤慨的是国民党人对邹容的诬蔑。1929年6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西湖设立博览会,内设革命纪念馆,馆内设有“落伍者丑史”,在其目录中,竟列有“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所谓“事实”。邹容在清末做《革命军》一书,鼓吹革命,1905年死在监狱里,当时才20岁。鲁迅抨击了国民党人歪曲史实、诬蔑先烈的行径。(注:《鲁迅全集》第4卷第129页。)至于章太炎先生,他虽没有为革命战死,但他在创建和维护中华民国的事业中所做的贡献和所受的磨难是少有人可与之相比的,在思想学术上,他也成为卓然大家。1936年他去世时,上海举办追悼会,“赴会者竟然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注:《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页。)这实是令人悲哀之事;至于他死后被骂作“章疯子”,则表明了许多先驱者的共同命运:由于他们走在时代太前头了,不能为世人所理解,故常被看作“疯子”。
其次再看“生前受尽磨难,死后声名显赫”的那类先驱者。这是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先驱者最为普遍的命运模式。生前,他们的理想往往未能实现,他们的事业常常不能顺利展开,甚至遭受着物质生活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迫害与折磨;死后,他们的学说被证明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他们的事业被绝大多数人认同,于是,“伟人”、“先烈”、“文豪”、“先贤”等等名号纷纷落在他们的姓氏前。在中外历史上,这类先驱者不胜枚举,从孔子、屈原、司马迁到王安石、李贽、陈独秀;从苏格拉底、耶稣、哥白尼、伽利略到卢梭、狄德罗、达尔文,中西社会史、文化史上众多的先驱者的遭遇正是不断地重现着这一悲剧性的命运主题。鲁迅在杂文《无花的蔷薇》中总结道:“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时,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据说如果是孔丘、释迦牟尼、耶稣还活着,他们的教徒必定会迫害他们。鲁迅感慨道:“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
其实,鲁迅本人生前的备尝艰辛与迫害,死后的被捧入“云端”,正是对这一悲剧性文化命题的最好注释。
1997年岁末于北大燕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