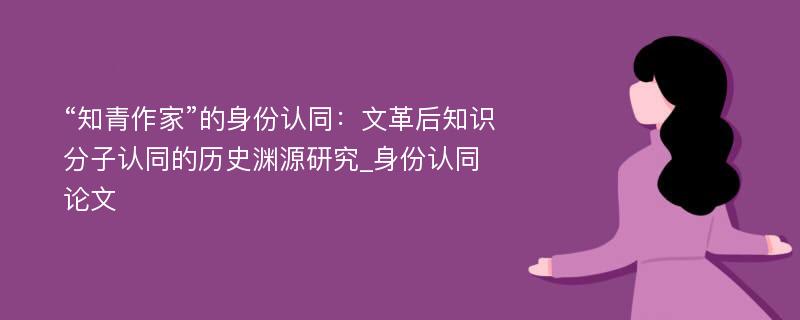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知青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文革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1)05-0119-07
“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新时期”的开始,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型时期,对于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来说,这无疑也是极为重要的历史时刻,在向新的现代性目标艰难挺进的历史征途中,作为在当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文学知识分子,当时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主要是以他们的话语活动参与其中的,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及“十七年”时期的“历史讲述”所包含的话语立场、历史及未来想象,以及所突显的人文精神及价值吁求,对于当时及以后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新的现代性文化空间的建构,均都有着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特点。任何话语都有其言说主体,而话语主体的历史处境及身份认同,必然又会影响或制约其话语活动,因此,研究“伤痕”、“反思”小说这一“文革”后最早兴起的文学思潮,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便是研究作为话语主体的“伤痕”、“反思”小说作家(特别是其中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在“新时期”之初(1976.10-1984.12)的身份认同,研究这些文学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和意识形态背景之中身份认同的独特性与必然性,以及这些认同对其话语活动的影响,并对这些影响作出一定的历史评估。
这里,我们将主要根据H·埃里克森(Erik·H·Erikson)(1902-1994)的认同(Identity,亦译为“同一性”)理论,深入研究“知青作家”对于他们的历史身份——“知青”——的强烈认同。
“文化大革命”以后,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对于“文革”时期所建立的身份结构体系进行了被称为是“拨乱反正”的重新调整,“文革”时期“革命者”的政治光荣已然丧失,他们在“文革”中的所谓“革命行动”,变成了须待忏悔的罪恶与迷误,所以,他们中也极少有人还以当年的身份自炫于人,但是,“新时期”之初“伤痕”、“反思”小说作家的身份认同,却有一个相当有趣而且颇有争议的现象,即其中的许多“知青作家”往往通过对他们“文革”时期“知青”身份的浪漫“重申”,来强调自己的“知青”认同。
明显的怀旧色彩,是“知青作家”对于已经属于历史了的“知青”身份的认同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除此之外,我们更应注意的,是这种认同所体现出来的为“知青”身份重新正名的色彩。鉴于“文革”时期便已产生、“文革”以后更加盛行的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对于“知青”一代的惋惜、误解以至于指责,这种认同往往伴有鲜明的“无悔”心态、纪念色彩和对于他们所特有的青春时代进行价值重申的意图。如叶辛就曾经说过:“那个时候,社会上只要一提起知识青年,不是唉声叹气,就是闭目摇头,仿佛知识青年们一无是处。……其实呢,他们并没到乡下去过一天,也不知知识青年们究竟怎样在生活,往往根据一些夸张了的传说在下判断。实在地说,知识青年在乡村的生活,是复杂而又丰富、艰苦而又充满了向往色彩的。知识青年,这个当年我们用汗水和眼泪、期待和希冀、憧憬和追求充实起来的字眼,饱含着多少更加深沉的意义阿!”,“我是从那条路上走过来的,我的青春、我的追求、我的事业,甚至我的爱情,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1],“这段岁月虽已过去,却值得记忆”[2]。孔捷生《南方的岸》的基本主题,就是对“知青”身份的重新认同,他在谈到这部作品时指出,他的小说是“忠实于我们许多老知青的感情的”,“怎能因为我们的些微贡献远抵不上十年浩劫的空前损失,便觉得毫无价值呢?”[3]。“知青作家”对于“知青”身份的浪漫“重申”和坚定认同,以张承志最具影响:“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思索、痛苦、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感动着、甚至温暖着自己的东西”[4](p.112)。在这里,“知青作家”不约而同地所表现出来的代群意识以及“知青”代群的“代言人”身份相当鲜明,对于这一特点,我们姑且暂置不论。
“文化大革命”时期,“知识青年”基本上都有着一个“光荣”的“革命”前身——“红卫兵”,“红卫兵——知青”,正是“知青”一代在“文革”之中确凿无疑的历史形象。但是,从“知青作家”在“新时期”的身份认同来看,“革命”的“红卫兵”或者“红卫兵”的“革命”的身份形象,却遭到了他们的“剥离”,“革命”遭到了不同形式的“否弃”。一种情况是,在表达自己的“知青”认同时,绝口不提自己作为“红卫兵”的过去,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对其作为“红卫兵”的过去的“忘却”或者“回避”,如前面所引叶辛和孔捷生等人的言论;第二种情况是,虽然能够正视自己“红卫兵”的历史身份,但是仍然将这种历史身份中的“革命”成分充分“剥离”,与前面一种相比,由于这一倾向“稍加”正视历史的真实,所以,颇有认真辨析的必要。
梁晓声曾经明确指出“知识青年”真正的发生史、成长史,特别是形象而又明确地承认了他们身上难以去除的“红卫兵”(“革命”)的“胎记”,但在同时,他又极力清除了这一“胎记”中的“革命”内容:
“文革”是知青的“受孕”时辰。
“广阔天地”是孕育知青的“子宫”。
“红卫兵”是知青的“胎记”。
这胎记曾使知青们被上几代人和下几代人中的相当一部分视为共和国母亲教育彻底失败的“逆子”。又好比《水浒传》中林冲们杨志们被发配前烙在脸颊上的“火印”。
那是秩序社会的“反叛逆子们”永远抹不去的标志。
在知青“上山下乡”30周年之际,当我们整代人回忆我们差不多共同的经历时,我们几乎一致地,心照不宣地,讳莫如深地避开这一点——32年前,在我们还不是知青的两年前,我们很多人的另一种经历另一种身份是红卫兵。
而红卫兵曾给许许多多家庭许许多多中国人造成终身难忘的伤痛。
它不仅声名狼藉并且是“文革”暴力的同义词。
的确,它是我们的“胎记”,是我们脸上的“火印。”
很显然,对于梁晓声以及整个“知青”一代来说,这一“胎记”都是他们所不愿触及的、极为深巨的内在隐痛。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一“胎记”代表着深深的历史罪衍,承认了它,便意味着要有对此罪衍的承担以及新的历史时期所要求的忏悔:
中国当代的知青们,由于经历了“文革”,由于在“文革”中十之八九都曾是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当年的恶劣行径和后来的声名狼藉,不分男女,知青们便似乎都与“十年浩劫”难逃干系,便似乎都应承担几分历史罪责了。
但是,由于并不是每一位红卫兵都曾有过过激的“革命行动”,所以,真正应该忏悔的,只是那些凶恶的“极少数”:
我认为,当年很凶恶的红卫兵,只是极少数。大多数红卫兵,只不过是身不由已地被“文革”所卷挟的青少年男女。他们和她们,既不但自己没打过人,没凌辱过人,没抄过别人的家,而且即使在当年,对于此类“革命行动”也是暗存怀疑的。起码是暗存困惑。
正是基于上面的认识,所以梁晓声认为,作为虽有“胎记”但却没有“凶恶的”“革命行动”的大多数“知青”,都“可以毫不躲闪地、坦率地、心中无愧地”说:
我们大多数的本性一点儿也不凶恶。……我们这一代无法抗拒当年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抗拒的事。我们也不可能代替全中国人忏悔。“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我们的命运,我们从未将此命运当成“报应”承受过
对梁晓声而言,否认了大多数“红卫兵”都曾有过过激的“革命行动”,便意味着消除了“红卫兵”的身份之中曾经有过的“革命”内容,进而,“知青”身上所具有的“胎记”(即梁氏自己所说的“红卫兵”),也便丧失了原来所包含的“革命”色彩,其所强烈认同的“知青”身份,似乎也就成了一种十分纯粹、没有丝毫的“革命性”的历史身份。除了梁晓声,另外一些“知青作家”如张承志和张抗抗,也曾经以这样的思路来突出自己对于“知青”甚至是“红卫兵”身份的重新认同,而与此相关的“青春无悔”或“我不忏悔”的心态,却在更多的“知青作家”那里有所体现[6]。
梁晓声们的观点,无疑存在着一个相当明显的“逻辑问题”。这些年来,思想文化界所着力要求的对于“文革”的“忏悔”,并不仅限于忏悔者在“文革”之中所犯的实际罪行如“打、砸、抢”等所谓的“革命行动”,它的更加广泛的意义还在于重新检讨个体生命的历史承担,这是在巨大的社会灾难之后包括“施暴者”和“受害者”在内都应具有的思想姿态,所不同的是,那些“施暴者”们,还应该承受与其实际罪行相应的“政治的”或“法律的”追究,否则,作为“受虐者”的巴金老人的忏悔便失去了意义。以此来看,梁晓声们的“逻辑问题”,显然是把思想史和精神史的问题“置换”为“政法问题”,并且以此来遮盖或取消历史反思特别是精神忏悔的重大意义。埃里克森曾经指出,在专制性的社会中,青少年们对于专制性的意识形态为他们规定的未来身份的偏执认同,必然会导致“全国性的青少年犯罪”[7](p.85)。显然,重新检讨具有“全国性的青少年犯罪”特点的红卫兵运动,除了要对当时的所谓“革命行动”进行“忏悔”之外,还应该对当时红卫兵们的身份认同以及当时的专制性意识形态(即当时的所谓“革命”本身)进行深入反思,在此意义上,当年对“红卫兵”这一“革命”身份曾经有着强烈认同的“知青作家”,似不应该若无其事地以“我不忏悔”的姿态而将问题一推了之,只是单纯地强调自己的“知青”身份,而不去反思他们在当年的“红卫兵”认同。然而,这些“知青作家”在“新时期”对于其“知青”身份以“辩护”与“重申”的方式所表现的强烈认同,却显然是将“革命”排除在外的,他们所强调的,恰恰只是纯粹的“知青”身份,从而遮蔽了他们曾经有过的对于“红卫兵”的身份认同。探讨这一特点的形成原因,主要应从“知青”一代身份认同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
至“新时期”之初,“知青”一代的身份认同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基本阶段:
第一阶段,是截止他们学生时代的“青少年时期”。“知青”一代“从诞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某种理想,他们也真诚地信奉这种理想”[8](p.141),他们的使命和幸福就在于实现前辈革命者已经现成描画好了的“革命理想”,对于这种理想,他们无须也绝不应该有着丝毫的补充、质疑以至于重构的企图,否则,那便是不可饶恕的背叛与犯罪。确实的,主要是由于当时意识形态的灌输,这一时期的“知青”一代往往都有强烈的“革命”认同,在他们的心目中,“革命”身份有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张抗抗曾经说过,在整个中小学时代,她“最喜欢的是《红岩》、《欧阳海之歌》和《青春之歌》”,“也喜欢《青年近卫军》、《卓亚和苏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勇敢》,这些都是我早期读的书。我自己认为,这些革命英雄主义的作品对我世界观的奠定和文艺观的形成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我在中学三年中所接受的,是老师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灌入的种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似懂非懂的政治概念”[9]。实际上,张抗抗的自白已经充分显示出,“知青”一代的世界观虽然已经受到“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概念”的“积极的影响”,但对这些“概念”,他们却又是不甚了了和“似懂非懂”的,当时的所谓“革命”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形成埃里克森所说的“坚实的内在同一性”,即“坚定的革命身份”[10](p.254)。埃里克森曾经屡次强调这种“坚实的内在同一性”对于形成坚定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性,他说:“只有一种坚实的内在同一性才标志着青年过程的结束,而且也才是进一步成熟的真正条件”[7](p.75)。应该承认,这时的“知青”一代已经初步形成了对于“革命”的身份认同,但对他们而言,这种认同“对后期生命还没有形成一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式”[7](p.79),还很不够坚定,所以,这种状况便很必然地导致了他们在下一个阶段,即走出校门、踏上社会,也即是“上山下乡”之后“革命”认同的迅速破灭。
在第二个阶段,开始时的“上山下乡”、后来的“林彪事件”和在穷乡僻壤的实际经历,都对“知青”们早先就不坚实的“革命”认同作了严重打击,由此便产生了极为普遍的“革命”的“幻灭”情绪:“68年秋,我尚未满16岁,便到农村去插队,……我在那里晒蜕了几层皮,担断了两条扁担。但随着壁上蛛网的增多,我感到了幻灭”[3]。“到了偏僻的山寨生活了一段日子,我才知道我们插队的寨子很穷。……面对这一现实,五光十色的理想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11],这批所谓的“革命者”们,正因为有了这一个时期的“革命的幻灭”,才导致他们在下一个时期的身份认同具体有了新的特点。
第三个阶段指的是“新时期”之初。“新时期”之初的中国,显然是一个认同重组的时代,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要按照“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所建构的身份结构体系,对其“文革”时期的历史身份进行重新评价,进而建构新的身份形象。“知青”的上一个代群即“右派作家”在新的身份形象中融入了很多“革命”内容[11],而曾因发现受骗而产生“革命的幻灭”的“知青”一代,却绝不会再在自己新的身份形象中融入丝毫的“革命”因素,他们已经“从虔信走向了不信”,形成了“对种种伪理想的拒斥”,“不再盲目地相信什么”[8](p.141)。他们在青少年时期以及红卫兵时代“革命理想主义”中的“革命”成分,被他们彻底地“剥离”,所剩下的,唯有单纯而热烈的“理想主义”,这正如一位属于“知青一代”的学者在谈到其身份认同及精神变迁史时所曾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噩梦,我在那些年月里表演得很充分,过分的充分。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的行动全然受‘革命理想’的支配。……不管我在‘文革’中做过多少令自己悔恨的事,不管我遭到多少人的误解、攻击、咒骂,我从未怀疑过,我的一切行动出于要当‘革命者’这一动机,我想向人表明,我可以做一个不比别人差的‘革命者’。和许多人一样,忘我地投身于‘革命斗争’,换来的却是欺骗和愚弄,我最终不得不抛弃‘革命理想’。不过,被抛弃的很可能只是理想的外围部分,它们由华丽而空洞的词藻构成。如果说理想的核心是追求生命的意义,是使每个人享受同等社会权利的愿望,那么理想并未粉碎。就像流亡之后的亚瑟一样,我可以用嘲笑的口吻谈理想,但我深知,它仍是我内心最神圣的东西”[12](p.2-3)。“知青一代”的“革命理想主义”在“剥离”了“革命”成分之后所剩余的“理想主义”,往往只是一种浪漫的“精神品性”,“而不是意义话语”[8](p.133),因此也丧失了具体的意识形态内容。这样,“浪漫”地和“理想主义”地回访历史、构设民族与自我的未来,便成了“知青作家”及其文学作品最为主要的精神特点,其突出者,如梁晓声及其《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孔捷生及其《南方的岸》和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之初“知青作家”理想主义精神品性的形成,除了与这一代作家独有的身份认同历史有关之外,亦应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转型及意识形态的变化等方面寻找原因。在“新时期”之初,围绕着“潘晓来信”所集中暴露出来的“意义——信仰危机”成了青年一代极为普遍的精神现象,看破红尘、玩世不恭及庸庸碌碌、胸无大志的实利主义生存态度和市侩哲学,是他们突出的精神病状,然而,当时改革开放的历史情势已经初步显示出整个民族以及青年人自身必将具有着巨大而广阔的未来,因此,并不甘于真正的“一无所有”的“知青作家”们,便企图以自己的理想主义精神对此现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由于上述的未来空间已经被主流意识形态甚至整个民族认定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其中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关于未来的制度构想,也意味着这种制度下的个人应该具有一如既往的“革命化”生存,显然,这已无法解答曾经产生过“革命幻灭”的“知青”一代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而其中的“四个现代化”,主要是指“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它们全部仅仅关涉技术与物质层面,却与当时的青年人所迫切关心的“人生意义”全然无关。“知青作家”们不愿意继续认同已被他们“剥离”了的“革命化”身份,也无法具体地提出未来的人生图景,却又对不甚明朗的未来充满向往并且执着追求,这样,其仅仅是作为一种“精神品性”的理想主义便由此产生。对此,“知青作家”自身亦有极好的自白。如张抗抗在当时便认为:“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十年浩劫所遗留下来的种种后果,其中突出表现为青年一代自我否定与重新确立自我的思考、迷茫、彷徨的混乱状态”,他们“对于现实大量、深刻的发问,也苦于没有正确有力的思想武器而寻不到自己起步的路口。三中全会确立的我党的方针路线,为我国走向四化指引了一条宽广的大道,每个公民都充满了这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否每个人都能走上这条路,同时代的潮头一起前进,是否每个人都找到通往自己心灵的小径,显然是差异很大的”,这是所充分说明的,正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青年们的身份选择既很巨大而又极为有限的“限定”作用。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认识,张抗抗创作了散发着理想主义光辉的小说《北极光》。她说:“我写《北极光》,内心深处抱着一种美好的祝愿,愿青年们能在理想的召唤下,看到希望,加强自信力,从而由彷徨、犹豫、朦胧走向光明”[13]。但是,正因为作品以“北极光”作为象征来表现了仅仅作为“精神品性”的理想主义,所以,它才被一些批评家指责为“是非常虚飘的”,认为女主人公“是始终飘浮在对生活的所谓‘思索’中的”,她的理想和追求,脱离了“脚踏实地的青年人的具体的变革、矛盾和斗争,劳动和学习的艰辛和欢乐等等实际生活内容”,不具有充分的实践意义,因此,它便很自然地会“受到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是否意味着具有“革命”身份?——引者)的怀疑和冷淡”[14]。孔捷生在当时创作了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南方的岸》,“不少农友尖锐地指出”,小说“脱离现实!”,“结尾太浪漫、太理想化”。孔捷生也承认小说的结尾“也许它真的‘不现实’”,但是,他在关于小说的“创作谈”中,充分表现了对于“新时期”之初的青年人特别是其下一代青年丧失理想的精神状态的严重忧虑,并且指出:“只有一点可以断言:任何民族,她的青年一代缺了理想,缺了志气,便将要衰败灭亡。我真希望中国的青年变得更浪漫一些,与那种市侩式的‘现实’离得远一些,对前途热血多一些,而冷嘲少一些”。由于“几亿青年中各色人等俱全”,所以,“《南方的岸》便只好给愿意读的人去读了”,“改出一个大家都欣然同意的结尾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3]。易杰在最后虽然作出了似乎“现实”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与《北极光》里美丽而遥远的“北极光”一样,都不过是一种作为精神而存在的理想主义的召唤。
在剥离了“革命”、只是保留了强烈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精神品性”之后,“知青作家”对于“知青”身份的重新强调,需要作出恰当的历史评价。
“知青作家”对于“革命”身份的彻底“剥离”,意味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革命”认同的终结,在此意义上,他们的“知青”身份的前身即“红卫兵”,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代“革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将以此作为新的起点,去除此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对于“革命”身份的偏执认同,进而塑造知识分子自身独立的身份形象,与此相关,知识分子的话语实践也将不再会仅仅是对“革命”话语的简单复制,而是应该创造出独立的话语体系。在此意义上,“知青作家”理想主义的精神品性由于有着充满希望和面向未来的重要特点,也为具有独立性的身份形象的树立和话语体系的创造提供了足资依赖的精神前提和精神动力。这无疑是一个富有希望的起点,但在这一起点与上述目标之间,还有着大量的需要克服的问题,从“知青作家”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在“新时期”之初的当时,还是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知青作家”在对“革命”身份和“革命”话语进行“剥离”和“反叛”的同时,如何正视自身曾经具有的“革命历史”,并且避免因为对此“历史”的否认或回避而导致的、在进行历史反思时对于“革命”问题的“悬搁”,从而也避免因此而造成的反思深度的欠缺甚至虚妄?二、“知青作家”如何“正视”和“珍视”自己不同于前、后两代知识分子的独特的成长经历,并且通过对此经历的深入反思来重新思考历史?三、“知青作家”如何由其动人的理想主义的“精神品性”、通过艰苦深入的历史反思,逐步生成新的、属于知识分子的“意义话语”体系?
收稿日期:2000-12-25
标签:身份认同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历史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社会认同论文; 北极光论文; 红卫兵论文; 理想主义论文; 梁晓声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