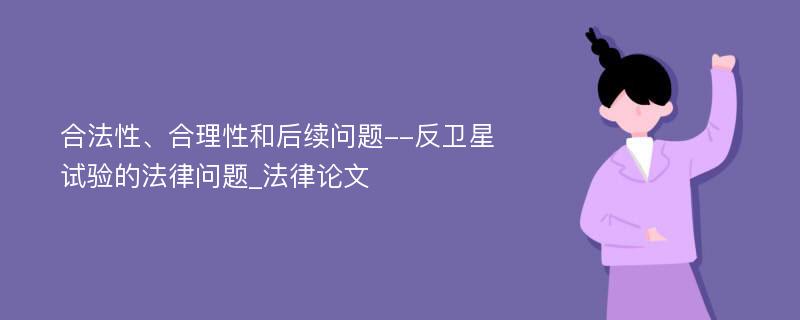
合法性、合理性与后续问题——反卫星实验的法律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合理性论文,法律问题论文,合法性论文,卫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9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204(2009)03-0046-06
2007年中国进行的反卫星实验已经过去了两年,但关于这一事件的影响和争论似乎并没有停息,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①美国在2008年又进行了一次反卫星实验,让人猜测是一次针锋相对的炫耀武力的行动,从而给前一个事件增加了更多的色彩。②此后,各方对这两起事件的解读更进一步折射出事件的复杂性。
的确,每一个国家所采取的行动都有其目的。但如果剔除对目的进行的各种猜测和鼓噪,仅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来看,无非是两起前后发生的合法事件。
法律规则在法律理论上区分为现行法(lexlata)和应有法(lex ferenda)。现行法是判定一个行为是否合法的依据;应有法是判定一个行为是否应该有进一步的更加合理的规则予以规范的依据。应有法针对的是现行法的漏洞或不妥之处,是可能出现在将来的“现行法”。一个严谨的法律学者,不会混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会站在应有法的立场用“合法”或者“非法”来描述一个行为的现实法律性质。
笔者将从国际法的角度探讨中国反卫星实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为将来进一步规范各国的空间行为、空间活动提出一些个人见解,以期有助于各方考虑问题。
一、反卫星实验的合法性
作为调整与规范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体系,国际法的作用一直引人注目。在外层空间领域,规范国家行为的无疑就是空间法了。稍有国际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国际法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即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所体现的规则是国家行为过程中应予遵守的。但是,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之间有些微差别:国际条约仅仅约束其缔约国,对于非缔约国无益无损;国际习惯则约束所有的国家,除非某国明确表示反对某一特定的国际习惯规则对该国的约束效力。
因此,一个国家行为是否合法,在国际法的层面上,主要是基于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进行判断。不违反现行的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的行为,就不是非法行为。
众所周知,国际空间法从20世纪50年代发轫,60年代-70年代迅速发展,到70年代末基本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涵盖了空间活动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这个体系是以联合国的空间法条约和有关原则为基础的。其中,具有法律效力的五个条约,分别是空间条约(1967)、责任公约(1968)、登记公约(1974)、营救协定(1972)和月球协定(1979)。此外,还有一些原则和宣言,但它们不具有法律拘束力。
以上条约规定了从事空间活动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涉及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从事空间活动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如何承担责任、空间物体如何登记、营救宇航员方面应当如何行动、在月球上的活动如何进行。从参加的基本情况看,这些条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很大。截止到2009年初,外空条约的缔约国达到100个,新增26个签署国;营救协定缔约国90个,新增24个签署国;责任空约缔约国87个,新增23个签署国;登记空约缔约国52个,新增4个签署国。换言之,基本上主要的空间活动国家都是这些条约的缔约国。月球协定的参加国家比较少,到目前为止仅有13个,新增4个签署国。③这些条约是各国从事空间活动的准则。公约规定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情况,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存在习惯法的证据,从而使公约中所反映出来的构成国际习惯的法律原则产生超出缔约国的效力。
中国作为一个空间活动的大国,已经参加了这五个条约中的四个,只有月球协定没有参加——当然,几乎所有的空间活动大国都没有参加月球协定,包括截至目前惟一曾经实际登月的国家——美国。
在这五个条约中,最早的外层空间条约(以下简称OST)通常也被称为是外空宪章,在整个空间法体系处于规定一般原则规则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判断一个国家在外层空间的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法,最重要的依据之一就是OST。
根据OST的有关规定,中国有权进行反卫星实验,对自己处于外层空间的卫星实施打击行动。不仅中国有此权利,其他登记国对于自己的空间物体,同样具有此种权利。
首先,空间物体登记国拥有其所有权,有权处置自己的空间物体,该处置行为的实施并没有排除反卫星实验的方式。
从空间法的角度看,根据1967年空间条约第八条的规定,发射外空间物体的登记国对于自己的空间物体是“保有管辖权和控制权”的,不管它是处于外层空间,或是在某一天体上。空间物体的所有权,并不因为其在外层空间或者在某一天体上或因其返回地球而受影响。这一所有权,既涵盖了该空间物体,也涵盖了该空间物体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在某一天体上着陆或者建筑的物体及其组成部分,所有权同样不受影响。④
如果某一空间物体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则国家毫无疑问可以对其行使所有权的全部权能。一般认为,所有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种。其中,处分的权能,就是对自己享有所有权的物体进行处置的权能。这一处置的权能既包括事实处分,如销毁所有物;也包括法律处分,如转让所有权。处分的权能一向被认为是拥有所有权的根本标志。而且,所有权的性质是对世权,其他任何人均不能够损害所有权人的权能。因此,所有国家对于自己拥有所有权的空间物体,都可以行使处分权能,包括摧毁该空间物体。
从中国摧毁自己的卫星这一具体事件看,该卫星是中国有权进行处置的空间物体,中国的行为正是行使了处分权能的行为。这一权能的行使,其他国家、组织或者个人不能干预、不能妨害。任何否定、阻碍该权能行使的行为,都是对所有权人正当权利的侵害,是错误的。而且,中国的这一行为并没有侵害到任何人的权利,对其他国家、组织或者个人既没有造成物质损害,也没有造成人身侵害,因此,反对这一行为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空间条约涉及武器的规则,并没有禁止反卫星实验。
如果笼统地说空间法禁止武器实验,而不对涉及武器实验的规则进行具体分析,那么,这一说法不仅不确切,而且是对现行条约法规则的严重误读。实际上,空间法的有关规则并没有禁止所有的武器实验。
根据1967年空间条约,其第四条涉及武器的问题,规定“各缔约国承诺不在环绕地球的轨道上放置任何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禁止在天体上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工事,实验任何类型的武器和进行军事演习”。其中,明确提到禁止武器实验的范围是“天体上”,而不是“环绕地球的轨道上”;“环绕地球的轨道上”所不能够采取的行动是“放置载有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种类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⑤换言之,关于发射导弹摧毁自己空间物体的行为,不在国际空间法的禁止之列。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法律不禁止的行为。
具体来看,2007年和2008年中国和美国分别进行的反卫星实验,都是对在轨道上的卫星实施的打击行动,而不是在月球上或者其他的天体上进行的武器实验,即并非“在天体上”进行的武器实验,不违反国际空间法的有关规则。
第三,各国在外层空间具有探索和利用的自由。
该自由的范围极其广泛,针对卫星所进行的实验——包括反卫星实验——并没有超出该自由的范围。
OST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内,应由各国在乎等基础上并按国际法自由探索和利用,不得有任何歧视,天体的所有地区均得自由进入。”⑥该条强调,各国不仅对于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是自由的,而且该自由对于各国都是平等的,不得有任何歧视。对外层空间的探索和利用,并不是哪一个国家的特权,而是各国都享有的,是全人类的事情(the province of all mankind)。具体而言,不仅美国享有这一权利,中国也享有这一权利;不仅发达国家享有这一权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也享有这种权利;不仅西方国家享有这一权利,东方国家也享有这一权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当然,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该为了所有国家的福利和利益,而不管其经济或者科学发展程度如何。⑦
无疑,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就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实验,只要这些实验不违反国际法,都是允许的。⑧这类行为,被称之为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当然,一国从事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时,如果对其他国家造成侵害,则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受到侵害的国家,可以主张自己权利,从而依照国际法得到救济。
实际上,OST的第九条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及了空间实验的问题。该条规定,缔约国之间在外层空间“计划进行的活动或实验”方面可以进行磋商,理由是该活动或实验“可能对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内的活动产生有害干扰……”。⑨从该条的规定看,即使某一缔约国的外层空间活动或者实验可能对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产生有害干扰,OST也并不禁止此类行为,而是赋予了有关缔约国提出磋商请求的权利。⑩值得注意的是,磋商请求的结果应当如何,该条并没有规定。OST在该条明文规定的是要求缔约国避免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受到有害污染以及将地球外物质带入而使地球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如有必要,缔约国应当采取“适当措施”。(11)
至于这一活动是否是第九条意义上的“有害污染”(harmful contamination)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定义问题。到目前为止,国际法、尤其是OST并没有对“有害污染”给出明确界定。该关键词语,有赖于各缔约国对其作出共同接受的解释。然而,即使在联合国大会上,也不曾有过关于该词应当具有何种含义的建议提出。因此,很大程度上,该活动性质究竟如何,是一个由各国实践予以解决的问题。在国际法上,并没有将活动定性为“有害污染”的法律依据。如果对“有害污染”进行理论上的解释,各种不同的解释可能都有一定道理,其程度范围也许会涵盖从严重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验到轻微的空间物体部件的丢弃这样一个长长的清单。严格来讲,人们可能无法确定出人类的哪一种空间活动是没有“有害污染”的。因此,为了规范此类活动,国际社会很有必要对“有害污染”进行明确界定。
二、反卫星实验的合理性
中国进行的反卫星实验,不仅不违反国际法,具有合法性,同时,从法律的观点看,也具有合理性。这一合理性的根本依据,是国家主权原则。
首先,国家主权原则意味着各国有权制定本国的空间政策,进行符合自己政策(包括国防政策)的空间活动,只要不违反国际法即可。
国家主权原则是长期以来国际法明确承认的基本原则,是各国进行国际交往的基本准则。国际法承认各国的主权,也就意味着,各国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不受其他国家的指挥或支配——除非它自己同意将自己置于后者的指挥和支配之下。一国可以自主决定发射或者不发射空间物体,发射何种功能的空间物体,何时发射(12),何时报废,如何处置该空间物体,等等。对于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进行干预,就会违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根据国际空间法的规定,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应当本着为所有国家谋福利和利益的精神进行,这当然也包含着从事空间活动的国家为自身谋福利和利益。换言之,除非从事了违反所有国家福利和利益的行为,否则,从事空间活动的国家在活动中包含有为自身利益的考虑并不与空间法的精神相冲突。
因此,各国的空间政策、空间活动,一方面是为了所有国家谋福利和利益,另一方面必然也体现着该国的国家利益。在国家利益之中,当然包含着国家的国防利益,而且,国防利益常常是各国优先考虑的问题。以美国为例,美国总统布什在2006年8月31日签署新的《国家太空政策》,称美国有权禁止“与美国利益敌对”的任何人利用太空。(13)
其次,主权平等原则意味着各国有权平等地行使主权,平等地维护自身利益,平等地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
主权平等原则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它不考虑国家大小、强弱、经济发展程度等各种因素,不会因为这些因素而认为各国拥有不同的权利。相反,主权平等原则要求各国在国际社会地位平等,反对歧视。如果一个国家有权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有什么理由禁止其他国家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一个经济和军事力量都发达的强国主张有权进行反卫星实验、并且一直在进行着各式各样的反卫星实验,那么,有什么理由禁止另一个发展中国家主张并进行同样的活动?
实际上,进行反卫星武器实验时间最早、次数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控制空间,既是美国长期以来就确立的空间政策,也是美国空间活动的现实写照。早在20世纪,美国总统肯尼迪就曾公开说过:“谁能控制空间,谁就能控制地球。”[1]根据有关资料,“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美国的防御重点是反弹道导弹,同时,美国也利用已有的反导系统进行反卫星技术探索,并进行了约40次反卫星技术实验。”[2](P63)不仅如此,2002年6月,美国正式退出已加入多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再限制部署太空武器;[3](P13)2008年2月20日又进行了一次反卫星武器实验,打掉了一颗老化的卫星。[4]而中国仅仅进行了一次这样的实验。[3](P11)如果把针对指责和谴责中国进行反卫星实验的言论,和以上这些形成鲜明对比的数据叠加在一起,是否可以得出一个有趣的推论:打卫星越多的国家越不应该受到指责,反而偶一为之的国家倒应该受到指责?这个自相矛盾的结论的负面影响当然是,所有具备反卫星实验能力的国家都会迫不及待地进行越来越多的反卫星实验。实际上,印度前总统阿卜杜尔·卡拉姆博士(Abdul Kalam A P J)在美国进行反卫星实验不久,于2008年2月22日宣称,印度有能力打击外国空间物体。(14)
如果审视一下事件的另一方面,就可以知道,中国进行反卫星实验是迫不得已的。实际上,中国一直在努力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国际社会限制外空军备发展的呼声也一直很强烈。在2000年和2001年的裁军会议上,俄罗斯与中国提出了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草案,遭到美国的反对。[2](P62)在十多年来屡次要求美国参与缔结禁止太空武器研发和部署的国际公约始终遭拒后,在美国长期对台售武的严峻形势下,在中国学者中出现以下观点就毫不奇怪了:中国被迫开展卫星实验,从而增进国家的安全,纯属为了打破美国的空间霸权。(15)如上所述,中国进行反卫星实验既具有合法性,又具有很强的合理性。因此,对中国反卫星实验的指责,不仅不具有法律意义,而且显得极其虚伪,甚至基本上达不到应有效果。国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自己的政策,包括空间政策,只要不违反自身的法律义务,是不容他人置喙的。
如果从确认登记国有权利打掉自己的卫星这一规则的角度看,中国打一个可能还不够,必要的时候可以再打第二个、第三个……。实际上,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既然不能肯定2008年美国打掉卫星是美国最后一次反卫星实验,那么,也没有理由相信2007年中国打掉卫星就是中国的最后一次反卫星实验。问题只不过是选择以何种方式进行?从目前美国反卫星武器的发展状况看,导弹、高能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与微波武器、小卫星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方式。[5][6]因此,这些方式也有可能是中国将采取的方式。
国际法中,国家的实践是形成国际习惯的前提,而国际习惯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家实践(practice)和法律确信(opinio juris)是国际习惯的两个构成因素。只有存在国家实践,才可能去确认在实践中所反映的规则的法律效力(即法律确信)。就反卫星实验而言,目前在空间法领域是没有禁止性规定的。因此,如果一个国家通过自己的行为反复表明自己的态度,有可能就会形成或者确认这样一个规则:自己主动摧毁自己的空间物体是合法的。当然,这也不是一个新的规则,只不过是对已有规则的明确确认而已。
通过行为确认已有规则的做法在国际法中并非特例。正如在20世纪40年代国际法院审理的科孚海峡案(Corfu Channel Case)那样,英国军舰主张在科孚海峡中享有无害通过权,并通过自己的行为对该规则进行确认,虽然当时阿尔巴尼亚反对该权利;国际法院在判决中同样确认了英国军舰的这一权利。此后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规定了过境通行制度,以公约规则的清晰语言规定了该有关权利。(16)
一旦此一规则形成或者得到明确的确认,反而不会有人再评说什么了。即使评说,也没有法律意义。
当然,在国际法的发展过程中,并不妨碍国家也可以选择相反的行为,即坚决反对这样做,以便形成相反的国际习惯。国家也可以选择原则上不反对这样做,但是,对于此类活动或者实验应如何进行,规定详细的限定性规则。如联合国空间碎片缓减指南中提出:“如果有必要进行有意分裂解体,则应在足够低的高空进行,以缩短所产生的残块的轨道寿命。”(17)
三、应有法:空间碎片的规范
中国的反卫星实验是否可能引起承担国际责任问题?目前来看,答案是否定的。空间活动造成的责任问题,是由责任公约规定的。根据该公约,只有空间物体给地面上的人或物、或者另一国外层空间物体或人员造成损害时,才会承担责任。如果中国在进行反卫星实验时,由于打击而飞进的碎片击中其他国家的空间物体,如卫星,从而给其他国家造成损害,则中国应当承担有关责任。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反卫星实验并没有造成损害,因而也就不存在由此行为直接产生责任的问题。
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将来会不会产生责任问题?例如:打击之后所产生的碎片以后是否会造成损害?如果将来空间碎片造成损害,仍然不外乎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于地面的人或物;第二,对于另一国外空物体或人员。那么,根据责任公约,前者实行严格责任,后者实行过错责任,根据这两个规定来确定即可。(18)以后者为例,即使碎片撞坏了其他国家的空间物体,是否承担责任还要以中国是否有过错为依据,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如对方操作失误或出现故障撞上了碎片,其本身有过错造成损害,中国无需负责。实际上,任何一个空间物体都可能存在着这两方面的责任,并不在于它是不是空间碎片,换言之,即使不摧毁它也不能避免一定不产生这两方面的责任。
关于主动打击之后产生的碎片问题,国际上很早就有一个空间碎片减缓指南。2007年外空委的报告中再次附上了空间碎片减缓指南,提出避免故意自毁。(19)但这一个指南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不构成法律义务。实际上,减缓虽然有作用,但其本身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清除才是最有效的办法,目前有的国家已经完成了捕捉空间碎片的装置的概念设计。(20)考虑到外层空间清除碎片的代价太高,目前尚没有行之有效的途径。
随着空间活动的发展,空间碎片会越来越多。发展下去的可能结果是,最终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发射一个空间物体。如何行之有效地鼓励各国处理此问题?笔者设想,一个可能的途径是:由参与空间活动的各个国家投资成立一个共同基金,由该基金负担清除空间碎片的费用,并将清理出来的轨道位置分配给各个出资国使用。当此种轨道位置的使用价值超过清理成本时,这一设想就能够得到实现了。
四、结论
综上所述,根据现行国际法,中国所进行的反卫星实验并不违法。不仅如此,根据目前的国际法规则、原则和理论,该实验还具有很强的合理性。
从长远发展来看,各国的反卫星实验可能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尤其是在目前没有禁止性规范的情况下,这种试验是不会立刻停止的。从短期来看,出现禁止性规范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
实质上,真正值得人们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规范空间碎片或者规范反卫星实验的具体规则,这也是可行的途径。杞人忧天式地担心中国的一次简单的反卫星实验会对哪一个国家造成威胁,不仅仅是毫无必要地过度夸大了实验的效果和影响力,而且,也将解决问题的关键方向引向了歧途,变成了对正常发展过程中的正常事件的过度关注和夸张的担忧。
收稿日期:2009-05-07
注释:
①关于该事件的消息,参见2007年3月16日温家宝总理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上答中外记者问,新华社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7-03/16/content_5858201.htm,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hn/pds/wjdt/fyrbt/t291116.htm,2009年5月26日最后访问。国外媒体报道可参见英国广播公司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6276543.stm,2009年5月26日最后访问。
②关于该事件,参见环球网http://mil.huanqiu.com/world/2008-02/66133,html和央视网http://news.cctv.com/world/20080226/101321.shtml,2009年5月26日最后访问。
③参见联合国文件A/AC.105/935。
④参见该公约第八条。
⑤参见该公约第四条。
⑥参见该公约第一条。
⑦参见该公约第一条:“……应本着为所有国家谋福利与利益的精神,不论其经济或科学发展的程度如何……”。
⑧参见该公约第一条:“……应由各国在平等基础上并按国际法自由探索和利用……”。
⑨该条部分条款规定:“…… A State Party to the Treaty which ha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an activity or experiment planned by another State Party in outer space,including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would cause potentially harmful interference with activities in the peaceful exploration and use of outer space,including the Moon 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may request consultation concerning the activity or experiment.”
⑩第九条规定:“……如果本条约某一缔约国有理由认为,另一缔约国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内计划进行的活动或实验,可能对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内的活动产生有害干扰时,则该缔约国可请求就该活动或实验进行磋商。”
(11)参见该公约第九条:“……本条约各缔约国对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在内进行的研究和探索,应避免使它们受到有害污染以及将地球外物质带入而使地球环境发生不利变化,并应在必要时为此目的采取适当措施。……”
(12)当然,具体时间的选择是以科学计算为依据的。
(13)参见美国2006年U.S.National Space Policy第二部分关于原则的规定“and [the U.S.]deny,if necessary,adversaries the use of space capabilities hostile to U.S.national interests”。该文件来源美国政府网站http://www.ostp.gov/galleries/default-file/Unclassified Natlonal Space Policy-FINAL.pdf,2009年5月26日最后访问。
(14)参见http://news.cctv.com/world/20080225/104518.shtml,2009年5月26日最后访问。
(15)人民网2007-05-30报道:沈丁立:“专家:中国被迫反卫星实验纯属为破美空间霸权”。
(16)参见国际法院关于科孚海峡案的判决,第27-33页。参见《海洋法公约》。
(17)参见联合国文件A/AC.105/890。
(18)参见该公约第二条、第三条。
(19)参见1999年联合国文件A/AC.105/720,2002年联合国文件A/AC.105/C.1/L.260,以及2007年联合国文件A/AC.105/890。
(20)参见联合国文件A/AC.105/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