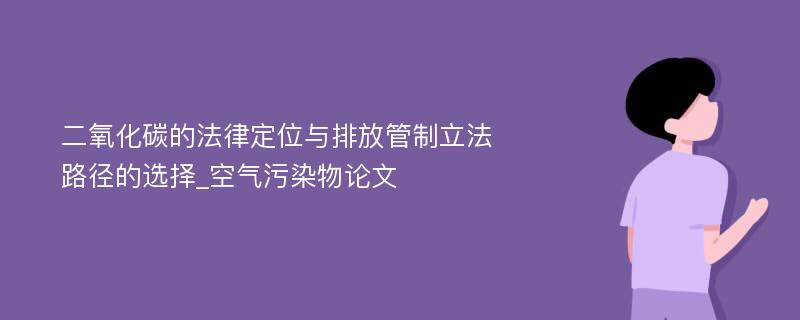
二氧化碳的法律定位及其排放规制立法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规制论文,法律论文,二氧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46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2-0030-05 二氧化碳作为一种物质,它在物理属性上是无色无味的气体,密度大于空气,能溶于水。在化学属性上,二氧化碳通常不能燃烧、不能供给呼吸、能与水反应、能参与光合作用。就其自然属性来讲,二氧化碳不仅无毒无害,还可以用作气肥、灭火、碳酸饮料、苏达水和致冷剂等的原料。正因为如此,在气候变化成为问题之前,二氧化碳只在自然科学的视域之内,并不是法律关注的对象。二氧化碳成为社会科学特别是法律关注的焦点,始于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问题之后,特别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以来。二氧化碳虽然无毒无害,但是大气中过量的二氧化碳,会形成温室气体效应,导致气候变化,进而导致极端气候变化灾害发生、海平面上升等问题,从而危害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也就是说,虽然二氧化碳不能直接致害,但是可能通过气候变化的作用,对人的身体和财产安全构成妨害,甚至会导致地球不适宜人类的生存,危及整个人类社会。因而,在气候变化情景下,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法律规制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国际上有关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但是国际社会自身不是减排主体。因而公约的主要内容是就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达成共识并对减排责任在各国间进行分配。各主权国家就自身承担的减排责任通过制定内国法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时,需要考虑的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否符合各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空气污染物”定义的规定?如果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符合空气污染物的定义,是否就意味着必须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来控制其排放?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制定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专门立法,何种方式更为可行?我国当前正在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论证进行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或者低碳发展促进专门立法的可行性,我们应当如何选择? 一、二氧化碳能够作为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空气污染物吗 大部分工业发达国家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制度在1992年《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时就十分成熟。如美国《清洁空气法》从1970年颁布到1990年修正后未再作改动。日本、英国、德国等国的情况亦基本相同。这是因为,工业化国家在制定大气污染防治法时,气候变化还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更谈不上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作出旨在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专门规定。 将二氧化碳与空气污染物联系起来始于各国对如何通过国内立法解决二氧化碳的排放以及监管权的探索。从各国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立法情况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或者路径:第一种路径是制定新的专门规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法律,并妥善处理专门立法与既有法律之间的关系,如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等多数国家;第二种路径即纯粹在既有立法框架与制度下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规制,如美国。 二氧化碳的法律定位问题是在第二种模式下提出的,即在不制定或者不能够制定新的法律、而又试图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规制,那么就只能借助于现行法律如空气污染控制法律来解决问题。依此模式,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空气污染物吗?如果是空气污染物,那么可以依据空气污染控制法律来规制其排放;如果不是,那么就不能够通过空气污染控制法律来规制其排放。 美国是唯一一个通过判例法将二氧化碳解释为空气污染物,并确立环境保护署依据《清洁空气法》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管的国家。而美国走上这条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美国就不断有议员提议制定“气候管理法”,①在2005年到2006年间,美国国会共收到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议案106件,自2007年1月到2007年7月间,美国第110届国会共收到125件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立法建议,包括议案、决议和修正案[1],但是所有提案都惨遭否决。2009年6月,《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Waxman Markey bill)以219:212票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最终还是在参议院搁浅。 在专门立法前途未卜的情形下,美国民间组织企盼通过判例法推动美国环保署在《清洁空气法》框架下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管。早在1999年10月20日,包括技术评价国际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Assessment)在内的20家组织向美国环保署(以下有时简称EPA)就提出申请,要求环保署按照《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简称CAA)》第202条(a)款第(1)项对新机动车(New Motor Vehicles)排放的四种温室气体(CO[,2]、CH[,4]、N[,2]O、HFC[,S])进行监管。[2]2003年12月8日,环保署正式拒绝了这一申请。理由有两个:一是EPA无权按照《清洁空气法》对温室气体进行监管;二是即便它有权监管,基于自由裁量权也不会进行监管。 环保署拒绝监管后,2005年7月15日,马萨诸塞等12个州和一些地方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将环保署诉至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要求EPA对新机动车及其发动机的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监管。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支持了EPA。之后,原告方又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此即“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保署案”。[3]在该案中,原告主张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是EPA应当规制的空气污染物,而EPA认为温室气体不是《清洁空气法》第202(a)(1)条规定的污染物。因此,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不是空气污染物就成为本案的焦点。 对于什么是“空气污染物”,《清洁空气法》第302(g)条解释为“任何空气污染物质或这些空气污染物质的混合物,包括任何排放到清洁空气中的物理、化学、生物、放射性物质”。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从字面上看,《清洁空气法》关于空气污染物的定义是一个宽泛的规定,“二氧化碳符合美国法律对空气污染物所下的广泛的定义”,环境保护署负有对温室气体进行监管的职责。② 该案判决后,美国联邦政府一直推动美国环保署对二氧化碳排放行为进行规制。美国环境保护署也陆续出台了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进行监管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强制报告规则、针对移动源的危害调查报告和尾气管道规则以及针对固定源的时限规则和剪裁规则等。 之后,针对美国环保署颁布的“危害调查报告”、“尾气管道规则”、“时限规则”和“剪裁规则”等四个规则,美国多个州政府和工业组织将美国环保署告上美国联邦法院,并一直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达到推翻该四个规则的目的。联邦最高法院将该案审理范围限定在“EPA对机动车温室气体排放的监管权是否会引发其对固定源温室气体排放监管?”[4]联邦最高法院于2014年6月23日对该案作出判决,判决认定:在《清洁空气法》“防治控制质量重大恶化计划(PSD)”下,任何因其排放的传统空气污染物而受到监管的固定源,其排放的温室气体也将受到监管。[5]这就确认了美国环保署至少对部分固定源排放的温室气体的监管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清洁空气法》的解释,不仅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解释为空气污染物,而且为美国环保署确立了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广泛监管权,EPA不仅有权监管由机动车产生的温室气体,也用权监管由固定源排放的温室气体。 除美国之外,欧盟1996年颁布意在整合许可证发放条件与程序的《污染预防和控制整合指令》(96/61/EC)(Integrated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Directive)在其附件1关于工业污染物的列举中,包括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2010年,欧盟出台《工业污染物排放指令》(2010/75/EU)(Industrial Emission Directive)代替1996年颁布的《污染预防和控制整合指令》,但两个指令关于工业污染物的定义相同。欧盟虽然将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列为工业污染物类型之一,但是并没有依据《工业污染物排放指令》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规制,相反,欧盟制定了专门的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欧盟排放交易指令》(2003/87/EC),并注意《欧盟排放交易指令》与《工业污染物排放指令》的衔接。凡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适用《欧盟排放交易指令》;未纳入EU-ETS的,适用《工业污染物排放指令》。 欧盟、美国经验表明,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作为污染物并通过污染防治法或者《清洁空气法》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二、将二氧化碳作为空气污染物由大气法对其排放加以规制,是最佳选择吗 尽管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作出了关于温室气体符合《清洁空气法》下“空气污染物”的广泛定义的解释,奥巴马政府及其领导下的美国环保署也一直坚持通过《清洁空气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但是这种做法在美国国内有相当大的争议。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阿里托法官和托马斯法官坚持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对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境保护局一案的判决本身就是一个错误[6],因为国会在制定《清洁空气法》时并未考虑诸如温室气体之类的污染物,联邦最高法院在“美国电力公司诉康涅狄格州案”中对《清洁空气法》取代美国联邦普通法的分析,“依赖于这样一种假设,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马萨诸塞州诉美国环保署’案的判决中对《清洁空气法》进行了正确的解释,从而允许EPA依据该法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管”。[7]斯卡利亚大法官也认为,温室气体不是标准的“空气污染物”,它不会导致污染也并不脏。[8] 在美国国会,也存在针对是否将二氧化碳作为空气污染进行监管的政党较量。从2011年到2013年之间,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占多数)还通过许多个关于取消EPA对温室气体监管权的议案,但这些议案最终在参议院(民主党微弱多数)遭到否决。 美国虽然可以通过《清洁空气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但这种做法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 第一,对传统空气污染物排放的规制措施不一定适合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规制。以美国《清洁空气法》为代表的传统空气污染物控制制度,主要依赖“命令与控制”措施,如空气质量标准、许可以及大量的禁止与限制性规范,但是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而言,更有效的措施是能源效率的提高以及低碳能源的使用。因而立法的重点是如何鼓励对低碳能源的使用和激励提高能效,而不是命令与限制。 第二,对传统空气污染物(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臭氧、悬浮微粒、氮氧化物、铅)等的末端排放控制,可以依赖“最佳可得技术”、“最佳经济技术”;而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而言,往往缺乏末端控制技术,即便存在末端控制技术,末端控制的技术也并不成熟,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尚不能商业化运用,更谈不上经济性。 第三,通过诸如《清洁空气法》等的大气污染防治法难以实现对所有温室气体排放的管制。传统空气污染物伴随工业化进程产生,因而各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重点集中于工业废气,但是温室气体的产生途径并非如此简单,“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森林”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也占相当比例。而且,与传统空气污染物不同的是,在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在商业、工业领域具有广泛的利用价值,甲烷作为天然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还是一种重要的能源。对这部分温室气体就无法、事实上也不可能作为空气污染物。所以,即便将二氧化碳作为空气污染物,大气污染防治立法也只能解决工业与能源领域的碳排放问题,并不能对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规制。 虽然美国当前通过判例法将二氧化碳解释为空气污染物,并且在《清洁空气法》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但是这种做法将温室气体排放规制完全纳入既有制度框架,因此,就涉及与现有制度的彻底契合。因此,较多涉及对既有法律的解释、修改与运用,相当复杂。当然,即便美国当前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作为空气污染物进行监管,也不能表明美国联邦层面已经放弃了制定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专门立法的努力。我们更倾向于认为美国当前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做法,实际是在无法通过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情形下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宜之计和无奈之举。 三、中国要不要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作为空气污染物,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来控制其排放 我国作为后起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近几年面临十分严重的雾霾天气,这一方面表明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其执行并不完美,迫切需要加强立法和执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改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并列入十二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的。2014年6月5日,由环境保护部起草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已经提交国务院,目前,国务院正在征询对送审稿的意见。 就送审稿的内容来看,其附则第192条第(一)(二)项对“大气污染”和“大气污染物”的定义进行了明确规定。照此规定,“大气污染”是指大气环境因某种物质的介入,而导致其化学、物理、生物或者放射性等方面特性的改变,使其功能减退或者丧失,从而影响大气的有效利用,危害人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或者破坏生态环境,造成大气环境恶化的现象。“大气污染物”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向大气排放的、能导致大气环境污染的物质。这条解释虽然没有列举到底哪些物质属于大气污染物,但是可以看出,它包含的大气污染物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也符合本条关于大气污染物的界定,亦应当属于大气污染物。或许,送审稿的起草者有意如此解释,其意图就是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包括在大气污染物之内。 与此相对应,送审稿设专章(第六章)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了规定。不过,就送审稿对控制温室气体进行专门特别规定来看,至少环境保护部认为即便将温室气体作为空气污染物,它也与一般空气污染物不同,不然为什么不对其他空气污染物进行单章规定,而只对温室气体进行单章规定。就送审稿对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所设规范来看,其控制措施显然与其他空气污染物的控制措施有巨大区别,这些措施主要涉及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效率提高、监测考核和标准、低碳技术、能效标识、增强碳汇以及国际合作等,不仅十分原则,而且相当简陋。 我们认为,如果我国采取美国的模式,将二氧化碳作为空气污染物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规制,可能会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法》难以向社会传达一种低碳发展的理念和信号。气候变化的应对是一个长期问题,它所依赖的能源结构转型也是一个长期问题。因而无论采取什么样的立法模式,关键在于促进全社会形成一个低碳发展的理念。但是《大气污染防治法》不可能担当此重任。这并不是说《大气污染防治法》本身有问题,而是因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使命难以让它的功能辐射至低碳领域。 第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主要涉及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的调整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等,远超出污染防治范围。产业结构的调整属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范围,主要由国家发展改革部门负责;而结构能源调整特别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新能源的职责属于国家能源局。另外,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减排还涉及建筑、交通、工业、农业等多领域,亦需要强有力的部门协调。这些宏观事务很难只作为一个污染问题来处理,环境保护部门也难以胜任。 第三,《大气污染防治法》难以对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源进行监管。传统空气污染物及其排放源,来源相对明确,无论大小,均可以适用相同的管制措施,而且以追求“零排放”为最高境界,但是对于温室气体排放来说,则不完全相同。温室气体排放源相对空气污染物排放源,不仅有工业排放,而且有能源、农业、林业、土地利用等领域的排放,针对不同领域的排放源,管制措施也难以统一,而且也不可能追求“零排放”,特别是对于来自于农牧业、土地利用等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就很难管制。 第四,对空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管制的要求不同。在我国当前空气污染特别严重的情况下,不难想象,此次大气法的修改“严”字当头。而且只要国家有决心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就完全可能通过采取强势的行政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明显治理效果,但对温室气体的减排则并非如此。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公共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方面采取强势的行政措施来进行控制,因为如果其他国家不积极,一个国家的减排会因为“碳泄露”而消减。所以各国均采取激励为主的减排措施。在中国尚没有强制减排义务以及未来国际谈判以“自主承诺、国际确认”为发展趋势的情况下,温室气体减排应当以“激励与约束相结合”进行适当的管控。大气法与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差异,也决定了如果将两种缓急不同的问题整合进同一部立法,其后的问题也就不言自明。 当然,即便不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纳入《大气污染防治法》,并不等于环境监管部门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无所作为。[9]基于提高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减少因为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报告、排放许可而给受控企业造成的过度负担,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具体的监管权限设置中,通常将温室气体监测、排放报告制度、排放许可等监管职责赋予环境保护部门。这种做法在大多数国家盛行,如美国、欧盟、加拿大魁北克省等都是如此。 四、我国二氧化碳排放规制的立法选择及其地位 考虑到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下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气候变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国际合作的复杂性,都决定了在对待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上,应当作为一个宏大的特殊命题,运用以一种更为系统化的规制方式来对待。或许基于此,世界各国在履行自己所承担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责任时,普遍通过专门立法的途径来解决,据统计,全球有66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放的专门立法和政策。其中10余个国家有国家层面的专门立法。而这些有专门立法的国家,逐渐趋同于综合立法模式。 我国虽然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对低碳发展工作提出要求,但其效力仅局限于“十二五”期间,无法为社会公众、尤其低碳投资者提供稳定的预期;虽然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但内容太过原则;虽然有《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森林法》以及《大气污染防治法》等能源和环境法律,但都不足以匹配实现低碳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变革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的规范性要求。 笔者认为,我国迫切需要借鉴和吸取多数国家的经验,制定一部专门的、综合性的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立法,这部立法应当能够统领在低碳发展中所涉及的各类社会关系,成为全面涵盖生产和消费领域一切温室气体排放活动,在节约使用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统领现行相关立法的上位法。它不仅能够处理与能源、环境等各类低碳发展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问题,也为控制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所需建构和维护的新型社会关系提供了专门的平台。至于具体名称,如是《气候变化应对法》还是《低碳发展促进法》,则不是主要问题。因为无论名称是什么,都需要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的基本原则、主要制度措施、管理体制与机构、减排的主要领域、激励的方式作出规定。因此,建议国家加快气候变化或者低碳发展立法进程,以为低碳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持。 ①参考美国环保署网站,http://www.epa.gov/climatechange/EPAactivities/economics/legislativeanalyses.html,访问时间2014年7月19日。 ②Massachusetts v.EPA,549 U.S.497.标签:空气污染物论文; 碳排放论文; 低碳经济论文; 法律论文; 全球气候变化论文; 环境保护论文; 环境污染论文; 环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