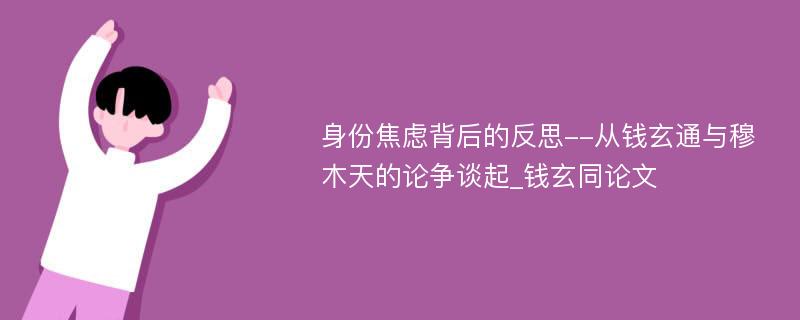
身份焦虑背后的省察——从钱玄同与穆木天的一次论争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焦虑论文,身份论文,钱玄同论文,穆木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8)04—0094—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向来被视作象征诗派最重要的理论代表。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被作为重要的文学事件写入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史著作——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中。很长时间以来,研究者大都不假思索地将这篇文章与穆木天的象征诗创作并置于同一维度上进行考量,认为两者天然地互为参考系:即《谭诗》以注解的形式完整地将穆木天象征诗创作实践纳入到理论范畴,而其诗歌创作亦处在《谭诗》的理论烛照之下。这种采取“共时”姿态介入穆木天诗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并非没有合理性;然而这无疑斩断了我们考量《谭诗》的另一种可能:即在“历时”的向度上梳爬《谭诗》的理论资源流脉,揭示出《谭诗》成立背后种种驳杂、生动的文学生态。①下面,笔者试图从一次几乎被遗忘的论争中(即1925年《语丝》杂志第20期、第34期登载的新文化运动著名学者钱玄同与诗人穆木天关于“国民文学”的论争)钩沉事实,并由此考察《谭诗》以前穆木天诗学-文学资源的生成过程,从而将穆木天的早期的诗学-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予以重新观照。
一、一次被遗忘的论争
如果认真考察史料,不难发现,现在被认为是创造社重要成员的穆木天最早在1926年4月之后才真正投入创造社的工作之中。而事实上,自1918年至1926年,穆木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日本留学生活中度过的。这期间,穆木天与周作人的两次接触颇值得注意:第一次是在1919年7月间,周作人重游日本(此时距周作人离开日本已经有近5年),并虔诚地到九州日向武者小路实笃建立的新村“朝圣”;②我们今天知道穆木天也参与了此事,据郭沫若《创造十年》中的记载:“那时听说他(指穆木天——引者)参加了周作人的‘新村’运动,我也觉得像他这种童话式的人物也恰好和‘新村’相配。”[1](P33)第二次可查到的记载是在1924年冬天,穆木天由回故乡探亲返日的途中,亲自到北平拜访了周作人,并将自己的诗作《我愿作一点小小的微光》和《泪滴》送给周氏,这两首小诗随即便在《语丝》上发表。这之后,穆木天常常将自己的作品通过信件寄给周作人。后来引起争论的那一篇《给郑伯奇的一封信》其实即是经周作人之手刊登在《京报副刊》第80号上的。
论证首先由“五四”闯将钱玄同挑起,在1925年3月30日第20期的《语丝》上,钱玄同发表了一篇名为《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的文章。这篇文章保留了钱玄同“五四”以来的一贯风格,对于批判对象毫不手软,且颇有些“骂”的言辞。文章在略谈了作者看1925年1月28日刘半农给周作人(启明)的信之后便直奔主题,树起批判的靶子:
但我却要提出一个修正案:“同时这应该打破国家底迷信”。年来国内最时髦的议论有三种。一是成日价嚷着“赶走直脚鬼”者。他们狠(即“很”——引者)赞美拳匪;他们说,中国的财匮,匪多,兵横,都是“直脚鬼”闹出来的。二是大喊“爱国”者。他们底议论,我见的狠少,偶然想到的,是说,蔡元培提倡美育教育,应该弹劾,因为艺术早没有国界的,所以提倡教育,即不是爱国……三是所谓“国民文学”底主张者,他们“要夸我们民族历史的浩浩荡荡,澎澎鼓鼓,放浪汪洋”,“要歌颂盘古,轩辕,项羽,仲尼”说“关雎是乐而不淫呀!但他们尽在淫中贪恋”“不要管他们的时代思潮……我们作顽固的人罢!”;并且还有“复活精美的古文古话”。这三派底一切主张,虽然并不相同,有时或且相反,但痛恨‘洋方子’之心是一致的。”[2]
钱玄同提到的“国民文学”主张者,实际上所指即是穆木天、郑伯奇和王独清三人,而尤其针对的是穆木天:在上面的引文中,钱玄同用以批判的大量摘引文章皆出自穆木天《给郑伯奇的一封信》。不难看出,钱玄同的批判思路仍保有非常明显的“五四”式言说痕迹。关于国族问题的想象(同时这应该打破国家的迷信)钱玄同始终不忘记以文学—文化的维度作为基本的切入点。由是,他对于全盘西化的坚定信念便自然地要安置在对“国民文学”的极端批判上来。对于大喊“爱国”者的言论钱玄同引述甚少;然而对于国民文学的批判却非常精确地引用原文,这些看似细微的差别都标示着某种有趣的症候:以文化作为基点从而突围政治的批判构图仍在此生动地表现出来。“我也很爱国,但我所爱的中国,恐怕也和大同世界一样,恐怕未有此物,这便是‘欧化的中国’这句话,老实人若要误解,尽管请误解,我可不高兴负解释底责任。至于有些人要‘歌颂’要‘夸’的那个中国,我不但不爱它,老实说,我对于它极想做一个‘卖国贼’。卖给谁呢,卖给遗老。”[2]这里,钱玄同将针对穆木天的“国民文学”批判成功地重新转换成新与旧的二元对立式上来,将“国民文学”中试图以个性主义调和本国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努力简单地缩写成为“五四”时代的话语符号:新旧之战。于是,我们再次如此熟悉地从钱玄同的这篇文章中找到“磕头”、“请安”、“托鞭子”、“裹小脚”、“拜祖宗”、“拜菩萨”、“拜孔丘”、“拜关羽”一类具有隐喻性的符码,对这些旧俗的再次批判无疑标示着退潮期中对“五四”话语的抚摸与召唤,在以穆木天等人为假想斗争对象的同时,钱玄同的“五四”式言说无疑具有某种悲壮感,甚至比“五四”的语言更加决绝地说:“爽性划出一块龌龊土来,好像‘皇宫’那样,请他们乔攒聚到那边咬干屎橛去;腾出这边来,用‘外国药水’消了毒,由头脑清晰的人来根本改造,另建‘欧化的中国’岂不干脆?”[2]
显然,钱玄同如此决绝的话语方式带给穆木天的不仅仅是诗学-文学追求上的打击,从1925年7月6日他发表在《语丝》第34期上的《寄启明》一文来看,穆木天对钱玄同表现出非常彻底的失望;同时,他也隐隐认识到自己和钱玄同探讨的问题似乎并不在一个话语系统内部。文章第二段用大量篇幅反复谈到对钱玄同误解“国民文学”的失望:“哪想到堂堂的钱玄同先生——中国的学术界的泰斗钱玄同先生,竟把我们小学生的话,误解到这般的利害!真的‘谜’(enigme)呀!竟把我们的‘国民文学’的主张与‘爱国论者’同仁的所说堪称一致了!”[3]如果说在《给郑伯奇的一封信》中,由于采用诗体而难免产生偏向,那么在这篇《寄启明》中,穆木天对“国民文学”的表述则非常清晰而老到。事实上,“国民文学”的起点正在“五四”,而它试图超越“五四”之处则是以“文化寻父”的情结重新找寻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调和稳健的一面。在穆木天看来,经历数年的“五四”运动发展到现在,似乎已经涵养了足够的包容度,可以在好与坏、新与旧、内与外等等二元对立中解脱自己。穆木天坚持认为国民文学的思潮与欧化“他们是一个东西的多面相”,[3]为了更清晰地表述观点,穆木天索性将“国民主义”、“个人主义”、“世界主义”三者关系纳入视野,并作出下面的界定:
一边“欧化”是得肯定的,一方“国民的”(national)之分子是尤得肯定的。两方面同时同等的肯定,才能结果出真的调和。Influence是外来的,而Originalise是内面的,自己的,国民的。我们的“国民文学”的主张,根据在“个性”上,国民主义是“自我进化”的一形式,在与Individualism,Cosmopolidanism成正的比例;国民主义的实现越法(即“越发”——引者注)的澈底(即“彻底”——引者注),个人主义是越法的深刻,世界主义是越法的坚固。[3]
穆木天的论说策略非常清楚:即首先与“五四”言说合谋,承认并接受既有的思想资源;然而,他的着力点又在这些已经形成思维惯性的观点中超拔出来。这里有一点颇值得注意:穆木天的“调和策略”始终站在一个基点上,那就是人的“个性”。这实际上秉承的正是周作人自“五四”以降“人的文学”的观念。我们注意到,在穆木天那里,无论是内部尊重传统还是外表欧化,个人主体性始终都是国民必须秉持的“根据”:“在我们的愚想,当然得提倡国民文学,发现出国民的自我,同时才能吸收真的欧化来,才能有真的调和,才能作出真的越发彻底的自我来。”这里实际上暗藏着“人的觉醒”的必要性。而非常有趣的是,周作人在同一期上发表的言辞暧昧的《寄木天》,虽然对“国民文学”表示基本赞同,然而还是一再用大量篇幅强调“提倡国民文学必须提倡个人主义”。[4]
同期刊出的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一文,仍保持着钱玄同固有的风格,其“五四”情结进一步明朗化,不仅仅是满篇的“都”、“就”、“只”这样不允许任何例外的表述,而且如“五四”一样决绝的反抗诅咒孔子:“至于‘努力实现’四个字,我实不懂,即使‘望文生训’似乎也装不到孔老二底身上。”[5]对穆木天“国民文学”的解释,钱玄同仍然毫不理会,同时宣称:“至于现在的中国国民,我从没有说过‘不要他们’的话;但我希望他们‘洗心革面’努力追求欧化;根本反对他们再来承袭咱们祖宗那种倒霉的遗产。”[5]穆木天并未再对此做任何回击。
这场尘封已久的论战非常生动地为我们再现了当年的文化与文坛生态,先后参与进来的钱玄同、穆木天、周作人、张定璜、林语堂等,作家之间微妙的关系同样有趣地呈现出来。不过,更让人关心的则是:穆木天这种具有独立于当时文坛生态的“国民文学”观念③究竟涵养于何处?它是何以形成并最终发展的?显然,这样的考察对我们的研究是有益的。
二、结点:身份焦虑与萨曼情结
——东京帝大毕业论文《阿尔贝·萨曼的诗歌》
考察穆木天文化-文学的独异品格固然不能忽视其与“五四”闯将们的代际差异,然而更为重要的恐怕是作家对自身地域身份的焦虑以及留日期间接触到的萨曼、维尼等法国诗人的作品。很显然,在1925年末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之前,对于身份的焦虑使得穆木天格外重视萨曼、维尼等人的诗歌,特别是作为“外省诗人”的萨曼对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而更多时候,身份焦虑与对萨曼诗歌的迷恋相互绞缠在一起。所有这些都深刻地改变着穆木天对待主流文学观念的姿态,并由此促成了其面对“五四”主流文化时的独立思考。
在1920年穆木天的诗歌中,“心欲的故乡”几乎成为他创作的母题。故乡吉林市的北山坡、天主教堂、江雪等纷纷烛照在象征法则之下,呈现出一幅幅有趣的构图。这类象征诗与其说在艺术上达到了完满,毋宁说它们更表征了非常生动的文化症候。借用穆木天评价法国诗人萨曼的一句话:“在自愿成为象征主义诗人以后,我认为他远非他本人了,也远离了最初的浪漫主义影响。他变得越来越自觉地——正如在上面这首诗歌中所唱的那样——憎恨几乎所有这些影响。”[6]对涵养了自己的边缘文化(外省文学)的发现与不断确认使得穆木天对于象征派的选择超脱了对于技巧的迷恋,成为获得自我身份标志的关键。有意思的是,无论如何对他者影响表示不满,诗人都必须首先以主体介入的姿态将自己吸纳到整个文坛的中心。在文学资源仍旧相对稀缺、文学生产渠道仍旧相对闭塞的时代,获得自身话语权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只能是介入文人“圈子”。穆木天显然具有获得此种话语权的优越性,留学日本的经历以及东京帝大的文凭都标明了他的身份。不过,穆木天的毕业论文中,我们始终能够看到强烈的自我质询(下面将要详细说明之)。在以一个外省人的身份介入主流文坛的时候,穆木天对于“五四”风潮中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意见。早年在南开中学求学期间发表的一批文章中,我们发现穆木天在对进化论表现出兴趣的同时(《札记》《格物家之心理》等文章),更在《我人》这篇小文中提出:“我者世界之我也,人者世界之人也。我我人人,世界所宜也。人我我人,世界所须也。宜也须也,世界之所以立,万物之所以成也。”[7]此种“独养其身,兼善天下”的风格具有非常明朗的个性主义色彩。以个体性介入而非随波逐流,从边缘文化进入主流文化中的穆木天因为个体身份的焦虑实际上获得的是一份旁观的冷静。当主流文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当时仍然占据非常高的文坛地位的旧派)在新与旧、善与恶、全盘肯定、全盘否定等等问题上拼杀之际,穆木天以边缘文化身份介入其中最先看到的却是两者融合的可能。“我们都是历史的产儿,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开传统。一位诗人的特色在于其作品的复杂性,即他把各种不同的潮流结合起来,并把它们与自己的个性融为一体。”[6]穆木天对象征派的选择本身即是将欧化技术实践与中国表述融为一炉的标本,而对萨曼诗歌的迷恋则始终提示着诗人自我的外省身份和独立思考的可能。
在《阿尔贝·萨曼的诗歌》④中,穆木天通过与萨曼诗作的不断磨合,逐渐展开自我找寻与确认的过程。他试图迫近萨曼矛盾焦灼的内心世界,揭示林林总总的“影响”在萨曼内心形成的张力。不过,他捕捉这些细节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萨曼师承渊源的庞杂,而恰恰把落脚点放在阐述萨曼是如何一点一点地甩掉所有的羁绊而逐渐成为自己的过程。穆木天始终抓住诗人萨曼抉择的矛盾来展开自己的论述。“成为象征主义者还是依然作为浪漫主义者和帕尔纳斯派诗人,与新的运动结合起来还是恪守传统:这在他初涉文学的时候几乎是一场激烈的斗争,他的内心为此备受折磨。”“他早期的作品受到在他之前的各个流派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他的最后作品之中。”穆木天深信萨曼拥有伟大诗人的胸襟,他包容吸纳任何具有审美价值的流派,用所有具备高尚艺术性的传统启发自己。而同时,“像浪漫主义和波德莱尔的影响一样,象征主义的影响也不能使他满足”。对于萨曼,穆木天既是一位研究者,又不断用自己的诗人身份与他互参。作为一个同样来自外省的青年诗人,他从萨曼的诗学精神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在不断的考索与用心的体验后,研究者兼诗人的穆木天捕捉到萨曼的生命意识:“温柔的怜悯、虔诚的怜悯和纯朴”,他看到了萨曼诗歌的精髓:“(萨曼的——引者注)大部分诗歌都可以解释为他感受到人类的痛苦的崇高,以及对人类的贫穷感到怜悯。前者是哲学诗歌,是一个突出的道德家的诗歌;后者是通俗生活的诗歌,即主题诗歌。崇高庄严和通俗亲切:这是阿尔贝·萨曼的诗歌的两种主要类型。”[6]在大量阅读了萨曼的创作之后,穆木天的心灵受到了淘洗,同时他也找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方向。在诗集《旅心》中,我们可以找到来自中国本土传统文化的因素、浪漫主义的表意手段、象征主义的诗学技巧,此时的穆木天像萨曼一样在不同的影响间游走并且很快脱离了单纯模仿阶段,找到了诗歌创作的“自我”。同样以一个外省青年的身份,诗人穆木天用充满象征的眼光重新观照自己的故乡,找到了自己的风格。
以边缘文化身份介入主流文坛的穆木天,在经过了诗人萨曼的影响之后实际上消解了边缘文化自身的偏激姿态,获得了超越性的自我意识。以此种意识重新介入主流文坛的他显然更愿意用自己的思考来缝合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于是“国民文学”的提出显然有其不可忽视的资源背景。
三、余论:从“国民文学”到“交响论”
1926年3月16日,穆木天归国前一个月,《创造月刊》创刊号刊登了他最重要的一篇诗论(后来被很多研究者认为是象征诗派最重要的理论著作)——《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在这篇诗论中,“国民文学”的观点有了更加精彩的发挥。国民文学在注重国民性的同时,更注重文学性。此时的“国民文学”已经被重新整合入象征诗的“交响论”中来,交响的内涵必须有所延展,除了艺术本体以外,“国民的生命与个人的生命不作交响(Correspondance),两者都不能存在,而作交响时,两者都存在。……国民文学是交响的一形式。人们不达到内生命的最深的领域没有国民意识。……国民文学的诗歌——在表现意义范围内——是与纯粹诗歌绝不矛盾。”这使得原有“国民文学”在深度上有所加强:国民意识产生在“内生命的最深的领域”,这里国民意识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素质。他应该在内心深处保有对生命的哲理性思考,他应该对自己的生存本身进行理性的观照。这样才不是封建时代人之为人的浑浑噩噩,现代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正是要求一种时刻对自己行为的理性拷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国民才能被称为是国民,他们既要做一个群体中的人,同时更要做一个具有独立个性的自我。穆木天认为,“国民的历史能为我们暗示最大的世界,先验的世界,引我们到Nostalgia(怀古)的故乡里”。象征主义的诗学实践与“国民文学”的理性追求在此被缝合。
笔者曾经在一篇谈及穆木天诗学的文章中说过:“如果说,五四初期林纾敏锐地捕捉到了全面否定的危机感,用自己微薄的力量苦苦捍卫着民族文化的根;那么经过了五四潮涨潮落后的穆木天,已经直接体验到了危机的产生,他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喊出寻根的第一人,尽管这声音在时代话语中同样微弱。”[8]在现代性急速推进的过程中,来自主流文化外部的声音往往能提供一种有益的参照,如同穆木天这样以“外省人”确认自我身份的作家正是如此。不过,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将他这种清醒的认识涂抹掉,仅仅留下其作为技巧的“象征诗”手法,这不能不说是遗憾的。而我们今天的研究,则要在努力还原历史真实的同时,发掘出作为“国民文学”的真正价值所在,从而为我们的文学史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注释:
①事实上,关于目前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笔者在拙文《新旧的裂隙之间:穆木天给郑伯奇的一封信——兼与林纾比较》(《天中学刊》2008年第3期)中即已开始探索另外一种解决的途径。
②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可以参看钱理群所著《周作人传》中的相关记录,钱氏的文章详细引述了周作人下述日记:1919年1月6日:“阅新シキ村生活”;1919年1月10日:“寄新シキ村本部函,附金二丹”;1919年1月25日:“下午得新シキ村本部稻垣芳雄君十八日函”;并引述了周作人后来追述自己此次“朝圣”的文章《访日本新村记》。
③虽然在“五四”初期,陈独秀等人提出了“国民文学”概念,后来的郁达夫等人也提出将“国民文学”作为《创造》的办刊宗旨;然而穆木天的“国民文学”概念显然与此有别。这种以国民“个体性”作为基础,由此“不偏不党、不同不合,用自己的自我力,内发挥个性——国民的方面,外吸收世界潮流,要有判断,要不盲从”。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提出无疑是卓越的,超越中国当时的文坛生态的。
④1925年穆木天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阿尔贝·萨曼的诗歌》是他同年写就的毕业论文。这篇被尘封在东京大学近70年的论文终于在1994年与大陆的研究者见面,发表在当年的《吉林师范学院学报》上。这篇论文旁征博引,提到的诗人、作家将近百位,显示出作者法国文学功底的深厚。穆立立(穆木天的女儿)介绍说:“我父亲穆木天于1926年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科毕业,这篇论文写于1925年12月。记得与我父亲同学的冯乃超先生曾说过,此文当时曾得到导师的好评。从寄来的论文前面的‘论文审查委员氏名’中可以看到担任导师的是辰野隆幼教授和阿鲁伯科路特讲师。丸山昇教授在专为此事而写的一篇短文中说,我父亲在学的那一段时期,正是东京大学法国文学专业的第一次黄金时代,与穆同时毕业的有市原丰太、川口笃、杉捷夫,前一届有伊吹武彦、渡边一夫,后面两届有小林秀雄、今日出海、三好达治、中导健藏等。在佼佼者甚重的情况下,穆敬熙亦能秀于其中,想来是不易的。”
标签:钱玄同论文; 文学论文; 周作人论文; 穆木天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语丝论文; 诗歌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