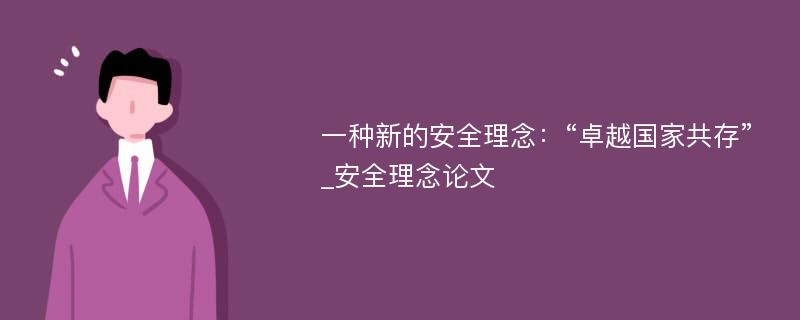
安全哲学新理念:“优态共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理念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全哲学为安全实践提供指导行为的核心理念,不同的安全哲学的核心理念又产生了不同的安全认知方式与安全行为模式。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的蔓延,导致人们对传统安全理论的质疑与对新的安全哲学理念的普遍需求。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给安全罩上重重阴影的各种传统安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环境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等)的“风险”,也正在构成某种“全球化”的势态,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并使“政治成了战争的继续”[1](p.ix)。因而,对安全哲学新理念的期待成为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共同心愿。
一、“优态共存”拓展安全实现的可能性限度
哲学是对存在的理性反思,安全哲学则是对人的安全生存状态及其实现的可能性限度的理性反思。安全问题是人类生存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追求的首要价值,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首要指向,甚至还是人们视为“超自然的信仰”而顶礼膜拜的对象[2](p.25)。
安全的内涵首先可以从与安全相关的行为中得到描述:如避免受到攻击、侵犯、伤害乃至灾难等显在或潜在的危险;消除种种由不确定感、不稳定感、无保障感等导致的恐惧心理;控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犯罪蔓延、瘟疫传播、毒品泛滥、移民过度、经济崩溃、环境恶化等趋势;努力防止使用武力、扩散武器、种族冲突、爆发战争,等等。因此,人们总体上形成的最朴素的安全内涵是:太平无险。其次,还可以从词源上进行解析:如英文中的安全词汇有形容词“Safe”,其含义是免于危险与伤害;有名词“Safety”,其基本含义是安全的条件以及避免危险与伤害;另一个名词是“Security”,它的基本含义是免于危险的条件和感觉,以及确保此条件与感觉而进行的努力[3](p.1271,1309);《现代汉语词典》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所以,从广义角度来看,安全的含义包括身体上没有受伤害、心理上没有受损害、财产上没有受侵害、社会关系上没有受迫害的无危险的主体存在状态,或者是国家没有外来入侵的威胁、没有战争的可能、没有军事力量的使用、没有核武器使用的阴影等状态。
从安全哲学的角度分析,理解安全内涵的视角本身制约着安全实现的可能性限度。如从“威胁论”的视角把安全理解为“没有威胁”,安全则是一种“危态对抗”式的均衡;而从“和合论”的视角把安全理解为“和合互动”,安全则将是一种“优态共存”式的共建。
国外的国际关系理论多从“威胁论”的角度理解安全。现实主义理论学者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注:Arnold Wolfers: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see Terry Terriff,Security Studies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2.)同一立场的对安全的概括还有:安全就是“摆脱战争的相对自由”(注:Ian Bellany,"Towards a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See Barry Buzan,People,States and Fear: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Second Edition,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 Press,1991,p.16.),或是“获得价值时威胁的不存在”[4](p.2)。另外,大卫·A·鲍德温(David A.Baldwin)在《国际研究回顾》(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杂志上发表的《安全的概念》一文中,提出过对安全概念至少要做七个方面的基本分析;巴端·布赞(Barry Buzan)在《人、国家和恐惧》(People,State and Fear)一书中,则归纳讨论了12种不同的安全定义。而《当代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 Today)一书则对安全作了全面的总结,其作者坦利·特里夫(Terry Terriff)认为,关于安全首先要回答的是:第一,我们关注安全将聚焦于谁或者什么?它应当是国家、建基于民族或性别上的团体还是个体?我们必须置哪个层次为安全考虑的优先层次?第二,谁或什么在威胁着安全?是国家还是被决策者制定的政策?或者是从环境问题上产生的非国家因素,如贩毒及跨国犯罪等方面产生的功能性威胁?与此相应的两个新问题是:谁提供安全以及以什么方法保障安全?而后两个问题的回答又有赖于对前两个问题的回答[4](p.3)。坦利·特里夫的设问很有理性反思的水平,但他的种种设问均建立在“威胁论”安全观的立场上。“威胁论”安全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危态对抗”式的安全思维,因为我们不难从西方历史中获知,在“不安全”的名义下,“人们把恐惧、权利和权力汇集于神、君主或主权国家,以在自然的变迁兴衰,防范其他的神、君主或主权国家中保护他们自己;在它的名义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出来,并被美化为为了国家利益而使用这些武器于具有自杀性意味的安全困境中;在它的名义下,人们很少注意到在国际关系中数十亿各种各样的武器被制造出来的同时,数百万、数千万人却在科学知识进步而智能保持沉默中被杀害”[2](pp.24-25)。“威胁论”的安全观引导行为者一定要划定我、你、他的明确的安全界线,进而制定出相应的对抗性策略,如扩大军备以防止最坏情况等,这恰恰限制了安全在本质上实现的最大可能。
而中国历史上的安全认识则多从“和合论”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有不少与安全相关的成语,如“安然无事”、“安枕而卧”、“安居乐业”、“安邦定国”,“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危而不持”、“危机四伏”、“危在旦夕”,“天灾人祸”、“天下大乱”、“天下太平”等,其中有些成语产生的特定语境是指涉王朝盛衰、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的。可是,在如何确保安全与维护安全方面,中国人表现出一种更为宽广和合的安全思维。中国人历来把安全与和平结合起来考虑,因而显示出对安全的一种特别的理解与独特的视野。
最早全面反映中国人传统安全思维的是《易经》。《易经》是一本有着独特安全意识、安全范畴、安全原则与安全思维的理论典籍,因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深刻反映安全哲学理念的奇书。《易经》因为重视安危吉凶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关系,因而通篇文辞多有警戒危惧之意,反复强调“预警安全观”与“防范安全观”的确立与重要性。如《周易·系辞下》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绐,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可见,“易之道”在于通过始终不懈地警戒惕惧,努力求得平安无险,没有灾咎。通观全书,《易经》的安全哲学可概括为“保合太和”四字,与此相应的安全理念则是“和合中庸”,安全原则是“预防在先”。因为以“和”为本的安全思维能使人心气平和,透析事理,知晓艰险,明断天下吉凶得失,进而帮助人们预防风险、度过难关、保证无咎、取得成功。由此可见,《易经》可视为一本蕴含着微言大义的安全哲学典籍,并且一直影响与规范着中国人的安全思维。
安全内涵的理解程度与安全可能性的拓展程度,反映着安全哲学观的深刻性程度。《易经》“保合太和”的安全哲学源自“自强不息”精神与“厚德载物”德性的完美统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待人情怀与“中庸”处事原则的完美结合。根据《易经》“保合太和”的安全哲学与“和合中庸”的安全理念,我们会发现,从避免威胁与恐惧的角度所理解的安全,只是一种狭义的有待于深化的安全认识。事实上,威胁和恐惧在现实生活中是警戒性很强的词语,它总是被人们关联到处于生存危险的生命体验与生死存亡的国家历史中。如果我们只承认安全是“威胁的不存在”,就会在现实中寻找威胁并试图进行消除,于是设想的敌人或对手就会成为去不掉的影子,进而使对抗与复仇成为无休止的延续。倘若我们从生存状态与发展状态的“和合”、“优化”角度来关照安全和体现安全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提出一种新的广义的安全观,即把安全看作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superior co-existence)[5](p.9),这样,对安全本质的理解就从危险状态的避免拓展到“你安全我也安全”的优化状态的建构上,从而使安全的理解趋向于更加积极和深刻的认识。
就国家安全来说,“优态共存”的安全哲学理念表征出一种新的安全思考维度,进而可拓展安全价值的可能性限度。首先,“优态”是安全指向的对象,表征的是行为体可持续发展的生存境况,把“优态”作为对象的安全置于发展国际关系的最基本前提上,不仅表明国际关系理论从起源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注:"The rise of thinking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nature of,and conclusion of,a war-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First World War."See Terry Terriff,Security Studies Toda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10.),转向了“和平与发展”的思考,而且标示出安全所要达到的更深远的价值目标是“发展与安全”。其次,“共存”是安全获得的条件,表征的是行为体追求安全的历史性条件。在全球体系中,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行为体若要获得安全,其基本立场与途径都只能是通过“互惠共建”达到“共优共存”,这就需要国际关系任何一个层次中的“自者”与“他者”间的共同努力。
因此,以“威胁不存在”来界定安全,其安全的可能性边界永远划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而安全也只能是相对的安全。而以“优态共存”来界定安全,其安全的可能性边界就拓展到了安全建设的双方甚至多方,安全就有了某种绝对的意义。正如巴端·布赞所描述的:“理想的世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成功地确保安全的世界,而是不再需要去谈论安全的世界。”[6](p.485)
二、“优态共存”提倡一种“和合共建式”的安全模式
数千年来,不同的民族与国家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安全思维”特征,并表现出不同的安全寻求的行为倾向,这些特征与倾向经过世代沉积、演化,逐渐成为不同国家政治与社会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考方式。从总体上看,安全维护与国家的安全保护有以下四种基本的形式:
一是“隔离防守式”的安全模式。这种安全模式反映的是“好篱笆才有好邻居”的安全哲学理念,表现为“我安全重于你安全”的心态。就“隔离式”的安全模式而言,首先是寻找天然的“篱笆墙”隔离,依地理上的天险而居,高山、海洋、江河、沙漠等都是地理隔离的最好屏障;其次是建立人为的隔离屏障,如历史上的长城就是以人为的努力防止游牧民族侵扰的安全举措。有险可守,有屏障可依,是传统国家面临生存威胁时采用的最自然也最合理的安全理念与方法。“隔离防守”的安全思维,尽管以防守为先着,但这种安全思维的立场仍然是相信任何时候都有战争的危险,相信只有依靠武力才能最终保证安全。“隔离防守”的安全思维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重要来源。
二是“进攻拓展式”的安全模式。这种安全模式反映的是“危态对抗、强者为王”的安全哲学理念,表现的是“你不安全我才安全”的心态,其安全战略的动机是与其被动地居险自守,不如主动出击,推进边界线,甚至直接以他国的领土为本国的安全缓冲带,以他国的安全屏障为自身的屏障。“进攻拓展”的安全思维更是以武力作为自己的安全支柱,把安全看作国家所最稀缺的资源,国家应该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安全利益,甚至认为可以不顾其他国家的安全,以破坏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保障自己安全的条件。“进攻拓展”的安全思维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情形下,对多边合作组织在安全上的维护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充分暴露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扩张本能。
三是“结盟协作式”的安全模式。这种安全模式反映的是“安危与共、进退同步”的安全哲学理念,表现的是“你不安全我也不安全”的心态。“结盟协作”的安全思维,比较重视国家安全的相对获益,认为与其通过侵略或武力扩张费力地推进安全的边界,不如相互立信守约,互为盟友,共同维护具有相同安全利益的安全边界,一起摆脱“安全困境”。当然,“结盟协作式”的安全模式的实践类型比较复杂,它可以是“集体防御型”的或“集体推进型”的,也可以是“集体协作型”的。“集体防御型”的安全行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反映的是防御性的现实主义安全哲学,我国确立的“韬光养晦”的安全战略以及与周边国家长期修好的种种努力,均体现出防御性的现实主义安全理念。“集体推进型”安全行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反映的是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安全哲学,冷战后北约的不断东扩,即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推进”的安全行为。当“协作”走向多边,特别是以国际组织为主体进行安全调节时,就会表现出“集体协作型”的安全行为,这一行为模式的理论根据则是自由主义的安全观。美国第28届总统威尔逊倡导与践行的国际合作就是一种典型的自由主义安全行为。威尔逊在《论国家》一书中强调国家间关系应遵循道德要求与民主原则,强调成立国际组织和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认为健全的国际法和国际公约可确保和平。当然,以上几种模式在特定的条件下也可以综合起来运用。唐世平对此有过专门论述:“按照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大概有四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来获得安全:武力、联盟(集体防御)、安全合作以及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总体说来,进攻性现实主义仅仅相信武力与联盟;防御性现实主义认为除了武力与联盟之外,安全合作也能够带来安全。新自由主义则强调除了武力、联盟、安全合作之外,多边安全组织也能够带来安全。”[7](p.237)
四是“和合共建式”的安全模式。这种安全模式反映的是“优态共存、顾全本土”的安全理念,表现的是“你安全我才安全,我安全你也才安全”的心态,因而是一种体现“保合太和”安全哲学与境界的安全模式。在当今“威胁不可预测、敌人不能确定”的世界中,这一安全模式对人类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合共建式”的安全模式在国际政治中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建构主义的安全理论。建构主义从认识论变革出发,用社会结构范式颠覆物质结构范式,强调“社会关系”规定国家的角色,“社会规范”创造行为的模式,“社会认同”建构国家的利益与安全,“社会文化”影响国家的安全战略。于是,建构主义把社会的“关系”、“结构”、“规范”、“认同”、“文化”置于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地位,充分相信规范、法律、习俗、技术发展、学习和机构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行为和利益,文化的“共存”与伦理道德的“认同”可以成为国家安全保障的举足轻重的因素。
“优态共存”在建构主义安全理念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国家作为最高的安全行为体,具有团体性的集体身份,以及因这种身份而产生的利益驱动。如果说华尔兹强调生存安全是国家的惟一利益,那么,乔治和基欧汉在将生存安全视为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还强调独立与经济财富必须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主义理论的代表温特在这三种利益上加上了“第四种利益”,即“集体自尊”。集体自尊指一个集团对自我有着良好感觉的需要,是对尊重和地位的追求。温特认为,表达集体自尊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集体自我形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一方面,负面的自我形象往往是通过自己认知到,因他国的蔑视和侮辱而产生的,这使得国际关系产生高度的紧张。如果团体要满足其成员的自尊需求,就不能够长期忍受这样的形象,因此也就会通过抬高自我或贬低和侵略他者的行为来弥补自我的负面形象。另一方面,正面的自我形象则来自于相互尊重和合作,主权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在这里尤其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至少在形式上,一个国家被他者视为具有平等的地位,意味着主权的制度不仅仅通过保证国家能免受征服的实际威胁使国家趋于平和,而且还通过保证国家能免受担心没有国际地位的心理威胁使国家趋于平和。温特的观点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使国际安全问题研究具有了新的伦理视角。他视“集体自尊”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利益”,突显了国家具有自我实现的性质。温特认为,国家寻求的是“观念自我”或“理想自我”,即使国家趋向追求利益本身,“这些利益的真正意义也在于它们驱使国家认知它们,解读它们的涵义,并依次决定应该怎样定义主观安全利益”[8](p.237)。
三、“优态共存”为非传统安全确定价值取向
安全与伦理在生存论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家安全与人类生存在价值追求上同样有重要的相关性。冷战以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9.11”恐怖袭击事件、SARS疫情、禽流感等的相继发生,对国家安全的非传统挑战被置于日益重要的议事日程。环境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等安全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的安全、社会安全等重要安全概念被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的范畴体系中。非传统安全在安全行为体、安全内容、安全状态、安全价值中表现出与传统安全的诸多不同,这表明,传统的安全理论有待于转变其价值立场与范式,而“优态共存”的安全理念正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新安全范式,它将为非传统安全确定合理的价值取向。
“优态共存”的安全理念重在突出“人的安全”。非传统安全涉及的行为体拓展到个体、团体、国家、国际、跨国、全球层次而呈现“多元化”。个体层次如“人的安全”突破了传统主权的限定,因为“人的安全与人的权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9](p.536),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安全的充分保障便是人的权利的充分保障。如在信息安全中,个体对安全的影响更加彰显,以往的“战争是所有人的最重要的事业”将转变为21世纪的“战争是个别人的最重要的事业”[10](p.242)。全球层次的“生态安全”,如环境恶化(特别是污染和疾病),除了成为政治不稳定与冲突的因素,进而引起对主权的侵犯属于传统安全外,其他的直接影响人的健康与福利,并因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占用而导致生存关系紧张,则更多地涉及国家安全以外的层次[4](p.118)。因此,如果不以“优态共存”为必然的价值取向,那么,个体和全球总是被排除在国家安全的范畴之外而得不到有效的保障,最后,国家安全自身也难以得到很好的保障。
“优态共存”的安全理念重在关注“社会安全”。非传统安全涉及的系谱内容囊括人类生存的一切方面而呈现出“多样化”。如经济安全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市场等安全内容;社会公共安全包括人权安全、跨国犯罪、移民难民、洗钱贩毒、走私偷渡等安全内容;信息安全包括网络恐怖主义、黑客袭击、病毒撒播、机密窃取、网络犯罪等安全内容;环境安全内容涉及全球性的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大气污染、海洋污染、水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疾病传播以及地方性的污染如汽车废气、工业废水、城市雾罩、有毒原料泄漏、水源污染等。因而,“优态共存”的安全理念必然要求各国面对如此复杂的安全困境时,和平共处,共同努力,为全球安全治理做出自己的贡献。
“优态共存”的安全理念重在提倡“全球安全”。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非传统安全还涉及安全价值基点从国家中心逐步转向全球中心而呈现出“多重化”,非传统安全有着超越国家主权的挑战性质,因而设定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坐标必须统筹国家与全球两个维度,必须以全球共同体的价值秩序为安全的评价基点,进而体现出与“危态”对抗消极思维相反的、体现“优态”共建的积极安全思维;传统安全的价值基点主要是“国家中心”,“优态共存”安全理念的价值基点则拓展为“全球中心”。因此,从“类本位”的伦理意识看,任何不利于人的“类存在”生存方式的局部行动必然将让位于以全球利益为核心,具有“类价值”伦理性质的世界性行动,这样,以“类生命一类价值”为基点的全球视野、全球意识、全球利益、全球命运……就不能不成为现代社会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所必须共同遵循的伦理价值坐标[11](p.103)。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只有确立在“共优范式”上,才有其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在全球政治的价值坐标中,“优态共存”为我们真正认识非传统安全的现实境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价值尺度,也为我们指导国际行为体共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优态共存”为非传统安全确定了重视“人的安全”、“社会安全”与“全球安全”的价值取向,要求国家之间的互动体现“类时代”中的“类伦理”,以共同实现人类的普遍安全。在双边互动中,“优态共存”理念要求国家之间体现“平等性”、“互助性”的道德原则,所有国家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是主权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对双边互动中的国家来说,平等性是体现这种国际法原则的基本伦理精神。互助性体现在国家之间有事相商、有难相帮、有急相救上,同时,两个国家还应在互助中体现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权利共享等。在多边互动中,“优态共存”理念要求国家之间体现“融合性”、“规制性”的道德追求,“融合性”体现在一方可以另外两方为对象开展协作性活动,“规制性”则体现在任何一方均可以在确保安全与公平的前提下展开竞争。在全球联动中,“优态共存”理念要求国家之间体现“共和性”、“归一性”的道德价值与机制建构,全球联动的运动取向往往是在多样性与异质性的不同社会基本模式或社会文化价值中的“多元共和”,“共和性”要求行为体从国家本位中跨出,走向地区主义,再发展到全球主义;“归一性”的道德建构主要体现在对世界事务的全球治理上,联合国或者具有世界政府性质的“新联合国”或体现“自由人联合体”性质的全球一体化治理机制将在这种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2](pp.163-189)。
总之,“优态共存”是一种以人类共同体为整体价值尺度的安全哲学新理念,是依照人的类本性、类生活、类价值的要求所确立的人类活动与国际关系的终极准则。“优态共存”能为安全维护确定合理的价值取向,以人类为本位来思考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其中,中国的“和平崛起”发展战略是遵循“优态共存”价值理念的最佳设定。“优态共存”在人、社会、国家、国际、跨国、全球的“类关系”上蕴含着人与国家的全部关系的“交互融合”,在安全维护过程中体现为突显以“人的安全”为本的价值超越,在类活动上则达成跨国界、超种族的“社会公共安全”为纲的多元和谐。“优态共存”安全哲学的新理念以及与此相应的“和合共建”的安全范式所指明的,也正是这种符合“类伦理”精神、顺应人类发展走向、使人类真正走出“安全困境”的光明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