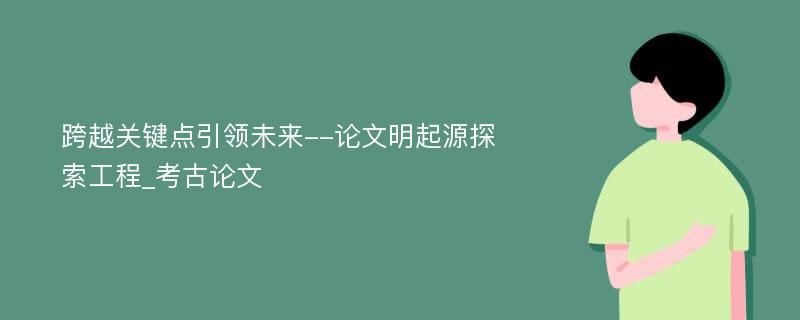
跨越重点 引领未来——试论文明探源工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重点论文,未来论文,工程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久前将秘鲁苏佩河谷的圣城卡拉尔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该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苏佩的圣城卡拉尔考古遗址拥有五千年历史,以其金字塔和庙宇著称,是世界已知最古老的文明中心之一。这不禁令人回味。我国很早就开展了文明起源研究,实施对史前重要大遗址的保护,国家领导人10年前的对外讲演就已经开始采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的提法①。但如何进一步做好文明探源工程,仍值得反思。
笔者曾从事考古和遗址保护的管理,并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科技中长期规划战略研究及文明探源等重大专项工作,在不同场合曾提出过一些认识,如应将文明起源阶段大型工程遗迹,考古发掘现场有机物辨识、记录技术作为研究重点等②,现整理阐述如下,与辛勤于一线的同行们共享。
一 大型工程遗迹
文明探源研究什么,什么是人类最早文明的构成要素或标志,比较公认的是安志敏先生的观点:文明指高级社会组织即国家开始出现,而文明的具体标志则是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③。此外,水利工程包括农业排灌系统也很重要。而且,城与水利工程有些难以截然分开,有些城垣也兼有御敌和水利的作用。例如南阳在清代还筑就复杂城垣,称“梅花城”④,据当地同行介绍也具有防洪作用。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在《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曾引用学者钱穆一句他认为很中肯的话——“耕稼民族筑城有两种用意:一是防游牧人的掠夺,而另一是防水灾的飘没”,并且继续写道:“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主要的城恐怕是筑起以防宗邑帝丘的淹没,余下的防御其他都邑。规模也许相当地大;不惟包围人民的庐舍,并且包围他们的耕田。”⑤
人类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国家属于制度文明。礼仪性建筑是制度文明的实证,也是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重要性不可低估。辽西牛河梁遗址的重要性,就在于发现了五千年前的坛、庙、冢等大型礼仪性建筑群。
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古城考古成果于1995年发表⑥,颇具影响力。中原地区很可能也有距今约五千年的大型礼仪性建筑。如三门峡铸鼎原北端黄帝庙所在,曾发现仰韶时代的瓦片和石铲,许顺湛先生判断为“黄帝时代的一处祖庙和祭坛”⑦,但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一般没有将其作史前祭祀遗址对待。那里是延伸向黄河的高耸台地,登临环顾,气象万千。笔者1999年在现场曾见到陈列在一起的彩陶盆和大石铲,据介绍为建庙施工时同出,似能说明一定问题。而杭州良渚遗址群却远不止此,除祭坛外,20世纪90年代还发现30多万平方米面积的矩形正方向的莫角山“台城”遗址,且发现拱卫它们的约6500米长的塘山遗址。后者被认为是当时的水利工程——防洪大堤⑧,与现代防洪设施杭州西险大塘的走向相一致,另从航片和大比例尺地图上还依稀可见大范围水网残存,或许就是很早时候的农田排灌系统。该发现打破了“考古学上在东周以前也没有大规模水利建设或农业灌溉的证据”⑨的沉寂,可惜的是,我们很多“考古队员对灌溉问题并不敏感”⑩。
中国领导人之所以由“几千年文明”转而使用“五千年文明”、“五千多年文明”的提法,是依据中国文物考古界的长期探索。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史前大型公共工程遗迹已多有发现,研究也获得突破,震惊世界,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进行保护与研究的重点。鉴于城市化建设的威胁和盗挖的破坏,国家文物局曾超前指定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两次专函浙江省政府同时抄报国家领导人要求将其列入国家重大计划加以抢救保护、调查发掘和宣传展示。其中1996年还曾指出该遗址群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城市、礼仪性建筑、水利建设活动,或还有其它建设,都可以归结为人类最初的大型公共工程,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和关键的因素,应成为文明探源的重点。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大规模、复杂的公共工程需要更高级、复杂的社会组织和制度,需要规范语言交流的文字,需要技术和工具的进步,所以才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分化的飞跃。
世界上有关文明起源的遗址,除了前面提到的卡拉尔,巴基斯坦的莫亨朱达罗遗址也值得注意。该遗址在1980年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1]。简介资料指出:它以三分之一面积的发掘展示了世界最古老的市政布局,是印度文明(公元前2350-前1750年)成熟期最有代表性的城市。这种提法意味着它已不属于文明初创。该遗址也出土有带文字的印章、小件青铜制品,但大概是其并不体现该世界遗产的主要价值,简介竟未提及。苏佩河谷的圣城卡拉尔并未发现文字,但经发掘已被国际公认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中心。
史前大型公共工程遗迹及其群体,包括相关环境,作为研究重点特别是考古发掘的重点加以突出,并非指其它研究就不重要。文字、金属器等遗址包含物的发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比较而言,大型工程遗迹及分布地区是可遇也可求的,而且为抵御人为和自然力破坏,大面积考古发掘势在必行,同时也就增加了遇到文字、金属器的机会。
二 早期文字载体
文字发现和解读对文明探源意义重大。中国商代甲骨文已是成熟文字,此前的原始文字(12),良渚文化陶器上也出现多例。由于成篇出现,作为文字产生的证明应无问题。但这些发现并非结束而是开始,是文明探源工程必须应对的考验和挑战。
既然有文字,就需要发现更多,甚至发现档案性质的文字,以期经过考释来说明历史。两河流域古文明所发现的文字数量大、年代早,都是因偶发线索获得破译的。罗塞塔石碑,因用希腊文、象形文字圣体和俗体三种字体同时铭刻一篇文献,成为破解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钥匙。该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9年,1799年于拿破仑远征中被发现时嵌在一座中世纪城堡的墙体里(13)。两河流域尽管发现3种不同楔形文字的摩崖石刻,但破译它们却复杂得多,时间也漫长得多。意义更为重大的是一批“辞典学”泥板文献的出土,为楔形文字的破译和正确阅读做出了巨大贡献。1923年《苏美尔语语法》问世,“从此后,就再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人们对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所有文献的阅读和研究了”(14)。上述说明,我国早期文字的探索之路还极其漫长,需抓紧时机,寻求可遇与可求的突破。
如何发现而且大量发现比甲骨文早的文字,是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问题。但为什么总是不能发现?如何增加发现机遇?这就提出了早期文字的载体问题。文字载体,包括附着物和书写材料。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玉器上的刻符,现已发现不少,但其与商周甲骨、青铜文字之间存在着巨大空白。是否还有陶、玉、甲骨、青铜之外的竹木、布帛等物体承载早期文字,而且除刻划外,是否还有以颜料书写的呢?如果存在,它们或许就是战国、秦汉竹木简牍及帛书的前身。
有机质物体及其表面痕迹不易在地下保存,地下水位的涨落变化即可使其消失殆尽;即使有幸存者,在出土后也会瞬间发生变化,化为乌有,无从辨识。所以,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类似发现,即使偶有机会,也稍纵即逝,无法记录,无从取证。
出土竹木、布帛等有机质文物的保护一直是个难题,经过几十年努力已经取得不少成就。但主要还是考古学家发现后,由科技专家来协助提取、揭示、加固、修复和保存。将目标集中于早期文字载体的发现,是在已有基础上提出的新问题。在国家文物局“九五”(1996~2000年)规划中提出:加强考古发掘现场有机物的辨识、记录、提取、保存的研究。该用语之所以如此细致,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寻求我国早期文字发现的突破。发现,是提取、保护的前提,只要辨认和记录下来,哪怕是无法提取和进一步保存,也是难得的积累。
五千年前的有机质文物在我国并非没有考古发现,值得总结并提炼些问题出来。最近,浙江考古学者介绍1986年良渚遗址反山墓地出土嵌玉漆杯的发现、提取和修复的细节情况(15),就颇有启发意义。试想,如果此件有机质器物,无小玉粒附着于漆皮,甚至无漆皮残留,我们还能够发现吗?为释读出土简牍、帛书等需要,古文字学者已经在室内使用比较尖端的仪器设备,难道不可以使用于考古发掘的现场吗?为发现早期文字,创新和引进相关技术及设备,提高对考古发掘现场的有机质遗物及微痕的观察、辨识、记录技术水平,早当提上日程了。当然,谁也无法预想什么时候早期文字冒将出来,但机会永远属于有所准备者。为了增加可遇机会,只能锁定这一重点目标,尽最大努力,实现可求得的相关田野考古技术和设备的突破及推广。即使短期内没有惊人发现,也可以提高考古发掘和现场文物遗迹保护的整体水平。以局部问题的突破,带动整体水平提高,正是科技重大专项设置的目的所在,何乐而不为呢?
三 特殊阶段的田野考古性质
文明探源研究,以大型工程遗迹及环境研究、和发现早期文字为重点,意味着该研究属于田野考古性质,而且是史前特殊阶段的田野考古性质。为设计好项目方案与技术路线,并坚持实施、取得成果,还需要进一步认识这一性质,并有所把握。
史前考古的性质及方法与历史考古的差异,夏鼐先生主持完成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考古学》一文如是介绍:“史前考古学的研究范围是未有文字之前的人类历史,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则限于有了文献记载以后的人类历史,两者的界线在于文字的发明……史前考古学承担了究明史前时代人类历史的全部责任……两者所研究的遗迹和遗物在性质上有一定的差异,所以它们的研究方法也有所不同。从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来说,史前考古学要充分与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相结合,历史考古学则必须与历史学相配合,同时还要依靠古文字学、铭刻学、古钱学和古建筑学等分支。从断定绝对年代的手段来说,史前考古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技术,而历史考古学则主要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16)
文明探源,就是探索从没有文字到有文字的人类历史,属于史前考古,但又与一般的旧、新石器时代考古不同,属于史前考古的最后阶段。因此,该史前考古,也需要历史考古经常依靠的一部分科学技术,特别是针对大型工程遗迹及其环境的有关工程技术科学;所需物理学、化学等范畴的自然科学的技术,也不只用于断定年代,更需致力于早期文字载体及附存环境的研究,致力于发现它们的技术攻关和推广。检讨这一特殊目的和时段的史前考古、田野考古,需要结合或依靠那些新的科学和技术,这是文明探源工程成功开展的关键。
关于田野考古的发展,《考古学》则指出:“世界各地的田野考古转入以发掘为中心……调查发掘的对象也由一般的居住址和墓葬等扩大到道路、桥梁、沟渠、运河、农田、都市、港口、窑群和矿场等各种大面积的遗址,从而使得考古工作者必须与各有关学科的专家协作,才能完成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任务。”(17)这里主要所指,即大型工程遗迹及环境的调查发掘,而且强调“必须”与有关学科协作研究。文明探源的田野考古研究,也必须注意把握的特殊性质。与历史考古不同,其对象是人类大规模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最初遗迹,也就需要去开发针对性较强的、与人类大范围原始工程以及自然环境演变研究更加贴近的田野考古技术。
把握上述性质,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将目标集中于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大型工程遗迹及环境的研究,以及相关的田野考古技术攻关,实现自主创新、重点跨越。当然,这并不是说只以五千年前后的遗迹、遗物作为工作对象。对于大型工程遗迹,需要研究自古至今的演化,而且往庄有较晚近的遗存叠压,也有必要仔细研究。对于早期文字载体,则根本就没有现成的对象,需要的是锤炼技术,倒是需要在不属于五千年前后时段的发掘现场“练兵”。已经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延生的成果——田野考古现场保护移动试验站和工作车,立项时就有解决发现早期文字有机载体技术问题的考虑,现在可以大派用场,将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点。
四 扩大多学科、多层次合作
扩大多学科合作,说来容易,其实很难。每一现有的学科、部门、单位等,都有自身长期形成的目标、规律和习惯,甚至利益诉求,不愿意改变,或不愿意有大的改变。但科学毕竟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面对新的公共目标和资源,进行新的课题和技术路线设计,需要创新的勇气、眼界和一定的办法,甚至将民主、争鸣和利益调整考虑其中。
对于大型工程遗迹的研究,建筑学、土木工程学、环境科学及各专门史学的加盟十分重要。目前在此方面,考古学者主要是与各个专门史特别是建筑史的研究学者合作,这当然必要也需予以支持。但各专门史学者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为所属专门学科发展和现代应用服务,主要方法是依据历史文献和已有的考古发现,长期以来形成自家习惯,很多还达不到前面所引《考古学》所说“应用于遗址发掘、测量、制图,对发掘出的遗迹进行复原或在现场保存”(18)的要求。而对于没有文献记载的人类最初的大型工程遗迹,几乎完全属于对未知领域的探索,问题复杂得多,不是一般的协作和综合研究能够解决,需要扩大参与研究的学科领域,将研究位置向考古现场前移,共同制定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计划并实施,进行复原研究和实验考古项目,着意创新理论、方法和技术。我国的一些采矿冶金史学者就是从被动利用考古出土资料开始,到主动“订货”,不断发展着与考古学者的合作。不久前又有学者与考古学者一道深入中条山进行田野调查,就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开拓。
此种跨学科合作的有效开展可能还需要有制度和队伍建设的考虑。如有些国家的考古组队制度,即要求考古队伍必须有专业的建筑师、测量师参加的做法,就值得借鉴。而我们往往是发掘出重要遗迹后再找专家,而且专家就那么几个人,于是留下诸多遗憾。
就扩大多层次、多单位合作而言,学术界与基层的文物考古机构的广泛合作,不可轻视。机遇永远属于基层、属于一线。
首先,大型工程遗迹的研究需要对很多重要古遗址地区的动土建设——不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给予特别注意。如牛河梁遗址群的人居聚落中心在哪里,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是否在附近现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之下也尚未可知。但现山西运城市市区的地下,却有些线索。市区有池神庙,面南临盐池,正对着中条山,现存大殿殿基是元代的,长达近百米。追溯盐业早期发展,可能也与文明起源有关,野外考察固然易行,但城镇建成区之下也不可放弃。当地领导曾十分重视文明探源。多年前造访时,该地委书记历数当地十大优势,第一就是与文明起源有关的盐池,最后才讲到关帝庙建筑群。大型工程遗迹,包括城市遗址,多有早期甚至史前的来源,历代沿用、层叠分布,开展城市考古并探索早期遗迹十分必要和迫切。但由于这些遗迹一般破损严重,没有大面积考古揭露无法认识,所以任何动土对总体认识而言,都可能是资料的积累。这方面的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如地处广州市中心南越国宫署遗址的最初发现,当年基建施工暴露的石砌遗迹,若非那位研究革命文物的黎显衡先生散步时关注,或许就与我们失之交臂。又如长沙吴国简牍在市区建设中的发现,被誉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城市考古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若非文物工作者在挖土机前拼死争取也是无法得到的。记得宿白先生就曾指出:像长沙走马楼一类的地方,应是考古重地,先列预算考古。
其次,发现早期文字载体,也需要多样化的考古发掘现场。除了对特定时代的遗址、墓葬发掘安排技术攻关外,根据技术和设备研究开发的需要,在田野考古发掘项目较多的地方也可做出适当安排,增加机遇、积累,寻求多点突破。地区一级的多学科合作的力量,因为深谙当地状况,又便于长期深入合作,似应注意吸纳参加文明探源工程。如绍兴越国印山大墓发现后,当地的理工学院曾与文物考古机构合作,对出土木质文物的现场保护开展了坚持不懈的研究。
扩大多层次合作也包括国际合作。文明探源既是中国文明探源,也是世界文明、人类文明探源。中国人自己的研究当然为主,但要令人信服,还要广泛争取多国合作。要合作,当然首先是对方有兴趣、有基础列入自家的计划;但我方也要据我所需,有所主导和选择。或可考虑这样两点侧重:
1.以研究文明起源的田野考古学者为主
历史考古的国际合作对象可以汉学家为主。文明探源则不尽然。选择合作者需扩大范围,最好是研究世界其他文明起源的专家。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早就开始了,愿意合作者应该大有人在。十几年前,一位美国学者,研究美洲玉米农业起源的老专家,身兼总统顾问,曾不辞辛苦到江西省的大山中,与我国学者合作研究稻作农业起源,给世界和中国留下了重要成果。
2.以研究大型工程遗迹的有经验的专家为主
如富有经验的区域考古学者、景观考古学者和实验考古学者等。据美国学者介绍,为了使区域方法更系统化,尤其是使人们能更好地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新出现了考古学分支——景观考古学。如秘鲁考古的例子会很有启发。1980年,在秘鲁的的喀喀湖,美国考古学家和秘鲁农学家发现了古人大规模改变景观的遗存。为了确定该系统的作用和潜力,他们修复了其中一片田地。这一实验考古项目证明该系统比现代机械化农业要优越得多,于是高原农民开始使用祖先的农业体系以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19)。这种景观考古,特别是作用于大地的实验考古方法,我国还缺乏经验。而这种方法,不仅对文明探源工程,就是对大遗址保护、生态文明建设,也有重要意义。
国际合作还应当是双向的。中国学者也有必要走出国门,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人类文明起源。
五 超越既有 引领未来
经过我国考古和有关学界的不断努力探索,中华文明探源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只不过与世界其他几大文明的研究相比较,还有一定差距。多年前科技部、国家文物局将其确立为重大科技专项,称之为文明探源工程,并非要取代正常进行的研究,而是从政府职责即促进科技进步和加强文物保护出发,组织更为广泛的多学科合作和更突出重点的经费支持,以使得这一与自然环境、人类工程等密切相关的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在中央科技和文物工作方针指导下使文明探源工程取得实效,科学和技术界,包括已经参与和有待参与研究的各学科各领域,有必要不断提高对于工程意义的认识。
人类和中国的文明起源阶段的遗产,是全部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遗产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新中国首任文物局局长和考古所所长郑振铎在1956年曾作过巧妙而且中肯的概括:“希望人人能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地面和地下的文化保藏,这不仅仅是为了学习遗产推陈出新的需要,还要为后代的子子孙孙保存文化遗产,作为对他们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力证。”(20)推陈,这里当然不是推倒、推掉的意思,而是学习、推敲、研究、探索。对于任何国家、地区甚至乡村,保护遗产,都有他所指的两重意义。增强人民及其后代的创造力、凝聚力与和谐度,无可指摘且应提倡。但对文明起源阶段的遗产进行研究和保护,还有其特殊意义。
文明探源是世界性的重大课题,对于中国政府和科学技术界而言,对现今国土上人类文明起源的研究也是不可回避的责任。文明探源,就是探索从没有文明到有文明,从没有国家到产生国家。这样一个过程在世界各地虽有差异,但共性为主。个性的发展以及相互的纷争主要是进入文明以后的事情。人类文明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在经过了几千年纷争和对自然界破坏以后,已经应当考虑如何建立和谐世界的问题,即人类社会各国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而凝聚世界力量的目标,是共同善待自然界。因此,探索和总结文明开端时的人类作为,特别是与大自然的关系,应是文明探源的主要目的,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对这种意义的思考,笔者曾受到某电视台译制播出的“寻找‘玛雅文明’的母亲城”考古专题片的启发。该片介绍一些考古学家在中南美洲调查发掘最早的文明遗迹,开始找到的遗址群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不过后来发现一处,经研究属于公元前2600年。该片认为,那里简直就是“台型建筑群的世界”。这是一个多么新颖的概括!(江浙一带距今五千年前后不也是台型建筑群的世界吗?可惜这一世界正因城镇化而被夷平)更为令人惊异的是,那位考古主持人特地请来研究军事考古的专家现场考察,结果不见任何战争迹象,于是得出结论:“战争催生文明”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和平也可以催生文明。
思考人类正面临的根本问题,实现古与今、中国与世界考古的接轨,也是中国文物考古界的长期追求。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曾写道:“距今一万年以来,从文明产生的基础——农业的出现,刀耕火种,毁林种田,直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取得巨大成就,是以地球濒临毁灭之灾为代价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人口众多,破坏自然较早也较为严重。而人类在破坏自然以取得进步的同时,也能改造自然,使之更适于人类的生存,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中国拥有在这方面的完整材料,我们也有能力用考古学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这将有利于世界各国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关系。”(21)
以更丰富的视角观察文明起源,有益无害。对文明最普通的解释就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野蛮包括杀戮、战争,在国家文明产生之前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当然不可避免。但只靠战争和杀戮,人类无法应对自然。通过有组织的劳动,摆脱野蛮,取得更多自然资源,正是人类的进步。例如寺墩水利较良渚发现早;东山崧泽大墓的锛显然是工具;良渚文化的玉钺,难道一定是象征军事权威而非生产劳动的权威吗?那就不一定了。砍伐大概在当时很重要,不仅为了建造,可能还有获得农耕土地、改善环境、防范瘟疫等作用。人类最初的国家文明,应当主要是团结起来应对大自然的产物。人类最后的国家文明,就是进入新的非国家文明之前的高级阶段,或是共产主义“大同”之前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吧,也应是如此。
因此,所有已经取得成绩的各界都应设法调整和超越自己,突出重点,把握性质,扩大合作,去完成这一人类和中国文明探源的伟大跨越,支撑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
收稿日期 2010-03-04
标签:考古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文物论文; 文化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史前时代论文; 遗迹论文; 田野考古论文; 博物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