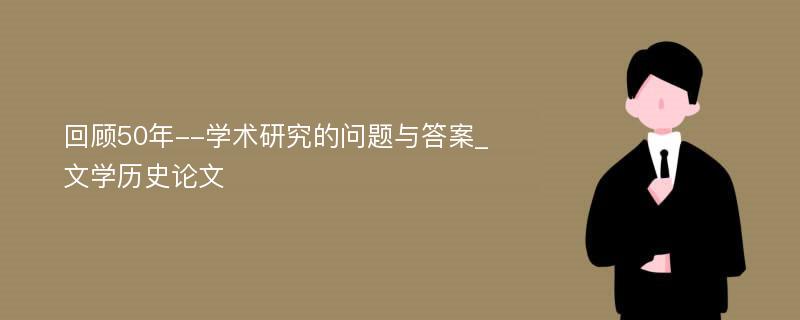
回眸五十年——学术研究答问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研究论文,五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陆先生,请谈谈您的治学经验。
陆:谢谢。“经验”说不上,只能谈谈情况。从1955年起,我开始发表与文学有关的文字,迄今已五十年。新时期以前二十二年,我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与人合著论文集《论〈红日〉及其他》(共收5篇,我写的2篇)等。这些文字,正确和错误参半。正确或言之成理的大多是对新作的评论和相对而言是纯学术问题的探讨,从数量上说占多数。错误的文章,虽只几篇,但性质和影响很坏。我粗暴地批判过胡风同志、丁玲同志、冯雪峰同志,也错误地反对过李何林同志、周勃同志的很宝贵的观点。近二十多年来我在不同场合,以口头或文字形式坦诚地谈及,作过自我批评。而所有被我反对过的同志,无一对我表示不满。胡风同志无一面之缘;雪峰同志,在七十年代中期为《热风》注释曾请教过他,蒙他热情接待。丁玲同志在1980年曾来武大,校长要我致欢迎词。我说,我不宜讲话,如定要我讲,我得先检讨,会引起丁玲同志不愉快的回忆。终于未开口。周勃兄是我的至交,他多次说,我们在五七年是观点不同的同志式的讨论。李何林先生的态度,更令我一生难忘。1975年冬,我将武汉大学中文系我、孙党伯、唐达晖等执笔编写的《鲁迅及其作品》,寄请李先生教正。蒙先生多所嘉许。湖北人民出版社原已拒绝出版,得知李先生给予很高评价后,主动索取李先生信(注:这封信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有关领导传阅未退还我,故《李何林全集》中李先生给我的信,缺第一函。)及我们的书稿。并于1977年11月正式出版。这时,李先生与我并未谋面,但主动向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同志推荐我到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工作。此事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我感激之情更深。新时期以来,李先生和王瑶先生、唐弢先生等前辈学者给了我许多支持、帮助,我在学术上的微小成绩,和前辈学者的鼓励分不开。例如在研究鲁迅与尼采的过程中,王瑶先生命我给北京大学的研究生、青年教师作学术讲演,乐黛芸、严家炎两位学兄陪同。李何林先生邀我到鲁迅博物馆作学术报告,他老人家亲自督促其他同志为我安排住宿,离京那天,他先令司机送我到火车站,然后他才回家。我在搜集新诗史资料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新、老朋友(1956、1957年因我工作需要在文学所借住一年半)都给了助力。上海、浙江、广东、云南、湖北、四川等省、市的不少同志也伸出了援助的手。没有这些支援,要完成新诗史的写作,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能否请先生总结一下呢?
陆:从我新时期前二十多年的教训中,我逐渐拟定了自己从事学术活动的一些准则:第一,从观念上、思想方法摒弃“二元对立”。认识到:对任何事物,并非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往往是多种,经过矛盾、冲突、互融、互补,然后抵达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因此,不能跟“风”,不能轻率表态。结论只能产生在自己认真研究之后,第二,严格区别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的界线,一时分不清的,宁肯作学术问题对待,千万不要将它作政治问题。因为后一种做法会伤害那些最有作为的学者,会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第三,在学术讨论中,对人对己,坚持以理服人,以史实和事实服人。反对以势压人,以众“唬”人。在学术领域,人人平等,谁都没有横蛮的特权,这里不许霸道通行。
记者:我想可以进一步请您谈谈真正的学术研究的经验了。
陆:可能会使您和读者失望,我谈的一部分只是理想,自己也未能做到。
搜集资料,尽管现在传媒已现代化、信息化,但难度仍很大。且不说大的课题,仅就单个作家资料而言,要想达到无遗漏境界,几乎也做不到。《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我得杭州大学郑择魁、陈坚二教授之助,抄得半篇,另半篇迄今未发现,但《新浙江》系公开发行的报刊,也许将来会有人查到。又如徐志摩委托凌叔华保管的“百宝箱”中的文字资料,据凌叔华八十年代初给赵家璧(注:八十年代,赵家璧先生曾将凌叔华女士寄给他的几封亲笔信示我。凌叔华在信中说,有两位著名的女作家分别写信给她,要求把徐志摩日记中涉及她们的部分去掉,信点明二人的名字。因牵涉隐私,故此处亦不便明说。)先生亲笔信,其中有多人隐私,徐氏日记原件恐已毁,估计只能间接推断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集全国鲁迅研究界数百人之力搜集,也不能说,已搜罗无遗。至于写新诗史,我家有三人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除一人只花了近十年时间外,二人集二十五年之功,搜集有关资料,所用岁月,远远超过我撰著的时间。而这,只是资料的主体部分,其他尚有很多需要必须掌握的东西。
理论原则。“新诗史”顾名思义,应坚持“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1](P15)。“史论”很重要,但反对“以论代史”,“论”是不能代“史”的,也“代”不了“史”;我也不同意“以论带史”。历史有它自身运行的轨道,并不按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指令或主观愿望向前发展。
记者:听说您对诗歌流派问题有些自己的看法,请谈一谈。
陆:我在《新诗史·前言》中说过,任何一个流派,都有其他流派的缺失和自己的优长,也有这一流派的特有的局限:任何一个流派,大多数或绝大多数诗人是平庸的,只有少数是优秀的,如果有杰出的,也是个别的;并非有某一流派的特色,就身价百倍。我不太同意现在流行的庸俗的进化论:认为后出现的流派优于先出现的流派,现代主义优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后现代主义又优于现代主义。是的,现代主义有它独特的艺术素质,但同时也失去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所具有的某些艺术魅力。一些诗人在不断变化中,如创造社的王独清由浪漫主义成为比较典型的未来主义,《IIDec》字体和标点符号的特异(注:有时表现为字体和标点符号愈来愈大,有时用象征性的符号作为诗意的表现。),是明显的标志。后来,他又并不坚持未来主义。戴望舒融化了多种流派,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有,艺术营养中外古今都取。
我不以流派定诗人地位的高低。各个流派也不是一成不变。现实主义演变为魔幻现实主义,有了新的艺术魅力。
无论哪一流派,不断地突破,创新,就有光辉灿烂的未来。
记者:请问,研究文艺的人来研究诗,对研究者有新的要求吗?
陆:肯定有。要用诗的眼光去阅读,用诗的心灵和情感去感悟,用诗的种种思维方式去思考,用诗的艺术整体观去把握研究对象、评价研究对象。我在别处说过:文学艺术最富多样,创新、创造是它的生命线,很难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条条框框。就诗而言,有人强调客观重要,有人强调主观的重要。从终极来说,客观是决定性的,从诗的形成过程来说,则主观是决定性,现实主义以外的诗歌流派尤其如此。有人说,情在诗中极端重要,无情无以为诗;但也有人说,诗人对生活和写作,感情应该是“零接触”。有人强调意象、意境重要,认为是诗的核心;也有人疾呼解构意象、意境。有人突出诗中音乐、韵律的地位;又有人主张把音乐、韵律驱逐出诗……。两种或几种不同的意见,都有合理性或合理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有相对的真理。还有,不同流派有不同的诗学主张,不同的审美标准;不能用任何一个流派的审美标准去要求别的流派。对不同流派的诗人,应根据其特点,有不同的要求。
我想,任何一个优秀诗人的诗,总含有民族特色和个人特色(有些人还有流派特色或诗人群特色)。个人特色是艺术魅力的生命线,是诗歌学者研究的重点。
诗史研究和一般的诗评不同。诗歌时评大多不存在“历史还原”和坚持历史观点的问题。而治诗史则处处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时空。现在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胡适早期的诗不像诗,“八不主义”也是袭用美国意象派的某些主张。这种评价最多说对了一半,就是有若干历史事实根据,但错了一半,甚至是一大半。历史上很多革新运动都是受异国某一或某些事件的激发而提出的,美国的新诗运动就主要是受中国唐诗的启迪而提出的(注:参见赵毅衡《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如果说:中国新诗的兴起,主要原因之一是受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那么也不是不光彩的事,甚至也不是罕见的事,因为就前前后后看,无非是“出口转内销”。胡适针对中国诗歌革新的需要,吸收了中外文学革新的经验,确定以语言为文学革命的主攻突破口。实践证明,这是相当高明的战略战术。不管“五四”文学革命受他国何种影响,也未能除去“五四”文学革命的光辉,也不能减弱中国诗歌由旧诗到新诗这一巨变的历史意义。
尊重历史,实际上关系到方方面面,如“九叶派”这个名称,我一向不同意作为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现代主义诗派的代称。这是由于:一、在1981年7 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九人(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的诗选集《九叶集》之前约四十年时间内,从未有过这一称呼;二、这九人第一次同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作品,是1948年6月至10月出版的《中国新诗》,但在该刊1至5期上发表作品的达35人之多。九人中袁可嘉先生仅发表诗二首,而在《中国新诗》上发表二首或二首以上诗的还有方敬、李瑛、马逢华、杨禾、方宇晨、羊翚、鲁岗、孙落、南缨。唐湜先生为圣思(辛笛先生的女公子)编的诗选集《九叶之树长青》写的书评说:“书中除第一辑选九叶的诗外,还有个第二辑选人九人外的诗人们当年发表于《诗创造》与《中国新诗》的部分作品,包括前辈诗人如方敬、臧克家、徐迟、李白凤、金克木与同辈诗友青勃、方平、方宇晨、野曼、林宏、圣野、杨禾、陈侣白、羊翚、邵燕祥、袁鹰、马逢平、叶汝琏、李瑛们的作品各二、三首或四、五首。如果没有出版《九叶集》,而出了册《中国新诗派诗选》,我想,他们都应该是与我们九人一样的成员:其中有几位,如方宇晨,诗的现代风格浓得近于穆旦,……第二辑篇幅不多,却多少可以弥补《九叶集》的不足,遗憾的是没有编入莫洛、汪曾褀的两篇颇有分量的散文诗,少了一个散文诗品种与两个有成就的诗人,两篇成熟的作品。”[2]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唐湜先生后来也发觉,“中国新诗派”的名称比“九叶派”形容一个诗派或诗人群更准确;“九叶派”云云,一思考就可产生许多疑问:从《中国新诗》35位作者中选出九人根据是什么?标准何在?是以诗作的风格相近与否取舍还是以命运相类似感情上亲密为决定性因素?从唐湜先生的上引文字中,作为诗派,他似更倾向于称之为《中国新诗》派。仅从中国新诗作者群这个简单的问题,也可见坚持历史观点的重要,可见回到历史的真实的不易。又如谁最早写新诗的问题。本来问题不存在,没有争议。胡适在1917年2月在《新青年》2卷6号发表《白话诗八首》,形式上基本是五言、七言,旧诗味很浓,不太像新诗。1918年1月15日印行的《新青年》4卷1号发表的胡适(4首)、沈尹默(3首)、刘半农(2首)诗九首,才真正揭开了新诗的序幕。他在1933年12月3日夜写成《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1934年1月1 日发表于《东方杂志》31卷1期。文中说他1915年夏季开始的与任叔永、 梅光迪等就文学革命进行的讨论与争执,并引当时写的不新不旧的白话诗作例证。并说“一九一六年,我们的争辩最激烈,也最有效果。”写了混杂有三、四、五、六、七言、八言的《誓词》。这样,就把新诗的试作推前了两年左右。郭沫若公开发表的新诗,末尾自署的时间整个二十年代及以前,均标“1919年9、10月间作”(《立在地球边上放号》),“1919年9月间作”(《浴海》),“1919年间作”(《夜》、《死》、《Venus》),“1919年3、4月间作”(《新月与白云》、《鹭鸶》)。但1936年9月4日夜写的《我的做诗的经过》突然把自己写新诗的时间提前了三年。他说:
因为在民国五年的春秋之交有和她(指安娜——引者)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辛夷集》的序也是民五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她的一篇散文诗,后来把它改成了那样的序的形式,还有《牧羊哀话》里面的几首牧羊歌,时期也相差不远。那些诗是我最早期的诗……。
民八以前我的诗,乃至任何文字,除抄示给几位亲密的朋友之外,从来没有发表过。当时胡适们在《新青年》上已经在提倡白话诗并发表他们的尝试,但我因为处在日本的乡下,虽然听得他们的风声却不曾拜读过他们的大作。[3](P140—141)
对此,我不禁产生了困惑和疑问:一是《女神》出版于1921年8月, 离最初创作不过二年,而且不只一首(至少有四首!)怎么会记错?二是这和郭与安娜谈恋爱有关,不可能记错。三是为什么到近二十年后,作者记忆变得好起来,一一记得清清楚楚?四是为什么不见于郭沫若先生致任何一位友人的信,也不见于写在1920年1月至3月的谈诗和文学的《三叶集》?因这些疑问,我不敢相信诗人的“1916说”。这不是对谁尊重或不尊重的问题,而是是否坚持科学的历史观。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人说的,而是看符合不符合历史的真实?
记者:请谈谈您关于继承传统接受外来影响的看法。
陆: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每个作家的个性和各方面的素养不尽相同,因此每一个作家如何对待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应由自己决定,应有绝对自由。这与是否爱国不能混淆在一起。爱国志士多有主张文学应以接受外来影响为主者,“五四”时期的鲁迅、郭沫若等大多数文学革命主张者都是如此。划清了这道重要的界线,文学继承传统、接受外来影响问题,作为一个学理就较单纯,容易弄清楚了。从中国历史看,国力强大时,对接受外来影响少顾忌,汉、唐时就是这样;有时是国力羸弱,被迫不得不接受域外影响,魏晋、五代、元时是如此。古老的中央之国,两千年封建一贯制,背离传统、反传统是大逆不道。而从“五四”开始的文学革命,新诗的初期来看,正如我在《“五四”新诗与中国古代诗词》一文中所说:
凡是古典诗词中明显的忠君思想,奴才思想,民族矛盾中甘心作异民族的奴才;家庭与家庭之间关系上,甘心作另一家庭的奴才;个人与个人之间,甘作权势者、富人、强人、能人的奴才;节烈观念、封建的等级观念等,确实“断裂”了,只有个别作品例外。如果说这是“断裂”,那无论着眼于中国,抑或是着眼于世界,都是应该的,是社会发展的必需,是民族生存的必需。而作品涉及爱国、爱情、亲情、友情的抒写时,新诗往往是古代诗词的发展、变异,准确地说,这不是“断裂”。……由于爱情、亲情、友情与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有时无直接联系,往往具有超时空性,因而古典诗词和新诗所抒写的爱情、亲情、友情,并无重大区别。……有些观念,似相近实则相去甚远。如儒家讲仁政爱民,这当然比暴政虐民好;但“仁政”的“仁”,决不会跨过封建制度这堵墙;“爱民”,无论哪一位圣人、贤人,也只爱遵守封建规范的民,只爱服从统治的顺民;不可能爱心怀不满的民,更不会爱造反的民;如果是逆民、乱臣、贼子,则诛之。儒家的仁爱学说与人道主义有联系又有区别,区别就在人道主义主张对一切弱者、穷者都给以人应得享有的基本权利。我们主张爱的纯洁,与儒家所宣扬的“贞”、“节”、“烈”不同,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已讲得很清楚。儒家的尊老爱幼,固然是对老、幼的关照,但因这观念建立在家族制度之上,因而与建立在普泛的人类生存基本权利之上的人道主义有所不同。儒家在对“老”、“幼”的先后轻重上是先“老”后“幼”,重老轻幼。孝子郭巨埋儿,被儒家奉为“孝”的典型。这和现代的进化论以“幼者”为本位的思想是相左的。如果说中国新诗“断裂”了“致君尧舜上,但使风俗淳”的传统,“断裂”了与封建制度、封建思想体系紧密联系的思想乃至伦理道德的传统,实在不是一件坏事,应该说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这一问题,值得中国每一个国民深思,值得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深思。[4]
我自己自然也在深思。鉴于十七年和“文革”中自己不断地跟风跟错了的教训,新时期以来,我在学术活动中,时刻提醒自己警告自己:不要跟风。记得在八十年代初,某刊编辑来就某一事约稿,据说是权威人士的旨意。我和教研室同事都拒绝撰稿。林毓生先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1984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蒙嘱出版社惠赠一本,并希望我写一评介。这本书使中国几乎是一代研究生接受了“五四”文化“断裂”论。我不同意林先生的观点,却佩服他的睿智,评介文字终于未写。这二十几年,我的研究,我的写作,没有违心之举。
关于继承传统与接受外来影响,我觉得研究愈细致愈深入,愈能触及问题的核心。闻一多先生前期大体上是主张“兼取”的。我就翻了翻闻先生喜爱的晚唐杜牧、李商隐、李煜、韦庄、韩偓等人的诗词,发现闻先生的新诗中,融化和借用了晚唐诗人的一些词语,据粗略估计,仅借用的词语,即达100以上,《奇迹》一首诗, 就有“火齐”、“幽怨”、“矜严”、“璀璨”、“一阙”、“藜藿”、“膏梁”、“诛求”、“罡风”、“阊阖”、“户枢”、“砉然”、“綷縩”、“半启”等18个古诗中用过的词。从具体的影响而言,以闻先生最喜爱并自认有些诗受其影响的李商隐为例,李诗中常用的“阊阖”最早见于《离骚》,指传说中的天门,后或指皇宫的正门,或泛指门。闻一多诗中,《李白之死》写道:“阊阖还不开”;《南海之神》写道:“阊阖洞开了”;《奇迹》写道:“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意思似均指传说中的“天门”。“寒雁”在李商隐诗中,似只《野菊》诗中用过:“已悲节物同寒雁”;但李喜用“寒”字,诗中多有“寒花”、“寒梅”、“寒尽”、“寒雪雨更寒”、“寒溪”等词。闻一多的诗,如《闺中曲》说,“寒雁的呼声从伊心中穿过”;《“你指着太阳起誓”》说,“你指着太阳起誓,叫天边的寒雁”;《什么梦》说,“寒雁的哀呼从她心里穿过”,与《闺中曲》极相近;此外,他也在《大鼓师》中用过“寒蕉”,在《你看》中用过“寒溪”,在《长城下之哀歌》中用过“寒梅”。这种影响,都是有形的显性的,无形的隐性的未计。但足以说明,辞汇的继承与创新的复杂关系。闻先生“化用”或“借用”古诗词中的词语,有成功之处,也有不成功之处。“化用”“借用”传统的东西多了,创造性就少了;何况,有些已经没有生命力的词,“借用”到新诗里,既不能使新诗增辉,又不能挽救已经“死去”的词语的生命。闻先生喜用的“寒”字,偶一用之,颇觉新鲜,多次重复就成了陈词滥调了。“阊阖”,可以说是今天人们不再在口语和书面语言中使用的词,闻先生使用后,也没能救它的命。新诗不像旧诗对字数有严格限制,“阊阖”改作“天堂之门”或“天神之门”,也未必逊色。就文艺的继承与创新而言,创新更重要;继承是为了创新。
接受外来影响也切忌生搬硬套,文艺史上只有学徒才依傍大师,照样画葫芦。中国现代如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作者本人中文最高也是初中生水平;英语大约达到中学程度;法文学了一年多,相当于法国小学生,这样的文化水平,要写出较美的象征主义诗歌,简直不可想像。
记者:目前对《学衡》的评价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您有何看法?
陆:《学衡》派反对新诗,谁也改变不了这基本事实。对此,沈卫威同志作了扎扎实实的研究工作。《学衡》派中的吴宓,生前出版的专著很少,发表论文也不多。代表《学衡》反对新诗和新文学的主要是胡先骕,他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和长达二万言的《评尝试集》,就是明证。自然我们也不应抹杀他们也做了一些有益于新文学的事。不过,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学衡》的消极影响,一是《学衡》在全国都有呼应者,吴宓在《新文化运动之反应》中提及、鲁迅在《热风·一是之学说》列举的几种刊物:《民心周报》、《经世报》、《亚洲学术杂志》、《史地学报》、《文哲学报》、《湘君》,都是《学衡》的同盟军;另外,某些反新文学反新诗的高调,与《学衡》的影响不无关系,如1922年在新诗、旧诗争论中,东南大学和南京高师掀起反对新诗的小高潮,有人斥新诗主张者为“一条疯狗”,只是一例。
记者:为了让读者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请谈谈您的诗学观。
陆:诗必然首先是诗,“诗史”必须首先是“诗”之“史”,不能也无法用别的什么取代它。在评价诗人及其作品的时候,在为每一个诗人定位时,力求贯彻这一原则。
诗肯定要表现生活,但它不是或不完全是原生态生活的再现,如同用粮食酿酒,经过了“酿造”的过程。诗总是要抒情的,智性诗作者中的一派主张“零接触”,我感觉也是一种隐性抒情。鲁迅说:“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5](P300) 在朴素的心和情的基础上“诗化”,成为“诗心”和“诗情”。与这类似,一般的“意”(也包含“理”)与“诗意”。一般的语言与诗的语言等,都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回事。其分界线在“诗化”,前者未经“诗化”,严格说来,还在诗的宫墙之外,只是诗的原材料。原材料与成品既有紧密联系,又有重大区别。
衡量诗作和诗学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否有利于诗歌创作和诗学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二者的创新与发展?胡适的新诗,水平不很高,但从创新从新诗萌芽期的发展态势考量,应给以很高的历史定位。李金发的诗尽管有不少毛病,但从创新角度考察,还应给以一定历史地位。所以诗史评价作品应与一般的作品评论有所区别和差异。
作为诗史,不能不触及新诗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我不主张简单机械的“二分法”;认为二者在具体作品中,内容是形式的内容,形式是内容的形式(表现),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如果在理论上对二者有偏至,必然会产生消极后果,故不赞成内容第一、形式第二的规定。比如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写一个日本女郎与异性告别时“一低头的温柔”。内容不能说很丰厚,更不能说有多大的社会意义,但作为一首诗,是很美的,它是多样交融的美,是说不完道不尽、不可把捉、难以言传的美,富诗味,把文字、音乐、绘画的魅力,都充分发挥了出来。如果持内容决定论,对《沙扬娜拉》和一些抒情诗,就难以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也无法解释诗美中的某些现象。如果硬要我表态,我倾向于形式、内容“并重”。每个时间段的诗和诗学,往往有多派多家,也许其中某一、二派有某些优势,但我一般不作“主流”“支流”之分。离文学历史现象愈久,主流、支流愈难确定。“五四”时,新诗只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个别作品有现代主义因素,尚很不成熟。到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形成三分天下的“一分”,如果仍用歧视性的“支流”形容,就欠史家的尊重历史了。不管某一派一家成就多高,优点多么突出,我也不主张以这一派一家为圭臬,去要求各家各派,而期望俯视各家各派,重在注视各家各派的独创性,此外,既注意各家各派之间的差异、矛盾、冲突,又注意各家各派之间的交融与互补,各派各家互有短长,少有一无可取者,也无十全十美者。
从新诗诞生不久,诗坛就有平民化与贵族化之争。我认为二者可以共存共繁荣。诗凭借文字而存在,在古代,识字者多为上等人、权贵,故诗本身就有贵族化倾向。歌主要是口头吟唱,不识字的平民百姓也可参与,歌本身就有平民化倾向。贵族化的诗以精美胜,平民化的诗以鲜美见长,前者偏于雅,后者偏于俗。诗史所载,多为前者;体力劳动者口头流传,几乎都是后者。笔者据实而从,不怀偏见。
在传媒现代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诗歌都面临民族化和世界化问题。作为诗人个人,他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从学理上说:有的重民族化反对世界化;有的重世界化轻视或反对民族化;有的采兼顾并取态度。三者都可说出充足的理论和事实,证明各自主张的正确。我对三种倾向,理论上不置褒贬,评价上据实而论。如对《王贵与李香香》,既不沿袭过去独尊民族化的评价,也不取今日后现代派对它不屑一顾的态度,把它作为民族化的一个典型现象进行剖析和估价。
鉴于曾有长期忽视诗艺的偏向,我尽力向这一方面倾斜。也许因实力不足,心有余而力不逮,那就只有待后人来补正了。
(吉林大学中文系王桂妹副教授记录)
标签: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学术研究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诗歌论文; 九叶集论文; 新青年论文; 诗史论文; 学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