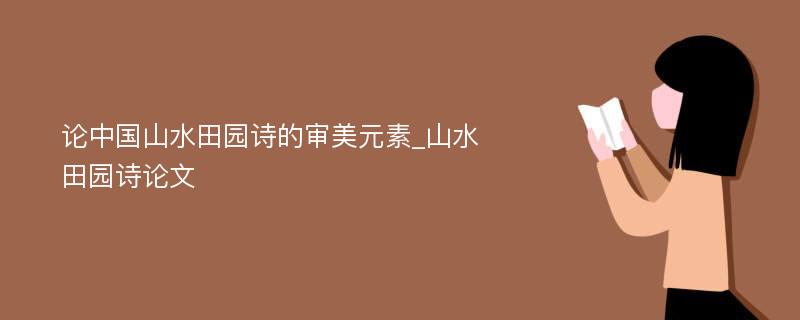
浅谈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审美构成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园诗论文,浅谈论文,中国论文,山水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诗源远流长永不衰竭。不仅有源源不断、新人辈出的创作集团,而且拥有广泛的几近全民性的欣赏队伍,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山水田园诗有着别具魅力的审美构成因素。具体表现为:赏心悦目的感官美;对于精神解放与精神家园追寻的满足;对自我人格的强化和认识;恋土情结的深层实现以及对老庄哲学的认同。
关键词:审美能力 感官美 精神解放 精神家园 古朴 自我人格 强化 净化 峦土情结 老庄哲学
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山水田园诗的诞生要早近十个世纪;而中国的山水田园意识更要追溯到老庄时代,比西方十八、十九世纪发现的自然美要早二十个世纪。在中国文学史上,山水田园不独别开生面,历史悠久,同时更兼有源源不断、新人辈出的创作集团以及广泛的几近全民性的欣赏队伍,而挂在中国老百姓家的山水田园画,以及梅、竹、兰、松扁,栽在门前屋后的竹、菊、兰等,则是这种情形和趣味的进一步泛化。为什么中国的山水诗如此发达和普及?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封建文人醉心于它的创作和欣赏?它究竟美在何处?是什么因素在激动人心?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求我们把目光投向山水田园诗的审美魅力的构成上。我们以为,山水田园诗的审美构成因素有五:
一、赏心悦目的感官美
在物我感应的关系上,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一段形象而精辟的描写说明不同的景物使人产生不同的情感波动:在天昏地暗,阴风怒号、阴雨连绵的季节登上岳阳楼,涌上心头的是离开故乡,怀念家乡,担心谗言,害怕诋毁的情绪。举目一片萧条冷落,让人感到无限悲凉。而在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时候,湖上风平浪静,天光水色在万顷波涛上连成一片,此时登楼,便觉得心情开朗、精神愉快,可以暂时忘记一切荣誉和耻辱,当风举酒,喜气洋洋。在这里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残破黯淡的景物,给人的是悲凉冷落的感受,而明朗优美的景物,则让人心旷神怡,赏心悦目,给人愉快轻松的感受。而山水田园诗所着意展示的主要内容,便是自然界一切美好壮观的事物,是自然的清新和纯朴,无限的生机和无穷的活力,无比的和平宁静和无尽的姿彩变化……是“林泉高致”、“云霞奇趣”、“山水清晖”、“泉石清音”,总之,它将自然美着意展示给我们。谢灵运道出了此间的真谛:“山水有清晖,清晖能娱人。”——大自然的清新纯朴,富丽活力,能让人愉快激动和悦起来,给人带来身心感观的美。放眼蓝天,让人心旷神怡,神思飞扬;触目高山,让人肃穆、肃然起敬,涌起庄严神圣的情感;放眼旷野,让人心胸开阔,豪情万丈;纵目大海,让人心潮澎湃,热血奔涌。而山水田园诗描状的画面,首先带给我们的也正是这种表层的感官的美。
二、对精神解放与精神家园追寻的满足
文明的每一次进步,总是伴随着道德的每一次堕落而实现的,也就是说,文明的进化是以道德的堕落为代价的,这是马克思的论断。与之相适应的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命题:文明的进化程度越高,人的异化的程度就越严重。人类社会的历史残酷地印证了这两个论断:社会越发展,人与人之间越发难以沟通,越发现人群对自己的陌生,名利的角斗越发冷酷无情,人伦亲情越发淡薄。在科技方面,人类创造了最先进的机器,而自己却荒唐地成了自己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人发明了时钟,随之变成了按部就班的人;人发明了机器,随之变成了机器的仆人,终日守候在它的身旁;人发明了交通和高速公路、交通规则,便从此永远失却了行走的自由;人发现了价值观念,随之便终身背上了沉重的功名利禄的包袱……在日益文明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反倒更加感到孤立、冷漠、无助、焦虑,感到层层压迫和不自由,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远古,产生了强烈的返朴归真的渴求。因为在那里,没有欺诈,没有压迫,没有做作和拘束,而有的只是纯朴、自由、平等、和平与宁静,就像陶渊明的《桃花园记》一样。而山水田园诗着眼于青山绿水、泉石清音,漾溢的是自然之趣,回荡的是古朴之风,展示的是天然自成、未经污染的大自然,这里,没有文明的足迹,没有人间的烟火,人处其中,只有纯朴、自由、平等、安全,而这恰恰投合满足了文明社会中文明对精神解放的需求,成了文明人的精神家园。这种情形具体表现为:当作者在创作,读者在欣赏山水田园诗时,一时间都会浸淫其中,沉醉于山水云霞,在自然的清新古朴之中,洗涤灵魂的污垢,卸下精神的重压,远离尘世的喧嚣和烦恼,得到身心的和悦轻松,精神的升华和自由。
三、对自我人格的强化和认识
在确认山水田园诗的主体色彩上,中西方文艺理论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西方文化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山水风物描写,都已不再是纯粹的客观的山水风物了,而是作者主体精神和人格投射的结晶体,呈现出物我一体,主客交融的态势。清代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大师王国维认为:意境可划为两类: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从这里,我们可以集中抽象出一点:“一切景语皆情语”。在一切景物身上,都有作者人格的烙印,精神的孕含,情感的寄托,是人化了的自然——这显示着人,折射着人,或象征着人。这样,景性物性便成了人性的象征,景心物心就成了人心的写照,这只是部分抒怀言志山水田园诗倍受青睐的奥秘所在。因为,对作者而言,可以借山川风物寄托自己的志向,抒写自己的灵性,外化内心深处的主体形象,使自己对自身的状态有进一步的体认,进而得到强化,而对有类似身世感受的读者而言,通过读诗,唤起内心类似的感情,进而和作者达到共鸣,从而实现了对此类感情的确认和强化。例如:曹操《观沧海》一首,文面意义是写大海的壮阔、雄伟、吞吐日月的怀抱和包揽宇宙的气魄,而深层意义却是作者本人人格、胸襟、气魄的象征。
与这种情形意绪相通但形式相异的,是中国人对山水画卷和君子五友的厚爱。仔细体察,我们便能悟出个中三味:堂中挂着《芙蓉山水》等清秀画卷,盆中养着兰花芝草的主人,大多是素雅好静、趣味高超的人;堂中挂着梅、菊等画轴、屋前栽着竹子、菊花的主人,大多是坚韧不拔,注重气节贞操的人;堂中挂着虎豹画轴,房前屋后栽着松柏、柏杨的主人,大多是心情高傲、威猛势豪、气概超群的人。因为,在画轴花草上,不仅体现出主人的审美趣味,更体现出他对某些品质、理想的肯定和充分追求,可以说,主人栽树挂画,事实上是在树立自己、显示自己,用含蓄的方式肯定自己。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山水田园诗人是在用山水田园诗树立自己,显示自己。画自己,用诗的方式肯定自己,因为诗是诗人人格的写照。正因为这样,后人评价《观沧海》是对曹操的穷形尽像;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是陶渊明的形神写照;“诗的孟浩然”,则是对孟浩然的最准确的把握。
四、恋土情结的深层实现
关于人的由来,东西方神话的解释殊途同归。在西方的神话中,上帝在创造了光明日月,天地万物之后,发现美中不足的是一个明媚美丽,生机勃勃的世界竟缺乏管理者,于是在创世的第六天他用泥土创造了人,这人本来应该长生不死,就是死了也该进天堂的,但由于犯下了原罪,就被上帝惩罚必死,而且死后也要埋进泥土。而在东方神话中,也是用泥土造人。人类始祖女娲开始用黄土造人,速度太慢,于是改用长绳抛进泥土中抟人。而人在百年之后的归宿也是泥土,汉语雅称“赴黄泉”。拂去神话的臆想色彩,在这两则神话之中,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个共同的命题;人来自泥土,终将归于泥土,泥土是人类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这里沉淀着人类对于土地的无限深厚的崇拜,热爱和依恋之情。这种感情随着历史的绵延,慢慢地凝结成人类的恋土情结——人类的一种心灵结构、情感郁积,或者可以说是人类的特性。(现代心理学称这种情结为历史心理沉淀,马斯洛称其为史前意识或集体无意识。)这种情结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随着历史遗传而代代相因,挥不去,抹不掉,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每一个人,一经触动,随时随地发挥作用。
恋土情结的实质在于人对“土”的无可逆转的本能热恋。人类对大自然何以有这种强烈、深厚、本能的情感呢?原因在于:
(1)人类来自大自然,大自然是人类古老的家园,大自然孕育了人类,又养活着人类,承载着人类,又保全着人类,人类最初的记忆和感情就是关于大自然的。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与生俱来,最悠久、最直接、最深厚、最柔密,大自然是人类的摇篮、母亲。
(2)人类是大自然的一分子,而大自然中的天地万物曾是人类亲密的朋友和伙伴。
(3)与古代的农业特征有关。作为一个农耕民族,山村田野是其养育之母。如果说在长期的劳动与生活实践中,自然变成了人化的自然,那么,人也就相应地变成了自然化的人,也就是说,人对自然具有一种自然的本能的需求。
而山水田园诗所触发的正是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古老记忆,满足的是人类渴求接近、回归大自然的愿望,从感性的最深层实现了人对恋土情结的激活和满足。具体情形表现为,当人们创作或阅读山水田园诗作时,便仿佛回到了古老的家园,童年的时光和母亲的怀抱,同时便回复了赤子之心,那种亲切、满足、愉悦是不言而喻的。
五、对老庄哲学的认同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思想和灵魂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儒家倡导积极入世,奋发进取,建功立业。而道家则告诉人们清静无为、自然淡泊、回归自然。儒家倡导进取、执著,“知其不可而为之”;[1]而道家提倡放弃、退隐、听天由命,“其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2]儒家的社会理想是天下大同,“老有所养,幼有所教,壮有所用,”[3]人们知仁守礼,而道家的社会理想则是纯朴自然,浑沌未开的小国寡民,人们“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正因为有以上的差别,所以,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的时候都要儒家,而在失败的时候则是道家。儒家和道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个方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则是对这种情形的最好的注释。由此可见儒家和道家对中国人影响的深远。这也深深地影响到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和欣赏。它既是人生战场失败或厌倦之后的一种退避,又是一种新生活的开始。人们为了保持自己身心的自由,在山水田园等政治之外一切美好的东西中去发现人生,发现生活的美好。
以上五点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魅力所在,是它深得创作者和欣赏者青睐的根本原因。
注释:
[1]见杨伯峻译注:《论语泽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7页。
[2]见《〈十大古典哲学名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见陈澔注:《礼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0页。
[4]李耳:《老子》,见《〈十大古典哲学名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