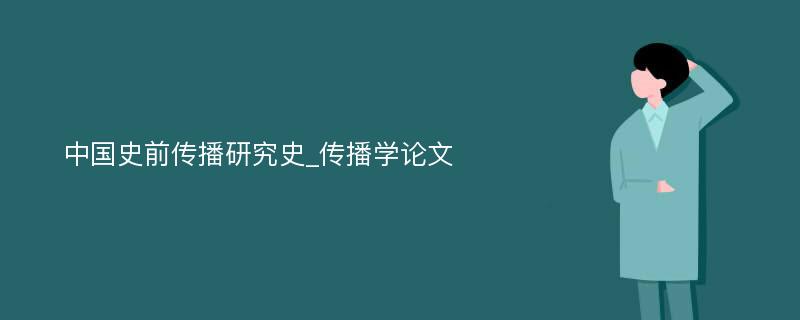
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前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传播”还是“交通”?
起源神话的作用在于通过建构历史,为当下的正当性提供护身符。中国大陆的传播研究自1978年的新闻学界开始,这是目前传播学界普遍接受的主流叙事。①因为传播学是在这一时间点正式从西方,确切地说是美国,引进到中国的(如未作特殊说明,本文所说的中国均指中国大陆),因此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便有理由以横空出世、截断众流的方式加以叙述与组织。为了让这一叙事自圆其说,便会对一些令人感觉“不方便”的事件做特殊处理。比如20世纪50年代,复旦大学的郑北渭等人已经使用了美国传播研究的个别概念。②为了强调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史实被处理成孤立的事件。论者会以当时将mass communication翻译成“群众思想交通”等事实为证据,说明那时的认识如何模糊,反衬20世纪70年代末正式引进传播学后对西方传播研究的理解才真正登堂入室。
包括笔者在内,一直以来都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常识”。但是如果仔细推敲,这段主流叙事存在两个疑点:(1)在1978年这个节点上,中国学界所说的“传播学”究竟是哪个传统的传播学?(2)“思想交通”这个概念究竟是凭空杜撰,还是另有所本?如果是后者,来自何处?
关于第一个问题,近年来已经有一些研究指出,早期中国新闻学者对于传播研究的理解曾堕入一个“学科陷阱”。为了和“新闻学”相对应,他们将相对模糊的“传播研究”想象成有严格建制的、具有普遍性的“传播学”。③当时对舶来的传播研究的理解是去历史的,认为世界各地都有传播学,而未认识到作为一个学科建制,“传播学”并不是一个普遍现象。④而且因为人际网络的缘故,施拉姆的弟子余也鲁和大陆学界的交往,使中国学者较早地接触了施拉姆及其著作,因此以传播的5W为理论框架,以四大奠基人的研究为历史线索,以量化的行政研究为主流的传播学科占据主导地位,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的引入便成为中国传播研究的起点。凡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传播研究,被遗忘在“传播学”之外。不少具有反思性的学科史研究,也默认了这种说法。这个框架限制了我们对中国传播研究史的理解,导致我们对施拉姆版传播学以外的传播研究在中国的接受与扩散甚少关注甚至视而不见。
关于第二个问题,近来也有突破。黄旦曾提出,1978年之后中国学术界所建构的“传播”概念,其实不是英文中的communication,而是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⑤这个解读很有启发性,然而问题似乎还可以再向前延伸:这一“误置”是否只发生于1978年之后?中国是否一直缺乏双向互动的communication概念?
考察清末民国时期的文献,就可以发现“传播”一词早已有之,只不过它对应的是“传布”、“流布”、“传达”、“扩散”之类的单向撒播(dissemination)概念,其中不少是基督教会和医学、生物学、农学所用,这倒是和黄旦所说的1978年后对“传播”的理解接近。比如1919-1921年杜威在华演讲的中文翻译中,“传播”二字便经常出现,像“传播知识”、“激烈思想的传播”等,均是单向的对大众的扩散之意。⑥1930年,为了规范社会学概念的中文翻译,孙本文发表了《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一文,其中将diffusion定名为“传播(或播化)”。⑦所以这个“误置”并不是传播学引进之后才出现的,而是早已有之。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20世纪初期中国就没有真正的communication的观念。只不过晚清民国时与西方communication对应的概念是“交通”而不是今天的“传播”。那时的“交通”还不是一个不可分的合成词,而是“交”(交互、交流)与“通”(相互联接)两个词的并列。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用法,它甚至比“传播”更接近communication的本意。《辞源》上有类似的解释:
交通:互相通达。管子·度地:山川涸落,天气下,地气上,万物交通。陶渊明:《桃花源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⑧
在杜威的中国演讲(1919-1921)中,communication有时被翻译作“交际”,有时翻译作“交通”(如“减少各种因隔绝交通而发生的弊病”)⑨。社会学家林耀华在介绍芝加哥学派的大师罗伯特·派克(现译作“罗伯特·E.帕克”)的理论时提到:“盖人有社会嗣业,从交通(communication)造就而成,又从交通传递而来;社会之生命及其连贯,全视乎前代之民风、教化、技术与理想能否传于后代,然交通厥为社会互动之灵媒(communication as the medium of social interaction),于是文化造就与变迁,又皆从社会互动次第递演而产生……”⑩)帕克在华讲义中译本中也有这样的表述:“社会生活必须有交通和交感,若只有互相刺激,只有身体接触,那不是我们所谓的‘社会的’。”(11)“(新闻)若不具重要性,就不能交通,也不能传播。”(12)前面提到的孙本文的《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一文中将communication定名为“交通”,intercommunication定名为“互相交通”。(13)帕克访华(1932年)后,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编了一本论文集,在文集末尾专门制作了一个中英文的译名对照表,其中的communication译作“交通”,interaction译作“交感、互动、交互作用”,反而是acculturation翻译作“文化传播”。(14)可见最晚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界不仅已正式引入了“communication”的概念(译为“交通”),而且将它与后来类似于大众传播的“扩散”(译为“传播”(15))相区别。
同一时代的中国新闻研究者也使用“交通”来表达communication的意思。比如高海波对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27年版)的语频做过统计,发现其中出现了37次的“交通”一词多数与communication的意思接近,而出现了18次的“传播”则是单向的“流布”、“扩散”之意。(16)如果抛弃communication理所当然应该翻译成“传播”的刻板印象,再来看上世纪50年代郑北渭等人翻译的“群众思想交通”,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全无根据的杜撰,而是有其思想传承的。
再回到黄旦提到的那个问题,就很清楚了。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学者对(单向的)“传播”与(双向的)“交通”便有明确的区分。前者仅指单向的大规模的扩散,后者则含有双向交流的意义。因此对“传播”的误置不是从来如此,1978年后之所以出现“误置”,只不过由于下文所说的种种原因,发生学术传统断裂,这一精致的区分被学术界集体遗忘了。
“交通”概念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窗口。在语言和概念的发生阶段,一切处于模糊状态,范畴的界限模糊,语言还未能充分对象化。在这里,语言与我们遭遇,启示和改变着我们。此时表述与经验的关系浮动多变,孕育着丰富的可能性。(17)以此为突破点,考察由“交通”产生的话语,复原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可以认识20世纪初的传播观念与传播研究,重新检视中国传播研究的“起源神话”和集体记忆,为今天传播学科建制的诸种弊端找到问题的症结。
社会学传统的传播研究
20世纪初期,西方传播研究进入中国,主要通过两个传统:一是社会学传统,二是新闻学传统。但是遗憾的是,这两个传统都在50年代之后被截断。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对传播问题的研究最早是在社会学者中展开的。中国的传播研究,也随着西方社会学进入中国,先在社会学中生根。20世纪初期,美国在处理中国的事务中,理想主义占上风,率先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高等教育,教会与基金会也大力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美国社会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中国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是美国社会学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由于美国早期的传播研究主要在社会学家中开展,所以它们顺理成章地通过社会学的潮流,流入中国。
20世纪初期,美国传播研究的重镇当属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这个集合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学派也被公认为美国传播研究的发源地。除了查尔斯·库利(但他深受杜威、米德的影响)外,其主要人物杜威、米德、帕克、伯吉斯等均在芝加哥大学有相当长的任教经历。这群学者尽管理论取向和观点不尽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研究兴趣:强调传播对于个人及社会的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认为传播在形成人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认为它对于社群的形成和社会的民主自治起着关键作用。(18)因此,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便成为中国早期传播思想引进中的主旋律。这其中最重要的事件当属杜威和帕克的来访。
按照贝尔曼(Sheldon Lary Belman)的总结,传播问题是杜威的思想的基础,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人类理智和社会的起源问题;(2)人类联系(社群)的理想类型的社会哲学问题;(3)美国民主的问题诊断和解决方案。(19)但是他在中国的演讲很少涉及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主要集中在第二个问题。
杜威在中国做了不下两百场演讲,且社会影响巨大。《晨报》社编辑的《杜威五大演讲》到杜威离华时,印刷13次,每次印数都在1万册以上。(20)考虑到当时的识字率,这个数字实在令人咋舌。据现在留下的记录来看,杜威在华演讲中数量最多的是关于教育的演讲。(21)杜威在华期间与其关系最密切的胡适也有同样的印象。(22)从杜威1919年以前发表的论著数量来看,教育问题确实是他当时用心最多的话题。他集中讨论第(1)个问题的主要论著(如《经验与自然》、《作为经验的艺术》等)还要在若干年后才问世。其次,鉴于中国当时对西方理论的陌生,杜威的讲座大多是在做知识普及,对于传播与人类本性这类较专门的问题还未来得及介绍。同时,杜威对中国的影响也与陶行知、胡适等杜威的中国弟子的学术兴趣和关注点有关,他们的中介与阐释也有意无意地影响了“杜威博士”在中国的形象。比如陶行知大力强调杜威的教育哲学,而胡适则弃杜威丰富的哲学议题于不顾,专注于利用杜威的实验(用)主义来为自己的研究方法寻找正当性。
杜威抵华时(1919年4月30日)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民众对于政治正义的诉求让政治哲学问题凸显。这个古老国度里学生和民众的民主政治运动也令杜威感到意外,中国民众的理想主义和热情使他意识到中国可以成为自己政治学说和政治理想的实验室。他的演讲中关于民主政治的内容仅次于教育问题。因此,在杜威关于传播的理论中,最直接地被介绍给当时中国人的是政治哲学中的传播观念,这也是这个时期杜威正在思考的问题。杜威晚期(1925-1953)的研究中,传播与公众的形成问题是重要的主题。
他在演讲中提出,所有看似是国家和个人的冲突、社会和社会的冲突,其实都是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冲突。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缘自群体的利益与兴趣的差异。因此,所有社会冲突都是可以解决的,过去那种一群人压倒另一群人的做法会让社会更加不稳定。要解决这些冲突,首先就要研究人性的需求。他把人性的需求总结为三点:(1)风俗习惯、(2)社会体制和(3)共同生活。其中第三点最为根本,前两者都是为了达到第三种理想。杜威对共同生活的定义便是自由交际(communication)、互相往还、交换感情,交换种种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定义体现了杜威以及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和社会交往的重视。
杜威所说的这种共同生活,是建立在自由交流的基础之上的。“社会一定使各分子有自由的发展、自由交换、互相帮助、互相利益、互通感情、互换思想知识的有机社会;社会的基础是由各分子各自能力自由加入贡献的。在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太强固,实在是强固得很;不但强固,并且可以减少各种因隔绝交通而发生的弊病。”(23)
杜威在中国的演讲中,向听众明确地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传播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社会整合至关重要。他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传播的社会功能。当然,这时他的认识与他1927年在《公众及其问题》中谈到的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其中的核心观念已经在中国演讲中得到清晰地表达。他对于传播与民主(民治)的看法也为中国一批学者(多有海外留学背景)所接受,在1929年以胡适、罗隆基为首的一批新月派人士对国民党训政体制的批判(后收入胡适1930年编的《人权论集》)中,便可看到大量类似的观点。(24)
早期的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进入中国的过程,可以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来形容。当时没有“传播学”这门学科,甚至连研究者也是在一个更大的学术背景下进入传播问题的。杜威把传播问题夹带在“政治哲学”中,帕克则把传播问题嵌在了“集合行为”这个题目之中。所以传受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些引介对于中国传播研究的影响。
罗伯特·E.帕克对于传播问题的关注,主要缘于以下契机。一是他11年的一线新闻工作经验所导致的他对新闻本身的研究,比较著名的是对新闻自然史的研究和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新闻的分析。(25)二是由上一问题引申出的新闻的社会功能的研究。这个题目在城市社会学和社会整合的背景下展开,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移民报刊及其社会控制的研究。(26)三是在社会群体及集合行为研究中涉及的新闻、流言、个人意见、公众意见的关系,重点讨论了群体中传播机制对群体意识和行为的影响。(27)
与杜威类似,中国听众的预期使得帕克没有能够完整地阐述他对于传播问题的看法。1932年9月到12月期间,他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授了两门课程,一是《社会学研究》(Soc.149-150 Seminar in Sociology,高年级研讨课),二是《集合行为》(Soc.143 Collective Behavior)。(28)因为听众是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所以关于新闻的研究不是主要内容,只是在集合行为的讲座中,涉及到了新闻对群体意识的影响、群众与公众的区别、公众意见的形成原理等大量当代政治传播的研究话题。(29)这些话题也是当下热门的社会运动领域仍然关注的问题。
除了来华讲学的杜威、帕克外,芝加哥学派中对传播有专门阐释的查尔斯·库利(柯莱)的学说,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学者而言,也不陌生。(30)
中国社会学者对传播问题的探索
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初处于鼎盛时期,他们的传播思想随其社会学、哲学、心理学思想一起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当时在美国刚刚出现的社会心理学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也为中国学者所关注。
中国心理学史的先驱之一高觉敷在1941年编写了《宣传心理学》(31)。在这本书中,高觉敷引用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结果,介绍了宣传心理学,也介绍了宣传的应用与不同媒介的宣传技巧。这本书诞生在抗战期间,社会环境促成了传播研究中工具理性很强的宣传研究在第一时间进入中国。美国1937年成立了“宣传分析学会”(the Institute for Propaganda Analysis),其中最著名的成果是李夫妇(Alfred McClung Lee and Elizabeth Briant Lee)1939年出版的《宣传的完美艺术》(32),这本书提出的辱骂法、光环法、转移法、证词法、平民百姓法、洗牌作弊法、从众法等宣传技术,在高觉敷的书中有较详细的介绍。彼时美国心理学界开展宣传效果研究的时间也不长,可以说,同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界在引进美国最新的传播研究成果方面,几乎与后者同步。这种状况与1978年后中国新闻学研究者对西方传播研究的陌生形成鲜明对比。
心理学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较早地接受了统计学的训练,因此社会心理学家也是中国最早严格进行民意调查(测验)的群体。1922年,在北京高等师范任教的心理学家张耀翔利用该校成立14周年的机会,对来宾进行了非随机调查。(33)尽管该研究的抽样并不符合民意调查的要求,但是罗志儒使用张耀翔调查数据所做的分析却可圈可点。除了之前的单变量描述之外,还进行了双变量的交叉分析,试图探索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文章最后还对数据和问卷中存在的问题作了探讨,展示出了科学严谨的态度。(34)到了20世纪30、40年代,民意测验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已经相当普及。(35)
除了引进西方的传播研究外,中国的社会学者也进行了原创的传播研究。就像西方早期的传播研究者一样,他们在从事传播研究,却没有今人的传播学学科意识,甚至不会承认自己是在从事“传播研究”。孙本文被公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36),但是他的博士论文《美国报刊中的中国:报刊揭示的美国对华公众意见的基础及趋势》(1925年)却是一项典型的传播研究。(37)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研究可算中国当前数量多至泛滥的国家形象研究的滥觞。
这篇文章研究了两个问题:(1)美国人从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公众意见的基础);(2)美国人通过媒体表达了对中国的什么看法(公众意见的趋势)。孙本文接受了李普曼等人的观点,认为美国的公众意见由少数精英决定,大众媒体在公众意见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他认为,虽然面对同样的信息,美国人的反应并不完全一致,但意见是信息加思考的产物,普通人的意见会以这些信息为基础。因此通过统计美国媒体中关于中国的报道,便可以了解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通过研究美国媒体中的言论,便可推测美国公众对于中国的看法。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孙本文通过内容分析和文本解读的方法,统计了美国报刊中涉华报道的总量和主题分布,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项,并进行了横比和纵比。他发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数量较少,多集中在政治方面,经济与文化方面较少。与其他国家(英、俄、德、日、意、法)相比,关于中国报道的数量排在第6位,仅高于日本。当然,美国媒体的国际新闻总体数量也很少。纵向看,1900年是转折点,之前美国媒体对中国兴趣不大,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影响,其后关于中国的报道有所增加。
除了对新闻进行量化内容分析外,孙本文还以排华条约、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华盛顿会议几个典型事件为例,用类似今天文本解读的方法,分析了美国主流报刊对华言论的分布与框架(当然,他没有用这个概念)。他的总体结论是,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和言论,都是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简单的有闻必录。
尽管现在看起来,这个研究在方法和理论上都显得很原始,结论也平淡无奇,甚至今天作为硕士论文都不一定能顺利通过,但是如果考虑到它写作的时间(1925年,李普曼在此前三年才出版《舆论学》,要到1927年拉斯维尔才出版《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就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其实直到今天,中国大部分所谓国家形象和外国对华报道分析的研究,基本思路还停留在这个层次。对中国传播研究来说意义重大的是,它意味着中国社会学者在20世纪初期也曾对传播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并且愿意将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38)如果我们仍然固守着施拉姆的“传播学”的学科框架不放,便会忽视类似的重要思潮与证据,抽掉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语境和传统。
新闻学传统的传播研究
由于美国的传播研究最早兴起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中国的新闻学界反而对这部分知识缺乏应有的关注。而1978年之后,中国新闻学界对于美国传播学的兴趣与热情显然超过了中国的社会学界。这种前后冷热迥异的态度值得注意,此问题留待后面再详加讨论。
尽管20世纪早期中国的新闻学界对学术性较强的传播基础理论研究缺乏关注,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与传播研究就完全绝缘。与新闻有密切关系的宣传研究及公共关系研究也引起了新闻学界的注意。他们从另一条路径也接受了美国传播研究的部分成果。
1932年曾留学日本,后任职朝鲜领事馆的季达出版了《宣传学与新闻记者》一书。(39)他从外交实践出发,论述了宣传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此书在宣传学部分介绍了西方20世纪初期关于宣传研究的主要成果,并且对于1927年才出版《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的拉司维尔(现译为“拉斯维尔”)亦不陌生。这些积累在20世纪50年代后完全中断,1978年后新闻研究界才知道这本书,直到2003年才有中译本。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主任(1934-1937年)梁士纯1934年在燕京大学开设“实用宣传学”课程,并出版《实用宣传学》(1936年)。他可能是最早在中国大学开设宣传及公关方面课程的学者。(40)梁士纯认为,宣传“就是要把一种消息或意见陈布于公众之前,藉以左右他们的主张或行动的一种力量”(41)。他所说的宣传概念接近于英文中的publicity。他不仅认为宣传是一种中性的手段,并无善恶之分,而且提出宣传必须要以事实作为基础。梁士纯所说的宣传概念大致等于现在所说的公共关系,它赋予了这种宣传以积极的意义,认为这是社会现代化的表现,并能促成社会进步。(42)
从全书的结构和核心理念看,梁士纯的宣传观念受爱德华·伯内斯的影响很大。伯内斯是美国公共关系理论的奠基人,早期曾使用过“宣传”来指称后来的“公共关系”,并出版了《宣传》一书。(43)一战后宣传概念具有了负面色彩,专业的公关从业者已经倾向于不用这个概念指称该行业。但是在中国,为了动员全民抗日,“宣传”一词反而成为流行词汇,并具有了正面的感情色彩。
梁士纯相信在战争时期,宣传会发挥巨大的团结作用。他认为战争时期“统制”舆论具有两个途径:(1)检查——消极的,(2)宣传——积极的。这两者之中,“统制或操纵舆论最有力量的工具还是宣传”。舆论(公众意见)是宣传的关键概念之一。梁士纯对李普曼并不陌生,他对舆论的定义便沿用了李普曼的定义,以为舆论就是由大众的刻板印象形成的。受到精英主义视角的影响,他在讨论舆论时经常使用“统制”、“操纵”等词。
断裂与延续
以上史料尽管挂一漏万,但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两个印象:(1)1978年前,甚至1950年代以前,中国就已经引入了西方的传播观念,只不过没有用当前的“传播”二字,而使用了“交通”一词。(2)20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不仅熟悉西方(主要是美国)刚出现的传播研究成果,而且自己也朦朦胧胧地开始了传播研究。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传统后来中断了。
这就引出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1)为什么20世纪初的传播观念和传播研究会发生断裂?(2)为什么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历程会从新闻传播研究者的集体记忆中消失?
第一个问题让人想起美国传播学者伊莱休·卡茨前几年提出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社会学会抛弃传播研究?”(44)无独有偶,在中国早期的传播研究中,社会学也充当了实验田的角色,而真正让传播学开花结果的,却是新闻学。至少从表面上看,这一过程与美国的传播学发展轨迹惊人地相似。当然,他的问题与回答都基于美国的语境,他在自问自答中极力为哥伦比亚学派辩护,反指责社会学家缺乏耐心、贸然离去,这一观点也未必得到所有人的赞同。(45)
如果在中国提出卡茨之问,答案可能完全不同。中国社会学家之所以会离开传播研究领域,首先反映了美国传播研究范式的转变。无论是中国近代的社会学,还是“文革”之后的传播学,都是舶来品。20世纪初期对中国社会学影响较大的芝加哥学派,其时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也如日中天。很自然,芝加哥学派对传播问题的强调也随着当时流行的社会学思潮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国社会学的早期研究者。因此,在20世纪初期,社会学者成为中国传播研究的主力军。
但是随着美国传播研究范式的转变,哥伦比亚学派逐渐取代了芝加哥学派的统治地位。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多个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比如有限效果理论的提出导致社会学家对传播的功能失去兴趣,研究基金的兴趣转向工具性的题目,以民意调查、市场调查为代表的注重短期效果的应用性研究取代纯学术研究,新闻学科接管传播研究后将其学科化与体制化,排除了其他学科的介入等等。这些原因在卡茨和普利的文章中均有讨论,这里不再赘述。至于这些解释是否充分,另当别论。但是至少从表面上看,在20世纪40、50年代间,对中国传播研究影响最大的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确实经历了由芝加哥学派向哥伦比亚学派的范式革命。施拉姆所包装的“传播科学”便是新范式的胜利宣言。
因此等到中国学界结束了政治运动导致的中断与空白期之后重拾传播问题时,面对的已经是改头换面之后的传播研究。后者把新闻院系作为拓殖的主要目标。施拉姆来中国推销他的传播学时,便主要在新闻系活动,不再关注社会学领域。因此传播学在中国的命运,反映了美国传播研究学术场域的重大转型。
第二个原因与中国社会学自身的命运多舛有关。早期的社会学研究直接受到西方影响,教会学校甚至仿效美国办学模式,人员交流频繁,在理论资源方面几乎可以做到与美国同步。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学科调整和院系改革过程中,苏联高等教育模式一统天下,社会学被批判为鼓吹孔德的改良主义,与主张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水火不容,遭到取缔。(46)社会学被腰斩导致这一传统下的传播研究被迫中断。1980年代社会学恢复后,补课和现代化建设成为主流,社会学领域的传播研究被边缘化。再加之新闻学的介入,中国的社会学者遂与传播研究渐行渐远。由于今天传播技术对社会的深远影响,这一相互隔绝的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社会学与传播学之间的学科藩篱仍未打破,传播问题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并未恢复到20世纪初期的状态。
第三个原因恐怕与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传播产业不发达有关。传播对芝加哥及美国其他地区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影响促进了芝加哥学派对传播问题的关注。他们观察到了蒸汽船、蒸汽火车对芝加哥城市亟速扩张的影响,也经历了大量移民导致的文化冲突、传播不畅、社会整合滞后等城市问题。因此,广义的传播(既包括交通运输,也包括思想的交流)理所当然成为他们研究社会时的中心问题。(47)哥伦比亚学派对于传播问题的关注则缘于商业传播产业(主要是广播)的高速增长和民意调查产业的兴起,这些行业催生了对工具理性式研究的增长,基金会和商业资助对研究课题的左右加剧了这一趋势。(48)作为一个与现实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学科,美国传播研究的两个传统都受到社会环境的直接影响。相比之下,中国的传播产业一直不甚发达,社会动荡和经济落后使得传播技术的影响局限于少数沿海大城市。1949年后情况虽然有所改观,但宣传的需求超过了商业需求,再加之国家对媒体的绝对垄断,传播研究的动力依然不足。20世纪初期社会学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城市底层问题、农村问题和社会现代化的问题。和社会学关注的其他问题相比,传播问题便显得次要得多。社会学在1980年代恢复以后,短期内情况依然如此。传播研究便被“发现”传播学的新闻学划为势力范围,断裂由此加剧。
新闻学领域发生的断裂则主要缘自政治原因。因为强调新闻研究的意识形态属性,非马克思主义学说均受到猛烈批判。少数对新兴的传播研究有兴趣的学者被迫只能从事私人阅读和思考,无法公开交流。
然而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正在于它具有顽强的延续性。外在的、人为的断裂与库恩提出的范式革命或福柯所描述的知识型的转换不同。它表面上切断了与传统的联系,但是并不能阻止政治大潮下的暗流涌动。那些之前因为机缘巧合受过西方社会科学影响的中国学者在相当长的“断裂期”中依然顽强地保持了对西方学术发展潮流的兴趣与敏感。一旦条件允许,传统又会重新复活。比如中国大陆早期从事传播研究的张隆栋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在前面提到的社会学传统与新闻学传统中,燕京大学均扮演着重要角色(49);郑北渭有美国的留学经历,早在留学期间便对施拉姆和传播研究有所了解(50)。在社会学界,传播研究的传统也未完全湮没。1980年代,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社会心理学教授沙莲香便在《社会心理学》一书中的“集合心理”一章对传播、舆论问题专门做了讨论,而这正是当年帕克关注过的问题。1990年,她还专门出版了《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世界之谜》一书。沙莲香当时并不属于以新闻学者为主要成员的传播学研究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她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传统进行了独立探索。(51)
如果没有20世纪初中国的传播引介与研究作为背景,便无法理解20世纪50年代为何要将“传播”翻译成“交通”,郑北渭、张隆栋、沙莲香等人为何会在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传播研究。对中国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便容易堕入“英雄人物”的套路,仿佛一夜之间,这些学者突然顿悟,开始大谈西方的传播学。这种“创世纪”式的元叙事除了归因于传播学界的行为主体缺乏反思外,还与学科的体制化有必然联系。要破除这些束缚,就必须重构新闻传播研究者的集体记忆。
结语:重构记忆
如果20世纪初的传播研究对于中国的社会学来说,是传统的断裂;那么对中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来说,则是陌生与遗忘。我们引进了“传播”,却遗忘了“交通”;反复书写施拉姆访华的盛事,却对杜威、帕克等人的讲学视而不见——尽管后两位社会学大师的学术地位远远高于前者;我们记得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群众思想交通”,20世纪70年代末翻译的“公众传播”等只言片语,却忘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家对帕克、库利、李普曼、拉斯维尔、伯内斯曾经做过系统的介绍与研究;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自以为发现了学术的新大陆,却忽略了中国传播研究在20世纪初就曾在此有过短暂的拓殖。
本文并不打算单纯提供仅供瞻仰的“辉煌过去”,因为民国时期的传播研究并不见得达到过很高的水准。然而这些经验的复活却会帮助我们反思当下传播学的问题,应对追求理论本土化等内心的焦虑。反思和重新解释历史往往是摆脱学科发展瓶颈和内卷化的必经之路。
20世纪初的传播研究之所以被新闻传播学界集体遗忘,最容易想到的解释是人员的变动。20世纪初了解并从事传播研究的是社会学家,而20世纪80年代后从事传播研究的主要是新闻学者,后者并不清楚前者的贡献。但是如果考虑到郑北渭、张隆栋等人对之前传统的延续,这个研究人员变动的解释就不太令人满意了。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传播研究者的结构发生了质变。传播学是外来学科,20世纪初的传播研究主要在社会学者和教会学校的新闻系开展,这两者都与西方学界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才会出现上文提到的几乎同步了解西方传播研究的状况。而1949年后大学的新闻系教员以共产党培养的干部为主体。接收下来的民国时期的新闻学者并不受到重用,且在政治运动中处于危险境地。和当时其他学科的那批知识分子一样,他们的知识体系被批判为资本主义的,必须接受思想改造和不断学习,不敢乱说乱动。
成为新闻教育和研究主体的共产党干部,大多比较年轻,很早便从事共产党的新闻实践工作,有丰富的经验,但并未在民国时期的高校真正系统学习和研究过新闻学和社会学。对西方学术的了解多限于在批判资产阶级学说中接触的只言片语。这导致他们对20世纪初期中国的传播研究非常陌生。比如为中央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虽然在新闻研究和传播研究中都走在国内前列,但是当1978年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内川芳美教授来访时,“不到一小时的讲演,现在看起来内容极为浅显的平常,可是当时竟有一半译不过来。然而,他写在黑板上的‘Mass Communication’这个概念已足以使新一年轮的新闻学研究者激动起来,他们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除了我们那套几十年一贯制的新闻学理论外,还有另外的天地”。(52)
集体记忆必须借助交流方能存在,甚至个人的记忆也须依赖必要的社会互动才能保存。(53)思想禁锢造成的对中国学术研究传统和西方学术研究现状的无知,导致中国传播研究者对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集体失忆。从个人角度来看是无心之失,然而从体制的角度来看,这一失忆则是刻意为之。因为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和西方的研究恰好被认为是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记忆清洗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研究资源的浪费。早在民国时期便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人和理论,又要新一辈人花时间当作新知识重新引进和学习。当时人员频繁互访造成的对知识掌握的鲜活感要到今天才勉强重新恢复,在此期间只能依靠数量和质量都有限的中译本进行想象,其中的误读自然随处可见。(54)
遗忘的第二个原因与学科建制有关。20世纪初社会学和新闻学引入传播研究时,其视域和语境与20世纪80年代新闻学引进传播研究时有明显的差别。20世纪初美国的传播学科建制尚未完成,传播研究是一个正在酝酿之中的模糊地带。施拉姆曾把传播研究比作“十字路口”,而那个时候,连这些路是否会交叉还未有定论。未被对象化的模糊体验必然导致知识的碎片化。因此尽管那时有了现在意义上的传播研究,却因为未被命名而无法形成有效的言说。这些经验自然无法从历史和记忆中被召唤出来与我们对话。
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重新引入传播学时,以施拉姆为代表的新闻学科已经成功地将传播研究学科化、体制化。学术组织、教材、课程、学位培养计划和就业方向等已经完备且得到承认。1982年施拉姆的来访,与其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不如说给中国带来了传播研究的学科观念。他在中国的演讲强调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把传播学说成是新闻学发展的新阶段,努力证明传播学科的正当性。(55)听过施拉姆演讲的学者印象深刻地记得他讲过传播学未来将会统一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成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宝石。(56)但是目前无论中外的传播学科史的研究者都对施拉姆所建构的这个狭隘的“传播科学”颇多微词。它将凡是不符合行政研究取向的量化研究都排除在传播学主流之外,比如芝加哥学派、批判学派等。但是这一版本的传播学却几乎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闻学者理解传播学的唯一参照系。从这个框架来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引进与研究,先入为主地去搜索“传播”而忽略“交通”,自然会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仿佛中国的传播研究是从引进施拉姆版本的传播学开始,而且只有新闻学者们参与了这个发现与引介的工作。对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缺乏反思,导致中国传播研究的历史被压缩成了一个单维度的线性过程,失去了丰富的多义性与可能性。
对这段被遗忘历史的考古,也可以让我们对新闻传播学界流行的辉格史观的学科发展进化论叙事有所警惕和反思。学科的发展未必都是向前的,甚至还会有倒退。如果任由政治和经济力量干预学科的发展,这样的倒退未必不会重演。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刚进入中国时,新闻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同时对它产生了兴趣,最后新闻学取得了对传播学的专有权。如果在成王败寇的主流历史书写之外,同时将目光投向那些可能被遗忘的片断,我们不禁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发生本文所描述的断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新闻学一起依然参与中国传播研究,今天会是怎样的情形,是否会给这个学科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通过历史的回顾,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如果不是外部条件的干预,中国的传播研究可能会沿着一条不同于今天的道路走下去。这会为我们批判地看待今天的传播研究现状,提供新的想象维度。比如,如何看待传播学的跨学科问题,思考当年对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努力,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观念的思考,反思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建制问题等。也许,这段历史会以新的方式参与未来的中国传播研究。
①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李彬:《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大众传播学》,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第5-10页。袁军、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内地》,载于段鹏、韩运荣编:《传播学在世界》,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龙耘:《传播学在中国20年》,《现代传播》2000年第3期。廖圣清:《中国20年来传播研究的回顾》,《新闻大学》1998年冬季号。
②郑北谓译:《美国报纸的职能》,载《新闻学译丛》1957年第2辑。刘同舜译:《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载《新闻学译丛》1956年第3辑。
③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
④例如在引进传播研究中最有力的《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2、3期在介绍“传播学”时,刊发了《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日本的大众传播学》、《西德的大众传播学》、《意大利的大众传播研究》、《法国的大众传播研究》。可是严格来说,作为学科的“传播学”主要是个美国现象。
⑤黄旦:《传播的想象:兼评中国内地传播学本土化之路径》,载冯应谦、黄懿慧编:《华人传播想象》,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⑥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演讲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3页。
⑦孙本文:《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原载《社会学刊》1930年第一卷第三期),《孙本文文集》第八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⑧《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82页。
⑨[美]约翰·杜威:《杜威五大演讲》(胡适口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⑩这里不仅communication的翻译与今天不同,值得注意的是medium/media也与今天“媒介”、“媒体”的翻译有所不同。见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5页。
(11)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2页。
(12)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8页。这句里的“交通”对应是现在的“传播”,而“传播”则对应的是现在的“扩散”。
(13)孙本文:《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原载《社会学刊》1930年第一卷第三期),《孙本文文集》第八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14)孙本文:《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原载《社会学刊》1930年第一卷第三期),《孙本文文集》第八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28-231页。
(15)当然,这个时期的“传播”不仅指大众传播,也可以指群体传播甚至人际传播中的信息扩散。
(16)高海波:《论戈公振的传播思想》,《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4期。
(17)[德]马丁·海德格尔:《语言的本质》,载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18)Sheldon Lary Belman,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Unpublishe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1975.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
(19)Sheldon Lary Belman,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Unpublishe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1975,p.61.
(20)元青:《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中国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2期。
(21)袁刚等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演讲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2)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1921年7月),载欧阳哲生编选:《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0页。
(23)[美]约翰·杜威:《杜威五大演讲》(胡适口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24)胡适编:《人权论集》,载欧阳哲生编选:《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23-608页。
(25)Robert E.Park,"The Natural History of the Newspap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3,pp.273-289.Robert E.Park,"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0,pp.669-686.
(26)[美]罗伯特·E.帕克:《移民报刊及其社会控制》,陈静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27)Robert Ezra Park,The Crowd and the Public and Other Essays,edited by Henry Elsn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
(28)Yenching University Bulletin:Gerneral Announcem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Work(1932-1935),北京大学档案,编号YJ1932016。另见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29)派克教授讲,蒋旨昂记并译:《集合行为》,载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9-142页。
(30)高海波:《库利传播理论在中国的早期接受》,“新闻史研究路径与方法创新研讨会”论文,北京,2013年。
(31)据纪念高觉敷的文集中所收年谱,高写作《宣传心理学》的时间为1941年,没有正式出版。目前看到的这个版本没有出版时间,出版单位为“国防部政工局出版”,属于“心理战术丛书”第三种,可能是内部出版物。见叶浩生编:《老骥奋蹄:心理学一代宗师高觉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2)Alfred McClung Lee and Elizabeth Briant Lee,The fine art of propaganda:a study of Father Coughlin's speeches,New York: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39.
(33)张耀翔:《民意测验》,《心理》1923年第2卷第1期。
(34)罗志儒:《“民意测验”的研究》,《心理》1923第2卷第2期。
(35)范红芝:《民国时期民意研究综述——基于民国期刊文献(1914-1949)的分析》,《新闻春秋》2013年第2期。
(36)周晓虹:《孙本文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37)Pen Wen Baldwin Sun,China in American Press,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New York University,1925.
(38)当然,孙本文是将新闻媒体与公众意见看成是文化现象和国际关系现象加以研究的,所以新闻或传播并不是他真正关注的对象。但如果以今人的眼光来看,会毫不犹豫地将其划入传播研究。而且令人困惑的是,孙本文后来再未回到这个领域。
(39)季达:《宣传学与新闻记者》,广州:国立暨南大学文化事业部,1932年。
(40)王晓乐:《民国时期公共关系教育创建始末——中国近代公共关系教育若干史料的最新发现》,《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6期。
(41)梁士纯:《实用宣传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42)梁士纯:《实用宣传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页。
(43)见Edward L.Bernays:Propaganda,New York:N.Y.Horace Liveright,1928.
(44)Elihu Katz,"Why sociology abandoned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Sociologist 40,no.3,2009,pp.167-174.
(45)比如Jefferson Pooley后来在一篇与卡茨合作的论文里(Jefferson Pooley and Elihu Katz,"Further Notes on Why American Sociology Abandone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58,No.4,2008,pp.767-786),便从学科体制出发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释。
(46)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4-301、330-336页。
(47)Sheldon Lary Belman,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Social Thought of the Chicago School,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1975,pp.42-50.
(48)[美]大卫·E.莫里森:《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
(49)张隆栋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学系,1948-1952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1948年9月至1949年8月兼任代理主任。从1982年张隆栋发表的介绍传播学的长文《美国大众传播学概述》(上、中、下)所附参考文献数量来看,显然对这个问题有长时间的关注与积累。而且许多学生回忆他曾在课堂上偷偷讲过西方的传播研究(讲这些内容时专门告诫学生停止录音)。
(50)姜飞:《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30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注解5。
(51)沙莲香曾留学日本,但是日本的理论体系受美国影响很大,所用的概念及方法均与美国无异。同时,沙莲香也并不是与新闻学界的传播研究者毫无关系,比如1988年首都高校学生自发成立的“青年传播学研读小组”的顾问中,便有沙莲香的名字(见阎欣:《青年传播学研讨小组在京成立》,《国际新闻界》1988年第2期)。但是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许多重要事件中,沙莲香却始终缺席,所以只能算边缘成员。
(52)陈力丹:《新闻学:从传统意识到现代意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新闻学研究10年:1978-198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页。
(53)[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
(54)刘海龙:《被经验的中介和被中介的经验——从传播理论教材的译介看传播学在中国》,《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5期。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55)[美]威尔伯·施拉姆:《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王泰玄记录,《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2期。
(56)徐耀魁:《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影响》,《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标签:传播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芝加哥学派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新闻与传播学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新闻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