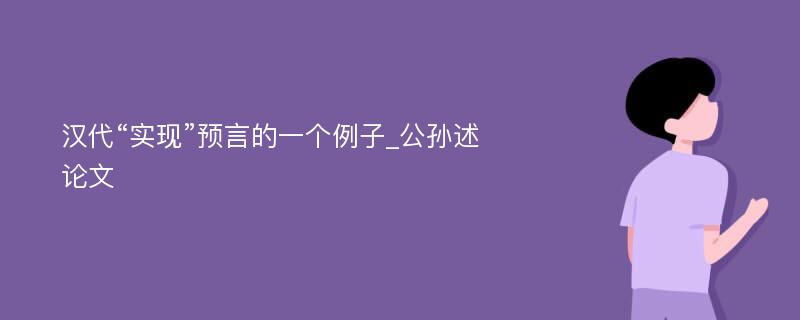
汉代“应验”谶言例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谶言例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中国学者对谶纬文化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早[1],但后来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在资料整理和研究方面,取得了独步一时的成就[2]。可喜的是,近年来大陆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3]。谶纬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秦汉史研究方面具有重大的价值,已是学者共识。谶纬之说,为何能在汉代盛行一时?除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我认为,至少有一个原因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当时人认为“应验”了的谶语,产生了震摄人心的作用。在本人所见知的既有研究成果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相对薄弱的,欲真正深入研究谶纬文化,就必须正面研究这一问题。避而不谈,无补于事;简单地斥为统治者的骗人之术,亦不足以使人服膺。本文愿意为这一研究的深入,抛砖引玉。
本文之旨趣,有三点说明:其一,谶纬是汉代神秘文化的核心,对它的研究,不能持神秘主义的态度,而只能持理智的态度;同时,对其中某些目前还难以得到科学解释的现象,也不应该勉强为解,存疑可也。其二,对汉代人已明确认定属于人为编造的政治预言,不管当时曾产生过多大影响,皆不列入研究范围。其三,当代学者已经阐发破译的谶言,本文亦无意复述。
一、“公孙病已立”与“废昌帝,立公孙”
这两条谶言,是汉人笃信的应验灵谶。但应在何人之身,却有不同说法。解谶分歧的关键在于对“公孙”的不同理解。
“公孙病已立”,分见《汉书·五行志中之下》和《汉书·眭弘传》。它的来源最为神秘,影响也极为深远。汉昭帝元凤三年,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上林苑中有断枯的大柳树亦自立发芽长叶,并且有虫咬食叶面而成文字“公孙病已立”。这自然成为轰动朝野的一大奇事。当时习《春秋》明灾异的眭弘,作出了这样的解释:“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当复兴者也。”应当代汉而兴的公孙氏,眭弘尽管“亦不知其所在”,却有勇气上书汉廷,盛言汉家“有传国之运”,建议朝廷“求索贤人”,禅让帝位。结果,辅政的大将军霍光以“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的罪名,将眭弘诛杀。虫咬柳叶竟成语句,实为不可思议之事,且从史籍寻觅,又不见人为编造之迹。对此,我们如不愿以“神秘”相释,只能推断为虫咬痕迹与文字笔划的偶然巧合。
眭弘虽诛,“公孙病已立”的影响却没有消亡。时隔五年,昭帝死,霍光等人择立昌邑王刘贺继位。不久,霍光又以荒淫无道之罪,废刘贺,改立自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而流寓民间的刘询为皇帝,是为宣帝。奇迹出现了:宣帝本名“病已”,他是已故戾太子之孙,自然可称为“公孙”。这位来自民间的皇帝,随即征召眭弘之子入朝为官,这无疑是为昔日被杀的眭弘平反昭雪。至此,朝野上下,认为五年前的虫咬柳叶文字已经应验了,似乎忘记了眭弘据此推断出的“传国”“禅让”之说。这并不难理解,昭宣时代本为西汉盛世,谁事先关注汉政权衰亡之后的问题?但到元帝之后,国家日渐衰败,眭弘当年提出的“传国”之说,再次复活,演化成“再受命”的理论,上演了哀帝自行“改元易号”的闹剧,最终以王莽的代汉而宣告西汉政权的灭亡。王莽败亡后,与柳叶谶有关的“公孙”预言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割据蜀中的公孙述,在称帝之时,援引谶记为依据,首列《河图·录运法》之说:“废昌帝,立公孙。”公孙述以“昌”来代表以“火德”自居的汉王朝,以自己的姓氏应谶,在当时很有蛊惑人心的作用。正逐鹿天下的光武帝刘秀,致书公孙述,颇有逸致地探讨谶言的隐含内容:“图谶言‘公孙’,即宣帝也。”(《后汉书·公孙述传》)即是用柳叶谶文的一段既往公案,来解释《录运法》的预言,希望借此以破解公孙述称帝的“天命”依据。
柳叶谶文出于西汉中叶,《河图·录运法》行世,也远早于公孙述称帝之前,显然,皆非出于后来的当事人妄行编造,而是在某种偶然性巧合的基础上,以曲解和附合的方式,凑成了它的“应验”。
二、“刘秀当为天子”,“赤伏符”,“刘氏复兴,李氏
为辅”
这一组三条谶文,在两汉之交,影响甚大。
论史者,往往囿于《后汉书·光武纪上》所载文字,认为光武昔日同学强华自关中奉“赤伏符”谒见于鄗,始为光武称帝提供了天命依据。此论不确。其实,“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早在汉哀帝时,就已流传;王莽代汉之后,曾引发过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内讧;光武在起事之前也曾闻知。
哀帝建平元年,刘氏宗室中最具才气的刘歆,突然易名为刘秀(《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他未曾说明动机何在,但同时代的人,却多把刘歆的易名与意图“应谶”联系在一起。王莽地皇四年,发生了国师公刘秀(歆)、大司马董忠、卫将军王涉合谋劫持王莽的谋叛事件。起因恰在于卫将军王涉素养方土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他告知王涉说: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名应图谶。(《汉书·王莽传》下)刘歆卷入这一谋叛事件,应当与相信西门君惠之说直接相关。事泄,谋叛者被诛,西门君惠临刑之前,仍对围观者大喊:“刘秀真汝主也!”其对谶言的笃信,可谓至死不渝。这番刑前遗言,直到东汉初年,仍对雄据河西的窦融决策归附光武帝产生过影响。他认定当年刘歆之所以改名,正是“冀应其占”(《后汉书·窦融传》),光武为天命所归,无需怀疑。
光武帝在王莽末年,曾与兄伯升、姐夫邓晨共同拜访蔡少公于宛。“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邪?’坐者皆大笑,(邓)晨心独喜。”(《后汉书·邓晨传》)此时的光武胸无城府,口无遮拦,所发实仅为戏言,在坐者的大笑,正表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把《邓晨传》的这段文字,过于简单地斥为史官的附会、拍马之作,联系西门君惠与刘歆之事,可以断言:王莽时社会上确已流传着“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至于这是否即来自于“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去集龙斗野,四七之即火为主的《赤伏符》,尚不得而知,歧解的关键在于谶言中的“刘秀”究竟指代何人?
我认为,谶言从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隐语式的政治预言。离开了隐语、暗示这一特点,谶言的神秘性必为锐减。谶言中出现的姓名,也须经过事后分析与“顿悟”,才能理解其中真实含义——只有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应验谶语。例如,秦始皇时代的谶言“灭秦者胡也”,按当时习用语,把“胡”直视为匈奴的泛称,所以有秦始皇的筑长城以备胡之举。等到后来秦二世胡亥暴政亡国之后,汉人才恍然大悟:“赢擿谶而戒胡兮,备诸外而发风。”(《张衡:《思玄赋》,见《后汉书·张衡传》)对秦始皇不识天机、不辩隐语的嘲讽之意,最清楚不过。正如顾颉刚先生所言,谶言“不假借隐语而直揭其官阶与姓名”,实始于王莽之时。(《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谶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48页)而这种“直白之谶”,大多是闹剧,往往受到人们的嘲讽。如王莽根据佞人匡章所造的谶言,重用匡章和王兴、王盛,就是一个显例。依据这样的思路,我认为:上述谶言中的“刘秀”如果所指为姓刘名秀之人,就毫无隐喻可言,岂不令人索然无味?
秀,有出类拔萃、优秀之意。如此,汉家宗室中,任一杰出人物,都可视为“刘氏之秀”,而不必坐实即以刘秀为姓名。如果我们相信刘歆改名为图应谶之说,那么,“刘秀当为天子”之谶,当在哀帝时即以流行。我认为在这一时期编造这一谶语的可能性最大。成哀时期,汉政日衰,“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汉书·李寻传》)之说,正如日中天。刘歆改名的第二年,就有哀帝听从夏贺良建议,改元易号。在“重受命”的气氛弥漫朝野的情况下,编撰“刘秀当为天子”谶言,实在是大有市场的。若从常规而言,由刘氏之俊秀人物,取代已失人望的哀帝,实在要比由哀帝本人自行所谓的“重受命”更为合理。换言之,不论哪位刘氏宗室登基,这条谶言都可以被解释为应验。与预言家的期望相反,西汉后期的宗室成员中确实无人可以重振汉室,这条谶言的应验时机,只好推迟下去。王莽代汉之后不久,人心离散,群雄并起,人心思汉成为一时风潮。割地称尊者,纷纷打起刘氏旗帜以作号召,汉室再兴,已成为天下共识。在这一背景下,“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自然又可大行其道。反莽起事的刘氏宗室有多人,其中不论谁最后获胜,也大可用“刘氏之秀”这种说法,为自己的称帝营造理论依据。光武帝刘秀平定河北之后,已经在诸多割据者中显示出独到的优势。于是时人把谶言的隐喻特征置而不顾,径自把他的名字与谶言对号入座,这才出现了“名应图谶”之说。虽然东汉人都指此为“应验”,但据上述分析,可以断言,这与谶言制造者的本意不符,是一例曲解的“应验”。换言之,只有在刘秀确立其逐鹿中原优势地位之后,人们才普遍地把谶言中的“刘秀”当作一个实在的人名来看待。在此之前,仅有少数人做此种理解。我可举出下列佐证:如果人们早已把谶语的“刘秀”理解为直言姓名,刘歆在哀帝时易名为秀,岂不有凯觎帝位之嫌?涉此罪名,汉宗室子弟避之唯恐不及,以刘歆之精明,当不至于自择死路。同理,王莽代汉之后,也没有理由把刘歆继续视为心腹,委以重任。另外,光武帝刘秀虽然早就与闻此谶,但他在起兵后,先是自甘隐遁于其兄刘伯升的英名之下,“王莽时,所难独有刘伯升耳”。(《汉书·寇恂传》)刘秀并无称雄的企求,外界也不以未来的天下之主相许;后来光武又依附于更始政权之下,更始帝对他的猜忌,只是源自于担忧其为被屈杀的兄长刘伯升复仇。更始政权的实力派人物朱鲔、李轶几次建议控制乃至于诛杀刘秀,所述理由虽多,却从未涉及“名应图谶”的问题。这一现象,可有两种解释:其一,更始君臣不知有“刘秀当为天子”之谶。但,更始君臣多为南阳人,理当有机会听闻乡党名流蔡少公传播的谶言。特别是李轶,与其从兄李通同为最早鼓动刘秀起兵以图天下的人物,他与闻蔡少公之谶的可能性最大。后来他背叛光武兄弟投依更始政权,显然是把更始帝视为复兴汉室的应谶者了。远在河西的窦融尚能闻知此谶,近居南阳的更始君臣如若未闻,恐有悖情理。其二,更始君臣未把谶言中的“刘秀”理解为直言人名。否则,光武早受杀身之祸了。实际上,纵览历史,光武是最无“雄心”和壮语的开国皇帝。他在起兵前夕,自述其志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后汉书·皇后纪上·光烈阴皇后》)也只是寻常富贵梦,不见丝毫帝王气。如果此语发于既闻蔡少公谶语之后,更说明“刘秀”必有它解,是包括光武在内的南阳豪杰的一时共识。光武起兵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未以窥取天下自许,也足以说明这种共识的约束效应。不宜悉以光武之权变视之。
南阳宛人李通,世以货殖著姓。他在鼓动光武起兵方面,有独特建树,后被光武视为“首创大谋”的人物。原因在于一道谶语起了决策作用。史载,李通之父李守“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他先告知李通“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言,李通心有所动。王莽末年,天下兵起,李通与族弟李轶计议,拥戴刘伯升兄弟起事,即往见在宛城避难的刘秀。“具言谶文事,光武初殊不意,未敢当之。”(《后汉书·李通传》)后在李氏兄弟的劝说下,刘秀才与他们决定联合起兵。今人论史,往往有一种想揭破“神秘”的责任感,见到李通凭借这条谶言而在东汉开国之后安享富贵,遂指李通父子是这条谶言的伪造者,实为不当。详察史籍,李守李通父子仅是这条谶言的传播者。李守与刘歆的关系,应当引起注意,或许李守有可能闻知其它谶言(包括“刘秀当为皇帝”)。只是由于李通的功利选择,而过多地传播了这条谶言。显然,从受益关系寻找谶言的伪造者,不适于破解这一案例。李氏曾为此付出了杀身破家的代价,密谋泄露之后,除李通、李轶逃脱之外,包括李守在内的全家人,都被王莽政权所诛灭。并且,我查到了这一谶言在李守之前就已出现的记载。王莽地皇二年,魏成大尹李焉谋叛,被王莽所杀。起因在于卜者王况为李焉设谋:“新室即位以来,……百姓怨恨,盗贼并起,汉家当复兴。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当为汉辅。”(《汉书·王莽传》下)这是目前所见“汉家当复兴,李氏当为汉辅”的最早记载。此谶仍不可遽断为卜者王况所编造,但却说明了“李氏为汉辅”之说,起源于两汉时代无所不在的“五行”学说。把姓氏与五音(宫商角徵羽)相配合,进而与五行发生联系,是汉代的一种迷信习俗。《图宅术》称之为“姓有五声”。(《论衡·诘术篇》)李姓属五姓之中的“徵”,“徵”与五德之中的“火”相应,而汉王朝为火德,转而得出“李为汉辅”的结论,在汉人心目中是一个严密的逻辑推断。当然,与徵音相应的姓氏甚多(如,田氏即为其一),谶言的编造者何以单独选中李氏,使居汉辅地位,现已无法考出。
由于这条谶言有五行理论为据,故当时人坚信不移。王莽因为惧怕“李氏为辅”的谶言,设法给以压胜破解,就任命李棽为大将军,并赐名为“圣”,以求“以圣代谶”。(《汉书·王莽传》下及颜师古注)李通随光武起兵之后,曾同隶更始政权之下,更始帝亦出于对“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的崇信和利用,任命李通为柱国大将军、辅汉侯,后又晋封西平王。从职位而言,素居刘秀之上。后人因光武中兴之后,李通身居高位,而把它视为此谶的应验。其实,如果更始帝获胜,李通仍可以“辅汉”的特殊身份安享尊荣,此谶也仍可视为应验。推而言之,李姓本为常见姓氏,只要有刘氏宗室重建国家,都不难推出李氏部属以作应谶之人。只是李通一家最早懂得利用这条谶言,遂取得对它的垄断权。
三、“代汉者当塗高”
这条谶语与东汉王朝相伴始终。东汉初年的公孙述,东汉末期的袁术,都曾以此作为其代汉称帝的依据,由于他们很快败亡,只落得一场笑谈。但是,当着魏王曹丕废汉自立时,很多人确实相信它在流传二百年之后,终于应验了。
这条谶语在两汉之交即已盛行,确无可疑。公孙述称帝,多引符命谶言为助,他以自己名字的“述”字,有“路途”之意,认为与该谶言的“塗”字相应。光武帝千里驰书,以破其说:“代汉者当塗高,君其高之身邪?”(《后汉书·公孙述传》)值得注意的是:光武绝未斥公孙述伪造谶语,而只是说公孙述并非当高其人。他坦然相告:“承赤者,黄也;姓当塗,其名高也。”(《后汉书·公孙述传》注引《东观记》)前半句讲的是五行循环之论,以土(黄)代火(赤),光武方以中兴号召天下,而对这条预言汉室将被人所取代的谶语,竟不敢斥其虚妄,可见当时它已经为人所周知,虽帝王之尊,亦不足以遏制其流传。光武既无法否定它,只能煞费苦心地增设它应验的前提条件。所以,后半句指实当塗高为姓名,当塗为自古罕见之性,出现的概率很低,或许正是光武帝尽量延长汉祚的一种努力。
光武帝指“当塗高”为人名,虽用心良苦,却并未得到社会认可,将“塗”字解释为道路者,仍大有人在。东汉末年战乱方起之时,军阀袁术“少见谶书,言代汉者当塗高,自云名字应之”,(《后汉书·袁术传》)即为显例。
曹丕代汉前夕,这条谶语再度鼎沸于中原。太史丞许芝向曹丕条奏魏代汉的诸多谶纬,以作劝进之助,其中即有“当塗高者,魏也;象魏者,两观阙是也;当道而高大者魏。”(《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古代皇宫门前,有两座装饰性建筑物,分立当道,称之为“阙”或“两观”,因其高大,又多以“魏”“巍巍”联称。许芝等人把“当塗高”解释为魏阙,译解了流传二百年的谶语谜底是“代汉者魏”,在当时确有使人恍然大悟之感。魏之代汉由此增添了天命悠归色彩。
我认为,许芝等魏臣的译解,虽然也属于附会之列,但至少较之公孙述、袁术仅借“塗”字一义与其名字相应而妄称天命,具有较多的说服力。因为,把当道而立的双观,称为魏阙,或以“巍巍”来形容,在汉代是极为普遍的。我可以举出三个显例。张衡《东京赋》有“建象魏之两观,旌《六典》之旧章”(《后汉书·张衡传》)之句。安帝至顺帝时的名士李尤,有《阙铭》之作“表树两观,双阙巍巍”(《全后汉文》卷五十,李尤《阙铭》)。高诱注《吕氏春秋》“心居乎魏阙之下”句,即解释为“魏阙,象魏也。……魏魏高大,故曰魏阙。”(《吕氏春秋·审为篇》高诱注)可见两观建筑与“魏”的联系,是由来已久的。只要人们把“当塗高”解读为当道而立的两观,那么把魏代汉认作上述谶言的应验之事,应该说,其牵强附会的色彩是最少的。因而其折服人心的效果,也就是最明显的。
再索史籍,我认为,许芝等魏臣固然有有意利用谶言为政治服务的嫌疑,但把“当塗高”解读为“高阙——魏”,却不是魏臣的发明创作。最早明确作这种解释的,是汉末蜀中名士周舒。史称:“时人有问:‘《春秋谶》曰代汉者当塗高,此何谓也?’舒曰:‘当塗高者,魏也。’乡党学者私传其语。”(《三国志·蜀书·周群传》)周舒的生活年代,可根据其子周群的仕宦生活推得,周群在刘璋任州牧时,曾被辟为师友从事。其最早的政治言行见之于建安七年(《三国志·蜀书·周君传》及裴注引《读汉书》,其时,曹操尚未平定北部中国,周舒既为周群之父,其年辈应略早于曹操、刘备诸人。他释当塗高为魏的时间,当在三国鼎立之局尚未确立之前,其距曹丕代汉至少有几十年的提前量。这里,有几个问题应该讨论。
其一,蜀地士人对“代汉者当塗高”的谶言,有理由较之外地,有更多的关注和理解。因为东汉初年公孙述割据蜀中时,曾大力传播过此说。东汉末年,刘焉割据益州时,曾经“阴图异计”,博通图谶的蜀中名士董扶,也以“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相动(《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故汉末战乱方起,蜀中人士对早年流传的谶言必有“温故而知新”之感。
其二,周舒周群父子所传学术,实以图谶、灾异理论为主。周舒少学术于广汉人杨厚,杨厚行事,见于史传记载的,仅有“究极图谶”四字。(《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裴注引《益部耆旧传》)周群幼学父业,精于侯气之说。在这样一个世传神秘之术的家庭里,周舒对谶言作出了不同于别人的解释,当极有可能。
其三,周舒之说不应该被视为陈寿有意神化魏之代汉而编造伪托。关于陈寿“帝魏帝蜀”之争,历代论史者各陈己见,实令人有不容置喙之感。但有一个现象,还是应该注意的:在分记曹丕和刘备登基时,陈寿详引蜀臣劝进表,其中引用了大量的谶言;而对于曹丕即位,却未及任何谶言,倘若不是裴注增补,后人当无以知晓在曹丕代汉时,魏臣亦曾大量引用谶纬为据。这种对比,可以给我们一种暗示:陈寿此种记事方式,可能暗寓以蜀汉得正统之意。那么,陈寿记载周舒解释“当塗高”为“魏”,决非有意识地神化魏氏之代汉。倘若陈寿果有此意,自当在《魏书·文帝纪》详载。
以魏之代汉作为“代汉者当塗高”应验的依据,从其解释动机而言,却判分为两种。一是蜀人周舒,立足于他所信寿的一种学说而破解谜底;二是许芝等魏臣,立足于一种政治需要而附会时政。同时,魏臣为了扩大其影响力,以这条久已流行的谶言为基础,编出了几种新的谶言,“许昌气见于当塗高,当塗高者昌于许。”“汉以许昌失天下,”“代赤者魏公子”(《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注)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新出谶言,已毫无隐喻、多解可言,一味的“言之凿凿”,恰证明了它们是出自于拥护曹氏的帮闲文人,临事编造。所以后者全然没有索隐探幽的价值,而前者却不同。
周舒作为述其言者,并无政治功利可图;陈寿作为记其事者,亦无故意神化曹魏的嫌疑,这就使得这条谶言的应验,具有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我认为,这实际上不过是词义多解基础上的偶中事件。“当塗高”三字,光武帝释作人名;公孙述袁术则抓住一个“塗”字,解作道路;周舒、许芝则归纳为“魏”,已有三种解释。其实,只要刻意寻觅,还可求得多解:如,当塗,一转为“当塗”,则指辅佐大臣,韩非早就有“当塗之人擅事要”(《韩非子·孤愤》)之说。那么,任何身居高位的辅佐大臣代汉,都可视为谶言应验。当塗,又是地名。汉时隶属于九江郡,东汉后期的名士荀淑就曾任当塗长。(《后汉书·荀淑传》)如解作地名,不仅原籍当塗的人,甚至曾任职于当塗的官吏,再配以“德高”、“才高”、“位高”,乃至于巧合姓高,都可以作为“当塗高”的隐喻人。这并不是无谓的文字游戏,我相信,东汉一代,对于“当塗高”索解的答案,完全可能包举、乃至于超过了我的上述“臆想”,只是由于它们与后来的政局演变找不到联系的纽带,而被人淡忘了;而周舒、许芝的破解,则由于偶中、或称之为稍有关联的附会,而载入了史册。于是,神秘在这里荡然无存。
结束语
本文以案例剖析的方式,论述了汉代几则有影响的被当时人认定“应验”了的谶语,都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把谶言全部斥为妄人所造,并被统治者用为愚民之术,未免过于简单。本文已涉及到的几个观点,愿再综述如下,以期引起研究谶纬文化的专家和同好的讨论和指正。
1.必须充分注意谶言的“隐喻性”。“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六·易纬坤灵图·馆臣案语》)清人这一定义虽然晚出,但道出了谶言的主要本质。直到王莽之前为止,这种隐喻性还是一种普遍遵循的规则。从王莽开始,出现了直道姓名官衔的谶语,这是部分谶言编造者的一种肤浅甚至下流作法,它降低谶言的神秘性而增加了滑稽感。就常情而言,隐喻性越强的谶言,越容易嬴得人们真心的折服,也就越具有研究的价值。当然,我也并不认为所有“直白性”的谶语,均可视为儿戏,关键是对它的初造涵义和后来的附会涵义,应作区分和研究。
2.谶言编造者未必皆出于利己动机,初造之意与后来的“应验”之事,可能相去甚远。利用谶言为自己谋取利益者诚然有之,同时,也确有部分人是出自于对“五德终始”等学说的笃信。今日斥之为荒谬绝伦者,在术数之世的汉代,却可被奉为神圣信仰。他们概括自己所尊信的学说原理,做出推断和预言,并托名源于上帝或孔圣,或许在他们看来,并非伪作,只是“代圣人立言”而已。造托者在谶言中所隐含的预言,总是根据一定的时局而作出。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使它丧失了在近期内应验的可能;然而,又经过了若干时期,这种预言又可能被视为“应验”在一个相似的事件上,这种“应验”虽能“言之成理”,但与初造者的原本寓意却是毫不相干。同一条谶言,在不同时代,不同人事上被多次认为“应验”,就是证明。如上述分析不谬,那么,就不宜于片面地根据某一谶言的受益关系,去找寻它的编造者,把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化为功利游戏,至少失之于轻率。
“应验”谶语的神秘性,主要来自于文字的多义多解及附会,同时,也必须正视“偶中”因素的巨大影响。古代哲人早对偶中有清醒的认识。春秋时,有人预言郑国将有火灾,事后应验不爽,执政大臣子产却力言其妄:“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传·昭公十七年》)汉代各地皆食鹳鸟,唯独三辅民俗不敢猎取,依当地传说,倘若取食,或有霹雳暴响。对此,思想家桓谭明确指出,这一民俗是形成于“其杀取时,适与雷遇”(《全后汉文》卷十五,桓谭《新论·离事第十一》),世俗之人视为神秘不可解之事,哲人以“偶中”折之,则毫无神秘之可言。史书所载谶言,固以应验者居多,但实际上未曾应验的谶言,则不知超出于它的多少倍之上。只是由于它们未曾应验,而不被世人所重,不为史官所载,故而失传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来,现载于史籍的谶言,皆可视为披沙捡金的偶中部分。由于古人对这种“偶中”加以夸张和附会,从而使之表象为“屡中”,人为地造成了一种神秘气氛。时至今日,我们完全可以对某些尚不能给以破译的灵谶,以“偶中”或“偶中+附会”的思想,给以解释。“一语成谶”,不是现代生活中仍有类似社会现象吗?我自信,坦言“偶中”及其被夸张后的影响,与把谶言的“应验”现象简单地斥为“骗术”之说相比较,是一种更为理智的选择。
注释:
[1]陈槃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发表了《谶纬释名》、《谶纬溯源》等文章,参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一册、第十六册、第二十一册。
[2]日本谶纬学的代表作: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编《重修纬书集成》,东京明德出版社1970-1985年;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著《纬书の基础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976年;安居香山著《纬书の成立とどの展开》,同上,1979年;安居香山编《谶纬思想の综合的研究》,同上,1986年;安居香山的晚年力作《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中文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其余相关论文不胜枚举。可以参见林庆彰主编《日本研究经学论著目录(1900-1992)》,台北中央研究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发行。
[3]近年新出论著较多,笔者见知之作有: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王步贵《神秘文化——谶纬文化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郑先兴《论谶纬》,《南都学刊》1991年第3期;晃福林《周太史谶语考》,《史学月刊》1993年第6期;王利器《谶纬五论》,吕宗力《纬书与西汉今文经学》,两文皆收入(日)安居香山所编《谶纬思想の综合的研究》一书中。
标签:公孙述论文; 光武帝刘秀论文; 李通论文; 刘秀与阴丽华论文; 汉朝论文; 光武中兴论文; 后汉书论文; 历史论文; 汉代建筑论文; 王莽论文; 西汉论文; 东汉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汉书论文; 历史学论文; 史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