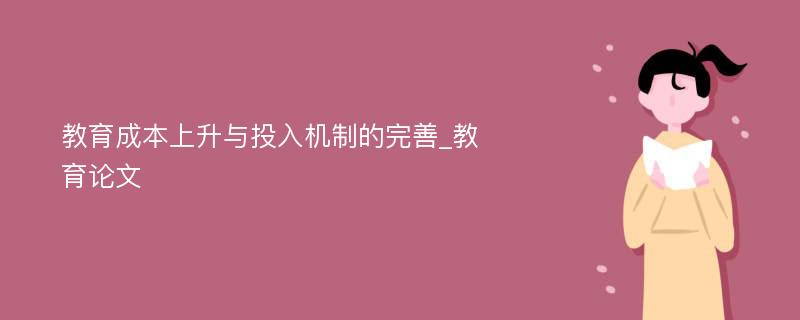
教育费用攀升与投入机制改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费用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居民良好的教育状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费用持续攀升,对居民的教育状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社会蓝皮书》,子女教育费用在居民总消费中被排在第一位,超过养老和住房。教育费用持续攀升会产生什么效应?它反映了教育投入机制有何缺陷?应该如何完善?本文对此作一些分析。
按第三产业经济学的划分,社会产品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包括实物型生产资料和服务型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则包括实物消费品和服务消费品。教育业的产品即教育工作者的“传道授业解惑”是一种非实物形态劳动成果,可称为教育服务产品。
从实际生活过程来说,教育服务产品被用于个人生活消费是显而易见的。社会成员从出生时起,就需要接受各种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这些教育服务产品因用于个人生活消费,就属于教育服务消费品。从另一方面看,教育服务产品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用于生产消费。国民经济各部门为了进行实物产品或服务产品的生产,往往以公费支付学费的方式,对员工进行教育培训。公费支付的教育服务产品就成了教育服务型生产资料。中国教育服务产品约有89.7%用于生活消费,10.3%用于生产消费,0.69%、4.60%、5.03%分别用于第一、二、三产业的生产消费。因此,教育服务产品包括教育服务消费品和教育服务型生产资料。
由于教育服务产品主要由教育服务消费品组成,因此影响教育消费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对教育的消费。按照消费结构发展趋势,家庭对教育服务产品的需求必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趋于增长。这是因为教育服务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发展资料,其需求收入弹性高于实物产品,在社会收入达到温饱水平并持续提高和闲暇时间增长的条件下,对教育服务产品的需求就会以快于货物需求的速度增长,从而引起教育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比重上升,这是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这种趋势在发达国家早已存在,在中国也显露端倪。在20世纪70~80年代,在中国还哀叹“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之时,欧美发达国家早就进入高收入与高学位相关的消费阶段。从另一方面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升级使教育培训对企业通过人力资源改善提高企业效益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此,越来越多的现代企业不惜花费大量培训费用购买作为教育服务型生产资料存在的教育服务产品。这样,中国伴随着高学历化趋势、望子成龙期望和企业人力资源素质提高,出现教育消费量增长的趋势,是顺乎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事情,也是正常的。
教育消费通常通过以货币形式支付学费的方式购买教育服务产品来实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教育产品消费量的大小与教育费用的多寡正相关,与教育服务价格高低负相关,因此,教育服务产品的消费量不能只是根据教育费用的多寡来估计,还应该综合考虑教育经费的支出量、教育服务价格水平、在教育投入的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货币币值等多种因素。考虑到农村居民的家庭消费不完全采取货币化形式可能产生误差,下面以城镇居民的教育消费数据为样本分析教育费用与教育服务价格的关系。
根据对近20年来消费结构统计数据的分析,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教育支出在家庭生活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的趋势。城镇居民家庭人年均教育支出占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在1986年仅为1.6%,1990年升到2.6%,1998年突破6.3%,2002年高达8.2%。同期人年均教育费用大幅度攀升,由1986年的12元,增加到2003年的2728元,增长226.3倍。那么,中国居民对教育服务的消费量是否也增长了226倍?
对相关统计资料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中国居民教育费用的大幅度攀升主要是教育价格提高引起的。1986年~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100提高到341,增长2.4倍,同期教育服务价格指数由100提高到2314,增长24.1倍。如果剔除价格上涨的影响因素按1986年不变价计算,1986年~2003年人均教育消费额仅由12元升到22元,教育开支占家庭消费开支的比重实际是下降了:由1986年的1.6%降低到1993年的1.5%,2003年的0.8%(详见附表)。
中国城市居民教育消费占家庭消费的比重(1986—2003)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当年价1.6
1.7
2.1
2.5
2.6
2.8
3.8
4.4
4.5
4.7
5.2
5.7
6.3
7.0
7.3
8.1
8.2
7.9
1986可比价
1.6
1.6
1.6
1.3
1.3
1.4
1.6
1.5
1.2
1.0
1.0
0.9
0.9
0.9
0.8
0.8
0.8
0.8
中国城镇居民教育消费变化(1986—2003)
生活消费(元)
教育消费(元)
价格指数教育消费比重(%)
(1986年=100)
年份
当年价 不变价
当年价 不变价
教育
生活
当年价
不变价
消费
消费
1986
799
799
12
12100
100
1.61.6
1987
884
869
15
14108
109
1.71.6
1988
1104
1049
23
17137
131
2.11.6
1989
1211
1220
30
16190
153
2.51.3
1990
1279
1275
34
16209
160
2.61.3
1991
1454
1304
41
18226
163
2.81.4
1992
1672
1417
64
23273
177
3.81.6
1993
2111
1645
93
24383
206
4.41.5
1994
2851
2056
128
24525
257
4.51.2
1995
3538
2401
166
25674
301
4.71.0
1996
3919
2613
204
25818
327
5.21.0
1997
4186
2694
238
24993
337
5.70.9
1998
4332
2677
275
241153
335
6.30.9
1999
4616
2643
323
241375
331
7.00.9
2000
4998
2664
364
201811
333
7.30.8
2001
5309
2682
428
202128
336
8.10.8
2002
6030
2704
495
222223
338
8.20.8
2003
6511
2728
514
222314
341
7.90.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计算求出。
注释:
1.本表统计的是全国城镇居民消费状况,不包括农村居民。
2.生活消费和教育消费分别指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的消费性支出和教育消费(包括教材及参考书、学杂托幼费)支出。
3.生活消费价格指数和服务消费价格指数分别指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教育消费价格指数。因不少年份没有涵盖教材及参考书、学杂费托幼费在内的教育消费价格指数,故用学杂费托幼费价格指数代替教育价格指数。
4.不变价以1986年为基期计算。
5.教育消费比重指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的教育消费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比重。
一、教育服务价格迅速上升的原因:
首先,这是与非自动化服务产品价格上升的总趋势是相吻合的。教育服务产品从总体上说属于非自动化服务产品,应用自动化、机械化的可能性不大,生产率的增长率比较低。新中国建立50多年来,尽管工业生产率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教师靠“手工”备课,靠“口工”讲课的状况没有多少改变,教育服务生产率提高幅度很小。在实物产品生产率迅速提高的情况下,非自动化的教育服务价格必然以更快的速度上升。托夫勒把这种趋势称为相对不经济定律。
其次,教育服务需求坚挺,支撑着教育服务价格的攀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温饱问题的解决,收入水平迅速提高的居民对粮食的需求量相对下降,使粮食价格疲软;对服务产品尤其是高层次教育服务产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对教育服务产品的坚挺需求,形成了服务价格攀升的需求条件。
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在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的教育制度改革,在原来全靠国家财政资助的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使教育部门必须在财政资源投入以外寻找更多的教育经费资源,弥补日趋下降的财政经费资助。教育投入资源的多元化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使中国教育形成通过提高教育服务价格来解决教育价值补偿机制不完善的问题。教育领域市场补偿机制的强化、财政补偿机制的弱化必然驱使教育服务价格提高。
上述三个原因都有其必然性,这就使教育服务价格上升得比实物产品快。这也可以说是对中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的低价制和免费制的一种纠正。
客观地讲,教育服务价格上涨有双重效应。
一是抑制教育服务需求效应。对于教育服务的需求者来说,教育服务价格上涨无疑抑制了接受教育者的消费欲望,或者因教育费用开支的增大挤压了百姓的其他消费需求。这就是传媒对教育费用上涨普遍持抨击态度的基本原因。中国在校大学生按2003年普通高校招生数382万,学制4年算,为1528万人。其中,在校农村学生按农村生与城镇生为56∶44的比例算,大约有856万人。每个大学生年均学费按4000元计,月生活费按400元计,年生活费4800元,年教育费用为8800元/人,相当于2003年农村人均纯收入(2622元)的3.36倍;856万农村学生的年教育消费额为753亿元,相当于2003年全国农业各税(872亿元)的86.4%。教育服务价格上升使很多农村学生上大学的希望被打破。农村一个孩子上大学就能把家里的积蓄花光,家里有两个孩子上大学更是不可想象的。农村学生考上大学,却读不起大学就是因为教育费用昂贵所致。
二是推动教育服务增加供给效应。价格是一支双刃剑,价格高了伤及消费者,价格低了供给者受损。教育服务价格也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服务价格的持续上升实际上也在发挥其促进教育服务供给,这就是教育服务价格上涨的第二个效应。它使教育部门有条件提高教师待遇,引进高层次人才,改善教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扩大教育服务再生产。在20世纪80年代有一个口号,叫做“要使教师成为最令人羡慕的职业”。其出发点不错,但是,在当时“脑体报酬倒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这只能成为无法实现的良好愿望。如今,教育部门特别是高校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教师真正变成了一个被人羡慕的职业(欧美早就如此),这与教育服务价格的大幅度攀升密切相关。
需要说明,本文阐述教育服务价格上升有其客观必然性,并不意味着赞成教育服务脱离服务价值漫天要价。
二、教育投入机制的问题与改善
对教育服务价格上升造成的上学难问题,政府不应该无所作为。
根据对世界教育经济统计资料的分析,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居民个人对教育服务的支付比重有下降趋势。这是因为国家政府以各种方式对百姓接受教育的资助在增加。然而中国资料却显示,中国学杂费在教育费用中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由1991年的4.4%上升到2002年的16.84%。这提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在教育服务的提供中发挥的作用在下降。
面对教育费用上升的形势,政府应该增大对教育的投入,应开辟奖学金、勤工俭学、教学贷款、社会赞助等多种渠道,资助高素质人才接受高层次教育。文革前,中国的贫困学生只要成绩好,还有免费就读农、林、师、矿等高校的机会,随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进行,目前这些优惠就读机会已基本消失。这会造成千军万马只挤收费高校一条路的窘境,不利于贫困学生的培养,也不利于解决高等教育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中国教育管理部门借鉴。
与此相关的是义务教育投入机制亟需完善。义务教育制是多数国家已普遍实行的强制公民接受一定年限学校教育的制度。中国是在1986年开始施行《义务教育法》,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与此相伴的是教育体制的两项重要改革:发展基础教育的权利和责任下放:中央政府决定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规划,具体实施由地方政府负责;教育融资渠道多元化:政府由完全负担所有教育经费,变为只负担部分教育经费。
实践表明,义务教育体制改革虽然对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三个非常突出的问题:
1.义务教育投入责任承担主体分工不明确。义务教育的核心是投入问题。现行《义务教育法》对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投入责任,即中央、省、市和县级政府各应承担多少、怎么承担,表述笼统,难以据章操作。国家未对具体投入责任进行划分,只是模糊地表明要通过转移支付来支持困难地区,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以财力较弱且不均衡的县级政府投入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机制,引起下述投入不足和发展不均衡问题。
2.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总量严重不足。中央政府提出普九政策后,没有制定任何资金配套计划。在基础教育筹资地方化,地方政府自身财政收入匮乏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均等化转移支付相配套。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中国义务教育经费78%由乡镇负担,9%左右由县财政负担,省里负担11%,中央财政负担低至不足2%。财力最薄弱的乡镇政府承担了占全国义务教育学生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不堪重负;而中央和省级财政投入则偏少。这就造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总体水平不高,基础薄弱。
3.义务教育发展严重失衡。在基础教育筹资地方化的机制下,地区和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必然造成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的条件、水平和质量的巨大差距,且有扩大趋势。全国还有10%的县级单位未实现“普九”;贫困地区、贫困家庭适龄儿童和进城务工农民子女难以获得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形成新的文盲和半文盲;已经“普九”的广大农村地区工作基础相当薄弱,巩固提高的任务十分繁重。
上述问题,都与中国义务教育投入机制不完善直接间接相关。可见,修订《义务教育法》重点应是完善义务教育投入机制问题。
首先,举办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责任,理应由政府而不是社会力量提供投入保障。要建立起义务教育经费由各级政府共同分担,非义务教育由政府、社会、个人分担的机制。政府应该牢记自己在提供免费义务教育服务方面的公共职能,应该清楚:贫困地区、贫困家庭适龄儿童未实现“普九”,折射了政府职能的缺位,应该从公共财政投入不足方面找原因,通过增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资来解决,而不应该靠在传媒上提倡社会力量“认领”、资助失学儿童,或捐建“希望小学”等方式实施“普九”义务教育。
其次,中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严重失衡是义务教育经费筹措方式的弊端造成的,它导致义务教育投入不足和地区失衡,使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教育质量下降。要从根本上解决中西部经济落后问题,必须从缩小全国义务教育的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进而缩小新一代劳动者人力资源的质量差距入手。这就需要在中央、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中,重点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资责任,改变当前两级政府在义务教育公共投资中比例过低、作用过微的状况。
最后,农村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产品,具有使农民脱贫致富,为国家输送人才,提高国民素质的外部性,不应该主要由乡镇承担其投入。20年来,农村中小学主要依靠农民负担的农业税、教育费附加、教育集资维持运转,乡村两级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的义务教育投入, 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很少,造成了农村教育水平的停滞甚至倒退。应合理划分中央、省、县三级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责任和行为,把更多的公共资源配置在义务教育这一层面上。国家要制定义务教育最低财政标准,对低于财政标准的县乡,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自上而下地通过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或专项补助制度给予财政支持,以此强化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全国义务教育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中央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供给水平,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