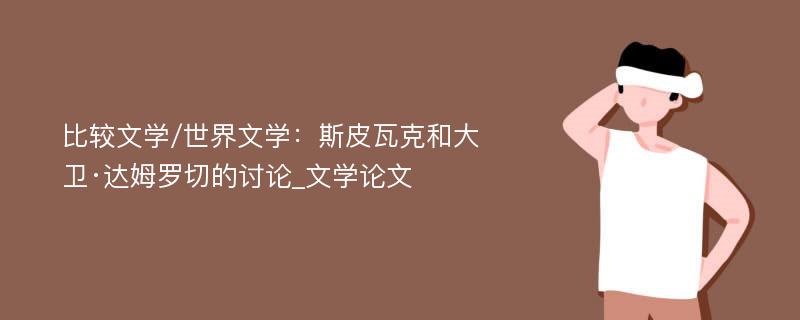
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斯皮瓦克和大卫#183;达姆罗什的一次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皮瓦克论文,大卫论文,比较文学论文,达姆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下文是两位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大卫·达姆罗什和斯皮瓦克之间的一次讨论。这里是他们之间对话的誊本,该对话是去年4月2日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召开的“2011美国比较文学会议”上,二人在众多观众面前进行的一次对谈。时任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主席的苏源熙对他们二人进行了介绍。
[大卫·达姆罗什]很高兴同我的老朋友和老同事佳亚特丽·斯皮瓦克在这里聚会,我与她一直分享着具有创造性的不同意见直至今日。(转向斯皮瓦克)所以我今天试图就这些问题同你一道进行一些思考,较之于我们老一代还在上学时的那种状况,这门学科确实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比较文学真正所指的只是极少数文学的研究,而且大多数还是西欧主要的文学。1960年,瑞士的比较学者沃纳·弗里德里希(Wernet Friedrich)曾说:“世界文学是一个专横而傲慢的词语。有时在不严肃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应把我们的项目称为‘北约’文学。然而,即便如此称呼仍显得奢侈,因为我们通常处理的文学数目还不足北约成员国总数的四分之一。”①或者如平川佑弘(Sukehiro Hirakawa)在其书中写到他在1960年代,在东京大学的日本第一个比较文学项目中的学习,以及对韦勒克(Wellek)、库尔齐乌斯(Curtius)和奥尔巴赫(Auerbach)的阅读:他说他被这些杰出的学者深深打动,但是对他和他的日本同事而言,比较文学似乎就“是某种大西欧共荣圈”。②多么有趣的类比。
但了不起的是这个世界已经向欧洲和欧洲之外、大大小小、范围更广的一系列国家开放,如此,《朗文文学选集》现在才收录了佳亚特丽对印度女作家马哈思维塔·德维(Mahasweta Devi)的《哺乳者》极富才智的翻译,以及来自源语为纳瓦特尔语、闪族语、中古高地德语、波兰语和越南语的翻译。这种种事件几乎从不曾出现在比较学者的视野中,所以,我认为我们此时有许多的理由予以庆祝。
我个人认为,在今日新近扩展的比较研究领域中,确实仅有三个问题存在。我知道我同佳亚特丽都在关注这些问题,虽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视角或许有所不同。这三个互相缠绕的问题就是,世界文学的研究很容易在文化上变得孤立,在语文学上破产,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同全球资本主义之最糟糕的倾向合流。
除了佳亚特丽·斯皮瓦克,还没有人对这些问题更为关注,如我们从她2003年出版的有影响力的《学科之死》的序言中所看出的那样。在书中,她写道:“在2000五月我在韦勒克图书馆的讲座和2002年这本书的定稿之间,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经历了一次巨变。”她继续写道:“许多出版集团已经意识到存在着一个翻译的世界文学选集的市场。取得大笔预付金的专业学者们正忙于编辑这些选集。”(编辑选集的这些取得大笔预付金的专业学者们是谁呢?我希望我能了解。)她接着说:
这个市场是国际性的。通过美国组织的翻译,中国台湾和尼日利亚的学生将会了解到世界各地的文学。这样体制化和全球化的教育市场将需要教师,大概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将会培训这些老师。所以,你们将要读到的这本书,比起2000五月的韦勒克图书馆讲座,会更为严重地同时代脱节。我一点都没改变对呼唤新的比较文学的迫切感。我希望这本书将作为一门垂死学科最后的喘息来阅读。③
佳亚特丽的序言已经把我关心的三个问题全都谈到了:翻译的语言学问题,美国专家径自组合世界文学选集的方法论问题,以及出版集团试图将世界美利坚化的意识形态问题。
据我所知,这些世界文学选集还从未面向全球市场出版,原因倒不是为了避免向世界散播美国的观念,却仅仅是因为市场之故:出版许可的费用过于高昂。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选集的出版许可权:你可以获得北美的出版许可权或者全球的出版许可权。全球出版许可权的费用是北美出版许可权费用的两倍,还没有任何一部主要的概论选集选择费用更高的全球出版许可,因为在北美之外,还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市场。因此通过这些选集我们真正能做到的只是向北美读者呈现一个世界文学的图景。针对这些选集的批评也确实非常适用于加拿大市场,这里的学生正在获得的诸种版本的世界文学选集中,包含着大量美国文学的选文,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选自加拿大文学的作品。尽管北美外的其他地方,如尼日利亚或者中国台湾的一些学生从网络上获得了这些选集,但这是朗文、贝德福德和诺顿无法操控也无意进行营销,或者计划出版的地方。因此,资本主义本身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在保护着更广大的世界不致遭受美国世界文学选集的侵袭。
即便如此,这里有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佳亚特丽的批评卷入了一个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长期论辩,世界文学的课程当时在美国开始崭露头角。1959年,位于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举办了一次关于世界文学教学的重要会议。第二年,该会议的论文集《世界文学教学》由哈斯凯尔·勃洛克(Haskell Block)编辑出版。如果你阅读这本论文集,它所显示出来的是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的深深分歧。分歧就摆在那里,依据阶级和地理的界线而划分。
你们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见到的是东海岸的精英学校,它们拥有雄厚的语言学系,这些学校的比较文学系期望懂得法语、德语和拉丁语的学生进入它们的研究生项目——预科学校一般都教授这三种语言。如果你要以另外一种语言来工作,相关的语言学系将会提供相应的培训,要是该大学不能提供某些语言的培训,如孟加拉语或者纳瓦特尔语,那么你就不能研究它们的文学,而这些项目对于翻译有一种内在的抵触。然后还有一些平民公立大学,大多位于中西部、南部和落基山脉诸州,世界文学在这些学校里恣意生长。在威斯康星的会议上,发言人们略带尴尬地谈到发生在爱荷华的一个例子:该商务学院主任开始要求他的学习商务的学生选修一门世界文学课程,在此鼓励下,注册就读世界文学的学生人数从1950年代的40人,仅数年后就增长到400人。在我说到这些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佳亚特丽的不快,我理解其中的缘故并抱有同样的关注。
但极为有趣的是,参与此次整个论争的世界文学研究者们,主要是来自中西部和南部的学校。威斯康辛会议上的一位发言者遗憾地表示,此次会议上没有来自更为遥远的地方的学者,而我觉得他其实真正感到遗憾的是觉得没有来自东部精英学校的人士与会——事实上,东西海岸的学者们均未与会:没有一位发言者来自斯坦福、伯克利或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世界文学的推动者们十分清楚他们不断壮大的新概论课程正遭受着语言和文化上不够专业的指责。当沃纳·弗里德里希提到大部分项目所教授的不过是“北约文学”时,他的意思不是比较文学这一概念理应扩大,恰恰相反,他主张要放弃“世界文学”这一称谓,因为比较学者们真正想讨论的是四分之一北约国家的文学。
弗里德里希接着澄清了他的反对的性质。在论文集里的文章——《论我们计划的操守》中,他说:
我坚决反对这类大范围的概论课程,如每周3小时为时一学期的、介绍从埃斯库罗斯到田纳西·威廉斯的“小说和世界文学中的戏剧”课程。正是因为此类课程,攻击如砖块一般从四面飞来,有的来自实力雄厚的语言学系,他们不屑地认为这是最浅薄的完全外行的课程,有的来自声誉卓著的比较学者,他们抱怨正是因为这些课程,使得自1920年代以来的比较文学遭受耻辱并名声扫地,以致至今尚未完全恢复。④
弗里德里希的问题不是翻译本身,而是概论这个概念。“在北卡罗来纳,”他总结说,“我们在希腊戏剧、法国古典主义、歌德研究中,有大约八门或者十门翻译课程,但是我们却没有一门世界文学的概论课程;我们的人接受不了这样的课程。”
于是,在此次会议后不久,美国比较文学学会委托起草了弗里德里希所呼吁的第一份“标准报告”,由哈佛的哈里·莱文(Harry Levin)主持。于是就有了东北部的精英学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康奈尔、阿默斯特等等学校,维尔纳·弗里德里希所在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就俨然成为了那种精英模式的前哨阵地——结盟起来以对抗规模大的公立大学,公立大学位于美国的中心地带,如爱荷华、威斯康星、科罗拉多,哈斯凯尔·勃洛克的世界文学会议的参与者们主要来自这些学校。当美国比较文学学会设立第一届“标准委员会”时,他们将哈斯凯尔·勃洛克拉回到阵营里并让他加入委员会,而他最终也这么做了。
哈里·莱文的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报告发表于1965年,在报告的第一段中,他宣称:
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在每一所学校中设立比较文学项目是否必要、可取或者切合实际,在语言准备和知识视野方面是否应有特殊要求,而这些理应为更有资格的学生所预备。而且,是不是应对语言学系、文学系和图书馆的现存力量有前提要求,对于这些要求,不能期望太多的学院或是每一所大学都可完全达到标准。⑤
更为严格的是第二份“标准报告”,由耶鲁的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e)在1975年主持。正是那一年,我进入耶鲁他所在的系的研究生项目。格林的报告指出了近些年来全国范围内项目的快速增长,他甚至肯定了对于世界文学的一种新奇的展望。格林说,“它是一个展望,它很快就会开始让我们舒适的欧洲视野显得狭小。”很快,也许吧,但是还不是现在。格林写道:
我们相信,严重关切我们学科的转变是有理由的,我们不应贬低它得以建立其上的那些价值标准。对于标准的下滑,一旦允许其加速进行,将很难控制。至少,在某些学院和大学,比较文学似乎是以特价的大杂烩形式提供给学生。在本科生阶段,一些大学里近期出现的让人最为烦扰的潮流就是把比较文学同翻译的文学关联起来。⑥
格林的批评击中了要害。在他的时代,没有一门有自尊的学科愿意被看做是“美国购物场”里美食区的教育等价物。
如果运用后殖民理论,我们就能很好地理解这种地域和阶级的划分,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如此地感谢佳亚特丽,感谢爱德华·萨义德以及其他人。事实上,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尚未发表的十年之前,美国高等教育的殖民动力学已经出现在了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和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合著的《学术的革命》中。他们在书中谈到了战后繁荣年代里高等教育的崛起,尤其关注了天主教学院、历史上的美国黑人学院和一般的公立学院。而且他们做了一个有趣的类比:他们说美国的研究生项目对待综合性学院和本科机构的做法,非常近似于殖民大国对待其殖民地的做法。他们从那些殖民地获得原材料——本科生,并将他们带到大都市的中心予以加工,然后又将增值了的他们送回到那些殖民地,去教授那里的本科生。因此,詹克斯和里斯曼在1968年极有见地地认为,综合性的州立大学以及学院同帝国式的研究生项目是处于一种殖民关系之中。我认为佳亚特丽在《学科之死》的开头部分对于世界文学的批评,在世界文学的当代研究兴起之前,实际上是很好地谈到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传统比较文学的局限。而今天的问题可能是,全球经典的开放本身可能还不能解决长期困扰比较文学的深层结构问题。
有一个批评就是,如果进行得很糟糕,那么世界文学在事实上就会陷入方法论上的幼稚、文化上的孤立、语文学上的绥靖和意识形态的嫌疑,如果我们接受该批评的严重性,那么我们怎样超越这种新殖民主义的境遇呢?我想就三个层面来开始这个对话:语文学层面,方法论层面,意识形态层面。
语文学层面,我认为我们事实上需要更多的语言和语言学习。其结果就是,我们更多地需要一种语言学习上的“浮动标尺”。比较学者的一种旧有模式是要求在英语之外的其他几种语言上,获得“近乎母语的流利”。这样,你就同国别文学系里其他人一样优秀(那些人在自己学科之外的知识是很狭窄的)。
如果能在母语之外对一两门外语的掌握达到近乎母语的程度当然很了不起,但是问题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其他的语言。而我的观点为,应对这一问题的方式是学习更多的语言。我认为理想的是每位学生都能掌握一门语言到近乎母语的程度,但是同时对其他几门语言有着深浅不同的掌握。
方法论层面,就我看来,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世界文学的追求不再停留在仅仅是或主要是介绍性的概论课层面,我们似乎需要更多的学术合作以及教学合作。我当前的兴趣是要面对大学二年级概论课程的诸般挑战,我觉得现在的讨论太过专注于初级阶段。
在世界文学中保持宽阔的视野所具有的新的学术重要性意味着,我们必须严肃看待在多种语言中,我们超越我们每个人所具有的有限能力这一问题。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更多的合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正着力奉行这一原则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对于合作的新的强调将会对教学以及研究产生影响,而且它也应该重新构建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影响关系。与其费力去获取一点不熟悉的文学文化的背景知识,倒不如同我们的学生进行合作。
在我自己的本科生的世界文学概论课上,我一改过去常要求每学期提交两篇论文的做法,现在我要求一篇论文和一份维基百科词条。每一周,两到三位学生为本周的阅读去合作准备一份维基百科词条。非常典型的是,其中一个学生具有某种特别语言知识或者文化背景,或是通过传统,或是因为已开始选修相关领域的课程。而精彩的是,我发现通过学生们可以接触到多种的语言。而维基组的另外一些学生可能不具有相关的语言知识,只是出于对材料的积极兴趣,他们经常表现出特别的才干,能为维基百科的这一词条找到很好的信息。
这根本不只是常春藤学校的特点,我也听说了拉斯维加斯的内华达大学有相同的报告,他们那里在使用《朗文选集》,以及在奥本的密西西比大学。在一代人以前,这些地方的学生还几乎不具备如此丰富的文化视域。于是,这让我们去探索一类不同的方法论,它也涉及一种使用新科技如维基百科的可能性,以此鼓励合作,让学生对我们的作家有了把握。没有哪种方式能像合作一般给予学生一种准入和权力的感觉。去年在我的班上有一次了不得的事件,一位学生凭记忆用波斯语朗诵了一首哈菲兹的诗。这是一位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二年级学生,完全没有任何文化传统的背景,他不过是在进行第二年的波斯语学习,而他背诵了这首诗。他的这次朗诵获得了班上极为热烈的喝彩。今天的教室,正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另一个完整的世界。
最后是意识形态层面,我认为我们的确需要大量的多元主义。在我们这个领域,总是有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我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者,我也为之自豪。有许多的比较学者比我左或者比我右,这是在更为传统的意义上针对他们所做的研究而言的。但是,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在某一点上是处在同一立场,那就是我们需要利用任何可能的机会去击退市场的影响,比如,所有最好的世界文学选集事实上都深深地关注从内部去奋力迎击市场,去真正地摆脱美国狭隘观念的局限,从而帮助学科超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那种语言和文化上的舒适区域。
以美国为基地的比较学者们面临着一种特殊的挑战,要去同被佳亚特丽批评为“多元文化”(multi-culti)的美国例外主义作斗争。这是一种未经检验的信仰,它认为,在不用经过艰辛的努力去确实了解其他文化的情况下,一个移民的国家可以为迪斯尼式的多样性进行庆祝。这当然是一个美国的问题,但是我得说,很少有国家不存在秘密的例外主义,秘密的民族主义,甚至公开的沙文主义,而它们已深深地渗透到了比较研究之中。它在不同的国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在意识形态上和体制上。但不管我们身处何地,我们的工作就是要使用世界文学将比较文学从教条式的麻木中摇醒,去批评它自我牵涉其中的民族主义,去真正地利用每一个机会反击市场的影响。所以,一部好的选集,或者一门好的课程,或者一个好的研究项目,会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流行意见,会反击民族主义自我满足的欢欣。
需要强调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教得好的世界文学会大大激发对语言的学习,对世界更真实的理解。而实际上,世界文学的课程能更好地促进莱文和格林报告中不屑提到的那些学校里的语言学习。他们认为那些学校甚至不该有比较文学项目,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严谨学者从事足够的语言研究。我们这次会议的东道主,西蒙弗雷泽大学,就我看来,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表明如果进展良好的话,世界文学是能怎样运转的。当这里的老师决定怎样在萨里(Surrey)的新的卫星大学里建立文学研究时,他们曾考虑设立一个标准的比较文学项目,但在保罗霍尔塔、他的系主任以及他们同事的启发下,他们却建立了一个世界文学的项目;在旧的模式之下,你根本不可能在萨里进行一个比较文学的项目,因为该学校不能提供足够多的语言,而且在主要由工人阶层群体构成的学校里,你也可能没有足够的兴趣去从事七八十年代那种高深的欧洲理论,而这些理论之于这门学科却已变得如此关键。鉴于他们的学生群体来自于数十个国家,既具有本土性也非常具有国际性,他们发展起了他们的世界文学项目。过了这些年,在今天,这个项目还在壮大,注册人数已三倍于他们本来期望的数目,而且有了一百多个专业学生。
他们的课程主要依赖于翻译,然而这个项目也积极地为学生提供学习语言的机会,这是超过了萨里的小型大学能够提供的机会的。两位在机场为我接机的学生抱怨萨里的大学不能提供太多的语言学习机会,但是这个项目正在帮助其中的一个学生去意大利,而已经帮助了另一个去了日本,去进行他们的研究。这个项目的成功也在于给学校当局施加压力让学校提供更多的语言学习,但另一方面,住在日本的一户寄宿家庭的学习经历也不错啊,这不正是那两位学生中的一位所已经经历的吗?或者如另一位将要做的那样,去意大利学习,那里的饮食很不错呢!这有什么不好呢?
做一个总结,我认为在两者都没做好的情况下,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对于世界文学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于比较文学的批评。我们的挑战是要将我们各异的方法凝聚到一种积极的关系之中,从而使我们在全球语境中重新构建我们的比较研究,运用它来拓展对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以及在任何一个可能的阶段来反击全球资本市场的种种难以预测的变化。
[斯皮瓦克]大卫和我认识很久了,他的劝说也使我得以持目前这个立场,我认为我想要代表的方法将是坚定不移地去“补充”(我不能让自己同意使用“合作”这个词)那些开明的世界文学“家”们。然而,我想以一种反对两极化的调子来开始,一极是比较文学在其全盛期时必应获取的高深理论,一极是内置于世界文学中的平民主义,这一点内含于大卫发言的许多部分之中。对于世界文学的补充是尤其必需的,因为认为世界文学是更加平民主义的这一观点本身是非常前卫的,一个属于我们时代的观念。在北京,在大卫的邀请之下,我做了“补充前卫”的发言。真的,我在爱荷华教了12年,离开时是比较文学的主任。这个项目在它的基础系部上,由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同罗莎莉·科利(Rosalie Colie),拉尔夫·弗里德曼(Ralph Freedman)和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n)所建立。哈斯凯尔·勃洛克(Haskell Block)是我的朋友。我还在那里教书的时候,布朗大学给了我邀请函,我拒绝了,阿默斯特的马萨诸塞大学给了我邀请函,我也拒绝了,因为实际上,爱荷华同“高视阔步”的东海岸没有大的不同。但是我没有陷入那种地域主义的偏见,即便那时候也没有。如果以为常春藤学校有些东西被“施了魔法”,即便我们俯视地对待那些“他者”的学校,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就是亲历者。我是加尔各答大学的毕业生,引用我可尊敬的具有反讽色彩的朋友萨义德的话说,“逐步前进到东北部”,在50岁还差六个月的时候登陆在哥伦比亚的门槛的台阶前。然而我几乎没能成功,因为一位同事(他将永远保持匿名)让临时委员会投票的票数持平。而且,那里的学生们进行了极力抗议。我不是以精英的方式进入的——这非常近似于我在世界文学中的处境。
当然,承认美国教室里语言和文化上的多样性是一个了不起的主意。成立维基百科小组并且赞扬多米尼加学生使用波斯语记诵哈菲兹诗歌的能力也是很好的练习。然而,作为一个身处两个世界的人,我建议进行一个测试。该学生从其他某个地方所获得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背景,在他的本土国算不算是高等教育?如果不算,那么这个学生就不能成为课堂里合适的信息来源。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拒绝承认多样性。但是如果我们要这样做,我们必须找到理由能判断这位学生给课堂带来了什么。
在全球化呼吁认识论的转变之前,我一直在倡议反对这种因为数十年来忽略这个问题而带来的双重标准,现在认识论的转变已经是我讨论的一个部分了。我想在这里从我1992年的文章中引述一段,或许还不能算是毫不相关:
一个典型的自由的多元文化课堂其“最佳情形”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某一天,我们在阅读某国别文学的一个文本。在一般政体的意义上,教室里来自于那个国家的学生群体能够认同所讨论“文化”的特质的丰富性。(我在此甚至不涉及“文化”的定义问题。)教室里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就是,盎格鲁之外的)同情但肤浅地说这与自己有关,散发着同样差异的气息。而“懂得其他文化”的盎格鲁背景的学生,则慷慨地说一切都与自己有关,闪烁着相对主义的光芒。⑦
我们必须,当然,也应该,追踪第一代移民怎样变成后来的移民从而以各种方式成为美国人,除非我们想让世界文学研究——不管它旅行多远到达各处——总将面向新的移民,这对于严肃的学科转变不是一个好的论题。
那么,我所代表的观点——目前并不是非常受欢迎——应仅仅将自己看做是对于世界文学之利益的一种补充。
我们关注的不是怎样去确定在扁平的环境下世界上文学生产的高峰,而要询问是什么使得文学的案例成为独特的。这种独特性总是可通用的,但永远不是普遍的。阅读之地就是让独特性成为可见的。
我不认为我们能够阻挡世界文学的边界的发展。但是我们对文学生产的独特性感兴趣,我们总是努力避免对其进行最后的编码。进入一种“普遍性”,“世界”就成为形容词。
我们作为一个分布于全球的、多样化的集体,可以补充那种似乎要将世界置于一个网格之内加以控制的实践意志。我指的不是概论课程,我指的是对于世界文学的种种预设。请记住,补充就是要弄清楚一个因为空虚而需要补充的地方的准确形状,是缩小,而不是放大。
最后,如果我有足够的时间,我会尝试去使另一个例子区域化:那位杰出的印度典范,他就是泰戈尔。
各处的人们都在以一种赞许的态度对我的发言进行评论,我说在全球化中,我们身处一个符号的岛屿上,踪迹的海洋中——这个也同你所在说的正相对应,大卫。一个符号系统承诺意义。我们只能在一些语言中追随那种承诺——对意义的承诺。我同意你的意见,我们应该扩大那一点。一个踪迹却不能承诺什么。踪迹就是某种事物似乎在暗示此前有过某物。在全球化中,我们身处符号的岛屿,踪迹的海洋。我可以给你许多例子,但是其中无聊的是——这个不是出现在全球化中,很早以前就有了——你要是不懂得一种语言,而只是说“啊,这书法看上去真漂亮,听着真悦耳”,那就从反面使得野蛮人之被称为野蛮人的理由合法化。
马克思将踪迹看做是不充足、不完全的,因为表现理论从未结束。因为对于他而言,一般等价物,金钱,剥去了它的物性,就成了一种数字系统一样的东西。然而,他启发性地带领我们回到如何理解踪迹。商品的拜物特点和《资本论》开始讲述商品语言的外套,是最为人所知的两个方面。因为只有那能进行改变的培训,而不需要等待前卫主义来违越集体精神,才会改变我们生活细节的性质,让精神不自在。尽管所有的那些维基百科和微博可以创造出一种亲昵感,在这种学习的地方,你会失去。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对话,我再次引用一下我的一段话,这是我最近为一个书目写的东西:
文学教学本身的底线是教会如何阅读,在最坚定的意义上阅读;同样,哲学教学本身的底线是教会如何思考,在最坚定的意义上思考。它是教会一种想象和智识的行动主义。它是教人把自己作为一件乐器来弹奏——距离遥远却又相联系——阅读,思考。只有少数一些人(这是教师不期而遇的快乐)被教会学着失去,这是你在人文学科里可以成为一位老师的唯一方式。在这里什么失去了呢?当你学着失去的时候,你想失去吗?比如苏格拉底?比如那些父母或者老师呢——他们寻求被自己的孩子或者学生击败(Putrat shishyat parajayam)?但那是有益的失去——这是我从解构那里学到的一课(我这么认为)。一个深渊里的博彩,大厅里的镜子,获得而失去到获得而失去——但剩下的是什么呢?⑧
为了在这些艰难时代里深思人文学科的人文主义,你必须完全进入人文主义自身的亲昵之中,你也不能通过两极化东海岸的语言学习和中西部的道德想象,而去逃避那个问题。
百科全书式的世界文学的欲望正落入了这种体系的传统,这是一种好的体系传统。不幸的是,在着眼于系统性的益处上,它也会去巧妙处理某些类型的历史踪迹,极具重大意义的是对于西亚地图的重新追踪,在上世纪的头些年,创造出某种类型的世界,成为拜占庭命运沉浮中的一个插曲,其最新的例子就是在马扎里沙利夫(Mazar-i-Sharif)发生的那些事件。当牧师特里·琼斯(Terry Jones)说我们不用为他们的行动负责,我们比较学者却不能将他看做一位不见经传的狂热者而置之不理,忘掉了历史要比个人的良好意愿大多了。所以不管我们说了多少,一种不分先后的语言和文学体因为移民的增加已经到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假定,说美索不达米亚是文学的发端,我们也不能取消这一点。
当我们计算2011年4月发生在马扎里沙利夫联合国大院里的伤亡情况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当W.E.B.杜波伊斯敢于指出,联合国继续了旧的强权路线时,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体面地解雇了他。你不可能懂得整个世界。你采取了一种帝国主义式的反帝国主义的立场,做出了某些类型的选择,雷蒙·威廉斯巧妙地对此做出了分析,称之为“布鲁姆斯伯利小团体”(Bloomsbury Fraction)。
千万不要把我们那些代表补充的反系统立场的人看成是“惯唱反调的人”。我们就是泰戈尔所称的“奢侈的花销者”(bajey khorcheys)。泰戈尔有过两次越界的时刻,这使得1906年的普通读者对那篇文章感到费解。英语中“比较文学”,他用英语引用在自己的文章中,是一个未经解释仅仅公然宣称的翻译,是“bishsho shahitto,世界文学”,他说,根本没有解释。“你曾经要求我,”他用孟加拉语写道,“谈一谈比较文学,但是我愿意称它为‘世界文学’。”
(看了一眼大卫)那篇文章值得看看。
泰戈尔的每一步都在远离后藤新平(1857—1929)的那种风格,反对上世纪头些年的泛亚洲主义。他的态度是世界主义的,他批判单纯的民族主义——我认为大卫的说法是正确的,世界文学可以对抗单纯的民族主义——而这又同他对可能的人道印度的爱联系在一起。他于是同民族主义传达给世界的信息展开了严肃的交锋。然而,在误译的世界文学名义之下,他使这种想象的、跨越国界的创造性的纽带理论化为“奢侈的消费”。
这个世界如果缺乏对于人文学科的强调就会很糟糕。泰戈尔传达的这条信息——跨越边界之物并不马上产生利益、可以估值,它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优惠,等等,还有,它的“增值”是在不可通约的没有任何保证的意义上的——面对通过知识管理达到体制权力的意志,这样的典范是很难学习的。
我们为什么应该去无休无止地引用歌德?他是一位权威作家,但在历史上毫无疑问地被那种帝国主义的反帝国主义所影响。
我在想象一个极具全球差异性的学者和教师集体,在补充和学着补充,一种世界文学的认识论表现,它怎样建构它的知识对象,怎样教会学生们去建构他们的知识对象。也就是说,大卫刚才非常正确地为我们提供的就是我们应该,真正地,去拆解老式的比较文学的局限以及国别文学的自负,尽管现在很难反对比较文学和国别文学,因为从预算上来说,它们的日子也根本不好过。
对于我而言,在文学教室里对知识对象的这类建构似乎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补充,而不仅仅是阅读同样的旧文本,以熟练的语言技能去读这些同样的旧文本,反而应努力地去阅读这些同样的旧文本,去拆解它们,将它们带离普遍化,而给予它们一种独特性。如果它真的是针对北美,让我们去抗击主流。这不是文化的战争。只是在数量上增加经典文本并不是提上议程的惟一任务。现在是时候了,要把比较文学的欧洲语境独特化而不是区域化,仅仅提供一个替代物,一副在其疆域和全球化教室之内的北美图景,给我们提供某种以这样的方式建构自己对象的被称作世界文学的东西。
[达姆罗什]我想我得再说几句来回应,而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毫无疑问,现实情况是佳亚特丽的作品如此各异,以致想从她的作品中仅仅引用一段,是不能准确代表她的。我想那就是她歌德式的一面,让我想起了爱克曼曾这么评论歌德:“他就像一颗钻石,从哪一面看,他都呈现出不同的一面。”那个评论当然也适用于佳亚特丽。
我同意泰戈尔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人。这周,我和我的朋友们刚刚编辑完《劳特利奇世界文学指南》,在此书的开头部分关于本书的奠基性论述中,我们有一些关于歌德和泰戈尔的文字。再次提一下,当我还在念研究生时,我从没听说过泰戈尔的文章。大纲里根本没有提到他的作品。
我非常赞赏佳亚特丽对于独特性的强调。把“比较文学”同“世界文学”相比,我认为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世界文学一旦进行得糟糕,世界就变成扁平的了。我们当然不希望那种情况。对我而言,有趣的是,要是世界文学做得出色,它就会以种种新的方式重新构建这种独特性。比如,在这次会议上,有很大比例的文章都谈到了某位特别的作家。那不是我们老师们曾经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学曾像我母亲的晚餐盘子:有点红色的,有点白色的,还有点绿色的,有点像每天晚上把吃意大利国旗当做晚餐。所以,你需要有法国的,德国的,还有英国的,可能的话,还得有意大利或者俄国的。即便在这些受欢迎的文学中,文本范围也不够大。当年我在耶鲁写毕业论文的时候,系里所有正写着的毕业论文中的一半,都涉及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或者巴尔扎克(Balzac),或是两者。
但有趣的是,那个时代的比较文学对于独特性有个特别的问题,就是你不得不将两种或者三种东西放到一起,你才可以成为比较学者。几年以前,我写了一本关于《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书,这本书就是关于世界文学作品的一个文本,讨论了一系列的指意如何从巴比伦扩散上行至亚述,又从亚述到维多利亚时代得到复兴。我的书里有两个主要的人物:第一位重要人物是伊拉克的考古学家,霍姆兹德·拉萨姆(Hormuzd Rassam),通过至为关键的挖掘出来的泥板,他发现了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藏书,另外一个是史诗的解码者,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一位来自英国工人阶层的有趣人物,他从没上过中学,更没上过大学。通过研究《吉尔伽美什史诗》在世界上的流传,我得以仔细讨论种族、阶级、帝国主义的政治和这部稀世之作的特异性以及它非凡的历史等问题。
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研究来努力干预我们的文化,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学术之外。写作这本关于《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书来自于我的一种忧虑,因为在“9.11”事件之后,有很多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谓的那种“文明冲突”的非常不严谨的信口之论。于是我就问自己我可以继续做些什么来表明:如果人们真的上溯,那么只会有一种共同的文明潜藏在西方文化和中东文化的背后。“好吧,”我做了一个决定,“普通的大众需要一本关于《吉尔伽美什史诗》的书。”这不是过去那种类型的比较文学,我是将它作为一个历险故事,依据拉萨姆和史密斯的传记,来讲述这部史诗是怎样发展和扩散的。我所发现的是那个文本具有多重独特性,而不只是独一个事物。这部史诗在亚述巴尼拔的宫廷是一种东西,在巴比伦是另一样东西,当它被挖掘出来后,它又变成了某个不同的东西,今天当它流传回到中东,它又一次成为别样的东西。我不知道我能在干预防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言论方面取得多大的成功,但是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本在《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上被评论的关于新亚述帝国的书。我希望有读者能在这个历险故事中读到文化一政治的教训;我不能肯定,但是得有人去做。
再补充一点关于语言的问题。我上研究生时确实学了点西班牙语,这是因为在第一年新生的艺术史概论课上,出于那种你可能会看做是最糟糕的、肤浅的“让我们学点多元文化的东西吧”的态度。作为一种典型的20世纪70年代初的做法,这门课程只关注西方艺术,从古希腊到达芬奇,再一直到抽象的表现主义。我所在的那个研讨班的负责人,亚瑟·米勒,碰巧是一位中美洲学家,刚刚被聘为副教授。他不满于这门课程的欧洲中心主义,于是上了一周的中美洲艺术,我觉得那是极为有趣的内容。我因此决定针对放在墨西哥城国立人类学博物馆里神秘的夸特里姑(Coatlicue)女神塑像撰写我十页的课程论文。我发现了一本米盖尔·利昂·坡提拉(Miguel León-Portilla)写的《阿芝特克人的思想和文化》的书,里面引用了许多诗歌来论述阿芝特克人的思想。我觉得这是最令人惊异的诗歌,即使这是使用英语转译了利昂·坡提拉的西班牙语译文,而他的译文是从纳瓦特尔语原文翻译而来的。这是我此前还未曾见到过的一个新世界。我被深深触动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我愿意去学习这门语言。”
四年后,我仍在读研究生,我发现人类学系在上一门纳瓦特尔语的课程。我就去问我的研究生导师巴特·加马提(Bart Giamatti)先生,我能否把它选为我的学分课,他威胁要把我从窗户扔出去,当时可是在伯明翰公寓的七楼!这让我有一小会儿晕头转向。还是多亏他,他最终允许我选修这门课作为学分课。我报名时,注册的人数翻了一倍(由一人成为两人)。正是因为学习这门语言,使我认识到我必须学习西班牙语,因为许多出版的书和学术研究都是西班牙文,没有西班牙语,我不可能研究纳瓦特尔语。于是我学习了西班牙文,其结果是,现在在我的世界文学课上,我可以使用塞万提斯的西班牙文作品。这样,通过纳瓦特尔语,我们回到了曾经是我们私立学校关注范围之外的下层阶级的语言。多亏了在概论课上短暂接触到的诗歌翻译!
类似的经历可能会在任何时间发生。你猜不到什么样的事情会激发一个人潜在的终身兴趣。对于我们老师和学者,在一种意识到全球化和政治化的背景下,我认为去敦促那种独特性是一种道德的必需。
[斯皮瓦克]爱德华·萨义德在他的修订版《东方主义》中不动声色地写道,民族解放运动表明了属下人(subaltern)在说话,意味着上层资产阶级领导人如尼赫鲁(Nehru)和甘地(Gandhi)事实上都是属下人。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看到这个的,因为我亲爱的朋友和战友(指萨义德)在其出版后送给了我一本,我当然有第一版的《东方主义》。由于我在一片狼藉的办公室里找不到这本书,我就又买了一本。然后我就在他增写的“后记”中看到了这个说法。他从没告诉我这个,因为他知道我不会同意,而且他无疑也没在书中为我备一个脚注——属下人仅指非欧洲人和被殖民者,这不是一个好的提法,这一点你可以在迈克·哈特尔(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的用词“属下国家”中看到,因为按照葛兰西的经典定义,属下阶级还是一群实际上并没有建构进(民族)国家的人,葛兰西的定义在构建一个完全不是扁平的立体地形图方面,仍是有益的。
大卫,一位年轻的北美学生从没听说过泰戈尔这件事情——我不是在针对你个人而言——同这位诺贝尔桂冠诗人广为人知并无关系。让我同你来谈谈这点还没读过的片段,因为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把这些放到一起的民族人物区域化——你刚才说到谁,泰戈尔和谁?
[达姆罗什]歌德。
[斯皮瓦克]歌德,对了,就是他。就是说泰戈尔是歌德式的人物,然后有这么一些越界的时刻,曾让印度的广大读者不能理解。我的意思是泰戈尔自己引述过这一点,所以他不得不解释。因而,请让我们不要因为他恰好以另一种语言写作,就把他看做一位属下人。如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最近所写的那样,泰戈尔在西方被看做是某种穿着奇装异服的纪伯伦。
在2月份提交到巴罗达(Baroda)会议上的论文里,E.B.拉马克里希南(E.B.Ramakrishnan)建议说,我们应该将多语种的印度文学地域化,我们不应老是尝试找到一个例子并把它翻译成英语,然后把它同另外的东西并排放到一起。他要求我们宁可通过语境和语言去“地域化”——他使用的词语——多语种的印度文学,以悖论式地恢复它们的印度性。印度性同“欧洲”一词一样,是一种理论上的地缘政治的虚设,它或许要求比较文学、所有的世界文学去把叫做“印度”的东西作为一个历史的符号系统,可以进行后理论的追踪,而不是在这里仅仅通过全球化的英语对其进行一个轮廓式的描画。
我应该在这里做出说明,单数性(singularity)并不一定意指单个的文本。它仅仅意味着,在任何文本中独特的东西就是可普遍化的东西。我们必须要追求这种东西。
大卫和我可能——引用他的话说——要再次说个明白。这个任务对我们两人来说都很重要。下一次,我们可能会说些不同的事情。在土耳其——我们当时对彼此都很尊重和礼貌。今天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会互相补充。我同意他的意见,他同意我的意见,在他谈话的开头部分有点批评,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彼此喜欢对方。这不是对话的终结。请你们下次再来,看我们是如何走向对方的。谢谢!
注释:
①译者注:原文题为"Comparative Literature/World Literature:A Discussion with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nd David Damrosch",载于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Vol.48,No.4,2011,第455-485页。因篇幅所限,译文为节译。
②Sukehiro Hirakawa,"Japanese Culture:Accommodation to Modern Times," 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28(1979):47.
③Gayatri C.Spivak,Death of a Disciplin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xii.
④Friedrich,"On the Integrity of Our Planning," p.17.
⑤Harry Levin et al.,"Report 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http://www.umass.edu/complit/aclanet/Levin.html(accessed 7 Oct.2011)
⑥Thomas Greene et al.,"Report 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http://www.umass.edu/complit/aclanet/Greene.html(accessed 7 Oct.2011)
⑦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Teaching for the Times," Journal of the Midwestern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25.1(1992):183.
⑧"Playing to Lose," in "Loss," written for the Seagull Press's annual catalog(Kolkata,India).
